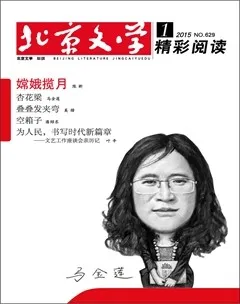恪守小说的道德
萧潇的小说最先抓住我,就是两个字:那边。源自小说开头第一句话:等下你去给“那边”打个电话,说下你爸的事情……稍有阅历就能体会,“那边”这两个字透露了复杂的生活信息——再婚家庭、出事了。问题是作者是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会怎样把握如此复杂的素材。看下去之后我更吃惊,故事不但涉及再婚家庭,还是大陆台湾之间的纠葛,牵涉到战争、婚姻情感、财产分割、亲情伦理、生死……要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把这些重量级元素摆布到合理的位置,不是一件容易事,没有相当的语言功底很难做到。很庆幸,萧潇做得很好。每个人物、每个细节都恰如其分,展现了她出众的叙述能力。
因为最近在读卡佛,我愿意引用一下卡佛对小说语言的观点。他说: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萧潇不同于普通作者的地方,在于她一出手就不安于匆忙地叙述故事,而是遵循情感的流动,用准确的语言捕捉细微的生活感受,并能赋予这些东西“惊人的力量”。“那边对我和妈而言,是扎在心里的一根刺……”这种灵动的意象,几乎弥漫全篇,“黝黑的皮肤下竟隐约露出一丝红晕,眼角深邃的鱼尾纹骄傲地上扬着,依稀间我似乎看到他眼底的水汽……”可以说,萧潇是语言的小兽,她的文字踏过留痕,或鸟鸣鱼跃,或龙腾虎跳;有时烟尘滚滚,偶或风轻云淡。她紧紧帖服着小说人物的心灵走向,让语言尽可能贴近那些倏忽即变、微妙深幽的精神世界。看山写山,写山即山,这一点,不少写作者做不到。格非说,优美的语言已经没有意义了,需要有力量的语言。萧潇的小说有两大长项,一是语言的魅力,她在确保语言准确性的同时,坚持诗意叙述,通篇有一种流动的波光之美。二是故事的格局。小短篇大容量,小姑娘敢写,能驾驭,一个成熟作家都难以把握的题材,在她笔下有信手拈来之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能在沧桑、幽暗的生活层面,制造人性的暖意,这在很多写作者满足于愤世嫉俗、挖掘阴暗丑陋、陶醉剑走偏锋之际,她能用理性的微光,烛照生活的复杂,这与其说是天赋,不如说是道德。
我和作者聊过几次,面对她,我是矛盾的。这么有才气的一个小姑娘,除了文学她应该还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她只要文学。文学,显然不是她心血来潮的非理性选择。让我纠结的是,到底哪一种写作走向适合她,我有时觉得她的叙述能力太适合类型写作了,她有很强的逻辑能力;可我又觉得她能像奥康纳一样,在所谓纯文学领域有一席之地,命运给她那么丰富敏锐的感受能力,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奥康纳。每次她走后,我都会沉吟一会儿,为自己和她说的一些话,反思。我这样对她说,真的对吗?和现世的安乐比,东野圭吾也好,奥康纳也好,又怎么样呢?所以,我有时会想,萧潇,小姑娘啊,我相信你会是一位成功的作家,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你站上某一个领奖台时,能想起我曾经发过你的处女作。然而,我更希望你健康幸福,希望你此生安好。这是我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