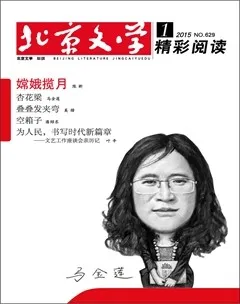父亲的遗产
一
“等下你去给‘那边’打个电话,说下你爸的事情……”
爸去世那天,妈坐在空荡荡的病床边,平静地对我说。
沉默了片刻,我点点头,起身走出病房。
“那边”,对我和妈而言,是扎在心中的一根刺,既忽视不了也拔不掉,只能任由它横在那里,时不时地隐隐作痛着。
在爸去世前,我对“那边”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只知道在海峡的另一边,爸还有个家,仅此而已。
电话打通了,是个中年男人接的,我极尽可能简略的语言告诉他:“我爸去世了,你如果方便的话,来参加葬礼吧。”
对方似乎愣住了,电话那头久久都没有声响。
就在我的耐心即将消耗殆尽时,终于传来了一声哽咽:“我尽快安排一下,马上动身!”
我应了声,而后默默挂了电话。
二
三天后,中正国际机场大厅外,我终于见到“那个人”——那个与我同父异母的亲人,那个跟我分享父亲却彼此陌生的男人,那个应被我称作“哥哥”的人。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藏蓝色西装,衬衫领口处的纽扣紧紧地勒住他的脖子,仿佛随时会引起窒息一般。我不自觉地感到一阵气闷,只好将视线移开,却不经意地瞥见他脚上那双过时的尖头系带皮鞋,我嫌恶地别过脸,尽可能不望向他。
“是小旋吧?”
他脸上带着近似讨好的笑容,微颤的语调里透着明显的紧张。
“嗯!”
我点点头,指指车子的方向,便自顾自地转过身朝车边走去。
一路上,我们两人都沉默相对。谢天谢地,他没有坐在我身边,而是坐在了后排的座位上,否则会更加尴尬的。
“那个,我们现在是要去礼堂吗?”
“不是。去酒店帮你办理入住手续,还有,替你接风!”
我边说边从后视镜里观察他的举动,他似乎有些意外,先是一怔,而后勉强地笑笑。
我猜,他以为我们会安排他住在家里。
“呃,你知道的,家里就我跟我妈两个女人,不是很方便……”我不认为这样的安排有何不妥,但仍良心不安地解释着。
“嗯,我明白!”他用力点点头,而后便将视线转向车窗外。
短暂的对话过后,狭小的车内再度陷入尴尬的安静中。
入住手续办好后,我带他来到酒店中餐厅的包厢里,妈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他走进来的时候,妈微笑着起身朝他点点头。
“这位是我妈!”
“阿姨好!”他此刻的表情与才见我时如出一辙,刻意拔高的音调里透着一丝紧张。
“是怀生啊,常听你爸提起你呢!”妈客气地说着。
他闻言旋即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看起来既兴奋又诧异。黝黑的皮肤下竟隐约露出一丝红晕,眼角深邃的鱼尾纹骄傲地上扬着,依稀间我似乎看到他眼底的水汽……
“真的?”
真的才怪,世上有哪个男人会笨得在老婆面前,经常提起他与别人生的孩子?
像我这般二十出头的女人都不相信的客套话,却让这个年过四十的结实汉子感动不已,他究竟是太过老实,还是太傻?
席间的气氛虽然还有些尴尬,但比起刚见面时,大家似乎都自在了些。
桌上的菜肴被吃了大半,妈突然放下筷子,端起水杯润润嗓后,对他说:“怀生,阿姨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阿姨,您说!”
他也急忙放下了筷子,一脸聆听教诲的样子。
“是这样的,你们的父亲刚刚去世,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要过了头七之后才能下葬。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但是在台湾这里,如果家族有墓地的情况下,是可以不必火葬的,我们家在台南乡下正好有块家族墓地。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将你父亲葬在那边……”
在今天见面之前,我与妈为此烦恼了很久,妈想将“父亲”留在台湾,我也不愿他死后的尸身,还要经过千百度的炙烤熔炼……
可这毕竟不是我们单方面,一厢情愿便能作主的事情。
他,毕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先生,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父亲。虽然再怎么不愿承认,但,这就是现实。
“好啊,那就按照阿姨的意思办吧!”他平静地说。
我与妈妈相视一眼,从彼此的眼中都窥见一丝诧异。
这个困扰了我们良久的烦恼,竟被如此轻易地化解了,他居然愿意将父亲长埋于台湾,而不是与他家乡的母亲合葬在一起吗?
“父亲与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突然离开了,您心里一定非常不舍。就让他像以往那样,一直陪在您的身边吧。”
“可是你那边……”
事情虽然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着,但妈妈突然犹豫了,或者说不忍了。
“不瞒您说,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我妈怀着我的时候,父亲就被抓走了。我是到了37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父亲,虽然有很多话想对他说,但似乎也过了那种围在父亲身边撒娇的年纪,即使每年能见到他一两次面,我们之间的对话也总是很少。比起我来,你们才是一直陪在父亲身边的亲人,我怎么能硬生生地把你们一家人拆散呢?”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可是我看在眼里,却感觉心疼极了。
他说他不愿拆散我们一家人,可又是谁拆散了他们呢?他们原本也是一家人啊……
父亲每年都要回大陆一两次,每次都会住上十几天,对此我与妈虽然没有竭力制止过,但脸色终究也是不好看的。
今日听他说起与父亲之间的相处,我竟有种后悔不已的感觉,如果当时我们的态度能积极些,让他与父亲能多些时日相聚,会不会能续接上他们原本已渐行渐远的父子之情?
我不知道,况且我也再没有机会知道了……
三
葬礼那天,他依旧穿着那身藏蓝色的西装,坐在家属区的一隅。
我们起身向来宾致意时,他也会跟着我们躬身施礼,而后便默默地坐下,既不自我介绍,也不与大家寒暄。
我知道,这是他对于父亲最后一点尊严的维护,还有对我和母亲的体贴。
一个被忘却了三十几年的人,应该得到本属于他的名分,何况他还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又是长子身份,却只能暧昧地以家人的身份混于我们之间,不能以长子的名义接待来客。
这不是我与母亲的决定,但不得不说他的这番安排,让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在父亲最后的告别式上,为他验明正身似乎并不是个好的时机。可斯人已逝,如今已到了盖棺论定之时,此时不讲,那么他的身份何日才能被真正揭晓呢?
他的退让,让我心疼!
父亲在与母亲认识之后,才信了基督。在我看来,他信仰什么并不重要,只是让他的精神有所寄托罢了。
他所有难以启齿的忏悔,以及他来不及弥补的错误,都需要一个宣泄的管道,我与母亲自问不是个好的倾听者,我们甚至不愿提及那段令他纠结不已的往事,所以他只能向主去一一道明吧。
整个仪式都是在牧师的主持下进行的,有条不紊,气氛虽然沉重,却好在不算冗长。我不时地侧头打量着他,一整天他都紧锁眉头,望着屏幕上父亲的影像发呆。
为了让来宾更好地记住父亲,我们在荧幕上播放了一些父亲的照片影像,剪辑成一个短片播放。
父亲留下的单人照片不多,大多都是与我或妈妈一起的合影,至于影像也大抵如此。我一面看着短片,一面回忆着我们一家人幸福的时光,不禁鼻头发酸,我不愿当着众人面前落泪,只好偏过头去拭泪,却看到他直勾勾地望着短片,眼眶已蓄满了泪水……
“对不起!”我淡淡道,伸手覆上他粗糙的大掌,轻轻摩挲着。
他没有吭声,只是笑着转过头来望着我,先是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最后将视线移回到了屏幕上。
我与他的手,始终握在一起,直到葬礼结束时才分开。
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受到了所谓血缘的魔力,我们分明才认识三天,见过两面,可我却能从他的眼神中分辨出他的心思,清晰地了解他的想法。
我自问不是个察颜观色的好手,能如此轻易地了解一个人,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有一半是完全相同的。
葬礼结束后,母亲陪着一干亲属吃饭,我们极力劝说他一同留下,他却客气地拒绝了。
父亲是只身一人来到台湾的,他在这里除了我与妈外,不再有半个亲人,所以今日一同吃饭的也都是妈妈这边的亲戚。我明白他除了害怕自己的身份尴尬以外,更多的是考虑到我和妈妈的面子。
“妈,你先陪大家吃饭,我去送送他!”
我抄起皮包追上他的脚步,不顾他的婉拒,执意将他拉进车里,这次他坐在了我身边的位子上。
也许是今天葬礼上的牵手,让我们感觉不再那么尴尬生疏。虽然车内的气氛还是有些沉默,但我已经自在很多了。
“今天累了一天,等下回到酒店,你吃点东西就休息吧。明天上午我来接你,带你在台北好好转转!”
“不用了!这几天你也辛苦了,我自己在这边转转就好了。况且,我已经订好回程的机票了!”他摆摆手。
“什么时候的?”
“后天晚上的!”
“难得来这里一次,当然要好好玩玩,为什么要着急回去?”
“我跟单位就请了一周的假,自然不好久待的。”他冲我笑笑,而后又转过头去望向车窗外。
“好吧,那你明天好好准备准备,后天中午我跟妈帮你践行……”
“小旋,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他突然转过脸来望向我,黝黑的脸颊涨得通红,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一般。
“好,你说吧!”
“后天的时候,我能不能去你家里坐坐?”
“好!后天中午我去接你!”
本来我应该与妈妈商量后才能答应,可是我实在无法拒绝他,尤其是在他为了我们一再地隐忍退让之后。
“嗯!”他笑着点点头,看起来像个青涩少年一般。
四
“抱歉,阿姨,打扰了!”
才刚一进门,他就满怀歉意地对着妈妈说道。
“看你这孩子,都在说些什么话啊,快进来吧!”
一进门,他便忍不住环顾起来,我主动担任向导,带着他走进父亲的书房。
“这里是爸的书房,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忙些什么。”我笑着解释道。
这里说是书房,事实上倒更像个杂物间,里面的书籍不多,却摆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些年代久远的东西,散发着陈腐的霉味,每当我跟妈妈想要动手清理时,便会惹来父亲的暴怒。久而久之,我们也不再靠近这里,就任由它杂乱下去。
他摸摸这里,看看那里,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无比。我不懂这些穿旧的衣裳,破破烂烂的摆设,究竟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或者这也是那奇妙的血缘在作祟吧?
“我可以坐坐吗?”他指着父亲的摇椅问我。
“可以,不过要小心一点!嗯,你知道的,这椅子已经不大结实了……”
他点点头,轻手轻脚地坐了上去,许久不曾载重的摇椅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仿佛随时会崩塌一般。
他想要晃动下身子,似乎又担心那样会造成摇椅的解体,几番思量之下,他只得恋恋不舍地起身了。
“如果你想坐的话,我去找个工具把椅子加固下,应该就没问题了!”我看着他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有些心软。
“不必了。”他摆摆手,又望望那摇椅,感慨道,“再结实的东西,也终有损坏的一日,就像人一样,再强健的身体,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的轮回……”
他的眼神迅速转开,最后落在了墙上父亲的独照上,照片中的父亲一身戎装,年纪大约与他现在这般,双目有神,意气风发。
“我们出去吧!”
说着,他又望向那张已经破旧不堪的摇椅,定睛看了一会儿,而后才走出书房。
午饭是在家里吃的,妈妈亲自下厨为他准备了丰盛的菜肴,他似乎吃得十分尽兴,还提议与我们共饮一杯。
妈妈一向不爱饮酒,那日也破天荒地拿出父亲珍藏的高粱酒,与我们一同畅饮。
“来,让我们为怀生饯行!”
几杯酒下肚,他的话也多了起来。
“小旋,你不知道,我从小就想要个妹妹,就跟年画里的娃娃那样好看的妹妹。我总缠着我妈让她给我生个妹妹,我妈说等胜利了,爸回来了,就给我生个妹妹。我一直等着盼着爸回来。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了,我妈却已经不在了。当时虽然我已经三十好几了,但还是挺伤心的,我一直盼着的妹妹没有了。可当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虽然我妈没给我生个妹妹,可我还是有妹妹了,长得就跟年画上的娃娃那么好看的妹妹……”
说着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个红绸布包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居然是个银质的锁链,做工不算精细,样式也格外土气。
“那天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就寻思着要给你带点什么见面礼,毕竟我也是做哥哥的人呐。想来想去,我就买了这条银锁链。我知道你看不上这东西,可毕竟是我的一点心意,就算不戴,你也收下,就当是留个念想吧!”
“好!”我点点头,小心地把银锁链装回红绸包里。
“阿姨,我、我爸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我?”他说这话的时候,眼光明显飘移不定,两颊也微微涨红。
我与妈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妈妈点点头,转身走进了睡房。不一会儿工夫,便拿出个信封来交给他。
他颤抖着将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现金支票,我想这个数目对他而言,应该不算小了。
“这、这是?”
“我们将你父亲留下的财物按比例分配了下,这是你应得的那份!”妈说。
“是吗?可是阿姨,我想要的不是这个……”
他还想说什么,被我跟妈妈制止住了。
“你不必觉得不好意思,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那份,不必推辞,你就收下吧!”
他好像还想再说些什么,但也只是张大嘴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阿姨,我爸他有没有什么纪念品,我想带走一样留念!”
妈略微想了想后,走向爸的书房,出来时手里拿着个小小的红木盒子。我从未见过这等东西,也伸长了脖子望着那个盒子。
“我想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留给你!”
他接过盒子,小心地打开,不大的木盒子里只放着一条金属手链,或许是年代甚远的关系,那链子已经乌黑斑驳,失去了金属原本的光亮色泽,看起来十分残破。
“这?这是父亲的军籍牌?”他惊讶道。
我从那斑驳模糊处依稀分辨出父亲的姓名、血型、隶属部队……
“嗯!据说这军籍牌就像是士兵的分身一般,家属本是见不到这个牌子的,如果见到了就代表这个人已经阵亡了……”
“谢谢阿姨!”
他把那牌子放进衬衣口袋里,贴在他的胸前,就好像是稀世珍宝一般。
“我知道你会好好保存的,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你的父亲一直陪在你身边一样……”
五
中正国际机场大厅内,各色行人匆匆穿梭,我与妈妈跟怀生站在角落,进行最后的告别。
“你这孩子,让你多留些天,就是不肯!”
“阿姨,这次真的来不及,下次我再来时,一定多待些日子,到时让小旋带我到处转转去!”
“到时我可不一定有时间呢!”
几天的相处,我们已经可以很自然地开玩笑了。
他憨笑着望向我,目光却久久地定在我的胸前。
“你?”
“这条银锁链虽然土气了点,却是我哥哥送给我的见面礼,说什么我也应该戴上它啊!”我边说边抚上了锁链,虽然跟我时尚的衣着品位不符,但我还是将它挂在胸前的位置上了。
“真好看,跟年画里的娃娃一样好看!”他笑得由衷。
候机大厅里传来温柔的女声,提示着旅客们就要登机了。他看看手上的腕表,有些不舍地向我们摆摆手。
“好了,看来我真要走了……”
我与妈妈分别上前与他拥抱,他抱着我的时候,我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下次,带我去拜会下你的妈妈吧,大哥……”
短暂的拥抱后,我看到他的眼眶布满水雾,他笑着轻轻点头,似乎担心一个用力,会令眼中的泪水滑下。分别之际,他掏出个信封塞入我的手中。
“有些话我终究当面说不出口,还是写出来比较好!”
说完,他朝我跟妈妈点点头后,便转身迈着大步走入闸口,直到再也望不见他的踪影后,我们才离开。
晚饭过后,我突然想到他临行前交给我的那封信,抽出信纸展开,一张支票忽悠悠地落在地上。
我与母亲相视一望,不由得连连摇头。
信纸上并没有什么长篇大论,只是一行简短的字迹而已。
“虽然遗憾与父亲生活的时间太短,但我仍旧感谢上天让他有你们相伴,一道海峡阻隔了三十年的父子情缘,却终究剪不断那条血脉亲缘……”
父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就是这条绵延不断的血脉亲缘!
作者简介
萧潇,女,1985年生,北京人。法学本科毕业,曾在司法机关担任近三年书记员工作,后辞职在家专职写作。本篇系小说处女作。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