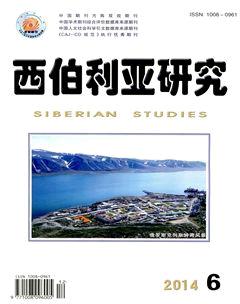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小说《切文古尔镇》中的梦境分析
冯小庆 徐佩
摘要:《切文古尔镇》是苏联回归作家普拉东诺夫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重要作品。作品中梦境描写丰富,揭示出反鸟托邦世界中主人公复杂的思想与情感。
关键词:切文古尔镇;鸟托邦;普拉东诺夫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4)06-0066-04
《切文古尔镇》是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反乌托邦小说。作品通过描写几位无产者在荒原上建设梦想中的完美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表达了普拉东诺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政策偏差造成的种种违反自然和历史规律现象的深度思考。作品中的梦境描写十分丰富,“梦就是作品的主题”,并且“每一个梦中的情景都蕴含着特别的意义”。作家通过梦幻把握人和世界存在的本质,借助梦境营造出的种种异常场景,从不同侧面表现和渲染处于反乌托邦世界中主人公的思想与情感。
一、德瓦诺夫的梦与反乌托邦意识
德瓦诺夫是《切文古尔镇》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漫游在俄罗斯大地上,以寻找共产主义完美社会为终极目标。俄罗斯人性格中暗藏着一种对未来宗教般信仰的情绪,因此在追寻之旅中,德瓦诺夫也对共产主义产生了过于执着的态度、不可避免的精神依赖和偶像般的崇拜,且赋予其以统治一切的尊严和权力。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使德瓦诺夫对世俗物质生活的好坏丧失了明确的感知,也使他压抑了精神上的对爱的渴求。和母亲与父亲有关的梦就将此真实地表现了出来。
有母亲出现的梦都是追忆式的,因为母亲早已逝去。普拉东诺夫将梦中时间设置在德瓦诺夫的幼儿时期,不断地强调他害怕母亲离开。“母亲正要去赶集,他迈开还未习惯走路的不稳当的双脚去追赶她,他相信母亲一走就永远离开了,因而痛哭起来。”而在捷尔马诺夫林区,德瓦诺夫又一次梦见自己“是个小娃娃,带着孩提的欢乐,一如他看见别的孩子吃奶那样的吮吸着母奶,但是他害怕抬眼看母亲的面孔,而且也无法抬起”。
文学作品中的潜意识可以通过人物的其他语言行为间接表现,但是它有时很难外化为某些具体的行动,但又是人物内心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需要被表现和被展开。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哈利泽夫认为:“可用于直接刻画人的内心世界的语言艺术手段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有人物的日记,乃至对梦境、幻觉的描写,那些梦境与幻觉揭示出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潜藏在内心深处不为他自己所知的东西。”弗洛伊德也指出:“梦的揭示是通向理解心灵的潜意识活动的皇家大道”,越是深层次的感情,就越适合作家选择梦境作为掩护继而进行更为合理的表现。“普拉东诺夫非常熟悉弗洛伊德”,因此他借虚幻的梦境来表现深藏在追逐崇高理想的德瓦诺夫潜意识中的对母亲的复杂感情。现实中德瓦诺夫的心灵和感情已经奉献给了共产主义理想。他认为安宁平和的生活与充沛丰富的感情阻碍他寻找共产主义。为了在广阔的天地中寻找光明和完成共同的事业,他选择禁欲式地冰封自己的感情。他以为舍弃物质和精神的某些羁绊,就可以轻松地缩短自己和未来理想之间的距离。但潜意识中的德瓦诺夫对爱的渴求十分强烈,梦中母亲的形象是清晰和温柔的,他偎依着母亲,吃着奶,享受着孩童的欢乐,这都证明母爱让他感到温暖和幸福。同时,德瓦诺夫担心母亲一去不返,这说明他渴望母爱,害怕失去。德瓦诺夫是孤独寂寞和无助的,只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感情,不希望受感情羁绊,因此他的理性就将正常的感情包括对母爱的向往打压下去,使其不得不暂时从有意识的思维中退出。然而,对感情的渴求并没就此消失,尽管主人公自己对此并没有清晰的感知,但这种渴求还是进入潜意识,依然或明或暗和或轻或重地对其精神产生影响。
作品中,德瓦诺夫的心理状态在他的追寻之旅中无法全面表现,因为轰轰烈烈的乌托邦运动无形之中已经剥夺了人的感情和愿望,它所拥有的强大力量足以让人心甘情愿地奉献,但正常人所拥有的情感需求又总是蠢蠢欲动,作家只能借助梦境将德瓦诺夫追寻之路中表现出来的激情与内心得不到满足的情感结合起来,给读者呈现出其整个精神世界,尤其深刻地揭示出他不能向外表露的愿望,因为这一部分才是最真实和最可靠的情感,也是全面了解反乌托邦世界中人物真实性的关键。
德瓦诺夫与父亲相见的梦同样是追忆式的。在去切文古尔镇之前,德瓦诺夫在家里又一次梦见了父亲。梦境是片段式的,几个片段进行切换,因此梦中的时间跳跃错乱,情节不连贯、无逻辑。
第一个片段的时间是德瓦诺夫的童年时期,空间是穆捷沃湖附近的父亲的坟前。一个秋雨纷纷的傍晚,德瓦诺夫站在亲生父亲的坟前,手里拿着一个空袋子和一根小棍子。他要出远门,因此来同父亲告别。
第二个片段的时间普拉东诺夫并没有说明,根据作品内容,推测是德瓦诺夫成年后。空间是穆捷沃湖的湖面。父亲坐在独木舟上,他用手划着小船,扒开水草,将等待他的孩子搂入怀中。
第三个片段的时间没有变化,空间是穆捷沃湖附近。德瓦诺夫和父亲坐在水草里,他们之间展开了一段是否该去切文古尔镇的谈话。
“我怎么能去切文古尔?”孩子问,“那里我会寂寞的。”
“别烦恼”,父亲说,“我躺在这里也很冷清。你去切文古尔干一番事业吧:干什么你要像死人那样躺着呢……”
第四个片段的时间已经是太阳升起时。德瓦诺夫在父亲的怀里睡着,阳光照得他的眼睛发痒,于是他睁开眼睛,梦也随之结束,德瓦诺夫回到现实之中。现实中正是清晨,阳光同样照射着德瓦诺夫的脸。第四个片段模糊了梦中时间和作品内的现实时间,看起来梦境情节和现实情节连在一起,现实好像是梦境的一种延续。
在有父亲的梦中,德瓦诺夫不愿离开,即使父亲长眠地下,他也要找来一根木棍,把它埋在坟堆里,代替自己守护在父亲身旁,永远地感受父亲温暖的怀抱。他想让父亲知道,自己独自离开十分寂寞,“无论何时何地萨沙(德瓦诺夫)都会再回到这里——找棍子,找父亲”。处于非睡梦状态中的德瓦诺夫从不轻言对父亲的思念,但是却在睡梦中将一根埋在父亲坟堆里的木棍当成大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来寻找。现实中的德瓦诺夫放弃了与索尼娅组织家庭的机会,舍弃了养父诚挚的爱,却在睡梦中将父亲的坟堆当成家一样的地方来依靠。在现实中清醒的他排除万难,为切文古尔镇营造同志式的情谊氛围,但梦境却道出他的真实感受:去切文古尔镇他会更寂寞。德瓦诺夫鄙视爱,但是潜意识中的他却在寻找不可能再获得的爱。因此,忽略梦境中的德瓦诺夫,恐怕只能看到一个为理想奋力拼搏的勇士,却永远无法了解那个无助、被崇高理想伤害的孤独人。
二、科片金的梦与乌托邦理想
梦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超越性,因此虚构的梦境可以突破现实障碍增加作家表达思想的可能性。梦中死者可以“死而复生”,也可与生者在梦中交谈和相处,这就混淆了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关系,营造出超现实的气氛。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梦就常常讲述与逝者有关的事情并表达与逝者重新相见的愿望。德瓦诺夫穿越现世在梦境中与故去的家人相聚。科片金在切尔诺夫卡村做相似的梦,梦中科片金与死去的母亲和罗莎·卢森堡相见。科片金是《切文古尔镇》中与德瓦诺夫并肩作战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怀揣着对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爱恋奔跑在俄罗斯大地上,同一切阻碍和破坏革命前进脚步的落后势力斗争,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革命彻底成功,共产主义就会自然地产生。从本质上讲,科片金对立刻进入共产主义完美社会形态宣传的认知与为之采取的相应行动,是一种出自于对遥远未来世界绝对信仰和渴求精神重生的宗教情怀,因而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什么,他并不清楚,也不探究,只是把全部的肉体和精神都奉献给梦寐以求的乌托邦。
此处要分析的科片金的梦与德瓦诺夫的梦相比更加具有跳跃性,且虚幻性更强。梦呈现出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效果,尽管是动态的,但是却有内在的接续性。
梦的第一个场景中只有成年后的科片金和母亲。母亲在长大的儿子面前显得矮小和憔悴。她埋怨儿子因为有了新恋人罗莎而背弃自己。
“你又给自己找了个放荡女人,斯捷普叶卡(斯捷潘·科片金的小名)。又扔下你母亲孤单单一个人去受人欺侮!随你的便吧。”
“妈妈,她跟你一样,也死了”,科片金说,他因对母亲的怨恨感到无可奈何而难受。
“哎呀呀,好儿子,你就听听人家都说什么吧!”母亲开始胡言乱语了,“她会跟你说话,她会扭头转身,全都像样,可是等你一结婚——能跟谁睡去啊!一把骨头加一张皮,脖子上净是丹毒。瞧她,给你灌迷魂汤的妖精,扭搭着来了:哼,下流女人,勾引小伙子!……”
第二个场景中只有罗莎和科片金。罗莎在大街上走着,科片金想看清楚罗莎的模样,于是将屋里的玻璃砸碎。
第三个场景发生在乡村的大街上。一群人抬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罗莎。当科片金想再次认清楚她的时候,却发现罗莎变了模样。科片金非常意外地喊了一句话:“你们把我母亲埋了吧!”。
第四个场景中只有科片金。他在等待庄稼汉从墓地回来。一阵风吹来,科片金想把打碎的玻璃堵上,却发现它完好无损,此时的科片金已经回到现实中。梦的第四个场景与现实之间似乎没有界限,科片金完全是自由穿梭的。普拉东诺夫使梦境与现实交错,做梦的科片金也分不清是做梦还是在现实中,丧失了明确的时空感。德瓦诺夫的梦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普拉东诺夫在描写德瓦诺夫的梦的时候也有意使作品的现实时空和梦幻时空相连,忽视了它们的差异,使实境与虚境相互渗透。
普拉东诺夫将梦作为小说的叙述手段之一,因此必然要对梦中人物精挑细选。母亲和罗莎都是塑造科片金人物形象和展示其内心世界的关键。“科片金同样地爱母亲和罗莎,因为对他来说,母亲和罗莎都同样的重要,犹如过去和未来同时活在他的生命中一样。”而在科片金的这个扑朔迷离和神秘莫测的梦中,母亲和罗莎成为一个人。弗洛伊德指出,梦中的情感为了逃避稽查,往往会通过凝缩和移置的方式,重新拼接组合不同的观念材料,因此在将隐匿的潜意识转化为外露的梦象的同时,梦中事物的形状、性质、功能都会发生变化。母亲与罗莎成为一个人是因为在科片金的潜意识中她们是自己灵魂中无法舍弃的重要部分,而母亲象征的“过去”和罗莎象征的“未来本来也应该是融合的,不相斥的,因此普拉东诺夫使科片金母亲和罗莎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异,使科片金无法辨认出她们。两个人合为一个人是违背自然规律的,现实中不会出现的怪异现象却被梦的神奇和怪诞赋予了合理性。梦突破了理性制约下的现实秩序,帮助普拉东诺夫建构出一个超越现实的作品空间。
这个怪异的梦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科片金分不清棺材里躺着的是谁,但最后决定该去埋葬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喊道:“你们把我母亲埋了吧!”科片金可以同时爱母亲和罗莎,过去和未来也可以相容,但是在母亲与罗莎之间,即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抉择的时候,他只倾向于未来。科片金的选择完全符合反乌托邦世界中人的普遍行动准则。反乌托邦世界中的人抛弃历史,对未来过多投入。未来就像科片金母亲所言,给所有的人灌了迷魂汤,让他们失去辨别力。普拉东诺夫没有直接去抨击这样的危险行为,而是将它隐藏到这个令人惊讶、不合逻辑的梦中,一点点地用梦的语言去演绎。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段,正如维尤金所指出的,“《切文古尔镇》的梦可以使人十分清晰地看出隐藏着的作者意图”。
弗洛伊德认为,梦念大多数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愿望、欲望和期望等主观感受,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讲,梦是现实生活的延续。尽管梦中的感情经过了思维和大脑一系列的删除、减缩以及颠倒等复杂过程之后才得以形成,但是经过详尽的分析后,它们是可以成功地被辨认出来的。科片金的这个梦就是其日常精神的最终体现。现实生活中,罗莎是科片金一切行动的理由,他骑在战马上,“心花怒放,因为再奔跑一个夜晚,就可以和罗莎·卢森堡相见了”,因此梦中的那些惊异行为,已不仅仅是梦的无逻辑和无厘头,而是来源于他白天活动着的思维。科片金的现实生活和梦幻世界已经完全被罗莎的形象填满,以至于他根本分不清梦幻和现实,两个空间对他来说俨然是不分离的。普拉东诺夫在描写科片金的梦境时也刻意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使虚实相渗,在作品中“梦是现实生活的延续”,“所有梦中的感情都和现实有关”,这样“现实的生活影响了梦境,梦境影响了现实生活”。而超现实主义者也认为,“不仅现实生活深深地影响着人的梦幻生活,而且梦幻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的现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承认梦幻是现实的继续,那么反之亦然,现实也是梦幻的延伸”。
由于分不清梦幻和现实,科片金在整篇小说中都处于一种意识不清的状态,他只活在一个美好的梦里面,活在与罗莎相见的期望中。德瓦诺夫也期望与死去的父亲相见,不同的是,德瓦诺夫在失去了对未来世界的信心之后,企图与死去的父亲相见,去寻找另一种生活的意义;而科片金的罗莎则是美好未来,迫切地想与之重逢表现出的则是反乌托邦世界中主人公盲目而无知的对未来简单和幼稚的单方面幻想。
梦境似乎创造一个独立和超越于现实之外的世界,但是超现实世界根本无法超越现实,只能与其密切相连,因为梦的所有要素都来源于生活,有时简直就是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真实,因而普拉东诺夫十分重视梦境描写。《切文古尔镇》中主人公的现实生活和梦中生活都必不可少,甚至梦中的生活对反乌托邦世界中的人来说更为重要,只有在梦里才会流露出人真正的渴望和感情。作家是把梦当作了认识手段。他使主人公的心理机制在梦中全面启动,让他们的大脑处于松弛状态,从而将他们精神世界呈现出来。
梦可以深入人的心灵,表达个体对世界的印象和感受,探视个体精神深处的世界。普拉东诺夫将梦作为“作品的主题”,他对梦境的钟爱可见一斑。作品中,除了不断地描绘德瓦诺夫、科片金、切普尔内伊等人物的梦境之外,还频繁使用“梦”以及和梦有关的字眼:“这里人人都有一个职业——做梦”,“你哪怕在梦里见他还是活着的”,“科片金已进入切文古尔,恍若进入梦乡”,“他们就不再分离,在睡梦中靠彼此的提问御寒”。普拉东诺夫没有将梦境和现实对立起来,而是刻意模糊了它们的界限,将它们融为一体,这样人物分不清自己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境中。梦的无逻辑性、片段性、跳跃性,使作品世界具有了神秘和非理性的特征。
[责任编辑: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