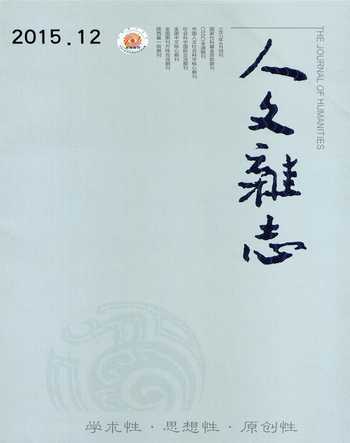《大学?首章》发微
王新水
内容提要 朱熹以《大学》为孔孟儒学入门的纲要,但是他对其首章的注解不但有不少支离和自相矛盾之处,而且与他自己也无法否认的诸多孔孟要旨相疏离。他对“亲民”“止于至善”和“明明德于天下”的解释,完全忽视了孔孟养民先于教民、以德取位和以“修己以安百姓”或“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最高境界等要旨。他没有阐明“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与“平天下”三者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解释修身与正心的关系时,他没有对心之三用——道德心、认知心和情欲心——做出必要的分疏。他对“致知”的范围做了超出“诚意”所需的扩大,进而导致他对“格物”也做出了完全越出《大学》首章语境和旨在建构其自己理论体系的诠释。“知”与“物”在《大学》首章中有明确所指,“物”指身、家、国、天下,“知”指知修、齐、治、平之终始先后。因此,“格物致知”之义在语境中是自明的,根本无需像朱熹那样用补经的方式再另作解释。“格”训“正”,“格物”即端正身、家、国、天下四者之本末关系;“致知”即获得关于修、齐、治、平四事之终始先后的知识。八条目中各相邻条目之间的逻辑关系有两种: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
关键词 明明德 亲民 至善 平天下 修身 格物致知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2-0012-10
无人能否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中国思想与文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无人能否认他在“四书”注解中的精义迭出,虽然学界都知道朱熹对《论语》《孟子》的注解与孔孟本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些关键的差别。但既然朱熹以《大学》为“四书”之首,为孔孟儒学入门之纲要,“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4,册1,中华书局,1986年,第249、252页)这就意味着他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或许是有意淡化了,《大学》思想可能与孔孟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重要差异。既然如此,则他对《大学》的解释就本应该避免与他自己也不否认的孔孟思想要旨产生分歧。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以《大学》首章为经为纲,并认定其“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但他自己对这章的注解,却与他自己也不否认的孔孟要旨存在一些不可小觑的疏离。另外,虽然朱熹认为《大学》是先秦儒家文献中为数极少的论述严谨、条理清晰的篇章之一,“可将《大学》用数月工夫看去。此书前后相因,互相发明,读之可见,不比他书。……惟此书首尾具备,易以推寻也。”“《大学》一字不胡乱下,亦是古人见得这道理熟。信口所说,便都是这里。”(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4,册1,中华书局,1986年,第250~251页。)但仅仅在他自己所认定的首章,朱熹就留下了数个关键点未做必要而清晰的解释,支离其义,令后人难免有遗珠之憾——尽管他从38岁时完成《大学解》初稿,至其71岁时(1200年)临终前三天,一直都在修改对《大学》的注解,可谓穷尽了平生精力。朱熹自道曰:“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4,册1,中华书局,1986年,258页。)不知这是由于朱熹所定的《大学》首章的思想本来就粗疏含混,支离难解,颇具旧学功底的周作人曾在他于1938年3月5日所作的《读〈大学〉〈中庸〉》一文中道:“读《大学》《中庸》各一过,乃不觉惊异。文句甚顺口,而意义皆如初会面,一也。意义还是难懂,懂得的地方都是些格言,二也。”(周作人:《知堂序跋》,钟叔河编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6页。)还是由于朱熹本人理解的局限?本文在分析朱熹注解的支离、内在矛盾及其与孔孟要旨分歧的同时,试图对其所遗留下的问题,给出一己之见,从而期望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的深入理解。
除了前人已指出的对“亲民”“致知格物”的解释存在争议之外,朱熹的《大学》首章注还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三者含意及其之间关系的解释,未紧扣养民先于教民、以德取位等朱熹自己也不否认的孔孟思想要旨做解;二是对“明明德于天下”与“天下平”之间的关系未遵循孔孟要旨给出必要的、合理的解释;三是对“修身”与“正心”的关系,亦即“心正而后身修”之所以然,未给出充分而清晰的阐述;四是对于“诚意”“致知”与“格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欲诚其意,先致其知”亦即“知至而后意诚”之所以然,未给出必要而清晰的阐述,对“格物致知”解释也远远脱离了首章语境。
一、“三纲领”的内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为论述方便,兹据朱熹《大学章句》录首章于下,并据其注分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下文凡引《大学》原文,皆只随文标明《大学章句》之章数;凡引朱熹之注解,皆只注书名和页码。)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二句原本在此,朱熹移至“传五章”。为论述之需,今移回)
朱熹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大学》的三纲领。⑥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他释“亲民”为“新民”,“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⑥这是认为,“亲民”是“明明德”之人根据儒家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所应为之事。他释“止于至善”曰:“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⑦此以“止于至善”为“明明德”和“亲民”应遵守的原则或应达之结果。朱熹这样解释三纲领引发了以下问题。
首先,这种解释疏离了孔孟养先于教的安民要旨。《大学》主旨乃修齐治平之道,郑玄注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礼记正义》下册,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36页。)朱熹本人《大学章句序》云:“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则“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当为“大学”应有之义,理当贯穿于三纲领。而孔孟所谓的“为政以德”“安百姓”之道,特别注重养先于教。冉有问:“既富有,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论语·子路》)在此孔子认为当先富民而后教民。孟子同样认为,当先使民有以养而后教之为善。“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但是,朱熹对三纲领的解释恰恰淡化了上述要旨。朱熹训“亲”为“新”,解“亲民”为“新民”,“新民”即“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此解丝毫未涉及养民之意,遑论养先于教之意。训“亲”为“新”虽不乏训诂之根据,然则孔孟养先于教的安民之旨即全然不见。因此,如果朱熹真的把《大学》视为孔孟思想入门之纲要,并且认为首章乃孔子之言,他自己就不该把“亲民”解作“新民”。“亲民”之“亲”应作本字,解作亲近、亲爱,“亲民”即爱民之义。孔颖达解“亲民”为“亲爱于民”。(《礼记正义》下册,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40页。)而爱民包括养民和教民(即朱熹所谓的“新民”)二意在内,这更合乎孔孟大义。既然“亲民”本含“新民”之意在内,则后文出现诸多包含“新”字的引文(《大学章句》传2章)正是呼应前文,而不必像朱熹那样以此为据谓“亲”必作“新”。
如果像朱熹所说的那样,“明明德”是指每个学者都就各自天赋本有且本来虚灵不昧、昭明不息、能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明德,去除其由于气禀之拘、人欲之蔽所导致的昏昧染污,而恢复其本有之明;“明明德”,郑玄和孔颖达分别解作“显明其至德”和“章明己之光明之德”。(《礼记正义》下册,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36、2240页。)朱熹《大学章句》解“明德”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亦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4,册1,中华书局,1986年,第265页。),比郑、孔更进一步,直探“明德”之本源。然朱熹此解似以“明德”为孟子所谓的良心,且他自己也确曾先引孟子而后接着说“良心便是明德”(《朱子语类》册1,第269页)。他在别处对“明德”之解释,与此有异。“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许多道理在这里。本是个明底物事,初无暗昧,人得之则为德。”“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许多道理在里,其光明处,乃所谓明德也。”(《朱子语类》册1,第263、268页。)这两处乃以“明德”为天生于心中且已彰显出来之道理,或者说,乃心中天生之理的显明。但如果“明德”已是心中天生之理的显明,那何以还要“明”之呢?朱熹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亲民”即“新民”,是指学者自明其明德之后,又推以及人,使万民也能去除拘蔽其明德的旧染之污而复其本来之明,那么,所谓“新民”应当止于至善,即达到尽夫天理之极、除尽人欲之私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是针对什么而说的呢?是说实施“新民”之教的学者,即已经自明其明德进而推己及人、明民之明德的学者应当止于至善,还是说“新民”这件事应当止于至善呢?若为前者,则与“明明德应当止于至善”之意相重复,因而不可能。因此朱熹应该是指后者,即指“新民”这件事应当止于至善。所谓“新民”之事应当止于至善,就是说应当不但让全民本有之明德都明起来,而且还要都达到尽夫天理之极、除尽人欲之私的境界而不退堕。如果这样,那么,孔孟养民先于教民之大旨,就被朱熹淡化疏离了。在对上引《论语·子路》第9章和《孟子·梁惠王上》第7章的注解中,不但根本不见朱熹对富民和养民先于教民之旨的揭示,而且对第9章的注解着重揭示的反倒是养而不教的危害与人伦教化的必要性。(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43~144、211~212页。)当然,大凡思想家对前人经典的注解,都难免因其所处的时代境况而有所侧重,朱熹大概也不例外。
其次,上述解释忽略了孔孟以德取位之大义。无论是解作“爱民”还是“新民”,“亲民”都不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那样,乃所有人都应为之事,而只能是为政者或在位者的应尽之职——因为无位的庶人只有应为的助人之义,而无“亲民”的应尽之职。如果把只有在位者应尽的“亲民”之职,等同于人人皆应为的助人之举,那大学三纲领就与其治国平天下之旨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但是,如果因此就像某些现代诠释者那样,认为“大学之道”只是针对在位的王公贵族而言,“由此也可以看出,从‘亲民到‘新民的诠释转向,《大学》一书遂由天子王公的教科书成为一般士人修身的教科书。”(郭晓东:《从“亲民”到“新民”:也谈宋明儒学中的“现代性”精神》,《江汉论坛》2005年第10期。)那也明显有违儒家之教。因为在儒家看来,“明明德”“止于至善”确乃人人应为之事。对于这些矛盾,朱熹似乎并未意识到,因为从他的注解中找不到化解上述矛盾的出路。朱熹的注解只是从儒家的恕道出发,认为学者既已明己之明德,就应该推己及人,也明他人之明德。这样就把“亲民”当作人人皆应有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德,而非为政者或在位者的应尽之职。
其实,“亲民”当然是指为政者或在位者的应尽之职,而不是指人人都应为之事,但同时也的确是就包括庶人在内的所有人而言,而不仅仅是针对在位者而言。因为在孔孟思想看来,应尽“亲民”之职的在位者,必然首先是有德者,其位之获得和保持,须有德方可。有德才可有位和保位,人人皆然。早在孔子时代,即已官学下放,礼失于野,在位之贵族日渐没落无德,因此孔子认为“大德必得其位”(朱熹《中庸章句》17章),朱熹《中庸章句》二十八章曰:“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此似乎承认有德未必有位,似与孔子所言相左。我们认为,或许孔子乃就应然或先天当然之理而言,而此处乃就后天之经验事实而言。主张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论语·里仁》),提倡以德取位,以此警戒、对抗有位无德之贵族。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6页。孟子绍其绪,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从之”(《孟子·告子上》),“天爵”即指德,“人爵”即指位。而《大学》成篇乃在孔孟之后,梁涛认为《大学》成文在孟子之前。因其论证欠充分,兹不从。(梁“新证”见其所著:《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115页。)平民通过进学修德而致位的观念,其时已然盛行。因此首章先言“明明德”乃人之皆应为,德高方可得位,故进而言及唯有位者方应尽的“亲民”之职。因此,“亲民”既非如朱熹所解乃人人应为之事,亦不如今人所言乃专门针对天子王公而言。如《大学》不仅在首章即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且在最后一章又强调“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大学章句》传之10章)。
第三,朱熹对“至善”和“止于至善”的解释,不但疏离了孔孟养先于教之要旨,而且因此也偏离了孔子有关在位者的最高境界——圣之教义。孔子认为,在位者的最高境界——圣,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或“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谓之“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安百姓”或“天下平”都包含养民在内,而不仅仅是教民。
先秦儒家文献,除《大学》之外,似乎未见言及“至善”者。在《大学》之外的儒家文献及先秦诸子经典中,只找到一处言及“至善”:“至善之为兵也。”(《管子·幼官第八》)此“至善”即“最好”之义。朱熹对“至善”的解释,不是单纯地依傍训诂,而有合理的引申。他在《大学章句》中解作“事理当然之极”或“天理之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这是引申义。在其他地方他解作“极好”“最好”,这是本义。另外,他也解作“恰好”或“无过不及”。他既说事事皆有一最好的标准,因此事事皆应做到至善,又谓事事做到最好方可谓至善。上述各种解释,参见《朱子语类》卷14,册1,中华书局,1986年,第267~270、308页。又见册2,卷16,第319~320页。(后文凡引此书,皆只注书名、册数与页码)朱熹所谓的“明明德”“亲民”这两件事都应做到最好、极好、恰好,就是指学者自己和其他所有人,人人都应明其明德,都应尽夫天理之极,无一毫人欲之私。显然,朱熹这种解释与孔孟养先于教之要旨及其“修其身而天下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之最高境界——圣,存在明显的差距。
依朱熹本人的注解,既然“大学之道”的前两条“明明德”“亲民”都是就学者而言,其主语都是学者,那么第三条“止于至善”就也应该像前面两条一样,是以学者充当主语,而不应该像朱熹所解释的那样,是以“明明德”“亲民”这两件事充当主语。换言之,“止于至善”不是就“明明德”“亲民”这两件事本身而言,而应该是就为“明明德”“亲民”之事的学者而言。孔颖达释“至善”为“至善之行”,《礼记正义》下册,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40页。显然也认为“止于至善”的主语是人而非事。而《大学》后文所谓的“盛德至善”(《大学章句》传之3章),也是指在位之君子而非指事。既然如此,那么,对于为“明明德”“亲民”之事的学者而言,其所应止于的“至善”具体是指什么呢?顺便一提,不可把《大学》中的“至善”混同于康德所谓的“至善”(das hchste Gute)。康德所谓的“至善”包含“至上的善”与“完满的善”这两重含义。“完满的善”是指与所拥有的“至上的善”即德性成比例的、所应享有的幸福,即“至上的善”与幸福的成比例的结合;而“至上的善”是指人应为之德行,它因在“完满的善”中作为幸福的至上条件而成其为“至上的善”。幸福与德性在“完满的善”中这种成比例的结合,不是分析的,而是综合的。而且这种结合不是由经验推出来的,而是先天的,因而是实践上必然的。(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1~155页。)而《大学》中的“至善”,只指德行——最多相当于康德所谓的“至上的善”,而不指其所谓的“完满的善”。朱熹虽然对“至善”之义做了详尽的解释,但却并未明确指出“至善”在《大学》中具体内容到底何所指。对于一个以“明明德”为应为之事的庶人而言,能把“明明德”做到最好无疑就是最有德之人。而大德必得其位,得位则必进一步以“亲民”为其应尽之职。而“亲民”既已为其应尽之职,则其如欲“止于至善”,就必使人人有养而后教之,使人无不沾溉其德泽。而这其实也就是孔孟所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亦即孔子所谓的最高境界——圣。
果如上之所述,则三纲领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朱熹所说,“止于至善”乃“明明德”和“亲民”二纲领的原则。“止于至善”实为最高纲领,“明明德”则可谓最低纲领,而“亲民”则为由最低到最高纲领的过渡。
二、“明明德于天下”与“天下平”的内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大学》首章以顺逆两个序列给出了八条目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果溯因的序列:明明德于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由因至果的序列: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两个序列的其他七个条目都可以一一对应,但作为同一因果关系的最终结果却有两个:“明明德于天下”和“天下平”。何以会如此?这两者到底是一还是二?《大学》原文没有解释。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没有解释,在《大学或问》中也未有只字涉及。莫非无论是《大学》本意,还是朱熹思想,都以二者为一回事?至少朱熹很可能有此意,否则,他就不会认为只有“八条目”,而应该说有“九条目”。
但二者究竟是否一回事,我们首先得明白“明明德于天下”到底是何义。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说,“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这种解释显然是对前面“新民”之义的延伸。既然“新民”已淡化了养先于教的安民之旨,此处一以贯之,依然如故。不但如此,而且从句义而言,“明明德于天下”怎么会等同于“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亦即“明天下人之明德”呢?——这种含意用“明万民之明德”或“明天下之明德”来表达不是更妥当吗?而把“明明德于天下”解作“使自己的明德章明或光耀于天下”,不是更符合句义吗?孔颖达解作“章明己之明德,使遍于天下。”(《礼记正义》下册,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41页。)而所谓“使自己的明德章明或光耀于天下”,不就如同说让自己的明德泽被天下吗?而让自己的明德泽被天下,在孔孟思想看来,必然意味着让天下百姓皆有以养并进而有所教,而不仅仅意味着新民或教民。而在孔孟等先儒眼里,这不就意味着“天下平”了吗?如果像朱熹那样解释“明明德于天下”,那就忽视了养民为先之旨,因而很难令人把“明明德于天下”和“天下平”看成是一回事——因为“天下平”不可能意味着不让天下百姓皆有所养,从而使得“明明德于天下”和“天下平”成为含义有别之二事,乃至最终导致“九条目”的出现,因此与他自己所谓的“八条目”相背。
在《大学或问》中,朱熹的解释与上述有所不同。朱熹答门人蜚卿之问曰:“《大学》‘明明德于天下,只是且说个规模如此。……只是见得自家规模自当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得做不去处,却无可奈何。”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6,册2,中华书局,1986年,第381页。朱熹意为,“明明德于天下”是学者分内之事,本该做之事。所谓本该做之事,朱熹所举的例子,就是明己之明德,以使天下人人都得其养,都明其明德。⑤虽然朱熹在此也没有明显强调养先于教,但已涉及养民之事,因此向孔子所谓的“修己以安百姓”和孟子所谓的“修其身而天下平”靠近了一步。这种解释不但更接近孔孟要旨,而且与“天下平”之意也不产生冲突,因此允许人合理地把“明明德于天下”和“天下平”视为同意异名,异名同实,从而保住了朱熹自己所谓的“八条目”,而不会节外生枝,冒出“九条目”。
但是,朱熹在《大学章句》首章注中,不但并未对“天下平”或“平天下”做任何直接的解释,而且从“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这一简略的概述来看,他主要是从“明天下人之明德”这一“新民-教民”的角度去理解“天下平”之意。因此,从作为晚年定论的《大学章句》来看,似乎可以断定,朱熹在此可能始终未意识到或未重视孔孟养先于教之要旨。
然而,或许是受朱熹的启发吧,现代有学者以为,“明明德于天下”是就理想、道德实践而言,而“平天下”则是就现实、政治实践而言。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此处引用梁之观点做比较,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毫无否定之意。另外,笔者关于《大学》首章之解读,大旨虽与梁著相关论述多有契合,但论证的理由和过程皆有所不同。这种分别实于义难安。首先,持此论者虽然也强调儒家的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但其实就为政者的身份而言,很难简单地对其实践做道德与政治之分别。因为在孔孟儒学的视野里,政治行为全体都是道德行为,虽然道德行为除了政治道德之外还可以有与政治实践不直接相关的私人道德。其次,朱熹以“明明德于天下”为人必须遵循的、实际存在的当然之理,这与仅仅视其为人的主观理想有霄壤之别。第三,同样会导致九条目的出现,而持论者却又以朱熹八条目的分判为基础。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129页。
但是若说“明明德于天下”和“天下平”含意一致,乃同意异名,异名同实,则人尚可质疑:对于如此重要之意,为文者何以偏要用不同的行文来表达,难道仅仅为了行文的变化,就不惜冒被人误解的危险吗?我们可以从文意和文气两方面,来合理地推测作者如此异语同意之行文的可能原因。从文意而言,如上文所述,“止于至善”是说对于学者而言,最高的善就是把自己的整个道德修养好,进而让天下人在有所养的前提下,都受教化而向善。而“明明德于天下”正可含此意,故行文承此意而用语如此。从文气而言,上文既已出现“明明德”而未见“天下平”之语,故下文承上文而先在始句以“明明德于天下”之语表“天下平”之意,复于末句以“天下平”之语与“明明德于天下”互文见义,呼应始句。
另外,除了首章唯一一次使用“明明德于天下”这一短语之外,《大学》全文再也没有在其他任何一处使用它。最后一章解释“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大学章句》传之10章),据文意文脉可知明显是解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这句。但是却用“平天下”这一短语代替“明明德于天下”这一短语。
虽然对于上述情况,朱熹没有一字提及,但我们据此几乎可以断定,《大学》本文的确是在同一含意或所指上使用“平天下”与“明明德于天下”这两个表达,后者与前者之间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想与现实、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一关系。
如上所述,“明明德于天下”就是指“平天下”(“以修身为本”),就是指“止于至善”,因此,这个朱熹视之为八条目之末、之终、之后的“平天下”,实际就是《大学》的最高纲领,而其他七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不过是实现“止于至善”或“平天下”的具体次第而已。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乃修身之次第。
三、“修身”与“正心”的关系
何以“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亦即何以“心正而后身修”?正心与修身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也许不如在古代语境中那么显豁。或许正因为此,朱熹在首章注中于此着墨不多。但如果仅仅是着墨不多,那倒也罢了。麻烦的是,在他本来就不多的注解中,还存在着可做不止一种解释的歧义——无论是从现代汉语语境还是从古代语境而言皆然。
朱熹首章注曰,“心者,身之所主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仅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朱熹就把正心与修身之间的关系打发了。在“修身”一词中,“身”有特殊含义,是指本人的德行。具有这种抽象含义的“身”,很少单独成词使用。在与家、国、天下对比使用时,“身”虽单独成词,也具有“本人的德行”之含义,详见后文。而在“心者,身之所主也”这句中,“身”的含义并不确定,既可能是从生理上而言的“身”,也可能是从眼耳鼻舌四肢等五官之机能方面而言的“身”,因为古人认为从这两方面而言的“身”,也都是以心为主。正如《大学》所言,“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章句》传之7章)视、听、知味等正常的感官机能的发挥,也得先端正作为其主宰之心——认知心。然而,即使《大学》所谓的“修身”也不排斥对生理活动的关注,更不排斥对获取见闻之知的感知能力的培养,但至少在先秦儒家经典中,“修身”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含意,就是指修养本人的道德,与“修己”同义,而与关注生理活动倒未必相关。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不但人的生理活动、感官机能都主宰于心,而且道德也是奠基于人心或人性,因此“修身”就必先“正心”。朱熹当然明白这种古代思想的常识,但是他的注解略嫌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对于作为视听知味等感官机能之基础的认知心和作为道德之基础的道德心,未加必要的甄别。
也许在首章注中朱熹是为了求简明扼要而一语带过,因此他在《传七章》的注解中,从道德修养而非仅从情欲和感觉认知的角度,含蓄地点出了道德意义上正心与修身之间的关系。“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内,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④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8、8、1页。所谓“敬以直内”,即就道德涵养而言。
然而,《大学》所谓的“修身”和“正心”,到底有没有道德修养之外的含意,尤其是情欲方面的含意呢?《大学章句·传之七章》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朱熹接受程子“身当作心”的观点,并注解此段曰:“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④这里朱熹显然不仅仅把心看做道德心,看做是道德的主宰,而且认为心也能起情欲之用,并认为情欲之用过胜,则可能影响心的其他方面之用——“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至于这个可能被影响的亦即“或不能不失其正”的其他之用,是否一定是就心的道德直觉作用而言,朱熹未点明。大概因为《大学》原文本来就没有明言吧。这当然可以看做是朱熹注解尊重原文的严谨之处。但这就允许我们做两种推测:其一,“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只是指情欲心和认知心而言;其二,就《大学》强调道德修养的主旨而言,在其既定的语境之中,“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并非泛指任何处境中的情欲,而是专指道德处境中的情欲。而紧接着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虽看似完全论述“正心”对于正常发挥视、听、知味等感官机能的必要性,并不涉及道德修养,但也可认为,作者是以视、听、食等为例,来说明“正心”对于作为道德修养之义的“修身”之必要性。然而,朱熹没有点明这些。这些地方也许正显示了古人为文的灵活性和文学性,哪怕是论理之文。朱熹认为心为性情之统帅或主宰,孔孟则似乎融合情、知而说道德心,孟子尤其明显,其四心说即为明证。本文把心之用在逻辑上三分为认知心、情欲心和道德心时,所谓认知心和情欲心,乃专就与德性无关之知和情而言,与德性相关之知和情,则一并归入道德心。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大学》的语境而言,此处“修身”当然还是理解为专指道德修养更妥当。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限定,庶民之中,唯有俊秀者方可入大学学习治人之道。⑥前文曾说现代也有人认为《大学》本是天子王公的教科书。但这里却说无论天子庶人,皆当以修身作为平天下之本。这使得从朱熹到今人的观点难以安稳。然而,有人却别出心裁,另具慧眼,由这句话断定历代帝王不会喜欢《大学》。“在‘德上,‘道认为天子和庶人一样,都要‘修身,都是一个‘人。从这里已可看出这个纲领不会为帝王所喜。天子富有天下,至高无上,何必还要‘以修身为本?”(金克木:《读〈大学〉》,《探古新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金克木在此显然把“平天下”简单地等同于“富有天下,至高无上”,因此才会认为天子何必要“以修身为本”。
不管朱熹的限定与后人的高论是否合理,至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在《大学》中是有其历史根基与合理地位的。首先,如前所述,《大学》成文乃在官学下放、礼失于野、贵族没落无德、平民可以通过讲学修德而跻身朝政的战国中后期乃至秦之后,因此它提倡庶人与天子平等,从而认为庶人也必须以最终旨在平天下的“修身”为本,这是大势所趋。其次,就道德修养而言,“修身”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为人之本。以道德修养为做人之本,不正合乎儒家的基本教义吗?这里又显示出《大学》行文的活泼灵动、机趣盎然。“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本”既可指“平天下”之本,又可指做人之本,这不正可谓一字捅破儒家道德与政治一而不二的真相吗?
四、“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及“致知”“格物”的内涵
朱熹解“诚意”极精辟,意善一体,念行合一,不给伪君子任何钻空子的余地。但他对“诚意”与“致知”之间的因果关系,亦即“诚意”何以必先“致知”或何以“知至而后意诚”的解释,却难免令人感到迂阔茫然。“诚意”,朱熹解云,“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③④⑤⑥⑨B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7、4、4、7、4、7页。所谓“欲其一于善”,即让意完全专注于善,“无自欺”,即“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求必得之。”③对于要做到这种“毋自欺”(《大学章句》传六)的“诚意”何以必先要“致知”,朱熹没有直接解释。但他解释了“知至而后意诚”。他先把“知至”解作“吾心之所知无不尽”,④然后把全句解作“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⑤但是,难道要做到“诚意”,即要让意念完全专注于善,做到为善去恶,就必须先穷尽天下万物之理,“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⑥然后方能如愿吗?如果真的能先穷尽包括善恶在内的天下万物之理,那当然可以做到朱熹所说的“诚意”,这诚然不错。但问题是,要做到诚意,除了必先知道何为善恶之外,还必须先掌握其他所有的知识吗?当然不必。就像我们今天想要让自己的意念充满专注于善和想要为善去恶,难道我们就必须得先知道人为什么会直立行走吗?虽然朱熹也强调,所谓穷尽事物之理乃就理而言,就工夫而言,无须事事物物都去格,而应讲次第,先就切己者察之于身,然后由此及彼,由少及多,乃至最后豁然贯通,尽知万物之理。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6,册2,中华书局,1986年,第400~401页。但无论如何,即使仅从理上而言,朱熹对“知至而后意诚”的解释仍然失之于迂阔。
事实上,“知至”就是说“知识得到了”,而根本就不是朱熹所说的“知无不尽”之义。因此“知至而后意诚”就是说,知识得到了然后方可做到意诚——让意念充满专注于善和努力去为善去恶。按朱熹对诚意的解释,这里的“知”当然就是对善恶的知。郑玄注云:“知,谓知善恶吉凶所终始也。”(《礼记正义》下册,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37页。)同样,“致知”也不可像朱熹那样解作“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⑨而是解作“获得知识”。孔颖达解“致知”为“招致所知”。(《礼记正义》下册,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41页。)要想诚意,就要先获得知识——关于善恶的知识。但是,关于善恶的知识很多。而所谓的诚意、正心,必须要落实到修齐治平的实践。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具体要如何下手呢?为此,我们必须确定,在《大学》首章中,关于善恶的知识有无具体所指,亦即“致知”之“知”,有无具体范围。既然“致知在格物”,那么所致之“知”的范围当然就决定于所格之“物”。朱熹认为这里的“物”包括天下所有之物,因此“格物”就是要穷至所有物之理。B11且不论他对“格物”之解释是否妥当,仅论他对“物”的解读。如前所述,如果说朱熹所谓的知无不尽、尽知天下万物之理是不必要的因而他对“致知”的解释是不恰当的,那么“物格而后知至”之“物”,就也不必要被认为是指天下所有之物。
既然如此,那此“物”到底能否确定其具体范围或具体所指呢?立足《大学》首章的语境,当然是可以确定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四句话十六字本来就暗示了“物”和“事”之所指,只可惜朱熹因埋头于自己的解释而埋没了这个重要的线索。很可能是受上文“知止而后有定”这句话的影响,朱熹认为上述十六字乃“结上文两节之意”,认为“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朱熹此注可谓字字为营,滴水不漏,但却未必契合首章语境。因为下文出现“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等语,故上文“物有本末”之“本”与下文“修身为本”和“本乱”之“本”之所指,关系当更为密切,都与身相关。连朱熹自己解“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之“本”时也说,“本,谓身也。”②因此,上述十六字并非如朱熹所云乃“结上文两节之意”,而实乃开启下文两节之意。当然,它不仅有启下之功,也做承上之用。但其所承之上并非如朱熹所解,以本、末、终、始分别承接上文之“明德”“亲民”“能得”“知止”,而是以“则近道矣”之“道”,承接首句“大学之道”之“道”。而如前所述,此“道”的最终追求可以归结于“止于至善”,亦即“明明德于天下”或“平天下”(“以修身为本”)。所谓“近道”,是说离道近了或靠近了道。为何说“知所先后”则靠近了道,即接近于“明明德于天下”或“平天下”(“以修身为本”)呢?这就要进一步明白所谓的“先后”到底何所指,也就是“知”的具体对象或内容到底是什么。
如果“物有本末”之“本”是指身,那其“末”当然就是指家、国、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此“身”虽单独成词使用,但乃与家、国、天下对比出现。所以也指自身的德行。所谓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并不是说后三者没有前者重要,而是说,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应该先修身,即“以修身为本”。八条目之次第,“格物”最先,为何不说以它为本为先,而以修身为本为先呢?至少可以给出如下解释:其一,《大学》主旨在修身以平天下,故就平天下而言,当以修身而不以格物为本为先。其二,《大学》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皆以修身为重,格物也不过是为了修身,而并非最终目的,故不以格物而以修身为本。其三,格物之“物”若特指身、家、国、天下而言,则“以身或修身为本”之观念已然先于“格物”,故从逻辑上而言,修身已为格物之本之先。因此,“事有终始”之“事”,就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事,“终始”则分别指平天下、修身。此解最初受伍观淇(字庸伯,1886-1952年)解说《大学》之启发,然其解“格物”之“格”,取《说文》所谓之本义——“格,木长貌”,兹不从。伍解参见梁漱溟:《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156页。而所谓“知所先后”则并非如朱熹所说,“知明德”“知止”为先,“亲民”“能得”为后,而是说知道以修身为先,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为后。当然,如果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十六个字,并非特指身、家、国、天下四物和修、齐、治、平四事以及大学之道等而言,而是泛指万物百事及任何道而言,那它们在结构上就只是泛论以启下文,而无承上之用,但这并不妨碍本文后面对“格物致知”的解读。知道并遵照这种先后次第去做,就可以一步一步接近“平天下”或“明明德于天下”这一“至善”之道,最后完全实现它。
基于上述解释,所谓“格物”,就不是朱熹所谓的穷至天下万物之理。“格”训“正”,《方言》:“格,正也。”《孟子·离娄下》:“谓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赵岐注:“格,正也。”《古文尚书·冏命》:“匡其不及,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孔颖达疏曰:“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则格正之。”“格谓检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检括使妄心不作。”“物”就是指身、家、国、天下四者。劳思光认为,所有先儒对“格物”的解释都没有确定证据,我们今天同样也没有。但他认为“物有本末”之“物”是指意、心、身、家、国、天下等六者。参见劳思光:《大学中庸译注新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9页。“格物”即正物。正物意谓端正物之本末关系,亦即以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能端正身与家、国、天下之本末关系,则可“致知”或“知至”,亦即知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事之先后。此解最初受张岱年观点之启发。但他据《苍颉篇》“格,量度”之训,解“正物”为衡量物,兹不从。参见张岱平:《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44页。梁涛也持这种观点,但他接受杨柳桥“格物即正名”之见,解“物”为“名”,兹不从。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129页。端正了四物之本末关系,知道了四事之终始先后,就该知道“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原本对这种“知”有个总结性的评价:“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可惜这一评价性的总结被朱熹割移至他自己所谓的“传之五章”。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知本”之“本”,并非特就“身”或“修身”而言,而乃泛指。之所以认为这种知乃“知之至”,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知——“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知至”之后,再诚心实意地以之为念而求实现之,这就是“诚意”-“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理解,正与首章语境相吻合。
“格物致知”之意在首章语境中本来即如此自明,因此《大学》方才唯独对“致知在格物”没有另外再做任何解释。可是朱熹却因为要顾全他自己的理论,竟然认为《大学》原有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只是后来亡失了。于是乎,他就“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②做出了历史上最大胆的补经之举。
五、细论“八条目”之间的关系
虽然统而言之,作为工夫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都处在前后相随、次第井然的同一个因果系列之中,但若把八条目分成不同的亚系列而细论之,则各亚系列内部各条目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系列内部各条目之间的关系,实际存在着微妙而重要的差别。为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为了准确而全面领会《大学》首章之要义,分析并指出这些差别似乎并非可有可无之事。
就“格物-致知”这一亚系列而言,“格物”作为“致知”的充要条件之意味较重。因为唯有端正身、家、国、天下四者的本末关系,才能够而且也必然能够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事的先后次第,而知道了后者才意味着且必然意味着端正了前者。
而“致知”之于“诚意”,却并非充要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因为虽然不知修、齐、治、平四事的先后次第就无法做到首章所谓的诚意,但知道了也并不就必然能够做到,而还需要有其他的条件,如学者必须要有修齐治平的愿望和追求等。
“诚意”与“正心”这两道工夫,在时间上显然难以分出先后。“意”和“心”,也并非如“物”和“知”、“知”和“意”、“身”和“家”等那样,是虽相关但却相互外在的两物,而是同一物之显和隐、动和静的关系。“意”并不在“心”外与“心”相对成另一物,而本来就是“心”之所发。“心”不起念则为静为隐,一起念成“意”则为动为显。因此,就首章所赋予给“诚意”和“正心”的内涵而言,意之诚同时就是心之正,而绝非“意诚而后心正”。之所以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不过是因为“心”若不发为“意”,则静隐而致“正心”无从入手,心只有发为“意”而动显方可“即诚意而正之”,但并非先诚意而后正心,而是“诚意即正心”。虽然“意”的出现只有“心”存在之后才有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诚意”和“正心”之间有先后关系。另外,《大学》之所以认为“诚意”“正心”有先后,也是出于行文气势和行文方便之需要,这是古人为文的习惯。因为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之间有明显的先后次第,故为了行文的势畅气贯以成修辞之美,而谓“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从逻辑上而言,“诚意”之于“正心”,也是充要条件。唯有“诚意”才能够而且必然能够“正心”,“正心”了才意味着而且必然意味着“诚意”了。
从首章的语境来看,正心与修身,显然先后次第分明,正心是修身的前提和基础,未有心不正而身可修者。当然,也未有心正而身不修者。因此,正心应该也是修身的充要条件。唯有正心才能够而且也必然能够修身,修身了才意味着而且必然意味着正心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事,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显然都有先后之分。就事实而言,虽然修身可以是齐家之前提和基础,但修身了未必就能齐家,其余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后相邻的两两之间亦然。因此,修身之于齐家、齐家之于治国、治国之于平天下,在逻辑上就只是必要条件关系,与致知之于诚意一样,而与其他亚系列内各条目之间的充要条件关系不一样。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无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