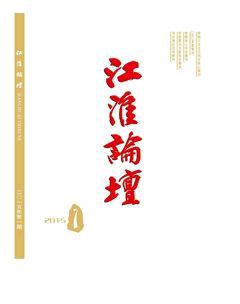制度自信与中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构建*
高奇琦
制度自信与中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构建*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1620)
对于政治学界而言,充分认识和理性激发中国制度自信的关键是构建中国自己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比较政治学可以对中国制度的自我有效性证明和他者有效性证明提供有益的帮助。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核心议题、基本价值和研究方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既要发现被西方忽视的问题领域和概念,同时也要对一些重要的、带有西方印记的概念进行创新。在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应该坚持一种“包容互鉴”的基本价值。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既要突出传统的多因解释和历史分析特征,还要整合西方比较方法中的一些优秀成果。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发展可以为中国的制度自信提供更有力的论证,同时,制度自信的提出也给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
制度自信;比较政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对于党进一步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主要针对“制度自信”这一论题展开。在讨论了制度自信的基本内涵和提出背景之后,挖掘制度自信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启示和意义。笔者尝试论证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对于政治学界而言,深刻理解和充分激发制度自信的关键是构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本文将重点剖析制度自信与中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关联,并就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基本价值与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性的讨论。
一、制度自信:基本内涵与提出背景
“制度自信”一词是客观内容与主观感觉的复合体。“制度”是客观内容,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总和。“制度自信”中的“制度”有特定的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八大报告对这一特定内涵有清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1]
“自信”是一种主观感觉,其原本是个体心理学的词汇。自信是一种具有复杂层次结构的心理构成物,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认,以及对自身能力、价值等进行正向认知与评价的稳定性格特征。简言之,自信是个体对自己的个性心理与社会角色进行的一种积极评价。它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一个人取得成功必须具备的一项心理特质。同时,这一个体心理学的词汇也会被用来描述群体的社会心理特征,如团体自信、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等等。
整体来看,“制度自信”是社会群体对自身制度绩效进行的一种积极评价。制度自信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即客观的制度绩效与主观的自我评价。客观的制度绩效是指各种外显的、以事实为基础的成绩和效果,如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等等。主观的自我评价是指内隐的、以群体感受为基础的对本群体进行评判和估量的心理活动。一般情况下,某一社会群体的制度绩效越高,该群体的自信也会相应增加,反之亦然。但是制度绩效与制度自信并不是线性的一一对应关系。换言之,制度绩效方面较高的社会群体未必一定具有与之相对称的高度自信。客观的制度绩效要达到制度自信需要经过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即主观的自我评价。
因此,在制度绩效和制度自信的关系上会出现两个特征:第一,制度自信往往会表现为对制度绩效的反应迟滞,即制度绩效已经发生变化,但感觉仍然停留在原先的状态。第二,制度自信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对制度绩效的认识不足,会产生制度不自信或制度贬损。同时,对制度绩效的认识过度,则会产生制度过于自信或制度自满。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会提出“制度自信”?这一提法实际上有两点重要背景: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良好的制度绩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有明显改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在显著增强。而且,中国在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成功抗击汶川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均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第二,与实际制度绩效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内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表现出明显制度不自信的特征。在理论领域,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知识和话语仍然是许多学科的主导性语言。在实践领域,当谈到制度创新时,人们时常还是会不自觉地以西方制度为蓝本或追求目标。特别是当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发展不平衡或腐败问题)等以事件的形式出现时,人们很容易因此而降低对整个基本制度绩效的认知。正是存在这些制度不自信的表现,所以十八大报告中才会提出制度自信的提法。
因此,在新时期提出“制度自信”实际上是制度绩效上升与制度评价不足之间矛盾的结果。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性做法,就是增加对现行基本制度绩效的了解和认识,并给予其正确的评价。这便是“制度自信”提法的题中之义。
当然,在这里还需要对制度自信与制度贬损、制度自满、制度自省和制度创新这一系列概念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制度贬损是对制度绩效过低或过于悲观的评价。制度自满是对制度绩效过高或过于乐观的评价。这两点都是需要避免的。制度自省是一种对制度绩效评价的自我调控,即在制度绩效特别好的时候,要较为低调地评价自己,而在制度绩效相对不乐观的时候,要自我肯定和自我鼓励。制度创新是推动制度绩效不断提高的价值目标。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制度贬损和制度自满是制度自信的偏差表现,制度自省是制度自信的调控工具,而制度创新则是制度自信的价值目标。制度自信并不是要故步自封,躺在原有的制度安排上享受其成果,而是要在自信的态度上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十八大报告对这一点表述得非常清楚:一方面,我们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自信,另一方面,我们则“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制度自信与比较政治学的关联
如前所述,既然存在制度不自信的问题,那么如何实现制度自信?因为制度自信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所以制度自信的关键是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积极和正确的评价。然而,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先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政治制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自信给政治学界也提出了一个既旧又新的研究课题:如何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积极有效的。之所以说这一课题是旧的,是因为之前的许多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实际上都在对这一点进行论述。之所以说这一课题是新的,则是因为在新形势下这一课题的论证要更为有力,其逻辑要更清晰、论据要更充分、方法要更先进。
笔者在这里试图表述的一个观点是,对于政治学界而言,充分认识和理性激发中国制度自信的关键是构建中国自己的比较政治学体系。制度自信有两层含义:一是 “制度的自我有效性证明”,即相信我们的制度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是较为有效的;二是“制度的他者有效性证明”,即认为我们的制度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类似问题可能有帮助。或者说,中国的经验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其特殊性体现为其是以中国经验和内容为基础的,其普遍性则体现在这些制度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会有效。
证明主要有三种方式:逻辑递推、实践检验和案例比较。在目前的政治学研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性证明主要是通过前两种方式完成。譬如,研究者往往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实现形式与民主本质的统一性,这主要是一种逻辑递推证明。或者,研究者用一些重要事件如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来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实践检验。[2]这两种方法都非常重要,并且是政治学研究中最常见的证明方式。然而,这两种方法也有一定的不足。例如,逻辑递推方法往往缺乏充足的实证证明。而在实践检验时,由于是一种自我检验,所以异议者则往往会用“自说自话”来批评这种实践检验。相比而言,案例比较则可以相对弥补以上两点的不足。一方面,案例比较是一种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案例比较往往运用多个案例,其中会包括其他案例,这一点会弥补自我检验的不足。这种案例比较的实质便是比较政治。
从这一角度出发,制度自信的两层含义可以在比较政治的逻辑下得到更为有力的证明。第一,比较政治将有助于“中国制度的自我有效性证明”。一般认为,自我有效性主要看其自我运行的绩效,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由于人们的预期是向前发展的,所以即便这个制度非常有效,但是在其内部往往还是会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所以,在内部很难客观地评价制度的自我有效性。但是,如果放在国际比较中,这种证明就很容易实现。在相对同等的起点下,对某一制度的采用与否会产生不同的制度绩效,然后对制度绩效进行比较就可相对客观地得出制度有效性的评价。
如果希望通过国别比较来实现中国制度的自我有效性证明,那么可以重点对以下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一是与起点相近或是起点略高的国家进行比较。通过与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发达国家(如亚洲“四小龙”或“四小虎”)的制度绩效进行比较,来验证我们的制度是否有效。二是与发达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进行比较。通过与发达国家早期一些制度的绩效进行历史比较,来检验中国的制度绩效。三是与一些绩效较差的制度也可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制度失败的经验会起到一种反向学习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避免我们走弯路,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中国制度的自我有效性。
第二,“制度的他者有效性证明”也需在国际比较中实现。许多好的制度不仅仅在本国可以适用,对其他国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制度和中国经验在别国中的运用来更加完整地认识中国制度的绩效。研究中国制度在他国的制度绩效,不是要劝说他国接纳或采用中国的制度,而是客观地描述和观察中国的制度和经验在这些国家的表现。在这一研究中,要坚持主权平等原则,不能把我们的观念和意志施加给其他国家,反对霸权性的制度推销和制度传播。
实际上,其他国家也在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制度和经验。这些国家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主要是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改革开放多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3],而朝鲜和古巴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也在学习中国的经验。[4]第二类主要是俄罗斯、印度等其他金砖国家。俄罗斯自普京以来在经济改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借鉴中国经验[5],而印度则在辛格出任总理之后在特区设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借鉴中国经验。[6]第三类主要是非洲国家。非洲国家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在学习中国的先进经验。[7]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问题。通过研究这些国家对中国制度的借鉴,可进一步验证和考察中国制度的他者有效性。
综上,制度自信的证明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紧密相关。实际上,近年来,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例如,以比较政治学为关键词的学术会议近年来有井喷式增长的趋势,同时,一些重点大学增设了以比较政治学为名称的系或研究机构。因此,制度自信的提出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正好契合在一起。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政治学整体恢复和发展的大潮中,比较政治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目前的整体现状来看,近30年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第一,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和理论得到较为完整的引介;第二,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的成果较为丰硕。从这两大成绩也可以反观目前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不足,即我们还缺乏反映中国主体性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知识。之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更多处于借鉴西方知识的阶段。从学科发展规律来看,这一点是许多学科都必经的阶段。但是,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不能总停留在借鉴西方的阶段。因为西方的知识主要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形成的,其与中国的实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今天我们的研究重心应该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比较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自信的提出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就开始讨论中国比较政治学构建的问题。[8]然而,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研究成果呢?这其中有多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未得到世界的认可,我们缺乏自信去总结这些中国经验。这一点是中国比较政治学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学者在比较政治学的一些核心问题上缺乏共识。例如,在构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体系中,三个问题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比较什么、比较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比较。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基本价值和研究方法。但是,我们在这三个问题上缺乏深度的争论,更缺乏共识,以致我们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乏实质性的突破和特色成果。本文在这里尝试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回答和分析,以期引起学界的进一步讨论。
三、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逐步转向民主化和民主转型,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中都蕴含着某种知识的霸权。按照西方学者的表述,民主化和民主转型都是指一种从非民主政治(权威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的过程。而且,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界定来看,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需要向民主转型的权威主义国家。[9]所以,按照这一思路,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差等制度。因此,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表述,实际上也就接受了西方知识对中国制度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安排。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是西方比较政治学学科最发达的国家,而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则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服务,即通过政治知识的传播,确立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模式的尊崇地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的一些比较政治学者长期接受美国政府部门(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这种资助使其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一定要发展自己的比较政治学,要找到客观反映中国问题和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议题,并在这些议题的基础上设计符合其特征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当然,这里的议题设计要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普遍性体现为,多数问题是共通的,在西方政治学中出现的一些议题同样也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问题。特殊性则体现在,西方的比较政治学往往在其价值的引导下偏向某些特殊性的问题,如前述的民主转型研究。换言之,在议题的排序上会更多产生特殊性的问题。
具体而言,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议题构建需要在以下方面更为努力:
第一,要重视西方比较政治学忽视的反映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现状的问题和概念。譬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政局动荡、国家分裂、军人干政、政党虚弱、种族屠杀、民族冲突等问题或者存在可能陷入这些问题的危险。因此,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领域或概念便显得尤为重要。譬如,国家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国家能力较弱,它就很难整合资源进行有效的现代化,也容易被一些地方力量所左右。国家能力是内蕴于国家自身的本质性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分析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范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与未来发展态势。[10]国家能力应该包括国家整合能力、国家动员能力和国家制度化能力等三个方面。国家整合能力包括将各民族利益、各地方利益、各部门利益整合进国家体制中的能力。这一能力的虚弱将会导致民族冲突严重、地方保护横行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国家动员能力则包括平时的常规动员能力和紧急情势下的非常规动员能力两种。紧急情势是对国家动员能力的特殊考验,也是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和政治不稳定的重要诱发性原因。国家制度化能力是指国家将政党、公民社团以及公民个体有效纳入政治体制的能力。如果一国的国家制度化能力不强,那么该国将会面临严重的街头政治抗争和民意的非制度化表达。
政党能力的概念也很重要。政党能力包括政党整合能力、政党动员能力和政党制度化能力三个方面。政党整合能力是指政党将社会意志整合进其党纲或政策主张的能力。如果政党整合能力不强,那么公民则会选择利益集团或其他代理人渠道进行意愿表达。政党动员能力是指政党获取社会支持的能力。如果政党动员能力较弱,那么政党将很难获得或巩固执政地位,而其他的社会集团如军人等就有可能成为执政集团。政党制度化能力是指政党作为一种渠道协助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如果政党制度化能力不强,那么公民将很容易用一些激烈的政治参与形式来进行表达。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其他社会集团都无法取代政党在现代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政党能力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在国家能力和政党能力之外,还有很多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例如,政治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如果一国处于政治上的失序状态,那么所有问题都将是空谈。另如,西方的比较政治学很少会研究政治回应性和政治效率,而这两个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政治回应性是指政治系统对公民意愿和需求的一种反应能力。如果政治系统缺乏回应性,那么公民将对政治系统缺乏认同感。政治效率是政治系统进行工作时所投入的资源与取得成效之间的比例关系。政治效率应该是评价政治系统的重要指标之一,尽管其不能成为唯一的指标。发展中国家都是后发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许多指标上的差距都很大,如果政治系统再不考虑政治效率的话,许多问题将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
第二,对一些重要表述进行概念创新。如前所述,民主转型是一个夹杂了西方意识形态的表述,同时,这个概念也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以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民主转型问题。民主转型概念的起点(威权体制)和终点(西方式自由民主体制)在中国案例中都不能适用。同时,民主仍然是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那应该怎么办?笔者的建议是,用“民主增效”的概念来替换“民主转型”。民主增效是民主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和改善的过程。民主增效这一概念蕴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民主更多是一种程度的问题。[11]将一些民主程度可能较低或者民主形态不同的政体归类为非民主国家,这种定性的归类是武断的,也是不客观的。二是民主制度存在一定的情境性。在某种情境下,某一民主制度的绩效可能较高,但是随着情境发生变化,这种民主制度的绩效可能下降,那么这时候这种民主制度就需要增效,即在新的情境下进行调整。
第三,要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议题重要性进行重新排序。在西方的比较政治学中,排序靠前的一些议题大致是民主化、选举、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政治透明度等。而在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中,排序靠前的议题应该是政治秩序、国家能力、政党能力和政治回应性等。如果缺乏政治秩序,那么所有的政治发展便是空谈。如果缺乏国家能力和政党能力,该政治系统在整合利益、动员社会和制度化参与等领域中的表现会很差,那么这个社会便会面临分配不均、动员无力、参与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政治回应性强调政治系统对公民意愿表达的及时反应,这种及时反应可以消弭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安定因素。
四、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
虽然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在宣称价值中立,但是这种价值中立却一直面临实践的困境。在一些意识形态特征较强的学科(如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中,这种所谓的价值中立则更多是一种神话。实际上,西方的比较政治学暗含了以下价值:西方的自由民主是目前人类政治发展的唯一的最佳形式,而且这种自由民主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即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采取这种形式就一定可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西方学者通常将这种价值界定为自由主义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非西方学者也接纳了这种观念,如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便主张这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12]这种自由主义观念的缺陷是,其会形成一种潜在的霸权效应。在这种自由主义的价值指导之下,西方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比较,而更多是霸权性地传播某些西方的主流观念。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应该主张一种“包容互鉴”的价值。十八大报告在“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部分,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三大精神。笔者认为,这一部分中关于“包容互鉴”的解释可作为中国比较政治学者开展研究时的指导性价值。十八大报告指出:“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1]在这一段表述中,前半段主要是对“包容”的解释,后半段则主要是对“互鉴”的解释。
具体来看,在这段表述中,“包容”有如下几层含义:第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要允许不同的制度存在,不能对不同的制度采取敌视、围堵和遏制的做法,这一点是“容”的本意,即先有“不同”然后才会有“容”。第二,要“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这种对自主选择的强调与中国一贯强调的主权原则,以及“外因需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辩证法思想是一致的。这一点与一些西方国家强调对他国制度的干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西方比较政治学中暗含的制度扩散逻辑也是不同的。第三,“包容”并不是反对“进步”,这一点可以从最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找到佐证。因为“进步”在现实中往往是由某些主导国家所定义的,所以“包容”要求的是,客观地看待“进步”,或者说要承认“进步”的多样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进步”并非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条道路,也并不是线形的。
“互鉴”有如下几层含义:一是主权平等。无论是大国或小国,富国或穷国,从主权上说,他们都是平等的。不能说“经济实力强就有话语权”,就可以干涉别国的政治制度。二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一个国家在某一方面的制度可能具有优势,而在另一些制度上的绩效则可能差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且,即便是一些治理失败的国家,也具有反向学习的价值。因此,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能一提到制度学习,马上就想到西方发达国家。三是“互”代表一种交互性和公共性。要有一种“人类”的观念和意识。这一点与“包”的含义也结合在一起。“包”意味着,即便一些国家的制度与我们不同,但是我们还是要与这些国家紧密交往,要有一种胸怀把他们包容起来,在“人类”的大观念和大视野下相互交往和相互学习。
从学理上来看,“包容共鉴”这一价值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价值相一致的。具体来看,要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体现“包容共鉴”这一价值,中国学者应该更多遵循如下原则:一是平等性原则,即各国主权平等,不能用综合国力或经济实力来过高或过低评价一国的制度;二是多元性原则,即尊重各国制度的多样性,不要用一种标准(特别是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或对自己有利的标准)来评价其他国家;三是自主性原则,即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其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不要以比较为工具干涉或影响他国的自主选择;四是内生性原则,即最佳的制度应该是其内部自身演化出来的,同时制度学习一定要以内化和地方化为基础;五是整体性原则,即要从人类文明的整体角度来看待各国的制度发展和制度实践,不要孤立地、片面地对某种制度进行评价;六是进步性原则,即要相信人类的制度文明是不断向前演进的,鼓励各国相互借鉴别国的优秀制度成果。以上这些原则一方面将“包容共鉴”的比较内涵充分展现出来,另一方面也较为集中和系统地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观点。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些原则的运用可以避免我们空洞地、抽象地讨论各国政治中的一些表面问题。
五、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次重要的研究浪潮。[13]总体而言,西方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偏重单因解释,即力图找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求同法和求异法是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而这两种方法的基本逻辑都是试图得到单因解释,即通过控制无关变量,找到关键性的实验变量与结果的一致性。[14]其二,更强调一种横向的、共时性的比较。西方许多比较政治学著作都是共时性比较的作品,最重要的代表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Gabriel A.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关于五国公民文化的研究。[15]其三,注重论证过程和研究设计,强调在论证中的逻辑严密和证据充分。符合规范的比较政治著作总是会先提出欲论证的分析假设,然后再介绍针对这一假设的研究设计以及选择相关案例的理由和方法,最后再运用严密的推理和翔实的资料来证实或证伪其最初提出的分析假设。其四,注重对概念进行操作化研究。在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一个概念被提出后,要首先确定可以将其操作化的指标,然后再运用这些指标对现实案例进行定性、定序、定距或定比的测量。譬如,国外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总是会强调这一概念的可测量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一些关于社会资本的比较政治研究也会将其结论建立在测量性比较的基础上。[16]
虽然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但是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一直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在西方的比较政治学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学者实际上也一直在讨论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所涉及的问题。中国学者会习惯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讨论比较政治问题。在研究中,中国学者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些关于比较的方法论特征:一是偏重多因解释。在分析某一现象的原因时,中国学者往往会给出一个多种因素的分析框架,而且还会在这些因素之间进行分层,如会区分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必然性原因和偶发性原因,同时也会在因素之间设定某种逻辑关系,如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以上这些特征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表现。二是更强调一种纵向的、历时性的比较。与西方学者强调共时性比较不同,中国学者更青睐历时性比较的方法。这一特点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表现,也与中国长期坚持主权原则有关。由于共时性比较往往涉及对各国目前状况的评价,因此中国学者会担心这种比较可能暗含了某种程度的主权干涉。三是更注重结论而非论证过程。中国学者在比较时会将主要篇幅分配在相同点和相异点的描述上,而在研究设计、选用案例理由以及论证支撑等方面往往会比较欠缺。因此,中国学者在阅读西方比较政治学著作时,往往不太看重其论证过程,而更为关注其观点和立场。四是注重概念的理念意义,而缺乏操作性研究。譬如,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中国后,多数研究仅仅用这一概念来论证信任的意义,而很少有研究对其进行操作性的测量。
当然,以上关于中西方比较方法特征的静态总结可能会面临动态变化的挑战。实际上,西方的比较方法也在出现一些新的调整。从本世纪初以来,西方比较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关于多因解释和历史分析的成果。譬如,美国学者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提出并讨论了多重并发原因(multiple conjunctural causation)的问题。[17]近年来,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些进展如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和模糊集合(Fuzzy Sets)等方法也都是主要围绕多因分析展开的。再如,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是近年来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兴起的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历史分析目前有两个最重要的分支发展:一种是中介性机制分析法,其尝试通过对中介性机制的发现,来找到自变量X与因变量Y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种时序分析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者注意观察各个事件在历史中的位置、持续时间以及先后顺序,并力图发现这些因素对特定结果的影响。西方比较政治学的这些新进展表明,多因解释和历史分析对于比较政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之前中国学者在比较时形成的方法特征有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
同时,客观而言,西方比较政治学中对论证过程和概念操作化的强调,是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要进一步学习的内容。对论证过程和研究设计的强调,可以使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比较政治中的客观规律,也有助于我们与世界各国交流这些研究成果。而对概念的操作化则有助于深化一些研究议题的讨论。通过确定指标和进行测量,一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准确度与适用性等相关情况就会清晰地展现出来。
整体来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可以在如下方面作出更多努力:第一,在整合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更为精细的多因解释框架。譬如,西方双层理论中运用了一些示逻辑关系的数学表达方式。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和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用*来表示“逻辑与”(logical AND),用+来表示“逻辑或”(logical OR)。[18]运用这些表达方式,整个多重因果关系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中国学者可以吸收和整合这些成果,以使我们使用的多因解释模型更为明晰有力。第二,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整合西方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成果。如前所述,西方比较历史分析发展了一些重要概念,这些概念有助于历史分析的精细化。在整合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充分地展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核心原则和重要观点。第三,对一些新的研究议题和概念要进行操作化和测量。譬如,在之前谈到的国家能力研究中,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比较研究方法,如确定国家能力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世界各国情况进行测量,以帮助其提高和改善国家治理状况。第四,在研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多进行一些跨国的实地调查研究。比较政治研究的跨情境性容易使得研究者戴着某种有色眼镜来观察他国,而实地考察则有助于消除研究者的偏见。实地考察所获得的材料也可以使得比较和论证过程更为客观和准确。
结语
之前,我们一直从制度学习的角度来看待比较政治学,认为比较政治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向西方学习。这一点有其重要性,但是却不完整。比较同样是深入了解自己的一种方法。因此,比较政治学的另一重要功用就是,在比较中树立自信。而且,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推动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中国经验在其他国家的实践,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制度有效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话语地位。简言之,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可以为中国的制度自信提供更有力的论证。
同时,多年以来,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蓄势待发中酝酿着新的发展。[19]之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一直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成果。这种借鉴和学习在学科建立之初非常必要,但是仅仅停留在借鉴的阶段也很难实现学科的成熟。应该说,中国比较政治学成熟的标志是有自己的议题、价值和方法,并在其基础之上产生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制度自信的提出给中国比较政治学创造了发展契机。理论和学科的发展建立在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之上。中国制度自信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经验总结的尝试。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经验究竟对自己是否有效,以及能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提供帮助,这便是中国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主题。在这样一个重大和鲜活的主题之上,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可以对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和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N].人民日报,2012-11-18.
[2]郭宝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
2008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为视角 [J].社会科学家,2012,(5). [3]李钢.师从中国的越南改革[J].改革与开放,2010,(5). [4]郭伟伟.古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十五年[J].上海党
史与党建,2009,(1).
[5]曹辛.俄罗斯在比较仔细地学习中国的经验[N].
南方周末,2007-10-25.
[6]胡佳恒.辛格改革镜鉴中国模式[N].财经时报,
2008-1-11.
[7]苑基荣,韦冬泽.“希望的大陆”要借鉴中国模式
[N].人民日报,2011-5-7.
[8]严强.比较政治研究的取向和方法[J].江海学刊,
1996,(4).
[9]Francis Fukuyama.China and East Asian Democra
cy:The Patterns of History[J].Journal of Democracy,2012,(23):14.
[10]霍建国.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前提审视[J].行政论坛,2012,(2).
[11]David Collier and Robert Adcock.Democracy and Dichotomies:A Pragmatic Approach to Choices about Concept[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1999,(2):561-562.
[1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4.
[13]高奇琦.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两次浪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4.
[14]GuyPeters.ComparativePolitics:Theoryand Method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29-33.
[15]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331.
[3]许耀桐.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N].北京日报,2008-09-09.
[4]赵耀.选人用人制度改革探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4).
[5]]蒯正明,陈华娟.中国共产党干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革路径探析[J].理论探讨,2011,(6).
[6]赵耀.选人用人制度科学化问题探讨[J].理论导刊,2012,(2).
[7]邹庆华,祝福恩.十八大背景下考核干部要摆正十对关系[J].行政论坛,2013,(2).
[8]黄卫成.选人用人要走好群众路线[J].党政论坛,2013,(11).
[9]范增玉.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N].人民日报,2007-06-25(9).
[10]李烈满.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J].学习论坛,2010,(6).
[11]李国良,李 玮.干部选用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成因及对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12]陈景春.干部选任制度改革问题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1,(3).
[13]薛冰.创新与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若干思考[J].求知,2011,(3).
[14]陈存根.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践看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J].党建研究,2008,(11).Press,1963.
(责任编辑吴兴国)
[16]Lauren M.Mclaren and Vanessa A.Baird.Of Time and Causality:A Simple Test of the Requi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in Making Democracy Work in I-taly[J].Political Studies,2006,(54):889-897.
[17]Charles C.Ragin.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Strategies [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20.
[18]Gary Goertz and James Mohoney.Two-level Theories and Fuzzy-set Analysis[J].Sociological Methods&Research,2005,(33):502.
[19]杨光斌.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学展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30.
(责任编辑吴兴国)
D6
A
1001-862X(2015)02-0055-00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野中的民主发展路径研究”(14BZZ002);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项目“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间互动机制的国际比较研究”(13SG50);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项目“国家参与全球治理(SPIGG)指数的指标与测量”(201473)
高奇琦(1981—),山西长治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