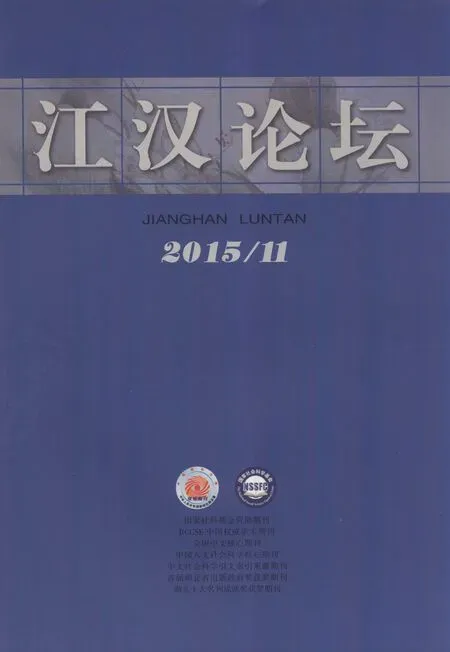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的发展策略*
杨彬
文学
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的发展策略*
杨彬
在新媒体不断丰富直至进入全媒体时代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小说采取了追求民族意识、张扬宗教意识、少数民族思维写作、民族文化交融的平等视角等策略,克服了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发展的弊端,使得少数民族小说朝着生态化、心灵化、内涵化的方向发展,为少数民族小说在全媒体时代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发展策略
一
1950—1970年代,是以纸媒为主的时代,在广播电视都不普及的情况下,作为纸质媒体翘楚的小说文本是主要媒体形式之一。在这个阶段,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展示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少数民族小说在当时政治化的格局下,采取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方法,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效果。他们在作品中大量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象和景色、穿插汉语直译的少数民族语言、塑造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人物。虽然此阶段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只是这些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生活的点缀,是阶级斗争故事展开的少数民族环境,是小说政治主题的少数民族色彩渲染,此阶段少数民族的风情和文化没有成为当时少数民族小说的主角,但是,少数民族小说的这些努力还是让全国读者感受到了清新的少数民族特色,为中国当代文学添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异样的风景。因此,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方法成为了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最普遍和最常用的方法。
在1950—197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主要采取如下具体方法来展示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第一,将当时的显性叙事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将当时主要的叙事类型:革命斗争叙事、土地改革叙事、农业合作化运动叙事、新人新风尚叙事、歌颂新婚姻法叙事等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叙事设置扩大了当代文学的内涵和描写领域,同时也凸显了少数民族小说的陌生化特色。第二,凸显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在作品中描写少数民族风景物象、风情风俗,从而让读者得到陌生化的美的享受,同时在自然风光中注入浓郁的民族情感。少数民族地区自然风光雄伟、辽阔、清新、奇峻,少数民族风俗新奇、陌生、美好、独特,成为那个时代少数民族小说最亮的看点。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大量描写蒙古族牧民的风俗习惯,展示蒙古族的草原文化。和同时代汉族的红色经典不同之处在于,作品在一个充满硝烟氛围的阶级斗争中,描写了蒙古草原上颇具自然美和浪漫气质的蒙古族特色。
但是进入全媒体时代后,少数民族的地理环境、少数民族自然风光、少数民族物象、少数民族风俗特色不再是遥不可及难以了解的陌生化对象,在任何一个媒体中,都有关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风光、风俗风情的介绍,尤其是网络,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因此少数民族小说还是采取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方法,已难以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何况,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方法本身就具有背景化、表面化的缺点。因此,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必须采取新的方法、新的策略,才能在全媒体时代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
进入1980年代后,媒体形式逐渐多元化,电视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媒体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小说适应时代发展,采取一系列策略,开始新的选择。
第一,追求少数民族意识。在1980年代初,少数民族小说克服以往只是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弊端,开始由外及里凸显少数民族意识。这种对少数民族意识的自觉追求,将少数民族小说从学习汉族文学、靠近汉族文学的框架中提升到追求少数民族的独立品格的状态中,将以往风俗风情变成文化主体,成为具有少数民族文化风尚的生活文化,从表层描写到具有文化底蕴的深层挖掘,从罗列各种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到将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审美化。其突出代表是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鄂温克族是东北的狩猎民族,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自己的以打猎为主的生活状态。乌热尔图以深沉忧患的笔触,描写鄂温克族的狩猎生活、民族意识以及那种鄂温克族特有的人和自然、人和动物相依相生的关系。乌热尔图以鄂温克族的文化心理选择题材、塑造人物、推动故事情节,也用鄂温克族的意识看待和解释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用鄂温克族意识建构独特的鄂温克族文学特质。乌热尔图具有强烈的鄂温克族民族意识,他在自己的民族中成长,他以自己的民族而自豪。鄂温克族特有的狩猎文化、原始文化是乌热尔图创作的源泉,鄂温克族特有的对自然敬畏、对森林热爱、和动物相依相生的观点是乌热尔图的生命本能,是乌热尔图的民族文化心理。乌热尔图说:“我力求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能够感觉到我的民族的脉搏的跳动,让他们透视出这脉搏里流动的血珠,分辨出那与绝大多数人相同,但又微有差异的血质。”①这种独特的民族意识,使得乌热尔图努力地追寻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意蕴和民族意识,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独特的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文化经验作为自己创作的土壤。
1980年代的少数民族小说实现了质的飞跃。虽然这种超越,还只是部分作家的追求。但是给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意义是非凡的,它直接开启了199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张扬民族意识、张扬宗教意识、认同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表达少数民族族群体验等等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独立品格。这种主体性的追求,使得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开始成为不可替代、难以逾越、具有独一无二的品格和价值的文学类型。
第二,追索民族文化之根。1985年前后,中国文坛出现寻根文学思潮。这个以汉族文学为创作主体的文学思潮,其主要特征是运用文化主题取代政治主题,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寻找中华民族之根。其目的是为了抵抗现代化过程中人欲横流、灵魂漂浮、与自然关系紧张等等弊端。这种状态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作家那里,具有更真切的感受,现代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更加明显。因此在寻根文学思潮中,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加入其中,开始少数民族小说的寻根之旅。少数民族小说加入寻根文学思潮,和以往追随主流文学思潮不同,不是一味地对主流思潮的追赶和靠近,而是汇入到寻根文学思潮中,成为寻根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少数民族的寻根文学占了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半壁江山。
1989年,经过长时期的军旅小说创作之后,满族的血脉牵引着朱春雨走向母族,开始把目光回观到自己的母族——满族的历史文化中,创作了长篇小说《血菩提》,开始他的民族寻根之旅。朱春雨是满族人,他对自己的母族有天然的基于血缘的亲近,因此他用充满崇敬的情感去描写他的民族,这是民族的认同和血缘的追寻。巴拉人——这支因为逃避女真人杀戮而藏匿在深山老林、无拘无束地生活在长白山的民族的生活状态、历史脉络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作者重点描写的部分。作者通过这部分描写,追寻满族巴拉人的历史脉络、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图腾崇拜以及他们的生命意识。那对巴拉人的历史文化的追寻,那对巴拉人文化心灵的描绘,使得该作品具有满族的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的价值。
扎西达娃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是一个地道的藏人,对藏族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扎西达娃是第一个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方法描写西藏生活的藏族作家,他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去西藏的路上》等小说,具有比较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他的作品将西藏神秘的藏传佛教和原始苯教文化、浓郁的藏族风情、纯净高远的高原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将神话、历史、魔幻、虚构、过去、未来等因素杂糅在一起,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西藏世界描写得亦真亦幻。有人将魔幻现实主义分为主观魔幻现实主义和客观魔幻现实主义,比如有人就称莫言为主观魔幻现实主义,因为那种亦真亦幻的特色,是作家极具主观化的外现。而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被称为客观魔幻现实主义,因为藏族文化原本就有魔幻的一面。扎西达娃并不是将魔幻色彩主观化,然后强加在他的藏族小说中,而是在藏族文化的内核中,找到藏族文化内在的文化心理和深层密码。扎西达娃采用象征和隐喻等手法,运用现代手法观照西藏的历史文化、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在魔幻而清晰的氛围中,追寻母族的文化之根。
第三,正面表达宗教意识。很多少数民族具有宗教意识,但是在以往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宗教意识表达很少。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宗教是欺骗人民的工具。在以往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一般把宗教和政治等同起来,认为如果政治是反动的,宗教也是反动的,而且主要描写宗教中摧残人性的消极因素,将宗教作为封建迷信或者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宗教要么不涉及,要么采取批判的态度,没有从少数民族主体的角度去描写宗教,没有去描写和宗教水乳交融的少数民族的独特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
进入新时期以后,少数民族作家开始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方面思考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审美追求,因此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小说不再回避宗教问题,而是将宗教作为本民族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进行观照。
对少数民族宗教意识全面地正面地表达,当是1989年著名作家霍达发表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用什么态度描写宗教意识,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一个重要问题。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以审美的姿态、以尊敬的笔触描写伊斯兰教信仰。作品将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结合起来,歌颂一个民族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的品德,并将民族的信仰和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从人性、审美等角度描写回族的宗教信仰,为199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张扬宗教意识的特点奠定了基础。作者站在回族的主体立场上,描写汉文化和回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描写伊斯兰文化和汉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协调互补和多元宽容,试图在两种文化心理的矛盾中,找到一种能包容两种文化的途径。
从这些少数民族的小说的方法来看,少数民族作家在媒体越来越丰富的新媒体时代,采用追求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寻找少数民族文化之根等手法,逐渐深入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处,弥补了一般媒体有关少数民族文化描写的表面化的缺陷。从人性角度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深入到人性的深度,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审美观照,是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的写作策略。
三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新媒体越来越丰富,媒体从单一媒体时代进入了全媒体时代。在这个时期,小说必须进一步体现独特性才能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以更加鲜明和强烈的姿态张扬少数民族意识,与1980年代相比,这种意识不是逐渐觉醒和趋于自觉,而是已经成熟。其主要策略是张扬少数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采用少数民族思维写作。
第一,强烈张扬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从文化角度描写少数民族生活,强烈张扬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是199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采取的主要策略。回族作家张承志在1991年发表了他著名的小说《心灵史》,这是张承志在作品中张扬回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最强烈的作品。张承志大都不采取描写风俗风情的方法来表现回族文学特色,他一直以来都是以描写回族意识见长。张承志不是为回族而写作,而是作为回族来写作。他说:“我沉入了这片海。我变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诱惑是伟大的。我听着他们的故事;听着一个中国人怎样为着一份心灵的纯净,居然敢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五十万人的动人故事。在以苟活为本色的中国人中,我居然闯进了一个牺牲者集团,我感到彻骨的震惊。”②张承志把自己作为一个哲合忍耶的成员,用鲜明的回族意识、明确的哲合忍耶思维写作《心灵史》,这是张承志张扬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最强烈的写作。少数民族小说到《心灵史》这里,经历了从外在描写到内在表现再深入到民族、宗教意识骨髓的真切感受的巨大变化,进入到真正具有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写作阶段。
第二,采取少数民族神话思维写作。采用少数民族思维写作是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小说最优特的策略。这种只有少数民族才具有的神话思维,使得少数民族小说具有了真正的少数民族思维。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1990年代发表了《你让我顺水漂流》、《丛林幽幽》、《萨满,我们的萨满》等小说,采用鄂温克神话思维写作。鄂温克族人和动物合二为一的思维是不以人为主体、人和动物平等的思维。在《丛林幽幽》中,乌热尔图采用鄂温克族独有的熊和人通婚以及熊是鄂温克族祖先的神话思维,将动物视为同类。对鹿的描写也是如此,鹿是鄂温克族人的朋友,是和人具有一样思维和情感的朋友,他们的忧伤就是人的忧伤。鄂温克族老人认为只有鹿的声音才是他心目中的歌。鄂温克人对自然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包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动物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在于鄂温克族人从不认为人可以改变自然,他们认为人只能在自然中获得有限的东西,不能按照自己的欲望去贪婪地索取。这在他们的狩猎生活中对动物的态度可以看出来。鄂温克人是个狩猎民族,他们对待动物有着今天看来是可持续发展的思维。他们为了生存必须猎杀熊,但是他们又敬仰熊、畏惧熊,认为熊是他们的祖先,因此熊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棕色的熊》描写了鄂温克族人对熊的敬畏心理,“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父辈们对熊的敬仰和畏惧之情:宰杀了熊后,猎手都很伤心。吃熊肉时,要学乌鸦叫,说明不是人在吃熊肉,而是乌鸦在吃。熊死后要把熊的骨架放到高高的树上安葬。“我”15岁时,独自拿起猎枪去打猎,在与熊的搏斗中,经历了紧张和恐惧,明白了祖祖辈辈敬畏熊的原因。鄂温克族人从不直接称呼熊的名字,而是称作祖父(鄂温克族语言叫“合克”),或者称作祖母(鄂温克族语言叫“额沃”),或者直接称作熊神(鄂温克族语言叫“阿米坎”)。人与熊的关系如此,人和其他动物的关系也是如此,比如《七岔犄角的公鹿》中的少年敬畏公鹿的彪悍、勇猛、力量,敬畏公鹿勇斗饿狼的勇敢,把公鹿当成心目中的英雄。鄂温克族猎人在和鹿的较量中,学习鹿的美好品德,和鹿共享山林。这是鄂温克族特有的思维,这种敬畏自然、敬畏动物的思维,在当今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人类失去对自然、对人类的朋友的敬畏之心而对自然疯狂掠取、对野生动物疯狂屠杀而破坏生态平衡之后,人必然给人类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因此人们通过阅读乌热尔图的小说,应该得到启发和警醒。萨满是通神之人,她能将鄂温克族人的历史、心灵、愿望融为一体,能表达鄂温克族人神秘的心灵以及神秘的文化。乌热尔图在他的作品中采用萨满的思维描写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和心灵,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祖先的热爱之情。萨满的内涵就是鄂温克族人精神和文化的内涵。在很多作品中,乌热尔图将萨满作为叙述者、回忆者,萨满用神性思维描述事物;在外人看来神秘的不可知的事情,在萨满看来却是实际存在的。这是鄂温克族人特有的神性思维。《你让我顺水漂流》中的卡道布和《萨满,我们的萨满》中的达老非,这两位萨满都具有超越常人的神性,能和神灵通话,甚至能预知自己的死亡方式。乌热尔图浓墨重彩地描写萨满,是替日渐失去家园的鄂温克族人表达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作品具有忧伤之感。在《你让我顺水漂流》中,作者就用这种忧伤和忧患的情感描写萨满卡道布,这是鄂温克最后一位萨满。他以无比忧伤的口吻预言森林的火灾,那是他对鄂温克族人赖以生存的森林的巨大忧伤之感,对即将被大火毁灭家园的预示和悲伤。他还预言自己将死在“我”的枪口下,因为已没有可以树葬的巨大树木,于是嘱咐“我”将他的尸体投入河中,让他顺水漂流,从而表达鄂温克族人即将失去森林、失去狩猎生活方式、失去家园的令人堪忧的前景。
四
新世纪以来我们真正进入全媒体时代,此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入到深层次和全面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作家不仅面临着全媒体的挑战,还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挑战。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出现碰撞、交融的趋势。因此新世纪的少数民族小说不能仅仅像1990年代以前那样,只是单一地张扬少数民族意识,而是要探讨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交融、少数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的深层次问题;不再只是表达少数民族文化融于汉族文化、西方文化的努力,而是开始采用双重视角,在不断融合的文化中坚持少数民族文化,并在少数民族小说中表现人类共同的审美特性和审美经验。
第一,现代化进程中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民族也在逐渐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民族普遍和其他民族交往,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化逐渐向汉族文化、西方文化学习并有逐渐融合的趋势,这是一个令少数民族作家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过程。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希望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保持自己独异的特色;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又希望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接受先进文化,促使少数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世界文化接轨。这是一个惶惑、矛盾却又充满希望的时代。在新世纪,少数民族小说在民族现代化和民族融合过程中坚守少数民族文化的追求更加明显。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小说就是力图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典范。他的生态小说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极力表现蒙古族独特的生态意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对草原不断攫取,蒙古草原因此不断沙化。作为出生在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作家,对这种现状心急如焚,于是他拿起笔来创作“沙漠小说”和“动物小说”。蒙古人和草原、动物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草原被破坏,相生相伴的动物就会遭殃;动物遭殃,人类也会遭殃。他的小说《大漠魂》、《沙狼》、《银狐》、《大漠狼孩》表达对草原不断沙化的忧患意识。作为蒙古族作家,他的描写对象是蒙古草原上的人和动物,他基于蒙古族对自然、对草原、对大漠、对动物的热爱,展示蒙古族特有的生态意识。蒙古人民对动物充满爱,这种爱是蒙古族特有的悲天悯人的爱,是蒙古族信仰佛教、喇嘛教、萨满教形成的独特意识,也是蒙古族世世代代和草原和动物和大漠和谐关系的表现。郭雪波用蒙古人意识描写动物、描写沙漠、描写草原,表达对人类破坏草原、掠杀动物的状态强烈的忧患意识。
土家族作家叶梅的《最后的土司》则将两种文化碰撞和交融描写得惊心动魄。覃尧是龙船河的最后一代土司,李安是闯入土家地区的汉族人,两种文化的冲突导致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虽然作品尽量客观地描写文化碰撞给彼此带来的伤害和影响,但是作为土家族作家的叶梅在情感上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土家族文化。从作品看,土司覃尧比李安要爽直、宽厚得多;对女人,土司覃尧比李安也要好得多。李安对伍娘的折磨以及最后带走孩子导致伍娘之死,主要是汉族文化在李安身上的表现。虽然两人对造成伍娘之死都负有责任,但从作品可以看出作者情感倾向于土司覃尧。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在描写文化碰撞和民族融合中,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追求。
第二,民族文化交融中对平等意识的追求。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交融现象更加突出,在民族交融过程中,采取什么态度和观点是当今一个重要问题。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平等意识的追求。
阿来在他著名的文章《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中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表明他穿行于藏汉文化之间的状态。他对于藏汉文化的交汇、碰撞没有如批评家所说的那种焦虑症,因为他认为:“在我的意识中,文学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的、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的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这种众多声音的汇聚,最终会相当和谐、相当壮美地带着我们心中的诗意,我们不愿沉沦的情感直达天庭。”③阿来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待藏汉文化的平等、包容的心态,这也是他运用双重文化视角创作《尘埃落定》的缘由。《尘埃落定》超越以往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新的特点,就是阿来在作品中进行了有目的的双重平等的文化视角的写作。阿来虽然是回藏血统,但是他受到的文化影响却是藏汉文化影响。他从小在藏区长大,后来考上中专后系统地学习了汉语,因此藏汉文化都对阿来有很深的影响。《尘埃落定》具有以藏族为主的藏汉文化的融合的特色,是一部用藏汉双重文化视角写作的藏族汉语小说。阿来说:“‘我’用汉文写作,可汉文却不是‘我’的母语,而是‘我’的外语。不过当‘我’使用汉文时,却能比一些汉族作家更能感受到汉文的美。”④
《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具有藏汉文化交融特色。傻子这个形象是藏汉文化交融的典范,藏、汉优秀文化和谐交融,形成了这个具有人类共性的独特形象。首先,傻子形象塑造受到藏族机智人物阿古顿巴的影响。其次,傻子具有汉族文化中老庄哲学的大智若愚的内涵。再次,傻子的形象包含汉族儒家文化的特色。阿来要表达的是各个民族具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作为人类有很多方面是有共通性的,从傻子的形象可以看出,他首先是一个藏人,一个具有鲜明藏族文化特色的人物,但又是具有汉族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特色的人,这些优秀的人类文化特色集中在傻子身上,说明了人类的共通性。阿来穿行在异质文化之间,在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基础上,用平等视角看待各种文化,同时探讨了人类的共同特性。
注释:
①乌热尔图:《写在〈七岔犄角的公鹿〉获奖后》,《民族文学》1983年第5期。
②张承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③④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中国文化报》2001年5月10日。
(责任编辑刘保昌)
I206.7
A
1003-854X(2015)11-0112-05
杨彬,女,1965年生,湖北恩施人,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项目编号:12BZW09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