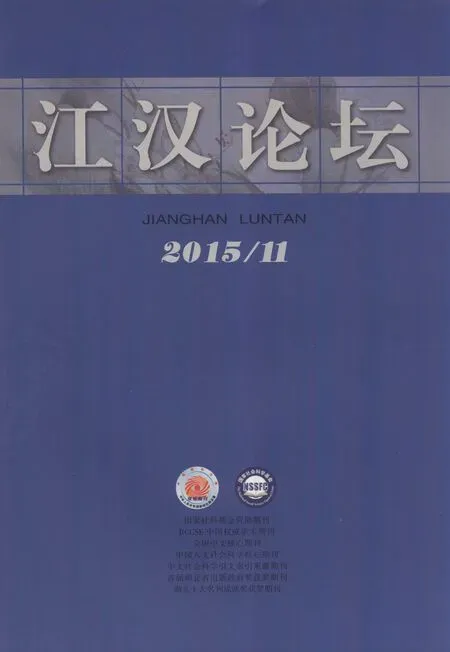论沙龙
冯黎明
文学
论沙龙
冯黎明
西方学者视沙龙为现代公共领域的源头,这是因为沙龙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学功能,即它的双重隔离功能与双重聚合功能。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沙龙,其一是专业性沙龙,其二是广场性沙龙。前者将国家权力以及乌合之众阻隔在专业活动之外,后者则将商谈伦理投向社会实践。沙龙最重要的社会学属性体现为一种谈论方式,这种谈论方式具有自治性、公民性和公共性的特质。沙龙的生存状态是公民社会的表现,也是国家治理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
沙龙;公共领域;谈论;商谈伦理
“沙龙”(Salong)这一名称,总是在人们眼前描绘出一场《雅典学院》(拉斐尔)般的镜像:一群高贵的专业人士相聚于雅致的大厅,上演着语言的盛宴。沙龙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鸿儒们的好去处,它在文化山上远眺红尘自娱自乐。但是在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等现代学人眼中,沙龙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政治革命的角色,因为它是公共领域的最为重要的源头,而正是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和扩展,公民社会以及民主政治才得以成为现代生活世界的一般形态。
一、在家庭和城邦之间
Salong这个词的原意为“客厅”,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客厅。被特称为“沙龙”的客厅跟家庭成员私密性活动的室内空间不同,它是为家庭以外的社会性访客的聚集而特设的室内空间,而且它的功能不仅仅停留在“接待来访客人”这一意义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客厅的沙龙构建了一片社会交往的空间,因为沙龙里出现的人员和事务,其存在和出场的意义都超出了家庭或者个人的范畴,所以,沙龙里冠盖云集之时,也就是沙龙“公共领域”的社会学属性得以彰显的时刻。汉娜·阿伦特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兴起之前是没有公共领域的,“将一切人类活动引入私人领域,并依照家庭的模型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当时城市里的各种具有典型中世纪特点的行业组织,如行会、手工业行会都采取这种做法,就连早期的商社也不例外”①。于是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与城邦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直面相对的关系,其中缺失着公共领域作为中介性的空间来构建私人和城邦之间的协商性政治关系。如此一来,城邦便可以凭借政治威权直接控制私人以获得强大的专制力量,而私人也可以扩展家族势力控制城邦以形成集权政制——其实中国古代社会也具有这些特点。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兴起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公共领域的出现。公共领域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介性地带,它将个人带出私人状态而进入依照普遍规则展开社会实践的公共状态。在公共领域里,个人平等地、真实地依照一般规则进行交往,因而它缓解了个人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建构起一种协商性的政治关系。汉娜·阿伦特声称:“我们和卢梭一道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种要求……”②这种社会性的要求就是个人按照普遍规则平等交往。
哈贝马斯这样界定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原则同公共权力展开讨论。”③这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在私人和城邦之间营造了一个商谈性质的社会空间,城邦对个人的控制以及个人对城邦的抵抗,都必须借助于公共领域的商谈伦理或者议事规则来实现。这里就蕴含着公共领域作为通向协商政治的路径得以形成的功能性机制。哈贝马斯发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源头就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而且是在所谓文学沙龙里。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沙龙“是宫廷的精神遗产”,但是早期的贵族庆典和宫廷宴会只是形成了社交聚会的高雅气氛而已,18世纪的室内沙龙则体现了“城市”取代“宫廷”成为文化生活中心的变化。室内沙龙的出席者既有城市贵族也有市民出身的文化精英,二者联手制造了一个独立于宫廷的谈论空间,而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则标志着资产阶级开始构建独立于贵族专制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实践场域。
哈贝马斯说:“‘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心;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冲突中,城市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的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过渡的桥梁。”④这也就是说,以谈论文学艺术为主题的沙龙孕育出了资产阶级与宫廷贵族之间文化政治对立和争论的公共空间。沙龙的社会学功能不仅仅止于“社交”,更在于它构造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一条交往通道,避免了古典专制社会中的那种城邦直接控制个人或者个人操控城邦的情况,因为在公共领域的调控机制作用下,国家和个人都必须遵循一种建立在“商谈伦理”基础上的普遍规则,这些规则最后可能成长为律法,即成长为一种限定国家和个人行为准则的“元规则”。
沙龙之所以能够孕育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是因为沙龙具有双重隔离和双重聚合的社会行动机制。所谓双重隔离机制,即沙龙一方面在自身与国家之间设立隔离带以保持其“自组织”的独立性,避免成为国家的附庸抑或敌人;另一方面,沙龙又在自身的公共性结构与个人之间设立隔离带以保持商谈规则的普适性,避免被强势个人操控或者被“乌合之众”纠缠。借助于这两种隔离机制,沙龙显示出自主和宽容两种伦理特质,而这两种伦理特质恰恰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所必需的禀赋。沙龙的双重聚合机制指的是,一方面它将私人生活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沟通起来,因而私人生活空间得以获得社会性的实践功能,即“室内”的生活具有了“广场”属性;另一方面沙龙又将个人的言说与社会身份的交往结合起来,构造出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商谈方式,即公民身份的“谈论者”依照交往理性展开“谈论”,在“间性”的话语活动中获得主体位置。沙龙的这种双重隔离和双重聚合的机制塑造了现代都市的社交场域,该场域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性结构,即它以个人身份与普遍规则相互融通的方式彰显出民主政治的商谈伦理。
二、从专业领域到公共空间
大多数关于沙龙的论述都指向“文艺沙龙”。国内学者初具昊论述了作为绘画艺术活动(讨论、展览)的沙龙这一专业性的社会实践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性⑤,明显受到了哈贝马斯以“文学公共领域”为公共领域之起源的观点的启迪。哈贝马斯认为,咖啡馆和沙龙在17世纪的欧洲国家出现并兴盛,“它们都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⑥。早期的沙龙大都是文人雅士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人士们谈论文艺的“文学沙龙”,后来它们逐渐向具有“广场”意义的政治批评中心转化,哈贝马斯以法、德等国家在17—18世纪的城市社会生活情况为例对此一观点进行了论证。不过后来文艺沙龙一类专业性的沙龙并未完全被政治批评中心性质的沙龙取代,比如当我们谈论“沙龙”时,脑海里大都浮现出文艺精英们的小众聚会以及他们天马行空般高谈阔论的图景。文艺沙龙或许可以视作公共领域的雏形,但是这类专业性沙龙对于公共领域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起源”或者“孕育”,它本身具有的公共性需要从另一个维度上来理解,即文学沙龙使得专业性的艺术问题成为广场上的一个批判性谈论的焦点。事实上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沙龙:一种以文艺沙龙为代表,可以称作专业性沙龙;另一种以政治沙龙为代表,可以称作广场性沙龙。广场性沙龙固然有着更强的公共性,但是它并不能完全取代专业性沙龙,因为两种沙龙各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
专业性沙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的沙龙画展。美国学者托马斯·克劳在《18世纪的巴黎:画家与公共生活》一书中曾经完整地描述过18世纪法国的沙龙艺术。根据托马斯·克劳的描述,沙龙画家大都来自学院,无论作为沙龙画家还是作为学院画家,他们都竭力表现一种高雅的宫廷艺术趣味和细致的学院技法。在一种浓郁的艺术气氛的聚会和谈论中,王权的政治诉求、蓬巴杜尔夫人的贵族趣味以及画家们的专业主义的身份确证,几者似乎取得了一致,这种一致的结果就是沙龙作为一项展览制度的设立。1699年在卢浮宫方形大厅举办的展览使得“沙龙”作为展览的名称而确定下来。1737年之后,沙龙展被定为逢奇数年举办,圣路易节(8月25日)开幕,持续五周左右。1903年,一批艺术家为对抗官方对艺术的干涉,以民间方式筹办了“秋季沙龙”。秋季沙龙后来成为了一批又一批现代艺术家走向世界的舞台。作为展览体制的沙龙跟作为商谈聚会的沙龙有着重要的差异,但是就其参与方式而言,它仍然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它把专业领域的个人经验推向了公众,同时它有利于维护专业领域的技术性自律而避免其遭遇权力的侵入。尽管在路易十四的“绝对国家”下生存以至于逐渐被权力改造成为一种展览体制,但是早期的绘画艺术沙龙在维护艺术的自主性方面还是有所作为的。
专业性沙龙最重要的社会学功能在于构建了特定场域(比如艺术场)在社会实践中的自主性“相位”。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1992)一书中细致地描述过“文学沙龙”参与构建自主性“文学场”的过程。专业性沙龙以“专业主义”或者职业身份来划定特定领域的排他性边界,让专业人士以自身独有的谈论方式表达一种场域性质的思想或知识,比如维也纳小组的哲学聚会、格林尼治村的艺术家聚会等等,这些沙龙性聚会拒绝广场化,他们以专业身份的宣示为荣耀。专业人士们借助于专业性沙龙维护着自己的身份,抵抗着权力或者资本对专业领域的殖民,并且推动自身专业的技术进步。通过场域的“自我封闭”来达到身份的“自我确证”,这是专业性沙龙显示其公共性的基本策略。波德莱尔以“沙龙”为题撰写的那些年度文化评论,总是表明着一种审美自律的价值立场,这种“脱俗”的立场恰恰保证了诗人的审美威权。专业性沙龙在历史上还曾有过一个典型,那就是休姆在1908年主持的“诗人俱乐部”。这个每周一次的诗人聚餐会(地点一般是在伦敦的“埃菲尔塔”餐馆)以谈论诗歌为主题,显示出强烈的专业主义特色。正是在参与“诗人俱乐部”活动之后,埃兹拉·庞德创造出意象派诗歌理论,为诗歌在现代生活中不可重复的地位做了一次合法性的学理论证实验。1980年代的中国,这种专业性的沙龙也曾遍布大学和城市文化区,而且那时的沙龙尤其热衷于从所谓场域自主性的视界展开谈论,如文艺沙龙谈论“艺术规律”、美学沙龙谈论“美的本质”、哲学沙龙谈论“人性及其异化”,等等。这些专业性的沙龙谈论,其真正的动机在于摆脱政治权力对专业领域的长期殖民,通过重新确证专业领域的所谓特殊规律而彰显专业人士自身在公共生活中的自主性地位。
比较起专业性沙龙来,所谓“广场性沙龙”则天然地具备了公共领域的属性。广场性沙龙本身就是一场公共性质的社会活动,只是这种活动以小规模熟人圈子的方式在室内空间里开展而已。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专业性的文学沙龙只是沙龙的起源,真正显示出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的乃是这种广场性的沙龙。由历史现象观之,构成现代生活之公共领域的最重要因素是社团,而社团则多半是以广场性沙龙为基础的。广场性沙龙的参与者身份常常是多元的,不像专业性沙龙那样唯有具备专门技能的人方可参与,因此广场性沙龙谈论的话题和谈论的方式也呈现为多元化特性,跟专业性沙龙的单一话题有着明显的差异。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广场性沙龙虽然话题关涉所有社会实践场域,包括政治等国家事务,但是它仍然只是精英人士的聚会,只是跟餐饮、社交等有关的民间活动,既非宫廷政治阴谋亦非街头民众运动,其意义仅仅限于有关公共事务的谈论,而并不能在法律意义上被视为改变秩序或规则的社会行动。
广场性沙龙的典范是所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这个人文知识分子群体活动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地区,也就是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伦敦大学等所在的中心文化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活动自1904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此地区安家开始,直到1941年伍尔夫自杀为止,前后持续了将近40年时间。该集团的参与者有文学家、艺术家、评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有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以及锡德尼·特纳这样的政府官员。这帮人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亦多有差异,其中有文化守成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正是因为身份、专业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始终体现着一种“广场”的性质,其谈论方式一直就是依照规则的自由表达。同时也正是因为它超越了专业视域的限制,所以这一沙龙文化圈的社会诉求并不限于推行某种专业范式,而是将谈论的话题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实践,他们展现出一种对社会或者国家事务的关切和思索,如西方学者所言:“布鲁姆斯伯里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处于对现存权利结构的抗争之中,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⑦由此我们就看到,广场性沙龙将一种“批判性”的谈论投向全部公共事务,彰显了公共领域构建“公民社会”的功能。民国时代著名的“太太客厅”,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家里的客厅聚会,也有些类似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只是这一沙龙尚未发展成熟就被灾难性历史事件给掐断了。
三、沙龙式谈论与商谈伦理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沙龙最为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特有的那种谈论的方式。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人员聚集、餐饮、仪式等等在沙龙里都不是主体,真正造就了沙龙之独特气质的就是那种依照规则的自由谈论。哈贝马斯和阿伦特之所以把沙龙视为公共领域的源头,其原因就是他们在沙龙的谈论方式中发现了公民社会必有的公共性。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在结构上类似于沙龙,而且,作为民主制度之标志的协商政治,在结构上也类似于沙龙。
沙龙首先是一种自治性的社会谈论方式。所谓“自治性的谈论”,意味着沙龙的谈论具有自发性或自组织性的特征。沙龙不是依据国家意志设立的政教论坛,它以“NGO”的存在形式向国家表明自己的民间身份。无论从参与者的身份及其参与谈论的动机还是从参与者聚集的方式以及谈论话题的选择来看,沙龙都显示出一种“自发生成”的机制。沙龙一旦形成,它就表现为一个松散的自治性民间社会组织,这一组织以自由聚会、自由谈论为其生存之道。它跟政府机构并无瓜葛,它甚至对国家权力的介入极为警觉,因为国家权力的介入将取消沙龙的自治性,而自治性恰恰又是沙龙生存的根本。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从伍尔夫姐妹在布鲁姆斯伯里区才登广场46号安家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离世,姐妹俩的客厅里经常是满座高朋鸿儒谈笑,长达几十年的知识精英聚会的沙龙自始至终没有受到外部的权力介入,集团成员完全出于自愿参与活动,谈论话题亦非机构拟定,呈现出典型的自组织的特性。因而其中发表的言论也可以确定为谈论者社会身份的真实表达。17世纪法国的艺术沙龙,后来由于官方的介入而失去了沙龙的本色,逐渐转变为一个展览体制,其自由谈论的沙龙属性也逐渐淡化以至于消失。沙龙的自组织属性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使沙龙发展成为民间社团,而一旦成为社团,它在公共领域里的社会功能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当然,这不包括江湖帮派发展起来的所谓“社团”,如旧中国的“青帮”、“红帮”等,这些“匪帮”组织更多地体现着黑社会的性质,远非现代公共领域意义上的社团。
沙龙其次是一种公民性的谈论方式。所谓“公民性的谈论”,意味着沙龙的谈论者都是以公民身份出现在话语场之中。阿伦特说:“按照沙龙的规矩,个体总是等同于他在社会框架里的身份地位。”⑧沙龙这个“客厅”之所以不能在“家庭”概念上理解的原因就在于,沙龙是社会性的交往空间,它已经超越了家庭事务的范畴,因此“家庭”的私人性被沙龙超越,沙龙的参与者只能是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公民”。沙龙的公共性来自于它对家庭事务的扬弃,沙龙谈论的话题指向公共事务,即个体以公民身份面对的社会或者国家事务。很少有人在沙龙里谈论私人事务,即使有人谈论这样的话题,也需要将其提升或者扩展至公共事务的维度上。另一方面,沙龙的公民性谈论也需要排斥所谓威权话语,因为沙龙的所有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身份地位,他们依照普遍规则进行一种“主体间性”式的商谈。“主体间性”就是沙龙的商谈伦理。这一伦理原则认可每一位沙龙参与者在差异性层面上的主体地位,要求谈论者遵循一般议事规则,在真实表达个人意见的基础上求取共识。商谈伦理不承认两种话语的道德合法性,即威权话语和臣仆话语。一旦有威权者出现在沙龙,将沙龙的谈论变成教化或宣传,沙龙很快就会作鸟兽散。同样,只接受他人教化而全无独立意见的臣仆人格在沙龙中也是没有生存位置的。公民性谈论的必需前提是谈论者身份的平等和谈论规则的普遍有效,当我们说沙龙中隐含着协商政治的基因时,指的就是这种公民性的谈论方式。即使在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里,女主人扮演的也许只是一个“议长”的角色。尽管她的魅力足以吸引众多的沙龙参与者,但是她仍然不可能把“客厅”变成布道的讲坛或传诏的殿堂,否则她的沙龙必然门可罗雀。因为有这种公民性的谈论作为基础,所以由沙龙发展形成的社团组织,一般来说是具有公共性的,跟江湖帮派发展出来的社团组织有着本质的差异。
再次,沙龙的谈论是一种公共性的谈论方式。所谓“公共性的谈论”,意味着沙龙的谈论指向公共事务,因而沙龙的谈论总是显现出一种政治色调。雷蒙·威廉斯发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文人们一开始谈论的是文学艺术,然后这一沙龙文化圈就把话题转向更为广大的社会或者国家事务,诸如失控的资本主义、男权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等等。⑨尤其是在那些广场性的沙龙里,大多数参与者并不满足于谈论风花雪月的诗歌和艺术,他们要对国家、社会、文化等“广场”事务发言。这种公共性的谈论使得沙龙在公共领域里呈现出极强的政治性。而且许多专业性沙龙也不愿意自我陶醉在“文化山”上孤芳自赏,除非是唯美主义者那种以孤芳自赏为生存之道的沙龙式聚会。沙龙谈论的公共性还表现为,沙龙的谈论是一种符合普遍议事规则的谈论方式。因为谈论者身份的真实和平等,也因为话题内涵的公共性,所以沙龙的谈论必须依照普遍规则来进行,否则沙龙的谈论就会变成无益的争吵。沙龙的谈论是谈论者个人意见的真实表达,同时沙龙又用一般性的规则确立“形式正义”以保证谈论的公共性。即使沙龙有自己特定的专业性话题,其谈论也需要遵循一般议事规则,这是沙龙参与社会实践的主要机能,也是沙龙通向协商政治的最重要的路径。在现代生活世界中,协商政治取代了前现代生活世界的两种政治方式——贵族的宫廷阴谋和群氓的暴力行动,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而这一进步的启蒙性“练功房”就是沙龙。
2)异味控制:该设备设计开始以半封闭、全封闭为集气原则,皮带机区域采取封闭作业、卸料点采用软通道卸料,使异味受控,或收集处理或喷洒除臭剂予以解决异味问题。
沙龙的谈论也许是严肃抑或生动的、幽默甚至戏谑的、思辨或者诗性的,这都无法改变沙龙话语的自治性、公民性和公共性的基本属性。就关于公共事务谈论的真实性而言,沙龙的谈论比机构或者组织性的谈论更能够体现谈论者的思想,因为沙龙话语是谈论者社会身份的真实表达。
四、沙龙与公民社会
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都把沙龙视为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古典形态的社会中,公共领域狭小而且功能微弱。由公共性的谈论到民间社团再到大众传媒、由行业协会到自由贸易再到市场经济、由市民到国民再到公民,与国家相对应的公共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公民社会。在此过程中,沙龙发挥了公共领域孵化器的功能。假如我们在这样的意义上来思考,即公共领域所建立的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通向民主法治的最重要的机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沙龙在社会进步坐标上的重要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沙龙里的自由谈论就是协商政治的起点。
从历史现象来看,沙龙的盛衰跟社会的开放程度是成正比例的。由于沙龙这一谈论方式具有自治性、公民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学特质,所以沙龙式谈论开拓了一片公共领域的“育种基地”,进而它也显示出与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的特点;又由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国家对沙龙的容忍程度常常能够体现出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程度。早期的沙龙形成于城市资产阶级与边缘化贵族之间的文艺性聚会,但是这种被哈贝马斯称为“文学沙龙”的聚会很快就被路易十四的“绝对国家”收编,转变成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支持的绘画艺术展览制度。在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公民的沙龙性聚会几乎绝迹,只有上流社会的休闲式聚会。这些聚会跟沙龙的宗旨相去甚远,因为其中根本见不到公共性的谈论。比如斯大林跟他的下属们在孔策沃别墅里经常性举办的酒会,其中充满了宫廷阴谋、颂圣话语和臣仆伦理,丝毫见不到以公民身份开展的自由谈论。与之相反,在国家权力受到公民社会的限制因而社会趋向于开放和自主的历史条件下,沙龙总是活跃而且繁荣的,比如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时代英国的知识精英沙龙。其实沙龙仅仅只是一种特殊的谈论方式,它本身不可能威胁国家权力的运行,但是一旦沙龙式谈论被组织化并成为社团,即它以机构性社会实践的形式展开一种公共领域与国家权力的对话,那么它就起到了公民社会的作用,因为它迫使国家权力以协商者的角色出现在政治舞台之上。沙龙的存在常常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疑问和评判,而任何一种国家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希图成为“全能国家”⑩,所以国家总是用警觉的眼光审视着沙龙。
在中国古典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几乎可以说从来未曾发展成型过。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处于一个两极平衡的结构模式状态,这两极就是家庭和国家。就像国家这个词在汉语中被书写为“国”和“家”两个字的连接一样,传统中国人在“朝廷”和“家族”之间非此即彼地找寻自己的生存位置。“国”与“家”之间缺乏一个公共领域作为“公民”身份的存放与展示的空间,因此中国古典社会一直没有提供沙龙的生成和存在的历史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长期的中央集权政制使得国家权力达到了“全能”的程度,以至于国家意志、国家伦理、国家行政治理技术从中央延伸至地方甚至延伸至日常生活行为,甚至于构建了一种国家主义的伦理意志,如此这般的结果就是强大国家对公共领域的挤压和排斥。当公共领域失去了生成和生存的历史条件时,沙龙也就不可能出现在社会生活实践之中了。中国古典社会中曾出现过书院、祠堂、商会、文人结社等,这些东西或者受制于官府或者受制于家族或者受制于学派宗师,都未能构成独立于权力和资本之外的社会力量,因而也很难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
帝制的解体和传媒的登场在清末明初的时代里催生了早期的公共领域,于是五四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知识分子圈中沙龙式聚会逐渐增多,像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一类的知识分子沙龙在北平、上海等地渐渐成为常态。这些沙龙也催生了民国时代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社团,显示出公共领域扩展的态势。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再度进入一种总体化的全能国家状态,民间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如社团、传媒、行业协会等等都被纳入国家权力体制,公共领域趋于消失,因此在那几十年里沙龙也难觅踪迹。在国家权力的全景监控下,沙龙式聚会及其谈论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偶然出现的民间性的自由谈论也常常处于“地下”状态,比如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中出现的许多地下读书会等。
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时代,中国沙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繁荣。改革开放形成国家政治相对宽容和市民社会再现端倪的历史语境,于是出现了公共性意义上的各种沙龙。不过1980年代的沙龙主要是专业性沙龙,而且以寻求专业自主性为其谈论的主题。1980年代的专业性沙龙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这些以专业自主性为话题的谈论旨在逃离国家权力对专业领域的强制性统治,重建专业性社会实践场域的自主性。
加拿大学者傅尧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国家主导下的公民社会”的公共性社会空间。傅尧乐在《国家主导下的公民社会》一文中引述澳洲学者的研究报告的内容:“在亚洲的新儒教社会中,公共领域由国家创造并源自国家,而不是出自私人领域,对国家也没有什么限制,个人没有多少机会可以扮演诸如独立公民之类的角色。他们想不参与都不容易。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中,总是被期待作为政治参与者去行动,国家有权侵入他们的‘私人生活’,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公民对此是无法接受的。”⑪但是傅尧乐坚定地认为当代中国是存在着公民社会的,只不过他将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理解作“国家主导下的公民社会”。依此思路,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理解为“国家主导下的公共领域”呢?甚至我们还可以延伸性地理解说,现在只有在官办性质的专业性协会的学术会议上才不时出现的专业性沙龙,也属于“国家主导下的沙龙”。但是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国家主导下的沙龙无疑已经失去了沙龙的本色。就像企业家沙龙里的谈论用官商结盟的方式让沙龙的谈论失去了公共性、自治性和公民性一样,官办协会上的学术沙龙,其参与者并不具备真实的公民身份。
注释:
①②⑧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7、73、73页。
③④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曹卫东译,《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4、136、139页。
⑤初具昊:《沙龙的起源与公共性问题》,《美术研究》2004年第1期。
⑦昆汀·贝尔:《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季进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⑨Raymond Williams,Sociology of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81.
⑩全能国家,又称“总体国家”,西方学界也有人以此称呼集权国家。卡尔·施密特对这一国家理论作出过深入的分析,他以全能国家来批判自由主义主张的限制国家权力的理论。
⑪参见卜正民、傅尧乐编:《国家与社会》,张晓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责任编辑刘保昌)
I206.6
A
1003-854X(2015)11-0106-06
冯黎明,男,1958年生,河南安阳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