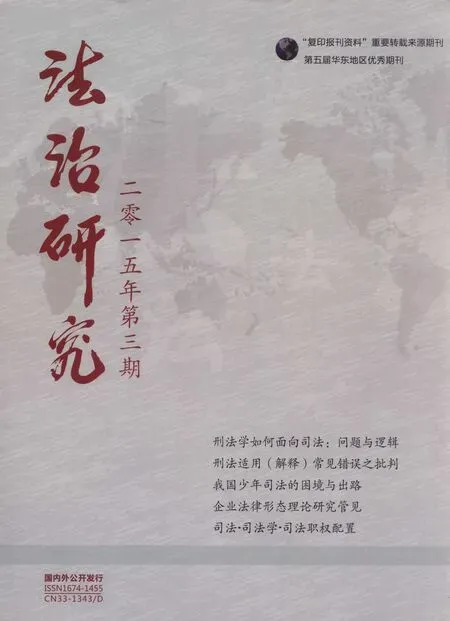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研究管见
张世明
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研究管见
张世明*
参酌国外企业形态整合的最新动向,为投资者提供多样性、便捷化的企业法律形态选项,从而达到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目的,是企业法律形态研究的出发点所在。我国企业法律形态的研究尽管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率性而言的策论彼此争鸣,仔细推敲起来却难称人意,基础理论的研究仍然存在深入发掘的空间。本文从企业经济形态与法律形态、企业法律形态与企业法定主义、企业法与企业的相关法律形态三个维度入手,以国外大陆法系法学界关于企业法律形态理论为参照系,认为企业法律形态与经济形态的关联尤其值得重视,不能将企业法律形态与企业法定主义简单等同视之,经济法学应该跳出企业法律形态本体论的范围而将视线进一步延伸至企业的相关法律形态的探索。
企业经济形态 企业法律形态 企业法定主义 企业的相关法律形态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除几近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外,其他所有企业形式一度销声匿迹。以企业财产的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对企业加以分类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国的企业形态立法大体沿袭以企业的所有制和行业为标准的做法,相应的立法主要包括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年4月13日通过)、《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国务院1990年)、《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国务院1991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国务院1988年)、《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 (国务院1987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7月通过,1990年4月、2001年 3月两次修订)、《外资企业法》 (1986年4月通过,2000年10月修订)、《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1988年4月通过,2000年10月修订)等。这些企业立法基本上适应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促进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集体和私人投资、吸引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立法方式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弊端。首先,按照所有制和行业划分企业形态往往意味着对不同企业的差别对待,结果造成私人为了某些政策优惠而不以真面目示人,通过挂靠、合作等形式将自己变作“假集体”、“假国有”、“假合资”企业,想方设法地争戴“国营”与“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名实相悖。其次,以所有制和行业为标准划分企业形态,使第三者对于企业的责任状态难以一目了然,不利于市场中的经济交往。是时,中国法学界开始关注企业法律形态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赵旭东的博士论文《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研究》为后来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导夫先路,贡献良多。关于企业法律形态问题的论著目前已经蔚为大观,但仍然在基础理论问题上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尤其对于国外的研究状况和趋势了解不够到位,以致形成“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时差。事实上,仓促而草率的策略设计可能欲速而不达,站在更高的立场上的企业法律形态基础理论研究亟待加强。笔者不揣谫陋,谨陈己见,就正于方正之家。
一、企业经济形态与企业法律形态
日本经济学界一般认为,企业形态的研究将法律形态与经济形态相区分的倾向,可以从德国经济学家里夏德·帕索①Richard Passow,Die Aktiengesellschaft.Eine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e,2nd ed.,Jena: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1922.、罗伯特·利夫曼②Robert Liefmann,Die Unternehmensformen mit Einschluβ der Genossenschaften und Sozialisierung,Stuttgart:Ernst Heinrich Moritz,1912.、赫伯特·冯·贝克拉特、梅尔希奥·帕里伊③Melchior Palyi,Das Problem der Unternehmungsform,in:Grundriβ der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Bd.2 ,Die Betriebsverwaltung,Leipzig:Gloeckner,1927.诸氏的论著看出。中国学术界在追溯企业法律形态理论时,往往按照日本学者的介绍将利夫曼《受合作化和社会化影响的企业形态》尊为这方面研究的先驱。按照罗伯特·利夫曼的观点,使经济上的企业赋予其法律的存在各安其位地与企业构造相关联法规的全部,就是企业的法律形态。这就是说,不是单纯决定属于何种形式的法律状态,而是全部的经济生活的事实意义上所使用的企业形态。罗伯特·利夫曼的企业形态理论尤其关注当时经济活动社会化与私人资本制度之间内在的张力与矛盾。这其实就是德国法学界力图突破商法的框架发展企业法一脉相传的学术理路。④这可以参考[日]増地庸治郎:《リーフマン氏企業形態論》,载《商學研究》1巻3号,1922年版,第901~916页。按照梅尔希奥·帕里伊的观点,决定企业法律形态构成的本质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在企业中企业者的人的关系的深浅程度;第二,企业职分的合一或者分割,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合问题;第三,责任分担的限度,分为有限与无限、连带与分割、直接与间接、基本与补充等等;第四,有无证券发行的可能性。⑤[日]増地庸治郎:《企業形態論》,千倉書房昭和5年版,第31~35页。这些作者,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学家,都会发现自己面对着多样性和多重性的现象。
这一时期德国经济学界对于企业法律形态的论述可以说奠定了此后日本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日本经济学家上田贞次郎的《股份公司经济论》不仅仅讨论经济形态,其既可以说是株式会社论,也几乎是法律论。上田将法律论作为形式、经济论作为实质,以至于批判性指出,存在与法律上的形式不同的经济论上的实质。该氏按照这种方法,认为与法律形态相异的实质的经济形态具有重要性,从而在对比中加以揭示经济论特色。增地庸治郎是上田贞次郎的高足,其企业形态、株式会社研究是在上田贞次郎的启发和指导下开展的。增地所进行的利夫曼《企业形态论》的翻译和介绍是上田指导的产物。增地庸治郎不仅讨论形式与实质的对立,而且对于企业的法律形态与经济形态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予以经营学的考察。增地庸治郎认为,企业的法律形态与经济形态具有密切关系,但两者在本质上全然不同,在研究上有必要加以严格区分。另一方面,企业的经济形态不能与法律形态全然割裂开来。例如,单独企业在采取株式会社的法律形态时参与经营活动,必然与个人商人的情形不同。因而,经营经济学的研究者对于企业的法律形态加以关注和理解的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正如增地自己所言,决不以法律论为自己的目的。⑥同注⑤,第35、46~48页。在增地庸治郎的著作中,企业形态的本质要素主要由出资、经营以及支配的合一抑或分离加以研判。⑦[日]増地庸治郎《新訂企業形態論》,千倉書房昭和13年版,第42页。
增地的分类体系见于其早期著作《企业形态论》,后期著作《株式会社》、《新订企业形态论》等等。其学说的基本框架没有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增地这里的分类体系是关于企业形态的经济形态。就法律形态而言,各种形态是与经济形态相对应的。堀越芳昭在《日本经营学的形成——增地经营学说的原理与形态》一文中将包含经济形态和法律形态的增地的企业形态体系化如下:(A)私企业:(1)单独企业(个人商人),(2)第一种少数集团企业(合名会社),(3)第二种少数集团企业(合资会社,有限会社),(4)营利的多数集团企业(株式会社),(5)非营利的多数集团企业(协同组合);(B)公企业;(C)公私合同企业。⑧[日]堀越芳昭:《日本経営学の成立——増地経営学説の原理と形態》,载《商学論集》第15号,山梨学院大学平成4年11月。增地企业形态理论是企业形态的经济上的概括。堀越芳昭认为,这种与所谓的法律上的规定(私人公司,合伙,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不同的、并以此为基础的以经济为主要因素加以扩展的立场,在日本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也被其弟子山城章从“企业体制论”的观点出发加以批评。⑨[日]山城章:《新企業形態の理論》,経済図書株式会社昭和19年版,第180、182页。
企业形态是企业采取的结构,大致分为企业经济形态和企业法律形态。法律形态是企业根据何种法律规定设立、运营进行分类。从总的方面来讲,企业法律形态是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的千差万别的企业表现样式的最基本的法律概括,是企业内外法律关系和法律属性的概括反映,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企业形式。就法律视角的企业概括而言,它不外乎是以企业诸利害关系者,尤其是对债权人责任负担的视角为主轴,对企业的创设者及其之间、企业创设者与企业之间、企业创设者和企业与企业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法律规制,并以此为根据对企业进行法律形式分类。其决定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企业的法律地位,同时也决定投资人的投资风险和责任范围。正是这样,企业法律形态被德国法学家称为企业活动“法律礼服”。企业在法律上的形态在吉永荣助的著作中被表述为“法形态”,以与“经济形态”相对称。通常,日本学者使用“法形态”这个概念时具有从宏观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实定法的理论把握的意味,而对于具体的法定主义的企业制度往往也使用“法律形态”的表述。实际上,前者相当于我国学术界企图创建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的学者所使用的“企业法律形态”的概念,后者可以准确地译为“法律形式”。这种细微的差异对于擅长类型学方法、法律教义学方法的德国学者而言似乎不成问题,两者被有机结合为一体。在德语国家,Rechtsform和Unternehmungsform两个概念在理论和实务中通常被视为同义词,但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京特·韦厄将Rechtsform der Betriebe作为Unternehmungsform的上位概念。⑩Günter Whe,Einführung in die Allgemeine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München:Verlag Franz Vahlen,1984,S.255.这种阶位是由于Betriebe和Unternehmung的概念定义所致。因为Unternehmen仅仅包括赢利性的生产单位,而Betriebe,尤其是公共企业,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致力于成本抵偿原则。埃克哈德·卡普勒和曼弗雷德·韦格曼则认为,Unternehmungsform的概念外延更为广泛。他们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在在皆是,他们具有更多的法律形态。例如,所谓两层公司在一个统一的经济构造物之下联合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形态。法律形态因此仅仅是企业的组织建构的一部分。⑪Ekkehard Kappler,Manfred Wegmann,Konstitutive Entscheidungen,in:Heinen (Hrsg.),Industriebetriebslehre- Entscheidungen im Industriebetrieb,Wiesbaden:Gabler,1985,S.159f.大多数学者赞同于埃克哈德·卡普勒和曼弗雷德·韦格曼的观点。⑫例如,可以参见Edgar Castan,Rechtsform der Betriebe,Stuttgart:C.E.Poeschel Verlag,1968,S.7。
企业经济形态是以其投资者类型、构成、出资方式的差异、人数加以分类的,划分标准有资本筹集的样态(帕里伊说),从业人数以及职能分化程度(利夫曼说),出资、经营支配的一体或分离的程度(增地说),经营、管理、作业的历史发展阶段(山城说)等等,正如菊浦重雄所言,企业经济的实质形态难以统一。⑬[日]菊浦重雄:《企業形態の歴史と展開》,制作社1992年版,第77页。例如,以出资为分类标准有3个路径。第一是依据出资者的数量,区分为单独企业(个人企业)、少数集团企业(合名会社、合资会社)、多数集团企业(株式会社),此法影响企业的统一的意思的形成;第二是依据出资者的性质区分为公企业、公私混合企业(公私合同企业)、私企业;第三是依据出资者的危险负担(责任的样态)区分为人的企业(包括无限责任社员:个人企业、合名会社、合资会社)与物的企业(资本的企业)(全体社员为有限责任:株式会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学界关于企业法律形态的研究由于当时话语建构的语境限制,在引进国外学术思想时极力强调企业法律形态与企业经济形态的迥异,从一开始就定向于使企业法律形态研究从企业经济形态研究中脱颖而出,力图通过企业法律形态的研究执简御繁,克服企业立法杂乱无章的格局。从当时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和学科专业化角度而言,这种立论发议取向本身无可厚非,但过于“我执”就会产生偶像崇拜,画地为牢。事实上,企业法律形态与经济形态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能更值得研究。这可以说是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研究的高级形态。当然,其间难度系数相当大。
吉永荣助认为,法律形态是指商法典上所规定的法律形式,或者以此形成的形态(法形成体)。与此相对,经济形态是指为了现实的经济目的,利用前述法律形态,或者在现实中加以具体化的具有机能的形式。如果说法律形态是规范,那么经济形态是事实关系。此外,与法律形态在形式上的规整不同,经济形态是各种要素的复合产物。前者是划一的,后者是个别性的。这种差异是基于商法和经营学的学问的品格、考察方法的差异。虽然希望法律形态和经济形态能够呼应或者对应,但很难总是一致的。经济形态中,重要的是数和量的问题,即企业的规模。具体说,企业的组成要素的资本、股东、利益、经营者、劳动者、交易关系者的数量成为经济形态的决定要素。经济形态所关心的不是股东的权利义务,而是股价、财务状况。企业的经济形态是从外部的企业及国民经济的价值关系为依据,与企业经济形态依据错综关系为评价基准相对照,法律形态相反是指内部的“人”在法秩序中具有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关系。一般而言,法律形态是在立法中基于历史的、具体的形态加以规整、抽象而制定法规所规定的常态。法律形态在私法中听任私人加以利用,仅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要求采取特定形态。经济形态与此不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一开始就合理地、合目的地形成的,其利用法律形态,以最经济者为最佳的手段作为判断标准。但是,无论如何,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法律形态,只能限于法律形态,不得违反强行规定,否则即产生违法、无效的后果,违反者负有损害赔偿、恢复原状的责任,此可称为法律形态最小限度的要求。另一方面,就经济形态而言,为了经济目的,在法律的许可限度内,对于法律形态加以修正、加工,在任意法以及所赋予的自治范围内,将法的本来的目的或者旨趣最大限度加以扩张,从而实现自身欲求。这可以称之为经济形态的最大限度的要求。在这两个要求限度的范围内,法律形态与经济形态之间合致、乖离与相克的现象得以产生。⑭[日]吉永榮助:《会社(企業)の法形態と経済形態》,载《一橋論叢》第41巻第2号,第129~144页。
商法学者直接讨论企业形态的论著在国际学术界比比皆是。植竹晃久1984年提出,尽管确切地依据商法和会社法对于各个企业形态之间进行比较、分类也是可能的,但应该将以责任负担问题为基轴的规范地构成的法律形态,从出资、经营、支配的观点出发,置于再构成的经济形态,主要以制度化的现存企业诸形态为对象,审视其经济本质。⑮[日]植竹晃久:《企業形態論——資本集中組織の研究》,中央経済社1984年版,第18页。这样的研究路径具有将规范与事实相结合的取向,包含对于单纯研究企业法律形态的路径的批评。石井照久教授的《企业形态论》就是从法学的立场出发采取这一路径开展讨论的产物。首先,其所揭示的企业,较之此前商法和公司法上所思考的企业更为具体,在更为广阔的基础上置于当时的经济体制或者经济动向的舞台灯光下。该书是与以企业的经济形态为基础的法律形态相关的立法论。与吉永荣助的观点相反,山本政一认为,企业形态被人们认为基本局限于资本的结合样态问题,但是,从过去的学术发展来看,企业形态论历来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外在的、形式的制度考察,如果深入下去加以经营经济学的检讨,企业内部的、本质的面相更加饶有趣味,必须对企业资本的结合过程以及发展阶段中企业资本的集中、支配过程加以揭示。⑯[日]山本政一:《企業形態論序説》(改訂版),千倉書房1972年版,第1~2页。他从个别资本说的立场围绕企业资本的结合模式,讨论了企业资本的发展过程、所有与经营的分离、企业集中、企业集团、合作社、公企业、地方公共企业等问题。山本政一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企业的经济形态为重心,但兼顾到了企业法律形态的思考。
如经典作家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法律只是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其实与乃师萨维尼强调法律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交集。温德尔·霍姆斯在1897年《哈佛法律评论》上所发表的《法律的道路》这篇在美国法学著作中引证最多的论文中同样强调: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哈耶克对于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探讨也表明人的理性设计是具有局限的。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理性主义设计的证据。以法学家方面对于从实际的要求产生的经济形态加以法制化的例子是德国1892年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这被夸耀为结合人合公司和资合公司的长处、近代立法者合理的创作、历史性的人工建构物。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在德国最常见的企业形式,其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德国立法者创设的。如果说,企业的其他法律形式几乎都是历史形成的,然后立法机关再从法律上加以确定,那么,有限责任公司则是立法机关人为的产物。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法律形式之所以被“创造”,完全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股份公司和合伙公司的法律形式不能完全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还需要在这两类企业法律形式之间人为地创造一种清偿责任为有限的企业法律形式,使经营者能够在避免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的前提下经营中小型企业。⑰张仲福:《联邦德国企业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0年版,第21~22页。当德国发明出这种企业法律形式之后,许多国家都引入了类似的企业形式,有时有意模仿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国于1925年、日本于1938年制定有限公司法规时,都从德国的法律中吸取了宝贵的营养。这种新的企业形式允许企业能够结合股份公司和合伙关系的要素,从而构成许多企业的卓越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使得从业者将股份制的形式与有限责任结合起来,构建适合其特定公司的治理规则,既可以推进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创新设想,又无自身的财产因经营失败而被悉数吞噬之虞。莱温·戈尔德施密特也许是当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商法学家。他在对股份法问题的分析中,强调他对目前合伙关系法律的不满,然后说,他希望一个加以修订的完整商法,允许在股份公司和合伙之间插补的一个“中间形式”。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其他的想法。在最初的几十年,许多人担心,投资者相对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会招致欺诈和其他滥用。这方面的关注,既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的经验,也与对可能会限制债权人的权利的法律机制更广泛的不安心理有关。许多德国的法学家当时反对有限公司的制定。他们有两条理论的攻击线。首先,一些人认为,商法典的目的是对实践进行法典编纂,而不是创造新的商业形式。商法应该简单地澄清和规范在实际惯行的基础上形成的规则。有限责任公司被蔑视为立法机关在法律逻辑以外的一个“创造”。其次,反对者从第二条攻击线出发辩称,有限责任公司不一致地混淆了合伙关系法与股份公司法的原则。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早期,评论者倾向于将有限责任公司解释为一个具有额外权利的合伙关系。巴哈尔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被广泛引用的攻击,反映了对于有限责任的普遍不安。巴哈尔承认,有知识的借贷者对有限责任公司几乎没有恐惧,但他辩称“笨伯”需要保护。⑱参见Otto Bähr,Gesellschaften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Sonderabdruck aus den Grenzboten,Leipzig:Grunow,1892。
前些年,中国学术界为了论证股份制改造,往往引述两段名言。一段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经典论述:“假如必须等待积累来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⑲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页。第二段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巴特勒在1911年曾经所指出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⑳Tony Orhnial,Limited liability and the Corporation,London:Croom Helm,1982,p.42.这两段话本身并没有错,我们以此论证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也没有错,不过要注意的是,中国法学没有像美国法学那样经受法律现实主义思潮的洗礼,对于问题阐述基本仍旧停留于主观的推论,缺乏实证研究,正如霍尔姆斯所言,“理性地研究法律,时下的主宰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㉑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10,No.8 (1897),pp.457-478.就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研究而言,目前德国商法以企业为对象的学说占主导,企业中心说的倡导者明显受到法学家卡尔·维兰德的影响,形成所谓维兰德学派。这除了单纯历史的对象随经济生活的发展的变迁之外,显示出商法学的研究方法的变革。此前研究方法是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即商法典)的字句、概念的解释,以沿革、比较法等为重点,而如今的关注对象是法律事实、社会经济现象的特性及作为其基础的经济体制、秩序等,采取的是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经济法的方法。在转向对企业法律形态研究的同时,商法本身开始具有观察科学的性质。㉒[日]米谷隆三:《商法概論》,営業法、有斐閣1942年版,第5页。易言之,局限于应然的规范研究不免空疏之弊,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的研究本身已经转向于细密的经验实证分析研究。这似乎体现了法学界在企业法律形态研究向企业经济形态研究主动出击的拓展和方兴未艾的反哺态势,颇有否定之否定的扬弃意味。我们可以以瑞士为例审视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德国法学的创造物,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前些年法学界关于现代企业制度讨论的认知。尽管1936年瑞士就引入有限责任公司,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可以利用的合适的法律形态,尽管股份两合公司结合私人公司和公共公司之长,理应可以形成与家族企业相分离的机制,但这两者在实践中却反响平平。事实上,各种法律规定使此种法律形式不利:通过最高资本条款划定了其扩张的界限,在此后转型为股份公司在法律上较为困难,又需要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和股份公司的后续新建。股权份额的转让、抵押和继承不能像有价证券那样容易。由于资本力量的虚弱,有限责任公司在瑞士被称为“小孩子的股份公司”㉓参见Roland Bertsch,Die industrielle Familienunternehmung:Ein Überblick über ihre Bedeutung und ihre Hauptprobleme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Finanzierung und Führung,Schellenberg:Winterthur,1970,S.206。,这和有限责任公司仅有有限信用而被称为“受有限尊敬的公司”的现象如出一辙。直到1987年,瑞士仅有9家股份两合公司存在,此种法律形态的罕见性彰彰甚明。其主要原因在于,个人公司(Personengesellschaft,指合伙)和资本公司(Kapitalgesellschaft)要素的结合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的优势,并且此种结合过于复杂,尤其是类似的组合结构可以通过其他法律形式轻易获得。㉔Robert Portmann,Die Wahl der Rechtsform als betriebswirschafliches Problem für Klein- und Mittelbetriebe,Z ü rich:Schweizerische Treuhand- und Revisionskammer,1987,S.62-64.
二、法律形态与企业法定主义
论及企业法律形态,势必与企业法定主义相关联。所谓企业形态法定主义,是指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可以设立的企业形态,投资者开办企业必须遵守企业形态法定原则,不能擅自选择法律未规定的组织形式,也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自行创造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对于中国目前是否实行的是企业法定主义,学术界的观点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法律实际实行的是“企业形态法定主义”,市场主体只能在国家规定的企业形态中选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进而批评,中国目前奉行这种“企业形态法定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存在某些不妥适之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企业形态法定主义,至少不存在明确的企业形态法定主义,而是一种默示的企业形态法定主义。
中国法学界似乎过分热衷于所谓的“法定主义”。民法里面大讲“物权法定主义”、刑法里面大讲“罪行法定主义”、税法里面大讲“税赋法定主义”,因此关于“企业形态法定主义”的论述也比较盛行。所谓“法定主义”是从日本法学文献中继受过来的术语,其在英文中为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即德文das Legalitatsprinzip㉕W.Wagner,Zum Legalitätsprinzip,in:Festschrift für den 45.Deutschen Juristentag,Karlsruhe :C.F.Müller,1964,S.149ff.。法定主义与便宜主义相对,是需要所有的法律以明确的、确定的和非追溯的法律理想,与法律形式主义和法治国理念是密切相关的,并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戴雪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前现代国家,以社会秩序维护法为借口,总是确立不适用于规定的刑法裁判的“断罪无正条”和政府规章不适用于向轻罪裁判而任由行政官员依据情理自由裁量权“不应为条”,允许对于类似犯罪行为运用类推适用的规定。受到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矫枉过正,纷纷趋骛于“罪行法定主义”。这可能和目前中国法律普遍简疏、举国上下向往“法治国”的理想境界、“法律万能主义”的思潮澎湃有关。然而,“法化”是与“去法化”“、反法化”等概念相对而言的。德国学者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过分法律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寻找各种能自我治愈创伤的社会力量,具有对法律万能主义和法律系统负荷过重的症候的反思意义。在苏永钦《经济法的挑战》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该书开篇之作即题为《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从民事财产法的发展与经济观点分析》,其中的反思发人深省。㉖苏永钦:《经济法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事实上,国外学术界对于法定主义的反思一直不绝如缕,对于法定主义的实效性投畀以根本的怀疑。有学者凛然于法定主义的危机四伏㉗Peter Ecke,Legalitätsprinzip in der Krise,Zeitschrift für Rechtspolitik,1973,S.1 35 ff.,提出与法定主义告别㉘Hans Serwe,Abschied vom Legalitätsprinzip,Kriminalistik,1970,S.377ff.。在诉讼程序法中,法定主义在保障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和恒定性的同时,也可能因为缺乏弹性而无法适应现实生活,当在有恶意的方面可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法律假设的事件发生时,从法律规定的最高刑罚出发,就可能难以严厉惩处,这一原则遂遭到批评,允许一定范围的便宜主义和作为现行的例外规定的裁量规定。
世界著名法学家费肯杰在其两卷本《经济法》中指出,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批评“死手财产”( biens de la main morte)的结果,法国民法典没有关于法人构成形态的规定,法人在19世纪法国民法中依据自由创立的原则得以发展,所以目前在法国的法人类型远多于德国。㉙参见[德]沃尔夫冈·费肯杰:《经济法》第2卷,张世明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37页。这一观点堪称确论。在法国民法典制定时,天赋人权观念普遍盛行,时人害怕封建势力借助团体的主体资格进行复辟活动,法人这一概念使人联想起刚刚被打倒的教会势力、“死手财产”,所以没有规定法人制度。在中世纪法国,为了防止财产流向农奴主以外的人,依据“农奴死亡,但他的主人需要生活”的原则,农奴死后将其财产归还给他的主人。故而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实为对中世纪财产法权的深恶痛绝的矫正和反动。1804年《法国民法典》有关公司的规定实际上是对被誉为法国民法之父的波蒂埃《公司契约论》的原封不动的搬字过纸。㉚Jean-Pierre Bertrel ,Le débat sur la nature de la société ,Droit et vie des affaires:études à la mémoire d'Alain Sayag ,Paris :Litec,1997,p.132在该法典中,公司或者被视为是一种普通的合同,或被视为是一种财产共有关系。根据1804年《法国民法典》,有关特定公司的股东无须公开其协议;除非作出相反规定,否则,每一个公司股东都是经理,每一个经理的行为都可以被其他经理所否决;只要具有适当的动机,任何股东都可以随时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解散公司,即便公司合同没有规定特定的持续期,其他股东亦不能阻止股东提起公司解散之诉。㉛Michel de Juglar et Benjamin Ippolito,Droit commercial:avec cas concrets et jurisprudence,Paris:Montchrestien,1970.有些学者认为,法国1807年《商法典》关于股份公司的规定是保守的、限制性的。这种观点以股份公司设立所采取的沉重而漫长的预先批准程序为论据。具体说来,根据法国1807年《商法典》,如果要申请设立股份公司,都必须预先获得政府的批准,向省长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各种法律文件。省长、内务大臣、法国行政法院等环节经过对这些材料的调查和研究,最后拟定法令草案,将其呈交法国国王最终作出是否同意设立的决定,并在法律公报上加以公布。基于此,这些学者认为,该法对一般公司和特定公司的规定都是极其过时的。但是,保守怀旧的情愫与昂扬激进的冲动事实上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正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所言,法国1807年《商法典》之所以对股份公司的设立采取如此严格的程序,是同法国19世纪初期人们对股份公司所怀抱的信任和恐惧心理息息相关的。这种心理正是前揭费肯杰所阐述的极其崇尚自由主义的时代背景的产物。正是由于对股份公司的不完全信任,法国1807年《商法典》仍然对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和董事规定了众多的刑事处罚。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公司的性质是以合同理论为基础,将公司的本质还原为原子式个人,同样是强烈的个人主义激情澎湃的产物。人们多谓美国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法律为商人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形态的菜单,但许多学者通过对工业革命时期法律制度与社会事实的研究,发现在当时法国使公司基本形态适应于特定目的的可能性较诸美国更为大些,商人可以利用这种灵活性控制其责任。法国在这一时期的企业具有更为广泛的组织选择,其责任在本质上是不断变化而非二分法的选择。除了《1673年商事条例》、法国1807年《商法典》等认可的无限公司、简单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等组织形式之外,法国《公司法典》将公司分为“商事公司”、“民事公司”与其他公司等几大类型。其中的“民事公司”主要包括:建筑师公司、律师公司、会计监察公司、法律顾问公司、专利顾问公司、公证人公司、商事法院书记员公司等。特殊公司主要是指:无法人资格的公司,如隐名合伙、事实公司;可变资本公司以及专门标的公司,如农业公司、农业利益混合公司、土地整治公司、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林业生产组合、合作保险公司、工人参与性股份有限公司、地方混合经济公司、国有化的公司以及“雷诺汽车国家管理局”等等。由是观之,所谓公司法律形式未尝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如果我们随着视野的拓展,就不会依然采取僵化的思维模式执着追求一些海市蜃楼。在这一点上,费肯杰所说的推参阐述的法律研究方法显然更为可取一些。
我国传统的法理学教科书都强调,法律只调整对于社会具有重大关系的法律事实。对于这种法学常识,一般学者均是可以接受的。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中众多的问题,法律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面地使其反映在立法之中并制定相应的专门法律、法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企业形态并非都具有上升为法律形态的法定化意义。为了突出和抓住主要问题,立法者必须加以取舍,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所有的制度设计均不可能是免费的午餐,企业法律形态的法定化其实也涉及到必须从经济学角度加以审视的成本-收益问题。一方面,企业形态如果不加以法定化,各行其是,在促进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的同时,则会使企业的法律地位和内外部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将给企业交易相对人对企业法律属性的认知带来困难,大大增加交易成本,从而引发社会经济活动秩序紊乱,不利于经济活动的高效率追求,导致不公正交易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采取刻板的法定主义,其实也会压制经济发展的活力,付出立法与执法的成本,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而言,即使配置性资源不可能实现最大化,亦将使权威性资源被徒然消耗。这与科斯对于企业性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加以研究是一样的。在科斯《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中,企业、市场与政府三者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三者所发挥的作用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之后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所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遂由此而生。科斯对于企业性质的这种思维模式也完全适用于我们对于企业法律形态的思考。如同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存在价值在于减低交易成本而在功能上具有可替代性一样,企业形态法定化其实就是政府以法律形式出面提供一种标准的格式合同,以取代当事人设立企业的私法合同,从而降低当事人的选择成本。企业法律形态问题与一个法律体系的空间结构密切关联。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巨型的跨国公司财大力雄,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日新月异,这将会对企业的法律形态改变产生重要影响。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西方企业法律形态的演变就与民族国家的产生、殖民地拓展的空间结构化过程形影相伴。赫斯特就曾经声称,无论是在殖民地时期还是独立以后,美国公司法基本上都是本土的产物。㉜James Willard Hurst,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1780-1970,Charlottesville: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0,pp.8- 9.不仅现代股份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时期的殖民地公司,而且有限责任公司的引进亦与殖民扩张存在关联。当时许多德国人认为,英国公司滥用英国公司法创造了小公司,使英国企业人具有竞争优势,从而在全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中戛戛独造。英国法律允许七人组建公司,但许多德国人断言,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余通常是“稻草人”,其作用只是单一的企业人为了创造条件以获取有限责任。在辩论是否引入有限责任公司的过程中,德国支持者的主张往往集中在殖民问题。因为德国当时获得了一些殖民地,许多人认为,当合伙人相隔千里时,合伙关系行不通。新的殖民地的开发需要一个新的公司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是一个领土广袤的大国,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这些年来强劲发展的坚实基础,这种海阔凭鱼跃的空间结构本身就是中国企业家可以纵横驰骋的宝贵资源。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致力于欧盟共同市场的建设,其实也是一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制度建构。大国的空间结构与小国寡民的境遇是不同的,这必将影响其法律制度的发展,而其法律制度的建构亦必须符合这种空间结构。苏永钦在研究经济法时反复强调国家幅员大小与法律制度设计相匹配的问题。笔者对此深以为然。例如,竞争法中关于企业结合、并购和拆解等等也涉及到企业法律形态问题。费肯杰在《经济法》第一卷谈及世界经济规制法时也这样指出,越是小的国家,越容易形成通常增长在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反而言之,国家越大,越是倾向于以反托拉斯法的手段和其他法律武器的抵抗政策驱动型经济。笔者从自己在欧洲学习的亲身体会中发现,瑞士、丹麦这些领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不需要像美国、中国这样制定反垄断法并作为市场经济法律建设的拱心石,因为所谓“大象婚礼”的巨型企业之间的结合、并购等在大国固可施以严苛禁限,但在小国则由于其本身领土空间狭小,唯恐自己的企业不能做大做强,能够有一家在世界上财雄势壮的大公司,乃是求之不得的幸事。正是这样,瑞士人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瑞士是一个特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企业法形态的设计上自然不可能与小国的模式相同,但统一的企业法律形态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是具有明验著效的事实,更何况不仅德国法上没有所谓“自由组织制度”,即便目前瑞士占主导地位的学说也主张这种企业类型法定原则。㉝参见Arnold Koller,Grundfragen einer Typuslehre im Gesellschaftsrecht,Arbeiten aus dem Juristischen Seminar der Universitat Freiburg Schweiz,32,Freiburg:Universtatsverlag,1967,S.96ff。从法律制度设计而言,某一法域是否采法定主义取决于法律行为的空间影响效力大小。如是,则法定主义可能大,如否,则法定主义可能性小。合同法中之所以贯彻合同形式自由原则而不若物权行为相对于不特定之人须采取法定主义原则,就是因为当事人的协约对合同外的第三人一般不会产生影响。㉞参见蒋大兴:《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1:法律哲学&碎片思想》,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368页。企业法律形态可谓至关重要的国寔。这和罪刑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物权法定主义同等并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主要的市场主体,拥有独立性、平等性和营利性,可以自主地决定人和物的结合形式和投资领域,但这难免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为了避免企业的混乱状态,国家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内部治理进行调整显然具有其合理性。法律形式是一个企业组织的法律形式。各种公司形式的法律规范不仅规定了股东(公司)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有助于在法律关系中的安全性。交易相对人可从公司名称就知道商业合作伙伴的大体情形,无疑大大节约了信息获得成本。
在德国,企业的法律形态通常可以区分如下:(I)私法上的企业形态:a.个人企业;b.人合公司,其中包括民法公司、一般伙伴关系、有限合伙、隐名合伙、合作公司;c.资合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股份两合公司;d.合作社和协会;e.双层公司、相互保险公司等特殊形式。(II)公法上的企业形式:a.非法人组织;b.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混合形式是从实践中发展的。对法律形式的选择是最显著长远的商业决策之一,其对于该公司的存在是一个关键的基础。其中一个问题是,何种法律形式对于企业的经济运作是可取的,不仅在建立阶段,而且在以后的阶段。当个人的、金融的、法律的或税收的因素显著变化,转变法律形态是必要的。某种企业形态在开始可能表现为最佳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劣势逐渐显露出来。因此,有必要在某个时间间隔后检查企业的“法律礼服”是否仍然合身,是否应该加以改变。在变化时,特别要考虑的可能性,即:在法律形态变化同时保留企业的一致性。法律形态的变化是按照转换法的规则进行的。㉟Ulrich Blum,Entrepreneurship und Unternehmertum:Denkstrukturen für eine neue Zeit,Wiesbaden:Gabler Verlag,2001,S.497.此外,法律形态的选择对税收负担、融资可能性以及年度审计和财务报表的披露要求的义务产生影响。税收负担较大的差异出现在人合公司以及个体企业与作为另一方的资合公司之间。资合公司作为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因此负有纳税义务。如果在资合公司中产生利润并准备分配给股东,那么首先该公司本身必须将所得以法人税的形式(企业所得税)缴税。由公司扣除法人税后,分配给股东的利润还须缴纳资本收益税。这种双重征税并不适用于个体企业以及人合公司,因为这些都不表现为独立的法律人格,因此无须缴纳公司税。对于公司的利润,其股东仅须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上述问题属于法律形态替代性研究的范畴。
企业法律形态之“体”的塑造必须服务于企业法律形态“用”的发挥,提供适合需要的企业组形式和机制。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于我国法律的不完善状态不无微词,往往批判法律规定过于疏简而难于付诸适应,一味强调法律规定的细密性,以无微不至为尚。但我们应该看到,有时候法律规定得越具体,越会出现制度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的情况,结果是法律的适用性下降。立法应该给法的实施预留足够的空间,否则,法的稳定性必然会导致法的僵化,这将出现南辕北辙的可悲结局。采取企业法定主义的原则必须考虑到这一偏颇倾向。观夫当今世界,我们也可以从日本学术界的发展得到某些启迪。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组织“关于组织形态与法的研究会”,他们的研究结果《“关于组织形态与法的研究会”报告书》在《金融研究》第22卷第4号上发表。围绕组织法的强行法规性的问题,日本学者将私人自治许容与强行规整的平衡视为不容回避的课题。按照能见善久先生的“企业形态论”观点,在法人法定主义原则下,法人形态的类型是法律以一整套加以呈现的制度供给,例如,A法人类型和B法人类型,似乎很好的结合,但却不可越雷池一步。日本目前正在考虑商法的现代化,就是尝试将株式会社和有限会社一种类型公司,融入一个合名会社和合资会社的类型,构成新的“日本版有限责任公司”。即使这样,当法律提供一定的组织形态的格式,该格式内哪些地方是被允许选择的,而不必选择一个设定的全部或不能选择,这被日本法学作为在未来探索的议程。㊱《〈組織形態と法に関する研究会〉座談会の模様》,载《金融研究》第22卷第4号2003年12月。
德国企业法律形态理论在当今世界上是比较成熟的。在法学界,法律形态被视为一个企业活动于其中的法律框架。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形态调整内部和外部关系,定义了企业的法律框架前提。其框架前提必须由法律或社会契约规定。法律形态规范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等问题:责任、股东的管理、盈利和亏损的分配。根据不同的法律形态,他们的成立、运作或清算则遵循不同的要求。这就是说,企业法律形态的确定渊源不仅仅包括国家法律,也包括社会契约。后一种观点显然不以企业法定主义为企业法律形态的唯一标准,力图在法律的形式强制和经营者的契约自由之间保持平衡,赋予企业自治以更大的空间。就此而言,企业法律形态与企业法定主义存在密切关系,但不宜将两者混为一谈,其内涵似乎应该较之企业法定主义远远复杂。或者说,企业法定主义只是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的一方面内涵,企业法律形态理论不能简单地压缩为企业法定主义,不能以偏概全。立法者对于法律形式的采取制订强制性规范,但在公司合同和公司章程中对于各个设置留有余地。这使得法定指导图像被弱化。在企业法定主义的情形下,商法和公司法赋予企业在法律上可供遴选的企业法律形态。投资者自己随意发明一种新的法律形式并引入到市场,这是不可能的。企业形态一经法定化,投资者便只能在法定化的企业形态中作出选择。如果存在选择自由,也只是对法定化的企业形态的选择自由。尤其中小企业的选择自由余地更多,也更为重要。但另一方面,法律制度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形态加以使用,让业主或投资者依据业务、税收等考量决定法律形式。具体法律形态被立法者所准确地确定,但企业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不过,由于实行“法定条件制度”,基本自由的法律形式选择在几个方面受到限制,因此不是每个企业都可以随意选择的。它承认并尊重投资者选择企业形态的自由,但又为投资者的选择自由设定必要的限度。在投资者选择企业形态方面,正是投资者的意思自治和企业形态法定化两者的良性互动,推动着企业的日益繁荣。这种法律形态虽然是可以改变在运行过程中,但对大多数企业具有长期效果性质,故而这种法律形态的选择被称为“元决策”。㊲Ekkehard Kappler Manfred Wegmann,Konstitutive Entscheidungen,in:Heinen (Hrsg.),Industriebetriebslehre- Entscheidungen im Industriebetrieb,Wiesbaden:Gabler,1985,S.81 und 161.不存在普适性的、封闭性的、无冲突的要素体系以解决法律形态选择,大部分的标准均为非量化的,难以进行经济学分析,其特性的意义和价值因目标设定而异,经营活动的、税法的、继承法的考量和决定因素具有交叉特性使得明确区分几乎不可能。在德国,企业自行支配规范的嵌入往往缓释了企业法定主义的形式强制,形成当事人在结社自由方面尽可能大的活动空间。学术界也认为,在法律强制限制的违法形态与尚允许的形态之间界限确切在何处,不由抽象的规则所确定。非类型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以刻板著称的德国人所接受的。在滥用所谓法人的法律形式时,法律系统的其他机制可以发挥纠偏功能,例如利用所谓“直索”,通过法律、特别是法律判决将滥用法律形式的康采恩和合并的法人的法律形式予以否定。
三、企业法与企业的相关法律形态
现代汉语中“企业”一词源自日语。与其它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基本词汇一样,它是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与制度的过程中翻译而来的汉字词汇,而戊戌变法之后,这些汉字词汇由日语被大量引进现代汉语。据笔者所见资料,1901年《湖北商务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德国人在重庆企业计划:译中外商业新报》的文章。㊳《德国人在重庆企业计划》,载《湖北商务报》1901年10月。1905年《新民丛报》第3卷也有《论托辣斯之利害:伴于独占的大企业托辣斯之利害》的长文。㊴《论托辣斯之利害:伴于独占的大企业托辣斯之利害》,载《新民丛报》1905年第3卷第21期,第 49~59页。曾主持《新民丛报》报务的梁启超在1910年发表的《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中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这样写道:“企业二字,乃生计学上一术语,译德文之Unternehmung,法文之Enterprise。英人虽最长于企业,然学问上此观念不甚明了,故无确当之语。”㊵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1910年11月2日),载《梁启超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89页。据德国学者迪特·赫尔伯斯特夷考其实,德文“企业”一词又是来自英语 ,世界上最早出现企业(enterprise)一词,是1771年英国的钟表匠阿尔克莱特在曼彻斯特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毛纺织厂开始使用的。
㊶参见[德]迪特·赫尔伯斯特:《企业标识》,王草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按照马克·布劳格的观点,古典经济学们的理论框架之一就是“他们没有企业理论”。㊷[美]麦克纳尔蒂:《劳动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杨体仁等译,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博尔丁也认为,企业在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实体,与企业相关的问题大多没有被论及。1937年,科斯在其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对企业的诠释,在经济学界被视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观点。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均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两者的不同表现在于: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则由权威来完成。企业形成的原因,在于其以企业内部的权威取代企业外部的市场价格调节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可以在非市场环境中更高效地进行生产。就此而言,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机制;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㊸Ronald 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4 (16)1937:386-405.科斯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于企业加以阐述,并不完全适合于法学的研究。
在德国,如同在大陆和英美法系其他国家一样,经济企业组织法存在于商法和公司法,基本规定见诸商法典以及民法典。前者的基本组织概念是“商人”“、商业公司”和“商业交易”。“商法典”显著的风格和精神是,首先关注单个的交易商,其次为合伙,而有关股份有限公司只是第三位的。企业的概念仅仅偶尔出现。在19世纪初,人们已经可以在德国听到一些稀疏的声音,要求将企业作为相关的法律主体,以取代商人和合伙。1827年路德维希·哈森普夫卢格发表的论文即是这样的典型。㊹Ludwig Hassenpflug,Eine unter einer Firma betriebene Handlung ist als das Rechtssubject hinsichtlich aller aus Handlungsgeschäften entstehenden Rechte und Verbindlichkeiten anzusehen,in:Christian Friedrich Elvers,Themis:Zeitschrift für prak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Bd.1,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827,S.59.19世纪60年代,威廉·恩德曼根据其对于实际商业生活更详细的观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想法。㊺Wilhelm Endemann,Das deutsche Handelsrecht:Systematisch dargestellt,Heidelberg:Verlag von Bangel &Schmitt,1865,82 ff..虽然恩德曼并不是孤明之见,但他的意见没有占上风,殆以其违背当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故也。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企业”的概念获得了在一般语汇和法律术语上的重要意义,成为许多法律的基本概念和对象。㊻Mathias Schmoeckel,Rechts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Seit dem 19.Jahrhundert,Tübingen:Mohr Siebeck,2008.在这些法律中,相关的法规首先根据其目的对企业进行定义。但是,企业作为法律概念体现出的是以客观法的可识别的事实状态还是尽可能作为权利载体,尚存在着争论。维特赫尔特写道:企业“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是在对象和主体的地位之间来回反弹的”㊼Wietholter,Rechtswissenschaft(Funk-Kolleg zum Verstandnis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Bd.4),unter Mitarbeit von Rudolf Bernhardt und Erhard Denninger Frankfurt a.M./Hamburg:Fischer,1968,S.276.。一些学者尝试将旧的商法的观念适应于工业法,倾向于承认企业是可用的法律概念并从中获得法律后果。托马斯·赖泽尔建议至少从拟议法(de lege ferenda)角度赋予企业本身以法律人格㊽Raiser,Unternehmensziele und Unternehmensbegriff,1980 ZHR 144,S.214 ff.。他认为,在某些领域,新的立法经验已经表明,有可能制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法。许多企业法律问题有着共同的基本结构,可以在企业法通则部分予以规定和调整。这些问题有:企业的设立、成员资格、成员的权利义务、公司内部决策的形成、股东大会的错误决议的处理、共同决定权、组织机构的代表权、会计制度、信息公开义务、企业的解散、清算和破产、康采恩、分立、合并和企业形式的转换等等。但托马斯·赖泽尔的观点鲜有人接受。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可能无法确定一致的企业概念,更多的是企业概念的意义随着每个法条关联而游弋。“法律上的企业仅能在特定的规定范围内考察才能全面理解。”㊾Ernst Steindorff,Einführung in das Wirtschaf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77,S.57.不可否认,企业的概念在大量的经济法规中扮演着迥然不同的角色。例如,企业的概念在反对限制竞争法与公司法中是不一致的。㊿Ulrich Immenga &Ernst-Joachim Mestmäcker (Hrsg.),GWB: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nkungen:Kommentar,München:C.H.Beck,1981,§1 Rdn.32-104.Johannes Zollner,Zum Unternehmensbegriff der §§ 15 ff.Aktiengesetz,1976 ZGR 1 ff.因为它需要被表述,依据不同的意义和每个法律目的而异,在不同的语境中经常被用于不同的指称,而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亦色色不同。
在本质上,企业是被作为与古代传统社会的生业、家业相对立的概念。从这种二元对立出发,企业的社会化程度是逐渐扩大的;企业被纳入法学研究的视野自始就是对于个人主义藩篱的突破。英语enterprise和德语Unternehmung的构词都是相同的,均由两个部分构成,“enter-/Unter-”和“-prise/-nehmung”,前者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可引申为“盈利、收益”;后者则有“撬起、撑起”的意思,引申为“杠杆、工具”。这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表示“获取盈利的工具”。企业是一个从事商品生产或流通的经济单位,营利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但是,企业作为社会组织自然免不了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不过,早期占主导的观念却对此不以为然,法官们一般认为,企业没有权力去做其业务范围以外之事,否则,就是过度活跃(Cultra Vires)。(51)[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张志强、王春香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时为德国最大的企业之一通用电器公司经理、后来成为德国外交部长的瓦尔特·拉特瑙,在众所周知的《论股份制》一文中,提出“企业自体”(das Unternehmen an sich)概念。经过弗里茨·豪斯曼的体系化(52)Fritz Haussmann,Vom Aktienwesen und Aktienrecht,Leipzig:Bensheimer ,1928,S.13.之后,“企业自体学说”将企业从其法律根基的所有者中分离出来,力图将其把握为独立的存在,从国民经济的立场上保护并维持之,并赋予与此相适应的责任。这其实蕴含着对“股东是其公司的主权者”理念的否定,反映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趋势,昭示着所有者的权力下降,是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宣谕。诚然,“企业自体”学说无法突破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概念的阻力,但它对于立法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德国员工共同决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1918年十一月革命。1920年,德国企业顾问法带来了工厂组织框架的第一个综合矫治。大型企业监事会中两个雇员代表的位置在该法中被明文规定。这一雇员参与权的确认,产生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的一种本能的对抗思想之中,是在德国为了同化和包容在这些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南和为俄国革命成功所鼓舞革命力量而付出的成本。(53)参见张世明:《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3页。事实上,变化尽管如此微小,但风起于青萍之末,其对于后来影响至为深远。1931年,德国公司法被修改,后又得以彻底改革,新的精神洋溢在1937年的公司法中。同时,它已从《商法典》分离出来,被编纂为一个详细的公司法典。据此,公司的经理指挥企业经营,各司其职,满足生产单位及其成员的福利、人民和国家的共同福利的需要。如果我们从该公司法的表述将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予以剔除,那么,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法律分离,企业管理相对于员工、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责任于此昭然可见。
现代经济法不惟是国家对于经济进行“干预”,干预、规制仅仅是从外部而言,其实国家对于经济调控已经深入到企业内部。战后德国制定了一系列经济调控法、经济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中小型企业政策、保护环境政策、保护消费者政策以及社会救济政策。所有这些法规和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企业的自由决策空间。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企业形式、企业的内部管理机构都逐步成为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但是在法律上依然根据私法的模式来构建其形式和内部组织机构,即这些新的变化并不影响其固有的私法结构。实际上,新的观点主要在以下方面发生了变化:企业之间的重要区别应该根据其规模或者经济重要性的不同而不同,而不是仅仅根据企业的法律形式;至少在根据企业的法律形式对企业进行区别时,必须同时考虑企业的规模。新修订的德国1965年股份公司法的确使用了“公司”一词,不过,在关联企业的新增部分,“企业”的概念替代了前者。术语的变化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这部法律旨在成为一个一般的关联企业实体法,至少作为一个概念的结构,不再基于法律形式加以区分。关于特定企业和康采恩的账目公开计法亦然,不考虑它们的法律形式,使大型企业承担在股份公司法中所包含的标准相当的财务报表、审计和报告责任。1952年和1972年的企业组织法、职工共同参与决定立法也同样使用了企业的概念。企业的概念成为有关经济指导和监督的法律法规中的主体,其中,决定因素是企业的规模而不是公司法律形式上的差别,呈现出逐步淡化不同企业法律形态之间区别的新趋势。企业法衔接并结合公司法和劳动法,以便详细阐明员工代表的法律权利和职责,业主、雇员和经理的谈判过程。(54)Gerhard Dilcher,Rudi Lauda,Das Unternehmen als Gegenstand und Anknüpfungspunkt rechtlicher Regelungen in Deutschland 1860-1920,in:Norbert Horn;Jürgen Kocka (Hgg.),Recht und Entwicklung der Großunternehmen im 19.und frühen 20.Jahrhundert.Wirtschafts-,sozial- und rechts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Industrialisierung in Deutschland,Frankreich,England und den USA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0),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79,S.535ff.在考虑国家的经济政策、产业结构等宏观调控法的维度上,德国的企业法学从企业的规模入手进行讨论,这其实涉及到笔者所称的“企业的相关法律形态”。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的政治和法律界辩论中一直被扩大大型企业的管理员工共同决定的争议所主导。1967年成立的联邦政府共同决定委员会信奉的观点是,共同决定基本上是不依赖于企业法律形态、为所有大型企业的普遍组织机制。(55)Mitbestimmung im Unternehmen.Bericht der Sachverständigenkommission zur Auswertung der bisherigen Erfahrungen mit der Mitbestimmung.BT-Drucksache VI/334,1970.自1969年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后,又召集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就是否有必要将公司法改造为综合性企业法向联邦财政部提供咨询意见,对公司法的转型提供建议。(56)Unternehmensrechtskommission,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Unternehmensrechtskommission,hrsg.vom Bundesministerium d.Justiz,Köln:O.Schmidt,1980,S.78.f.在该委员会结束工作之前,1976年共同决定法即已然颁布,该法规定的所有2000名员工以上的大型企业监事会名额在出资者代表和从业员工代表之间的平分,使德国形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唯一规定劳资双方等额或接近等额参与企业机关的立法体例。该法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法律形态有所区分,排除了个体所有人和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除外),不过强调对于所有规模的商号同样适用一般企业章程。在1980年出版的一份全面的报告中,因为其多元化的成员,企业法委员会未能圆满完成政府的委任而发展出一个自成一体的企业法。然而,共同参与决策模式被发展到独资经营和合伙。在该委员会的报告中,不仅在共同决策方面,而且在会计、审计和报告要求方面,基于企业的规模、宏观经济的意义及法律形态,企业被分为封闭(人合)企业和公共(资合)企业两类。(57)Unternehmensrechtskommission,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Unternehmensrechtskommission,hrsg.vom Bundesministerium d.Justiz,Köln:O.Schmidt,1980,S.90.ff,100f.,352ff.,424f.,429f.,477f.
德国企业法领域的领军人物库尔特·巴勒施泰特在1977年将法律学术界的争论局势概括为如下特征:被理解为法律科学制度的连接点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争议的尖锐度可能甚至超过在19世纪下半叶罗马主义者和日耳曼主义者之间的教义冲突。期望“企业法”为一个系统概念的人,很有可能遭致对其市场经济信念并不虔诚皈依的可怕质疑。(58)Ballerstedt,Was ist Unternehmensrecht? in:Festschrift für Konrad Duden zum 70.Geburtstag,Hrsg.:H.-M.Pawlowski,G.Wiese,G.Wüst,München:Beck,1977,S.15-36.Raiser,Die Zukunft des Unternehmensrechts,in:Festschrift für Robert Fischer,Hrsg.:M.Lutter,W.Stimpel,H.Wiedemann,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1979,S.571 ff.企业法学者企图为作为一个系统性学科的企业法的左右摇摆规定企业的一个基本法律概念。他们试图说明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不再应等同于股份持有人的公司,而是其中包含其他参与者,特别是员工和管理,其被构成是通过在经济原理下提供经济的商品或服务,其合法性来自于共同利益,而不是从私人利润最大化的努力。从个人主义到社会利益的兼顾,企业法迤逦走来。企业法企图囊括所有企业,而不论其法律形态或者活动的性质,改变企业法律形态的同时淡化传统的法律形态的区别,强调企业的大小而非企业的法律形态。在企业法的法律王国中,企业法律形态的诸侯封疆逐渐被消弭畛域,肩负社会责任的企业新法律形象被日益描绘出来。德国法学界对企业法律形态关注的这种发展趋向为我们提供了继续深入思考的空间。在当下中国,仅仅关注企业法律形态本体论而目无余子,可能造成思维的枯竭、法学的贫困,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到制度建设层面,而对于企业相关法律形态的研究则可能“缘溪行”,“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最终豁然开朗,发现别有洞天的桃花源景象。
四、结论
经济法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就是对于国外的认知,另一个维度就是回到中国实践。我们反对食洋不化,但并不排斥察洋而化。国人对于外国的了解的模糊,其实很容易造成对于自我认知的偏差。揽镜以正衣冠,总是要有一面清晰的镜子的。只有对于西方认知得更清楚,疏通知远,察变观风,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才能更中国化。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最初研究企业法律形态的利夫曼并不是法学家,而是经济学家,无论德国还是日本,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初都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副产品。即便后来法学界研究企业法律形态问题蔚为大观,企业法律形态的研究也并未与企业经济形态研究完全相区隔,相反,其间复杂的关联更是研究的难点所在。法律形态并非是紧身衣,而是一种宽松的运动服。制度的、一般的企业形态研究目前在国外学术界似乎已经过时,而中国学术界相反则似乎力图进行抽象与概括的体系化工作,这可能与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水准不无关系。不过,正如龟仓正彦在《关于企业形态论研究对象的考察》一文所言,日本学者的企业形态论研究者可以说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的“1940年体制”的影响。研究者出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学问不能不受到世相的影响,两者是共生关系。但与此同时,仍
然不能将资本主义的一般法则、原理与时事问题混同,应该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对于资本主义的一般法则、原理进行进逼透视。(59)[日]亀倉正彦:《企業形態論の研究対象に関する考察》,载《名古屋商科大学総合経営·経営情報論集》,名古屋商科大学論集研究紀要委員会編,2010年第3号。这其实关系到费肯杰所说的法学推参阐述问题。我们固然可以甄采国外的制度设计,但不要以为异国企业法律形态理论构若画一,企业运作在深度治理之下皆有法式,便可以援以为准,企业形态的体与用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深究其本。卡多佐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的原则:“我们必须保持两种警醒。一方面,我们尊崇法律的确定性,但必须区分合理的确定性与伪劣的确定性,区分哪些是真金,哪些是锡箔;另一方面,即便实现了法律的确定性,我们仍须牢记:法律的确定性并非追求的唯一价值;实现它可能会付出过高的代价;法律永远静止不动与永远不断变动一样危险;妥协是法律成长的原则中很重要的一条。”(60)[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法律,就像一个旅行者,必须准备翌日的旅程。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企业法律形态绝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地冥思苦想为封闭的体系结构。后现代思潮的解构作用就在于其对现代性的反思,以非理性主义矫正理性主义的僵化。企业法其实是一种继续革命,是从自制框架解脱。经济法在本质上更是变法之法。企业形态法定化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结果。中国应该采取企业法定主义原则,提供对企业形态的法律模式选择菜单,备置一格,俾企业人各视其业之所适,及其所愿负担责任之限度,随意采择使用。企业形态法定主义的原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属于一种基础性的法律建设,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否则乱象丛生,治丝益棼。目前这种默示的企业法定主义其实也是中国人惯常的实用理性主义的做法。不过需要注意,企业法律形态的丰富内涵不能被化约为抽象的企业法定主义原则,否则就会将投资兴业的康庄大道变为羊肠小路,与增加投资者对企业法律形态选择空间的初衷背道而驰,无法为已经具有相当金融、经济资源的公民、企业和地方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组合载体。在某种意义上,企业法定主义原则如果不希望停留于口号的话,那么其贯彻必须以企业法律形态的合宜性、充分性为必要条件。中国学术界普遍性的观点认为,企业形态法定主义不仅强调企业外观的严格法定,还要求企业内部关系组成的严格法定化,通过对企业外观和内容的严格法定,从而避免非典型的企业形态及非规范的内部关系为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安全状态。(61)徐强胜:《企业形态法定主义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1期。我国目前以责任和组织化程度为标准划分的独资、合伙和公司三种企业形态立法过于概念化和封闭化,与此认知偏颇不无关系。
张世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