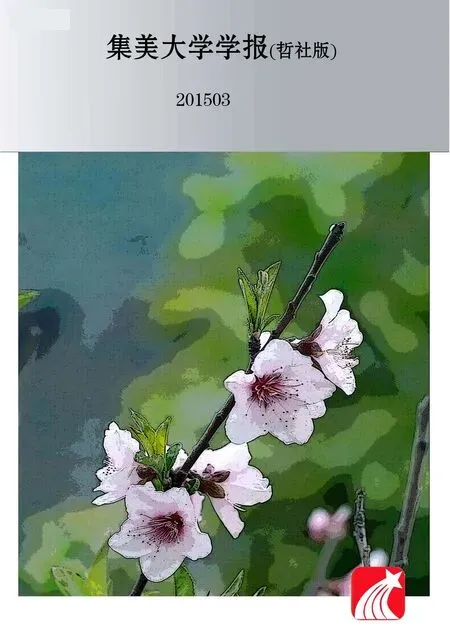超越异化 返归本真——卡尔维诺小说的异化主题研究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 2015) 03-94-07
[收稿日期]2014-12-27
[修回日期]2015-03-20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Y201432113)
[作者简介]郭红玲( 1978—),女,山东潍坊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1923—1985)是一个以善变而著称的作家,他在终其一生的创作中,不断追求新的文学表现样式,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姿的小说世界。从初登文坛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 1947),到以单元组合式结构的《马科瓦尔多》( 1952)为代表的关注现代人生活境遇的系列作品,再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意大利童话》( 1956)及童话色彩浓郁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 1952—1959),再到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实验风格的融入科幻因素的哲理小说《宇宙奇趣》( 1965)、由图画与文字组合而成的《命运交叉的城堡》( 1969)、数字排列组合结构的《看不见的城市》( 1972)、由10篇小说合成的长篇小说《寒冬夜行人》( 1979),直至80年代的最后一部哲思小说《帕洛马尔》( 1983),我们可以发现,变化无穷是他的乐趣所在。在这些变化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永远不断创新、其作品如晶体般折射多面光彩的作家卡尔维诺形象。
有着如此丰富的创作成就,卡尔维诺自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目光。国外学界的关注点主要有:卡尔维诺作品中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童话和民间文学思维对其创作的影响、卡尔维诺小说中的形式元素、后现代主义写作模式、卡尔维诺小说的叙事学考察、卡尔维诺文学观的理论考察、卡尔维诺与康拉德、海明威和博尔赫斯等作家的互文性考察、卡尔维诺创作风格的演变受之于文学社团“乌利波”( Oulipo)的影响等。有关卡尔维诺的传记作品、生平创作与评价作品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为卡尔维诺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相较于国外的丰富成果,国内学界的研究略显单薄,主要集中在其作品的后现代特征、童话与民间思维、诗学理论、科学文本观、空间建构等方面。
通过爬梳整理卡尔维诺的主要著作,笔者发现,尽管卡尔维诺的小说形式在不断变化,创作理念在不断更新,但求新求变的背后,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那就是对异化的关注与思考。基于此,笔者拟对卡尔维诺小说的异化主题进行梳理,探寻其超越小说形式变化的兴趣所在。
一、异化理论及卡尔维诺对异化的关注
异化( alienation)一词源自希腊语,本义为分离、疏远,现在一般指由主体创造出来的物反过来与主体对立,具体到人自身,就是指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控制,人变得非人化了。在哲学史上,黑格尔于19世纪初最早提出关于异化的完整概念,指的是“精神主体的自我异化,而精神实存的一切向客观现实的过渡和对象化的活动都成了主体走向异己物的自我疏远化”。 [1]与黑格尔认为异化的主体是绝对精神不同,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神学,强调了神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继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异化理论。马克思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提出了关于异化问题的四个要点: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虽然马克思对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但他的异化理论对后世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影响深远。以卢卡奇、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随着工业社会的急速发展,在今天,异化的发生不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已扩展至所有社会类型工业化国家的政治、文化、思想、消费、日常生活等众多领域,遭遇异化的人类主体也不再限于被统治阶级,同时包含了社会中的普通人。可以说,异化无处不在,遭遇异化是当今人类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本文的异化主要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理解认识层面上进行探讨的。
二战结束后的三四十年间,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西方各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物质的繁荣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看似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与此同时,异化问题日益凸显。卡尔维诺正是生活和创作在这个“黄金年代”。从事多年记者和编辑工作的卡尔维诺对周遭世界的变化异常敏感:“我确信我是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人。我们那个时代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我写的任何作品中。” [2]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作家不可能不注意到日益突出的异化现象。事实上,笔者认为,卡尔维诺对异化问题是极为关注的。他在1967年曾经说过:“现代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说出了社会和个人本来想说而又没有意识到的一切,这就是文学所不断提出的挑战。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 [3]342他看清了一个无奈的现实,那就是: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发展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这是无法阻挡的人类社会大趋势。但也正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发明的科技成果越先进、享受到的物质越豪奢,人类就会感觉到自己与本真的生命状态渐行渐远。孤独、茫然、恐惧、绝望等心理时时折磨着我们这个所谓文明社会中的人们。
在当代社会的全面异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事实的情况之下,各路作家、学者、思想家给出的扬弃之道也不尽相同。马克思主张要依靠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否定私有财产、消除经济上的阶级划分来将全人类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卢卡奇、列斐伏尔等人提出以总体性克服异化,即人从支离破碎走向自由,其中艺术具有关键作用;弗洛姆要求回到人本身,可通过制度及精神变革;存在主义者与上述见解均不相同的是,他们不主张通过经济或社会制度变革,“真正意义上讲,存在主义者更倾向于认为人们消除异化感的真正方法潜在地存在于他们的世界观之中”。 [4]43存在主义者认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二元论是世界的异化感产生的根源。海德格尔关注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努力寻求将人们从对于存在的疏离中拯救出来的出路。“面对此在的沉沦和被抛,面对现代科技对本真性的彻底背离,海德格尔设想了两种返乡的途径:一为技术的自救,二为诗意的栖居”。 [5]但第一条途径很快被海德格尔自己否定,最终,就只剩下了“诗意的栖居”。
卡尔维诺为寻找文学的新出路而不断实验新形式,他的《美国讲稿》(又译《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重点探讨了文学创作中的技巧问题,而在不断进行文学新形式实验的同时,其关注点始终不脱离人类的异化问题。意大利当代文坛重要作家埃利奥·维托里尼( Elio Vittorini,1908—1966)是卡尔维诺走上文坛的领路人和导师,1960年与卡尔维诺合编《梅那波》( Menabo)杂志,即是“探索如何以新的小说形式使人们意识到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问题”。 [3]165
深切体悟到人类异化之痛的卡尔维诺在自己的创作中不停思考、探寻解决之道:“如果人类没有一部分人性格内向,对世界的现状很不满意,如果没有一部分人盯着不会发声、不会活动的文字整天整天地苦思冥想,那么文学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的性格当然符合这类人的特点。” [6]364“我喜欢说的故事都是人类追求完整的故事,然后透过实质及精神上的同时考验,超越被强加在现代人身上的异化与分裂”。 [7]8考察其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卡尔维诺对异化问题的持之以恒的关注。
二、卡尔维诺小说中的异化现象
从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路》( 1947)到最终的总结之作《帕洛马尔》( 1983),卡尔维诺对当代社会愈益突出的异化现象有着持续的关注和多样的描摹与展现。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人的自我异化
在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中,卡尔维诺就塑造了一个“非儿童化”的儿童主人公形象——皮恩。皮恩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与做妓女的姐姐相依为命,在大人们的眼里,他是一个“没教养的孩子”。孩子们不愿意和皮恩做朋友,“皮恩只能留在大人的世界里,尽管大人们也不欢迎他,大人对他来说和对别的孩子一样,是不可理解的,是有距离的”。 [8]10就在皮恩所不能了解的大人世界里,他接触到了性、暴力这些本应远离孩子的事物。皮恩就在这个错位的情境中经历着迷惘与困惑,他参加了游击队,却不知在做什么,更不知为何而做,只是被革命洪流裹挟着向前走而已。皮恩正是我们时代被异化的人的典型之一:置身于生活的滚滚洪流之中,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交织而成的迷雾。在倾注了卡尔维诺诸多心血编撰而成的《意大利童话》( 1956)中,首篇即是《无畏的小乔万尼》,小伙子乔万尼勇敢无畏,战胜了以肢解自己吓人的巨人,并得到了三罐金币和一幢楼房。但在成为富人后的某天,他却被一转身看到的自己的影子吓死了。原本英勇无畏的年青人遍历世界都安然无恙,却最终因停留于一幢有金币的房子而吓死,这似乎正可看作是从原始自由中一路走来到现在身处迷幻物质世界中的现代人类的写照。正如前面所引述的卡尔维诺所言:“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小乔万尼最终由于无法承受生于自身的鬼影死去。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们更多的财富,但与此同时,感受到的人际疏离、不安全感、孤独感也是空前和无以复加的。按照弗洛姆的分析,异化否定了人的生产性本能,富人乔万尼的生活只剩下了“在窗口抽烟斗”,正如现代人的工作与生活日益专门化、单一化,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局限于狭小的天地与封闭的空间,体验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墙上的鬼影”由此显现出来。正如弗洛姆所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 [9]370
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卡尔维诺对现代人被异化的灵魂的描摹更加突出。《分成两半的子爵》( 1952)中,梅达尔多子爵被炮弹劈成两半,从此分裂成善与恶两个半片,无恶不作与乐善好施皆为他之所为。应该说,集中于一个人物一身的善恶对立题材并不鲜见,如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 1839)、英国作家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 1891),相信卡尔维诺在创作《分成两半的子爵》时也确实是受到了前两位作家特别是坡的启发(卡尔维诺自己曾说过,坡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但卡尔维诺既不是为了创作出恐怖神秘气氛的哥特小说,也不是为了宣扬艺术美之永恒,而是重在表现现代人身上的异化与分裂。在作品的后记中,作家说:“我采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叙事的对立来突出我所感兴趣的那个东西,这就是分裂。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 [10]94在经历痛苦的决斗后,子爵的善恶两半重新粘合在一起,这也表达了作家对人类由分裂复归完整的期望与信心;《不存在的骑士》( 1959)的主人公阿季卢尔福则彻底成了一个盔甲之下荡然无存的空心人。他有身份、有地位,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是查理大帝手下的出色军官,但作为人之本性的“食”“色”却无一能为之。他不停地追寻自我之存在的确证,却最终失败至消失无踪。现代人常常叩问的“终日忙碌为何”在阿季卢尔福身上似乎显现出了答案:我们只是自己外壳的工具,为了它的完整与光鲜,我们不惜掏空自己去听命于它、受制于它。
(二)人与自然的异化
人是自然之子,原始人类敬畏自然,奉之为神灵,今人则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力图成为自然的主人。对此,我们曾一路高唱凯歌。时至今日,我们已然慢慢意识到:人类征服自然之途,也是亲手毁灭家园的罪恶之旅。换言之,人类的生存空间被人类自己的活动大大异化了。对此,卡尔维诺在多部作品中均有所展现。《阿根廷蚂蚁》( 1952)讲述了一个海边小镇所遭受到的蚁灾:蚂蚁们无孔不入,甚至爬进孩子的耳朵。因为肆虐的蚂蚁,镇上的居民永无宁日。至于本应保护民众的政府机关“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却实际上是当地所有蚂蚁的大本营。这很难不让我们想到,蚁灾看似来自自然的不幸,实际却是荒唐人类的自酿苦果。在1984年1月30日的一封信中,卡尔维诺说:“《阿根廷蚂蚁》不是像所有的批评者一直说的那样,是卡夫卡式梦幻小说,它是我在一生中写的最现实主义的小说……” [11]《烟云》和《阿根廷蚂蚁》是被作家自己并列在一起的作品,源于“一种结构和道德上的相似”。 [11]《烟云》中的主人公和《阿根廷蚂蚁》中的主人公一样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所不同的是,《烟云》中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再是成群的蚂蚁而是无处不在的烟尘:载重卡车“喷着令人恶心的浓烟”、黑猫出去转一圈“都成了一只灰猫”“你只要用手摸一下阳台栏杆,你手上就会沾上黑色的痕迹”“那些熏黑了的房子,那些昏暗的玻璃窗户,那些脏得不能依扶的窗台,那里面居民的为别人看不到的面孔,还有天空中这层笼罩着一切、使人们看不清一切、使一切失去其原有形状和价值的烟雾” [8]148……与《阿根廷蚂蚁》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人公所供职的环保刊物《净化》竟是打着治理环境污染旗号的制造污染的核心机构。我们惊讶地发现,卡尔维诺小说中的想象如今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一一兑现。
在马科瓦尔多系列短篇中,也有多部作品展现人类生存空间的异化:如《好空气》( 1953)中,生活在贫民窟的孩子身处城市中污染最重的阴暗街区,以致“面色发黄和羸弱虚脱”,连医生建议的呼吸一点好空气都需要“乘电车走过很长一段路程”,大批的工人们因为工作患上了严重的肺病;《高速公路上的森林》( 1953)中,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及公路边的广告牌取代了森林成为遮蔽人们视野的奇怪阴影;《河流最蓝的地方》中,主人公马科瓦尔多因为“连最简单的食品都受到诡计和掺假的威胁”,努力寻找安全的绿色食物。当他雀跃着以为捕到了最干净河流中的鱼时,却被警卫告知,看上去最干净的蓝色河水实际上是油漆工厂的蓝色所染;《月亮与霓虹灯》( 1956)给我们展现的是月亮和星星已被霓虹灯广告牌的强光逼退的夜空。在已被异化的这个空间环境中,人们找不到安全的、安静的、能让人身心放松的所在,人彻底成为了破坏自然的恶果的最终承担者。
(三)人与社会的异化
在分析劳动异化时,马克思指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 [12]37也就是说,人被自己的所造之物奴役,这个所造之物可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有形的劳动产品、商品,也有可能是无形的社会制度、价值规范等。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当代社会,人与社会的异化突出表现在科技异化、交往异化、消费异化和思想、文化的异化等。《马科瓦尔多逛超级市场》就突出表现了当今社会中的消费异化:贫穷的小装卸工马科瓦尔多带领全家逛超市,原本袋中无钱只能看看的他们却不由自主地在各自的购物车中装满了货物,周围人群更是如此。人们不问自己有无需要、需要为何,而只顾在广告的引诱下疯狂购物。正如弗洛姆所言,这种消费的虚假需要为人们所接受正是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的内在需求所致。 [9]只有人们不断地消费,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利润的最大化。商品由人制造出来,但市场中琳琅满目的商品又胁迫人们做出疯狂的举动。《圣诞老公公的孩子》中,一到圣诞节,富人们便大派礼包为穷人营造“安乐乡”的假象,好在这祥和快乐的氛围中迎来明年更多营业额与红利。“可以说,在生产和日趋现代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处于社会组织的控制和商品化之中,甚至旅行、休闲、节假日也成为一种被商业化流程和日程操控的活动”。 [13]48人们的节日活动都被笼罩在了商品利益追逐的大网之中,这不啻为日常生活异化的生动刻画。
曾被卡尔维诺设想为“五十年代新闻档案”三部曲之一的中篇小说《房产投机》( 1957),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是“以知识分子面对消极事实的反应为主题”。 [7]224作品的主人公是文人知识分子奎因托,所谓的“消极事实”指的是以滚烫的水泥迅速侵占主人公家乡——利古里亚海岸的房地产热潮。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 [14]25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中最耿直、勇敢,特立独行,为弱者代言的一类人。但我们和作者一同失望地发现,奎因托虽然从内心里并不认同将绿被密植的家乡变成水泥森林,但糟糕的收入却让他完全败下阵来,因为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在国家对一个缺少收入的家庭实施如此不成比例的恶行中,那种一向被优雅语言唤作‘立法者意图’的东西实在是以一种高明的逻辑奏效的:打击不可生产资本,打击任何不能或是不愿使其资本再生产的人。” [15]511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本应坚守底线的知识分子奎因托只好选择随波逐流,纵身跃进房产投机活动中。奎因托的无奈、茫然、惨败,典型地表现了当代社会中经济制度对人的奴役及人在此间的异化。
三、卡尔维诺对异化问题的思考
如何超越被强加在现代人身上的异化与分裂?笔者认为,卡尔维诺对异化解决之道的思考是倾向于存在主义者一边的。通过对其作品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卡尔维诺对此一问题的思索随创作发展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这一哲思发端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马科瓦尔多系列。在这一系列短篇小说中,作家以小工马科瓦尔多人物形象为中心,展现现代工业化社会底层工人的悲惨处境与巨大生存压力: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冰凉的午餐、满身的债务、羸弱的孩子、缭绕的烟雾……但与一般的描写工人的小说不同的是,作家以他自己所提倡的轻逸笔法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人形象:身处异化世界中的马科瓦尔多并未被工业社会中艰难的、机械的生活磨去作为一个人该有的丰富与敏感,在他的身上保留了儿童的天真与诚挚。为生活所迫必须停留于城市,但马科瓦尔多却不喜欢城市,他感兴趣的是被油漆、柏油、玻璃和水泥覆盖的城市背后的自然一面,他“有一双不是很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他喜欢“树枝上一片发黄的树叶,纠缠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没有一只马背上的牛虻,没有一个桌上的蛀虫洞,没有一块人行道上被碾扁的无花果皮,是他不注意的,不用来作为推理的对象的,通过它们,可以发现季节的变化,理解自己灵魂中的愿望,体会对自身存在的痛苦”。 [15]173可以说,这是一个卡尔维诺将自身思考植入其中的人物形象。繁华都市中,当绝大多数人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享受中成为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时,马科瓦尔多却是其中难得的清醒者,保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的敏感者。就在看树叶吐芽、望飞鸟翱翔的难得宁静中,乐观的马科瓦尔多暂时忘却了为工业生产机器所奴役的悲哀,体验到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感。这个寓言式的主人公可以被看作是50年代初期卡尔维诺的自画像。
50年代末期的“祖先三部曲”聚焦现代人的异化。在《树上的男爵》中,面对压抑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社会,柯西莫男爵选择了逃离到树上去。这是一种面对异化世界的决绝姿态,他不再像马科瓦尔多一样必须蜗居于令人生厌的繁华都市,而是以十足的行动力与社会拉开距离,“在启蒙话语中重塑自我,开拓全新生存空间”。 [16]但最终,这个新的生存空间随男爵的离开也瞬间消失了。男爵式的逃遁自然太过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有效操作。同属50年代作品的《阿根廷蚂蚁》和《烟云》的主人公都用斯多葛式的冷静来对待已被异化的空间环境,这也预示了卡尔维诺后来的冷静沉思者帕洛马尔的出现。
六七十年代的卡尔维诺将自己的创作重心转向小说的形式探索。直至1983年,凝聚作家后半生思想结晶的《帕洛马尔》推出,为我们提供了作家面对异化问题一生思索的最终答案。《帕洛马尔》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不讲述故事,而是由主人公的27个相对独立的思考片段组成。帕洛马一词来自于装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马山峰上的世界上直径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卡尔维诺借用此名来命名作品主人公,透露了他要观照宇宙的雄心。帕洛马尔以观察与沉思作为自己主要的生存方式。卡尔维诺说:“帕洛马尔是我自身的映照。这是我创作中最富自传色彩的一部作品,一部用第三人称写的自传。帕洛马尔的任何经验,都是我的经验。” [17]在这部自传式作品中,作家对自然、社会、宇宙、人生等进行了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在海滨、在庭院里、观天象、在阳台上、购物、在动物园里、旅游、处世待人、默思。马科瓦尔多那里偶一为之的凝视在帕洛马尔先生这里都变成了长时间的注目沉思。他的这些观察与思考是带着问题进行的,即在这个异化世界中,面对着全体人类的分裂、压抑、孤独、茫然等普遍状况,人应如何自处及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相较于马科瓦尔多的童心、柯西莫男爵的执拗,帕洛马尔多了现实生活中必需的成熟与稳重: ( 1)帕洛马尔认识到,人不可能离地而居,“这就是我的栖息地……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只能在其中生存”; [6]242( 2)帕洛马尔先生在观察壁虎时领悟到,应该像壁虎捕食时一样安于现状、减少消耗; ( 3)帕洛马尔先生抹掉了自己头脑里的各种模式,决定寻求自己内心的安宁,观察世界,同时也是更加深入地了解与观察自己。作家借帕洛马尔先生宣称,他要尽一切努力,与世界协调一致、和睦相处。如果说前两者都是带有寓言色彩的童话式人物的话,那么帕洛马尔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卡尔维诺式知识分子的肖像画。这一现实性也说明了作者一生哲思最终的成熟。
我们看到,帕洛马尔在摒弃了一切可能甩掉的束缚后,用最原始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思考存在。帕洛马尔努力打破一切世俗既定之模式,摘掉所有有色眼镜,“使自己的信念保留着没有具体形状的流体状态” [6]299以适应人类社会支离破碎、毫无规则逻辑可言的生活现实,由此,一切以最原始、本初的状态显现出来,我们也与这个世界、与他人、与自我恢复了直接的、本真的联系。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即是要求人返回本源后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可见,卡尔维诺在对如何超越异化的探寻之路上,最终与存在主义者走到了一起。
四、结语
在《看不见的城市》的结尾,马可·波罗告诉可汗:“存在着两种免遭痛苦的法子,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持续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18]299这也正是卡尔维诺想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大多数人都已在这个异化世界中心甘情愿地接受一切享受一切,被异化而不自知,自知而不自我救赎的同时,还有一小部分人在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苦苦搜寻返归本真之途,并努力给有助于我们返归本真的事物以存在空间。诚然,作家形而上的思考在当今轰鸣声声的工业社会中略显苍白无力,但只要是读到了卡尔维诺文字的人,谁又能无视心底的那份触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