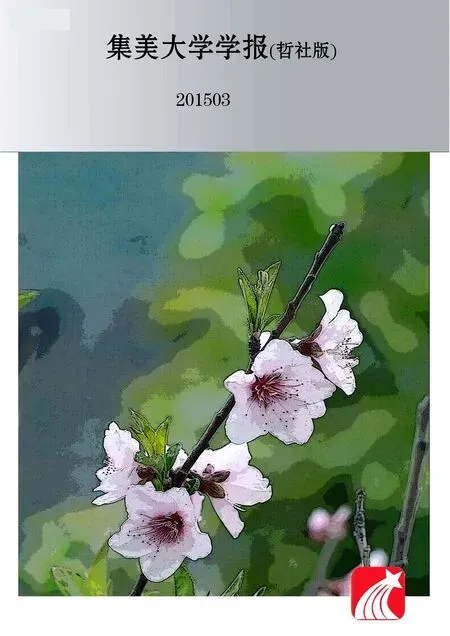创意时代“困局”中的传统手工艺——以竹编工艺为例
[摘要]传统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竹编工艺无论从实用价值还是操作工艺上来说,都是传统工艺的典型代表。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生产方式的两次转变,传统工艺在自给自足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中进入两难的境地。以竹编工艺为例,在分析其生产方式与边缘化原因后,提出了在当代艺术中发掘传统工艺与当代生活的一种新思维。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 2015) 03-19-04
[收稿日期]2015-05-10
[修回日期]2015-06-30
[作者简介]汤南南( 1969—),男,福建漳州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图像创作与批评研究。
自人类进入机械时代以来,手工与机器的矛盾成了人类社会的核心矛盾。这在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论述中尤为明显,也在现代主义艺术中引发了关于“艺术何为”等问题的争论与斗争。传统手工艺在创意时代的“困局”就是一个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
一、当下传统竹编工艺的消泯
随着包豪斯主义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流水线上获得巨大成功,这种具有人文关怀的“理性主义技术观”与“作为人的总体艺术观” [1]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次美术运动与设计运动中得到了体现,因而也迅速在各大美术与建筑专业院校设立了工业设计等专业。但是,就在我们已经能够如美国人一般制造出具有冷冰冰的机械感与后现代的杂乱喧嚣的艺术与设计产品时,很多人却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丢失了中国文化深处的人文情怀。这种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味道,这种味道散发在生活的点滴之中,小到一杯一盏的小物什,大到修心治世的个人抉择。故而在日益粗糙的行居坐卧的物件中我们能感知到的是一份文化情怀的渐渐消泯。依如传统竹编工艺在我们生活中的消退。
竹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四君子的代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各种手工艺品的形式伴随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到明清时期,竹子在中国传统工艺中还是备受宠爱的对象。作为中国古老的生活使用素材,其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和吴兴县(今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皆有出土竹编织物,且在当时已经有了较为规则的编织纹样。 ①在后来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对这一材料使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从单纯的储水器、盛放食物的器皿发展到制作成竹席、竹扇、花灯、竹篮等生活所需品,揭示了竹编工艺在现实生活中的演变与发展,朴素、接近生活的实用性使它成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中国的竹编工艺早在殷商时代到战国时期就已经非常精致了。在湖北江陵一带的楚墓中,已经出土了编制非常精美的彩色竹席和竹箧,而且当时已有流传下名姓的竹编工艺师。据传说,是一个名叫泰山的竹编艺人,他从学于木匠大师鲁班,潜心研学竹编工艺,对当时竹编工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故而,时至今日仍有人把泰山作为竹编的祖师。悠久的传承历史,加之竹子本身具有繁殖能力强、生长快、柔韧性高的特点,亦适用于农耕时代人们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成为竹编工艺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种经过人的双手千万次的抚摸,融入了匠人的劳动与智慧的竹编制品在现代生活中变得珍贵而稀有。在我们童年时代还能看到妈妈用竹编的篮子买菜,看到老爷爷编的竹椅、竹凳;现在,塑料袋取代了妈妈的竹篮;各种材质的座椅取代了爷爷的竹椅、竹凳。在中国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伴随着飞速发展的经济,旧日里温情脉脉的手工艺制品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消逝。它们脱离了实用功能,变成了带有怀旧味道的装饰品。
二、传统手工艺陷入困境的分析
近年来,仿效日本而在各地掀起了为数不少的“中国民艺运动”。运动的支持者认为,机械化取代手工劳作,压制了人们手工劳作时带来的价值感、存在感以及成就感。施莱默在《包豪斯舞台》一书中直接阐述了这一运动的缘起:“机械往往被用来逐利,而产品则粗制滥造。而且,由于人类为机械所左右,剥夺了工人的种种乐趣。” [1]尤其是竹编,这种蕴含东方传统价值元素的手工艺,在机器的运转下变得荡然无存。
随着这些大大小小的“民艺运动”的兴起,另一些问题也越发凸显。因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需要,笔者曾多次深入中国各地竹编文化发达地区考察,这些民间工艺面临的危亡境地远远比描述的严峻得多。浙江安吉曾被称为“中国竹乡”,是全国竹工艺最集中的地方。10年前,安吉的手编艺人随处可见,而如今,却个个转行,仅剩的几户也转型做起了竹纤维生产,手工艺人已难寻觅。
首先,竹编作为一种经验型技术,对竹编艺人的手头功夫要求高,且成品过程缓慢。行业的作坊制形式、师傅的口传身教又大大加长了一个学徒转型成为成熟手工艺人的成长周期。学徒们在老艺人教授的生产实践中,从原材料选取、操作流程都要不断地实践学习,这种经验性技术一旦被掌握也很难更改。其次,机械化取代手工劳作,压制了人们手工劳作时带来的价值感、存在感以及成就感,机械往往被用来逐利,而产品则粗制滥造。而且,由于人类为机械所左右,剥夺了工人的种种乐趣。流水线的劳作无法带来幸福感,仅仅是用劳作时间去交换一些生活资料,没有署名权,做得好也没有荣誉感。而且当下的竹编流程也趋于流水线生产,他们分工明确,编织的只会编织、磨光的只会磨光,让磨光的人去编织一定弄得他们一头雾水。换而言之,如果他们脱离了工厂便什么成品也做不出了。这种传统中世代传承而需要几代人经验累积的工艺被机械的流程所摧毁。用体力交换生活资料令工人们例行公事地工作,创造中产生的自我价值的定位消失不见,工作变得枯燥而没有心意。但手工劳作却是有的,在制作的过程中,人的感觉和创造力的调动,让每一件物品做出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让仅存下的编织艺人坚持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民艺运动之所以迟迟不能形成规模,主要的问题是由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所引发的。一个学徒需要花上3年时间来学习如何劈竹子、劈蔑,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篾匠,而年轻学徒宁愿进城打工也不愿在作坊里待上3年破竹削篾苦练基本功。这就是快节奏的流线生活、快餐文化影响下的手工艺面临的最大困境。
另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已经随着网络化与数字化的快速普及,进入了后工业的“创意产业”时代。任何可以令人新奇的产品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不菲的价值。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使得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到我们的传统工艺。但事实上,矛盾也在于此——好的手工作品,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而在当下“泛创意时代”中,一件物品“创意”价值被不断抬高,让手工艺人想找寻捷径走向单纯设计者的道路,使作品越来越脱离制作的劳动过程。
三、经济与传统手工艺的两难
艺术的创造性是从劳动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创意与劳动并不是决然分割为两个阶段,而是平滑地过渡。一味迎合市场口味,想方设法将竹编转型,放弃以往轻车熟路的操作方式,从中加入“新”的元素,让年轻的手工艺人们一时无法掌握方向,时常制作出哗众取宠的工艺品,导致传统工艺失去了原本的实用性,让这一功能性领域逐渐被工业产品占领。一些艺人则将农家乐屋子做成竹制装潢,用创意来弥补竹编本身的局限。虽具有一定的视觉效果,但其风格也不能应对当代居住空间的多样化环境,更不可能大规模地生产。
器物如果失去了原本的生活语境,将很难延续发展下去。竹编工艺如此,当代民间工艺亦然。因而,我们事实上面临的是一种两难的困局——人们在工艺美术与工业设计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当代的设计教育越来越朝着专业化、工业化的方向发展。设计学科不断学习西方后工业时代以及计算机时代的数字设计课程,持续地将传统工艺美术转换为现代工业设计;另一方面,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成功,又在打破着工业化、单一化的生产方式,让人们的生活重新回到“温暖”的手工时代。全球化因区域竞争而呈现出一种单一的业态,以此形成专业分工的集群式效应;当代社会却同时又需要让这些行业的人们适应网络化的个性化与手工化的生产方式。一个区域只负责一种产品,确实是具有区域竞争性优势,但与此同时到来的是手工艺脱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脱离了当地文化丰富的营养,而成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这对传统工艺技术传承造成了消极影响。
从经济层面的角度来看,传统工艺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存在着很难简单调和的矛盾。传统工艺生产的小规模使其很难具有生存能力。高品质和独特的艺术性决定了手工艺的低产出,而这些又意味着高价位和长时间的投入。但是产品可能会因为过于昂贵而无法出售。出于经济的考量,出路就是增量的生产,扩大规模,进一步的劳动分工,使用机器,最终使得工艺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距离缩减。怎样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很大程度地缓解目前传统手工艺的困境。针对这一问题约翰·沃克在他的《设计史与设计的历史》提到一个调和的方案:“许多成功的艺术家——手工艺人通过为他人进行设计——外部工作人员或作坊——来进行弥补(威廉·莫里斯的生产就是如此)。” [2]这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但并不完全能解决中国复杂且日益衰微的手工艺。
如何使传统工艺在能延续幸福感的同时又能在现代社会站稳脚步仍然是手工艺人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将这些工艺重新引回地方文化与人们熟悉的生活语境成为成败的关键。日本曾受中国竹编艺术的影响,在茶道中加入了许多编织类的相关物品,他们把竹编器皿转型为装饰性物品,在进行茶道仪式的时候作为摆设并使用。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竹编大师从功能性的编织类品逐步向雕塑型编织品转型,做出了大量的竹编雕塑品。这些竹编雕塑品,承载了传统手工艺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涵。这给竹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在制作作品的劳动中体会到了幸福感,最后的成品也是手工艺人们价值的体现。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了手工艺与艺术的微妙转化和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国内些许一线当代艺术家开始关注传统手工艺在自己艺术作品中的组成比例,甚至他们展出的作品(一些装置和视觉作品)有些直接是经过自己设计的手工艺。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出身学院的科班艺术家并不具备熟练的手工艺技术,往往他们提供的只是一个主题或者某一个形象。例如一个当代艺术家需要一个“花木兰”的形象,而这一形象需要用竹编技术完成,这时手工艺人与艺术家必然产生一场困难而有意义的交流。看到手工艺人的作品出来之后,艺术家震惊了,技术和思想的力量成就了这件艺术品。正应和了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柳宗悦的精彩说法:“手与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手总是与心相连;而机器则是无心的。所以手工业作业中会发生奇迹,因为那不是单纯的手在劳动,背后有心的控制,使手制造物品,给予劳动的快乐,使人遵守道德,这才是赋予物品美之性质的因素。” [3]手与心的相通赋予了竹编“花木兰”蕴含文化韵味的美的性质。这种艺术家与多年竹编经验的师傅合作的方式提供了另一种解决艺术与手工艺之间距离的方式。
手工艺人的地位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和艺术发展泡沫中有着比较尴尬的状态。正如上面谈及的那个“花木兰”竹编艺人,他的作品可称得上是当之无畏的艺术品,但他的署名权需要征求艺术家的同意。手工艺者处在这样的地位值得我们思考。一方面他们获得正式展示的机会很少,大多是在各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卖会上,他们的技术和用心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和公众形象方面的不确切性可能具有负面意义。传统手工艺在当今市场化的局面中有太多质量低劣或粗俗不堪。同时,它又在人们心中具有一种“历史的荣宠”。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手工艺和艺术之间更多的接触和默契。无疑,当前,在这场交流中当代艺术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和占据的资源成为主动者。
四、传统手工艺与当代艺术结合
在当下的中国,如何在复兴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将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和技术传承下来,在这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界做出了积极地探索。与柳宗悦领导的日本民艺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的转变十分相似的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在2003年当代艺术市场不断活跃之后,也出现了一线生机。大量当代艺术家纷纷涌入景德镇,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气质的生产核心,而景德镇也随着当代艺术的介入,开始从新的视野、从自身的生活现实出发,来改造传统手工。中国美术学院不但成立了专门研究陶瓷的研究中心,还将漆器也同时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邱志杰教授,在竹编之乡安吉所设立的工作室,亦成为了安吉当地乃至当代艺术界竹编类作品制作的中心。
与艺术家的联合是手工艺尖端产品有效的推广手段。但以此来拯救整个手工艺界,这似乎是困难的。如今是一个“创意”快速发展的时代,计算机创造的网络平台几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如何有效的将这一平台与手工业的发展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很大的契机。如今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的发展,发展出一种新的产品类型来顺应消费者的需求。这种经济可行的小批量生产,甚至是一次性生产,在当下的经济模式下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可以期待,它也将成为解决手工艺与传统工业之间冲突的最具有潜力的模式和武器。
创意时代“困局”中的传统手工艺终究该何去何从,面对着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对其未来抱着积极期待的态度。通过当代艺术作品对手工艺的精致要求,对日常生活的重新挖掘,我们有理由期待传统手工艺将会逐渐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与当下时代的诉求相融合,打造一套有关于心灵与劳动的生活方式——就如同包豪斯为德国人们所打造的现代主义生活一样。手工艺是一门技术,更是手工艺人自我修行的过程,手艺的精熟程度代表着手工艺人的精神境界的高度。手和心连在一起的时候,手艺不仅创造出了手艺品,也成就了心灵手巧的手工艺人。在那些熟能生巧的时刻中,它创造了艺术品,也让每一个从事手工艺的人,发现了自己,转而为艺术而创作,这也成为我们从事现代艺术创作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