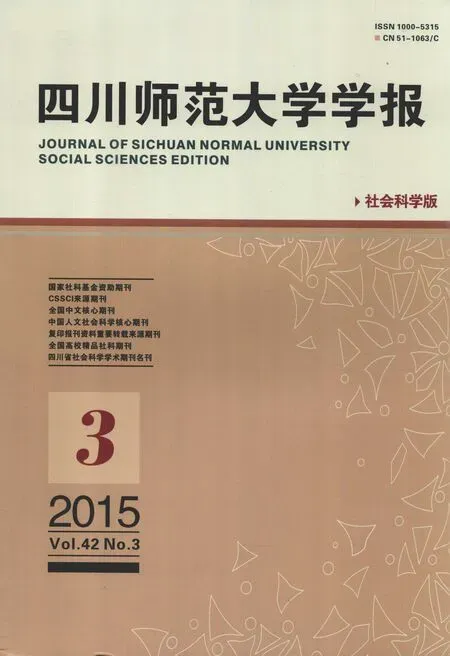空间的表征:《小伙子布朗》对生存整体的探问
蒙雪琴,张 琴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610101)
空间的表征:《小伙子布朗》对生存整体的探问
蒙雪琴,张 琴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610101)
美国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纳桑尼尔·霍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小伙子布朗》通过被宗教伦理浸润的社会空间、闹鬼的森林空间及人物心灵空间的呈现、对立与互动,形象而艺术地展现了布朗所生活的那个清教文化社会空间通过规训、监控、惩罚等体系对生活于其中的人心灵的强大掌控;表现出作家从生存问题的本体论意义上对人在宗教文明状态下生存的深入探问,是对人生存整体、价值结构、人生境界等的深刻忧思。这样的空间呈现,与现当代空间批评理论的空间意蕴相似。
空间批评;纳桑尼尔·霍桑;《小伙子布朗》;生存整体
不同于传统空间概念把空间看作静止的、固定的,供人在其中上演自己人生戏剧的容器的思想①,西方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空间批评理论家看到了空间的本体性地位、空间的丰富性与辩证性,把空间与人的生存和主观感知、设想等联系起来思考。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Wegner)如此总结这种当代西方空间理论中的空间概念:“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各种不同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反过来,它也是一种力量,它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1]181西方当代空间理论最重要的先驱之一的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任何空间均暗示、蕴含、隐藏多种社会关系”[2]82-83,“社会是一种空间,是包含各种观念、形式与法规的体系结构,并把其抽象理性强加于人的现实感觉、身体、愿望与欲望中”[2]139。即是说,社会空间蕴含的观念、规范以及各种秩序都可以在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活动、意识中找到影子,其蕴含意义渗透进生活于其中的人,对人进行制约、规训,使之成为符合该空间特征的顺应体。中国学者包亚明在其主编的《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中也介绍了当代著名的后现代政治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illiam Soja)相似的空间理论,在索亚看来,“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的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3]1。
从空间批评的视角,探讨美国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纳桑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小伙子布朗》,我们认为小说通过被宗教伦理浸润的社会空间、闹鬼的森林空间、人物心灵空间的呈现、对立与互动,形象而艺术地展现了布朗所生活的那个清教文化社会空间通过规训、监控、惩罚等体系对生活于其中的人心灵的强大掌控。在此,人的原欲是原罪,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属于全能的上帝。人在原罪邪恶的压迫下、在上帝的威严中自我被遮蔽、扭曲而失去了任何生之活力。人物心灵由此受到极度的煎熬而陷入极度紧张焦虑之中,对自我及他人感到极度失望而最终导致人格的严重失衡的生存悲剧。这一切,在森林空间的隐喻中,及它与心灵空间的对应、互动中,从意识、无意识的深处得到了形象、艺术而深刻的呈现。这是作家从生存问题的本体论意义上对人在宗教文明状态下的生存进行的深入探问,是对人生存整体、价值结构、人生境界等的深刻忧思。考察过去对霍桑及该作品的研究,虽已有大量评论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阐释,但还鲜有从该视角进行的探索②。
对宗教文明状态下人生存境况的如此探问,不仅在其作品中可看到其审美展现,而且他的人生经历也可见此种思想形成的轨迹。霍桑出生于有浓重清教传统的家庭,是他家移居美洲大陆后的第五代传人。从其代表作《红字》序言“海关”中的陈述,我们可见他对祖先们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对他那在清教历史与萨勒姆镇历史中名声显赫的第一位祖先威廉·霍桑充满敬畏,感觉到一种“威武雄壮的色彩”,认为他“始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巨大成就绝非是我所能企及的”[4]8;另一方面,又为他及他儿子约翰·霍桑对其他教派的残酷迫害而感到羞耻,问道:“我的这些祖先们是否曾经想到过忏悔,请求上帝宽恕他们犯下的残酷行为呢?”[4]9他的这些个人经历,既反映出、也帮助形成了他对清教信仰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深受其影响,有着清教人性本恶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他对清教主义的严酷及其对人的压抑性也充满憎恶。所以,他1842年8月在其日记中写道:“我们确实需要一种新的启示系统——一种新的系统,因为旧的启示系统似乎不能给人予生命的活力。”[5]165
一 压抑的人类社会空间
小伙子布朗生活的那个清教小村有着一个沉闷的社会空间。虽然作者对其直接着墨不多,但它对人进行塑造、规训、压抑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却跃然纸上。首先,故事开篇作者看似不经意的笔触即刻以形象的图式意象(cartographic image)把人类社会空间的巨大力量与作品中悲剧人物的神秘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那夕阳西下的时分,布朗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要离家去附近森林过一夜,他新婚才三月、名为淑珍(Faith)的妻子温柔地乞求他那夜不要离家,使那家凸显温暖与甜蜜;但另一方面,因淑珍的英文Faith意为信仰,其人又被布朗描述为“福祐的人间天使”③[6]305,其所代表的宗教含义与道德约束力就被形象地表现了出来,使那个家、那个小村的空间也强烈地隐喻着它们的文化含义。然后,布朗“匆匆上路,到教堂旁边,正要拐弯,回头一望,但见(淑贞)仍在伫望,神情忧伤”[6]305。这个定格画面含义深刻,极具艺术性与表现力。它通过这巧妙的地理位置标记,标出了除如此哀怨的Faith与教堂之外而无它物的小村空间,从而达到了形象地突出前面故事隐喻的宗教文化在此空间的巨大规训力与控制力的作用。因此,小村空间的描写不仅在为故事提供故事背景,而且也是一涵义丰富的象征系统,有着自己重要的叙述作用,在形象地表现着布朗所生活的那个小村、那个社会的形态与属性等,述说着什么是其中主导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文化意义与社会属性,暗示着生存于其中的人的生存体验与境遇。用英国当代著名空间批评家麦克·克朗(Mike Crang)的文化观点及对文学文本空间的评价来分析即是:文化是“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它们使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意义。生活中那些物质的形式和具有象征性的形式产生于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7]2;因此,人的生活空间深刻地蕴含着人的思想文化体系。用福柯从社会、权力的角度对社会空间的分析来说,“空间是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形式运作的基础”④[8]118。 即,这种通过权力建构的人为空间是权力机构控制人的一种方式,强调这种嵌入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空间凸显权力社会的属性。因此,每个人都生存在一个巨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中,被长时间地操纵和监督。
在紧接其后的故事对布朗心灵空间艺术形象的呈现中,可进一步看到小村空间对人的这种严密监控的强有力程度。从小村进入森林空间后,布朗心灵空间活动都紧紧围绕着小村,而且都集中在他祖祖辈辈虔诚的清教徒及那些平时表现得非常虔诚、堪称村中典范的古迪·克洛伊丝太太及牧师、教堂执事等身上。身在原本象征自由、释放与野性的森林空间中,布朗对森林的这些特性却毫无感知。这森林空间因此就起到了对那个小村社会空间延展的作用,继续在表现它,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它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以及它约束力量的巨大;其意识形态——宗教,是布朗人生经历的主要事件,在他的心灵深处沉重地压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是控制他的巨大力量:古迪·克洛伊丝太太在他儿时对他进行教义问答,而后两位现在是他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顾问。所以,他首先有愧于列祖列宗:“我父亲可没为这种差使上林子里来过,他父亲也没有过。我们家世世代代忠厚老实,全是好样的基督徒,打殉教先圣遇难起就是。难道我得成为布朗家头一个走上这条道的人”[6]307;接着又想到,他“今后如何有脸见萨勒姆村的大善人,那位老牧师呢?哦,不管安息日还是布道日,听到他声音我都会发抖”[6]308。而后,当他内心深处的善恶斗争中善的力量一时又一次占了上风,决定不再向前进时,“年轻人在路边歇了一会儿,对自己大加赞赏。寻思明天早上碰到牧师散步,该何等问心无愧,也用不着躲避他的目光”[6]311。所以,对于他那魔鬼旅伴所列举的其父辈也参与了森林中的阴暗活动时,布朗当时的反应是,那不可能,因“这种事情哪怕有丁点儿谣言,他们都会被逐出新英格兰的”[9]67。 因此,布朗心灵空间的如此呈现,把那个小村空间、那空间所隐喻的社会对人的监视作用、规训作用、威慑作用、乃至惩罚作用都形象而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再加之,许多读者也熟知新英格兰历史上也确有许多惩罚所谓异端的残酷事件,如169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萨勒姆一带大规模搜捕处死所谓的巫士事件,以及历史中著名的对持不同宗教观者的驱逐事件,如对安·哈庆生(1591—1643)、罗杰·威廉(1603—1663)等的驱逐等⑤。在此,历史事件的暗指与作家小说中虚构文本的呈现间的互动,进一步地使作品的呈现更加真实、形象而具说服力,起到强化那小村空间的作用,使其性质的实质得到更加清晰、形象而艺术的呈现。
二 对布朗心灵的控制、扭曲
这种蕴含着深厚文化含义、宗教含义的沉闷的社会空间,严格地控制着人的思想、人格的形成,在主人公心灵空间激烈的心理斗争中得到了形象而深刻的呈现,表现出人物身份建构遭遇到的巨大冲突与困难,及小说对人自我的形成与影响人自我意识的无意识过程的探讨。布朗从小生活在如上所述的那种社会空间严格的道德体系监控下,——祖祖辈辈清教传统的严格培养,村中教会再以各种方式的教义灌输(从孩提时代的宗教教义问答到终身所受的牧师布道、监管等),布朗对清教极力强调的上帝的威严、人性的堕落早已铭刻于心而时刻都在检审着自己的内心、自己的举止,乃至于外出遇到牧师时,都会“躲避他的目光”[6]311。 但人的本性中那动物性的一面又是那样富于生命力,时时刻刻在寻找着释放、自我满足的机会;更何况布朗现刚成年,新婚才三个月,刚进入成人世界,过去教堂、家庭、社会对他的教育都强调人必须否决自己身上的自然欲求而朝向光明的一面、圣洁的一面,可是在他现在进入的成人世界里,自己心里的自然欲求越加旺盛,对他人心里的自然欲求也都渐渐有了认识。这一切强烈的矛盾对立在他的内心深处形成的强烈的冲突对立,在强烈地争夺着他、撕扯着他、分裂着他,在小说开篇布朗的心里活动中就有形象的展现:“可怜的淑贞!”他骂着自己,“我真够可耻的,竟为了这么趟差使丢下她!……唉,她真是个福祐的人间天使,过了今晚这一夜,我再也不离开她的裙边,要一直跟着她上天堂”[6]304。另一方面,这样的描述也很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布朗的另一种心理,这是人经常在止不住的欲望冲动下,在自己内心深处为安慰自己常找的借口,说明当事人在面对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而做的自我欺骗行为;表现出面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空间对原罪、人性的阴暗面的强烈否定、强大压制面前,布朗深知自己不是自己表现出的那样完美,符合社会的要求,时刻小心翼翼地带上一种被荣格称为人格面具的面具以隐藏自己真实的自我⑥。这样的严重压抑使布朗的人格遭到严重的扭曲,初期表现为失去了自己的创造性、独立性,后期表现为那种严重的精神错乱、人格失调的状态,失去了认识自我、他人、社会与自然的能力,而生活于一种紧张、忧郁、绝望的状态之中。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格是由不同系统组成的,有些系统之间还存在冲突,比如荣格的阴影与人格面具,弗洛伊德的本我与超我。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要能和谐、宁静地生活,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人格,就必须将这些对立冲突的因素统一到有机整体中。也就是说,对立冲突的各方需要平衡发展,而不是对一方的过分抑制、另一方的过度膨胀而使人格处于冲突、对立、矛盾之中,使人变成分裂的人,不能建立起完整的自我而出现身份认同危机。超我、人格面具的过度膨胀会抑制人性中的本我、阴影的发展。虽然这一部分是人性中的阴暗面,或指人性的兽性面。由于它的存在,人类就形成不道德感、攻击性和易冲动的趋向。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查尔斯·泰勒总结说:“它是人身上所有那些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的发源地。”[10]37-38弗洛伊德叫它为“本我”,说它是“我们人性中黑暗的、触及不到的那部分,……其中大部分带有负面性质,……我们可叫它为一口沸腾的大锅。……它充满着来自本能的活力,可它是无序的,不考虑任何集体意愿,只考虑努力满足遵从快乐原则的本能需求”[11]105-106。 因此,本我的性质是双面的,它具有破坏力,是死亡的本能(death instinct);但也富于创造的驱动力,是人的幸福生存必需的生之本能(life instinct),人的智慧、创造力、情感的源泉⑦。一个成功地压抑了自己天性中动物性一面的人,可能是个文雅的人,是在社会中遵纪守法的人,但他的生命力与活力、智慧与创造力都会受到相应的削弱。
从故事的呈现我们可以看出,霍桑对这些道理有敏锐的洞察。所以,布朗在那强大社会空间的监视、控制下,在强调压制本能、向善的强音中,把自己的本我或曰阴影强硬地压制着,自己时刻谨守着社会的规范,是一个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活力与智慧,失去了和谐、自如、独立地处理问题的能力的人,乃至于他“不管安息日还是布道日,听到他(牧师)声音我都会发抖”[6]308。他是一个被遵从原则控制而失去独立的人,因此他决心,“过了今晚这一夜,我再也不离开她(妻子淑珍)的裙边,要一直跟着她上天堂”[6]305。
摧残还不仅于此。小说描写布朗在压制不住的冲动驱使下去参加森林里的巫师聚会,并在那里看到魔鬼及全镇平时是道德典范的圣洁之人(包括从故事开篇以布朗心目中“福祐的人间天使”的形象出现的妻子淑贞)都参加了那邪恶的聚会,表现出了对邪恶的强烈崇拜后,从此改变了他对人、对自己的信心,使他变成了“郁郁沉思的人”。安息日一到,会众们唱起圣诗,他却听不进去,“因为罪恶的颂歌正大声冲击着他的耳膜,淹没了所有祝福的诗句”[6]320。过去决心要紧跟妻子的裙边,一直跟着她上天堂的他,现在“时常在夜半惊醒,推开淑贞的怀抱,卷缩到一旁”[6]320。 他如此忧郁地走完了一生。死时,“人们不曾在他墓碑上刻下任何充满希望的诗句,因为到死他都郁郁不乐”[6]320。这样的故事可看作是布朗对清教社会、对原罪、对上帝威严的过度强调的病态反应。而且,小说结尾时设问——“他难道只是在林中打瞌睡,做了个巫士聚会的怪梦?您若这么想,悉听尊便。”[6]320——也是在引导读者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因为梦是人日常生活经历的反应,是潜意识的反应,是内心深处的真实的精神状态。弗洛伊德解析说:“只要外界对神经刺激和肉体内部的刺激的强度足够引起心灵的注意……它们即可构成产生梦的出发点和梦资料的核心。”[12]142小说的描写表现出霍桑深知梦产生的机制。如此,不但布朗的真实精神磨难被表现了出来,小说开篇看似不经意的对布朗妻子淑贞此方面的意识的描述——“求你明天日出再出门旅行,今晚就睡在自家床上。孤单单的女人会做些可怕的梦,生些吓人的念头,有时候连自己都害怕。”[6]304——在前后的映照下,通过表现淑贞也受着同样的苦,把布朗的痛苦引向了普遍。宗教教育否定人的原欲,视它为人的原罪,但不管怎样压制它,它总在人心里顽强地复活、扎根生存、时时刻刻寻找着宣泄的机会。这种内心的冲突、矛盾,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寻求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要严格压制,使人为此总会被内疚感、自卑感、焦虑所缠绕,从而被转化成了淑贞梦境中的可怕景象。而社会对原罪的强调在布朗的心上打上了更深的烙印,使这种内疚感、自卑感在他的心上更加沉重地久久地积压,从而使其产生更严重的焦虑,最终人格失调,把恶看成了自己的全部、世界的本质,转而与自己为敌、与世界为敌;反过来,世界也抛弃了他——他失去了与世界的和谐、自己内心的和谐,成了在内部与外在同时都失去支撑的人,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而郁郁终生而死。
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来分析布朗的心理崩溃、人格分裂,即为:人的本能欲望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人精神上的不适与痛苦,甚至导致人格失调等精神障碍现象的发生。神经症症候是“矛盾的结果”,是“潜意识活动的结果”[13]286,即遭受过压抑而被摒弃于意识领域之外的潜意识欲重新进入意识,而被患者所抗拒。这样一个压抑和克服抵抗的过程,推动一系列恐惧、痛苦、烦恼等焦虑情绪的产生。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动力学认为,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为冲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正反相互作用,冲动力就是能量发泄作用(id),阻力就是反能量发泄作用(superego),“实际上,人格的任何心理过程都无不受到能量发泄和反能量发泄相互作用的影响。有时候,二者间的平衡处于相当微妙的状态,哪怕是很少一点力量从前者转移到后者,都会造成行动与不行动的天壤之别。”⑧荣格也认为,过分发达的人格面具会造成对人格结构中的其他构成成分如阴影的严重压抑,从而使其与人格结构中的其他因素产生严重的冲突,使人生活在一种由此冲突引发的紧张心理状态之中,陷入心灵危机,失去正确把握自己的能力而陷入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之中,焦虑之中⑨。
三 闹鬼的森林:人物个体心灵空间扭曲、痛苦的形象图式表现
列斐伏尔认为,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由此而在其中显现才会得以延续[1]44。即,社会空间里的意识形态作用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在个体身体及心灵上打下烙印。因此,个体心灵空间也是表征的空间,它表征着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同时也在其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如前所述,作为自然空间的森林空间,它本该有自己的特性,但在此,主人公身在本能抚慰人的森林/自然中全然感受到的仍是社会空间的强大束缚,甚而,这森林空间变成了与他自己心灵空间相对应的情态,充满紧张、恐怖的气氛,是闹鬼的空间。因此,这森林空间既是社会空间的延展,也是布朗个体心灵空间的隐喻、表现,同时又与之相互映照、互动,从而把他内心深处的一切潜意识活动、一切对立双方的激烈争斗、人物所受的激烈的心灵震荡、人格为什么不能健全地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痛苦,都形象而逼真地在森林的地理图式结构中展现了出来,使布朗的这种心理崩溃、人格失调的悲惨人生境地得到了更加艺术而深刻的呈现与强化。故事开篇对那森林的描摹为:“阴森森的树木遮天蔽日,挤挤挨挨,勉强让狭窄的小径蜿蜒穿过。人刚过,枝叶又将小路封了起来,荒凉满目。而且这荒凉凄清还有一个特点,旅人弄不清无数的树干与头顶粗大的树枝后面会藏着什么,所以,脚步虽孤孤零零,也许经过的却是看不见的一大群人。”[6]305这样的描摹寓意深刻,可看作是对人的梦境,或说个体心灵空间潜意识形态的形象隐喻,体现了人潜意识的那种混乱无序、黝黑昏暗,是被社会道德禁止的各种强烈欲望滋生的场所。以此为背景,布朗最深层次的心理活动被形象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仿佛读者直接进入到了布朗的心灵空间,对其心理活动、心理斗争的激烈有了直接、形象的感受,看到了布朗内心深处代表善恶的两股势力不能相适相协地发展,而是一直在激烈地争夺着对布朗心灵的控制,使布朗一直处于紧张的矛盾之中、深层次的焦虑之中,终于一步步地走向心理崩溃,不能对自己的思想、情感、言行、人格结构的对立成分进行协调、整合,乃至于最后从人类现实世界广阔的空间彻底退缩进自己孤独痛苦而绝望的心灵空间之中。
森林空间因此就在这短暂的一场梦的时间内展现了布朗心灵深处的种种煎熬。从一开始进入森林时对魔鬼、对所要去做之事的既担心又期盼的紧张又矛盾焦虑的心态:他怯怯地回头看看,“要是魔鬼本人就在我身旁,那可咋办!”[6]305但见到魔鬼时对自己的迟到解释说:“淑贞耽搁了我一会儿。”[6]306声音有些发颤,因为同伴突然冒了出来,虽不算完全出乎预料。尽管小说以传统的方式描述说,这是魔鬼对他的诱导。但这魔鬼的外形神态、故事叙述的隐含意义等都指向这魔鬼就是布朗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是他心中那强烈的本能欲望的声音。所以随着布朗随后脚步的向前移动,他的内心深处就更加成了两种声音的战场。心中焦虑不断加重,在他的良心上沉重地压着,极力阻止他前行,首先是他祖辈们:“我家世世代代忠厚老实,全是好样的基督徒,……难道我要成为布朗家头一个走上这条道的人,而且是同(魔鬼一起)……”[6]307然后是那平时令他敬畏无比,乃至于听到他声音都会令他发抖的老牧师,再后面就是那对他来说最圣洁、因而也对他最有控制力的妻子淑贞。她两次出现阻止他的行动,“我老婆淑贞要知道了这事,她温存的小心儿非伤透了不行。我情愿自个儿难过”[6]308。再后一次是当他觉得他看到他无比敬畏的牧师与教堂执事也要去参加他意欲参加的那林中恶事时,心理遭到重创,对自己的信仰感到怀疑,面临崩溃时,“他头发昏,心沉重,痛苦不堪。仰望苍天,疑惑头顶是否真有天国。然而,但见天空蓝蓝,繁星闪烁。‘上有天堂,下有淑贞,我要对抗魔鬼,坚定不移!’古德曼·布朗呐喊道”[6]312。 然后,对淑贞的这种信心也在最后见她也被带来参加林中恶行时精神受到最严重的打击而消失,使他绝望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疯狂的地步。他在林中纵声大笑了许久,然后抓起魔鬼给他的拐杖又往前走,“顺林中小路大步流星,不像在走,倒像在飞”[6]314。与此相应,此时的森林空间“充满可怕的声响——树木吱吱嘎嘎,野兽嗷嗷嗥叫,印第安人哇哇呐喊。有时风声萧萧,酷似远处教堂的钟声;有时它在这夜行者的左右大吼大叫,仿佛整个大自然都在蔑视他,嘲笑他”[6]314。这是他心灵空间中紧张、混乱、焦虑、恐怖等情绪发展到极致的隐喻与投射,乃至于他把整个森林变成了闹鬼的森林。然而,他自己就“是这恐怖场面的主角,不肯在其它恐怖面前退缩。……他时而破口大骂亵渎神明,时而纵声大笑使整座林子激荡着他的笑声,好像周围的树木统统变成了魔鬼。这个他自己恶魔的化身,还不如他这个狂怒的人可怕”[6]314。
如此闹鬼的森林空间接下来呈现出更加紧急、恐怖的状况,隐喻、对应着越加激烈争斗着的极度紧张、焦虑、混乱的布朗的心灵空间。他最后狂乱奔跑到了一片看得见一片红光闪闪的空地,其灿烂的火光直冲午夜的天空。他在这里看到了所有村中的名流、平日里纯洁无比的人全变成了邪恶的崇拜者。一首首平日里在教堂唱过的圣歌唱了起来,可转眼都成了对恶的崇拜,如其中一首圣诗,旋律缓慢沉痛,“歌颂虔诚的爱,但歌词却表达了人类天性所能想象的一切罪行,并含糊地暗示着更多的罪恶。……其间,荒野之声犹如一架巨大风琴,发出深沉的乐声,愈来愈响。随着这可怕圣歌的最后轰鸣,传来了一个声音,仿佛咆哮的狂风,奔腾的溪流,嗥叫的野兽,以及荒野中各行其是的一切声响,统统交相混合于罪孽的人类之声,向万物之主致敬”[6]316。如此各种声音交杂的可怕的轰鸣声表现出当时布朗的精神状态焦急、错乱、恐怖到了什么程度:社会对他所做的向善的教育还依稀记得,还在他意识深处指引着他,可向善的呼唤已深入地与恶的声音纠缠在一起,让他难辨、迷茫于不知该听那一种声音,表现出一种深度的茫然、紧张、焦虑。本能让他不由自主地靠近会众,因“与这些人,他有着一种可恨的同教情谊,而这种情谊来自他内心的全部恶念。他简直敢发誓,自己已故父亲的身影,正从一团烟雾上往下看,点头示意他往前走。而一个形象模糊的女人却绝望地伸出手警告他往后退。 是母亲么?”[6]317从此可见,这两种力量是怎样激烈地冲突着,使他不能自已。所以紧接着,“牧师与古金执事抓住了他的双臂,把他往火光照耀下的巨石拉去。他无力后退一步,甚至也没想过要抗拒”[6]317——表明深层意识强烈地渴望着做那件事,可良心沉重地压迫着又不敢公开为之,只好为自己找了一个被人强迫的借口。然而,当他与妻子淑贞就要被引入那邪恶世界的紧要关头,他又发出了呐喊:“淑贞!淑贞!仰望天堂,抵挡邪恶!”话音刚落,他“发现自己孤单单身处宁静的夜,正侧耳倾听风声沉甸甸地穿过森林,消失无声”[6]319,他醒了。 这样的描绘形象地表现出了他当时处于怎样紧张、危急、恐惧的心情之中。
综上,通过社会空间的塑造,作者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一个富含社会、文化意蕴的社会空间、文化空间。这空间接着又在森林空间的塑造中、人物心灵空间的展现中得到进一步的延展。森林空间如此就既艺术而形象地强化这社会空间作为蕴含社会思想文化体系的空间怎样以其巨大的、沉闷的、密不透风的监控,严密地影响、掌控人的思想与生活,同时又以森林空间闹鬼时特有的形式在与人物心灵空间的互动中形象地从人的意识深处、无意识深处表现人物个体心灵空间在那严密的社会空间监控下所受的人性、人格的严重扭曲之苦,失去了宁静和谐的生活境遇而生活在内心的极度矛盾、冲突与紧张、焦虑、恐惧之中,对自己、他人都充满极度的怀疑,而一度把自己变成闹鬼的森林空间中最可怕的恶魔,凸显人物饱受的严重的精神分裂之苦、人性分裂之苦,因而导致最后在自己的社会空间中严重的心灵失调、人格失衡,充满对自己、对他人的强烈绝望,而忧郁一生的悲惨境地,把宗教文明状态下人生存的严重残缺状态描绘到了极致。
注释:
①把空间看作静止的、固定的,供人在其中上演自己人生戏剧容器的这种思想传统,西方许多空间批评理论家对此都有阐述。他们认为从远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基督教对人的理解,再到近代笛卡尔及康德的著述中都可发现这种思想。参见: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trans.Jay Miskowiec,Diacritics16(Spring),1986,pp.22-27;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179,p.181,p.87;Robert T.Tally Jr,Spatiality,London:Routledge,2013,pp.1-44.
②国外有一些著述提到了一些与空间批评相关的概念,但其论述不是从空间批评的视角进行的。如:麦克法兰德在其《康科德的霍桑》中讨论霍桑的《玉石雕像》时,认为该小说的场景描述有过度之嫌,使其不能更好地突出人物、情节等(参见:Philip James McFarland,Hawthorne in Concord,New York:Grove Press,2004,p.214);易斯顿在其《霍桑主题的形成》中讨论其早期的系列短篇小说《乡村故事》时,提到这些故事的场景描述是那样生动、细微,乃至于它们可以是理解人物的地学志(topology),但作者并未从此角度去讨论人物(参:Alison Easton,The Making of the Hawthorne Subject,Columbia,Mo: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6,p.43);麦尔德在其《霍桑的居住地:文学生涯考察》中把对霍桑的传记研究与霍桑一生居住过的四个居住地联系起来,从他的祖籍、他的第一个居住地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到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再到英国、意大利两个海外居住地,考察它们各自在他的性格形成与作品创作中的作用,虽然标题中就表明该作品与场所(place)有关,但麦尔德用的是传统的传记研究手法,而非空间批评手法或场所分析理论(参:Robert Milder,Hawthorne’s Habitations:A Literary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③文中所引《小伙子布朗》文字,均出自纳桑尼尔·霍桑《故事集:故事与小品》,姚乃强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本文引用时,文字略有改动。后同。
④文中引文,英文引用参见:Jeremy W.Crampton,and Stuart Elden,Space,Knowledge and Power:Foucault and Geography,Burlingto: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p.118;中文引用参见: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3-14页。
⑤文中关于1692年的巫士事件,参见:Susan Castillo,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xt to 1865,Malden,Ma: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2011,pp.51-52。关于罗杰·威廉被驱逐的事件,参见:Amy Allison,Roger Williams:Colonial Leader,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1,pp.35-37。关于安·哈庆生的驱逐事件,参见:Beth Clark,Anne Hutchinson:Religious Leader,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0,pp.45-53.
⑥⑨转引自: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48页、50页。.
⑦⑧参见: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陈维正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48-49页、43页。
[1]WEGNER P E.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Julian Wolfreys(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21st Century[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2]LEV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Basil Blackwell,1991.
[3]包亚明.前言:第三空间、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M]//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纳桑尼尔·霍桑.红字·福谷传奇[M].侍桁,杨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HAWTHORNE N.The American Notebooks[M].Ed.Randall Stewar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2.
[6]纳桑尼尔·霍桑.小伙子布朗[M]//霍桑集:故事与小品.皮尔斯编,姚乃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ELDEN S,CRAMPTON J W.Space,Knowledge and Power:Foucault and Geography[M].Burlingto: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
[9]HAWTHORNE N.Young Goodman Brown//Nathaniel Hawthorne’s Tales[M].Ed.James McIntosh.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87.
[10]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1]FREUD S.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M].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1991.
[12]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赖其万,符传孝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1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Presentation of the Spaces:Concern over the Wholeness of Existence in Young Goodman Brown
MENG Xue-qin,ZHANG 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101,China)
Young Goodman Brown by Nathaniel Hawthorne,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romantic representative writer,demonstrates vividly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interaction and contrast of a social space drenched in the religious doctrines,a haunted forest space and the mental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 how the puritan social space controls powerfully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through its complete system of disciplines,surveillance and punishment.This is the writer’s profound exploration into man’s existence in the religious civilization,embodying his concern over the wholeness,values and conditions of man’s existence in the sense of the existential ontology.Such presentation of spaces reveals similar spatial concepts to those of the contemporary spatial criticism.
Spatial criticism;Nathaniel Hawthorne;Young Goodman Brown;the wholeness of existence
I712.074
A
1000-5315(2015)03-0115-07
[责任编辑:唐 普]
2014-07-13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纳桑尼尔·霍桑的影响力研究”(编号:10XWW008)的阶段性成果。
蒙雪琴(1958—),女,四川西昌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张琴(1990—),女,四川大邑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