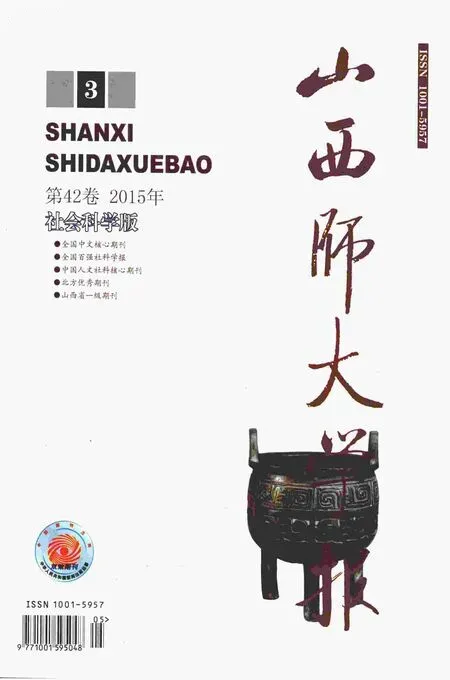论共和主义国家的基本属性
聂 静 港
(山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在政治生活中,国家被普遍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统治单位,但对于国家的基本属性这一基本问题却没有形成共识。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视域内,主要有三种国家观念,分别是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这三种国家观念各有自己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历史逻辑观照。就自由主义国家观念来说,它采取社会契约论的方法以证成国家(政府)的来源,认为个人权利先在于国家,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保障个人权利。威廉·冯·洪堡明确认为,国家的任务就是保障人的自由,检验它是否有必要存在的原则就是“单一的人及其最高的最终目的”。[1]29在这种逻辑推演下,国家被给予了一种完全消极的形象,成为工具性存在。不仅如此,在自由主义看来,国家“虽然不是必然、但是可能被滥用来限制自由,这是自然的理念”[1]29。显然,现代社会不可能依赖这种缺失公共精神的公共权力提供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论据。国家主义的国家观念与自由主义截然相异,它刻画了一种积极的,甚至是全能的国家形象。在这里,国家是第一位的,是本原,国家拥有自己的关于利益和价值排序的判断,而且可以为此采取任何手段和形式;社会与个人完全从属于国家,个人的至善和价值只能求之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调节也完全依赖于国家。它的前途极有可能是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坚持认为各种各样的政治权威都是不必要的,它以夸张的乐观人性判断为基础,认为自由的个人可以通过自愿协议与合作自行管理个人事务,社会中的一切弊病都来自于国家的控制和干涉,坚决要求取消国家(政府)。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虽然在对国家的态度上有差异,但它们在人性的基本判断上是统一的,前者可以说是积极的乌托邦主义,而后者则可以说是消极的乌托邦主义。因之,无论何者在政治生活中成为现实,都是一种灾难,都无一例外地会导致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绝对丧失,最终导致共同体利益的彻底毁灭。
共和主义国家观既不像自由主义,无视公共精神的养成,反而把公共精神和公民美德作为公民身份的关键构成要素;它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视社会中公民的差异性存在和互相竞争的关于好生活的观念,反而认为公民权利和自由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理论特质。具体来说,共和主义的国家观念向我们勾勒出国家应该是具备公共性和政治性属性的共同体,为超越自由主义等国家观念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道路。
一、公共性属性
国家虽然是一个近代政治学概念,但早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就已经孕育了国家的最初样态——城邦。城邦规模有限,但实行自治,表面上看是居住于同一地域上的居民形成的具有共同的神祇崇拜和遵守特定秩序的自然共同体,然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出身和血统而形成的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共同体。甚至可以说,城邦就是政治,二者同质且同构,政治领域的范围止于城邦的界限,政治的内容也只能在城邦中展开。城邦作为“至高而广涵”的共同体,追求的是一种共同的善,而且是最高的善,即“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幸福而高尚的生活”[2]90,其目的高于且涵容家庭等其他共同体的目的。
在古希腊,城邦具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它不是私人化存在,而是公共性存在。这是因为,首先,组成城邦的个体是公共性存在。“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命题直接点明了人的存在方式在于社会存在。要成为合格的“人”,就必须是“生而为政治”的人。人的自然属性的内涵被剥离,人的社会属性被抬高。其次,城邦的目的也是公共性存在。自足而优良的生活不是为个别人或集团准备的,城邦既然是由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成的,而且城邦权力的正当组织原则就是公民轮流执政,城邦的目的必然就是所有人共同的目的。最后,城邦所要求的合乎正义的行为方式也是一种公共性存在。城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获得一种“在他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他的政治生活。现在每个公民都属于两种存在秩序,而且在他私有的生活和他公有的生活之间存在一道鲜明的分界线。”[3]15在第二种生活和第二种秩序下,为共同体所要求的活动方式只有两种是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政治的”生活方式,即行动和言说,它们是所有动物中唯有人才具备的能力。
20世纪复活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践哲学”旗手阿伦特坚定地再次重申国家的公共性特征。其一,阿伦特注重思想史中的概念所具有的跨越历史的连续性和解释力,认为思想史“不是现实社会变化的反映,而是对思想和观念内在变化的描述”[4]8。既然如此,已经逝去的思想就不是无生命力的干巴巴的研究对象,而是会继续活跃于当下的生活之中。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分析就是一个可以用来观照当下的思想概念。其二,自1941年逃亡至美国后,阿伦特看到了大众社会消费主义的盛行、核战争的恐怖,以及可以与极权主义相媲美的“虚假政治”的泛滥。她意识到,现代世界正在发生公共性的普遍流失,由此而转向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公共生活图景,希望重新燃起人们对公共生活的激情,发现了公共生活优于私人生活的意义之所在。阿伦特对国家公共性的阐解主要见之于她对公共领域的界定。
第一,国家的公共性表现在它是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政治性组织,既不是私人领域,也不是社会领域,而是公共领域。阿伦特认为,现代以来,以家务管理及其活动、问题和组织化设计为内容,依照家庭形象建立的,巨型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社会——的崛起改变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对公民生活的意义。阿伦特不满于这一现状,想要努力凸显国家本该有的区别于家庭的公共性属性。她指出,家庭是一个受制于必然性的组织,这种必然性包括个体生存的需要和种的延续的需要,必然性统领着家庭内的所有活动。既然受制于必然性,家庭就是不自由的空间,就是不平等的场所。“成为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强制,亦不受制于自身的强制。”[3]20如此,仅仅在可以离开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意义上,家长才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是不完整的。与家庭领域相异,公共领域却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它挣脱了对必然性的束缚,也就是说,它是从生命的必然性中获得了解放的领域,它是公民表现自己个性,使自己与他人处在一个共同空间中的结果。
第二,国家的公共性还表现在它是实现参与者的卓越和形塑公共精神的公共领域。阿伦特指出,希腊人的aretê,罗马人的vitus,即卓越只属于公共领域,因为“只有在那里,一个人可以胜过其他人,让自己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每一个公开展示的活动都能获得它在私人场合下无法企及的一种卓越”[3]31。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社会领域的兴起遮蔽了这一事实,这完全是由社会的性质导致的。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古典时期的那种与维持生命有关的活动被拉进到社会领域中,原本属于私人的事务现在变成了共同的事务,国家也不再是纯粹的处理政治事务的场所,而是获得了一种“集体家政”的形象。关键是,社会像家庭一样要求成员“一样行动,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利益”,其结果就是“在社会中,到处相同的利益和全体一致的意见以纯粹数量的方式起作用,所释放的巨大自然强力最终废除了代表共同利益和正当意见的一个人的实际统治”[3]25,实现了无人统治(no-man rule),即我们熟悉的“官僚制”。不过,它并不代表统治的消失,而是一种集体的统治,甚至会成为比个人专制更严重的集体专制。在这样的社会中,表现差异的属于公共领域的行动(action)被统一的、“规范化”的属于社会领域的行为(behavior)代替,平等和顺从成为社会的主要关注和特征。与众不同不再受欢迎,标新立异也退出人们的视线,反而成为一件极其私人的事情,卓越终于成了我们最不可能从中得到的东西。然而正因此,公共领域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凸显。因为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会“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争胜精神,在那里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把他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以独一无二的业绩或成就来表明自己是所有人当中最优秀的”[3]26。公共领域使人得以在公共参与中维护自己的自由,并实现国家的政治自由。
二、政治性属性
国家的政治性属性之所以被确认并被广为接受,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理解,是对国家的宗教性面相祛除和剥离的必然呈现,而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则是对现代国家公民参与的价值和意义积极呼唤的必然反映。前者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贡献关系密切,后者则与对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超越有密切关联。
马基雅维里对国家政治性的强调是在批评国家的宗教性,或者说批评基督教国家的软弱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基督教奉行的二元政治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改变了西方人认识世界、处理事务的思维方式,把对人的宗教性分析“照搬并套用”到对国家属性的分析上。神学不仅统驭政治观念,而且还在解释并说明着政治世界,由此形成对国家的重新界定。国家沦为上帝针对人性堕落而给出的“补救工具”,基督教“一手握着道德的马勒,一手擎着上帝的尚方宝剑,对统治者实行道义上的监督”。[5]148原本简单的公民——国家的双向关系现在演变成了民众(选民)——国家——上帝的三角关系,属灵秩序独立于并高居于俗世秩序之上,个人产生了一种拒斥国家、远离政治的冷漠感。由于这层宗教的外衣,国家的意义和作用被大大地减弱和虚化,也由于基督宗教宣扬的独特的道德观和政治观而显得软弱。个人不再通过积极的公共生活以求得挣脱生命有限性和短暂性的禁锢,转而求助于通过苦修、冥想把自己从肉体中解脱出来,获得上帝的青睐而进入天堂。
马基雅维里根本不同意基督教国家的这种宗教性以及软弱性,认为它们对于现实世界毫无益处。他向往的是积极进取、尚武、爱好荣誉和荣耀、追求伟大事迹的公共精神。在他看来,基督教是公共生活的“毫无必要的障碍”,人们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行动的和沉思的——中选择一种而抛弃另一种。马基雅维里毫不迟疑地表现出自己对前者的偏爱,他深刻地意识到“人皆善良”是一场梦幻,一句呓语,基督教宣言的道德观不可能成为现实政治世界的“行动指南”。要创建并维持一个强大的共和国,最主要的就是激发统治者和民众的爱国热情和积极行动的政治信念,以科学的态度看待政治。政治本来就是权力的争夺,就是罪行、奸诈和谎言的竞技场。政治里的一切随时都在变换着位置:美好的会成为令人憎恶的,而腐朽的又会成为令人羡慕的。对意欲成为统治者的人来说,同时效法狮子和狐狸,成为“半人半兽”的存在,是值得称赞的。可见,马基雅维里关心的只是如何获得权力并在困难的环境中保住权力和国家的强盛。至于手段,可以通过目的来得到原谅。他还原了政治的本来面目,只要正视并遵循它,就能维持国家的长久存在。
自由主义明示,现代国家中的人们“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27。公民的政治行动少之又少,“政治人”被“经济人”和“自利人”取代,国家中处处都是追逐利益的个体,而少见积极奉献生命于共同事业和公共利益的“公民”。
与自由主义不同,共和主义的国家观念向来要求公民参与或者说自我治理,公民在逻辑上并不先于社会,因此个人也就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对共和主义来说,公民身份首先不是一种地位,而是一种被强调的实践和行动。正是通过实践和种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公民身份才得以显现。公民也只有在公共服务中才能定义、确认并维持隶属于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在共和主义的国家观念中,公民参与是政治本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公民的义务。在古典时期,它更是只属于公民的权利。
公民参与经历了从直接参与到间接参与的发展演进。古希腊罗马时期,数量极多的奴隶供养着数量相对少得多的公民,使公民有足够的闲暇和精力出没于公共论坛、集市以及司法审判活动中,他们用政治技巧公开辩论说服他人,在实践中锻炼政治能力,磨砺自己的公共精神,积极型构适合城邦共同体的公民身份。18世纪的卢梭仍颇为激动地说:“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他们的大事只是他们的自由。”[7]122他们积极地亲自参加公共集会,为着共同的幸福和利益而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可以想象,“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身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7]119。通过他人(代表)得到的是虚假的自由,经受的却是长期的不自由和奴役。作为主权者的公民应该认识到国家的事务同时也就是每一个公民自己的事务,唯此才配得上“公民”的称号。
直接参与固然值得向往,但它却受到国家规模大小、公民数量多少,以及政治事务复杂程度的限制。公民身份从雅典的政治型发展到罗马的法律型就说明了直接参与的“效益”和吸引力是随着疆域的扩大和事务的繁多而降低的。因此,通过代议制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就成了必须认真对待和积极处理的问题。
对代议制做出令人印象深刻且影响深远的分析的思想家首推孟德斯鸠。他认为,在三权分立之下,公民由于只是受到法律的约束,并摆脱了专制君主的个人好恶,从而享有真正的自由。这种结果当然得益于普遍的代表制。自己管理自己或自我统治的想象和实践“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应该让他们的代表来做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8]169。离开城邦,让所有人都大规模地讨论公共事务,既不现实,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此能力。因而,孟德斯鸠把公民通过行动和言说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看作是“古代共和国的弊病”。他说:“这是人民根本无法胜任的事。人民参与治国应仅限于遴选代表,……因为……每一个人一般都能知道某人是否比其他人更明白事理。”[8]170
美国的联邦党人吸收并精细化了孟德斯鸠的上述主张,使代议制及宪政深入人心。以麦迪逊为代表的联邦党人认为,选举虽然是连接公民和代表的有效中介,但在政治实践中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选举的次数,二是代表的规模。在他们看来,选举的次数不宜过于频繁,但选举间歇期也不宜过长。那么,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数如何确定呢?汉密尔顿言简意赅地说:“把所有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多数人。”[9]4必须坚守的观念是,人数的限度应该与保障代表们可以自由协商,并抑制他们随心所欲的组党结派的冲动。否则,公民自由就会被侵越,共和政体便也失去其本意。
综上所述,共和主义国家观虽然更倾向于直接参与和积极生活,并且进而认为“代议制政府形式绝非公民身份理念和实践的内生本性和要求”[10],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民间接参与政治已然成为当代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也成为维持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含义的必然选择。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代议制与公民之间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一部分公民或许会比另一部分公民更加积极地进入公共生活,那么如何在这种政治形态下最大程度地呼唤最大多数的公民投身公共领域,哪怕是投身托克维尔所说的社区性生活,就成为理论家和实践者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1] (德)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林荣远,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 (日)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M].斯日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7]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 Ralf Dahrendorf. Citizenship and Beyond: The Social Dynamic of an Idea. Social Research, Vol.41, No.4,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