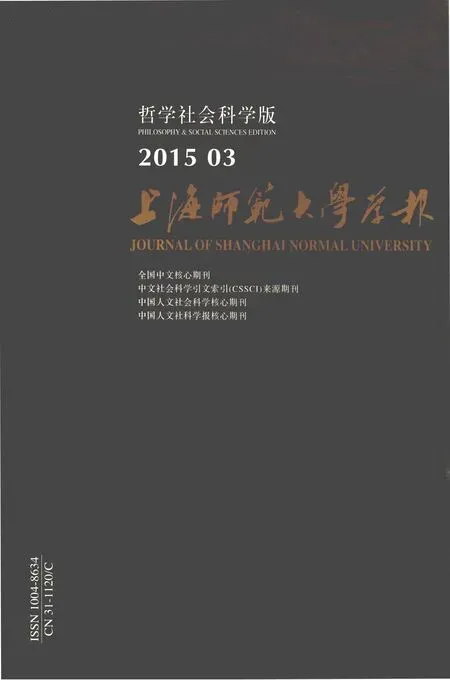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交往规律
——公共外交的视角
来 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一、全球化时代的城市
全球化是世界观、产品、思想、其他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导致的全球整合的过程,①交通、包括电讯与因特网在内的通讯基础设施的发展,是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并产生了经济与文化活动的相互依赖。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全球化的四个方面是:贸易和交易、资本和投资活动、迁移和人的流动、知识的传播。②随着人口朝城市集中,全球化特征在城市体现得最为明显。
1800年,世界只有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世纪末,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47%,今天,全球范围内,每天有10万人涌向城市。联合国2014年7月10日发布的《世界城镇化展望》预测,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再增加25亿。根据该报告,目前世界54%的人口(39亿)居住在城市,2050年该比例将上升到66%。③成为全球经济、信息流、全球性物资与人员流动枢纽的同时,城市也制造了全球大约3/4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引发交通拥挤、就业困难、资源短缺、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面临的问题与全世界关注的关键领域高度重叠,城市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主宰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因其在促进发展、化解冲突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其功能正日渐受到重视。城市间的交往可以缩短社会经济差距,消除文化隔阂,地方政府也可以动员市民社会在实际的议题甚至技术上与其他城市或地区共同合作,促进彼此的进步。④
实际上,以城市为载体,借助现代传播技术,以及媒体、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种种社会力量,城市交往开始冲击主权国家以政治力量界定的地理界限,⑤成为一个日益发展、形态逐步完备的国际交往形式。一直以来民族国家是构成现代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各国中央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即等同于国际关系,城市无权参与对外交往,它的作用仅限于处理纯粹的地方事务。这既是各国宪法普遍的规定,也是国际法的惯例。战后国际组织的兴起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城市为了自己的发展在国际交往中的日益活跃,对这一传统概念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了挑战,冲击着中央政府对外交往的专有权,使得国际体系出现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最根本的变化。城市不断加入全球及跨国网络、国际协会,在全球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城市和其他亚国家单位在促进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推进全球化的进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
实践的突破需要学理的探索。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在美国《外交事务》1994年春季号发表《地区国家的兴起》一文,在此基础上于1995年出版《民族国家的终结:地区经济的兴起》一书。他认为,在四个“I”(工业 Industry、投资Invest、信息Information和个人Individual)的作用下,世界将无边界,传统的民族国家会阻碍经济发展。在新的经济体系中民族国家的经济功能将被规模更小的“地区国家”取代。按照他的定义,“地区国家”是围绕一个区域中心形成的拥有500~2000万人口的地区单位,实际上就相当于城市群。他认为,这是当今全球经济中真正的自然经济单位。[2](P17)
作为新兴的国际交往行为主体,城市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也深受全球化影响。比如,受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的冲突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全球城市最容易受到攻击,城市安全成为一个大问题;全球人口迁移不断加剧,城市是来自全球各色人种的主要汇集地,外国商品、国际企业和机构大量涌入,城市变得更加国际化;城市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有的还会受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投资开发项目的影响;全球城市是国际资本的汇集平台,没有国家之分——纽约、伦敦等城市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
因此,全球一体化使得国家、地区、城市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前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罗伯特·W·格鲁普指出,“相互联系与相互合作是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国家、城市、各类社会组织之间需要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协作’的状态,以联系更多的不同利益相关者”。⑥
国际社会不断地呼吁新的国际交往秩序以适应如今时常提及的“城市世纪”。⑦它不仅是全球城市化趋势的中枢,还是世界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其举措为全球治理创造了新的机遇,需要赋予城市、城市交往新的内涵。特别是城市领导需要考虑如何将城市管理事务与国际组织的全球议程结合起来。
城市是世界的未来,当全球化发展逐步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模式时,[3]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表达、环境保护、城市治理与民主参与、社会整合等议题必将逐步增加,城市交往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愈加重要。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冲击与推动之下,“本土化 ”与“全球化 ”相互冲击,城市如何开发、挖掘、利用本地特色,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融入世界,成为重要课题。
二、城市交往
一般认为,“交往”就是“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互动百科是这样定义“交往”的:由于共同活动的需要而在人们之间所产生的那种建立和发展相互接触的复杂和多方面的过程,是苏联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俄语的“общение”一词,没有完全与之对应的英语词汇,大致相当于英语的“communication”,但是含义比沟通要丰富一些。
马克思认为,交往是人与人或人与群体之间因为一定的目的,通过中介物进行的相互往来和交换、相互作用和制约、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所结成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主要是指各种沟通活动。[4]
在哈贝马斯眼中,交往行动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5]
也就是说,交往行为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人;交往的手段是以语言为媒介;交往行为的主要形式是主体之间的诚实对话;交往行为的目标是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交往行为的原则是必须以公众认可的社会规范来作为自己的行为规则。因此,交往行为不仅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而且还是在行为主体共识基础之上,通过规范调节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6]交往的实质是行为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而达到形成共识、达到和谐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看,交往是一种交流沟通行为,内涵包括信息传递、公共交往、意义生成。交往的目的是达到相互之间的理解,并进而形成共识,达到协调一致,最终达到关系构建、形成良好的相互关系。
那么,什么是城市交往呢?对于城市交往,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借鉴马克思、哈贝马斯等人对于交往的定义,以及目前城市交往的实践,可以认为,城市交往是城市与外界之间的交流沟通活动,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相互之间的公众的理解、认同,从而建立互利互惠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交往与公共外交息息相关。
三、公共外交
各国学者对公共外交的定义大致有三类:[7]1.形象塑造,国家品牌管理就属于这一范畴,而且多为单向传播;2.促进相互理解;3.鼓吹国家利益。我国将公共外交定义为:“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8]这些定义均以国家为中心,视国家为唯一的国际政治行为体,认为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和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塑造国际合法性和认同度的一项重要战略。公共外交和传统外交的本质区别是:传统外交是由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代表之间进行的;而公共外交则将目标对准外国公众,尤其是非官方的团体、组织、个人。英文语境中,“Public”是名词“公众”而非形容词“公共的”,其本意就是注重与各国公众的交往。
现代公共外交起源于美国现实主义的考虑,有两个主要假设:第一,国家是国际政治体系中主要或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国家安全是一国最关切的问题。第一个假设限定了交往对象,将外国公众仅仅视为交往的中介而非终端,公共外交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影响他国公众的态度来影响他国政府的行为”。[9]第二个假设中,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就需要尽最大可能将权力最大化来确保国家安全,公共外交应服务于强权政治和国家安全。
正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所指出,传统的公共外交被广泛认同为一个主权国家针对外国公众的传播活动,通过信息传播来告知、影响海外公众,从而促进实现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⑧即公共外交是单向说服,通过对外宣传来“赢得世界的人心”,后来又增加了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尽管后来逐渐认识到单向传播的局限性,这一概念逐渐从单向传播演变为双向交流沟通,开展广泛的双边或者多边对话与合作,人们还是认为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服务于国家政策,国家是唯一有权决定、施行一国对外政策的行为体。
然而,全球化导致了国际政治环境的颠覆性变革,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对外交往行为体的出现,这些行为体在全球政治舞台的影响力、能力、合法性、信誉度与日俱增,⑨再加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联日益紧密,国家已经不再是外交的唯一主体。塔夫兹大学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克罗科·斯诺(Crocker Snow)认为,各国的媒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等都有资格参与对外交往。⑩
因此,与现实主义不同,国际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国家只是许多行为体中一个重要的行为体,而且其影响力正在下降。自由主义者也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执着于国家安全并将此作为头等大事,而是从世界经济、社会和生态等超越国界的全球福利的角度定义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更有必要与外国公众、各类非国家组织、地方政府、城市开展积极的交流沟通。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各国相互依存、利益相关的时代,由军事实力决定世界政治这一规则已不那么重要和有效,软实力正逐渐代替硬实力成为世界政治的硬通货。
“软实力”这一概念是1990年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创造的。奈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或收买手段,影响他人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结果的能力”,“软实力只能通过公共外交来实现”。[10]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方面的资源,但是软实力得以产生有公信力和合法性两个先决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资源才可以真正转化成软实力,才具有吸引力。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公共外交的作用就是创造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理念(政治、经济、社会系统)、政策的吸引力,来构建一个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的环境。他提出,公共外交尤其是政策的对外传播,需要言行一致,否则还是没法获得各国公众的认同。进入21世纪后 “软实力”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和使用。
但是对于软实力也有不少误解,比如为了争夺游客、出口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几乎所有国家、城市都在积极策划、组织一些大型活动来体现竞争优势,并通过市场营销的方法推广自身品牌与形象。这是对软实力的曲解。如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酷大不列颠”、“超酷日本”和“活力韩国”之类的活动,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来增加一个国家的吸引力。组织并策划吸引眼球的活动固然可以增加吸引力,但并非软实力本身,真正的软实力公共外交是指本身已具备有强大吸引力的软实力资源,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与世界各类公众交往、沟通,并且更加注重双向交流沟通。软实力归根结底是塑造他人喜好的能力,[10]是通过多层次的传播渠道逐渐展开的。尤其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导致的资金、贸易、信息和人的自由流动构成了软实力的传播渠道,这种传播不受政府控制,或者已超出了政府的控制。
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需要注意:一是移民。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机构发布的《2013世界移民报告》说,全世界移民从1990年的1.54亿增加到2013年的2.32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2%。数量上看,今天的移民不能与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潮相比,但移民的主要形式已从永久性定居转变成了临时性居住。就世界历史长河来看,作为一种特定价值观和文化的天然携带者,移民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始终是最有影响力的中介。移民全方位地接触迁居地的人、文化、制度和政府管理,感受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资源;比起其他任何一种传播渠道,移民是最有影响力的传播渠道,他们的切身体会、口口相传将深刻地影响对迁居地的评价。在全球人口自由流动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城市)传递的信息与其软实力资源的实际情况吻合,就会增强其软实力的公信力,从而提升这个国家(城市)的声望;反之,则会削弱这个国家(城市)的声望。再加上超越国界的现代传播技术与传播工具更新换代的加速,亲身接触、人际交往对于软实力影响越来越大。其结果就是,公共外交将不再局限于对外交往,还需要对移民到本地的人交往、沟通;更重要的是,促使政府建设软实力的实质性内容而非仅仅依赖形象塑造与品牌传播。这样,传统的文化、艺术、教育交流项目效果势必越来越有限,良好关系的建立不是依靠展示、传播自己的软实力资源,而是依赖实质性的软实力资源建设。
二是信息化对公共外交的影响。技术进步猛然降低了信息制造和传播的成本,结果就是信息爆炸,是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变成了稀缺资源,如何获得公众的注意力就成为传播者的首要工作,其中公信力是关键资源。比如美国宣称萨达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结果却是美国政府在伪造证据、撒谎、毫无公信力,这对美国外交是沉重一击。政府不仅与他国政府竞争公信力,同时也与新闻媒体、跨国企业、NGO、政府间组织等竞争公信力。奈认为,全球信息时代,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结合起来就是巧实力。公共外交是巧实力的主要工具,巧实力要求人们真正懂得公信力、自我批评的价值,以及公民社会在塑造软实力时的角色。[10]事实上,奈是委婉地承认光有软实力是不够的。
因此,从公共外交的发展演变看,起初公共外交被认为是主权国家之间外交的一部分,“政府与外国公众的沟通过程”[11]是政府运用单向传播进行形象塑造、维护自身利益、促进相互理解[7]的过程;其主要形式是教育交流项目、访问计划、语言培训、重大文化活动与交流、媒体传播等,通过针对公众传播以影响舆论进而影响他国政策,并逐渐运用双向传播开展公共外交以增进相互理解。
受“9·11”事件的冲击及新兴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公共外交被赋予新的色彩,城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都在以各种形式参与公共外交,并有着自己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传播技术与社交媒体极大地赋予并提升了非政府行为主体开展公共外交的权利与作用,新媒体和网络环境下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更有弹性。[12]这个弹性体现在新公共外交比传统公共外交内涵丰富得多。公共外交形式多样,其中的“文化外交往往是长期性的‘民心’活动,……旨在培养与海外公众的感情纽带以获得他们的认同。这样做是为了通过个人体验而不仅仅通过媒介,来直接影响舆论”。[13]新公共外交认为,公共外交对象不仅有外国公众,还有内部公众。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嫰堡传播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认为“国内公众是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国别界限愈加模糊,这使得针对本国公众的公共外交越来越重要。”
毫无疑问,这些思维对于研究城市交往具有极大的价值,特别是在打造城市软实力、塑造城市品牌的今天。公共外交能够为城市的文化、理念、管理、社会体系以及城市的利益创造有利环境,并从多个角度来思考怎样更好地开展城市交往。
四、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交往规律
概括公共外交对于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数字化背景下城市交往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勾勒出全球化时代城市交往的基本规律。
第一,代表城市开展交往的主体多元化,城市交往的权力已不再被城市管理者所独享。城市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主体,其对外交往的主体包括以地方政府为首的,由非政府组织、媒体、企业、社会团体、学术团体乃至个人所组成的城市交往网络。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学者认为,它们的领导人是否具有国际视野,是建立、维持一个世界城市全球流动力的最主要因素;一个有全球视野的城市管理者将会整合各方资源,积极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等机构之间的合作;长此以往,城市对外交往的社交网络将会形成并得以持续,城市交往能力将越来越强。
当前,我国在重视城市政府的对外交往的同时,往往忽视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企业在城市交往中的价值与功能。近年来城市外交、公共外交的研究一再证明其在城市交往中的价值。如1980年代以来美国西雅图政府、商界、劳工组织、教育界画地为牢,相互隔绝,有鉴于此,西雅图港务局局长和该地区商会主席牵头,组建大西雅图贸易发展联盟(TDA),通过协调西雅图的各类国际活动来推进西雅图参与国际市场,前副市长斯塔佛德(Stafford)由于有丰富的本地人脉关系,有能力本地各界领导人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聚拢起来,被任命为联盟主席。在他领导下,TDA优先支持企业,接待游客和从世界各地来的代表团,联系当地小企业和海外代表团;TDA发起年度对外贸易代表团和城市互访,访问各国城市以考察、学习最好的城市发展实践,为西雅图从一个依赖自然资源的城市发展成为高科技宜居城市立下了汗马功劳。
西方国家公众天然地不信任政府,这让以政府为主体的对外交往效果大打折扣,而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性、公益性、非营利性、自治性使其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在城市对外交往中就需要非政府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我国需要适当培育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交往。同理,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是否拥有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是优秀的企业公民也将极大地影响来源地的声誉。欧美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华通过公益慈善、环境保护、文化赞助、科技研发等各方面的公共关系活动赢得了我国公众的广泛认可,塑造了良好的口碑,进而提高了来源地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反之,我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后很少从事相应的公共关系活动,与社会普通公众之间的关系冷淡,没法赢得当地普通公众的认可,口碑不佳,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屡遭败绩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我们注意。
第二,城市交往对象的极大延伸,从单一的城市与城市的对等交往扩展到城市与国际组织、城际组织、媒体、非政府组织、普通公民的不对等交往。理论上说,与一个城市交往的对象是城市自身之外的所有公众,如城市管理者、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但是实际上,我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往往习惯与当地上流社会交往而忽视社会普通公民。通俗地说就是缺乏群众基础,导致我国对外交往中往往受到各国舆论的不良反应。西方国家就很重视与公众的交往,因此,我国城市对外交往中需要学习这种现成的手法。
随着全球城市功能的日益加强,城市之间的国际联系不断深化。全球化以城市为枢纽,渗透到地方性的区域及其社会生活,城市和区域的内部联系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被重新构造。[1]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生产网络、投资市场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群体相互作用,共同形成城市群(又称都市圈、城市带),[14]以国际化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区域内的交往与协调,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管理体制的调整,以达到区域整合与均衡发展,从而提高城市群整体实力,争取更大的地方利益、国家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群内部的交往尤为重要。所以,城市交往不仅包含国际社会交往,还包含本城市群区域的交往,这是需要各地在开展城市交往时特别重视的。
以往城市交往忽视城市的内部公众,而今的信息社会中城市政府必须注重城市内部公众在城市交往中的价值。就城市交往而言,内部公众就是城市居民,尤其是迁居此地的移民、企业是城市开展交往活动的重要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信息传播工具的涌现、新兴交流平台的出现,令城市居民兼具城市交往中信息的受者与传者,是全球城市交往中最具价值的信息传播中介。在人、资金、物资、信息自由流动的现代社会,随着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边界的日趋模糊,城市居民直观地接触到城市的文化、管理、政策,他们对城市的体验、感受、评价能瞬间通过无国界的网络虚拟社区传遍全世界,极大地影响城市交往的实际效果,进而促进或阻碍城市软实力的发挥及城市品牌的塑造。可见,城市居民是城市交往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价值是城市对外交往中无法忽视的。
第三,全球城市交往的内涵丰富多样,具有融合城市地方事务与国际事务的趋势。从开始时侧重政治关系的友好城市(国际上称之为姐妹城市)关系发展到现在包括地方安全、经济、文化、教育、城市建设等多领域的合作,以及深入到全球安全、环境保护、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全球性疾病等全球治理的更广阔领域。如加拿大多伦多前任市长大卫·米勒积极介入世界气候大会,执掌“气候变化领导集团(Climate Leadership Group)”,2009年12月他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说,“虽然气候变化需要全球行动,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不会等待别人采取行动”,“该轮到市长”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了。多伦多还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包括外国援助、人权保护、和平调解等活动,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吸引力。
以往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一些事务也需要城市的参与,城市已经站在国际政治的舞台。国际政治秩序的新变化势必要求城市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政治,这就稳步扩大了城市交往的内涵,模糊了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的高级政治议题和低级政治议题的界限。如“伊斯坦布尔水共识”,由伊斯坦布尔市长托帕斯(Kadir Topba)和国际地方环境协会共同发起,聚集了超过56个国家的1000多个城市参加,以2006年3月21日发布的《地方政府水资源宣言》为基础形成共识,表达了各国城市对水资源的关注,并呼吁各国、各地政府结成更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全球一致面临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问题。这要求我国的主要城市需要考虑如何参加乃至组织类似的、有利于世界公共福祉的活动。
第四,交往主体、交往对象、交往内涵的扩大导致城市交往的方式与途径产生新的特点。首先,在交往的途径方面,从媒体传播扩展到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多种途径,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再发展到网状沟通,尤其是人际交流“将保证最大的双边互利关系和相互信任”,此外社交媒体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次,从城市交往中以官方途径为主逐渐发展到官方途径与民间途径并举。为了建立更加坚实的相互关系,加强与目标群体的非官方关系至关重要,“民间社会的多层次多方面联系和非政府行为主体影响力的与日俱增”,[15]尽管政府仍将在公共外交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是草根文化将最终决定公共外交的走向,其中发展与意见领袖的良好互动关系又特别重要。比如日本公民良好的素质、各城市软实力的实质性建设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仅2014年上半年赴日旅游的中国人就同比增加80%以上,这还是在中日关系极差的状况下取得的,显然官方途径、官方口径的效果越来越有限。再次,各国城市普遍运用市场营销的方法开展城市品牌推广(或城市形象设计与推广)以促进城市交往。如纽约的“我爱纽约”、波特兰的“绿色城市”、海牙的“世界和平与正义之都”、巴塞罗那的“地中海的新首都”等;奥运会、世界杯、世博会等大型活动成为营销事件,是上海、雅典、巴塞罗那、首尔等举办地向世界讲述城市故事的平台。最后,在全球城市交往越发需要获得普通公众认同的背景下,势必要求城市运用多种资源开展交往,比如动漫之受欢迎对于东京、韩剧之受追捧对于首尔、巴塞罗那对巴塞罗那足球队和俱乐部的运用,等等。艺术作品、动漫作品、影视作品、体育活动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第五,全球城市交往的功能日趋丰富,从单纯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以维护城市利益、促进城市自身发展的地方性事务拓展到促进全球福祉的国际性事务,从单一功能朝多层次、多功能方向发展。起初,城市交往的核心功能是维护城市利益、应对各种危机与挑战,当前,世界的城市交往功能则趋于多层次、多样化。首先,城市交往有助于推动、增加城市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从而在这个利益攸关的世界建立良好关系,通过相互交往来取长补短,促进城市的全方位发展,为城市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其次,通过城市交往推动城市走向世界,进而带动企业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促进文化交流,全球城市也越来越是国家跨文化交流的战略支点,城市自身成为符号和展示一个国家文化的载体。再次,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软实力,进而在某种程度下也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整合城市的资源并将其转换为全球影响力。再其次,城市是国际间人、财、物、信息交流的枢纽,城市交往是国家外交活动的自然延伸,有利于盘活外交资源,拓展国家外交运作空间,推进国家整体外交,成为国家整体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城市外交活动议题灵活,形式多样,常常能够在总体外交的统一部署下,以其官民并重的形式在新领域或敏感问题的解决上有所开拓。[16]最后,城市交往不仅有利于推动全球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趋势,还为全球治理创造了新的机遇,在全球暖化、健康问题全球化的今天促进全球公共福利。[7]
正因如此,城市交往的这些功能往往还是多层次的,既有城市及地区层面的价值,又有国家、国际层面的效果。
当今世界各国的交往,不仅有城市安全、发展友好关系的需求,更有竞争与合作的需求。一方面,在经济、软实力等方面如同企业般展开竞争,还在更高层次代表国家开展竞争,因为全球城市本身就是符号、品牌,是交往的载体;另一方面,全球城市交往具有携手合作以解决单个城市无法解决的全球治理问题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城市开拓创新,运用多种手法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借助新兴传播技术与工具,在为自己城市获得竞争优势的同时,为国家交往在微观操作层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Al-Rodhan, R.F. Nayef and Gérard Stoudmann. (2006). Definitions of Globalization: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and a Proposed Definition,http://www.gcsp.ch/About-Us/Staff/Staff/Dr-Nayef-AL-RODHAN/Publications/Articles/Definitions-of-Globalization-A-Comprehensive-Overview-and-a-Proposed-Definition.
②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0), Globalization: Threats or Opportunity, 12th April 2000: IMF Publications.
③《联合国报告预测: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再增25亿》,http://money.163.com/14/0711/07/A0RVDM3M00254TI5.html.
④《移民、机会和吸引力:全球化时代下的城市外交》,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6235.
⑤《友好城市的地位和作用》,http://www.tj.gov.cn/zjtj/yhcs/ycdywj/200708/t20070831_3086.htm.
⑥Robert. W. Grupp,《全球化下的公共关系与公共外交》,第18届世界公共关系大会论文集。
⑦Michele Acuto,Urban Diplomacy:Local Leaders, Global Challenges,http://opencanada.org/features/the-think-tank/essays/urban-diplomacy/.
⑧What is Public Diplomacy? 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index.php/about/what_is_pd/.
⑨Teresa La Porte,(2012) The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Non-State Actors and the Public Diplomacy Concept. Public Diplomacy Theory and Conceptual Issues. ISA Annual Convention, San Diego, April 1-4, 2012.
⑩Definitions of Public Diplomacy,http://fletcher.tufts.edu/Murrow/Diplomacy/Definitions.
[1] 罗思东,陈惠云.全球城市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功能[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3).
[2] 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
[3] 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4] 万光侠.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0,(4).
[5] 唐晓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6).
[6] 王凤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J].理论学刊,2003,(9).
[7] Juyan Zhang, Brecken Chinn Swartz. Public diplomacy to promote Global Public Goods (GPG): Conceptual expansion, ethical grounds, and rhetoric[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09,35(4): 382-387.
[8]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9] Malone G D. Political advocac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ganizing the nation’s public diplomacy[M]. Boston: University of Press of America, 1998.
[10] Joseph S Nye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Z].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616: 94.
[11] Tuch H 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M]. New York: St. Martin’s,1990:3.
[12] Editorial,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The new frontier for public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2,38:643-651.
[13] Jacquie L’Etang. Public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An Issu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9,53(4):607-626.
[14] 任远,等.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5] Jan Melissen.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6] 熊炜,王婕.城市外交:理论争辩与实践特点[J].公共外交季刊,2013,春季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