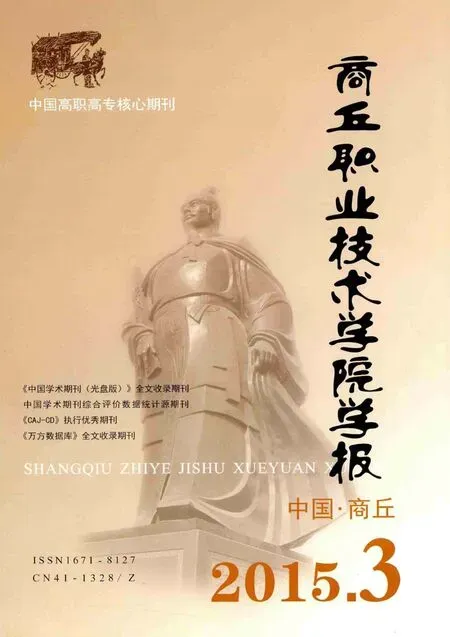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整体观思考
——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邓菁菁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整体观思考
——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邓菁菁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僵硬陈旧的研究范式,形成了新的整体观研究范式,这种整体观范式基本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沿用至今。但是,当文学批评实践未能充分体现这种整体观时,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拓宽整体观研究范式的内涵,将文化研究作为整体观研究范式的内涵外延加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中。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整体观;研究范式;文化研究
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随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文学史的编纂集中地体现了权力机制、知识分子精神与学科独立性之间的博弈以及学科的研究思路与状况。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以“中国革命”为线索、以“鲁郭曹巴老茅”为叙事经典、以扼杀论者的主体性为代价、以极具政治意义的1949年为分界点,将鲁迅神话为中国革命文学成绩的合理盾牌,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代文学传统。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与政权的集中,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控制愈来愈严格,出现了十四院校集体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标准”严重遮蔽了文学的“审美标准”,文学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讨论和成果,而像是为中国革命取得合法性的一种光荣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可以说是一种有选择的“意识形态”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无疑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僵硬陈旧的研究范式势必会被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新的整体观研究范式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应运而生,是对“意识形态”研究范式的宣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起初是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三位年轻学者私下讨论的想法,于1985年由黄子平执笔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形成的概念,文章中说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延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由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1]1。虽然,现在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整体意识也不无偏颇,也是一种经过选择,通过不提“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而使得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传统接续,这不能不与年轻学者的心态、时代以及学术氛围有关,三者都急需找到自己合理性地位的存在,但它却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研究范式扩大了文学研究视野和批评空间,活跃了学术氛围,达到了学术界的共鸣,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1]1。黄、陈、钱三人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意识概括为两点:一是把研究对象置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两个大背景中,二是“打破‘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的割裂”[1]18。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正是以现代性为线索、以整体观为研究范式编撰而成的。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
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2]464,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文革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3]84。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4]。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5]73。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1] 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
[2] 王德威.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
[3] 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J].南方文坛对话笔记, 2009(3).
[4] 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世界眼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Z].1985.
[5] 李凤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及其批评实践[J].文艺研究,2009(2).
2015-01-26
邓菁菁(1991- ),女,安徽六安人,安徽大学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
A
1671-8127(2015)03-0078-03
[责任编辑袁培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