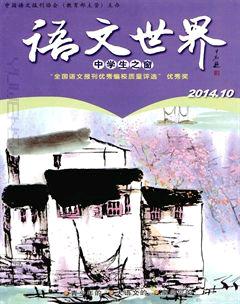我和父亲季羡林
季承
我们要把母亲接来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
1951、1952年姐姐和我高中毕业,分别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我是去北京参加高考的,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翠花胡同那一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址,但在历史上它却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正门在南面。深宅大院,几层几进,不知道有多少院落。那时,大门是开在翠花胡同路南一侧,其实是大院的后门,而父亲则住在从南面数第二个院落里,也就是从北面看是倒数第二个院落的西屋里。白天大院里有人工作,到了晚上,灯光微暗,阴森恐怖,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门房里值班,绝少有人敢深入大院。父亲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姐姐当时也到北京来了一趟,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父亲带我和姐姐吃过东来顺的烤肉和馅饼,喝过北京的豆汁,也在沙滩北大红楼外面街边的地摊上吃过豆腐脑和烙饼。除豆汁外,沙滩附近一家小饭馆做的猪油葱花饼加小米绿豆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在父亲的住处,还有美国铁筒装的白砂糖,那恐怕是他在德国时的“战利品”,我很惊讶,他竟能保存到那个时候。有时,我就把砂糖夹在馒头里当饭吃。
我的学校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西头的一所王府里。父亲则远在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工作。两地虽有公共交通,但很不方便,因此很少见面。他每个月都是通过邮局给我寄零用钱15元。因为当时学校免费供给伙食,所以作为零用钱,15元这个数目也不算少了,在学校里我是“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部分钱,我都用去买书,少部分零用,有时还接济实在困难的同学。每次父亲汇款,在邮寄汇款单的时候,总附有一个短信给我,上面一律写着:“今寄去人民币15元,请查收。”仅此而已,再多的话是没有过的。我看了觉得很生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他除了问我学校里都学些什么课程并认为科目太少之外,对我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打算从不过问,我也不敢对他谈什么心里话。我感到,父亲对我一直是一个生疏、冷漠的人。
1955年暑期,我和姐姐同时毕业。下半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俩参加工作,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他亲自带我们两个去王府井,在亨得利钟表店里挑选。在当时每块大约一百几十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我自己又花了27块钱在内联升鞋店买了一双皮鞋,在当时这已经是够奢侈的了。这是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期天去看父亲。我所工作的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是中关村的第一个研究所。我的宿舍离父亲住的北大中关园公寓,相距只有几百米远,在我们的办公大楼楼顶上就能看见他住处的灯光。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平常的时间里去看过他。姐姐住在马神庙建筑设计院的宿舍里。我们和父亲仍然很生疏。去看他的时候,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与家庭和个人有关的事情,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我和姐姐虽然感到很不舒服,也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才能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如何才能使父亲真正融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特别担忧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觉得如果他们那种冷淡的关系长期继续下去,这个家恐怕就要瓦解了。当时我们看到,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村北大的宿舍里,房间无人收拾,卧室由于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很多灰尘,父亲就蜷曲着睡在床上,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以后很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位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顾呢?那时我和姐姐就是想让他们团聚。于是我们决定先由我们做起,尽量多与父亲接触,增进感情,然后再解决叔祖母和母亲与父亲增进感情的问题。可是,也许我们做的不够,也许是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一般说来,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我们两个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而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则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有一次,我和姐姐去看父亲,终于涉及到家庭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家庭团聚的事免谈。我们失望至极,此后我们有很长时间就再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195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里有时间谈论家庭的事。但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后,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挣扎过活,这使我和姐姐不能忍心。我们吃不饱的时候,就想到她们也在挨饿。我们时时牵挂着她们。于是我和姐姐下决心旧话重提。这次我们的决心是一定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如父亲不同意,就让她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再也不能让叔祖母和母亲孤零零地在济南生活了,当然也不愿意再看着父亲过单身汉的生活。我们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于是我便开始行动。我于1961年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北京,就住在中关村我的宿舍里。我同时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报告。这样,叔祖母和母亲就回去到济南搬家,不久她们就到北京来和父亲团聚了。我和姐姐的果断举动,实现了家庭的团聚,但究竟是好是坏,难以预测,只有以后走着瞧了。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父亲对我和姐姐虽有不满,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只不过这件事仍不免是我们家庭内部难以理顺的问题。
家庭从形式上来看是团聚了。叔祖母和母亲内心自然高兴,可是也并不踏实——她们能和父亲和睦相处吗?
为了保护父亲,我们干了几桩蠢事
“文革”一开始,我和叔祖母就干了一些蠢事。我们想把父亲的许多旧信处理掉。于是我就在楼后面焚烧。正烧之间,恰巧有一队红卫兵走过,立即过来询问并把火浇灭,把尚未烧完的信件拿走。于是这便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无独有偶,红卫兵在剩余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张蒋介石的照片(这是父亲在德国留学时大使馆赠送的),这就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我和叔祖母为这件事感到非常内疚。不过蠢事却不断地发生。
北大抄家之风骤起,气氛极为恐怖。叔祖母害怕放在厨房里的菜刀容易为歹徒使用并且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将一把菜刀藏在自己枕头下面,这显然是一件幼稚而迷信的举动。红卫兵来抄家,发现了这把菜刀,他们硬说是父亲图谋杀害红卫兵用的,并且在批斗会上亮出了那把刀,真是铁证如山,有口难辩,父亲只好承受拳脚惩罚。这件蠢事又使叔祖母懊悔不已。
按照红卫兵的命令,父亲把自己住的四间屋子腾出两间,由原住楼下的田德望夫妇搬进来。父亲的许多家具无处搁置,只得堆在田家的一间屋里,占了很大的面积。时间久了,田夫人不满。叔祖母是个急性子,便和我商议要把一些家具卖掉。我随即便把一套高级沙发、一个七巧板式紫檀木组合方桌、两把紫檀木太师椅等几件家具送去西单旧货店卖掉了。一共卖了50块钱。第二天,家具店认为估价太少,又给添了5元。我们哪知道,那沙发没什么,可那套紫檀木家具却是宝物,那是清朝末年重臣赵尔巽家的珍贵陈设,是父亲在解放前夕购买的。父亲那时在农村,回来后得知他心爱的家具被我们卖掉了,大为心痛。叔祖母和我又干了一件蠢事,又一次懊悔不已。
可是我们干这些事,的的确确,都是为了父亲好,虽感到懊悔但于心却无愧。叔祖母和母亲来北京没有几年,就要和父亲共度艰难岁月,相依为命,真是令人难以接受。可是,叔祖母个性坚强,不畏艰难,不怕危险,无论看来有多么大风险临头,她总是咬紧牙关,坚韧面对,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情况越险恶,她的意志越坚强。她是我们家的一个擎天柱。她说话不多,但临危不惧,处之泰然。我母亲则以她那与生俱来的憨厚,面对这场她根本无法理解的灾难。她们俩总是想方设法为父亲做点可口的饭菜,用无言的支持帮父亲度过一次次难关,注意父亲不要做出轻生的事。
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我和姐姐也不敢回家,只有她们俩带着孙子过活。我有时冒着风险偷偷地回去看一看,送点钱,安慰一下,如此而已。有一次我回去,正好碰到父亲被放回家准备参加下午的批斗大会。所谓准备,就是要自制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再用红笔在自己的姓名上打上个大叉子。姓名要倒着写,表示反动并且已被打倒。他见我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如法炮制,只是在挂的绳子上做了点小手脚,选了根稍粗一点的绳子,以免脖子吃亏。父亲一句话没有说,他表情严肃,正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他虽然念过许多书,走过许多地方,可谓见多识广,但对那场史无前例的疯狂政治运动,除了愤怒之外,也是茫然无知。
我和姐姐单位的“文革”运动也开展起来了。我们中止了在安徽的“四清”运动,被调回北京参加“文革”。我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属中科院和核工业部双重领导,运动也是双重的。我当时担任原子能所中关村分部一、三、四、十一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和赵忠尧副所长的秘书、党总支委员、共青团总支书记。官衔不少,级别只不过是副科级。我没赶上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段时间,可是一到所里也是大字报迎接。我觉得我还算不上当权派,也有积极参加运动的愿望。可是革命群众总不买我们的账。我们这些所谓中层干部就整天关在屋子里无所事事。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和大家讨论要主动参加到运动中去。大家,包括党总支书记、分部副主任在内的全体干部,都表示让我出头组织一个“中层干部革命造反小组”,以赢得革命群众的信任。二机部的运动比科学院的要落后一些,我们自觉有了底,造反有理,便去核工业部煽风点火,闹革命。就这样到了部里就和那里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二机部革命造反总部”。我由于是中层干部的代表,又来自运动较为先进的科学院,竟然被选进了总部勤务组,成为一个勤务员,进而又被推选担任组长,俨然成了二机部“文革”的重要领导人。从1966年年底到1967年2月,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事件,直至所谓“一月风暴”夺权后离开。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开眼界,饱受考验。我作为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亲身体验了什么叫群众运动,也看到了共产党在执政仅十几年后在群众关系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确确实实整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当我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材料和部分内容时,我心中真的感到恐怖。
我老婆在国家科委工作,她是所谓的铁杆保守派,她保所有的领导干部,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她在保一位副主任××时特别坚定,甚至顽固。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争执,我并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直到后来我挨整的时候,她才表示,如果我是“五一六分子”,她就和我离婚。
我姐姐在二机部设计院工作,“文革”中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只是普通的一员。造反派里有许多人确实和我姐姐一样是较为正直的人。他们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有意见,特别是对整人的做法不满。他们有别于那些有个人野心、行为上胡作非为的人。我觉得对造反派也要有所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姐夫则抱定他的人生哲学,谁也不得罪,对谁都没意见,什么派也不参加,平稳地度过了“文革”。“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却考验了每一个人,包括季家的每一个人。
(选摘自《南方周末》第13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