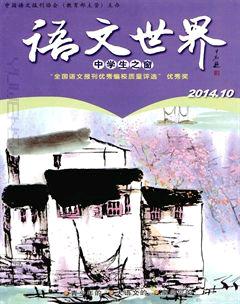千江有水千江月
钱建江
在所有的称呼中,对我而言,再没有比“语文老师”更觉亲切的了。
年少时,还不知道什么是“语文”的时候,我就在用种种方式对“语文”暗送秋波。
我家堂屋后面和厢房外面是一片竹林,竹林下面是小河,小河对面是农田。门厅外面是两棵橘子树,前面是场地,边上有几棵大树。庭院的角落里一年四季开满了花,最多的是夜饭花,还有凤仙花。这两种花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每天夕阳在翘起的屋檐下沉落后,铃铛一般的夜饭花静静开放;当凤仙花开过之后,成熟的籽荚吹弹欲破,我故意去碰碰它,褐色的籽粒顷刻弹射出来,花荚缩成一卷,正似邻家那位含羞的小妹妹。屋檐下是一圈黑得发亮的雨槽,我喜欢在雨天看着积水顺着雨槽挂下,就像缠绵的梦,很快不知去向了。雨过天晴,蜻蜓忽东忽西地飞。一会儿,雨又来了。燕子赶紧躲到堂屋前的檐下,眨着黑眼睛,周围只剩雨声了。——这些应该是我记忆里最早的“阅读”了。
童年阅读的另一种方式是看画。我很喜欢我家堂屋南北两边墙上贴的那些画。某一年,贴的是《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上,年轻的毛泽东身穿藏青色长衫,手持一把油纸伞,大踏步向前走去。那张画的上方挂着一只广播喇叭,每天晚上我都可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但我根本听不懂。后来,墙上贴了一张《林冲雪夜上梁山》,漫天风雪中,林冲身披斗篷,肩扛一柄银枪,挑着一个酒葫芦,双目紧锁,走向遥远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墙上换上了一张《洪湖赤卫队》。吸引我的,是那水乡泽国的景象: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浩渺烟波中,也隐藏着战斗的气息。我七岁那年,墙上多了一张《敬爱的华主席》,画里一个小姑娘在学妈妈绣花,绣的就是敬爱的华主席。随后,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大幅标准像并排贴在东墙最高处,我每天都能看到他们慈祥的面容。又过了几年,墙上贴上了一张《年年有余》的年画,那个胖小子抱着肥肥的红鲤鱼,着实令人羡慕。我读初中的时候,墙上贴上了一张艺术体操的图片,那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子,正在练习绳操,动作舒缓优雅,很多年她都是我的“梦中情人”。在那些画幅下面,还贴着我姐姐的三好学生奖状,大概有十几张,每一张上面都有旗帜和红缨枪,还有毛主席语录。那些奖状渐渐斑驳黯淡了,但我父母还是常常用它们来教育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冬天或者下雨的夏天,母亲不能外出劳作,便坐在窗下做布鞋。母亲夹鞋样的书,不知被我翻过多少遍。那是一本早已过期了的《人民画报》。当时家里的书少得可怜,更何况是大开本彩页的。我坐在母亲边上,安安静静地翻那本书,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页翻到第一页;从大庆翻到大寨,又从大寨翻到大庆。我的童年就这样一页页地翻过去了。家里的另一本书,是批判《水浒传》的,已记不清书名了。里面的文章充满火药味,把宋江批得体无完肤。我似懂非懂,看得晕乎乎的,心里一直庆幸我不是那个宋江。我对那本书本无兴趣,只是里面夹了很多邮票,我才经常去翻。那些邮票都是在福建永安林场工作的姑夫与我父亲通信时留下的。可惜后来随那本书一同不见了。都是那个倒霉的宋江,我就在心里一直记恨着他。小伙伴闹别扭时,哪个不相好了,就喊他“宋江”。
那时,镇上没有书卖,却有一家出租连环画的国营店铺。店里面有几百本连环画,封面一律被撕下,分别编了号,像招贴画一样挂在外边的木板上。被撕去了封面的内芯也一律贴上了牛皮纸,用笔墨写上号码,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书架摆放在用木栅栏隔着的里屋内。外面放了几条破旧的长凳,那时没有水门汀,高低不平的泥地被人们踩得光溜溜的。那儿也成了我神往的地方。但我还太小,够不到那高高的柜台,只能站在门外,出神地望着那些大孩子眉飞色舞地捧着书看。我有时忍不住悄悄地躲在他们背后偷偷地看上一眼,又免不了会遭到呵斥。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在一个雪花飞尽桃花又开的时节到来之后,我也终于可以踮着脚把大人给我买山楂的分币递进那高高的柜台上的窗口了。
“借一本《火车司机的儿子》。”我小心翼翼地说。半天没人搭理。我又鼓足勇气喊:“借一本《火车司机的儿子》!”终于有一位老先生探出头来,看见了柜台下的我,有些惊奇地说:“这么点大就来借书啦,你得要报出封面上的号码!”我才知道借书还需要这样的“暗号”。但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亲手翻动着书页,我的眼睛变得更明亮了。——那天下午我是一路欢跳着回家的,路边的油菜花金黄一片,我也仿佛成了一只第一次尝到甜甜花粉的小蜜蜂,我的心飞舞着。
我就读的中学,它的前身是一所寺庙——智林寺,初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后屡经兴废,最终在1957年改建为中学。学校里有三棵巨大的银杏树,每一棵都有500多岁了,它们成为每一个学子心中的骄傲。尤其是在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了通和尚拔木头”的故事后,这三棵古树以及这所学校在我心中更富有了传奇色彩。多年以后,在一篇回忆母校生活的文章中,我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年少时,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抬头仰望,那枝丫间有我五彩斑斓的梦想……记得当年为了建造礼堂,学校发动我们捐献砖头。我在自家竹园里捡了好多砖块,装在布袋里背到学校,交给老师过秤。挖壕沟打地基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去工地帮忙。汗流浃背之后,老师奖励我们每人一根冰棍,那凉爽的滋味至今不忘。
学校里还有一棵高大的雪松,静静矗立在教学楼前面。它年复一年地生长,也年复一年地出现在孩子们的作文里。现在每次读到“它像个哨兵,守卫着我们的校园”这样的句子,我就会想起三十年前,一个少年在作文课上咬着笔杆子,出神地凝视着教室外的大雪松,然后埋头写下这句话。那棵雪松上架着一只高音喇叭,伴着那里面传出的音乐,我做了六年的广播操。后来,我负责学校“智林之声”广播站时,那只喇叭里还播放过贝多芬的交响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裴多菲的诗以及马克·吐温的幽默故事……
下课铃声响起来,我们跑向操场——那长着柔软的青草的操场。没有人会去在意操场边的秋千上有没有蝴蝶停在上面,因为我们奔跑的姿态本身就像一只只蝴蝶。然后,我们就开始摔跤比赛。多数时候只需把脚伸过去一勾,手臂一扭,对手当即倒地。胜者又蹦又跳,败者不折不挠。反败为胜者亦时有之。反正操场很软,怎么摔也不会有伤痛。如今看到很多现代化的校园里铺设的塑胶跑道和人造草坪,那里,没有了官司草,没有了蒲公英,没有了蟋蟀,没有了蚂蚁,也没有了草丛间飞舞的蝴蝶,我的心头总有莫名的惆怅呢。
盼望已久的寒假到了,村里村外落满了雪。我坐在堂屋里做作业,脚跟头放着铜火炉。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单田芳的评书《杨家将》,我等着邮差送来我订阅的《课堂内外》和《黄金时代》。杨六郎舞着一杆素缨蘸金枪,已经把孟良、焦赞都收服麾下了,邮差先生还没有来。我猜想着门外一定是白茫茫一片,大片的麦田也早就隐藏起它们的绿色,邮差先生兴许是迷路了。
姐姐们对着窗口做手工活,我的作业做完了,便坐在写字台前写自传。那会儿我十多岁的样子,天知道受了什么蛊惑,用歪歪扭扭的字给自己写传记。直到今天,那些手稿还夹在书堆里,有时候偶然翻到,时不时触动着我的心。
童年已远去,青春也不见了踪影。柳眉儿长了又落,落了又长,我已做了二十多年语文教师。我知道,我这一生都将伴着书香度过。
“千山同一月,万户尽皆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嘉泰普灯录》中的这几句偈语,道出了我对语文的真实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