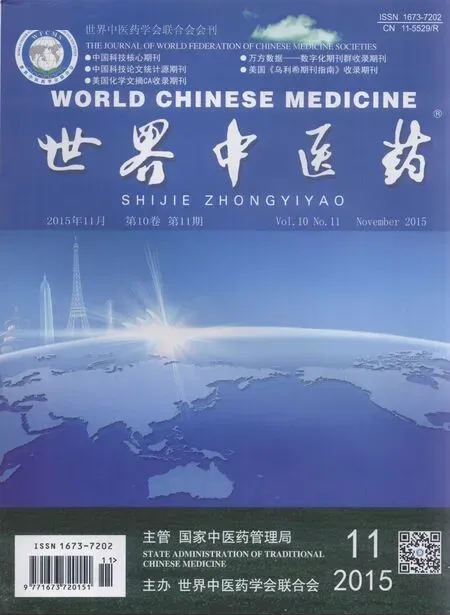肝藏血与血液储藏及运行的历史考察
李 丹 李成卫 王庆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临床基础系,北京,100029)
肝藏血与血液储藏及运行的历史考察
李 丹 李成卫 王庆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临床基础系,北京,100029)
肝藏血与血液储藏及运行的关系问题经过3个历史时期的考察得出,不同的时期肝藏血与血液的运行的关系有所不同,特别是汇通学派后由于西学知识的引入心脏循环理论的出现,使得中医理论开始重视血液的运行问题,弱化了明代以来形成的命门生气血的理论,引入了肝主神经说,使得肝藏血开始与调节血液的运行发生了联系。
肝藏血;血液;神经
肝藏血作为现代中医基础理论肝脏的一大生理功能,一直是藏象学说的研究重点。国家现行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一书在“藏象”一章中记载肝有两大生理功能,一是疏泄,二是藏血。其对肝脏的藏血功能的定义是“肝具有储藏血液调节血量的生理功能。”[1]其意为肝脏有储藏血液及调节血液运行之功能,并且认为肝脏藏血功能包含储藏及运行之意的理论源头为《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为此,我们在本文将从3个历史时期来考察肝藏血与血液储藏及血液运行的关系,旨在厘清历史,并希望借此考察能对中医肝脏象理论的研究发展有所裨益。
1 秦汉时期肝脏藏血以舍魂,营卫之气相随而行为血液的运行方式及途径
《内经》中肝藏血出现两次,分别在《素问·调经论》“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与《灵枢·本神》“五脏之所藏”的主题中出现。后世特别是现代医家多认为肝与血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肝藏血的功能就是此期所确立的,而且其发生原理来自解剖。何裕民先生在论述肝与血的时候写到:“揣测其说之起始,源于直观无疑。祭祀献脏或通常杀牲时,血淋淋的肝脏呈紫血色,柔软而富含血类,很容易使人萌生上述观念。作为有力的佐证:世界医学史专家发现许多民族都有类似的认识。如古巴比伦医学认为‘藏血器官的肝脏是重要生命力所在’他们的这一认识源于祭祀,因为其地早期的风俗是献祭的动物必须检查肝脏,并以肝脏作占卜之用。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上述观念是自然而然的事[2]。”实际上通过笔者对《内经》通篇的考察发现在《内经》中肝与血的系远不如我们想象的这么密切,经过统计《黄帝内经》中“血”共计出现了701次,血气同时并举为132次,而血在单独出现时其所指皆是可见的实质性的内容物,如:便血、衃血、出血、唾血、脓血、脱血、歃血、取血、舌下血、郄中血、太阴少阴血、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少阴太阳血、伤血、恶血、溺血、呕血、溲血、血衄、下血、血瘕等。由此可见肝与血之间的联系在这一时期远没有气与血的联系密切。
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派,发展及总结了关于宇宙的“道气”说,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所讲的“道”被认为是宇宙的起源,这种“道”在稷下学派这里发展为了“精气”学说。《管子·内业》篇:“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为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是为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精气所化生组成。可能正是由于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战国时期著名的稷下学派的精气学说的影响下使“血”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具有强大地位的气论甚至使“血”的概念被边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血”竟有被营卫概念所取代的境地。《营卫生会》篇:“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据《营卫生会》篇的描述流动在脉中的是一种红色的物质又称作为营气。对于营气与血的关系,很多人认为:营气是具有营养全身、充盛经脉和化生血液作用的气[3],即是认为血是由营气化生的,那么这就与《黄帝内经·决气第三十》一篇中的“气”被一分为六的论述相违背,从实质上来说在秦汉人眼中营气与卫气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在脉中一个在脉外,气血的运行方式便是营卫二者相随而行,二者皆被称为“气”,可见“血”概念的边缘化。
在《素问·脉要精微论》一篇中明确提到了血之府为“脉”;而《海论》篇中的“血海”是冲脉,此期的冲脉“冲脉者,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侠齐上行,至胸中而散。”多与肾相关,行文中没有发现其与肝及肝经有直接互属的关系。为此,与血关系密切的血府、血海皆与肝无明确的直接相关之联系,而肝和血相联系,除《本神》篇与《调经论》篇之外,见于《素问·五藏生成篇》:“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此处“卧”说文解字释义为“寑者臥也……引伸爲凡休息之偁”据此,我们发现《内经》中的肝与血的关系其连接有肝-魂(睡眠梦)-血这样一个关系。为此,《内经》中“肝藏血”的出现是为了说明肝藏魂,而魂舍于血,便有了肝藏血以舍魂,它不具备调节血液运行的功能,是以我们在《内经》中很难发现血与肝的关系。
2 宋明时期肝储藏血液,命门生气血相火主动
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写到:“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之医家,乃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求其理”[4]在这一时期虽然医学的发展开始从重视医疗经验技术发展到推求医理的重要性,而在肝藏血来说,此期在延续秦汉时期肝储藏血液的内容外由于易学的引入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后医学界掀起了引易入医的热潮,出现了朱丹溪、张景岳、赵献可、薛立斋等医易学大家,在这一时期生命的动力逐渐被确立为命门,使得肝脏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肝逐渐成为相火的代名词,成为了命门中主动的动力所在(具体命门的详细论述请见相火命门考辨),为此由于气的推动作用的来源是命门,秦汉的医学理论是气血相随而行,气的来源是“天”,而宋明时期气来源于命门,并把命门主动的功能归为了肝所代的相火,为此肝藏血的理论与秦汉时期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肝主动的引入首先就使得肝藏血所代表的血证的病机发生了变化,自此以后藏血和疏泄就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肝脏的主要理论也由秦汉时期的气血理论转变为肝疏泄与藏血的理论。
血证的病机在宋明时期被确立为肝火盛、肝升发太过,即使到后期出现了肝虚仍需补的观点,血证的主流治法仍然被认为是需要平肝的。虞抟在其《苍生司命》中便用相火动解释吐血,“大怒则血苑于上,令人暴绝,名曰煎厥。故多怒之人,肝火屡动……而所藏之血,随火上逆,大吐不止。稍久则并脏腑膻中之血,尽吐不留,所谓相火一动,则五火相煽而动,火动则血随之。”[5]认为相火妄动是致使出血的原因。赵献可在论吐血的治疗时说“凡吐血不已,则气血皆虚,虚则生寒,是故用柏叶。柏叶生而西向,乃禀兑金之气而生,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妇之道和,则血得以归藏于肝矣,故用是为君”由此可见血证的病机为肝升发太过需要平肝,早期治疗“肝气有余”多用龙胆泻肝汤、当归龙荟丸一类的峻泻方剂,造成了苦寒太过的现象,因此从明朝中期有了肝虚有无补法之争议。
肝脏的功能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丹溪时期肝虽有相火有主动的功能然其主动的功能却是只是在生殖之精中有,而发展至明朝肝的主升主动功能被扩大、肝常有余无补法之说发展到极致,导致了肝脏藏血功能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变化,从明中期开始特别是温补命门派的出现对“肝有泻无补”的治法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明中期以后的各家开始质疑肝无补法理论的缺陷并且采用肝的体用说以解决肝的争议。张景岳在《质疑录》中有肝有无补法、肝虚到底能否补肝等问题的讨论。《质疑录》:“足厥阴肝为风木之脏,喜条达而恶抑郁,故经云木郁则达之是也。然肝藏血,人夜卧则血归于肝,是肝之所赖以养者,血也。肝血虚,则肝火旺;肝火旺者,肝气逆也。肝气逆,则气实,为有余;有余则泻,举世尽曰伐肝,故谓“肝无补法”。不知肝气有余不可补,补则气滞而不舒,非云血之不可补也。肝血不足,则为筋挛,为角弓,为抽搐,为爪枯,为目眩,为头痛,为胁肋痛,为少腹痛,为疝痛诸症。凡此皆肝血不荣也,而可以不补乎?然补肝血,又莫如滋肾水。水者,木之母也,母旺则子强,是以当滋化源。若谓“肝无补法”,见肝之病者,尽以伐肝为事,愈疏而愈虚,病有不可胜言矣。故谓“肝无补法”者,以肝气之不可补,而非谓肝血之不可补也。”景岳将肝分为肝体与肝用,肝用是肝气不可补,而肝血却是可以补的。我们可以认为命门的存在肝的主升主动功能必须依赖于肝血的存在。到李中梓提出了“乙癸同源”之说,从理论上解决了肝有无补法的争议。《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曰:“盖火分君相,君火者,居乎上而主静;相火者,处乎下而主动。君火惟一,心主是也;相火有二,乃肾与肝。肾应北方壬癸,于赴为坎,于象为龙,龙潜海底,龙起而火随之。肝应东方甲乙,于赴为震,于象为雷,雷藏泽中,雷起而火随之。泽也,海也,莫非水也,莫非下也。故曰乙癸同源。”此篇揭示了肝肾在生理上存在着相互资助、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治疗原则上,李中梓倡导肝肾同治,“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北方之水,无实不可泻,泻肝即所以泻肾。至乎春升,龙不现雷无声;及其秋降,雨未收则龙不藏。但使龙归海底,必无迅发之雷;但使雷藏泽中,必无飞腾之龙。故曰:肝肾同治。”又说“然木既无虚,又言补肝者,肝气不可犯,肝血自当养也。血不足者濡之,水之属也,壮水之源,木赖以荣。水既无实,又言海贤者,贤阴不可亏,而肾气不可尤也。气有余者伐之,木之属也,伐木之干,水赖以安。夫一补一泻,气血攸分;即泻即补,水木同府。总之,相火易上,身中所苦,泻木所以降气,补水所以制火,气即火,火即气,同物而异名也。故知气有余便是火者,愈知乙癸同源之说矣。即不可妄补肝,不可妄泻肾,补肾水即所以补肝,泻肝气即所以泻肾。”因此,从李中梓“乙癸同源”论开始肝有无补法的争议在理论与临床实际上皆得到了解决。我们从廖希雍著名的止血三法“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可以看到这个时期肝脏的治法特点:苦寒泻肝法的滥用。为此,廖希雍在吐血中强调肝虽为将军之官然养肝才能令肝气平而血有所归,若一味伐肝则会导致肝虚不能藏血,而血愈不止。因此在治疗上他主张用白芍、炙甘草制肝多用甘寒法而忌苦寒。在廖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泻肝法在临床实际运用中的变化,在治法上不再一味的用苦寒泻法,而是明确提出了血证的治疗原则为“宜补肝不宜伐肝”。
综上,宋明时期由于医学理论的变化,命门相火理论的出现,肝藏血内容包括了储藏血液,相火主动理论的出现替代了秦汉时期的气血相随的理论,为此这个时期较多的在讨论相火的问题及相火与血的问题。
3 中西医汇通后肝主藏血主神经调节血液的运行
随着西医学知识的进入,特别是哈维血液动力学的发现及被引入中国,中医学理论在有关于血、气血等方面的认识也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最为明显的变化即是历来作为储存血液之用的肝脏开始有调节血行的作用,而血早期则被三个脏所分主不同的职能,主生血的心、主统血的脾、主藏血有调节血量作用的肝,到后期生血的具体脏器被弱化。
首先,心脏循环理论的出现使命门生气血的功能被它脏所替代。西学解剖知识的大量涌入使中医理论家们不得不开始对中医对血的理论进行调整,在明清形成的温补命门学派所创立的命门理论中主生血气的是先天命门,推动血液在脉管中运行的也是由命门所产生的气的作用,而西学知识的传入打破了这一认识,哈维发现心脏的搏动才是血液运行的推动力而不是中西方之前认为的脉管中存在的某种气的推动作用,这些知识的进入引起了中医学界的轩然大波使得各中医学家们开始思考与解决传统理论与新知识的冲突与矛盾。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心脏循环理论对传统中医学理论框架及临床实践的巨大影响和改变,如近代著名的回阳升陷汤便是张锡纯根据心脏循环理论所制定出来的,其说心脏有“左右上下四房;左上房主接肺经赤血;右上房主接周身回血;左下房主发赤血,营运周身;右下房主接上房回血过肺,更换赤血而回左上房;左上房赤血,落左下房入总脉管,以养全体;右上房回血,落右下房上注于肺,以出炭气而接养气。故人一身之血,皆经过于心肺。”为此在治疗上他通过生黄芪、干姜、桂枝、甘草增加心肺的热量助心推动血液的运行,用当归补心血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在心脏循环理论的影响下早期的中西医汇通家将心脏定义为生血的主要脏器,代表人物是唐容川,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早期中西医汇通家们所做的努力,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有“西医言心内,分左右四房,皆有管窍为生血回血之用,血受炭气,则紫回行至心右房。有一总管,接回血入心中,落右下房;又一总管,运血出而过肺,被肺气吹去紫色,遂变纯赤,还入心之左上房,落左下房;又有一总管运血出行,遍于周身,回转于心。此即内经营卫交会,于手太阴肺及心主血脉之说也。”心主火,血色赤故而得出心生血,唐容川最为著名的“水即是气,火即是血”之论便可能也是基于中医学气化论西医学心脏循环论所得出的新知。并且他还将心生血、肝藏血可以调血的理论用到了临床实际对药物的指导性应用之中,《血证论·卷七》“心生血,肝藏血,故凡生血者,则究之于心。调血者,当求之于肝也。是方乃肝经调血之专剂,非心经生血之主方也。当归和血,川芎活血,芍药敛血,地黄补血,四物具生长收藏之用……然谓四物为肝经调血之专剂,则深知四物之长者矣。盖肝主藏血,冲任血海,均属于肝。故调血者,舍四物不能为功。”四物汤由此成为了专门调节肝血行的方剂,而在此之前肝没有这个功能,生血的脏器也不是心。
在考察汇通学派的生血理论中笔者发现,到了中后期医家们不再提出血是由具体哪个脏器所生的问题了,比如张锡纯医学著作通篇竟然都没有有关某脏生血气的文献出现,多是某药可以补心血、补脾血、补肝血;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龙眼肉解中说“龙眼肉:味甘,气香,性平。液浓而润,为心脾要药。能滋生心血(凡药之色赤液浓而甘者,皆能生血),兼能保合心气(甘而且香者皆能助气),能滋补脾血(味甘归脾)”[6]说药物色赤液浓就能生血明显是受心脏循环理论的影响,而在代赭石解中说赭石能“能生血兼能凉血,而其质重坠……其原质为铁养化合而成,其结体虽坚而层层如铁锈(铁锈亦铁养化合),……生服则养气纯全,大能养血”开始用含铁药物补血,在曹颖甫的书中有血虚经少重用铁屑四两补血的病例,并且方后注中言此方的立方意义极妙,他所说的立方意义具体指什么,并没有论述但是很显然可以推知立方依据与张锡纯所差无几,俱是因为铁元素可以补血之故。当然二者在此都谈到了药物的补血的功效,却皆没有谈到是何脏在生血,究其原因可能是认识到西医学中生血的器官也并不是心脏。总之自此明清以来命门生血气的作用被替代,早期受西学影响强调心脏是主生血之脏,后期随着更多的西学知识的发现与进入主生血的具体脏器被弱化。
从肝主筋到肝主神经是肝脏理论特别是肝藏血理论的一个巨大变化,肝被赋予主神经之功用后便有了可以调节血行之功,肝的主神经功能是肝可以调节血行的理论基础。在西说融入之前中医肝脏在体合筋,而在西说不断进入之后中医理论中肝脏与筋的关系表面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在肝与筋的关系中“神经”被插入进二者之间,并有代替肝主筋直接变为肝主神经的趋势。早期的中西医汇通者只是将肝与筋的关系用西医学知识解释其合理性,如唐容川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将肝主筋用西医生理解释说“肝生筋之迹,实由肝膈,连及周身之膜,由膜而连及于筋也……筋属肝,是从肝膈而发出网膜,然后生筋……”[7]。并把肝风发作的病机归为风中筋脉“强直僵扑倒地,暴者猝然发作,风性迅速,故能暴发。凡风均属之肝,肝属筋脉,风中筋脉,不能引动,则强直矣,风者阳动而阴应之也,故风俱阴阳两性。”[7]
至恽铁樵肝与神经开始相联系起来并且提出了肝主神经说。肝藏血能够调节血量的原理被神经的调节作用所解释。如恽铁樵认为出血之证是由于血管的破裂,而神经可以调节血行,他在《生理新语》中说虽然推动血液运行的原动力是心房的张弛运动然而“张弛之程序则全赖神经为之调节”[8],他通过神经之变化由神经自为救济因此往往见筋挛抽搐之症皆是纤维神经剧烈反射异常紧张的缘故进而以《内经》之谓肝之变动为握多为拘挛之意而得出肝主神经之说。陆渊雷在《桂枝汤今释》中也有芍药入肝脾“肝谓神经,脾指吸收作用”[9]的说法。张锡纯治疗肝阳上亢也多用矿石类药物潜降谓可以调节神经。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中也把肝主神经当做了一种普遍的医学知识“犀角能降低血压,其主在血液。羚羊角能凉和神经,其主在神经。依旧说,血液为心所主,故曰犀角为心经药;神经为肝所属,故曰羚羊角为肝经药”[10]由此可见肝主神经之说在中西医汇通后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医学知识。
最早提到肝调节血行之说者为唐容川,他在论心生血论时便提到有关于肝有纤维神经有调节血行的作用论述,他认为“凡神经所到之处皆是血所到之处,血在脉管中行,神经亦即附于血管之壁。神经藉血以为养,血亦藉神经为之调节”[8]他提出心主生血、肝主神经二者是相联系在一起的,并通过肝主神经说解释了肝藏血调节血量之说。
唐容川之后的各医家都持肝能调节血量之说,如恽铁樵从解剖实验所得从而证明中医学肝藏血理论的合理性,他在《生理新语》中论述肝藏血“唯其含血管最富,故取生物之肝剖之,几乎全肝皆血……故肝为藏血之脏器”杨如候在《灵素生理新论》中有“肝为腺甚巨,含血滋多,名曰血海,以肝藏血也。使血不经脏腑藏之,则回血管之收缩及发血管之注射其障碍于心脏之功用者甚巨,故血藏于肝,正所以调节之,使血液各安其道”。陆渊雷[11]在其《生理补证·补证三·中医之所谓肝》中说“肝为身中最大之脏器,亦为含血量最多之脏器。全身血液之分布,肝脏得总量四分之一。又知卧寐之时,肢体脏器之各种动作(心肺除外)皆在休息状态中,休息而不工作,则不需要血液。若欲入睡,则大脑之血液亦须减少。若脑部充血,决不能入睡,然则卧寐时除心肺外,全身各处皆欲减少其血,血既不能暂时避出身外,必有其贮藏调节之处。肝体大而最能含血,则卧后血归于肝”李聪甫论述肝的生理功能:“1)肝脏能储藏血液,且能储藏多量的铁。李士材说‘是经多血少气,其合筋也,其荣爪也……’说明肝脏是人体中的储血库。在胚胎第六周肝脏已开始制造血球。2)肝有调节血液循环的作用。假如切除肝脏而使门脉直接与大动脉血液流通,心脏变立刻胀大而静脉血郁积。由此可见,肝脏对调节血液循环的关系。曾经有人试验:堵塞通肝的血管,或将肝本质损坏时,先起痉挛,逾时而死。说明《五脏生成篇》所指“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以及“筋脉皆肝所主”的道理,李士材说“肝见证也,头痛脱色,阴缩筋挛”是符合事实的。3)肝内可以制造阻止血液凝固的肝素,使血液在血管内不致凝结。又能产生血浆纤维蛋白元以帮助凝血。并能利用维生素子,在肝内制造凝血素原。”
由此可见,肝的藏血功能被中西汇通各家们根据西学知识不断赋予新的解释,从早期肝与神经联系以解释肝的调节血行作用,到后期的血细胞一类的解释以证明肝藏血理论的合理性。总之,肝的调节血行作用是由于西医学生理病理知识的进入才形成的,肝藏血的理论在此前完成了嬗变。
4 结语
肝藏血与血液储藏及运行的问题经过历史考察发现其成为热点的理论问题是从近代才开始的,由于西学知识的引入心脏循环理论的出现,使得中医理论开始重视血液的运行问题,弱化了明代以来形成的命门生气血的理论,引入了肝主神经说,由神经说嬗变为了肝调节血量之说。为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肝藏血包含调节血量之说的内容是中西医汇通之后才产生的新理论。
[1]郭霞珍.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52.
[2]何裕民,张辉.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4:296.
[3]孙广仁.高博《内经》中营气、卫气概念及相关的几个问题[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30(1):65-67.
[4]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46.
[5]虞抟.苍生司命[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55.
[6]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15.
[7]唐容川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8,53.
[8]恽铁樵医书四种[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61,202.
[9]陆渊雷医书合集[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224.
[10]曹颖甫.经方实验录[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216.
[11]恽铁樵.恽铁樵医书四种[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53.
(2015-11-02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Historical Documentary about Liver Storing Blood and its Correlation to Blood Circulation
Li Dan,Li Chengwei,Wang Qingguo
(Beijing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Beijing100029,China)
After looking up to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ages,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storing blood and blood circulation differed to each other, especially after the age of Huitong academic school when western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Western medicine brought the idea of heart governs blood circulation to China, and thus the “life-gate generating blood” gradually faded. Moreover, “liver governing nerve” has emerged, which explained why liver storing blood correlated to blood circulation.
Liver storing blood; Blood; Nerve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11CB505100)
李丹(1986—),女,四川眉山人,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医堂门诊部,研究方向:张仲景诊治体系的历史与临床应用研究;肝藏血主疏泄的理论与历史研究
李成卫(1971—),男,河北保定人,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张仲景诊治体系的历史与临床应用研究;肝藏血主疏泄的理论与历史研究,E-mail:lichengw@126.com
R256.4
A
10.3969/j.issn.1673-7202.2015.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