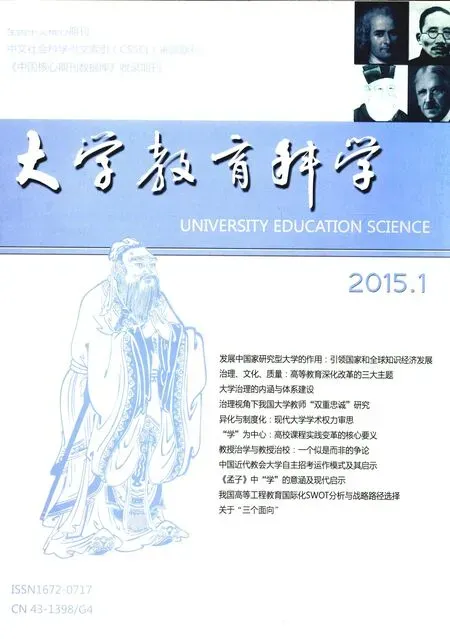异质文明下的游移:近代留美学生之身份二重转换
□ 张睦楚
异质文明下的游移:近代留美学生之身份二重转换
□ 张睦楚
在我国近代教育变迁进程中,留学生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又以赴美留学生起到的作用最为巨大。但假如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对留学生身份进行客观检视,留美学生不免处在二重转换的拉锯之中:留美生对于美国而言是旅居者;同时,由于长期的离乡背井使得他们对于故国又成为了陌生人。显然,对于留美学生身份双重二歧转换,需要从更为广阔的层面进行分析,剖析其中的过程与内在原因,从而为理解近代教育中西文化交流历史进程的特殊性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
近代留学教育;留美学生;异质文明;中西文化交流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经历着沧海一粟的激流变迁。在这一变迁中,其社会每一个体均经历着自身生命范式的独特转型及历史的选择。而近代教育体系特殊的变革历程,更是在彼时“西潮又东风”的背景下对异质文化不断相互调试与融合的探索——这一历史探索不仅见证着中国文化凭借自身生命力对西方文明的关系转换;更见证着本国教育体系在西风东渐背景下主动适应时代转换的期盼与实践。在这当中,留学生群体作为近代西方文明的“报春鸟”[1],鸣唱着中西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二律协奏曲,对两种异质文明融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也是偶然散落至大洋彼岸并载着文明种子的“蒲公英”,许久飘零之后却苦于无法找到来时的路完成理想的路径回归。正是因为游离于彼岸与此岸,不免产生了二重疏离,这与留学生当下时空主场的非逆性体现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造成他们的身份既是中西文化互通有无的“中介桥梁”,又是古与今、中与西双重共振产生向心力而抛到了时代外围的“边缘人”。
一、从新大陆的“过客”到故邦的“陌生人”
近代留美生被时代烙印上了“救亡启蒙”的符号,不可避免地承担起运用西方文明“药剂”医治中国彼时“顽疾”的历史责任,以期根据国内动态及社会走向西寻“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变革种子;他们也是“西学东渐”的最佳代言人,其角色同样意味着社会改造的责任——其中逻辑正是基于对留美生兼容并蓄活力与两种异质文明吸收与传播能力的正面假设。这是因为于中国固有文化而言,对异质文明的认同是隐藏在传统背后的一种巨大力量,正是这种生命力使得留学生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和好奇的心态迎接外来的一切文化,自然得以承担起以新式文明再造吾国文明的责任。然而,事实上,留美生的角色与身份却在现实中滑落至出乎意料的现实。
在彼时美洲“新大陆”,中西异质文化的每一次冲突与调和,随时都在冲击着留美生,他们面对新环境所产生的兴奋感与对故土留恋之情相互缠绕,这种缠绕之情伴随着内心的斗争:“试问功名何用处,秋月春花客里空空度”[2];“久为夷语乡音涩,不
见自由也自愁。今问今夕何处去,几曾梦做避秦人。恰同华表鹤归来,剩水残山太可哀,好奋雄图谋社稷,十年曾自受栽培。”[3]由此而来,留美生面对西方文明,既好奇又不免保持审慎的态度,一部分留学生甚至对西方文明感到略微失望:“彼邦多几座高逾百层的凌霄大厦、多密植着蜘蛛网般的铁路交通又算什么呢?没有灵魂的躯壳,没有生命的石像,有什么稀罕?欧洲大战不是他们造成的结果吗?像他们这样的专讲求物欲的满足,终日孜孜为利,充其量只好比一架机器,没有生命的机器。”[4]“美国文明,有产生其文明之特殊背景,然经济之弱点,劳工之间生活标准之差异,人民对政治讥讽之状态,均非吾人所敢学步者也。”[5]诚然,但凡从一种稳态熟稔的文化飘移至崭新却又陌生的文化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极大可能是理想与现实的难以精确对应这一现实,在留美学生中不可避免产生了心灵的矛盾与理智的冲突。在近代中国对“弱与强”、“文与野”、“中心与边缘”势力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倘若留美生所承担的角色仅仅定位为单纯地将两种异质文明融合加工的黏合剂,不免陷入到“工具主义”的深渊;而倘若又将其赋予能够救亡国家改造社会的使命,不免又显得压力重重,更使得他们对自身的使命产生着困惑与焦虑。但现实中,近代留学在彼时特殊背景下仍然是过渡时代的一种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留学生被赋予的使命仍然为“以期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一新文明、开一新天地。”[6]
时过境迁,当留美生纷纷回国时,本应是再造新文明的开始,然其却意外地成为一个“貌似的凯旋”[1],这是由于固有的体制障碍,使得西方文明之花难以大范围地在东方土地上生根发芽;加之近代以来在中西之间权势转换的结构中,留学生的角色虽被设定为中西文化的主要桥梁,但客观上仍然是鲜活的现实人,其不免受制于客观选择,对自身命运无绝对支配能力,更无从占据着西潮与东风交互的核心。对于人文学科归国生而言,归国意味着新旧理念的二度适应;而对于众多理工科留美毕业生而言,归国后面临的通常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尤其是在实业界,留学生由于对国内客观实业情况缺乏了解而往往过于乐观和理想化,从事最基本的研究也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即使有研究实业之机会,而苦无研究之材料或辅助设备[7]。这在同样留美学生任鸿隽的文章中解释得尤为清楚:“已经学成的学生为何不肯返国,国内建设,需才恐急,但他们不肯回国的理由大概有两个:一个是经济问题。目前国内物价高涨,生活困难是人人知道的事实。如其在美毕业之后而尚有事情可做,则他们均宁愿在彼邦暂住下来做月给二三百元的小事,而不愿回国就月给七八十万元的高位。略解吃苦的国人,当能不为这些物质的考虑而左右。工作问题,则当作别论。他们既已学成有独立研究的能力,最大的希望自然是回国以后能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可是目前国内的教育或学术研究机关,大都是经费支绌、设备简陋。不但研究进行是不可能的,即使教学必要的设备亦多欠完备。”[8]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巨大的惯性心理定势,留美生过海“喝过洋墨水”回国理应有鲜花簇拥,但随着时代更迭与人们思维的不断变迁,留学生遭遇到更多的却是冷嘲热讽。在世人眼中,留学生常常是与手痒眼热、只懂跳舞、一回乡就趾高气昂的“骡子”划上等号,既不属于中国固有文化又不属于美国文化。同样有着留美身份的顾维钧解释道:“这是由于长期受美国文化影响有很严重的性格扭曲;且容易骄傲、无法忍受反对意见、不愿意从基层做起、忽略工作中的细节并严重缺乏坚定信念;但是对美国那一套怎么学也还是学不像,到头来很容易成为尴尬的四不像。而今日中国的建设却无比需要每一位归国留学生,假如每一位留美生能够无私奉献,对国家始终报以持之以恒的热忱而贡献力量,国家终有振兴的那一天①原文为:V.K.Wellinton Koo,“All Chinese students educated abroad find some common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o face on their return to China, be they men or women, and it is thes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which I propose to discuss with you.Pride mingled with intolerance, disregard of detail, lack of capacity of hard work and want of a steadfast purpose are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complaint made against some of our returned students.China needs us and needs us all; for, at this stage of her development, she cannot afford to lose any one of us for any cause.It behooves us all therefore, to dedicate ourselves to her cause…once we possess the spirit of consecration, will kindle our love for China with ever-increasing vigor.” Address Made at the Platform Meeting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Conference at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R.I.,on September 6,1917”,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November 1917):20-27.”,这正说明了彼时存在于
留学生群体中种种不可取的态度虽然仅是个人选择,但却是对整个国家的复兴毫无益处的。甚至部分学人也对留美生做出了激烈批评,并和同一时期赴美回国帮助自己国家迅速崛起的日本学生做出比较:“当日本学生从国外回到自己祖国时,他们并没有以爱国者的姿态出现,结成友好的官僚政治,或是发通电,也没有给报纸写信,批评外国人或外国;也没有试图像外国人那样过奢侈的生活。相反,他们生活清苦,就是因为这种方式帮助管理了日本,并赢得了外国人的尊重,结果其治外法权最终得以取消。”①原文为: Ku Hung-ming:“When these Japanese students returned from abroad to their own country, they did not pose as patriots, from friendship bureau or send telegrams, nor did they write to the new papers to abuse foreigners or foreign nations, they did not try to live as luxuriously as foreigners, but on the contrary, lived on starvation salaries in order to help to organize and administer their country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and compel foreigners to respect them, with the result that extraterritoriality was finally abolished”,“Return Students and Literacy Revolution—Literacy and Education”,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August 26, 1919): 434.而在我国,正是由于客观体制与长久以来的传统大众复杂心理,使得留学生身份走进一种“里外不讨好”的复杂窘境:留美生在向西方求索时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却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在东归故邦途中期待满满却又无可奈何力不从心,仿佛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9]。其中原因正是由于个体跨文化经验,在吾国与彼国间的双重飘荡造成了陷于“两边都靠不上岸”的现实处境[10]。因此,从心理适应和文化意义而言,对于西方他们是“异邦的旅居者”;对于他们最为熟悉的故国,他们一不小心却又成了“适应不良的归家游子”。
二、历史与历史局中人的双重拉锯
近代留美生身份认同经历了耐人寻味的演变。这种演变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留学生自身生命历程发生历史转折的重要阶段,也体现了历史空间不断更迭的动态性作为整体系统对留学生产生的重大影响。留学生在横向时间轴上展开了中与西的转换,在纵向时间轴上也展开了古与今拉锯下的自我妥协。远渡重洋寻找文明之星火需要寻求到一条中庸路径得以兼容并包异质文化;而回归又需要为国家带来科技、文化甚至政治方面的革新,同时又需要为彼时社会所接受,毕竟新与旧两者融合过程并非仅仅是嫁接与移植般的简单。两种异质文明的融合如何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交互辉映,一切种种也都均非易事,这对于留美生是极大的挑战。究其原因,是因为近代中国留学并非仅仅是教育层面昙花一现的由政府主导对西方亦步亦趋的尝试,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交汇进程也并非只属于传播学的范畴,而是一个必须放在时代的脉络上来处理的问题[11]。由此,对于留美生身份的定位尤其需要特别关注彼时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以期探索出个人身份的设定与现实情况下的偏离或回归过程[12]。
事实上,对于国内而言,其早期西洋文明传播方式不免趋于“半文明”的方式,这种“半文明”体现在“伴着洋枪、洋炮而来的洋货、洋教及各种西洋科技载体,并未能够正向积极而深入稳固地根植于国人之文化内心。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虽有网罗众家兼容并包的能力,但西方势力的渗透采取的却是狂飙铁血的侵蚀方式,而这与散播现代化甘霖采用的渐进切入方式极为不同,工业文明的恩惠需要伴随的却是摧残本国民族主义自尊心的阵痛而来的”[13],这意味着新式文明在中国并没有很牢固的受众根基。另外,在近代中国非常特殊的时空坐标之下,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相结合,使得本土接受者对于外来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的谨慎和抵触,使得留美生作为“传播之利器”的角色大打折扣。然而对于留美生而言,在历史进程及文化变迁整体结构方面,但凡两种异质文明相互“冲撞”,其半文明之文化对于文明之文化不免呈现浮动上升式的主动悦纳状态。这种“悦纳状态”不免形成一股“文明气流的漩涡”,将处于这一场域的历史见证者席卷进去,使得留学生在主观层面对于西洋文明始终抱持着“理想乌托邦”的期冀;在个人工具主义层面,留学生需要于两种异质文明之间做出文化自决,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适应性做出理智判断。而其实对于留学生而言,这种文化自决及判断,从远渡而行负荆西洋寻求文明之曙光那一刻开始,即已时时刻刻深深根植其内心。由此而来,“西洋文明
在不同社会背景中所呈现出的“历史两歧性”作为留学生所需要面对的严酷却又现实的客观矛盾,凡此种种外层结构及个人主体认同的变动性,已非其留学生单纯的文化之力所能解决。这好比一把双刃剑,当留美知识份子头悬此剑时,必定要忍受依赖传统文明却又注定要忍受飘离传统文明的两难拉锯,对故邦既有留恋的热忱却又有排斥的纠结;对西方文明既有出于保守主义层面的怀疑,却又有强烈的渴望。如此的两歧性,投射在留学生主体层面,则体现为其文化认同意识的阶段不成熟以及犹豫不决,也可以说是其知识分子在经历两种异质文明洗礼之后,对自身传统文化信仰程度的极大挑战。于是,自身种种焦虑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这一特殊群体一生中需要解开的主要矛盾。
当然,文化的冲突位居其次,而其中交织的中外政治冲突则不能够忽视。在近代中国内部朝政更迭又同时于外部受“西风”之肆意吹刮,两种冲突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相互激荡、相互交织于近代留学生这一特殊的历史主体之上,其政治的角力不仅反映近代中国对汹涌而来西潮的适应不良,更反映了自身内部日益深化的危机。这表现在留学生群体则为双重拉锯:在他国看到西洋政体及工业文明的弊端,心中充满失落迟疑;在吾国的现实情况下,又表现为对国家政体的难以完全信任并由此呈现而来对于归国的踌躇与犹豫情绪。究其原因,正是因为社会及个人的变化是相连的,一种社会变化的原因,同时又可以为个人变化的结果,留美生所需要做出的任何改革是不能不过问现实的;而历史中的当事人也是不可能不与历史剧幕发生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也正是由于历史局中人与历史始终时时紧密关联的原因。因此,每一个漂洋过海寻求救亡之道的留美生,既是历史当事人又是历史局中人,从负笈西行之初命运就注定与历史每一个剧幕牢牢拴在一页扁舟上游离于两岸间,其身份也如海上扁舟般,摇摇晃晃、起起伏伏,始终难以精确定位。
三、超越与调和的再追问
如前所述,在近代辗转于两岸的留美学生作为中西两潮相互碰撞激起的朵朵浪花,无论是个体历程中对自身身份的转换与适应,还是自身身份回归的诉求,无疑都需要被重构、被选择,在某些方面还与现实有着讨价还价的妥协重组,但也正是这一个个体的重组过程的客观存在,成为了近代国家中与西、古与今文化交流的客观映射。对于他国而言,留美生究竟是心怀对西方之虔诚而亦步亦趋的“跟随者”又或是冷眼旁观的“观察者”?对吾国而言,究竟是“文明的使者”又或是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却又“无可奈何的勇士”?对于那些守承了千余年的旧式传统而言,他们是“破冰者”亦或依然是“卫道者”?对于当代新式文明汹涌袭来之西潮,他们是“推波助澜的弄潮儿”亦或只是历史剧本下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很显然,种种问题联结着两端,一端是对中国自身文化生命力与文化自决力该如何评定、对固有体制该如何始终保有审慎的警醒与恰当调适可能性的严肃叩问;另一端却是关于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究竟该如何定位之问?尤其对于这一部分有特殊经历的留美生而言,更是就其一生需要探索的问题。于他们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则表现为,在这特殊的十字路口上,在彼岸时究竟该如何顺利完成全新行为方式及思维模式对固有文化的有效缓冲?当回归此岸时,究竟如何做到既不能重走旧路,又不能“完全不过问现实”?对于以上种种问题尚且难以寻求到精确答案,更莫若说留学生如何在异国与故土上完成身份的二重转换,也是极富挑战之疑问。
“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近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14]正是由于二十世纪近代中国的历史特质与现实困境、传统卫道与现代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纠缠缠绕;西潮与东潮两者异质特性在广阔地缘中冲突撞击,加之彼时潮政风云变幻的空间背景,在大部分时间对于多数人而言,“认同”犹如过渡之扁舟,恰是难以捉摸并沉淀下来的东西,特别是对于漂浮于彼岸与此岸的文明方舟——留学生而言,多数人不可避免地挣扎于两种文化的双重夹缝与紧张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努力完成身份的转换及个人使命的回归,从而承受主观或心理层面的压力。更为复杂的是,留学生群体的认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情感,在一定的历史偶然和必然事件下会产生一定的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与时代相呼应,另一方面在整个历史变迁进程中
呈现不同的线性特征投射于留学生单个主体之上,演化为对自身前途命运抉择的多样性选择,加之每一个历史行为主体对这种选择并不抱持非左即右的确定意念,自然呈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理矛盾及“少小离家老大难回”的现实。正是由于留学生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异文化环境的冲击下,产生着比国内青年更为剧烈的动荡和危机,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留学之于留学生来说,无异于是一场自我认识的冒险[15]。这种“自我认识的冒险”不仅牵涉到身份认同,更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甚至是精神认同。凡种种体用公式力图确定其实质,都是非常辛苦的尝试,也是对不确定性的寻求。而采用超越的态度对留美学生身份二重转换进行更为弹性的分析或许是值得再探索的。
[1]叶隽.“教育冲突”与“文化抗争”——读《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3): 165-173.
[2]欧阳洲.留美存稿[J].文化与教育,1935(72):99.
[3]王德箴.留美杂吟[J].妇女月刊,1941(1): 68.
[4]百一.留美杂碎[J].粤风,1936(2): 8.
[5]江康黎.留美杂记[J].国际周报,1943(5):16.
[6]胡适.非留学篇[J].留美学生年报,1914(3):4-29.
[7]谢长法.任鸿隽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J].现代大学教育,2009(4):44-48.
[8]任鸿隽.留美学界的几个问题[J].观察,1947(2):45-48.
[9]余英时.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M].台北:三民书局,1992:49.
[10]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191-241.
[11]江勇振.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留美学生:一个在研究课题上初步的省思[M].纽约:纽约天外出版社,1999:126.
[12]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
[13]许继霖.走向反现代化的乌托邦——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M].//刘青峰.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485.
[14]梁启超.过渡时代论[A].清议报,1901-06-2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27-30.
[15][美]Jerome Chen.China and the West: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158.
(责任编辑 李震声)
Travelers or Strangers: The Dual-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Identitie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ZHANG Mu-chu
The overseas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 of China has posed a great influence o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y due to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However the identities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were also in a dual dimensional dilemma.Not only were travelers to America but also were strangers to their home country.Therefore, to analyze the process in broader perspectiv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reasons of the history process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path are necessary.This probably provides a useful inspiration.
overseas education;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G649
A
1672-0717(2015)01-0088-05
2014-10-09
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异质文明下的游移:近代留美与留日群体文化认同之历史考察(1903-1927)”(20140103B);加拿大政府资助项目“The comparative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means for Canada in terms of knowledge diplomacy”。
张睦楚(1984-),女,云南昆明人,北京师范大学与加拿大约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