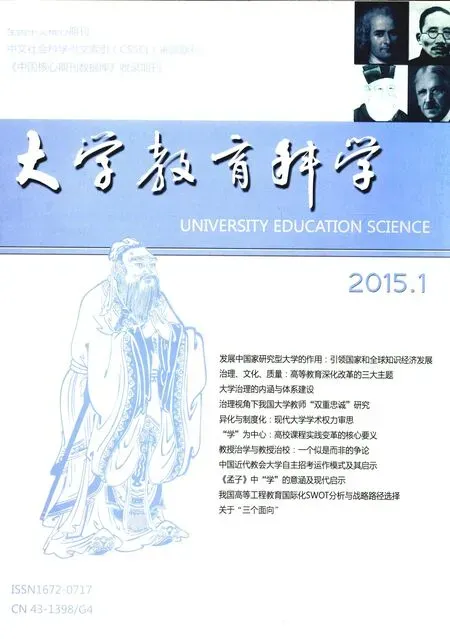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的作用:引领国家和全球知识经济发展
□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著,胡颖 译,别敦荣 校
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的作用:引领国家和全球知识经济发展
□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著,胡颖 译,别敦荣 校
研究型大学是各国学术系统的核心部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可以推动各国知识经济的成功。国际顶尖期刊的编辑、作者和评阅人都来自研究型大学,同时,研究型大学能够获取全球知识信息,汇聚各类学者团体,资助教师参与国际专业学术机构和国际会议,并位于互联网革命的中心,因此,开展国际学术知识交流和参与到国际学术网络中是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研究型大学作为“知识的仓库”和“批判中心”,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面临着语言的困境,并且亟需改善学术职业的条件。从卓越的研究型大学的典型特征来分析,各国应该思考如何改善研究型大学的基础设施和智力氛围以使其迈向成功。
研究型大学;发展中国家;知识交流
研究型大学处于全球知识经济的中心,同时也处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顶端。研究型大学常常出现在国际排名中,因此,它们也就成为最显而易见的学术型大学(Hazelkorn 2011)。研究型大学在学术系统中承担着一系列复杂的任务(Altbach 2009),包括开展研究、训练学生参与研究等,可见,研究型大学侧重研究生教育。研究型大学不是封闭的“象牙塔”,与广阔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校外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研究型大学开展研究。研究型大学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多层面的机构,具有多种社会功能(Altbach 2007a)。
各国的研究型大学有许多共同之处——起源于一个特定的传统并具备相似的功能。摩诃曼、玛和贝克(2008)发现了一个正在兴起的、极具共同点的研究型大学的全球模式,但是,不同国家之间还是有些显著差异(Altbach 2011)。这篇文章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在促进学术系统分类和有效运作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事实上,正是研究型大学使得各国有机会参与到全球知识社会中,并且能够在21世纪复杂的知识经济中与他国一较高低。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型大学被定义为从事各学科和领域知识创新、传播工作的学术机构,它以拥有足以支撑最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实验室、图书馆和其他基础设施为特征。虽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大而多层次的,但是,有些研究型大学可能是比较小的,设立的学科数量较少。研究型大学培养各学历层次的学生,这说明研究型大学不只侧重研究。事实上,研究型大学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全职学者,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
展开下面这些讨论,是因为我坚信,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必须遍及世界各地,世界各地都需要在知识网络中发挥作用(Altbach 1987)。世界各地可能既包括了“中心”国家,也包括了“边缘”国家。“中心”国家主要指工业化国家,它们能引领未来;但为了使全球范围内更多国家获得科研能力,全球知识网络必须为“边缘”国家留有必要的空间。尽管每个国家都拥有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能够建立起有能力开展研究、且有能力参与到全球知识系统中的大学。小国可以形成区域性的学术联盟,选择几门学科领域进行合作,聚合力量来促进各国在
全球科学中的参与。
为了能够掌握领先的科学技术和有选择性地参与到全球科学中,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拥有与全球学术系统相连的大学。小国或贫穷国家的大学虽然无法与工业化国家的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相抗衡,但是,大多数国家至少能够资助一所较好的大学参与到国际科学和学术的讨论中,并且能够在关系国家发展的一个或多个领域中开展研究。
研究型大学激起了全球不断高涨的热情。国际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是:研究型大学是开启21世纪知识经济大门的钥匙。研究型大学不仅培养全球领袖人物,而且通过提供一流的科学交流机会,打开一扇窗,使各国都有机会接触到科学信息。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与全球各地的“同伴”保持着联系,并积极参与到全球科学和学术中。美国和英国越来越担忧如何维持研究型大学的现有标准(Rhoten and Calhoun2011);德国担忧其顶尖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重新分配资源,将资源集中到一些关键的大学;日本政府启动了竞争性的资助项目来培育“一流研究中心”;中国在重点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印度也终于开始重视其主要教育机构的质量问题。类似上述旨在提高研究型大学现有水平的项目也在韩国、智利、中国台湾和其他一些地区得到了实施。非洲的数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为了达到研究型大学的水平,在外部赞助者的支持下,努力改进其质量水平;但是,总体而言,非洲大学的发展进程仍落后于其他大陆的学术发展水平。
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的不断涌现,改变了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分析者,甚至一些国际援助机构和世界银行的原有想法——只有基础教育才值得支持,现在他们都意识到了研究型大学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那些意图在全球知识经济中谋求一席之地的大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问题已经被提上政府的政策议程。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还没有跻身到世界大学排名的顶尖位置,但是,它们对于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和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虽然相对于北美和欧洲的顶尖大学,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还处于边缘位置,但是,对于它们所属的国家和地区,却处于中心位置(Altbach 2009)。毋庸置疑,全球重要发展地区中的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轨迹是上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持续的重视和资金投入,终有一天,它们将步入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世界各地的研究型大学都是活跃的“社团”的成员,所有成员都秉持着共同的价值观、研究重点和使命。
研究型大学与学术系统
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只是整个学术系统中很小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发达国家,情况也是如此。比如,美国拥有大约220所研究型大学,但是,美国的学术系统却是由4 0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的;英国拥有100所大学和300所高等教育机构,而“罗素研究型大学集团”仅仅包括了其中的24所高校。一些更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仅拥有一所研究型大学,也可能一所都没有。一些大国,例如中国,正在通过实施“985工程”和“211工程”,致力于建设100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而在全国范围内,中国有3 000多所学术机构。
研究型大学虽然小而专业化,但对于任何国家的学术系统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在实际运作的学术系统,但是,有些国家由于缺乏有序的管理,研究型大学很容易定位不清,并且缺乏足够的支持。如果研究型大学想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分类清晰的学术系统。这种分类清晰的学术系统的最好例证可能就是著名的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加利福尼亚总体框架建立了一个三级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三级系统依据不同的功能相互区别,又通过总系统的协调相互关联。这个系统已经成功运作了超过半个世纪。位于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顶端的是加州大学的10所分校,在伯克利分校引领下,这些大学录取全州最优的8所中学的学生,并且承担开展研究的职责。接下来的一层包括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23所分校,共录取约43.3万学生,这一层次的大学仅提供学士和硕士学位,不提供博士学位;同时,与加州大学系统中的高校教师相比,这一层次大学的教师并不被期待开展过多的研究。社区学院系统包括112所分校,拥有300万学生——这是全美最大的社区学院系统;这些学院都将教学和服务视为其核心职能,开展科
研的能力却十分有限。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三级,在资助类型、大学使命和管理方式上各不相同,并且州的法规也规定了公立学院和公立大学的不同使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框架使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各具特色。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又以其清晰的定位、有效的创新,服务了加州的发展。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总体框架坚持资源配置以效率为核心,并且在其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如伯克利大学中规定了这样一个使命:追求卓越(Douglass 2010)。
加州高等教育总体框架的设计师——克拉克·克尔,为系统中的研究型大学构想了一些关键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使得加州伯克利分校成为全球最好的大学之一。第一,教授掌控大学的内部管理权。只要是关系学术政策和学术发展方向的重大决定,即使是由管理者发起的,也需要听取教授们的意见。这种“共同治理”的观念是大学理念的核心。加州伯克利分校在实践中,无论是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学生的录取还是其他事务,都严格实行精英式管理。第二,该校中研究和教学是紧密结合的,但开展研究更具优势。学术自由是该校学术团体的核心价值。第三,从建校起,该校就与社会沟通联系,特别是一直与加州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该校后来的发展中,服务社会职能也一直被放在重要位置(Kerr 2001)。
与加州模式相类似,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系统也需要清晰地区分不同类型高校的使命,并依据使命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引导其发展。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如果能够实现清晰的分类,不同类型的高校就能依据自身情况采用不同的资助形式、教学制度、管理制度等。同时,在规划学术系统时,在一定程度上将迅速扩张的私立高等教育纳入其中,也是非常必要的。
上述愿景是美好的,但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学术系统很少能做到分类清晰。这仍然是一个关键的挑战。没有一个有序的学术系统,各国学术系统不能依据国家的需求去变革和定位,研究型大学就不可能繁荣地发展。各国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获得清晰的定位和足够的支持。同时,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应该是有限的,这样才能使其获得充足的资金资助和其他资源。如果研究型大学的数量能够得到控制,那么,优秀的教师资源也不会因为散布在各类高校而变得匮乏。
交流与网络
开展国际学术知识交流和参与到国际学术网络中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职责。研究型大学居于国家学术系统的顶层,应当在本国学术系统中发挥引领方向的核心作用。同时研究型大学还是一个国家学术系统与全球知识网络交流的媒介,因此,建立沟通交流网络也是研究型大学的一个核心任务。互联网的建立使得人人都能进行国际交流,人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获取信息——这样来看,教育实现了“民主化”。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交流其实是“集中化”的。
知识是有等级的。我们所说的“科学”和“学术”就是那些获得了“合理性”的科学和学术知识。这些知识被发表在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并且被各个学科的“守门人”控制着。因此,不难理解的是,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的学者们控制着学科的核心知识网络。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全球知识网络的一部分,并且有能力参与到全球知识网络中。全球的研究型大学应该通过共同参与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分享科学和学术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帮助全世界的大学教师建立起非正式的联系。
与研究型大学的学者相比,一些普通大学的学者虽然也能够共享全球科学知识,但这些学者在参与直接的“学术对话”方面存在极大的劣势。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与全球范围的同事有更多的直接联系,能够更好地参与到非正式的学术和科学网络中,更容易开展直接的学术交流。研究型大学是国际知识通向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入口,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传播到更广泛的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媒介。
当前人们讨论得较多的是科学的“民主化”和全球“知识共享”新时代的来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当前的情形更适合被贴上这样一个标签——科学的“无序化”。来源渠道多元的可用信息不断膨胀,但却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评估这些信息的价值和有效性。可以说,知识的“无序”使现有的知识网络变得更具影响力,因此,十分有必要在“混乱和无序”的信息中辨别出什么样的知识才是有用的。
期刊
虽然互联网入口的不断开放使得互联网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传统的期刊对于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仍然保持着核心作用。事实上,正是伴随着科学“民主化”的趋势,传统期刊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期刊系统提供了一种相对更可靠的方式来确保知识的质量。传统的期刊实现质量监控的有效方式是外部评审制度。投递过来的所有论文必须接受学术编辑的审阅,并且经过外部专家的“盲审”。尽管每个学科投递的论文都非常多,但是,大部分顶尖期刊都只采用其中的一小部分论文——有些期刊仅仅挑选2%的论文。大多数的学科、跨学科、专业领域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非正式的期刊等级。那些决定期刊影响因子和使用率的机构——例如,汤姆森路透(Thompson Reuters)的科学引文检索(SCI)、社会科学引文检索(SSCI)、人文引文检索(AHCI)——正不断成为众多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和作者的重要掌控者。
期刊影响因子和使用率的“决定者”都来自于世界学术中心,这些机构不会积极关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版物。另外,期刊出版人、编辑、编辑董事会、评阅人都主要来自于世界学术中心,他们也并不太关心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研究或者学术议题。许多顶尖期刊都是由跨国出版集团发行的,例如,爱思维尔(Elsevier)和斯普林格(Springer),都征收非常高的订阅费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费用超出了发展中国家大学的购买能力。尽管有一些特殊的折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还是很难支付购买信息端口的费用。近年来,随着在线“开放存取”期刊的广泛流行,全球期刊系统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在线期刊中,有些期刊的质量标准是非常高的,但是,有些期刊却不过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不可靠的“商业产品”。
期刊编辑、大多数的作者和评阅人都来自于研究型大学,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强化了研究型大学的作用。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是开展知识交流的中心机构。
图书馆
在传统观念中,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仅管理书籍和期刊,而现在,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还承担管理数据库和电子资源的职责。在发展中国家中,很少有图书馆能够追随当前的知识信息潮流。尽管常常预算不足,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还能够获得全球知识信息。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和信息科技职员提供的服务,也是在其他图书馆中不可能享受到的。这意味着研究型大学负有特殊的使命,即确保相关的信息能够为本国更广泛的学术群体所享有。在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的重大作用常常被人们所遗忘——确切地说,现今图书馆不仅仅是书籍和期刊的“仓库”,而且还是大学和学术群体的主要信息技术的“提供者”。
“无形的团体”
非正式的学者和科学家团体对于科学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Crane 1972)。这些无形的团体存在于每一个学科领域,并且常常是跨学科创新工作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时代的学者团体变得虚拟化——他们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研究型大学是各类学者团体汇聚的中心。在国际层面,学者们倾向于把研究型大学的同行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在地区或国家内部层面,研究型大学就是这些非正式的科学家和学者团体聚集的中心。
会议和专业机构
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学术会议都是实现科学交流的桥梁。互联网上虚拟交流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学术会议的减少——事实上,举行“面对面”的学术会议还是十分必要的。专业学术机构赞助的学术会议,或者其他类型的学术和科学会议,都为学者们沟通思想、分享研究成果、建立学术群体创造了机会,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往往参与其中。研究型大学的学者在专业学术机构中十分活跃,也往往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有足够的资金去资助教师参与这样的会议。一些学术机构专门从事特定领域的研究,也为那些在特定领域表现活跃的科学家和学者提供了展示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上述这些方面居于劣势地位。一方面,学术和科学机构被发达国家顶尖大学的学者们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很难获得话语权;另一方面,这些专业机构的学术会议常常选择在欧洲或北美国家举行,受距离和资金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很难参会。
互联网
互联网是过去数十年中通讯革命的核心要素,
互联网在未来也将持续影响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研究型大学位于互联网革命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可以获取到高速的网络,便捷地进行交流和获取资料。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其它大学,直到近几年,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拥有完全可靠的网络连接。研究型大学既拥有“硬件”,例如仪器设备和高速网络;还拥有“软件”,即具有信息技术能力的个人和在开展科研、交流方面都十分活跃的学术团体。
开展学术交流和参与学术知识网络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但却很少被人们提及。上述这些讨论对全球的研究型大学履行这一使命意义重大。这一使命是研究型大学的独特贡献,是其它任何机构都无法承担的。
知识的仓库
研究型大学是各种知识的储备中心。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职员常常是本国各个领域中最博学多闻的学者和研究者。教授们不仅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且通过咨询、非正式建议、甚至直接的公共服务来向社会提供信息。因此,在国家危机时期,研究型大学的学者被任命为政府顾问、部长甚至政府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教授们的专业知识有利于经济、环境、农业等社会领域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领域中的专业知识十分有限,所以教授们的社会服务就意义非凡。研究型大学的学者通过为广阔的社会领域提供专业知识服务,从而与政府、工业、公民社会建立起有益联系。研究型大学是提供有用知识和经验的主要机构,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知识也有助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研究型大学是历史资料、文化资料、文物的主要储存地之一。研究型大学有时赞助博物馆和其它类型的文化机构,如果某些国家政府在博物馆管理领域能力有限,研究型大学也会管理博物馆。博物馆涉及多个不同领域,包括艺术、手工艺品、科学、医学、文化等领域。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常常藏有珍贵的历史手稿和手工艺品,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有时,国立大学还掌管了国家主要的天文观测台。
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一般藏有最丰富的书籍和研究材料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被设计成为国家图书馆,汇集了国家珍贵的研究资料,因此,并不只有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使用这些资源,其他人为了开展研究也可以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现今,研究型大学也储备数字资源,并且实现这些珍贵的历史和文物的数字化,也是研究型大学对社会担负的责任。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拥有规模最大、装备精良的科学实验室,从而为国家的科学团体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其他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常常将大学的实验室视为共同的科研实验室。
研究型大学作为知识“仓库”的角色和职责常常在有关高等教育的讨论中被忽略。研究型大学在进行财政预算时,也往往不会划拨一定的资金来履行这一职责。
研究型大学——“批判中心”
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群体,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常常充当社会和文化的“批评者”。尽管时常不被政府领导人欣赏,知识分子还是敢于针砭时弊。教师常常在报刊上撰写专栏,现身电视节目;越来越多的教师撰写微博或者通过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大学学者在发表公开评论方面极具优势。大学学者都是某领域的专家,发言具有权威性,并且他们也能够在报刊和电视上清晰地、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们在社会中代表着尊敬和威望,公众通常非常重视学者们的观点。大学通常保护学者们的学术自由,即使是在一些言论并不完全自由的国家,学者们也比普通群众享有更大的言论、写作自由。学者们拥有渊博的知识,享有极高的社会威望,因此,学者们常常可以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
学生大多数时候也通过政治性组织和政治激进活动以多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批评意见。在发展中国家,激进活动的势头依然很强烈。学生抗议者就许多社会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反对政府、批评某个政策、要求高等教育改革,等等(Altbach 1989)。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学生团体充当了推翻政府的工具,有些国家的学生团体则重视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有时学生活动使大学变得极具政治性,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状态。学生的激进活动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大学完全关闭,有时甚至会关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学者们和大学都会创办一些期刊和出版物来促进知识和政治的对话。为了追随当前的科技发展,学者们和大学还创办了网站,并通过推特(twitter)和博客(blog)开展交流。大学教师有更多空闲时间,也习惯于为公众写作,因此,研究型大学在上述这些方面特别活跃。
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团体有动机、知识、责任参与到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对话中,他们还可以分享工业技术和专门技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的学者是极少数拥有这些技能的人。因此,相比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中极少有其他社会团体能够参与社会批判。
科学和学术知识的全球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而言,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Altbach 2004; Knight 2008)。研究型大学位于全球知识交流和知识网络的中心。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向下”将新思想和新知识传播到高等教育系统中,进而传遍整个国家。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向上”允许高校教师参与国际科学和学术活动。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能受益于全球化的知识。研究型大学资源丰富,因此,教师更容易和有效地参与国际交流。许多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可能是唯一能够与国际平台相联系的机构,因此,研究型大学为知识交流提供了互动的通道。
同时,对于许多大学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威胁”。教授和学生在全球学术市场自由流动意味着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可能会“流失”。在制定教授的晋升标准和制定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时,如果都以发表国际核心期刊论文为评价指标,可能会使“边缘”国家的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化潮流更有利于顶尖大学发展,而非一般大学。这样的情况并不利于真正实现科学和学术知识的“民主化”。全球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全球化潮流席卷了21世纪的各个学科领域。互联网可以使教授们“新鲜出炉”的科研成果立马传播到世界各地。科学期刊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世界各地的学者将论文发表在同一出版物上。科学方法论和学术标准前所未有地为全世界所通用和共享。曾经尖端和昂贵的科学仪器设备,现在各国也都可以购买到。但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备感压力。如果研究型大学想要参与到全球科学研究中,就必须斥资建立最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同时,随着研究者和大学都想要抢先获得最新的研究成果、专利、发现、发明许可证等,研究工作变得越来越富有竞争力。简言之,科学研究已经变成了一个“高风险”和“高竞争”的国际行为。尽管开展高端科学研究可以使大学更具竞争优势,但的确也耗费巨大。
建立先进的实验室和基础设施,已经使研究型大学面临巨大的经费问题。同时,研究型大学还面临着科学和学术的定义和方法论问题。科学全球化意味着所有的研究者都必须遵循美国或西方国家研究者所使用的学术标准。大型科研项目和著名科学期刊所偏好使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治世界科学。另外,世界领先的科学家和机构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也和“边缘”国家大学的研究兴趣不相契合。总而言之,“边缘”国家研究性大学参与到世界科学中意味着必须遵守现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主题。
参与全球科学知识竞赛,耗资巨大,这使那些缺乏科研传统和缺乏必要的科研设施和设备的学术机构陷入了困境。以前,大学提供的科研设施和设备足以支撑研究者开展当地研究或者地区研究,但是,现今如果一所大学想要参与到“国际联盟”中,原有的科研设施就不再能够满足需求了。那些想要成为研究型导向的大学必须参与到全球科学知识网络中,并且与全球范围内的学术机构和科学家竞赛。对于财力不足且在建立颇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机构方面毫无经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耗资巨大就变成了跻入研究型大学“联盟”的一个关键问题。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型工业化国家中的小型学术机构,都在试图转型进入研究型大学的行列,同样面临着资金的挑战。踏入全球科学知识大厦的大门,需要支付昂贵的门票,而持续的参与更将耗费巨大。
参与全球知识竞赛时产生的这种“利弊共存”的情况,总体上是和全球化本身相类似的。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便捷的交流、高素质人才的全球流动等,全球化使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科学、学术、思想的全球市场中。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所有的参与者不得不承受不平等的全球知识系统所带
来的压力。全球知识系统由发达国家所掌控,并且向所有的学术机构输出他们的学术标准和价值观(Altbach 1987)。
国际化与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通常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型大学通过积极开展科学研究、鼓励教师参与国际活动,成为国家学术系统与全球知识团体交流的纽带。研究型大学视自身为全球学术群体的一部分,为了能够支撑国际活动,不断完善校园基础设施;与其他的学术机构相比,研究型大学拥有能够开展国际活动的管理人员;也能够为海外学生和海外教师提供较好的校园服务(Altbach and Knight 2007)。
研究型大学招募的海外教师能够帮助其建立起海外联系。因此,研究型大学的研究项目可能包含更多的国际元素,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团队都是如此。与普通大学的学者相比,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更有可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与国外研究者开展合作、参加国际会议等,这意味着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与国际学术群体的联系更为紧密,并且拥有更多的参与国际活动的机会。
研究型大学是卓越的海外大学的理想合作伙伴。发达国家的顶尖高校特别倾向于与海外的顶尖高校建立联系,而研究型大学似乎就是各国声望最高的大学。
研究型大学通常开办了许多的国际研究、区域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常常会开设一些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化的课程。有些研究型大学设立了许多研究中心和研究机构,这些中心和机构侧重研究世界不同地区的问题。此外,研究型大学还能够为海外学生提供一些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学习项目——这对于国外合作高校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与国外高校合作进行“联合培养”、建立海外分校、合作开展其他类型的学术项目,等等。研究型大学能够挑选到最好的海外合作伙伴,并且达成高质量的合作协议。
为了建立更多的国际合作项目,与国外高校建立联系,从而塑造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研究型大学纷纷推出国际化战略方案。尽管这样的国际化方案以往一般都是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实施的,但是,当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也开始实施了。例如,中国的顶尖大学已经有所行动,而这种趋势也会慢慢扩大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型大学。
与“南方国家”的大学互通往来是“北方国家”研究型大学肩负的特殊使命。“南北国家”的研究型大学组成研究型大学联盟可以使所有的大学受益。“北方国家”的学术机构能够为“南方国家”的学术机构提供多种帮助,包括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学术管理、提供导师资源等;“南方国家”的大学也可以邀请“北方国家”的大学合作开展科研和教学。合作开展研究项目、培训项目等其它活动都是互惠互利的。当然,开展合作一定要坚持“平等”和“责任共享”的原则。伴随着全球研究型大学联盟的日益国际化,南北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都将从中受益。
语言的困境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而言,“语言”一直是一个复杂的议题(Altbach 2007b)。无一例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都必须使用现今的全球科学用语——英语。如果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够高,大学就不能够在全球知识网络中获得足够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学都要求入学新生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发达国家的大学,即使那些英语并不是本土教学语言的国家的大学,都希望用英语建立起国际学术关系。伴随着英文授课课程甚至全英文授课的学位项目的不断涌现,当大学设立“联合培养”学位或者在海外建立分校时,人们都希望这些项目和分校能够采用英语授课。
当前,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研究型大学中,全部或者大部分课程都采用英文授课,同时一些大学还将英语视为开展学术交流的有效媒介。南亚的大学保留了英国殖民传统,因此,大部分的高校都采用英文授课。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所有的大学都采用欧洲语言进行教学——其中,大部分采用英语教学,小部分大学采用法语、葡萄牙语、荷兰语进行教学。随着非洲南部的大学放弃使用荷兰语进行教学,英语获得了发展机会;卢旺达的大学甚至都已经放弃使用法语,而采用英语进行教学。最有趣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的大学,曾经一度放弃使用英语,采用马来语进行教学,而现在一些大学又逐渐
恢复使用英语。
虽然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英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例外情况。例如,非洲的法语区和葡萄牙语区,仍然保持着法语和葡萄牙语的权威性。尽管英语变得越来越流行,拉美国家的教学语言仍然是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
总体而言,在许多的课程和项目中,英语已经被广泛地用作教学语言。例如,中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为各学科的学生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英语授课课程。
高校鼓励并且时常要求教授们用英语发表研究成果,而且最好能够发表在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期刊上。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教授面临着语言的困境;另一方面,研究方法论和“同行评审”的评审专家都来自于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并不关注发展中国家研究者关注的议题。
本土语言和地域性的研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英语使用率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用当地语言进行科学、学术、文化对话的机会减少,这也使得本土语言和地域性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事实上,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语言也是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Lillis and Curry 2010)。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亟需在“跟随国际潮流”和“保持地域特色”之间做出权衡。
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选择哪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面临十分复杂的情况。例如,在沙特阿拉伯,自然科学倾向于采用英语教学,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倾向于采用阿拉伯语进行教学。在有些国家中,研究型大学采用英语教学,而其他大学则采用当地语言进行教学。虽然几乎没有大学会选择抛弃英语而采用当地语言进行教学,但各国高校在对教学语言进行抉择时,还是会充分地权衡利弊。
学术职业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研究型大学如果能够吸引到优秀的教师,就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当前,各国学术职业的状况既不利于教授个人的发展,也不利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Altbach 2003)。研究型大学要求教师拥有最高学历——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教师都没有博士学位,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要求就变得十分必要。研究型大学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可能要高一些。例如,中国几乎所有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都获得了博士学位(Ma and Wen 2013)。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是只有少部分教师获得了博士学位。
献身大学教学、科研事业的教授、学者、科学家推动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如果没有众多全职的大学教师,就无法形成一个忠诚的、高效的学术团体。研究型大学需要保持高度的学术自治和自主的教师管理模式,因此,全职教师不仅需要履行大学的核心使命,还需要参与大学的治理和管理。除巴西之外,大部分的拉美国家都因为缺乏数量足够的全职教师而没能建立起一定数量的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聘用全职教师后,必须提供足够的薪水使其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Altbach, et al.2012)。一般的大学教授并不追求非常高的薪资,但是,教授们必须成为所在国家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全职教授增加收入来源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在其他机构担任顾问或者兼职、承担额外的教学任务等。上述这些活动有损教授群体发挥其核心职能,也使教授群体很难维持其学术生产力。
在一些特定学科,教授们为工业提供咨询服务、开展应用研究,与外部机构建立联系等有利于教授推进科研工作。然而,许多国家的教授从事外部工作,过于依赖额外收入,实际上是不利于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当前,在全球范围内,一方面,棘手的学术工资问题被搁置一边,另一方面,校外机构给专业人员提供的薪资水平却急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吸引最好的和前途无量的学术人员,大学提供的薪资水平必须具有竞争力。
为了使学者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大学应该给予教师有限的教学任务。美国研究型大学一般规定教师一学期开设两门课程或者一个学年开设四门课程。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教师的教学任务甚至更少。欧洲大学也采取类似的做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却需要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因此,很少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美国最活跃、研究型的教授主要面向研究生开展教学,有利于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和提高学术生产力。在欧洲大学中,博士学位大部分都是学术型的,因此,教授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培养和指导博士生(Nerad and Heggelund 2008)。
学术职业有其自身的“学术阶梯”,有才能的教授可以基于工作表现、工作成果获得职业的晋升;学术职业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薪资结构,依据教师的能力来确定个人的薪资。但遗憾的是,许多国家的全职教师岗位就是“铁饭碗”,高校教师职位的晋升并不依据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表现,而是论资排辈;高校教师的薪资也并不取决于教师的工作表现,而是取决于教师的学术辈分、职位高低,有时,还取决于教师所在的学科。在有些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国家(Enders 2001; Altbach,et al.2012),视大学教师为国家公务员。在这些国家中,上述不合理的情况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公务员身份使高校教师获得了稳定的工作保障,但也导致高校不再将教师的学术生产力作为其晋升的考核标准。
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为高校教师提供合理的薪资,既要能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又要使教师获得职位稳定感而忠于岗位。美国高校的“终身教授”制度,尽管在美国备受批评,但可能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好方式(Chait 2002)。“终身教授”制度给教师们提供了“试用期”,在“试用期”内教师需要接受一系列严格的评估。教师如果通过了六年的试用期,就能够通向终身教职,至于进一步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仍取决于其工作表现,并且需要接受一系列严格的评估。大多数的美国学院和大学采用这种模式,其中研究型大学对教师的评估最为严格。现今,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建立“终身教职后评估”制度,这意味着教师即使获得了终身教职,高校还需要继续评估其学术成果。特别是对于薪资的提升,教师的工作表现和学术辈分同样重要。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职业也面临着挑战,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兼职教师的不断增加和非“终身教职”系列全职教师的涌现。尽管研究型大学“终身教职”系列的教师比例比普通高校要高(Schuster and Finkelstein 2006),但总体而言,在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50%的新增教师职位都属于兼职教师或非“终身教职”系列教师。
学术职业对于大学的成功至关重要。研究型大学需要聘用优秀的教授——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决心从事科研和学术工作,在学术好奇心的驱使下从事研究。研究型大学也必须为教师提供全职的岗位和足够的薪金。教师的职位晋升应该考量教师的个人能力,同时,高校给教师提供的薪资需要既能够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又能够使教师获得职位稳定感。研究型大学应该给予教师充分的时间从事创新性研究,还应该提供一定的科研设备和基础设施来支持教师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正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因此,更加需要改善学术职业的条件。
当前环境
借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话,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几乎每个国家都认识到了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都认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对于经济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建立研究型大学和巩固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是一项复杂、耗资巨大的工程,许多国家对此并没有深刻的认识(Salmi 2009)。
21世纪早期是许多国家建立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时期,是各国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壮大的时期,是各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期。
下面笔者试图描绘卓越的研究型大学的一些典型特征:
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分类清晰的学术系统,卓越的研究型大学就处在学术系统的顶端,并且获得外部支持来履行其职能。
除了美国、日本的部分研究型大学和拉丁美洲的少部分罗马天主教大学,大部分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尽管一些国家,如土耳其、印度和拉丁美洲的一些私立大学也开始侧重开展科研,但私立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很难拥有足够的资源建成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往往是一个国家中最成功的机构,原因在于研究型大学不仅不与校外科研机构竞争,而且还与之建立了紧密联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俄罗斯、中国的“科学院”系统、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及其它国家的校外科研机构并没有与大学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一些国家正尽力整合校外科研机构和顶尖大学的力量,甚至会将两者合并。毋庸置疑,这样的做法将极大地增强大学的科研实力。
研究型大学耗资巨大。与普通大学相比,研究型大学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提供开展尖端科研和教学所需的基础设施。因此,研究型大学的“生均成本”不可避免地要高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平均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为教师提供足够的薪金、建立装备精良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为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等。
研究型大学必须做好周密的、长期的经济预算,长时间的资金不足和剧烈的财政动荡都不可能带来研究型大学的成功。建立和维持一所研究型大学需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研究型大学有能力增加收入来源。研究型大学的学位社会声誉好、学生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并有机会接触到最优秀的教授,因此,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往往愿意支付更高的学费;研究型大学拥有一些知识产权、发明、创造等,这些在市场上也价值不菲。另外,一些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凭借其良好的社会声誉,也能够获得社会捐赠的善款。
研究型大学要履行其职能,需要相配套的物质设施。这就意味着研究型大学需要建立起昂贵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研究型大学也需要配备尖端的信息技术,所有这些都耗资巨大。完善研究型大学的基础设施是一项既复杂又昂贵的工程。
研究型大学需要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来设计和发展自身的办学特色。“自治”和“责任”之间的平衡,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而言,会更加棘手。
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享有学术自由,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学术自由更为重要。
建设和完善一所研究型大学所需的条件是十分复杂的,既包括物质条件和人文条件,也包括涉及学术事业的诸多理念和选择倾向。
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雄踞学术和知识系统的顶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可以推动各国知识经济的成功。发展中国家需要把研究型大学推向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因此,当前各国应该优先考虑的议题是:充分理解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并思考如何改善研究型大学的基础设施和智力氛围以使其迈向成功。
[1]Altbach, Philip G.1987.The knowledge contex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Altbach, Philip G., ed.1989.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handbook.New York: Greenwood.
[3]Altbach, Philip G., ed.2003.The decline of the guru: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developing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New York: Palgrave.
[4]Altbach, Philip G.2004.Globaliz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Myths and realities in an unequal world.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10: 325.
[5]Altbach, Philip G.2007a.Empires of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In World class worldwide:Transform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ed.Philip G.Altbach and Jorge Balán, 1 28.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6]Altbach, Philip G.2007b.The imperial tongue: English as the dominating academic language.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September 8:3608 11.
[7]Altbach, Philip G.2009.Peripheries and centers: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10: 15 27.
[8]Altbach, Philip G.2011.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In 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 ed.Philip G.Altbach and Jamil Salmi, 11 30.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9]Altbach, Philip G., and Jane Knight.2007.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Motivations and realities.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1, nos.3 4:274 90.
[10]Altbach, Philip G., Liz Reisberg, Maria Yudkevich, Gregory Androushchak, and Iván F.Pacheco, eds.2012.Paying the professoriate: A global comparison.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1]Chait, R.P., ed.2002.The questions of tenur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2]Crane, Diana.1972.Invisible colleges: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communitie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Douglass, John Aubrey.2010.From chaos to order and back? A revisionist reflection on the California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50 and thoughts about its future.Berkeley,CA: 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4]Enders, J, ed.2001.Academic staff in Europe: Changing contexts and conditions.Westport, CT:Greenwood.
[15]Hazelkorn, Ellen.2011.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attle for worldclass excellence.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6]Kerr, C.2001.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Knight, Jane.2008.Higher education in turmoil: The changing worl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Rotterdam: Sense.
[18]Lillis, Theresa, and Mary Jane Curry.2010.Academic writing in a global context: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publishing in English.New York: Routledge.
[19]Ma, Wanhua, and Wen Jianbo.2013.The Chinese academic profession: New realities.In The global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The BRICs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Philip G.Altbach, Gregory Androushchak, Yaroslav Kuzminov, Liz Reisberg and Maria Yudkevich.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Mohrman, Kathryn, Wanhua Ma, and David Baker.2008.The research university in transition:The emerging global model.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1: 5 27.
[21]Nerad, Maresi, and Mimi Heggelund.2008.Towards a global PhD? Forces and forms in doctoral education worldwide.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2]Rhoten, Diana, and Craig Calhoun.2011.Knowledge matters: The public missio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3]Salmi, Jamil.2009.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Washington, DC:World Bank.
[24]Schuster, J.H., and M.J.Finkelstein.2006.The American faculty: The restructuring of academic work and career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李震声)
Advancing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The Rol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SA]Philip G.Altbach, translated by HU Ying, revised by BIE Dun-ro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are a central part of all academic systems and are central to the success of any modern knowledge-based economy.Most top journal editors, and most authors and reviewers are located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universities support access to global knowledge, and are centers of communities of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nd more often have funds available to send faculty members to conferences and profess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even at the core of the Internet revolution.So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are at the center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mission.As the repositories of knowledge and critical centers, globalization is both a bene t and a curse to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esearch universities have developed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but meanwhile are facing the dilemma of language and are required to promote the academic profession.At last, this article outlines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ful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points out to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needed for successful research universities is a top priority.
research universities; developing countries; knowledge communications
G640
A
1672-0717(2015)01-0004-11
2014-11-18
菲利普·G·阿特巴赫(1941-),男,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莫南高等教育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胡颖(1989-),女,湖南长沙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商学院辅导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