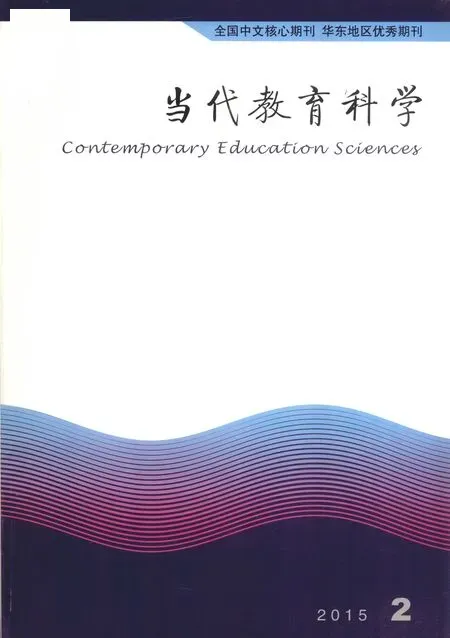教师生命教育的缺场与重构*
●易连云 邹太龙
教师生命教育的缺场与重构*
●易连云 邹太龙
教师带病上岗一向被视为高尚师德而广为传颂,人们对其缺乏理性审视与深刻反思,其背后实则反映出教师生命教育的缺场。教师带病上岗不仅阻碍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与生命价值的实现,而且也不利于学生生命的健康成长。关怀教师生命状况与改善教师生命质量,需要剥去教师隐喻的神圣光环,唤醒教师自身的生命意识,分离教师不同的生活角色,带领教师参加多样的生命体验。
教师生命;带病上岗;生命教育;生命关怀
2014年9月9日,内江市东兴区张晓蓓老师虽患有肾病综合症,身体浮肿,但她仍然“拿上备课本和教材,大步走进教室”,因为她不想落下功课,“要给孩子们成长的道路打好基础”。[1]2014年3月19日,郸城县秋渠一中校长张伟因连日工作劳累而脑干出血,“用生命铸就教育信仰”,最终倒在了办公室。据其同事回忆,张伟去年就检查出患有高血压、高血脂,但他并未把这些放在心上,仍然“夜以继日,殚精竭虑”,“高强度地连续工作”。[2]2014年2月18日,扬州市邗江区王红梅老师在身体严重不适后被迫去医院接受检查,结果发现体内已有4个恶性淋巴瘤。据报道,王老师如同“铁人”一般18年如一日地恪守着朝六晚六的作息时间,她不仅以微笑抗争病魔,还用上课转移病痛。[3]
以上见诸报端的悲壮事迹只是冰山一角,是教师带病上岗现象的极端反映,实际上,教师身体健康问题已不容忽视,新疆昌吉州2014年对全州17315名教职工进行的健康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有8626人患有不同种类的疾病,所占比例高达50%,[4]而十分有趣且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现象是,教师自身健康状况与自觉生命意识呈现双低态势,对自己生命的关注程度和对学生生命的关注程度极不对称,一项中小学教师生命意识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高达64.95%的教师认为很关注学生的生命,相比而言,只有26.45%的教师很关注自己的生命,而且52.31%的教师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5]
一、生者足鉴:令人反思的“高尚”师德
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浸染与影响,我国的教育往往高扬人的社会生命而漠视甚至贬抑人的自然生命,个体生命被贴上政治的标签或镶上道德的金边,当道德追求与爱惜生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甚至相互抵牾时,不少教师心甘情愿地以伤害体现道德,用死亡彰显崇高。
诚然,教师带病上岗是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追求生命的广度与深度,不但促进了学生的发展与完善,而且也升华自我的生命价值,然而十分清楚,这种方式是以漠视甚至践踏自我生命为代价的,以巨大的牺牲换取微小的价值,这种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做法究竟是否值得效仿和学习?是否应当加以理性的审视与反思?
《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中国文化的灵魂深处,生命与道德就具有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与通约性,珍爱生命,既是道德的要求,也是道德的体现,“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才会重德。”[6]人倘若不能作为自然载体而活着,舍弃了“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的物质生命,“道德”如何彰显与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活着也是一种意义,热爱生命,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同样,拥有道德,既是生命的恩泽,也是生命的特征,诚如鲁洁先生所说:“厚德载物就是一种厚生,有了厚德,她才能够有生命”。[7]说到底,“道德是为了人而产生,而不能说人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的。”[8]道德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人不能为了彰显道德而干预生活、摧残生命,更不能让道德变成束缚人生存与发展的工具,变成消解独立个体存在的手段。
如果教师在保证工作效率与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捷径或巧干来保持身体的健康,永葆生命的活力,这是否就是一种“投机”而不道德呢?现实的教育生活中,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尚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更遑论普遍传颂了。人们潜意识地或惯性地将具有复杂性与层次感的道德作了简约化理解,仅仅将其归结为一种具有利他倾向的品质与德性,而对“利己不损人”的行为则抱以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
爱人是自爱的延伸和道德的升华,“只要把自爱之心扩大到爱别人,我们就可以把自爱变成美德”,[9]休谟所说的“同情”、孟子话语中的“恻隐之心”都是由未受扭曲的自爱品质发展而来,作为有思想的人,能够 “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10]试想,一个不自爱、不热爱生命的人,何敢奢望他对学生倾注全部感情?给学生生命的春天抹上永恒的绿色?因此,“教师带病工作精神可嘉不宜提倡”。[11]
二、生命教育缺场:教师带病上岗的主要归因
反思与拷问现实教育,我们发现,“以往的生命教育多是应对社会危机的产物,具有偶然性与工具性”,[12]主要停留在预防学生疾病和防止学生自杀的现实问题上,这样的生命教育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疗法,并未从学理高度加以前瞻性地审视。生命教育出现了认识上的偏颇与实践中的偏失,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淡化与遮蔽教师生命教育、对教师缺乏生命指导与关怀的现象。社会与学校将目光与精力更多地锁定于学生身上,生命教育在师生会遇中出现了顾此失彼、偏于一端的状态,学生成了独享生命教育的唯一“顾客”,教师因囿于规定性生存尺度和确定性生命流程而旁落于生命教育的视野之外,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社会本位文化,传统师德观念犹如长河中的泥沙一样随着岁月的冲刷与洗礼渐渐淤积在广大教师的思想沟壑之中,“春蚕至死”、“蜡烛成灰”,多么可歌可泣的光辉写照;“至圣先师”、“道德楷模”,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圣人化身;“甘为人梯”、“无私奉献”,多么让人为之振奋的道德品质……殊不知,这些道德品质如奉献、敬业、牺牲精神的确立是建立在轻视、无视甚至蔑视教师生命的基础之上的。这种重名分、慕虚荣的传统文化余波无疑对教师带病上岗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师本是诸多职业中的一种,却被赋予了太多的精神含义,承载了太大的心理压力,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足以压垮那些原本平凡的教师。教师职业道德虽然反对教师沦为“物质巨子、精神侏儒”的及时行乐者,但也没有苛求其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
现实中的教育评价体制深受功利主义的侵染和政治权力的影响,教育部门将鼓励与嘉奖的优先权锁定在那些非死即病的教师身上,舆论媒体将教师带病上岗作为一种高尚的职业道德而大肆宣扬与推崇,各级学校也将评优的目光集中于因公殉职的教师身上,以期凭借教师的“因病出名”或“因公殉职”而增加学校名气。在这种评价机制下产生的万千“模范教师”、“师德标兵”、“教学能手”、“育人楷模”多数是因为忘我工作、自我牺牲而获得一份荣誉,这些荣誉光环与“牺牲生命”、“忘我工作”直接挂钩,似乎教师只有忘我、无我、非我才会有价值。由于社会观念的误导与评价机制的诱导,再加上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现实竞争,无数教师迫于无奈,只有以生命资本去换取事业上的成功,以致于自身生命迷失在虚妄的“捷径”中,陷入在浮躁的“虚荣”中,淹没在逐利的“强音”中,对生命的漠视和盲视代替了对生命的凝视和注视,对生命的冷漠与苛求销蚀了对生命的理解与宽容。
而且,不少教师把自我牺牲看作是于人有利、对己无益的单向献身,这也就意味着对自我存在的放逐乃至沉沦。教师在内心深处秉持着“人是工具而不是目的”的偏狭之见,已经将主体的外部价值与内在意义隔离开来,自己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性存在,而不是一个显示着“人”的价值的人,教师由此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无法领悟到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以致于有些教师难以承受生命之重而上演投缳赴水、饮鸩跳楼的悲剧,这些都是“重压”下的极端“宣泄”,心理扭曲后的异化外显,这也从侧面敲响了加强教师生命教育的警钟。因此,关怀教师生命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教师期待着生命教育的关照与眷顾。
三、关怀教师生命:教师生命教育的路径重构
(一)剥去教师隐喻的神圣光环
所谓教师隐喻,指的是“籍同‘教师’有某种类似点的有价值的人或事物,显示‘教师’职能的意义与价值。”[13]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对教师期望的变化,教师隐喻中的喻体也不断发生着相应改变,从最初的“桐子”说到农业时代的“园丁”说,由“蜡烛”隐喻过渡到工业时代的“工程师”隐喻再到信息时代的“桶论”,这些喻体的更迭轨迹表明,人们不满足于教师作为“教书匠”的实然身份的同时,也对教师应然角色的期望越来越高:在道德人格上,教师应该是德操没有污点与瑕疵的“完人”;在知识储备上,教师随时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应付自如,从“弱水三千”中取出“一瓢饮”。
由于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长期遗留下来的师德传统与教师隐喻不仅深深扎根于社会沃土里,也同样存留于教师脑海之中。“无论是教师的自我定位,还是他人角色期待,都使得教师‘神化’”。[14]对外界而言,教师似乎只有在融融赞誉声中忍受着牺牲自己的无奈,在殷殷期待中遭受着病痛的折磨,以至于在生命陨落之时,也要强颜迎接黑的美。对自身而言,教师生命似乎注定就只能在飘洒的粉笔灰中自我掩埋,在默默的三尺讲台上挥洒余生,就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尚需践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崇高与悲壮。这种讲牺牲、重付出的传统文化余波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下,我国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和社会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其实质仍然是一种“小我服从大我”的整体主义与牺牲精神,作为“伟大”的人民教师,更应该用无私奉献的“蜡烛”精神去照亮学生,“蜡炬成灰泪始干”,即使耗尽生命也在所不惜。
然而,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隐喻自不例外。隐喻具有本体与喻体之分,它们除了在功能上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点外,还存在着诸多不同,喻体毕竟不等于本体,教师的实然身份同其应然角色存在着距离甚至是冲突,所以我们不能将带有理想色彩的隐喻当做敲打教师的“紧箍咒”,更不能按照“园丁”、“蜡烛”、“工程师”等隐喻所蕴含的标准对教师“画地为牢”。其实,只有当教师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从属于更高的价值并应当为其牺牲时,自觉地保全性命才会产生道德苦恼,否则,教师不必为此难以释怀,也没有必要沦为道德的符号或道德的奴隶,更不能因为传统师德的捆绑或羁绊而成为殉葬品。“在传统教育中,教师这个群体受到了太多的压抑和控制,需要效法女权运动,像解放妇女一样解放老师”,[15]因此,社会各界需要 “以一份宽容之心真诚地搀扶我们的教师走下神坛”,[16]教师自身也应该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打碎思想禁锢的枷锁,主动地展现生命活力、感受生命律动、思考生命真谛、创造生命价值。
(二)唤醒教师自身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一个层次复杂的多重概念,是人对其物质“在场”与精神“存在”的体认与感悟,一般包括微观层次的生存意识、中观层次的生存能力意识和宏观层次的生存价值意识。作为生命载体的个人,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命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与根本前提,人首先必须保持和完善其肉体之存在。因此,教师生命意识的苏醒首先表现在教师能够“树立生命珍贵和敬畏生命的意识,学会珍爱生命和保护生命”。[17]教师不仅要敬畏精神生命,更要敬畏作为精神生命之载体的自然生命,因为“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18]教师作为个体生命,在依托外部环境的同时,更应具有实现生命价值与职业价值内在的融合与统一的生命自觉意识。
法国学者路易·勒格朗说:“热爱生命,首先是对我的存在的所有伤害的担忧,说到底是对死亡的担忧”,[19]因为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了生命,也就失去了一切存在的基础。从经验上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珍贵,也没有什么东西与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其他东西都会认可它们是从生命中获得价值的”。[20]如此看来,撇开其背后动机和现实因素,教师带病上岗这一行为是对生命的亵渎与践踏而不是敬畏与尊重。教师自觉生命意识的不完善,唯上、从众、逆来顺受的社会心态,以及“德领于世”“行高于人”的角色期待尚弥散于当今社会之中,这又进一步销蚀了教师的自我意识与自爱精神,加剧了教师生命意识的淡化与遮蔽。
教师的生命意识除了关注自身的自然生命和生存能力之外,更应该将视角定格在“超出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21]从而“把人引向比现实关切更深刻的关切”。[22]即对自己的生命给予一定的终极关怀与价值向导。
(三)分离教师不同的生活角色
职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分离是现代职业的一大基本走向,是社会文明与自由程度的晴雨表,更是教师实现生命自主与生活自由的重要保障。“教师生命的自主体现为教师按照生命本性所固有的内在要求支配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自由”。[23]教师只有充分享有自身发展的选择权,免受职业生活在时空上对个人生活的挤压与侵占,才能体验到生命的完满和充盈,才能从职业生活外的领域得到生命的自由,获得超越“职业人”的新生命。
然而在现实中,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更多的是关心教师的教学业绩,很少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应试环境下的教师评价把学生的升学率作为一项硬性指标,且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审等密切挂钩,这种教师评价的统一标准,势必使得教师在追求外在评价的同时,忽视自身生命的成长。假期加班加点、下班批改作业、课后义务补习等侵犯教师生命自由的现象就成为常态。在名目繁多的功利诱惑和步步紧逼的考评压力的推动下,不少教师不得不因“病”出名或靠“病”升职,以自我牺牲换取一纸荣誉。
教师首先是作为一个完整人的存在,他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而是肩负着子女、配偶、双亲、朋友等多重角色,过高的社会期望和理想的道德人格让教师不堪重负。教师作为人的存在,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生物人与社会人、感性人与理性人的统一体,学校不能以教师身份的应然标准来比照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教师,过分强调教师的社会责任而忽视其自然需求,过分看重教师的耕耘精神而对其生命质量漠不关心。在对待教师带病上岗的问题上,学校要理性对待,不能一味地以师德高度去捆绑教师,而应从人性化角度引导教师追求生存价值与生活意义相统一、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相平衡,不应鼓励或支持教师带病上岗,而应对真正有病的教师给予宽容与理解,责令其及时治疗,以免积重难返而因病致贫。教师早日康复,也就能尽早地回到工作岗位,更好地从事教育工作。
(四)带领教师参加多样的生命体验
作为世界性思潮的生命教育,目前正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形式与主题展开,如美国的品格教育、死亡教育、挫折教育、生计教育,北欧国家的孤独教育,英国基于主辅搭配的公民教育和健康教育,日本的寒冷教育,而生命教育在我国尚处于发展初期,尤其是死亡教育,似乎成了人们口中的“禁语”,往往被认为“不吉利”,学校更是谈“死”色变,在教育过程中甚至对“死亡”三缄其口。
死亡教育的缺失,不仅让教师漠视自己的生命,还可能会引起他们对他人和其他生命的漠视。其实,死亡教育能够“帮助人们澄清、培养、肯定生命中的基本目标与价值,通过死亡的必然性来反思生命的意义及其价值”,[24]正是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才激发了人们在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短暂生命中去追求永恒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向死而生”的道理,人们“关于死亡的一切思考,都反映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25]假如没有死亡,生命就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不会死亡,所以就不懂得珍惜生命。亲身体验过“死亡”的人,对生命的内涵、价值与意义有着比苍白无力的语言教育更加刻骨铭心的领悟,才会坦然面对死神的降临,欣然接受生命的终结。
在对教师的生命教育中,学校既可以带领教师去参观医院、育婴室、殡仪馆、丧礼病房等与生老病死相关的场所,也可以组织教师参加集科学普及、体验休闲、灾难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灾害体验馆。教师可以亲身感受海啸的汹涌震撼、地震的“天翻地覆”、台风的强劲肆虐……通过这些生死体验和灾难教育,教师不仅在“死去活来”中体验了死亡的奥秘,感悟了生命的真谛,而且还学会了在灾害来临时如何保护自身与学生的生命安全。只有教师真正明白了生命的可贵,自己才不会上演暴殄轻生、自杀身亡的悲剧,也才不会出现“范跑跑”视生命如草芥的切齿行为,只有教师真正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才会在生死时刻从容地选择,也才会有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舍身救人的感人举动。
[1]85后女教师不顾病痛坚持教学,被封“拼命三郎”[N].华西都市报,2014-09-12.
[2]倒在办公室的农村校长[N].中国教育报,2014-03-19.
[3]只要一上课,什么病都没了——记与疾病抗争的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教师王红梅[N].中国教育报,2014-04-10.
[4]中小学教师健康急需高度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教职工健康状况调研报告[N].中国教育报,2014-09-18.
[5]马雪莉,刘慧.中小学教师生命意识状况的调查[J].思想理论教育,2008,(20):12-17.
[6]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3.
[7]戚万学等.静水深流见气象:鲁洁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情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198.
[8][美]威廉·K.弗兰克纳著,黄伟合译.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7.
[9]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340.
[10][18][法]阿尔贝特·史怀泽著,陈泽环译.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34,131.
[11]教师带病工作精神可嘉不宜提倡[N].中国教育报,2014-09-15.
[12][17]冯建军.生命教育与生命统整[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22):8-11.
[13]陈桂生.师道实话[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
[14]覃兵.论教师主体生命意义的消解与重构[J].教师教育研究,2005,(3):39-43.
[15]Carl.Santa.JcIhn L Santa.Teacher as Researcher[J].Journal of Reading Behavior,1995,(3).
[16]赵宪宇.教育的痛和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8.
[19][法]路易·勒格朗著,王晓辉译.今日道德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00.
[20][法]居友著,余涌译.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30.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6.
[22]黄克钊.人文学论纲[J].哲学研究,1997,(9):3-13.
[23]张培.生命的背离:现代教师的生存状态透视[J].教师教育研究,2009,(1):50-55.
[24]Corr,C.A.&Nabe,CM.&Corr,D.M.(eds.).Death&Dying:Life &Living.(2nd ed.).Brooks/Cole Pub.tom,1997:17-18.
[25][美]艾温·辛格著.郜元宝译.我们的迷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4.
(责任编辑:刘君玲)
*基金课题:全国教育规划课题“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中的意识形态盲区研究”(课题编号:BEA130024)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易连云/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校德育、教育学原理
邹太龙/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校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