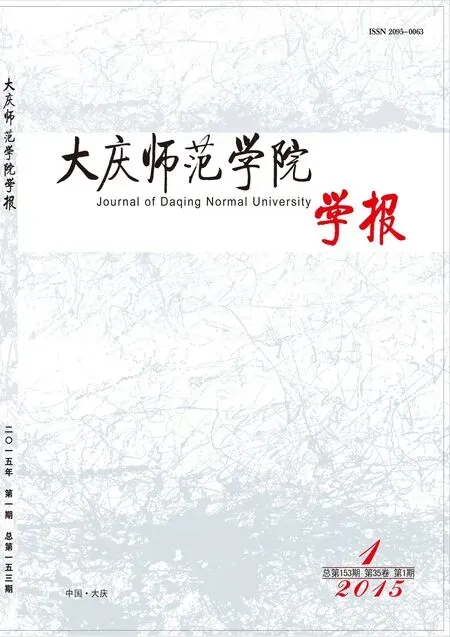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与现实的两难抉择——兼谈李光地的历史评价问题
作者简介:叶茂樟(1970-),男,福建龙岩人,副教授,硕士,从事古代文学及闽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资助项目“打造李光地文化产业链,助推安溪经济腾飞”(JB13705S)。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5.01.026
研究清初政治、思想史,李光地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个久存争议的人物。誉之者推为“儒林巨擘”(《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四》)、“学博而精”(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四十》) ;毁之者则讥之“纸尾之学”(全祖望《鲒绮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不学无术”(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三》),两者差距之大让人瞠目结舌,而“凡訾议其学问者,每多从讥斥其为人出发”,且此余风延续至今。其实,学问和人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把两者等量齐观是因噎废食的表现,何况众矢之的的李光地“三案”并不是简单的“人格”两字所能概括的。清史研究学者陈祖武先生说:“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都不能够脱离他所活动的具体历史环境。” [1]16鉴于此,对李光地的评价就不能脱离他所在的历史背景,局限于其生活的时代,更离不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语境。围绕李光地的是是非非,不能简单地停留于“道德”的层面,他实际上集中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与现实困境的矛盾,当面临抉择时,人性的另一面自然暴露无遗,与其说是人格的堕落,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剧。
一、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与现实困境的两难抉择
(一)独立性人格与依附性人格的矛盾
“士人”是现代人对古代知识分子的称谓。古代的读书人叫儒生、儒士,读书人做官,称之为出仕。当然,最早的“士”并不只指读书人。据《论语·子路》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就是说,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这是孔子对“士”理论标准的概括。北宋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语录中》),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追求的四个维度。“士”的黄金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真正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制度,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士人思想日益与现实政治结合,独立人格逐渐丧失,最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作治国的工具。
纵观士人的种种表现,其最大特质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源于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儒家政治思想是德治主义,目的在于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从德治主义出发,儒家认为君主应是“内圣外王”的统一,即以修身为本,从人格修养中推衍出仁政王道。这种圣贤人格,也是对士人理想人格的追求。“内圣外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所谓“内圣”是主体性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到仁、圣境界为极限;“外王”是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王道、仁政为目标。这种人生理想最早源于孔子的“修己以安人”并进而“安百姓”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内圣外王”的思想同样包含在《大学》之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所谓的“三纲领”和“八德目”,是对“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完整概括。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观虽然看上去很完美,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往往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资料显示,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间全国乡试平均中举率为3.95% [2],更不用说通过会试、殿试,到达统治者的中枢,辅助君王“治国平天下”的概率了。
另一方面,即使入“仕”也并非就能够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行道”。古代社会实行的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儒家伦理文化架构之下,知识分子只能孜孜于“食王爵禄报王恩”“忠君报国”“君尊臣卑”“君命臣随”,士人们的人格与尊严得不到起码的尊重。此外,虽然孔子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于议也”(《论语·里仁》),其高徒曾子也说过:“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但是,这种高难度的道德要求毕竟难以抵挡来自经济生活的压力,让士人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孟子说大丈夫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的要求,对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而言,并没有内化成为普泛意义上的道德自律。除了经济上的困窘之外,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更要受到来自政治权威的挑战,而且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政治权势的压力无疑要大得多。”“尽管知识分子以道自重,而且也作过相当的努力,以期来和权势分庭抗礼,但那至多只是一种美丽的愿望而已,这种‘道’与‘势’的不平等面对,也就基本上确定了知识分子持有健全人格的艰巨性。” [3]43
可以说,士人们都有“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的完美人格追求,但是,仕途的艰难、政治权势的淫威和经济生活的困窘,造成古代士人的独立性人格逐渐丧失,随之而来的是言不由衷的依附性人格。李光地身上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影子。
李光地出生于福建安溪的一个“甲族大家”。秉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李光地五岁便从师授读,“未尝一启齿,发声试之,辄已成诵,不失一字。善属对,矢口惊人。塾师弗能教也”(杨名时《碑传集·卷13·文贞李公光地墓碣》)。根据《文贞公年谱》记载,青年李光地读书十分勤奋,13岁遍读群经,18岁编写《性理解》,19岁写《四书解》,20岁写《周易解》,24岁辑《历象要义》,25岁通律吕之学,后又从著名学者顾炎武受音韵之学。他尤其致力宋明理学的探求,“以濂、洛、吴、闽为门径,以六经四子为依归”(杨名时)。因为学识功底扎实,李光地的科举道路相当顺利,康熙三年(1664年),李光地试策论举于乡;康熙五年(1666 年)中举;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然而,对于怀揣“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李光地来说,远远不够,而要进入封建统治的中枢,非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垂青不可。康熙十二年(1673年),李光地充会试同考官,不久省亲归里,从此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事情的源起还得从“三藩之乱”说起。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州。同为翰林院编修的李光地和陈梦雷适逢告假回乡省亲。根据《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二·李光地传》记载:“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燝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李光地、陈梦雷两人,同为福建老乡,“同岁举进士,且官编修”,却在“三藩之乱”波及下发生了天壤之别的人生逆转,让人们不禁感慨命运的反复无常。此后双方各执一端,彻底决裂。这桩历史“公案”迄今尚无定论。耐人寻味的是,陈梦雷被判处死刑行将论斩之时,李光地又上疏请求宽免陈梦雷:“律以抗节捐躯之义,其罪尚不能辞也。独其不忘君父之苦心,经臣两次遣人到省密约,真知确见,有不敢不言者。当逆贼初变,臣遁迹深山,欲得贼中虚实,密报消息。臣叔日燝潜到其家探听,梦雷涕泣,言隐忍偷生,罪当万死,然一息尚存,当布散流言,离其将帅,散其人心,庶几报国家万一。臣叔回述此语,臣知其心未丧也。”“梦雷言贼势空虚,屡欲差人抵江、浙军前迎请大兵,奈关口盘诘难往,因详语各路虚实,令归报臣。此密约两次,知其心实有可原者也。”(《清史列传·卷十·李光地传》)。可见,李光地与陈梦雷之间是有密约的。那么,李光地《蜡丸疏》中为什么独自具名呢?李光地的解释是“诚恐事泄俱毙无益”(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十三·抵奉天与徐健庵书》),“自贼中来,虑有他变,弗敢以闻”(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四·李光地传》),这种解释确实有些牵强。 [5]
窃以为,让李光地一生饱受人诟病的“卖友”案从深层来说,暴露的是李光地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人格与依附性人格的矛盾。李光地一生饱读诗书,其最终目的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他不得不为仕途“多长个心眼”,以致一时丧失了自己独立人格的尊严,依附于政治权威。类似例子在历史上举不胜举。“三藩之乱,蜡丸上疏”恰好为李光地提供了一个“矢志报国”契机,“谋划多称上意”(钱林)“深见契纳”(杨名时),也就一步步迈入朝廷中枢。只是从此以后,人们对李光地的评价也就脱离不了“道德”的窠臼,其中究竟蕴含多少道德的因素,是因为党派相争互相倾轧的结果,还是时代造成知识分子的人格悲剧,让人五味杂陈,难以言说。
(二)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道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儒家提倡“入世”;而道家主张“清净无为”“顺应自然”是一种超脱世俗之外的逍遥。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逃逸超脱,两者迥然不同又相互并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士人来说,“内圣外王”是其理想的人格追求和处世哲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生只能追求一种人格形态。仕途的艰险和政治权势的压力,士人们向往的理想人格并不能总是天遂人愿。于是现实中,士人除了具有独立性人格和依附性人格的矛盾之外,又伴随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当得意之时便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儒家的道德人格,而当失意之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追求道家的逍遥人格。这种得意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雄心壮志与失意时“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怀才不遇的解脱,就是儒、道两种思想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矛盾人格。“出仕还是隐逸,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两种不同的生存选择。对于选择者个体而言,‘隐’或‘仕’只是表现出形式上的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观照生命自身以期捕捉生存的最佳方式,努力实现生命理想与生存方式的和谐。但‘隐’还是‘仕’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正犹如‘生’还是‘死’对于哈姆莱特一样取舍两难、进退维艰,其选择实在要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痛苦得多。” [4]
“三藩之乱,蜡丸上疏”给李光地仕途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康熙帝认为“李光地不肯从逆,差人密奏地方机宜,忠贞茂著,深为可嘉,著从优议叙”(《清圣祖实录·卷六十六》),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擢为侍读学士。此后,李光地官运亨通,先后担任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通政司通政使、兵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巡抚直隶、吏部尚书、直隶巡抚和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可谓“位极人臣”,为统一祖国、革除弊政、澄清吏治、治理水患、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李光地48年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清朝初年,朝廷党派林立,大臣们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李光地虽然没有依附统治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派系,但也受到牵连。可以说,李光地的每一次升迁都迎来接踵而至的风波,一次次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给他“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精神带来不小打击。李光地深感官场政治尔虞我诈的黑暗,曾经多次以“乞假省亲”的方式试图回避。
据《文贞公年谱》记载:“公备蒙恩知,向用甚笃,当轴及躁进者,渐生嫌忌,而公闭户介立,莫之知也。”“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公四十一岁。夏五月,疏乞送母还里,许之。”李光地在家乡建榕村书屋,与亲友讲学其中,世称“榕村先生”,又“买山一区,粗营精舍,中有石洞,名成云洞”。但他并不能真正置之世外。期间,总督姚启圣常以地方兴革事宜相咨询,李光地备陈利弊,多有所建树。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还朝任掌院学士兼吏部侍郎,风澜迭起。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三月,疏乞终养,予假一年。陛辞,召对,荐德格勒、徐元梦、卫既齐、汤斌等。时母太夫人年益高,而城社争柄,羽党竞营。有布政使某者,秽声彰著,而柄臣嘱公为之荐达,公执不可,大以为憾。公自度不见容,思归养以避之,遂具疏乞终养。疏入,圣意方渥,不许,仅予假一年,且悬党院缺,不他授,以速公还”“冬十月,疏请展限”(《文贞公年谱》)。此举险些受徐乾学等人陷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李光地奔赴孝庄文皇后大恤,终因延期及与德格勒“彼此相互陈奏”结党营私为由遭治罪,只是康熙帝并未免去李光地的官职,“但李光地前为学士时,凡议事不委顺从人。台湾之役,众人皆谓不可取,独李光地以为必可取,此其所长。除妄奏德格勒外,亦别无如此启奏之事,姑从宽免其治罪,令为学士。嗣后勿再妄冀外任,并希图回籍。宜痛加改省,勉力尽职”(《康熙起居注》)。虽然陷害未成,但同朝一些眼红李光地的官员从未停止对他的妒忌中伤。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春正月,扈从南巡。公既蒙贷,嫉者益忌”(《文贞公年谱》)。这些罪名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贪位忘亲”,全祖望将其归纳为“中年夺情”案。《文贞公年谱》据此记载:“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春三月,丁母太夫人吴氏忧。固请奔丧,不许,在京守制。三月二十七日,讣至,即循例乞奔丧。上不听,有夺情之意,公再三固请,终不见许。于是杨、沈、彭三御史交章劾公不奔丧,而彭尤力。谗者曰:‘彭,闽人也,彼以乡情受嘱,名虽弹劾,实以诡上,冀得放归耳。’上因切责彭,彭急思自白,遂捕捉风影,别疏极诋公,上滋不怿。公不得已,自陈曰:‘臣在乱时,臣母勖臣以忘家之义;臣得假家居,又趣臣以就列陈力,少效夙夜在公之职。今臣勉遵母志,不敢丐归,惟求解任。’乃命在京守制。”
就这样,李光地一方面怀揣着“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另一方面却一次次在官场倾轧中受到恶意中伤,成为舆论的焦点。自然,儒家出身的李光地没有得意时雄心壮志与失意时怀才不遇的解脱,更多的是陷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居家还朝之际,曾采南宋裘万顷诗作《归兴》题于成云精舍斋壁:“新筑书轩壁未干,马蹄催我上长安。儿时只道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难。千里关山千里念,一番风雨一番寒。何如静坐茅斋下,翠竹苍梧仔细看!”或许只有这首诗才能深刻反映李光地的心情。终其根本,“学而优则仕”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出世的思想,“使读书人陷入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为了求得内心自由和愉悦,应当超脱飘逸、修身养性,不求闻达但仕宦的情结又趋使之媚俗以求青睐,违心以图出仕。于是进亦忧,退亦忧,最终消弭了‘修身’这一根本,以至禁锢了思想,扭曲了人性,模糊了人生追求真、善、美的目的性,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5]10-13。
二、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立足时代,着眼大节
许苏民先生说:“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把他放到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必须以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这样做,既是为了坚持历史研究的严格的客观性,避免把历史人物‘现代化’;也是为了防止苛求古人,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作隔膜的揶揄和谬误的判断。” [6]246然而,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儒家为主导的封建思想及儒、道、释相互并存的思想体系,必将在封建士人的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从李光地等古代知识分子的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他们面临理想人格与现实困境时的两难抉择,独立性人格与依附性人格的矛盾,入世与出世的矛盾,饱受心灵的煎熬。然而,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和胆量跳出官场来思考怎样改善这种中国式的官场政治,也想不到是否存在着另一种可能的政治学,让他人和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7]。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于,其“过”的性质、大小。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立足于其所处的时代,着眼于大节,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合乎时代的相对客观的结论。李光地一生饱受争议,然观其一生,为清初时期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奠定清政府思想统治重心的“理学名臣”,可谓大节彰显,无可厚非。因李光地得以保全生命的清初散文家方苞曾感慨:“康熙已亥秋九月,余卧疾塞上,有客来省,言及故相国安溪李公,极诋之。余无言,语并侵余。嗟夫,君子之行身固难,而遇盖有幸有不幸也。”(方苞:《安溪李相国逸事》)后人又何必津津乐道于李光地的“人格”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