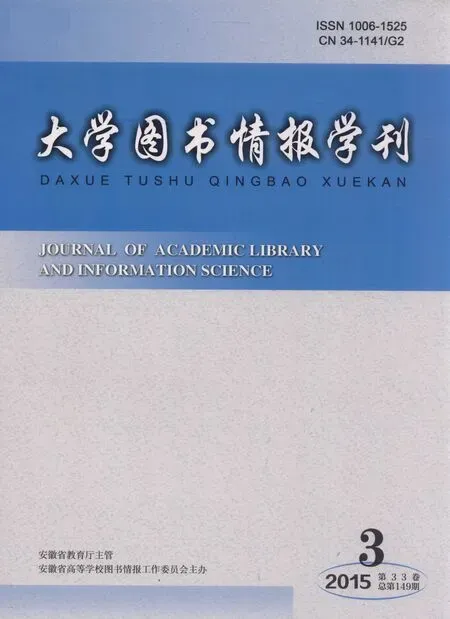图书馆的“变”与“不变”:浅议社会知识需求变化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图书馆的“变”与“不变”
——浅议社会知识需求变化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徐珊珊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合肥 230601)
摘要:社会记忆并利用知识的需求是图书馆缘起、发展及其服务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下,社会知识需求在其状态和结构上的变化促使图书馆的功能、形态以及服务发生变革。信息时代下图书馆的困境正是由于不能及时适应社会知识需求的变化而产生的。因此,可以尝试超越到图书馆及其相关社会机构之上探寻知识交流的社会机制,以期适应社会知识需求的变化并保障其实现。
关键词:图书馆;社会知识需求;知识交流机制;图书馆服务
中图分类号:G250.1
作者简介:徐珊珊,女,助理馆员。
收稿日期:2014-11-23
The changeable and unchangeable in libraries
——Research on impact of social knowledge requirement on library services
XU Shan-shan
(Anhui University, Hefei230601, China)
Abstract: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social requirement of the knowledge storage and utiliz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reform of the library and library service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social knowledge requirement, the library should make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its functions and service models to keep abreas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refore, it is advisable to explore the social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beyond libraries and other social institutions so as to conform to the social knowledge requirement and to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bligations of the library.
Key words: social knowledge requirement;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library services
1引言
2003 年 6 月,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召开“后数字图书馆的未来”(又称“泛在知识环境”)研讨会,提出数字图书馆要协同 NSF/ACP 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创建“泛在知识环境”[1]。自此,“泛在”一词迅速成为图书馆学领域谈论和研究的热点。随着宽带技术、人工智能、对象关系数据库系统、无线网络、VOIP、WiMax、XML[2]、web2.0等技术的引入与应用,图书馆学人纷纷提出“泛在图书馆”[3]“图书馆泛在服务”[4]“ 渗透性图书馆”[5]“ 弥散式图书馆”[6]等概念,或认为终于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将“任何地点任何时刻读取图书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了[7],或宣称“泛在图书馆”揭示了图书馆存在的本质和发展前景,应该是未来图书馆存在的重要型态和发展模式[8]。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而随着 RFID、物联网、传感器网络等又一批信息技术的兴起,“智慧”一词再次点燃了图书馆学人探讨图书馆未来形态的“热情”,构造出又一个新概念——“智慧图书馆”。诚然,各种新兴技术给图书馆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为图书馆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新的手段或思路,解决了许多图书馆的技术难题,出现了许多可供选择的新方法[9]。但是,不管是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现实中来看,信息技术究其本质是方法的革命,它只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并不是一场目的的革命[10]。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论证图书馆的目的、职能、形态等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令人莫名的是,图书馆学人在讨论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的冲击时,往往混淆了目的与方法之间的区别,导致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新几乎都会引发多数图书馆学人“预言”图书馆未来的狂潮。这些“预言”和“论断”并不能较好地解释图书馆与图书馆员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图书馆学人或沉浸在以追踪信息技术来提高图书馆服务效能的研究成果中沾沾自喜,或为图书馆“内忧外患”的困境而惴惴不安。在这一喜一忧之中,是不是可以尝试思考为什么信息技术能够如此轻易地左右我们的态度与情感?我们那么急迫地想要跟上信息技术的步伐以促成图书馆之“变”,而实际情况是图书馆“难变”甚至“不变”,究竟是我们的努力不够,还是以技术驱动图书馆之“变”这一想法本身就是片面而武断的呢?图书馆可能因为什么而“变”?在技术直接作用的图书馆实践活动之上,会不会存在内在、客观、本质的变革机制约束着图书馆全部发展过程[11]?笔者认为,图书馆经历过诸多的社会变革、技术变革,但其存在、发展的内在动因,即社会记忆并利用知识的需求(以下简称“社会知识需求”),至今未曾改变过,图书馆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机构。
2社会知识需求与图书馆服务
2.1 社会知识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同学校、教堂、医院等其他社会机构相类似,并不是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就存在的,而是当社会中的知识产生、积累至一定程度,“出于共同意愿,为服务于重大的人类需求,而建立人际关系的集成模式[12]”。这个“重大的人类需求”即社会知识需求。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不论个体、群体,都需要不断地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处理信息、总结经验、形成知识,并将知识经由基因和学习一代代地传承下去。随着社会的产生、发展,个体和群体对知识的需要因他们之间交流联系的加强而逐渐聚合成为社会全体共同拥有的社会性需求。社会知识需求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其存在不以个体或全体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同时,社会知识需求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从未中断对这一客观需求的发掘、充实与改造。但是,由于社会的内部结构差异、外部环境改变、历史条件不同等原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未必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只有社会不停向前发展,才能既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得到加强,又逐步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因此,社会形态的变化将直接引发社会知识需求的变化。
2.2 社会知识需求状态的变化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对外部世界的艰难探索更多依赖于体力和自然力,尚不能理解什么是“知识”,并且因为这种不理解对知识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因此,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对知识的需求是未明的、偶发的、零散的、孤立的。当时统治阶级、宗教势力等对个体实行长期的控制和压迫,或是刻意夸大知识对于人类而言的“神秘感”,以窒息科学认知的发展,因而,从整体上来看,社会知识需求处于未激活或局部激活的状态。即便如此,人们产生、收集、传递、运用知识的过程却从未间断过。知识渐渐积累到了较为可观的程度,其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了解,进而强化了人们交流、传播知识的意识,希望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更稳定的环境内利用知识,呼唤一个独立于个别主体之外的“客体”组织承担起知识的搜集、选择、整理、评价、推广等活动,从而克服人类个体在生理、时空等方面的局限性。一千册书分散于各个私人收藏者手中和一千册书集中在“客体组织”中,其作用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图书馆就是作为这样一种“客体组织”而产生了。但是,当时社会中能够比较明确自身知识需求的仅是社会中的少数或特权人群,因此,这一历史阶段的图书馆多存在于宫廷、书院、寺庙等处,与绝大多数个体相隔绝。
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的革新,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性的提高,推动人类开创了大生产时代,对科学发展及社会变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和技术的需要,推动科学研究事业的兴起与普及,相应地促进着各种科学知识的新生与发展,而人类工业的产物都是知识的物质表现形态,或者说是“物化的智力”。知识逐渐成为了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支配性力量,成了社会变革的有力手段,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意识到知识与改善自身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对知识的需求相应变得越来越迫切,知识交流的规模、深度、速度都有了相应的发展[13]。于是,社会知识需求在整体上进入到了激活状态,图书馆活动的内容、方式、影响范围等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图书馆不再局限于宫廷、寺院,而是涌现出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多种类型,其职能也相应地产生了细化与重组,从而极大地抑制了少数或特权人群对知识的独占态势(但未能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图书馆渐渐面向社会全体开放,其活动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满足了个体理解、获取知识的需求,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个体在知识利用的深度、广度、准确性、时效性、追踪性等多方面的需求,从而催生了情报工作的脱颖而出。
人类在工业社会时期的发展速度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而电子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推动下的信息社会将信息、知识作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把社会进步速度提升到了指数级增长的状态。信息社会中,产业结构、政治格局、文化制度、社会内部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至今仍在加速并逐渐走向融合、贯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子中的任意一个发生变化势必触发其他因子的改变,能否监控所有变化并做出及时、正确、适度的反应,对社会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而言至关重要。而要敏锐地发现“变化”,快速地做出“反应”,适应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知识的战略性甚至决定性意义便显得更加突出,知识成为对人的基本要求。人们渴望进行跨政治、跨文化、跨地域的沟通与交流来加强联系、紧密结合、提高凝聚力,社会知识需求进入到了空前活跃的状态。社会知识需求的急剧膨胀要求提高知识产生、流通、积累的速度。但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信息作为知识的“原料”虽然进入到一个数量大爆炸、传播大提速的阶段,却并未能够给知识创新构筑预想之中强大而稳定的保障,反而引起了诸多混乱,如信息污染、信息犯罪、信息侵权、计算机病毒、信息侵略等,导致当前信息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一点与人类曾经为了追求生产发展,一路不管不顾地高歌猛进从而造成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经历颇为类似。社会知识需求的急剧膨胀无法阻挡,然而,需求的表达、实现、反馈必须经过不断试验、调整来达到更优化,避免不了花费一定时间。信息、知识更新速度太快、质量难辨优劣,在现有的网络环境中又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追踪、评价、保存,社会利用知识的周期被迫缩短而造成的“消化不良”已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甚至危害。而图书馆这样一个社会机构,受其内部运作机制以及外部经济水平、政治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效益等因素的制约,更容易对知识产生“消化不良”,自然难以对社会知识需求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这或许是当下图书馆在信息浪潮冲击之下显得行动迟缓、无所适从的原因之一。图书馆当前的困境是由于知识控制机制、社会知识需求与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社会性制约因素之间互不协调而产生的,因此,如果忽视社会障碍因素而过分夸大新技术的作用、混淆目的与方法之间的区别将是危险的思路,在这种思路下推导出互联网及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谁都可以即时的、自由自在地纵览世界各地的信息”的说法不过是一场柏拉图式的欺骗[14]。
2.3 社会知识需求结构的变化
社会知识需求可以分为“记忆需求”与“利用需求”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部分。前者促使图书馆纵向留存和继承人类社会自古迄今的科学文化知识,后者驱使图书馆横向连接和贯通知识的获取与知识的创造。前者为后者构建“仓库”,后者为前者丰富“储量”。两者共同推动知识的进步,社会的进化。
在工业社会之前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从横向来看,图书馆能够服务的人群、辐射的范围、广度等是比较有限的,但从纵向来看,图书馆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而在满足社会记忆知识需求方面能够总体上保持连续,并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对知识进行了选择性记忆与有序化组织,同时整理了相关的实践经验,产生了目录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为之后人类知识大爆发、人类文明迅速进步奠定了基础。社会的知识利用需求未全面觉醒,记忆需求相对呈显性,这种状况历时很长,因而可能导致人们产生了图书馆以“收藏”“贮存”为其核心职能的错觉。
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社会知识需求的“记忆”与“利用”部分基本可以平衡,图书馆走下了神坛,不再居于高堂之上,渐渐为社会全体所用。图书馆服务呼吁将前一个阶段的一些工作经验提炼为系统化的科学体系,需要图书馆职业人员的支撑,直接催生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如火如荼。但是,受前述图书馆以“收藏”知识为主这一错觉的影响,图书馆学理论及其教育体系从一开始是围绕着图书馆作为纯粹经验性职业的理念而建立起来的。如杜威,强调图书馆员将知识传递给用户的职业神圣感,不过,知识的传播利用不是单纯经由图书馆员的职业素养就能达到理想效果的,而是会受到来自社会当中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到“芝加哥学派”之时,其实才真正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希望能使之真正拥有一门科学的品格与姿态,要站到图书馆这个社会机构之外思考作用于图书馆的“社会知识制度”是什么样的,以此为轴心来研究现实问题、预测未来风险及相应对策等。可惜的是,这种更注重基础理论的、或者说形而上的思路并未能够延续很长时间。随着信息浪潮席卷而来,因为技术应用可以很快促使外在效果的改变,图书馆学对基础理论的追问很快被对应用问题的求解所淹没。
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知识的利用需求突出,但恶劣的信息环境给记忆需求的实现造成巨大障碍。目前,两者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失衡。社会个体对“利用”的理解和实践进一步深化,不仅是吸收,更注重创造出新的知识,不仅是需要获得知识,更要内化知识,再与个体的知识结构相结合,从而创造出更多新知识,且人人都要参与到知识产出的过程中去。在这种情势下,对图书馆如何满足社会知识的记忆需求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即如何从浩瀚的信息、知识之中进行有选择的收集、评价、保存、组织。人类记忆的传承需要形成相对稳定的信息、知识集合。但是图书馆不可能也不需要对信息、知识照单全收,而应当有所甄选,特别是信息爆炸的当下,并不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信息、知识都需要忠实留存,对知识进行适度、合理、科学规范的评价十分必要。此外,图书馆在注重保存知识的那一段漫长岁月里,对于如何序化知识形成了很多可贵的甚至独有的经验性论述,而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将经验性论述整合成了科学理论,图书馆员所从事的主要也是序化知识和指导用户掌握序化技能的相关工作。因而图书馆学在知识序化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方面,今后的图书馆学可以在序化知识方面尝试走得更远一些,不仅要对已经产生了的知识进行序化,即已有图书馆学理论中信息组织那一部分,还要制定一些知识生成的规范,即从源头上控制信息、知识(如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规范等)以及知识评价规范,当然也可以尝试对一般性社会活动特别是网络用户在网络日常活动产生的各类信息进行产生前、产生中与产生后相应规范的探索,还可探索信息自组织方面的问题。规范不是为了限制信息表达的自由,而是为了保障知识获取的公平以及知识使用的公正、客观。当然,对于图书馆等相关信息机构进行知识评价、组织等工作也会产生巨大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图书馆应当将知识序化的相关知识即图书馆曾经是怎样组织信息与知识以供用户使用的理论传递给用户,促使用户具备自助服务的能力,以期用户在自身产生、利用知识的过程中具备更多的主动性,从个性化的角度出发寻找最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那一部分知识。对于个性化需求的把握由用户个体自己掌控是为最佳,因为个性化需求的价值就在于个体的主观性差异,而这个差异是不大可能完全由独立于需求主体之外的“第三者”(图书馆或图书馆员)来界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书馆要满足所谓用户个性化需求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但是,引导个体找到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是可行的并且是正在进行中的,如信息素质教育)。因此,图书馆困境之解可以从对知识进行序化的两个角度来进行,一为图书馆序化知识,一为图书馆帮助用户序化自身需要的那一部分知识。
个体知识利用得越多就越能了解自身,越能明了个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目的,如获取知识、身心调整、社群交流等。这些不同的目的相结合其实对图书馆提出了又一个要求,即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作用。这一点在如今网络愈加便捷但人们却日渐疏远的当下具有更重要的社会凝聚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西方国家可能多以宗教场所作为公共空间,中国却没有类似的公共空间提供给人们进行共同交流、协调,网络虚拟空间或许能起到一些作用,但虚拟的感情交流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如今,中国社会面临严峻的道德缺失、核心价值模糊、教育薄弱等问题,图书馆可以考虑提供一个公共空间或者引导这种公共空间的构建以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和谐发展。
社会知识需求急剧膨胀,图书馆一时不能很好地应对,一些相关的结构或组织应运而生,如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库服务商等。这些机构或组织实质上是图书馆某些职能的深化,尤其是满足利用需求那一部分的职能。与其视他们为竞争对手,何不思考这些机构的运行机制对图书馆满足社会知识需求有怎样的帮助和启发?既然两者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知识需求而生,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与联系?将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走势发展,是相互融合还是继续分化,抑或是两者都脱离社会机构的实体性差别,形成一种能够可持续性满足社会知识需求的开放性机制?这个机制可不可能不断吸收其他类似的社会机构如学校、法院、医院等?前文已论述过,是信息技术冲击了社会知识需求进而影响到了图书馆,实际上,这种影响不仅仅波及图书馆,学校、医院、法院等都面临着类似的境遇。如网络课程、Mooc的发展使得有人预言学校终将“消失”,医院、法院等因为其专业知识外在化的发展趋势也难逃“消失”的命运。图书馆之所以在此类“预言”面前显得尤为脆弱,可能是因为图书馆所“占有”的是社会中最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知识,而图书馆员职业化建设亦因此一直暧昧不清。我们是不是需要超越到所有这些相关社会机构之上,尝试探寻一种社会机制来解读其所映射的社会机构或组织的发展历程与变革可能?这一社会机制是社会知识需求与各个相关社会机构之间的中间层,可用以实时分析与监控信息、知识需求状态的变化,辅助人们做出及时、正确、适度的反应,掌握信息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对社会知识需求的历史、现状、影响因子等进行分析,可能需要借助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传播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家族的“同志”们以及信息技术研究等的合力,从而帮助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挣脱“技术主义”“人文主义”的简单界定。
3结语
当今信息社会的图书馆及其服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应对来自新兴信息服务产业的各种竞争。我们不妄言永存,亦无需轻言消亡,而应当以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思考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真正目的,以社会知识需求为核心,尝试理清图书馆千年以来走过的道路,思考并规划图书馆未来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张会田.泛在知识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8:30.
[2][7] LiLi Li. Building the Ubiquitous Library in the 21st Century[EB/OL].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150.8398&rep=rep1&type=pdf,2014-02-10.
[3] Neal Kaske. The Ubiquitous Library is here[J].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2004,(2):291-297.
[4] 初景利,吴冬曼.论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以用户为中心重构图书馆服务模式[J].图书馆建设,2008,(4):62-65.
[5] Ken Chad, Paul Miller. Do Libraries matter: The rise of Library 2.0[EB/OL]. http://library. nust.ac.zw/ gsdl/ collect/ toolbox/ index /assoc/ HASH0190.dir/ Do% 20Libraries %20Matter. pdf,2014-02-10.
[6] Wendy Pradt Lougee. Diffuse Libraries: Emergent Roles for the Research Library in the Digital Age[M].New York: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2002.
[8] 张会田. 泛在图书馆: 如何从概念走向现实? [J].图书情报工作,2009,(19) :40-43,87.
[9][10] 黄纯元. 变与不变之间——读伯克兰德的《图书馆服务的再设计》[J].图书馆杂志,1999,(1):28-29.
[11] [13] 宓浩,黄纯元.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5.
[12] Lowell Martin.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s a Social Institution[J].The Library Quarterly,1937,(4):546-563.
[14] 黄纯元.寻求与社会科学的接点——读弗舍的《信息社会》[J].图书馆杂志,1998,(1):28-30,45.
(责任编辑:王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