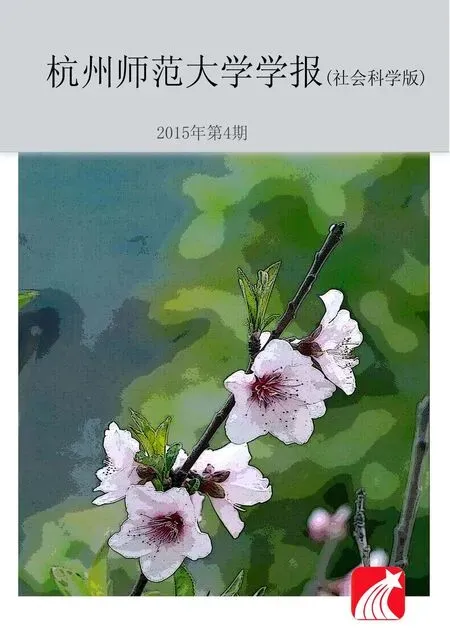同情及其超越
[英]罗杰·克瑞斯普著, 陈乔见译
(1.牛津大学 圣安妮学院暨哲学系, 英国 牛津; 2.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241)
哲学研究
同情及其超越
[英]罗杰·克瑞斯普1著, 陈乔见2译
(1.牛津大学 圣安妮学院暨哲学系, 英国 牛津; 2.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241)
摘要:讨论同情或怜悯这种情感及其相应的德性,可首先把同情这种情感置于道德概念图景中,经由批判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由玛莎·纳斯鲍姆发展出的一种亚里士多德版本的观点,转而支持同情作为情感的非认知性概念。由此可以勾勒出另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解释。同情之德性与其他德性的关系由此得以展开,同时也播下了同情之实践意义的怀疑种子。
关键词:同情;情感;德性;亚里士多德;纳斯鲍姆
同情(compassion)在情感(feeling)或情绪(emotion)①译者注:原文feeling和emotion经常同时使用或混淆使用,基本没有区别,本译两者一般都译作“情感”,偶尔分别译作“情感”和“情绪”。中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这同一英文单词既用于情感或情绪,又用于相应的德性(相比较害怕/勇气[fear/courage]、愤怒/和气[anger/even temper]、快乐/节制[pleasure/temperance而言)。这或许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感到同情总是或几乎总是值得赞赏的。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表明这种倾向的误导性,但首要目的在于考量这一情感或情绪本身的本质。
首先,让我试着把同情置于相邻的道德概念图景中。同情(compassion)与可怜(pity)、感同身受(empathy)和同情(sympathy)的关系如何?我简短提下亚里士多德关于同情的解释。亚里士多德的eleos的传统翻译是pity,不过,我跟随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②Nussbaum M.Upheavalsof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p.301-302.又见Kimball.APleaforPity.Philos Lit , 2004. p. 303, Kimball注意到,“pity”和“compassion”直到新近才大致同义。不取这一术语,部分是因为其屈尊或轻蔑的现代涵义。可怜现在也经常被认为是肤浅的和动机上无效的。一个人对乞丐感到难过,却忽视他们,这更应该说是感到可怜(feel pity);然而,一个人停下来去帮助他们却是感到同情(feel compassion)。斯蒂芬·夏皮罗(Stephen Shaprio)论残疾人公民权利的书《不要可怜》(No Pity )完全不能叫做“不要同情”(No Compassion)。[1](p.2)“感同身受”(empathy)的用法有时大略等同于“同情”(compassion or sympathy)。但是,我们应该再次留意纳斯鲍姆的有益规定,感同身受在于对他人经验的任何种类的想象的重构,而无关乎任何诸如它是好的、坏的或中性的评价。通常,感同身受的重构会涉及同情,但是,就我的理解,同情不一定需要感同身受,因为同情可以在他人的痛苦和悲伤出现时取得纯粹痛苦和悲伤的原始形式,而无需任何想象的重构(就像在婴儿的例子中)。sympathy和compassion的共同结构使得我们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存在一种微弱意义的同情(比如:“我赞同[sympathy]你的目标,但是……”);但是,如果就我们对他人苦境真正感到悲伤而言——正如18世纪哲学作品中经常谈及的那样——那么,sympathy与compassion就是一回事。然而,我们确实需要为这种情形留有概念空间,即我们消极反应,没有任何的感到悲伤。例如,想想亚当·斯密有关中国地震的例子,这是纳斯鲍姆自己[2](pp.360-361)讨论过的。1556年的中国大地震造成了830,000人的死亡,超过了任何地震的历史记录。彼时中国人经历的伤痛我断定非常糟糕,但是,一如斯密所言,做此判断并未导致我有“真实的心神不安”。类似地,人们经常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定期捐款,但对他人的遭遇没有任何地感到悲伤,仅仅是认为这样做是好事。我称之为慈善之事。
迄今为止,对同情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的。近来持续不断地对同情的考察,以一种修正的形式为此解释辩护的是纳斯鲍姆,首要的是她的《思想的剧变》(UpheavalsofThought)。[2]纳斯鲍姆的讨论含有许多洞见,但有几个亚里士多德立场的主要成分是有问题的,因为她总体上反对亚里士多德解释中的非认知性因素,而赞成斯多葛派有关情感的认知主义观点。她同样未能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德性之本质的总体解释,潜在地服务于一种更为综合与平衡的有关同情作为德性的观点。现在,在更为总体上反思情感在规范伦理学和知识论中的作用的结论之前,让我尝试为这些主张辩护。
亚里士多德对同情(eleos/compassion)的定义如下:
同情是对明显的坏事(evil)*译者注:这里的evil有“恶”、“坏事”、“不幸”、“灾祸”、“倒霉”等含义,本文译为“坏事”,因为“坏事”可涵盖以上所有情形。的一种伤痛,这种坏事具有毁灭性或令人痛苦,它发生在一个不该遭受(doesn't deserve)的人身上,并且,人们会料想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与己相近的某人身上,当它来临时。[3](PP.1385b13-16)*这段全文的英文翻译为作者自己所译。
此刻,我只要你们注意在此提到的包含在同情中的痛苦或悲伤。稍后对此会有详论。纳斯鲍姆[2](p.306)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发现了同情的三个“认知性必要条件”:(一)严重性条件:坏事(evil)*纳斯鲍姆的意思是指神学家所谓的“自然”的恶(“natural”evil)。必须被认为是重要的而非琐屑的。(二)应得条件:坏事必须被认为是不该遭受的。*Leonard Kahn向我指出,如果加上“或者比该受的更为严重”,那么,这个必要条件将会更加合理。(译者注:此所谓“应得条件”的实质是“不应得条件”。)(三)类似可能性条件:坏事必须是这样的事情,即正在感受同情的人可能认为这种事情会降临自身或与己亲近的某人身上。纳斯鲍姆接受前两个必要条件,但以其自己的另一个条件替换了“类似可能性条件”。我会拒绝所有四个条件。
首先,关于严重性条件。*它同样被Blum L.Compassion. In: Kruschwitz RB, Roberts RC.eds.Thevirtues:contemporaryessaysonmoralcharacter. Wadsworth, Belmont, CA,1987. p. 230; Snow NE.Compassion. Am Philos Q 28,1991.p. 198; Ben-Ze’ev A.Thesubtletyofemotions.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2000. p. 237所接受。Cannon指出,被认为是琐屑的事情通常并不琐屑,Cannon L.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 In: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Feministinterventionsinethicsandpolitics:feministethicsandsocialthe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D, 2005. pp. 99-100.纳斯鲍姆说,“我们不会”“可怜某人,他丢失了一件琐屑的物件,比如一只牙刷或一个纸夹,甚或是一件容易被替换的重要物件”。[2](p.307)然而,她继续引用了一份坎迪斯·卡拉克(Candace Clark)[4]在现代美国诉诸同情的研究中的调查对象谈及的“苦境”清单。[在此清单中]*译者注:方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便于读者理解,下同。除了贫困、疾病和萧条外,我们发现还有“车子麻烦、房屋麻烦(如漏水的屋顶)”和“不舒服(如……交通拥堵)”等。现在,可能是,人们不应该习惯性对他人感到同情,当他们遭遇挫折,而这些挫折与贫困、疾病和萧条相比似乎不过是琐碎的。但是,他们应该还是不该同情不是此时要讨论的议题。*又见Hestevold HS.Pity. J Philos Res 29, 2004.p. 334。尽管他区分可怜(pity)和同情(compassion),从而否定了前者的“严重性条件”。
同情是一种类似害怕或愤怒的情感或情绪,没有先天理由要求某个突然中断的临界点。针对他人的不幸,同情被感觉到,如果他们的不幸较小,那么,默认假定一定是同情感也将较小或微弱。请考虑下两个例子。其一,你从自行车上跌倒,你的腿被一辆路过的车压碎,你在创痛中。其二,你的指尖被订书机夹到,你有轻微的痛苦。为什么我们必须假定我对你在两个例子中的遭受所感到的伤痛形式反映了种类的不同而非只是程度的不同?*我这里使用复数,是因为感受同一情感有不同的方式:持续性、强烈性等等。
其次,关于应得条件。*可能更合理的条件是,惩罚不仅应得而且正当,因为从应得的惩罚不能得出它应当执行。这里请考虑下塔西佗有关尼禄对基督教的残暴行为的解释:“由此,甚至对应受惩戒性惩罚的罪犯产生同情,因为似乎他们被毁灭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满足一个男人的残暴”,Tacitus. Furneaux H. ed.Annals, vol 2, ClarendonPress, Oxford (2nd edn.,rev. Pelham H, Fisher C), 1907.15.44。纳斯鲍姆说,就我们认为一个人的苦境是其自身的缺点而言,我们会责备他们而不是感到同情。[2](p.311)也就是说,同情本质上涉及这样一种想法,即他人正在经受的折磨不是自作自受。[5](pp. 330,335)对我来说,这一看法是错误的,理由有以下三点。
首先,似乎有相反的例证。*又见Blum L. Compassion. In: Kruschwitz RB, Roberts RC.eds.Thevirtues:contemporaryessaysonmoralcharacter. Wadsworth, Belmont, CA,1987. p. 233; Carr B. Pity and compassion as social virtues. Philosophy 74,1999. pp.411-429 ; Hestevold HS. Pity. J Philos Res 29,2004.pp.333-352再次谈及可怜; Cannon L.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 In: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Feministinterventionsinethicsandpolitics:feministethicsandsocialthe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D, 2005.pp 97-110; Weber M. Compassion and pity: an evaluation of Nussbaum’s analysis and defense. Ethical Theory Moral Pract 7, 2005.pp.487-493.请考虑下《旧约》中的上帝,他的“同情并不缺乏”,“虽然他造成了苦难,但是他根据他的仁慈仍会有同情”(La.3.22,32,KJV)。*这个例子同样给纳斯鲍姆的以下主张提供了反例,即:“对自己造成的苦境哭泣纯粹是伪善”,Nussbaum M.Upheavalsof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313。然而,她可能被如此理解:伪善仅仅出现在起因该受责备的情形中。但是,我们会认为《旧约》中的上帝该受责备却不会控诉他伪善。也许同情要求旁观者相信他不会为坏事而受责备。但是,旁观者会后悔,然后感到同情。即便没后悔或遗憾,同样也是可能的。考虑下某人成功地从巨额的养老基金中骗取部分钱财。他会承认他所为是错的且该受责备,但并不后悔他的所为,也没有丝毫懊悔或自责的迹象。不过,当他反思其所为造成的不幸时,他会对那些由于其犯罪而带来的生活贫困的人感到同情。或者监狱访问者对囚徒的有同情心的关心,至少在一些案例中,这些囚徒认为他们被公正地关押。或者设想下,一个自身友善却因误解而犯了一项“无受害人”的犯罪,比如诈骗大型跨国公司;当此人走进牢房开始服刑(我们相信,完全应该)时,难道我们对他不会感到同情吗?或者对被其自尊所击倒的某人,比如安提戈涅的父亲克瑞翁,[难道我们不会对他感到同情吗]?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自己承认,我们会被极坏之人从好运跌入厄运的故事所感动[6](PP.1453a1-7),但是,亚氏这里所说的品质不是激发同情,而是博爱(philanthropon)。这里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不是完全清楚[7]( p. 47),但是,根据自然的友善,亚氏相信人对人能感觉到这种友善[8] (PP.1155a16-21),我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理解其意思。纳斯鲍姆自己在回应John Dengh时,承认同情这一情感有道德的与“非道德的”的区分,对前者的分析包含了应得条件,后者则意味着完全听从情感。[9](p.481)
这里引出我对应得条件的第二个反对理由。因为“完全”听从感情几乎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包含应得条件的解释结果证明是冗余的和太过复杂的。广而言之,描述情感与德性的最好方法其实就是广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把人的生活及其情感的各个方面划分为不同的领域,然后根据这种划分为核心的情感和德性提供解释。[10](pp.133-134,138-139)我说的是“广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亚氏自己有时表现出过度分析的倾向,背离了他作为一个植物学家的原初方法。例如,当他区分慷慨大方的德性(generosity,与给予和持有金钱有关)和高贵宏伟的德性(magnificence,与同一类事有关,只不过在规模上更大)时,亚里士多德获得了什么优势?[8](PP.4.1-2)又是什么阻止了他在每一领域中发明不同的“大规模”德性,比如“超级节制”(与大规模的肉体快乐和痛苦有关)、或者“超级勇敢”(与大规模的害怕和自信有关)?通常,通过放大同一单一领域中的情绪或情感什么也得不到。这当然是真的,我们对某人遭遇的关心可能会消失,当我们发现他是自作自受时。但是,那是有关同情的偶然事实,并不表明其他一些不同的情感或情绪也如此。请考虑以下类比:听从情感本身通常,虽然并非总是,受到厌恶的阻碍(这当然就是为什么纳粹宣传试图引起人们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的厌恶情感)。这一事实可以被充分考虑而无需假定两种类型的听从情感,仅有其中之一关乎非厌恶条件。
我的第三个担忧是应得条件代表着一种错误的注意方向。同情作为一种情感的核心是我们对他人之不幸或苦难所感觉到的。*正如Brad Hooker向我指出,我们应该把“苦难”理解为“对某人是坏事”。不需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精神状态。任何否认这一点的解释最好被理解为是在讨论其他一些情感,如义愤,或者其他德性,如正义。如果我们承认对他人苦难的关心是贯穿不同类型的同情的主要方面,那么,我们全部要做的就是说出这些不同类型中的异同,并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如那些所谓的情感或情绪之间的界限问题。纳斯鲍姆自己关于情感之本质的认知解释,就经常引起了这种类型的困难。纳斯鲍姆假定任何一种状态,如果要把它视作一种情感,需要满足不同条件(后文对此有详论),这样一来,她被迫在道德同情、非道德同情(与道德情感一样,但缺乏应得条件)与机械地听从情感(feeling)(这根本不是情感[emotion])之间做出区分。[9](pp.482-483)但是,所有这些最好被理解为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化而不是尽管相关却分离的情感。
现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三个条件:类似可能性条件。[11](PP.101-102)亚里士多德谈及它的两种含义。有两种人不会感到同情,一种是完全被毁灭的人,他们相信不可能再遭受进一步的坏事;一种是认为自己生活很幸福且无法被摧毁的人。[3](PP.1385b19-23)然而,首先请考虑下晚期病人的例子:他相信自己几小时内即将死去,但他头脑免于身体痛苦的制约,很清醒,她正在观看一些毁灭性自然灾害的电视新闻报道;看到那些人的遭遇,她深深地被感动了,尽管她真的相信她现在经历这种灾害的几率是极小的。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会好运的人又怎么样呢?根据亚里士多德,他们对他人之苦难的反应将会是傲慢的。
这里请考虑下一个斯多葛派者,他认为唯一的善好在于德性以及他总是且将总会有德性。难道他对其他人不会感到同情,这些人(自身也许完全没有缺点)最终处于邪恶的状态?一般而论,亚里士多德和纳斯鲍姆为同情描绘了一种太过细节化的认知背景。实际上,你不需要认定所有那么多才会感到同情,正如我们在下面讨论非人类中的同情时将会看到的。
类似可能性条件奠基于亚里士多德所假定的同情与害怕之间的联系,他说:“人们对他人感到同情,当他们自己所害怕的事情发生在他人身上时”。[3](PP.1386a27-29)大卫·康斯坦(David Konstan)很棒地解释了亚里士多德如此联系的理由。亚里士多德以假定同情是一种感觉开始,这意味着它要么与快乐要么与痛苦的感觉相关。在此例子中,当然是痛苦,亚氏引入与害怕的关联来解释痛苦:对临近的伤害的料想和印象是一种对痛苦的微弱感知,它本是痛苦的,但程度上次于直接和当下的经验。[1](p.134)[2](p.316)。
亚里士多德应该会承认的是,一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乎自出生就存在于人类和其他动物*例如,见Konstan D.Pitytransformed. Duckworth, 2001. p. 14,参 Hoffman and to Denham;Sherman N. “It is no little thing to make mine eyes to sweat compassion”: APA comments on Martha Nussbaum’s upheavals of thought.PhilosPhenomenolRes68,2004.pp. 463-464,nn. 6-10;De Waal F. Morality and the social instincts. In: Peterson GB.ed.Tannerlecturesonhumanvalues25.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Salt Lake City, 2005.pp.16-22;尤其是其中引用Carolyn Zahn-Waxler的研究:一岁多的小孩会对明显处于痛苦中的他人提供安慰,以及有证据表明老鼠和猴子中有同情(其中包括倭黑猩猩对一只鸟的安康表现出具有理解力的关心的著名例子)。关于神经科学对情感的论述,见Panksepp J.Affectiveneuroscience:thefoundationsofhumanandanimalemo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4:“许多古代人演化地获得了所有哺乳动物所共有的大脑系统,它依旧为人类心灵深刻感受情感的倾向起了基础作用。这一大脑系统在具有大量认知技巧的人类新大脑皮层出现之前已经演化了很长时间。”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自身感受痛苦和心爱某人所感受的痛苦意识激活了同一种大脑中的情感痛苦电路(Singer T, Seymour B, O’Doherty J, Kaube H, Dolan RJ, Frith CD Empathy for pain involves the affective but not sensory components of pain. Science 303,2004.PP.1157-1162; Singer T. The neuronal basis and ontogeny of empathy and mind reading: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Neurosci Behav Reviews 30,2006.PP.855-859)。 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证据开始使得对诸如同情这种情感的认知主义解释的倡导者坚持对痛苦本身也可能采取认知主义的解释。中的一种被其他存在的不幸或遭受坏事直接感动以及可能即刻感到伤痛的自然能力。
考虑到潜藏在亚里士多德“类似可能性条件”背后的同情与痛苦感之间的联系,纳斯鲍姆自己拒绝了它而以下面第四点来替代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四)好生活(eudaimonistic)判断条件:正在感受同情的人必须把坏事视为他自己目标或目的之规划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2]( p.319)
纳斯鲍姆宣称,即使在一些情形中,反思某人相似的脆弱性有助于“好生活的想象”,但是,这种判断能够被做出而无需明确聚焦于他人与判断者的关系:真正的全知全能的神应该知道人类受难的意义而不会考虑它自己的风险或坏前景,真正有爱的神会热切地关心降临凡人身上的疾病而无需过多考虑个人的损失或风险。*一个比意向性版本较为温和的弱版本的好生活判断条件,可以基于纳斯鲍姆这里所说的建构起来,它会主张:一个人一定不乐意把坏事视为她的目标规划的无意义部分。但是,即使这个版本仍然受到下文反例的挑战。
好生活判断条件来自对情感更为总体的好生活解释。[2](pp.31-33,49-56, passim)因此,如果这个条件在同情的例子中是可疑的,那么,它就会给这一总体的解释带来困难。对我而言,“类似可能性条件”的那个反例,略加改编,就能很好地适用于好生活判断条件的情形。*进一步的批评,见Deigh J. Nussbaum’s account of compassion.PhilosPhenomenol Res 68, 2004.PP.465-470;Cannon L.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 In: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Feministinterventionsinethicsandpolitics:feministethicsandsocialthe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D, 2005.pp102-103.因此,首先考虑下我们的晚期病人,你会记得,他相信自己只有几小时的生命。设想他现在处于这样的状态:太累了而不能从事哪怕是轻微费力的活动,唯有等待生命的结束。从他自己和他人的角度看,他的“目标或目的之规划”几乎萎缩到零。他不可能把他电视上所看到的那些人遭遇的坏事视为“正在影响他自己的好生活”,因为他一生中的任何好生活都成过去。但是,我找不出什么好理由来否定他被同情所感动的可能性,这种同情与任何其他人一样深沉。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那个斯多葛派者,他相信其好生活正处于最大可能的程度,而且不受时运变迁的影响。现在假定继续这种好生活的德性操练是有关心灵的理智德性:对他而言,所有的事情就是沉思。进一步设想他为之感到同情的那个人是一个完全缺乏严肃思考的人。现在的情况可能是,这位斯多葛派者为此人不能与他哲学对谈这一事实而遗憾。但是,让我们设想他认为,沉思最好是独自一人,又或,无论如何他有充足的机会与别人交谈。换言之,没有明显的方式,在其中,影响他人的坏事影响或能够影响到他自己的好生活。难道他不会感到同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会?因此,我认为,姑且不论纳斯鲍姆拒绝了类似可能性条件的事实,我们看到纳斯鲍姆与亚里士多德一样未能理解亲身的、直接感知的同情他人的本质和意义。
根据纳斯鲍姆,一种感受要是同情必需满足三个条件:严重性、应得和好生活判断。我已证明,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必需的。但是,它们三个集合在一起是充足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纳斯鲍姆自己对同情的解释(不采纳亚里士多德对痛苦的强调)可能是对的,而且,她受斯多葛派影响的认知主义解释至少在此情况下是正确的。
在纳斯鲍姆为其主张(即满足三个条件对同情来说是充足的)辩护中最有意义的工作是严重性条件。[2](pp.322-327)她承认斯多葛派圣徒可能具有我们所说的“人道关怀”,他的感受满足第二、三个条件,但是,这样的圣徒将会否认他人的不幸具有重要意义。相反,如果我们设想一个自足的存在,他真的深切地关心世事变迁,并且真的认为那是一件大事……那么,我认为我们确实想说三个条件不仅对人道关怀而且对激起那种情感本身[即同情]都是充足的。[2](p.325)
请注意纳斯鲍姆的自足的存在不只认为时运变迁是件大事,这对她而言足够满足严重性条件。自足的存在关心世事变迁。*稍后,在讨论涉及同情的“痛苦”应该是何种类型,纳斯鲍姆问道:“但是,这种精神痛苦是什么,如果不是把受难者在意的不幸视为一桩可怕之事?”(Nussbaum.Upheavalsof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326)再次,[纳斯鲍姆]把关心(或在意)的情感与认知某事是坏的结合在一起。这对我来说似乎更加难以否认其感受满足所有三个条件且怀有关心的某人不是感到同情这一情感,因为在感受同情之“痛苦”的意义上而言,同情的一个明显(虽然不是唯一的)显示便是关心。问题是,纳斯鲍姆这里所设想的自足的存在是否可能做出严重性判断而不会有那种方式的关心。无疑,他可以——反思下我们自己对远距离事件(如亚当·斯密的中国地震例子)所做的判断,我们发现有这种可能。换言之,某人的判断可以满足严重性条件而不会形成好像同情特征的那种关心。
纳斯鲍姆问道反认知主义者头脑中的痛苦是什么类型。她认为,如果是像胃痉挛的某种东西,那么,坚持认为任何如此特殊的痛苦在每一同情的情形中都得到呈现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感受情感的方式不同,或物理地感受,或现象学地感受。这似乎是对的,某人可以补充说,一旦我们把全部的同情感受纳入考虑范围——比如从婴儿听到其他婴儿哭声的同情感受到古希腊悲剧见广识多的阅读者的同情感受——其方式还会更具多样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坏事中的痛苦*比较下Peter Goldie的“朝向[某人]感到”(feeling towards)的观念Goldie P.Theemotions:aphilosophicalexploration. 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 pp. 4, 16-28, 58-62, 72-83,also Deigh J.Cognitivism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s. Ethics 104,1994.PP.837以及参考Greenspan and Roberts; D’Arms J, Jacobson D. The moralistic fallacy: on the “appropriateness”of emotions. Philos Phenomenol Res 61, 2000.p.67,n.4。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现——纯粹原始的不适、关切、焦虑,诸如此类。但是,对我而言,斯密称之为“人性中的原初(情感)”(斜体为笔者所加)是对的,它们都是为他人之遭遇和苦难而几乎普遍性地感到伤痛的形式,这解释和证明了它们可以被归在“同情”这一单一的类目下。
另一个纳斯鲍姆所使用的总体上反对非认知主义者的证明,在同情的例子中,是基于她所说的“无意识”情感的可能性。[2](p.326, passim)她认为某人可能有同情但却没有意识到它,比如,当人们不反思其情感时,或者被引导认为真正的男人感觉不到它:“人们可以很好地被思想所驱动,而不会处于任何可觉察的现象学状态”。
然而,无意识同情对反认知主义者来说并不是个问题,因为无参与的痛苦现象是普遍的且很好地被证实了的。*关于这一普遍现象的绝佳例子,见Goldie P.Theemotions:aphilosophicalexplora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2000. p. 62;öhman A, Flykt A, Lundqvist D. Unconscious emotio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psychophysiological data, and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In: Lane RD, Nadel L.eds.Cognitiveneuroscienceofemo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0. pp.296-327提供了一种进化论的解释。实际上,分散注意力的技术是标准的治疗痛苦的方法。痛苦还是一样,但由于主体较少注意它而更多注意其他事情而变得较少痛苦。*这种解释对于快乐和痛苦的所谓“内在主义”概念来说更为合理,据此种概念,有某种东西类似现象学地贯穿每一种感受。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标准观点,我在Crisp R. Reasons and the good. Clarendon Press, Oxford,2006.ch. 3. and Crisp R. Hedonism reconsidered. Philos Phenomenol Res 73,2006.PP.619-645为其提供了一些辩护。
总结一下,我已经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和纳斯鲍姆施于同情的各种认知条件是错误的,以及证明了同情的核心在于对他人痛苦或悲痛的非认知因素的痛苦或悲痛。我们可以把纳斯鲍姆的解释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的开场白做一比较:
无论人如何自私,其本质中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则,这些原则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使他们的幸福对他而言成为必要,尽管他从中没有获得任何东西,除了领会它所带来的愉快。这就是怜悯或同情,即我们对他人之不幸而感到的那种情感,当我们要么看到他人不幸时,要么我们通过一种鲜活的方式确信他人不幸时。[12](p. 8)
同情是斯密所恰当的称为“人性的原初情感”之一。在其最原始的形式上,就像婴儿似乎悲伤于其他婴儿的哭声(所谓的“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13]),这种本能的悲伤与其说是由他人之遭遇引起,不如说是置身于他人的遭遇。当它发展后,它会经常涉及(或作为原因,或作为结果)各种不同的其他认知的或非认知的状态,诸如这样的信念:失去伴侣是悲伤的、缓解痛苦的欲望、或者不要碰上坏事的愿望。*比如,见Hume D.Green TH, Grose TH.eds. A dissertation on the passions, in his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new edn, vol 2. Longmans, London, 1889. p.157,他把同情定义为对他人幸福的欲望;Piper AMS. Impartiality, compassion, and modal imagination. Ethics 101,1991. p. 743;Snow NECompassion. Am Philos Q 28,1991. p. 197; Carr B. Pity and compassion as social virtues. Philosophy 74,1999. pp. 411, 414; Goldie P. The emotions: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Clarendon Press, 2000. pp. 213-214.; Cannon L. 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 In: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ethics and politics: feminist ethics and social the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D,2005.p.103.但是,即使是最后一项对非原始的同情来说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对接受应受惩罚的人的同情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像害怕或愤怒一样,同情是基本的人类情感,在所有这些情感的例子中,我们不应当被这样的事实所误导,即它们经常以微妙和复杂的形式被感觉到,或者由于复杂的原因而以过分狭隘的和认知主义的方式来看待它们。*这里提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们在非人类的动物中经常发现这种类似的复杂的人类情感(Aristotle.Balme DM.ed. Historia Animalium, bks.7-10. Loeb, Cambridge, MA,1991.8.1, 588a18-b3)。
现在我们转向讨论同情的德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谓“中道”(doctrine of the mean)的陈述中,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些与情感相关的品质德性(virtue of character),如:害怕、自信、欲望、愤怒和同情。[8](PP.1106b18-19)令人失望的是,仅仅前四者在“勇气、节制与和气”的标题下被详加讨论。但是,中道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藉此可以建构我们自己[对同情]的解释。就这些情感而言,亚里士多德继续说:在恰当(right)的时候拥有它们,关于恰当的事情,朝向恰当的人,为了恰当的目的,采取恰当的方式,就是中道和最好的,这也是德性之事。类似地,在行动中有过度、不及和中道。德性关乎情感和行动,其中过度或不及没中目标,而中道则被赞扬并切中目标,两者都是德性的特征。[8](PP.1106b21-27)
这份情感清单误导了很多评论者去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每一德性都涉及一种特殊的情感,而且,每种德性的领域都根据那种单独的情感来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例如,慷慨的领域是金钱的赠与或获取,它非常清晰地具体化了亚里士多德这里所陈述的观点,即德性既关乎情感,也关乎行动。因为德性是一种涉及理性选择的状态[8](P.1106b36),任何德性一定既关乎情感,也关乎行动。因此,有同情心的人不仅感到同情,而且也同情地行动。
当他寻求理解人性时,如前所言,亚里士多德的一般方法是,寻找人类生活中广泛而有意义的领域,然后对每一领域提出合适的解释。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方法在德性中的运用:亚里士多德这里提到的情感或情绪对于任何人而言全部都是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因此,任何人都需要知道他们应该如何去调节。
由于亚里士多德把每一种德性置于过度或不及之间,许多人被引导认为,总是有两种恶德对应于每一德性。这是另一种误解。没中目标有很多种方式,尽管每一种方式结果证明是要么是过度的形式,要么是不及的形式;但是,我们可以在任一形式或两种形式中都发现大量的恶德。[8](PP.1126a8-31)这并非事实——再次,它经常被这样认为——即每种品质都可以被安置在过度与不及的范围里。[实际上],一个人的品质可能同时结合了过度或不及,以至于这个人最终有两种相反的恶德。这一点在慷慨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向错误的人赠与金钱(这是过度)很可能导致此人不能向恰当的人赠与金钱(这是不及)。[8](PP.1121a30-32)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同情这一情感。其德性在于倾向于对恰当的事情,在恰当的时间等等感到同情。什么是其过度呢?具有吸引力的看法是——部分是因为当他给出他的清单时,亚里士多德言及“太多或太少”地感受这些情感——它必定在于倾向于感到过多的同情,再次,许多评论者沿此思路进行思考。但是,实际比这更为复杂:亚里士多德提到的事实不仅仅是数量性的,而且涉及(例如)在恰当的时间感到这种情感。在错误的时间感到同情,这可能是过度的一种形式。但是,也有可能在恰当的时间感到同情同样错误,那是不及的一种形式。同样地,在其他条件下:例如,对恰当的人感到同情,将会是有德性;然而,对错误的人感到同情将会是过度,而对恰当的人未能感到同情则是不及。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同情的例子中目标有多种方式。不幸的是,不及总是比较常见,我们可以叫它“麻木不仁”。考虑下某些人当他面对遭遇灾难的人群图像时未能感到同情。他们未能感到同情,因为他们应该同情,在恰当的时间,就恰当的事上,对恰当的人群,为了恰当的目的。假如他们感到一阵轻微的同情,除此外再也没有什么,那么,他们就是在恰当的方式上未能感到同情。过度的恶较不常见,因此,很少听到“过度同情的”这一术语。*例如,见http://www. deathwithdignity. org/ voices/ opinion/ lewrockwell.11.14.05.asp;以及韦伯(Weber M.Compassion and pity: an evaluation of Nussbaum’s analysis and defense. Ethical Theory Moral Pract 7,2005.p.507)有关尼采对同情之态度的讨论。但是,某人向残疾人显示屈尊或不恰当的怜悯,这是向错误的人,在错误的时间感到同情。在此例子中,对残疾人的同情是需要的,但是,旁观者对残疾人感到可怜仅仅是因为他们如何看待残疾人(而不是因为通过他们如何看待残疾人而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责任),那么,这就是在错误的事情上,以错误的方式感到同情。某人或许在恰当的时间,在恰当的事情上,向恰当的人,在恰当的程度上感到同情,但是,她这么做,是因为她通过反思自己是如何有爱心,从而享受她获得的自我满足;那么,这种同情就是为了错误的目的或出于错误的理由。
在对单个德性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炼了恶德的种类。例如,在和气(even temper)的例子中,他注意到一个人可能很快地愤怒,或者持续很长时间,超过了恰当的时间。[8](PP.1126a13-20)很快发怒的人是易怒的,甚或是暴躁的,但是他至少很快又平静下来;而愠怒的人却保持愤怒很长时间。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过度同情的不同形式的模型——很快或很容易感到同情的人,与极端地不容易感到同情的人相比,后者一旦感到同情,就会沉湎其中而不忍离去。
同情的德性如何调节行动?作为德性的同情与勇敢、节制、和气属于同类范畴,因为其领域首要地是根据情感而非行动来描述。与此相对照的德性如慷慨、诚实守信,其领域分别是根据赠与或获取金钱、对自己真诚来描述的。我们可以称其为情感中心的德性与实践中心的德性(pathocentric and praxocentricvirtues)之间的对照。情感中心的德性的行动特征本身应参考适当的情感来描述。因此,勇敢的行动将会是某种具有适当地感到害怕特征的行动。例如,某人感到过度害怕,很可能使得他不该逃跑时逃跑了;而某人感到不害怕,将会促使他鲁莽地冲入敌人的阵线。同样,具有同情德性的某人,将会以他恰当地感到同情的方式来行动。他将以恰当的方式,提供恰当类型的帮助,而不是忽视他人的苦境,或者提供错误类型的帮助,比如以他的关心来溺爱他人。
关于同情的德性及其诸多相应的过度或不及的恶德形式,还可以讲更多,但是,我相信,我在这里所说的已经足够表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是如何提供有用的模型来安置我们所讨论的不同的品质状态。我当然稍微修正了亚里士多德对情感的解释,但是,我把德性置于他的中道框架中讨论,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即这一德性如何与其他品质德性相关。可以找到交集点的明显地方是友谊的德性,它既不是情感中心的,也不是实践中心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九章对此德性的长篇讨论中,亚里士多德把它与正义相关联,因此,人们会认为它面临正义德性在中道中所面临的同类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似乎没有情感或行动能够被中性地描述并且如此适合于中道的框架[14](pp.83-93)。但是,在友谊中实际上有中性的因素,尽管其解释比在其他任何德性的情形中更为复杂。比如,互相的善意是友谊的特征,正如表达敬意,在每一次实例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人在过度或不及的方向上是如何错误的。例如,对错误的人感到善意,或者未能以恰当的方式表达敬意。进而,很容易看出同情的情感与行动是如何与友谊密切相关。对恰当的人,以恰当的方式感到同情,经常被发现与善意相连。在互相支持和增援的关系中,同情所需要的行动通常就是友谊所需要的行动。
亚里士多德自己宣称,同情需要距离,在坏事降临亲近之人的情形中,我们感到的是害怕:因为这个理由,他们说,雅玛西斯(Amasis)在看到其儿子被带向死亡时没有哭泣,但是在看到其儿子的朋友乞求时却哭泣了。后者激起了同情,前者则是恐怖。恐怖之事不同于激起同情的事。它容易赶走同情并通常促使产生其对立面。*见Herodotus. Hude C.ed.Historiae. Clarendon Press, Oxford,1908.3.14。亚里士多德似乎混淆了雅玛西斯和他父亲。相关讨论,见Ben-Ze’ev A.Thesubtletyofemotions.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2000.pp.342-343。[3](PP.1386a20-24)
亚里士多德在此有关恐怖的说法是对的,但是,他把恐怖与坏事发生在亲近的人身上相关联则是错误的。发生在某些陌生人身上的恐怖同样会使我的同情能力瘫痪,至少是暂时性的。在初始震惊平息之后的情形中,对亲近的朋友或亲属会感到同情。设想下雅玛西斯的儿子,不是被拉去处决,而是死于罹患数月的疾病。
另一个与同情密切相关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慷慨大方及其同类高贵宏伟,后者本质上是大规模的慷慨大方。正如我提到的,慷慨大方没有情感特征,但是,慷慨大方的行动通常为同情所促使。在其他德性的例子中,重叠较稀罕:勇敢、节制、和气、才智等等。但是,这些德性经常起到了执行者的作用,促使具有同情心的人感到同情或同情地行动,当他们应该如此时(例如,战场上的勇敢、私人生活中的和气)。
最后,同情如何与善良(kindness)、仁慈(benevolence)或行善(beneficence)的德性相关,这些德性在当代德目表中当然比亚里士多德那里占据更为突出的位置?一旦去掉严重性条件,在下面的方式上,同情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善良的一种。同情的焦点在于他人的苦难,而善良的范围则更宽,以至于善良之人会很好地被驱使去帮助已经做得很好的人去做得更好。然而,同情被认为只有在此种情况[即有苦难观念的呈现]下才会感觉到,[比如下面这两个例子]。考虑下Scott Hestevold的丢失彩票的绝佳例子: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即你曾经赢得一张全国性彩票,但是你没有检查你的号码而未能索取奖金。我也知道,虽然你做得很好,但是有些时候,你无能力赠送你的伴侣你想给他的礼物,或者向你的孩子提供你认为最好的教育。当我设想你的生活[因为中奖]本可以发展得更好时,我会对你感到同情。但是,即便在这里,苦难的观念还是呈现了。你已经从损失中受苦并且还得受苦。但是,麦克塔伽(J.M.E. McTaggart)的猫又如何呢?麦克塔伽据说对他的猫感到可怜,仅仅因为它是一只猫——从猫的标准看,它的生活本该可以更好。然而,即使在这里,我想如果我们要对麦克塔伽做一有意义的回应,我们也可以以苦难来给予回答。他的猫受苦于它没有更高的品质(这是猫本可有的,比如大脑本可发展得比目前好)。那是一种古怪类型的苦难,但是,也许麦克塔伽的同情就是一种古怪的同情。
善良很好地涉及同情这一情感,并被它所促使而行动。但是,善良更加宽泛,不仅在于善良之人无需经由回应他人苦难而被驱使去帮助他人,而且在于善良可以在行动中被单独地发现,这种行动被纯粹的义务感而非体贴的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关心所驱使。如此,善良或许是实践中心的,它的焦点是帮助他人。仁慈,即一般地愿望他人进展好,不可能是实践中心的。愿望也不是一种情感。因此,我们这里需要其他范畴,或许可以叫做欲愿中心的(orexocentric)或基于愿望的德性(wish-based viryues)。这一范畴可涵括希望和仁慈。
具有同情心的人会感到同情并同情地行动,去减轻他人的苦难和不幸,在恰当的时间,向恰当的人等等。但是,这里的恰当(rightness)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完全开放性这一事实表明,德性伦理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是如何在两个层面发挥功能:形式的和实质的。在形式层面,我们有中道。在实质层面,我们有具体的理论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情形下什么使得情感和行动是恰当的。亚里士多德自己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区分,他说,提供中道作为一种实质性的伦理建议,就好像告诉病人他应该接受医学所要求的治疗一样。[8](PP.1138b18-34)在高尚(noble)观念的中心,他确实提出了一种关于恰当的理论,但是,当涉及亚里士多德的有德之人会像什么时,结果表明他(广义而言)很符合亚里士多德自己时代的贵族理想。这种依附于常识道德中的守旧观念在当代德性伦理学家的著述中也能看到,他们倾向于为常识道德辩护,并反对更为激进的不偏不倚的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的理论。但是,在形式层面,没有什么会阻止功利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提倡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参照体系。
那么,伦理学理论是否应该寻求吸收同情,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常识道德中所理解的那样?很清楚,关于同情,有很多值得赞赏的。同情使我们领会他人正在受苦,领会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一桩事,以及一般而言同情促使行动做得更好,有时比不行动做得更好。但是,同情具有偶然的演化和文化历史的因素很明显,尽管对于其历史是什么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因此,我们应该对此主张表示怀疑,即同情完全精准地追寻到了伦理学的真理。
考虑下以下四种方式,在其中,同情可能不可靠。*参Slote M. Moral sentimentalism and moral psychology. In: Copp D.ed.Theoxfordhandbookofethical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6.pp.227-228有关Batson and Hoffman的论述。Slote自己倾向于接受这些“偏见”(bidses),或者用他自己的词“偏好”(preference),承认他的道德动机的理想形式是完全发展了的人类的感同身受(empathy)。这里的要点是,一个人的规范性认识论至少受其一阶观点的影响。在一阶层面认为不偏不倚性合理的人不太会接受带有偏向性的情感在认知上是可靠的。其一,它具有偶然性。取决于早上我什么时候打开收音机或我阅读何种报纸,我可能被感动去帮助一些有关精神健康的慈善团体,如PDSA,或者帮助身边需要手术抢救的人。其二,它的线索通常绕过了理性。一部电视上的灾难片比报纸上颗粒状的图像可能更加感动我,年纪轻的小孩的图像比年纪稍大的小孩的图像可能更加感动我,小孩眼睛的图像比其整个身体的图像可能更加感动我——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我亲近的人的苦难比远距离遭受更大苦难可能更加感动我(比如斯密的中国地震例子)。与此相关,其三,同情被触发是根据这些苦难与观察者的亲近关系如何,这取决于观察者的感知。这里,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为同情的缺乏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在其中,纳粹]就好像对待高级灵长类动物那样做了很多实验。其四,同情有各种各样不确定的障碍。我就“应得条件”已经讲了许多,在许多情形下[如前文所说的自作自受],它们被普遍正当地认为妨碍了同情。*这个和先前的观点再次得到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证据的支撑,见Singer T. The neuronal basis and ontogeny of empathy and mind reading: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Neurosci Behav Reviews 30,2006.p.859。这似乎继续是错误的,不仅对于那些发现自由意志论或“软”的决定论难以接受的人来说,而且对于这样一些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自由意志问题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应该暂时假定那些犯了所谓错误的人没有错。另外几乎普遍的妨碍同情的是我们倾向于服从权威。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实验的受测者中,当他们的“受害者”伴随明显痛苦而尖叫时,大多数人继续提升电压,小部分人的反应是紧张地笑出来。①译者注: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服从权威,而在面对他人遭受苦难时较少表现出同情。
因此,同情本身不可能为我们的义务(就回应他人受苦而言)提供深刻理解的可靠来源。同情可以让我们对苦难有所警觉,并且经常提供一种可敬的动机来源去减轻它。但是,由于它的不可靠性,我怀疑最终真正有德之人感到的同情不会格外强烈,或许相当稀薄,他会通过如何尽己所能去帮助的理性思考来回应减轻他人的苦难。②就先前草稿和讨论的评论而言,我要感谢Fillenz, Leonard Kahn, David Konstan, 以及2007年英国伦理学理论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Ethical Theory)会议的参与者。
参考文献:
[1]Konstan D.PityTransformed[M]. London :Duckworth , 2001.
[2]Nussbaum M.UpheavalsofThough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Aristotle.ArsRhetorica[M]. Ross WD.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9.
[4] Ben-Ze’ev A.TheSubtletyofEmotion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5]Clark C.MiseryandCompany:SympathyinEverydayLife[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6] Aristotle.DeArtePoetica[M].Kassel R. ed.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65.
[7]Konstan D.PityTransformed[M]. London :Duckworth, 2001.
[8]Aristotle.EthicaNicomachea[M]. Bywater I. ed. Oxford:Clarendon Press, 1894.
[9]Nussbaum M.Responses[J].PhilosPhenomenol,2004,(68).
[10]D’Arms J, Jacobson D.The Significance of Recalcitrant Emotion (or Antiquasijudgmentalism)[M]//PhilosophyandtheEemotions,RoyalInstituteofPhilosophysuppl. 52.Hatzimoysis A.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Cannon L. 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M]//FeministInterventionsinEthicsandPolitics:FeministEthicsandSocialTheory.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 Lanham, MD: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12]Smith A.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M]. Raphael DD, Macfie AL.eds.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76.
[13]Hatfield E, Cacciopo J, Rapson R.Emotionalcontagion[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Williams B.JusticeasaVirtue,repr.inhisMoralLuck[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责任编辑:吴芳)
Compassion and Beyond
Roger Crisp1, tr. CHEN Qiao-jian2
(1. St. Anne’s College & Faculty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UK;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a discussion of the emotion of compassion or p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virtue. It begins by placing the emotion of compassion in the moral conceptual landscape, and then moves to reject the currently dominant view, a version of Aristotelianism developed by Martha Nussbaum, in favor of a non-cognitive conception of compassion as a feeling. An alternative neo-Aristotelian account is then outlined. The relation of the virtue of compassion to other virtues is plotted, and some doubts sown about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Compassion; emotion; virtue; Aristotle; Nussbaum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7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59-10
作者简介:罗杰·克瑞斯普(Roger Crisp,1961-),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暨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研究;陈乔见(1979-),男,云南陆良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伦理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