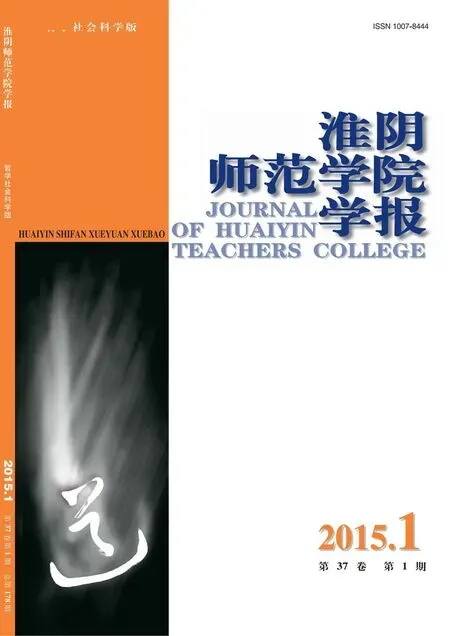略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阶段性发展
谢辉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者对此做出过富有价值的阶段性考察,丰富了我们对这个过程的理解。①参见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仲清等:《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宋学勤:《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而如果从中共党史撰述主体理论思维的发展趋势来考察,或许能为我们带来一点新的思考。事实上,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性认识很早就出现了,此后在一代代党史学人的著述中不断发展,直至今日,这种努力已经取得相当显著的成就。大体而言,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进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早期中共党史著述中史学理论的肇始(1924—1940年)
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21年瞿秋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和张太雷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两篇文献②详见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开端的分析。另外,也有人将陈公博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视作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早开始,因考虑到该文较为特殊,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但说到有明确的史学发展意识的最早著述,则要算是蔡和森1926年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此后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1930年),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1930年),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方志敏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1935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7年),叶蠖生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史》(1939年),李致工的《中国共产党史略》(1940年)等,都或多或少对党史撰述的价值、方法等作出过论述。
在1924—1940年间,中共党史的撰述者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所撰写的是回顾、记录与反思中共过往历程的史学作品,明白自己的著述活动所具有的价值,并希望以此贡献于革命事业,这从他们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史”即可看出。如张静如先生所说,作者们靠的是“个人的体验和理解”去说明党史,堪称“独断之学”,“大都有鲜明个性和风采”[1]13。在这些著述中,党史研究的理论性论述还不够明晰,也没有形成专论或专著,但已经提出了一些颇为可贵的理论认识。首先,他们对党史研究的功用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四项内容:
(一)党史研究能让大家了解党的历史,明白当前运动及其在将来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从而明确自己的责任。蔡文指出:“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他又说,我党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的,“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的”。同志们要做一个好党员,第一须明白自己的责任,“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2]2。在蔡看来,对党的历史的深刻了解必能深化对当前奋斗的意义的认识。1930年李立三谈论研究中共历史的意义时则强调:“党史对于目前政治路线和革命前途有绝大关系,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2]204这里,李不仅将党史研究的意义引申到当前,还延伸到未来,强调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然而无论他们所强调的意义为何,都是为了让现在的人能担负起当前革命的责任,这就恰如何干之在1937年所说的:“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认识,使人不得不放大眼光追寻着中国过去的历史。其实也只有深一层打开了历史的秘密,才能更彻底更明确的了解现在,追求将来。”[3]182
(二)党史研究能为党提供经验、教训上的借鉴,由此推动革命的继续前进。邓中夏在述说自己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的缘由时,强调这是为了“论述‘革命底经验’”[4]423。而华岗著述的起意则是“觉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5]3。如此,才能“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这便是我在百忙中编著本书的主要用意”[5]10。同样,方志敏之所以在狱中还要作“临死前的一滴努力”,动机之一就是要给后人留下革命的史鉴,他说:“我们从困难中甚至从许多错误中做出来的工作成绩,虽不能自满,却应写出来告诉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同志,以供他们的参考。我们做错了的,他们不再做;做对了的,他们可以效法做;遇着□□□遇着的困难,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6]198《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是如此,胡华在评论该书时就认为:“最精彩之处,应该说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分析。”[7]420
(三)党史研究能回击敌人的诋毁,粉碎抹黑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谰言,以事实说明革命的成就。华岗著书的重要背景,就是1929秋,托陈取消派攻击国际和中共,“不但不愿正确地去了解大革命的教训,而且还想一手推翻历史的事实”,因此确信“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由是“便又鼓励了我编著这部革命史的勇气”[5]4。方志敏写作,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用它的报纸言论诋毁苏区,武断造谣,所以他才要“用事实去打破敌人造谣的狗嘴,用事实□□□【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十分之好”[6]197-198。这说明这些革命者正是在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自信心的驱使下,将史学当做与敌人斗争的武器。
(四)党史研究能表达后辈革命者对革命前贤的哀思,以作不能忘却的纪念,教育后人。华岗在《中国大革命史》中表示要“敬以至诚”,“将此书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的战士”[5]4。方志敏更是明白地说道,在长期战争中,许多工农干部发扬了他们的智慧,作出了功绩,“使我至死都不能忘却”。“我应将他们可敬的活动和努力,□□下来,以作我对于他们的纪念,并鼓励他们前进。”[6]198
其次,在著史态度上,他们强调应当如实直书,只有“真确的史实”才能体现史学的真正价值。蔡和森作《党的机会主义史》时表示,自己所著史书“小的错误之处自属难免,大体则自信极其客观,极其忠实”[2]150。方志敏则在批驳了国民党的谣言后指出,“现在,我却要将赣东北苏维埃区域的建设情形,据实写出”,用事实来说话;并以严肃而负责的态度表示,“因为是叙述事实,我只要忠实地写下来就得了,绝用不着一点铺扬和夸耀,我写的态度是十分诚实的”[6]197-198。邓中夏则在其书的《著者声明》中直接表示,作者将“秉笔直书”[4]423。华著在《自序》中针对托陈取消派对“历史的事实”的推翻,也强调“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5]4,体现了作者对历史著作中史实真确性的高度重视。当然,他们所强调的如实直书,除了指史实的真确外,还指站在革命的、民众的立场上写作,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著述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人民性与客观性是统一的。
再次,在史料引用上,他们交待了相应的采择标准。早期中共党史著述多是在艰难、恶劣的环境下写成的,回忆的内容较多,在史料的搜集和征引上存在诸多问题,对此,研究者们并不回避,而是客观承认。蔡和森写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时承认:“这个报告中很少正确的统计的实际材料,而只是凭我的记忆所及而作的。”[2]1对于《党的机会主义史》,他交待道,写作时“身边无任何文件或材料,全是靠着脑中的记忆”[2]150。邓著也声明:“本书缺乏材料参考,大部分都是凭记忆所及。”[4]423华著则是在史料一度全部丧失后重新搜集,并谦虚地指出,自己是利用“仅有的一些材料和我自己参加实际运动的回忆”开始动笔的,而且大革命很复杂,区区三十万字不充分,难免有错误,参考书籍失散,难以一一注明出处,“这是事实上的困难,并非有意剽窃”[5]4。他们之所以花费笔墨交待自己著作中的史料缺陷,一是他们明白史料对于党史研究的重要性,二是要交待史料来源和成书经过,三是为了提醒读者在阅读自己著作时应当谨慎辨别。
早期中共党史撰述中所呈现出来的对史学功能、著史态度、史料采择的相关论述虽然未成体系,却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专门言说,是党史学理论的肇始。这些著述也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在史书形式上,经历了从报告到专文、专著的转变历程;在史书内容上,则从对中共党史的单纯记录与回顾,深入到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横向分析与革命运动的纵向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报告和专文的著述很大程度上出于组织义务,著史行为是被动的;而个人所作史著,虽然也会源于组织需求,但史家作史的主观愿望更趋强烈。而史著内容的不断深化,反映了史家更趋重视史著的革命阐释功能。早期中共党史撰述中史学意识的不断增强,为党史研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二、中共党史研究中统一的学科指导理论的形成(1941—1979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推动了中共党史撰述的转变。1941以后,延安整风兴起,毛泽东思想对史学的影响日渐加深,原本呈现散兵状态的党史撰述开始趋向统一的言说模式,党史学研究的专门指导理论也出现了。这固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有关,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党史研究作为政治手段与革命工具而被有意提升至政策层面——党史学习和研究成为全党性的活动。
1940年12月,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中共党内权威的关于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理论基础。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要聚集人才分工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克服无组织状态,并建议以《联共(布)历史简要读本》为研究马列的中心材料,视之为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唯一的完全的典型。[8]802-8031941年10月,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立,它所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1945年《决议》提供了雏形。同年12月及次年10月,作为干部学习材料的党内文件汇编《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先后编成,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大规模的系统的党史研究提供了理论、组织、人才和史料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这为以毛泽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党内路线斗争为主线的党史撰述模式的形成作了准备。
这些试图规范中共党史研究的努力事实上是在将其导向学科化,而学科化趋势的增强则呼唤着学科指导理论的出现。到1942年整风全面铺开后,为了给大规模的党史学习研究作出指导和规范,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文章论述重点不仅仅停留在具体的作史价值、态度、史料选取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尽管也提到了),而是在更基本、更宏观的研究对象、立场、研究法、分期等问题上。其特色在于:(1)提出“以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为对象,作“客观的研究”,并强调要研究“路线和政策”[9]399。这是与以往党史研究中侧重事件研究相区别的。(2)研究法上主张“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古今中外法”[9]400,更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科学、客观而非主观主义的方法[9]406。这也是以往党史研究没有或很少提的。(3)分期上,提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三阶段划分法,并分析了各期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和政治路线[9]400-406。这比以往的分期更好地概括了党史发展的大势,而将分期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史学发展的进步。(4)立场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实际[9]407-408。这是针对部分党史作品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立场为立场,不注意结合中国实际而言的。然而,该文也存在政治性过强的问题:(1)一再将路线和政策看作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易使党史变成干巴巴的文件;(2)视党史研究为革命宣传,如在肯定陈独秀功劳的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9]403。这里的“将来”恐怕是指取得政权之后了。
这篇文章并非从纯史学角度来分析问题,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所难免,关键是它作为“中共党史学史上第一篇专门探讨党史学理论的文章”[1]79,使党史研究“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1]55,从而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初步的学科指导理论。此后,党史研究开始围绕编写一份权威的中共党史书写定本展开。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炉,为认识党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导,其研究立场与方法论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党史撰述。如在中共党史的分期上,1945年以后的众多党史、革命史著作基本上一致,胡华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1946、1949年)、陶官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1948年)、黄祖英的《近百年史话》(1948年)、方且的《中国共产党史纲》(1949年)等著作,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历史分期上是高度相同的,这与此前党史撰述分期上所体现出来的多样性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种党史撰述的统一性也不宜被夸大,如在陈独秀错误问题上,相比于1945年《决议》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定性,陶官云、黄祖英、方且等更倾向于采用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的定性①陶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载《学习生活》1948年第5期;陶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光华书店1949年版,第22-24页;黄祖英、沈长洪、陈怀白:《近百年史话》,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56页;方且:《中国共产党史纲》,上海编译社1949年版,第28-29页。,这也区别于1949年后普遍流行的“投降主义”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发展在曲折中前进,虽说比之于学科实践上的进步略逊一筹,但仍然得到了完善。1951年,刘尧庭的《历史工作者对党史应有的认识》一文指出了党史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区别,强调党史不仅是从理论上明确革命的经验教训,还是从活生生的革命历史发展中更具体地来学习,使我们的体会更透彻更深刻。[10]该文的价值在肯定了党史是历史,而非理论。1956年,戴知贤的《对中共党史学习方法的体会》推进了对党史学科理论的探索,指出党史学习的法则就是要遵循历史科学的内在联系性和规律性;要先把基本线索搞清楚,加深对重要史实和理论问题的理解,再进一步研究专题;要注意考察各个时期、阶段的历史条件。如此,才能理解党的理论政策的客观根据和历史意义,明白它在革命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并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动。[11]这一分析既看到了党史发展的普遍性,也看到了其特殊性,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党史研究者对学科独立性的思索。
1958年以后,“史学革命”兴起,党史研究的教条化趋于极端,以毛主席的著作为纲,贯彻两条路线的斗争等以论代史的现象甚为盛行。历史主义思潮兴起后,胡华于1962年撰《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反思了“史学革命”中的极端做法,强调“党史科学也是历史科学”,自有其“逻辑、系统性和科学性”,文章虽没能跳出路线斗争的思路,但辨正了当时党史学界风行的片面观点。关于史论结合,明确提出两者皆不能偏废,如果“空洞抽象地叙述一些各个历史时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篇著作的一般内容”,脱离了活生生的史实,或以论带史,就会造成“论和史的脱节”,“没有了史,论也就显得概念化、公式化,同样不能成为党史科学,而顶多只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主要文件、政策的摘录和汇编”。关于联系现实,认为教好党史就是联系了实际,课程内容要适当地联系现实,避免穿凿附会。关于古为今用,强调尽管四卷《毛选》对现实有巨大指导意义,“但它终究主要也是针对那个时期的问题来讲的,不是直接针对当前问题来讲的”。文章还谈到讲稿的问题,指出“不要用许多不必要的‘伟大的崇高的……什么什么的’等等形容词”,对历史典型事例的叙述,“内容要准确,不可任意渲染”。关于科学研究,要熟悉党史的基本内容和材料,并谈到了研究中如何积累材料的问题。[12]胡文对此前党史学界过“左”行为的反思较为系统,代表了当时党史学理论发展的较高水平。此后,党史学科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而逐渐丧失其史学特性,学科理论的探索也中断了。
中共党史的研究实践也丰富着党史学理论。如《毛泽东选集》(1951—1960年)的出版在党史分期上提供了新的范例,在书中,新民主主义革命被划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四个时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革命内容和矛盾,对党史研究的影响直至今日。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呼应了毛选的出版,该书对中共革命历程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的梳理,对党史分期和重大理论问题的论述,肯定了中共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宣传了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0年)、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4年)、李新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959—1962年)则形塑了此后的中国革命史体系。
在“文革”中,学术意义的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是不存在了,理论研究更是无从谈起。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叶剑英和胡耀邦等在不同场合强调研究党史,为党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党史学科的理论重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其中心环节是围绕党史教研工作的探讨。胡华的《关于党史教学的若干问题》[13]和岳平的《当前党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4]集中体现了这种努力,要求在党史教研的指导思想、研究内容、对象、目的、原则等问题上,否定“左”倾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的党史撰述模式,恢复和重建实事求是的教学传统。
三、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体系化(1980年以来)
为推动党史研究发展,中共中央于1980年先后成立了党史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同年,中共党史学会创建,《党史研究》创刊。这些空前的举措说明官方正努力为学术性的党史研究创造条件。与此同时,相关理论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的出版宣告了党史学科体系的恢复[1]258,那么围绕党史撰述体系的争鸣则宣告了学术化新党史研究的起步。在这些争鸣中富有代表性的,如廖盖隆对党史分期的新论述——主张将六十年党史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两大段,上下编,又将党的成立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独立成章,并对不同时期的断限提出了调整意见,是富有新意的。另外,丁守和、方孔木对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关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系等问题的系统论述也表明了党史研究者对党史学理论的认识在不断深化。①详见廖盖隆:《关于党史研究和教学的几个问题》,《党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7期;丁守和、方孔木:《关于党史研究中的问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中共党史研究在1980年一年中所取得的上述成就意味着党史研究开始出现思想解放、学术活跃的局面,新的党史学理论体系正在形成。
指导理论和方法的进步是党史学理论走向系统化的最显明表现。首先,围绕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特点、研究任务、对象、内容、分期、价值等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有关学科性质问题的探讨最为核心。1985年以后,高校中的中共党史课程不再作为政治理论课开设,为长期政治化的党史研究松了绑,于是,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成为党史学界最为关注的理论问题。系子和马齐彬分别在1985年、1986年撰文强调中共党史作为历史学科和理论学科的学科性质,他们主张党史是理论学科的理由是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在紧密联系。②系子:《党史工作者要深入实际,研究现状》,《党史通讯》1985年第4期;马齐彬:《中共党史是党员干部必修的一门学科》,《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而周振刚、张静如、王朝美等则坚称它只是一门历史学科,认为不能因为党的有关理论是党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就说它是理论科学,它只是近代史时限内的一部专门史。③周振刚:《中共党史是理论学科吗?——关于中共中共党史性质的商榷》,《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的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王朝美:《略论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此后,随着党史研究史学化趋势的加强,有关中共党史是一门历史学科的看法逐渐赢得了更多的认同。而关于党史学科特点、任务等问题的探讨也受到关注,在这方面,学界已有众多述评,这里从略。
其次,要求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将后者应用到党史研究中,构建党史学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1991年)就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历史理论间存在着指导和包容的关系,党史研究必须借助理论上的中间环节来表现唯物史观的指导,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构建中共党史的科学体系。[15]122-123故而,该书就中共党史宏观理论和微观操作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举凡党史学科的基本理论,以及学科史、史料、史纂、史学批评、地方史、史学工作者的素养等问题均予涉及,包容甚广,确立了一个完整的党史学理论系统。易豪精认为,党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由党史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部分组成:本体论指关于党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其核心是社会历史观;认识论探讨党史认识的特点与功能、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阶级性与科学性等问题;方法论指关于党史研究方式方法的理论。[16]郭德宏则认为中共党史学体系应该包括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党史学史、文献学和史料学、编写学、研究主体学七个方面的内容。[17]此后卢耸岗主编的《党史研究概论》(2000年),谢萌明等主编的《党史理论纵横谈》(2001年)等也都从不同方面充实了党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宋学勤在201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学概论》,吸收了党史学理论的众多成果,除论述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外,又对史学理论的其他相关问题逐层阐发,如史观上考察了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史法上倡导心理史学、社会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史学方法,史料上论述了党史史料类型、搜集、校勘、编辑、考证、运用,史纂上则论述了论著编撰理论、形式、原则、规范、技巧、语言,层次清晰,结构严整,党史学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最后,新式研究方法不断得到提倡。如张静如、侯且岸等提出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坚持历史主义,恰当运用阶级分析法,考察社会心理,注意历史比较法、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方法、逆向考察法等。[18]尤其是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1995年)中,张静如将中共历史发展的过程视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也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用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宝贵探索和示范。高树森、孟国祥等则提出要构建党史学的方法论体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中心环节,使用历史比较法、数量分析法、科学假说法、系统分析法等一系列具体的史学方法。[19]郭德宏也提出了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即时史学、社会史学、心理史学、文化史学、政治科学、领导科学、长时段研究等史学方法。[20]前面提到的两本《中共党史学概论》也都对各种史学方法进行过论述。
中共党史分支学科的发展从另一方面表征了党史理论的系统化。譬如党史学术史研究的开展,最初局限在对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领导人的研究上。1987—1989年,在张静如的组织下,王京生、唐曼珍先后撰写了《中共党史学史概说》、《党史学初建状况研究》、《党史学成型期状况研究》等文章,提倡党史学史的研究,并对其学科性质、研究任务、对象、分期及各期特点、成就等问题作了初步考察,这三篇文章也因此被看作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开端。[21]此后,张静如、唐曼珍继续深挖广采,于1990年撰成《中共党史学史》,将党史学发展断作萌生、初建、成型、挫折、复兴五期,各叙因由,诸如各期中富有代表性的观点、著述、史学理论及其贡献皆有所涉,创获颇丰。90年代,周一平、唐曼珍、王子今、侯且岸、邹兆辰、王炳林等都为党史史学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周一平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1991年),以及后来的《中共党史史学史》(2001年)则成为党史学术通史的新代表。另外,党史史料学、文献学、史学批评的提法次第生发,有力地推动了党史学科体系的完善。
中共党史撰述和史实研究则从实践层面更新着党史学理论的体系。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与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因为总体“立得住”,对后来的党史研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1983年)在体裁上创造性地采用“纪事本末体”撰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打破了此前党史撰述中的编年史体裁。而郑德荣、郭彬蔚主编的《中共党史教程》(1989年)则在党史分期、史料去取等问题上“对传统纲目和教材体系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因而其编纂体例是富有新意的。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91年)实事求是地提出许多新观点和论断,富有理论水平,“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作为官方党史撰述的正本,在党史研究的史识上独具慧眼。沙健孙等的《中国共产党通史》(1996—2000年)作为党史研究上第一部以“中国共产党通史”命名的著作,以5卷304万字的篇幅贯通党史的方方面面,编者“努力收集党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主要是第一手资料”,力图“向读者提供一部内容比较翔实的党史著作”,史料的丰富是其重要特色。而在史实研究中,诸如朱成甲的《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1989年)之于历史主义方法论,程中原的《张闻天传》(1993年)之于口述史学,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998年)之于社会史学,等等,都是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范例。正是这些不断创新的党史撰述和党史研究,不断丰富着党史学的理论体系。
四、结语
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政治因素在其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如果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于党史研究的认识还是言人人殊,那么40年代的党史研究则因整风需要而走向规范化,由此才产生了学科理论。1949年以后,政治的一统形塑了一统的学术,政治越向“左”走,学术便越向政治靠拢,以致最终成了政治。而1978年以后,中共党史研究开始解放思想,党史研究逐渐被还原成原生态的历史研究,史学化趋势开始出现。
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进程。大体在1940年代以前,李大钊、李达等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和传播,郭沫若、吕振羽等对中国历史的探研,都还处于榛莽草创时期,党史学理论也同样处于初生阶段,相关理论认识与党史撰述融为一体。但到1940年代后,以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出现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取得了重要成就,尤其在延安地区更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化的趋势,受此影响,中共党史学理论从党史撰述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统一的学科指导理论。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入发展,尤其是1961年历史主义思潮的兴起带动了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也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得到发展。到了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热潮涌动,在此背景下,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热点频出,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纵观这个过程,尽管历尽挫折,却也卓有成效,中共党史研究内在本有的史学属性正是在这一代代学人的传承和创新中不断升华,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的规范化、系统化,这也就是中共党史学理论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
[1] 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 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3]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 邓中夏.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 华岗.华岗选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6]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刘尧庭.历史工作者对党史应有的认识[J].新史学通讯,1951(7).
[11] 戴知贤.对中共党史学习方法的体会[J].读书月报,1956(5).
[12] 胡华.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教学与研究,1962(5).
[13] 胡华.关于党史教学的若干问题[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4).
[14] 岳平.当前党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J].人民日报,1979-09-10(3).
[15] 王仲清,等.中共党史学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16] 易豪精,林强.要加强中共党史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综述[J].福建党史月刊,1988(9).
[17] 郭德宏.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18] 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J].中共党史研究,1989(1).
[19] 高树森,孟国祥.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J].南京社会科学,1990(3).
[20] 郭德宏.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J].中共党史研究,1997(4).
[21] 费迅,李子白.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史学史暨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J].党史教学与研究,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