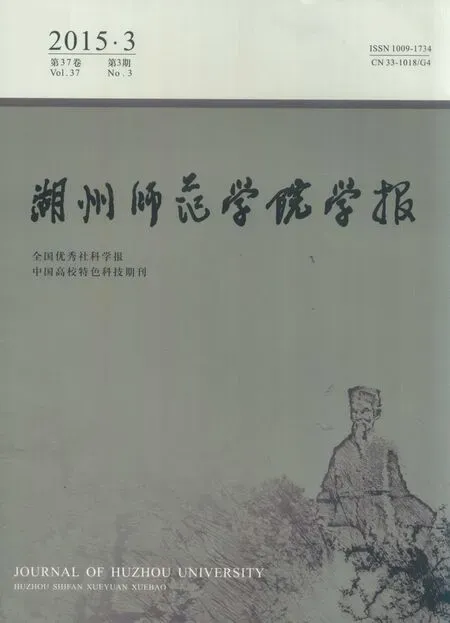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系统论分析*
彭德林
(湖州师范学院 政治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
程朱理学主张“知先行后”,这是王阳明绝对不能接受的。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知而不行”的道德现象,在王阳明看来,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必须破除“知先行后”的偏斜,才能从根本上治疗“知而不行”的时弊。所以,他提出“知行合一”说。运用系统论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知行合一”说及其当代价值,更好地在道德实践中把知行统一起来。
首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一个由目的、手段和根据构成的有机系统。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目的是安天下之民;安天下之民的手段则是让世人按照良知为人处事,克服知行分离,实现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手段是“要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以“德性之知”统帅“闻见之知”,最根本的是恢复人的本心;因为人的本心和良知之理是同一的,良知之理不能在人的本心外存在,人的本心之外也没有良知之理,要言之,致良知的本体论根据则是“心即理”“理无外乎心”、“心外无理”。其次,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内涵分析、对知行分离的原因分析及知行合一的根据阐明,也有着明显的系统论的色彩。基于以上理由,本文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系统论分析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从知和行的要素内涵看“知行合一”的系统内涵;对知行分离原因的系统分析;对“知行合一”的根据之系统阐明;对作为“知行合一”根据的“心即理”“心外无理”的系统评价。
一、“知”“行”要素与“知行合一”的系统内涵
何谓“知”。有多种说法。首先,“知”是“是非之心”,即良知。“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1](卷八)意思是,人都有是非之心,都有良知,良知是本来就有的,为现实的道德之知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必须在致知的道德行为中才成为现实的自觉的道德之知。其次,指“有自觉的道德知识”。“知至者,知也。”[1](卷二十七)知识的达到和完成,自觉的道德知识,就是知。那么,如何达到和完成自觉的道德知识呢?“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所以合一也。”即只有通过致知的行为才能完成和达到自觉的道德之知,否则不可能有知识,本然的良知之知也不能显现。自觉的道德知识非粗知,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把僵死的伦理规范看作是不变的法则,从而丧失良知的真正的指导作用。自觉的道德知识实际上包括了高于伦理规范的德性精神的领会和伦理规范的知晓。再次。“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1](卷六)道德行动不只是在实实在在地行动,而且是在纯乎天理之心即良知的监督指导下仔细思考和研究,才能明辨善恶是非,为善去恶,故行动的明觉精察就是“知”。第四,真正的知是知行合一的知,是具体行动中具体的人面对具体对象的亲身体验之知。王阳明在答徐爱问“知行合一”的问时,首先指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2](卷上)真正的知是行动中的知,是具体行动中具体的人面对具体对象的知,是已经完成的知情意行合一的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对真正的知同时有两种说法,即知孝悌的德性之知和知痛寒饥的生理感受之知。这并不说明王阳明哲学思考的非严密性,而是说,知孝悌的德性之知是不能离开知痛寒饥的生理感受之知的,比如,从自己感觉寒冷推知父母感觉寒冷,并为父母做些御寒的事。第五,单纯的口耳谈说不是“知”。[2](卷中)悬空讨论的道德知识不是真正的知。因为它不能根据良知的要求适应变化的道德情境,解决现实的道德问题,实现社会理想和道德价值。第六,知是过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卷上)知是一个在行中由开始到结束的过程。
何谓“行”。王阳明说:“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故他的行的含义很宽泛,包括多层具体含义:首先,求知行为。“著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1](卷六)如果王阳明是指道德行为中去求道德之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仅仅对道德知识做理论的学习行为难道不是著实去做这件事吗?如果是,那么,单纯的道德理论的学习行为也是行。其次。道德反省、诚意的心理行为。特别表现“在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只在心中克服不善的念,既是道德认知,又是道德修养的行为。但不能否认这种道德行为和事亲事君等道德行为有很大的区别。再次。事亲事君、交友治民等实际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行为,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行为。这是最重要的道德行为,理论学习、道德反省修养都要落实在这些行为上,否则也是“知而不行”。这种行为,同时是获得和深化道德之知的过程。第四,“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最真实实在的知、对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直接的具体的了解就是行。知就是行。第五,“行”是一个过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是包含了知的生成之有开始和结束的过程。
“知行合一”的内涵。从“知”“行”的概念界定可知,知就是行,行就是知,没有无知的行,也没有无行的知,知行在现实生活的具体行为中合一,特别是在事亲事君、交友治民等行为中合一,“知行合一”落脚点在具体行为主体的心中;“知行合一”是一个“即行即知”、“即知即行”的过程,道德行动就是化本然之知为自觉之知的过程;“知行合一”,既是以“德性之知”统帅“闻见之知”、以“德性之知”指导“闻见之知”的认知选择和使用方向,同时又是通过发展“闻见之知”提升“德性之知”的过程。[2](卷中)这很鲜明地体现了王阳明哲学的道德实践性。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讲“知”和“行”两字,“知”“行”在什么意义上分开呢?
王阳明说:“凡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功夫上补偏救弊说。[1](卷六)不似今人截然分作两件事做。”即古人说知行两分,是为了要救治生活中许多人不思维省察的“冥行妄作”和不肯着实躬行的“悬空思索”的弊病,纠正“知而不行”的道德偏差,通过“致良知”的功夫,存天理,去人欲,恢复良知本体的精明,依循良知去做,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的要求,知行合一。知行的本来体段是合一的。但生活中很多人却以为,知和行本来就是分开的两件事情,先知,然后照着既定的已经完善的知识做就行了。
二、“知”“行”分离原因的系统分析
知行分离的原因有哪些呢?一曰语言之遮蔽。王阳明认为,知行的本来体段就是合一的,“吾契但著实就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知得。仅却只从言语文义上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糊涂,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1](卷六)所以,不从身心上体履,不在具体的道德践行中去体认,只从言语文义上理解知行的含义,必然把知和行分开,把知行的整体弄得支离破碎,使人对知行越来越糊涂,陷入道德语言化的误区。因为语言的把握以区别语词概念为基础,必然把完整的存在整体切割,仅仅从语言了解道德存在是不够的。当然,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完善也可以部分消除语言对道德存在整体的遮蔽,可如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说理一样,采取把理论的逻辑论证和以具体事例阐释普遍性理论这两者密切结合的方式,或者以理论家的自身知行统一的榜样示范的方式,来部分地消除对道德存在整体的语言化、碎片化和曲解。
二是私欲阻碍。“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2](卷上)《传习录》第321条的语录,也可说明王阳明对知行分离的原因有同样的看法。徐爱又问:“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两个了?”先生曰:“说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为私欲间断,便是仁不能守。”“仁不能守”,就是知行分裂了,知而不行,原因是人受到私欲阻碍,不能依良知而行。
要克服“冥行妄作”、“悬空思索”等分知行为二的偏差,就必须回到具体的道德实践行为中把握知行。既超越反思语言中对知行的抽象理解,在具体道德行动中对知行具体体认;也必须重视道德动机和意念,重视内省功夫,克服意念中的私欲。因为,道德的意念不是纯粹的意念,不是纯粹的知,已经是道德行为的开始,当善恶的意念呈现的时候,存善去恶的功夫必然随之而至,人心中的那点良知为此提供了保证。
三是“剧场假相”,即错误的理论给人心造成的遮蔽,这就是析心与理为二,或认为“理外乎心”,“心外有理”,必然导致向外物求理,忘记收拾内心,忘记对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人伦天理进行反省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去恶为善,必然良知丧失,知而不行。所以,王阳明要讲知行合一,就要反对析心理为二,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
三、“知行合一”的根据之系统阐明
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根据进行了系统阐明,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王阳明关于“心即理”的心体同一性的论证。阳明说“心,一而已也。以其全体恻隐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此知行之所以为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2](卷中)即他认为,心只是同一个心,心具备恻隐一体的意识是仁,心主导下处事得体是义,心把握了事之条理就是理,仁义之心和条理之心是同一个心,既然仁义都不能在心外求,怎么独独理就要在心外求呢?外心以求理,就是知和行分裂为二的理论上的原因。若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就应即心求理,而不是象程朱那种“即物求理”,即“心即理”是知行合一的理论前提。因为良知天理在心中先天地内在存在着,只须时刻通过致良知的努力,依照良知的指导,内在的良知就既展现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又成为自觉的德性知识。致良知的功夫使内在的良知本体得到呈现,先天的良知本体使致良知的功夫成为可能,本体和功夫是合一的,知行也是合一的。不能在心外求理,不能以空无之心即物求理,如此,只能导致舍本逐末,空谈性理,知而不行,道德沦丧,物欲横流,个体幸福与社会和谐皆不能实现。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如果一味向外追逐物质利益,不去向内诚意修德,道德就成为一种外在的约束,道德作为人的存在之维度就会缺失,社会的发展就是片面的发展,因此,重视道德建设非常重要。“心即理”是知行合一的根据。
其次是王阳明关于“心即理”的认识发生学论证。如上所述,王阳明从心体的同一性论证了“心即理”,把握仁义的心和具备事物之条理的心只是同一个,论证了“理”和“仁义”一样只能在心中求,这还只是一个抽象的论证;他还做了理被把握的发生学的论证。他认为,从事物之理实际地被把握只能在物理与心发生作用的具体的行为中,否则就隐而不显。“山中观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意之所在便是物”这个被一些学者以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理论来解释的哲学命题,它只不过把物转变为事情,强调事情行为不能离开人的意识而存在,事物之理不能离开行为活动中的具体的人之心被把握,朱熹也承认“理虽散在万事不外乎一心”,故也可认为朱熹承认理不能离开人的心而被认识,在这一点上,他和王阳明无太大的区别;仅仅承认理不能离开于人的心而被认识,也不能把“客观事物之理”和“良知之理”区别开来,而且对王阳明来说,对解决社会道德沦丧问题最关键的事情是,要强调“良知之理”的重要性,要用“良知”约束人心中的私欲,并行之有效,这就不仅要承认人心和良知之理先验地同一,还要承认,这种良知之理要在人心与具体行为对象实际地相互作用之中才能得到具体显现,才能面向具体的人我关系矛盾,按照良知的要求处理这些矛盾,如此,个体才能把握心所天赋的良知之理的具体内容,良知也在个体身上得到更高级的实现。认识的发生学论证是对心体同一性论证的发展,是对知行合一的进一步阐明。
最后是“心外无理”对“心即理”的进一步规定。有学者对“心外无理”的讨论,把“心外无理”和“理不外乎心”“心即理”区别开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以为他对“理不外乎心”“心即理”的理解是有偏颇的,对“心外无理”的指责也是不符合王阳明解决人的现实生存问题的问题意识的。在他看来,王阳明的“理不外乎心”“心即理”既可指“理”在行为主体的心中存在,还意味着“理”可以在外部事物上同时存在。我认为,此说不符合阳明哲学的本意,因为,阳明还要强调“心外无理”。“心外无理”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性的命题,实是对“心即理”“理无外乎心”的进一步规定,是对心学根本命题的进一步阐明。
“理无外乎心”“心即理”不是仅仅指理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因为这样还可以认为理可以在外部事物和心上同时存在,如果承认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就有可能承认“向外求理”“即物求理”是正确的为学方向和生活方式,就有可能导致向外过分追逐物相,引起身体和心的自然节律的抗议,导致身心疲惫,导致心与身的内在和谐的丧失;导致物欲横流,你争我夺,对自然的过度利用,从而引起人与我、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人与我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丧失,所以,只有彻底否定理在心外存在,彻底斩断向外求理的可能,才能彻底关闭使心与身、人与我、物我之和谐丧失的大门,使“万物一体”得以实现,个体幸福,社会和谐,天人合一。可见,“万物一体”作为王阳明哲学理想,不能通过“向外求理”,“即物求理”的方式实现,因为“万物一体”的最后根据不在人心之外,而在个体之心中的那一点良知,因为“心外无理”。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这种求放心只能是向自己的内心反求,而不是像后世人虽然广记博诵古人的道德言词,却只是把它们作为追求个人功名利达的外在手段。[3](卷中)
四、对“心外无理”“心即理”的系统评价
阳明心学的“心”是社会性和个性、超越性和经验性、自觉和自愿的统一。王阳明的“心”本体继承了朱熹的经验之心的意义内涵,也继承了朱熹的性的超越性的向度,克服他的性对心的外在性。性不仅作为禀赋潜在于心中,性具备天理,性也直接与经验之心同一,个体之心不仅获得了经验的思维知觉意念欲望情感等意义,也同时具备了超越性的意义;良知之心既因为其绝对普遍性和超越性构成了对个体内心人欲的内在约束,体现良知的社会性,又因为其是现实的个体之心,在个体中获得了和谐与幸福的内在根据而具有个性。
阳明心学的“心”是自觉和自愿的统一。在具体行为中,个体之心既以思维去认知本来之良知天理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又以个体之心的生命感受、情意知觉和思维等对个体的当下生存处境与实践活动进行合目的性判断,对社会与个体的生活现实是否符合我的真实需要做出价值判断,并分析原因,寻找改善个体处境和社会现状的途径,从而体认良知天理与我的亲近,体认天理与自我身心需要的和谐,把理性的自觉和包含非理性因素的自愿的品格在个体的具体行为中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克服“以理杀人”、牺牲个体之幸福的“理性专制主义”和虚假的“普遍主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不顾社会规则的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就是说,以良知约束人欲不仅是社会和谐的要求,不仅是超越性的普遍性的社会共同生活存在和发展的要求,更是个体生存与幸福的必然要求,从而化外在约束为内在约束,个体自觉自愿地去服从良知天理,如此也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抹杀自愿的行为不可能是道德行为。
阳明心学体现了为学和生活的统一。“心外无理”、“理无外乎心”、“心即理”三大命题,共同构成要“在心求理”、而不能“即物求理”的根本理论根据,是个体幸福、社会和谐和天人合一的形而上的根据。“在心求理”也不是单纯的为学之方法,更是个体和人类所当然的生活方式,为学之方法是为人的生存和幸福服务的,可谓牢牢地抓住了为学的目的和根据,这正是阳明哲学高明的地方。当然,以“三纲五常”这样的不变的天理约束人欲,是否合理,是否真正能实现个体的幸福,这已经超出王阳明所能思考的哲学问题之外。同时,王阳明的本意是强调以德性之知统领闻见之知,不可把手段(即物求理)当作目的,反对过度向外追求而导致丧失人本身这个目的,所以,他讲“心即理”“心外无理”;但他讲求理于吾心,可能导致误解,以为他忽视客观事物之理,也可能使个体根据自己对良知主观化的理解和个体的情意需要“率性而动”、“纯任自然”获得某种合法性,从而达不到改善道德现状的目的。
阳明心学强调“德性之知”的统帅作用。王阳明心学的“心即理”、“理无外乎心”、“心外无理”的命题是否否定了追求客观事物之理呢?答案是:没有。因为他只是要以“德性之知”统帅“闻见之知”;还因为从他关于“心外无理”“心即理”的两个论证,即个体的心体同一性论证和理之认识的发生学论证,可说明他的理是能容纳客观事物之理的存在(本来是潜在的)和认识的;而且,从致良知的功夫上讲,“要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致良知”的依据上讲,说“此心在物则为理”,都不能离开各种行为,如事亲事君、交友治民、读书听讼等,这些行为要做好,除了求德性之知,难道不需要掌握闻见之知吗?所以,从文本和理论逻辑上讲,他并不是一个只讲“尊德性”、却否定或者轻视“道问学”功夫的思想家,这有文本中大量的讲求节目时变、多识前言往行、博学、审问、好闻好察、知新的说法可资证明,王阳明是重视物理之知、闻见之知的,否则,就不需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不需说“此心在物则为理”,只要说在心中求即可。所以,他说“心即理”“心外无理”“求于心”的目的,是要以“德性之知”给“闻见之知”以头脑。
阳明心学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毕竟是道德唯心主义的。虽然阳明心学的“心”把经验性和超越性、社会性和个性在个体的现实生存活动中统一起来,但他只是在政治实践、道德实践和教育实践中讲经验性和超越性、社会性和个性的统一,并未就此追根求源到物质生产,仅仅从伦理道德着手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外在物相之过度追逐,这是其道德唯心主义的体现。从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组成的更大的社会系统中,从当时社会的商品生产发展中探求道德沦丧的根源,审视良知之理的合理性,建构新的伦理道德,和其他手段共同作用,建设合乎人性新需要的新秩序,这比从良知之心中求理更为根本和重要,也才能真正实现“安天下之民”的目的。
[1][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北京:国学整理社,1936.
[2]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