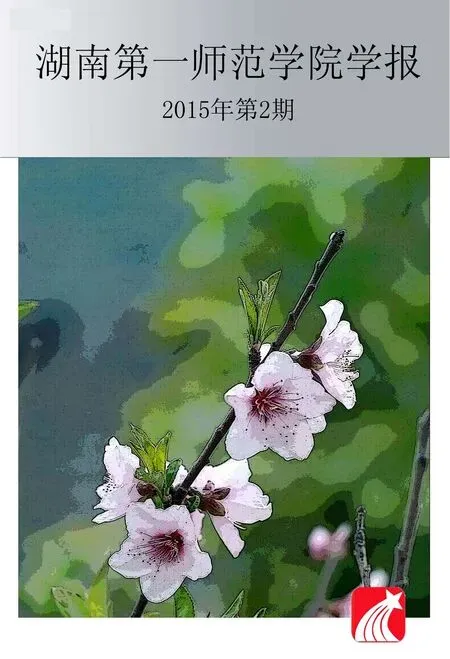影像屈原的建构与批评
刘伟生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影像屈原的建构与批评
刘伟生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影像屈原的建构既要有多元充足的类别与生动丰满的个案,也要尽可能让一些经典个案富含多层的意蕴。影像屈原体类建构的主流目标应该是正格的历史悲剧。从悲剧主体来看,它既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国家民族的悲剧。从悲剧本身的类别与层次来看,它既是社会政治的悲剧,也是历史文化的悲剧与道德理想的悲剧。影像屈原的构建终归要落实到叙事艺术上来,其中重点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与话语方式的讲求,要注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文学与影像的互动。
戏剧;电影;电视;屈原
文艺作品中的屈原形象,除了屈骚自我陈述外,后人所作诗文词赋及图画戏曲也屡有创建。以戏曲为例,自隋至清,代有佳作。据阿英、赵景深、姜亮夫、崔富章、徐扶明、吴柏森、王学秀、郭维森、齐晓枫、俞樟华、何光涛等人考察与统计,元明清以屈原为主角或配角的戏曲作品即多达21种[1]1。以屈原及其作品为题材的绘画,自南北朝至清末,也代不乏人。近人郑振铎、饶宗颐、姜亮夫、崔富章等多有著录,阿英、李格非、刘书妤、陈池瑜、张克锋等还有专文论述[2]81-90。至于诗文词赋以屈原及屈骚为事典、语典的就更可谓浩如烟海了。现当代以屈原及其作品为题材的戏剧与绘画都有新的发展。1942年,郭沫若创作话剧《屈原》,并于重庆公演,曾经轰动一时。受其启发,传统戏曲剧种如秦腔、越剧、川剧、曲剧、京剧、粤剧、蒲剧、晋剧等等相继将屈原形象搬上舞台。还有施光南作曲的歌剧《屈原》与吴双、潘伟行等执笔的话剧《春秋魂》,都曾在剧种形式或剧曲内涵上做出过可喜的尝试。更有盛和煜创作的湘剧《山鬼》,以荒诞的人物、奇特的情节与反常的手法成为反向创新的范本。绘画方面,著名画家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程十发、蒋兆和、黄永玉、范曾、李少文等都曾创构以屈原或屈骚为题材的杰作。与传统文艺相比,现代媒介尤其影视是更为庞大而直观的形象“加工厂”。上世纪70年代,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根据郭沫若同名话剧剧本改编有故事片《屈原》。新旧世纪之交,湖南电视台拍摄有20集长篇电视连续剧《屈原》。据报道,最近北京中视精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正在筹拍由熊诚和莫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40-50集的电视剧《屈原大传》。还有几种已播与待播的关于屈原的纪录片,都已为或将为屈原形象的现代建构注入新的质素。本文即拟以电影《屈原》、电视剧《屈原》、话剧《春秋魂》、湘剧《山鬼》等影响较大的当代戏剧影视作品为主要例证,参照古代屈原戏、话剧《屈原》及相关资料,从体类判别、史事处理、题旨定位、叙事技巧等方面探究影像屈原的建构与批评问题。
一、影像屈原的体类判定与史事处理
作为视觉性表述的屈原形象,虽不乏后来想象,却是曾经实存;换句话说,屈原形象先是历史的,然后才是文艺的。所以影像屈原的建构首先便面临着体类判定与史事处理的问题。
(一)影像屈原的体类判定
古代屈原戏以杂剧、传奇居多,现代屈原戏则既有话剧、歌剧,也有不同种类的戏曲及影视作品。受郭沫若话剧《屈原》影响,现代屈原戏及影视作品多为历史剧、悲剧,罕见戏说、穿越之类的娱乐喜剧,虽然也有湘剧《山鬼》这样的“荒诞史剧”、“非历史的历史剧”[3]22。倒是古代屈原戏多为升仙道化之类的题材构造,明末清初丁耀亢杂剧《化人游》,郑瑜杂剧《汨罗江》,清代前期张坚传奇《怀沙记》,乾隆年间楚客杂剧《离骚影》、月令承应戏《正则成仙》《渔家言乐》,咸丰、道光年间周乐清杂剧《纫兰佩》,晚清胡盍朋传奇《汨罗沙》等等,莫不写屈原死后升仙或复活之事。如丁耀亢杂剧《化人游》第五出写何皋在鱼腹国中修道,由鱼骨大王所派鱼肠剑士引见已入鱼腹国千年之久的屈原,两人共赋《离骚》、《九章》,并见南海所贡大橘中两老人言谈对奕。情节荒诞离奇,又服从全剧道化度脱的布局,当然也不影响作者“借荒诞的情节揭露现实的腐败,表现自己的愤世之情”[4]88。可见屈原戏也可以有多种体类与构思。
不过以屈原本人的事迹与历代接受情况及当今时世的精神需求来看,影像屈原体类建构的主流目标应该是正格的历史剧、是悲壮浓烈的精神文化史诗。学者们通常认为:真正的历史剧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艺术表现的基础上,发展历史的精神,寻求古今之汇通,具有一定史事性的戏剧”[5]3;真正严肃的历史题材创作,“更重要的目的是企图在满足人们打捞历史、窥探历史隐秘的欲望的同时,以古为镜,知古鉴今,来为现实社会提供一种精神支撑和价值理想”[6]295;所以它应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凸显历史精神、认清民族立场、张扬文化价值、提升哲学内涵、营造诗意氛围。而这重大的使命最好能通过最具感染力的悲剧来实现。
(二)影像屈原的史事处理
历史剧内在关联着历史精神,外在关联着历史事实。不管是否为正格的历史剧,只要是表现屈原,就要勘定与屈原个人及时代相关的史料。但屈原一向孤高特立、不合时宜,被统治集团视为异类,也不为正统史官所青睐,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疑点很多,而高度生活化、形象化的戏剧影视又离不开细节的支撑,并需与时代大背景发生必要的关联。这势必为影像屈原的史事处理增加难度,当然也会提供更多可以发挥的空间。所以总的原则应该是在遵遁学界定论与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还原历史与适度虚构来建造屈原形象。事实上,现当代多数屈原形象创作者与评论家们都是遵循这一原则的。郭沫若以“失事求似”的方式创作话剧《屈原》,给后来者以重要启示。电视剧《屈原》也利用屈原史迹及阐释所留下的表现空间,因人生事,“对已然逝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情境进行大胆的假定和建构,塑造出一个富有审美价值、血肉丰满的屈原形象”[7]111。在《屈原大传》改编前的研讨会上,李准对这部作品为实现历史品格和文学优势的互补共赢所做的努力进行了五方面的肯定:“其一,坚持以《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为主要历史依据。……其二,对史料中的模糊、相互矛盾处,作者作出言之有理的辨析。其三,参阅屈原诗歌中有关他生平的信息,采用《楚史》、《国王上下八百年》等二三手史料的某些提法以及野史中的个别提法,通过合理想象写出了青年屈原经殿试当上文学侍郎……等情节。……其四,按照人物性格逻辑的可能性,虚构出了屈原南台题匾、……等情节……。其五,生动描写了屈原《橘颂》、《东皇太一》、《云中君》、《离骚》、《招魂》、《哀郢》、《怀沙》等名篇的吟诵与歌舞,描写了山野水乡的民歌对唱,……发挥文学的功能和优势。”[8]82-83可见有了自觉意识的创作者与批评家们都在努力地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行。
相较而言,历史氛围的营造、历史精神的把握、历史文化批判的践行要难得多。战国时代,诸侯混战、百家争鸣,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更,屈原与楚国身处其中,必然与他国他人发生很多关系,历朝历代的接受者们也渴望了解这些关系。但史籍所载的屈原与他国的交往不多,偏居南方的楚国也不算当时中心,所以影像屈原构建中战国历史文化背景的展示是有相当难度的。方铭先生为纪录片《屈原》拍摄把脉时提到要注意处理十大关系,其中包括“屈原和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圣贤的关系”,“战国时代与春秋及春秋前社会以及秦以后社会的关系”,“楚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湖北湖南与战国时期楚国其他地方的关系”。[9]6这样的建议于戏剧影视同样适用,只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会更大。话剧及电影《屈原》因篇幅的限制很少涉及时代大背景。电视剧《屈原》从人物关联、情节构思、背景渗透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构造了孟子、田文、庄子等名流形象,展示了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盛况,提及到秦国的郡县制与商鞅变法等问题;这些努力既能给人以直观亲切的感受,又能助人思索更为深广的文化问题。当然,这样的努力没有止境,所以即便是新出的长篇小说《屈原大传》所受的批评也几乎都涉及时代大背景表现不够的问题。
历史氛围的营造是由具体人物与情节的设置来完成的,但它既源于历史事实,也受创作者历史意识的影响。自觉而健康的历史意识有利于创作者正确而快捷地了解历史规律,把握历史精神,进而通过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来营造历史氛围。吴卫华提到电视剧《屈原》的人物、情节与历史氛围、历史精神关系问题时说:“列国争雄和时代风云的急遽变幻,诸子、策士特别是纵横家的活动便构成了电视剧《屈原》的真实的历史精神和历史氛围的主要生活内容。电视剧始终将故事情节的敷衍、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情境的设置与这种精神和氛围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使作品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从而逼近历史的真实。而这恰恰正是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企图达到而又未能达到的高度。”[7]111吴卫华也特别提到历史意识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意识是一种跨越时空审视历史的思维观念和方法,它在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复杂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能力的基础上,把一切事物看成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理解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10]40从时间上看,历史意识关乎历史情境与社会现实以及它们之间漫长的衍变过程。从空间上看,历史意识的贯彻既包括历史事实的判别,也包括历史规律的提炼、并将由此确立的历史精神与历史文化批判植入到历史剧的具体情境氛围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真正的历史对象其实就是种种关系,历史研究如此,文艺创作亦如此。只是在实际的创作与批评中,往往会发生一些偏差,产生所谓“功利主义史剧观”或“泥古主义史剧观”。
文化立场影响到历史文化的反思与批评,当然也影响到价值观念的重构。具体来说,它会影响到影像屈原建构过程中对历史深度与广度的观照,对历史现象背后深层的文化意蕴、民族心理与价值观念的感悟与体验,可以为主题的宏观定位、叙事的具体操作提供指针。
二、影像屈原的题旨定位
(一)屈原理解角度及探究层面
对屈原的理解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也与角度有关,并涉及不同层面。两汉一统,君主专权,国家形态与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士人阶层不再具有独立的生存空间,所以对屈原为一方诸侯竭忠尽职而又露才扬己、责数君王的行为颇多责议。或不解其不忍去国,或否定其投江自尽,或非议其独异个性。唐承汉风,除了少数贬谪士人的引类共鸣,多半对屈原的处世方式持否定态度,大概盛世不喜桀傲之臣。历经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异族的入侵与暴政的蹂躏,屈原的爱国精神与独立品格在不少国人的妥协、圆通与狡黠的脱变中愈加可贵而又显耀。他成了抵抗外侮的旗帜、痛斥奸邪的榜样,当然也可以成为批判现实的动力、探寻理想的先驱。
因时之变除了受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的影响外,也受接受者身份、地位、个性、观念乃至所在地域制约,当然也与我们考察的角度有关。在二千多年的屈原解读史上,无论其政治举措、文学成就、思想路线、还是地域特质与个性品格尤其爱国精神,都曾成为专门的考察对象,也都存在着分歧与争议。其实只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方法来对待历史,屈原就会为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取之不竭的源泉。比如爱国,可以有不同层面不同范围,可以成为不断迁移的久远传统。我们欣喜地看到,学者们对屈原的爱国问题既作了大胆的质疑,也作了深刻的剖析,并部分地运用到了影像屈原的建构上来。张正明先生在爱国的内涵与外延上找依据,提出周人所爱之国实有“乡国”、“君国”与“祖国”三种,屈原爱国思想的历史特点为:爱乡国、爱君国与爱祖国的统一;爱国与恤民的统一;爱国与董道的统一[11]60-65。赵沛霖先生以发展的眼光谈爱国,提出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和爱国精神有三种形态:产生于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侵略者斗争中的爱国精神;产生于封建时代的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斗争中的爱国精神;产生于奴隶制时代的中华民族各氏族集团之间斗争中的爱国精神。这三种爱国精神,产生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与内容,并在纵向上形成了明显的发展系统。[12]郭建勋师从接受的角度论屈原的爱国精神,认为屈原的爱国精神是一个经由后人不断扩张与提升而渐次生成的过程,并指出这一精神在经由历次外患后已然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13]。周建忠先生以专文形式对屈原“爱国主义”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在肯定各家合理观点的同时,认为:战国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并不妨碍我们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发掘与肯定;屈原以实际行动强化了“热爱父母之邦”这一美好情操,对我们民族“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的形成,具有无法估量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周先生还分析说:“困扰我们对屈原爱国主义作冷静、理智研究的因素,主要有‘楚国视野’与‘秦国视野’的不同(空间距离)、‘历史意识’与‘当代观念’的差别(时间距离)。”[14]16笔者注意到,电视剧《屈原》也借孟子之口提出并解释了君国、乡国、祖国的概念。剧中的孟子说:“忠于君王那是爱君国,热恋乡土就是爱乡国,九州大地都是炎黄子孙、无论哪一国都是自己的祖国,只有以天下为知己,像苏秦那样兼六国宰相,那才是爱祖国呀。”电视剧中多次在孟子面前雄辩滔滔的屈原这次并未以什么高深的理论与高昂的气势来辩驳孟子,而是平心静气、质朴诚恳地坦言虽然齐楚燕韩赵魏秦都是自己的祖国,但出于养育与知遇之恩他更热爱自己的乡国、更该效忠于自己的君国,然后这种态度让齐王也感叹:楚国有幸、楚王有幸。
(二)屈原形象定位及悲剧意蕴
1.形象定位
戏剧影视作品中屈原形象的定位及整个作品意蕴的表现也存在着角度与层面的问题,并影响及于主人公性格及具体言行的构造。
从身份、职业、性格、思想、人格、精神、影响等种种角度出发,影像屈原的构建者与评论家家们给屈原作过“道德家”、“殉道者”、“政治家”、“改革家”、“诗人”、“诗歌泰斗”、“狂狷之士”、“爱国者”、“爱民者”、“贵族”、“哲人”、“思想家”、“爱的追寻者”、“人道主义者”、“先知者”、“理想主义者”乃至“伪君子”、“糊涂虫”等种种形象定位。
同一部话剧《春秋魂》,有人将它坐实为“两千年前一场法制改革的记录”,说它“记载了改革者与反改革者的势不两立和残酷斗争”[15]44;有人特别强调屈原的思想、精神、人格的价值,说它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人文精神的精髓,中国知识精英的生命意义、生存价值、人格精神的精髓”[16]15;更多的人两者兼顾。
同一部小说《屈原大传》,丁振海说其中的屈原形象是最悲情的政治家与最天才的诗人的统一[8]84;祝东力强调其中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爱国爱民者,一个悲惨命运的原型[8]87;蒋卫岗说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拥有家国情怀,崇高道德的诗歌泰斗形象[8]88;雷达、陈飞龙、岑杰则提到这部作品的写作态度、政治诉求、与时代主旋律的关系,肯定屈原的民本思想,肯定《屈原大传》在价值观上的引导,认为“《屈原大传》这个题材内容,正好契合了当下我们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导向”[8]88。
同一部湘剧《山鬼》,有人说其中的屈原是“‘可笑可叹、可悲可怜’冬烘十足的理想主义者”[3]23,有人说是“虚伪透顶,敢欲不敢求,出卖灵魂的伪君子”与“道貌岸然,只尚空谈不识时务的糊涂虫”[17]76。
同一部电视剧《屈原》,吴卫华在肯定其“忧国忧民、傲岸不屈”的屈原形象塑造与“爱国主义”主题凸现的同时,还特别阐释它的制度内涵与文化意蕴,认为这部作品“将思考的触角延伸到社会政治制度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意识、法制精神等所遭遇的抵抗和排拒,对人文精神的失落和老人政治的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找到了古人旧事与当下老百姓生活、心理的契合点,做到了人性化的阐释历史和塑造历史人物。”[7]111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文艺作品中的屈原形象与主题意蕴可以有多层多面。影像屈原的建构既要有多元充足的类别与生动丰满的个案,也要尽可能让一些经典个案富含多层多重的意蕴。
2.悲剧意蕴
当我们将表现屈原的戏剧影视作品定位为悲剧后,就要全方位多层次地思考这些作品的悲剧意蕴。
从悲剧主体来看,它既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国家民族的悲剧。
屈原的悲剧,是“改革者的悲剧”[18]33-34,是“先知先觉者的悲剧”[16]15,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生活在一个非理想时代的悲剧”,“一个政治上的失意者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是有着普罗米修期式救世精神与情怀的“英雄悲剧”[7]112,……在评论家们眼中,虽然形象的定位与悲剧的内涵有着侧重与分歧,屈原作为悲剧主人公的身份却不容置疑。
需要强调的是,屈原的悲剧同时也是国家民族的悲剧。因为屈原代表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因为屈原的爱国爱民精神与勤勉执着态度可以迁移、值得传承。
所以吴卫华说电视剧《屈原》既是“胸怀大志、壮怀激烈的屈原被如磐的黑暗所吞噬的悲剧”,也是“一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纷争,楚国由盛而衰,最后被历史无情淘汰的挽歌”[7]P112。
所以王雄解读话剧《屈原》说:“在郭沫若眼中,屈原对楚国社稷的眷顾,已经超越了一般民族主义者的价值范畴,实质上乃是对统一中国之理想的关爱,甚至是对天下百姓的关爱。屈原的悲剧自然不仅是楚国的悲剧,更是……全民族的悲剧。”[3]19
不仅如此,先行者的悲剧也衬托出了历史的惰性与民众的麻木。在话剧《春秋魂》中,以鲜灵的美丽生命为殉葬的不只是身居显要的曾侯世家,也有用以求雨的普通乡民,说明历史的惰性既源于上层贵族对既得利益的顽固维护,也混杂有普通民众的麻木与愚昧。显而易见,屈原的先知先觉与特立独行相较于其他历史人物,更利于反衬历史的惰性与民性的弱点。
从悲剧本身的类别与层次来看,它既是社会政治的悲剧,也是历史文化的悲剧与道德理想的悲剧。
郭沫若《屈原》重点突出的是一个爱国者的悲剧,《春秋魂》侧重表现的是一个爱宪者的悲剧、《山鬼》直接展示的是一个爱恋者的悲剧,电影尤其电视剧《屈原》则更具兼综性:爱国、爱民、爱宪、爱恋、爱诗……。但这些还只是社会政治与个人生活层面的悲剧,缺乏深邃的意蕴与久远的感染力,所以影像屈原的建构者与批评者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升屈原悲剧的层次,将屈原塑造、阐释、期盼为先知先觉者、理想主义者、殉道者、真正的“大诗人”,将作品的悲剧冲突上升到历史文化与道德理想的层面,甚至追索为终极与永恒的形上矛盾。这样的定位、评论或期盼有助于影像屈原建构中屈原形象的具体塑造。
3.性格内涵
在文艺作品中,性格决定着人物形象的本质特征,显示着人物形象特殊的美学价值。对屈原性格的评价处决于评价主体的身份地位与认识水平,也影响着戏剧影视作品中屈原形象的构建与作品意旨的定位。
从汉代开始,人们对屈原性格上的“缺点”就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创作家们与评论家们还在为要不要展示屈原性格上的“毛病”而纠结不已。在《屈原大传》的研讨会上,祝东力与颜慧都提到要写屈原缺点的问题,一个认为写缺点可以解释屈原政治上失败的原因,并籍此校正儒家传统总是强调人的动机之论,一个认为加上性格上的一些毛病可能会让人物更加可亲可爱,也更易于接受;作者熊诚则列举屈原“性格偏执”、“道德有洁癖”、“瞧不起同僚”、“一根筋”等缺点,并解释说他们不是不敢写,“是不敢编造虚构的故事和情节”[8]85。
笔者倒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虚构故事和情节,而在于对整个作品的定位。如果你只是将它写成接近生活的喜剧与正剧,而且不打算挑战相传已久的传统与体制,你就按中庸的标准去展示屈原“偏执”的毛病。如果你立志要创作一部感人肺腑的悲剧,并于中寄托几千年来士人阶层乃至人类社会追索不已的理想,你就将世俗眼中的毛病理解为屈原独有的精神气概。因为真正的悲剧冲突是不能调和的,从高处看,屈原式的困境更应该是国家体制的困境、历史文化的困境乃至人类文明进程中永恒的困境。
三、影像屈原的叙事技巧
(一)兼顾各类叙事要素
影像屈原的构建终归要落实到叙事艺术上来,其中重点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与话语方式的讲求。
1.形象塑造
如前所述,形象的塑造受制于作品的题旨倾向与主要人物屈原的评价定位,落实到技术层面,则要在人物事迹的经营、人物关系的建构、人物命运的安排与人物肖像的设计上下功夫。
电视剧《屈原》便有效地利用了历史盲点所留下的想象空间,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让齐王将义女紫珍许配给屈原作妻子,并以婵娟为紫珍使女,将南后、郑袖合为一人,并虚构郑詹与郑袖的父女关系、郑袖与子兰的母子关系,把山野女孩杜若子塑造成天真无邪的女神,使家奴庄矫一步步成为农民暴动的领袖……。这些安排遵遁历史规律与性格逻辑,合乎艺术原则与审美期待,有利于绾合不同人物、构造不同阵营,以加强矛盾冲突、丰富人物性格。
影视剧《屈原》,包括即将改编成电视剧的《屈原大传》,在次要人物尤其楚王与南后形象的塑造上也颇为用心,他们的正邪两赋必然引导读者去思考屈原悲剧命运的更深根源与现实意义。
当然也可以突破、也可以创新,只要是主题和剧情需要,湘剧《山鬼》中的屈原便是处处遭人戏弄的荒诞形象。
2.情节结构的安排
情节结构的安排关乎事件本身的可接受性与作品主题的显明性。
话剧《春秋魂》以反对人殉作为情节贯穿线,突出了变法图新与遵循祖制之间激烈的冲突。电视剧《屈原》以主人公屈原几度沉浮终因国破而投江的悲剧命运为主线,以家奴庄矫每受欺凌终于揭竿为旗领导暴动为副线,另外将屈原与杜若子、屈原与宋玉及景差、屈原与庄矫、屈原与齐国君臣等种种关系都以纵横交错的线索牵合起来,使之既立体复杂,又不离战国背景展示与屈原形象塑造的需求。情节结构本身也可以多元多类。在何益明看来,历史剧《屈原》的艺术结构便是:开放结构与闭锁结构的合成、团块结构与线条结构的合壁、情绪结构与情节结构的合一[19]。央视在拍的大型纪录片《屈原》,原本选取《橘颂》、《九歌》、《离骚》、《哀郢》、《怀沙》、《国殇》等六部作品为结构框架,方铭先生认为以屈原作品统领分集会有排他性,应该选取更有代表性和丰富内涵的作品,这个目录中《国殇》本属《九歌》,而《天问》这样一部体现屈原深刻思考的作品却没有体现,显然是缺憾,还有每部的篇名,未必由一部作品统领。方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六集结构,认为第一部的中心应该写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家,第二部中心写屈原是一个想有所作为,并且有政治坚守的政治家,第三部写屈原是一个有深沉思想的政治家,第四部写屈原是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文学家,第五部写屈原是一个追求社会公正的悲剧文人,第六部写屈原对后世的影响[9]6-7。这个纪录片最后的结构不得而知,在目前能看到的脚本里,六集结构所选作品分别为《橘颂》、《九歌》、《离骚》、《哀郢》、《天问》、《怀沙》,应该吸取了方先生的一些意见。至于坚持以作品统领并命名分集,可能有人、文并重,互为推介的好处,并便于大致按纵向历程叙述屈原的生平事迹。方先生的那个应该算是横向的结构,作为纪录片,横向的结构便于展开,也更具有独立性。其中核心是将屈原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的身份、事迹、精神说透。作为政治家,屈原是有坚守、有眼光、有思想的;作为文学家,屈原是关心楚国命运的、追求社会公正的;不管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文学家,屈原都是特立高标、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这个结构显然在作品的内涵上作了充分的考虑。
3.话语方式的讲求
叙事话语涉及叙事的人称与视角、时间与空间、文体与修辞、表演与影像等诸多方面,都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关键要素。在影像屈原的建构与批评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或自发或自觉的努力。
人称与视角的转换在古代屈原戏中就有,晚清胡盍朋传奇《汨罗沙》的第十九出《收场》,即以副末旁白的方式点破前面屈原还魂复活的情节不过是“赚得你仰天大笑”的“逢场作戏”。在古代戏曲中,演员是可以临时性地跳出人物直接与观众交流的。在时间与空间的展示方面,古代戏曲更具有虚拟性、写意性。现代屈原戏也多少受传统戏曲的影响,列斌就注意到了话剧《春秋魂》所用的写意手法:活用舞台空间、改变观众视点[20]19-20。
涉及屈原的戏剧影视作品在修辞技巧与话语风格上应该有着更高的要求,因为屈原本人是最伟大最浪漫的诗人,得用具有诗性特征的作品来加以表现。这些作品的诗性特征可以体现在诗性语言、诗作展示及由此构成的诗意氛围上。在整个的话语风格与修辞特性上,湘剧《山鬼》是别具匠心的,它通过对爱恋的叙述隐喻政治道德理想。王雄先生评价此剧说:“从叙事体制和风格上讲,《山鬼》开拓了新时期历史剧‘非历史化’的崭新路径,加强了史剧的‘陌生化’效应,达到了欣赏与思考同步的艺术效果。”[3]25
在哈佛管理导师课程中,我意识到自己遇到沟通难题时在如何处理、如何说服他人并赢得认同以及如何在需要展示自己的成果时做有效的演讲等方面犯了很多低级的错误,现一一剖析如下:
影像叙事的特别更在于表演与影像技巧的运用,这个恐怕是影像屈原建构与批评中最薄弱的环节。有三篇文章比较集中地谈及到这些问题。一是李霁的《论电影〈屈原〉主题曲中“橘树”的形象》,重点阐述主题曲《橘颂》在电影《屈原》中叙事写人的作用。二是列斌的《深入认识戏剧艺术,增强话剧的表现力——〈春秋魂〉导演手法的赏析》,谈到《春秋魂》导演对色彩、光的认识和大胆有机的成功运用。三是吴卫华的《试论电视剧〈屈原〉的审美意识》,从摄影照明、美术布景、影像构成等方面解读电视剧《屈原》如何刻意追求诗化、风格化的表现。也细致地分析了剧中音乐的地域特性,并对片头、片尾的主题歌曲作了阐释。
(二)处理三重叙事关系
综合起来看,历史人物屈原的影像叙事要注意处理好三重关系。
1.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本真的历史本不存在,人们所知的历史都是曾经梳理过的历史,或者是经由叙述的历史。这个或梳理或叙述的过程难免主观随意的成份,高明的历史叙述在于尽可能通达历史演变的规律,并试图究诘天道与人事之间内在的关联。具体到戏剧影视作品,就是要运用史识,定位史剧、安排“史事”。
2.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史事的安排不仅要合乎逻辑,还要有选择、有寄寓。大事确定叙事框架、勘定人物功过;小事增生情节曲折、丰满人物血肉。更有关乎时代、民族的宏大叙事,以增强历史人物、历史作品的纵深感。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要有寓托,都要指向中心本旨。回到上面的问题,历史演变也有宏观与微观、长段与局部的问题,所以上面这两重关系是相通互补并需辩证看待的。
3.文学与影像的互动
文学与影视分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一凭语言虚构、想象,一靠镜头捕捉、直陈。将想象性、虚幻性的文学改编为具象性、可听性的影视,需要进行符码的转换,这个转换的过程是相当艰苦的。在表现屈原的影视作品中,如何让屈原自身的诗作既尽可能保持原貌,又能通过镜头进行影视的表现,会是一个更大的难题。语言艺术中的屈原形象,已然丰沛,可用镜头来表现屈原,至今少见。因此影像屈原的构建之路还很漫长。好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对话语言可以为影视作品的叙事转换提供基础,而影视媒介又可以直观传播文学形象的内涵意义。
结语
就最大众层面的理解而言,“忠君爱国”无疑是屈原获取的最多的荣誉,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着力强化的内涵。但它忽略了屈原精神的兼融性与多元性。在屈原身上,我们可以找到自修、自律、崇高、峻洁、质疑、批判、创新、法度、力量、忧患、乡国、浪漫、理想等种种忠君之外的质素,其中不少还正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的。
自古以来,对屈原的心性品格与处世态度不乏讥讽与批评,我们当然可以在影视作品中反映屈原所受的这类讥讽与批评,但这种反映应该是严肃认真、公允辩证的。对于屈原这样高标特立的历史人物,我们甚至要以理想的情怀与崇敬的心态,充分运用现代媒介,来传承其所富有的历史精神、民族立场、文化价值、哲学内涵、诗意蕴含。
制作在人,批评也在人,影像屈原的制作与批评队伍需要大大扩充。要吸纳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人,以不同身份,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屈原。郭沫若以诗人而写诗人、以历史学家而写历史,应该是历史剧《屈原》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话剧《春秋魂》上演后,《中国戏剧》组织了创作座谈会,《广东艺术》又接连发表了专门文章,其中不乏来自各个行当的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之音。小说《屈原大传》出版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也联合举办了作品研讨会。研讨会上,作协、文联、理论研究所、出版社、新闻部门、发改委、影视制作等方方面面的人从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运用、现实意义、产业化发展等角度各抒己见,言论犀利中肯。说明严肃的态度与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戏剧影视艺术的健康发展。遗憾的是,两次座谈会都没有来自院校与研究机构的屈学专家参与。事实上,屈学专家与学院派学者所撰的几篇与影像屈原相关的文章都深入细致、富有学理。
就艺术技巧而言,现代影视艺术可资借鉴的东西很多,便是古代的屈原戏中,也有不少至今可以师承的手法。影像屈原的建构,理论比创作还缺乏,需要以叙事学为主的多重学科的介入。
崇高典正的悲剧曲高和寡,所以要在推广与普及上多下功夫。可以有专家的倡议、学校的号召,更要多角度、多层次、多媒介地开发产品。
在这样一个和谐盛世、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影像时代,屈原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大的平台,一个大的资源”[8]87。
[1]何光涛.元明清屈原戏考论[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2.
[2]张克锋.屈原及其作品在绘画创作中的接受[J].文学评论,2012(1).
[3]王雄.屈原:一个历史原型的艺术变迁[J].戏剧艺术,1998(1).
[4]石玲.蛇神牛鬼发其问天游仙之梦——《化人游》初探[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
[5]吴玉杰.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剧的艺术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吴卫华.电视剧《屈原》的当代意识[J].三峡文化研究丛刊,2002(4).
[7]吴卫华.试论电视剧《屈原》的审美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8]杨娟.《屈原大传》作品研讨会综述[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5).
[9]方铭.认识屈原和表现屈原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对大型人文纪录片《屈原》拍摄的几点意见[J].职大学报,2012(4).
[10]吴卫华.历史叙事与历史意识——电视连续剧《屈原》谫议[J].云梦学刊,2006(5).
[11]张正明.屈原爱国思想试析[J].江汉论坛,1986(3).
[12]赵沛霖.屈赋研究论衡[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
[13]郭建勋.从“恋乡”到“爱国”[N].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2004,11,24.
[14]周建忠.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A]//中国楚辞学:第一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15]刘傅燕.浅议《春秋魂》的“旧题出新意”[J].南方论刊,2000(2).
[16]廖全京.选择的痛苦与阐释的艰难——话剧《春秋魂》漫论[J].四川戏剧,1996(1).
[17]视见.这是屈原吗?[J].剧本,1987(17).
[18]童道明.新的屈原——看《春秋魂》[J].广东艺术,1995(4).
[19]何益明.论历史剧《屈原》的艺术结构特征[J].湘潭大学学报,1985(增刊).
[20]列斌.深入认识戏剧艺术,增强话剧的表现力——《春秋魂》导演手法的赏析[J].广东艺术,1996(1).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Image of Qu Yuan
LIU Wei-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unan Industry University,Zhuzhou,Hunan 412007)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Qu Yuan requires multiple abundant classification and vivid colorful individual cases,and also endows multi-dimensions of meanings to some classical cases.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Qu Yuan and such kind of images should be formal historical tragedies.From the subject of the tragedy,it is not only an individual’s tragedy,but also the tragedy of the nation.From the type and level,it is a social and political,historical and cultural,moral and ideal traged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Qu Yuan finally will be demonstrated by narrative art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shape of image,organization of the plots and ways of discourse.Historical and logical unity,macro and micro integration,literary and image interaction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process.
drama;film;TV;Qu Yuan
I207.3
A
1674-831X(2015)02-0076-07
[责任编辑:刘济远]
2015-02-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ZH05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BA116)
刘伟生(1970-),男,湖南涟源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及戏剧影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