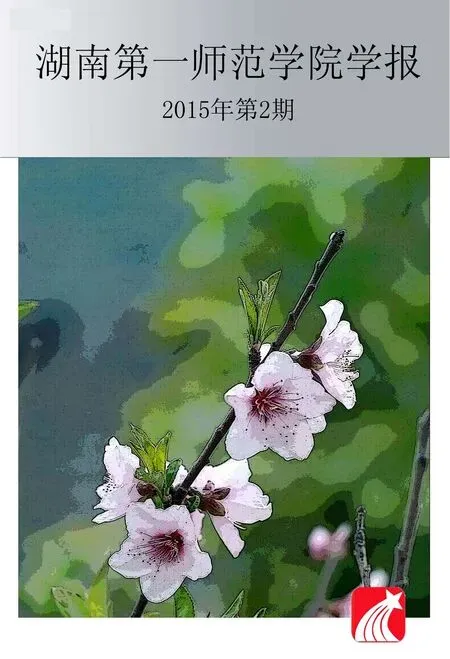青年毛泽东自学思想探析
申鸣凤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继续教育部,湖南长沙410205)
青年毛泽东自学思想探析
申鸣凤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继续教育部,湖南长沙410205)
出于对当时学校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条件的不满,毛泽东在求学期间坚持自学。通过刻苦研读,问难论辩、社会实践等方式,掌握了学习的自主权,让自己在各方面得到了充分锻炼,走上了成功之路。
青年毛泽东;自学;第一师范
在青年毛泽东成才的道路上,自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青年毛泽东学问的积淀,能力的培养,思想的成熟大多来自他的自学,可以说,毛泽东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自学思想和自学方法对于现代青少年的成长以及学校的人才培养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青年毛泽东的自学经历
毛泽东的自学经历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期。当他还在韶山读私塾的时候,就对私塾教育特别反感。他不喜欢读经,对中国古典小说却情有独钟,尽管老师反对看这些禁书并严加防范,毛泽东也是“常在学校里阅读,当老师走过来时,就在上面盖一本经书。”在这样的条件下,年纪不大的毛泽东读完了《岳飞传》、《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1907-1909年,毛泽东辍学在家。虽然是在家务农,这两年却是少年毛泽东成长道路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极爱读书的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学习,而是坚持自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继续读中国的旧小说和故事”。这两年的自学,让他开始“有了相当的政治觉悟”,忧虑祖国的前途,“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122-126
在经历了短暂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以及入伍当兵后,1912年,毛泽东考上了著名的省立第一中学。但这个“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的学校也无法让毛泽东满意,就读6个月后,他得出一个“还不如自学更好”的结论。退学后的毛泽东,为自己订了一个自学计划,坚持每天都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毛泽东怀着浓厚的兴趣,并以超常的毅力,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毛泽东很有收获,对它评价很高,以致在几十年后与斯诺的谈话中,他还强调“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这对我极其有价值。”[1]134
如果不是父亲不同意他自学,拒绝供给费用,这样的学习也许将继续下去。家庭的要求以及自己对未来职业的思考让毛泽东最后报考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来合并到第一师范),并在这个学校坚持学习5年半。尽管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了5年半并顺利毕业,但他对这个学校一直不满意,“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很多次,他都想退学,但在杨昌济、黎锦熙等人的劝告下,呆在学校,“孳孳不敢叛”[2]30。尽管毛泽东留下来了,形式上在湖南一师读书,实际上一直坚持自己的读书计划。据当年同学的回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除少数几门功课,比方杨怀中先生的讲课及国文课之外,有自己的学习计划;一般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他根本不去上课,而专读自己选读的书。”[3]44即使有时勉强去教室,“不管讲台上的教员在讲什么,他总是在看他自己带来的书。为了顾全大局和教员的面子,他把讲的教科书摆在上面,下面盖着他自己要读的书。”[4]56学校碍于校规,认为他是品行不正,几次决定要开除他出校,幸亏有杨昌济、袁仲谦、王立菴等老师力保,才未能实行。
1918年,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根据他毕业前的打算:“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2]89至于如何读书,他已不再愿意进学校。在后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2]441从第一师范毕业,毛泽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以后他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他的自学。
二、青年毛泽东对学校教育的不满
毛泽东之所以主张自学,主要源于他对当时学校教育的不满,新式教育的诸多弊端,让他对学校教育极端反感。
(一)人才培养无视个体差异
对于毛泽东而言,学校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他认为,人的性格各不相同,才能各有高低,领悟能力也有很大差异,而学校完全忽视这些。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学校教育整齐划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毛泽东看来,“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泛,高才的相与裹足”[5]。再加上毛泽东个性太过鲜明,“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2]441,“好独立蹊径”[2]7,不愿墨守成规。因此,尽管一师范在当时属于开明进步的新式学校,但对于毛泽东这种个性极强,思想独立的天才型学生而言,整齐划一的要求对他是一种限制和囚困,也限制了他兴趣的发展,个性的发展,导致了他对学校教育的深恶痛绝。
(二)课程设置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作为培养小学师资的省立第一师范,开设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国文、习字、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农业、商业等17门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注重小学教师综合知识的培养,体现了中等师范的办学特色。但对于毛泽东而言,当一名小学教员并非他的最终理想,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毛泽东“想专修社会科学”。因此,除了修身、史地等课程外,其他自然科学、艺术类课程无法令他感兴趣。他后来与斯诺的谈话反映了当时他的这一心态:“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程。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1]136。课程设置的繁杂,让毛泽东无法集中精力专攻其所好;而在自然科学、艺术课程上的短腿,让心气甚高的毛泽东大受打击。他可以做到每天“从早至晚,读书不休”,而“惟甚畏开学上课”[2]52。因此,走出课堂自主学习成了他解决这些矛盾的不二选择。
(三)程度太低,俦侣太恶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湖南省内较有影响的学校,有“亚高学府”之称。学校有很多名流,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也有一批杰出校友,如蔡和森、何叔衡、周世钊、李维汉、肖子升、肖三等。但这所学校毕竟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在毛泽东眼里,除了杨昌济、黎锦熙等少数老师让他佩服外,对其他老师并不认可。他的姨兄王季范(时任第一师范学监)曾劝他上课,因为要照顾学校规则,毛泽东回答:“那我就要向教员提出各种问题,教员答复不出来的时候,他怎么下台呢?”[3]45应当说,当时的毛泽东,在他自己热爱的学科领域,水平已超出了许多学校的老师。事实上,毛泽东还在报考第四师范时,校长看了他的作文试卷,就深为叹服,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6]12同样,当时毛泽东的水平,也超出了同期的大多数同学。在年轻的毛泽东眼里,他就读的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而他认为,在这样的学校读书“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2]30他一直心存退学的念头,在很多的书信中都提到“必欲弃去”,只因找不到更好的读书地方,只好留下来。因此,在这所学校,毛泽东“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读书计划在那里自修,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则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去止课。教师们都能谅解他,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的学生。”[6]13
三、青年毛泽东的自学方法
对于毛泽东而言,多年的实践让他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的自学方法。正是这套方法,让毛泽东感到非常自信,获益匪浅。
(一)刻苦研读
学生时期的毛泽东尽管想专攻社会科学课程,但他对于将来做什么,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世界的“大本大原”,即“宇宙之真理”,而“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而能否获得大本大原,既是人生立志之根本,也是区分是否成才的根本。在他看来,“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很显然,青年毛泽东对自己读书的定位是为“圣人”之学,因此,他对于普通的课程教学并不感兴趣,“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2]85-87而要探求本源,格物致知,主要的方法就是读书。正因为如此,他博览群书,“靠自己发愤求学,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凡是古今中外的一切名著—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外国人著作的翻译,哲学,文学……他无不浏览。”[3]41面对浩如烟海的学习内容,青年毛泽东在黎锦熙、杨昌济等人的引导和启发下,定下了“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2]7的为学之道,又自创了“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最后“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2]441根据毛泽东一师同学萧三回忆,“当抓住一个中心问题时,即专门研究它,一切别的杂乱功课就不管了”,“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把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无论新的旧的都找了来,于是继续不断,一本一本地研究。”[3]56“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是专门在研究地理,和专门研究历史时一样的办法——抓住中心,旁征博引,不离其宗,一直到有了相当的成绩,才告一个段落”。[3]69除了博览群书之外,他还大量阅读当时的报刊杂志。毛泽东在一师范五年总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元钱,而其中三分之一用在订报纸上了。大量的读报,让他在博古之余,还做到了通今,青年的毛泽东对时事了如指掌,对民间疾苦也了然于心。
(二)问难论辩
尽管主张自学,但毛泽东所主张的自学并非离群索居,闭门学习。因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2]8“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2]505他主张个人的学习应与老师的指导以及与同学之间的切磋讨论结合起来。尽管他反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厌恶当时的学校教育,但他对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情有独钟。他在很多文章、书信中曾历数学校教育的坏处,但对书院教育不乏溢美之词。在他看来,“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因为在书院里,“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5]。中国古代书院那种师生平等、生徒自学、相互切磋,问难论辩的学习方式特别为他所欣赏。正因为如此,尽管毛泽东对课堂教学相当反感,但对课外的师生讨论、共同研究却很感兴趣。他将“弘通广大,最所佩服”的杨昌济、黎锦熙等老师视为学习、生活中的导师,“甚愿日日趋前请教”[2]31。黎锦熙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仅1915年4月至8月,毛泽东就拜访他近20次,同他讨论的问题涉及“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等[7]。对于杨昌济发起成立的哲学研究小组,毛泽东更是积极参加。不论是周末还是课余,毛泽东与大家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讨论“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8]。从1915年至1917年,这种讨论多达上百次。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参加社会进步团体船山学社组织的各种讲座;走出校门,广交朋友,“效嘤鸣而求友声”;同时对于“长沙城里不时有从外省来的所谓名流学者,泽东同志常一个人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虚心请教,想从他们得到一些新的知识。访问回来之后,他又常向同学们谈论他对于被访问者的印象,并加以自己对他们的批判”[3]42。正是在这种求教和讨论中,年青的毛泽东学问精进,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强调,“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惜如前,未可知也。”[2]13
(三)社会实践
在毛泽东的自学思想中,“行”或者说”实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毛泽东而言,这一方面是长期浸淫湖湘文化中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治学传统的结果。他继承了杨昌济的“力行”主张,“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9]365。毛泽东指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2]546另一方面,这是他对当时学校教育缺陷反思后的结论,他指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撅,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2]9“4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2]415正是这种原因,毛泽东对于“腐朽的校规,他采取消极的态度。但自己发愤求学,锻炼身体,兼作各种活动,毛泽东同志却是特别积极的。”[3]45纵观毛泽东在一师范就读期间,尤其是最后三年,他对参加实践活动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积极担任学生自治组织的干部,自1915年起至1918年毕业止,他每个学期都担任了学友会的重要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学友会各项活动空前活跃。在此期间,他于1915年组织学生进行反袁世凯活动,又领导校内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1916年秋成立学生课外志愿军,培训学生初步掌握军事技能;1916年12月以学友会的名义开办工人夜学教育实践,在夜校里,毛泽东亲自给工人讲课。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帮助学校附近的工人学习文化,同时办夜学也是一次难得的实习经历,“设此夜学可为吾等实习之场,与工业之设工场,商校之设商市,农校之设农场相等。”[2]951917年11月他成功地组织了一场保卫学校和智缴北洋溃兵枪枝的战斗。为了进一步了解社会世态,熟悉风土民情,调查当地的历史、地理,不断增长新的知识,毛泽东走出校园,开展了较为深入的农村调查。1917年暑假,他与肖子升利用暑假游学。这次游学,历时—个多月,行程900华里,达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广大农村。1917年冬和1918年春,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调查。大量的社会实践,让毛泽东做到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开阔了眼界,了解了社会,也培养了他各方面的能力。
综观毛泽东的学生生涯,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学中度过的,大部分的学问来自于自学。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志于社会科学,有着极强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又有着鲜明个性的人来说,自学也许是一种最好、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在长期的依托学校进行的自学中,毛泽东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1917年6月全校的400多人的“人物互选”中,毛泽东名列榜首,他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通过这几年的自学,他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并“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1]135这些为他以后从事革命活动,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自学的成功,也为当今的中国教育事业留下了不尽的思索。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3]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4]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5]建党初期毛泽东的几篇文稿[J].党的文献,2011(2).
[6]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05.
[7]1915~1920年黎锦熙日记中有关毛泽东的记录摘抄[J].党的文献,1999(3).
[8]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
[9]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0: 365.
Exploration on the Self-study Thoughts of Young Mao Zedong
SHEN Ming-feng
(Department of Continuous Education,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205)
Out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curriculum setting and teaching conditions,Mao Zedong chose and adhered to self-study.Through hard work,discussion and debate with others,social practice,he made himself fully trained in all aspects and went on the road to success.
young Mao Zedong;self-study;Hunan First Normal School
A84
A
1674-831X(2015)02-0072-04
[责任编辑:葛春蕃]
2015-01-12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3C139)
申鸣凤(1982-),女,湖南邵阳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馆员,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