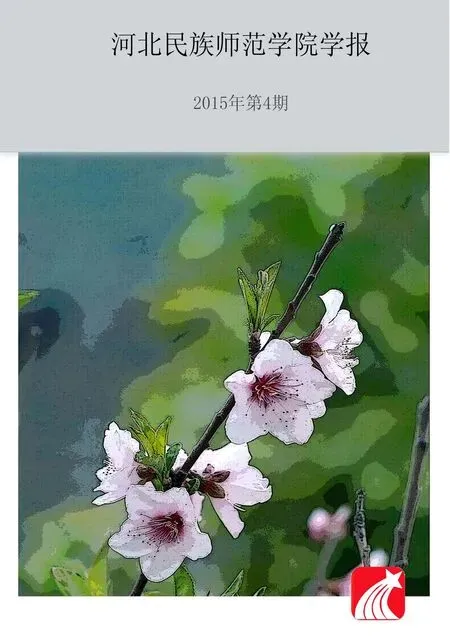试论潘云贵散文诗的情感与艺术特质
熊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试论潘云贵散文诗的情感与艺术特质
熊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散文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近年来在创作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其中一大批青年散文诗人的涌现更是其集中体现。潘云贵作为一位年轻的散文诗人,近年来在艺术探求和精神提升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尝试,是90后散文诗人的代表。潘云贵的散文诗灌注了浓烈的人文内涵,既表达了当下复杂语境中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思考,寄予了沉重的悲悯情怀和高远的社会理想,也凸显出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风格。
散文诗;潘云贵;情感特征;艺术特质
我们生活在信息便通和物质丰富的时代,享受着科技文明给生活带来的各种便捷与高效,但与此同时,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冷漠而脆弱的时代,人类为了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而抛却了心灵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一直遭受着政治意图和局部利益的侵扰。作为对世界、生活和生命有独到理解的诗人,潘云贵在他的散文诗中灌注了浓烈的人文内涵,他的作品既表达了当下复杂语境中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思考,也寄予了沉重的悲悯情怀和高远的社会理想。
一
优秀的散文诗应该是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结合,潘云贵的作品是对生活现实的观照,他痛心于我们生存环境的污染和生活空间的异化,从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维度上对当前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批判,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现代人在追逐物质利益和满足个人欲望的过程中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严重的生态污染危及着各种生物的生命安全。在一个无限伟大而又无限渺小的世界里,人类赖以存活的蓝色星球悬浮在宇宙中,如同一片棕榈树叶漂浮在偌大的湖面上。存在本身是虚无的,只有植物种子发芽时的“颤动”,昆虫飞舞时翅膀的“振动”以及鸟群向高空翱翔时“撒下清脆的音节”方能显示出地球的生机与活力,而被喻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只是在“年轮里”、“洞穴中”和“墓碑下”毫无生气地“伴随衰老、意外、疾病而深眠”。生命具有无法摆脱的悲剧色彩,我们为着那些与生活毫不相关的声名活着,除了跳动的心脏外完全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即便人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物种,如果死去也会“与最微小的菌类无异”,所以我们应该维护“心脏的跳动”。但人类的可悲之处在于,我们在设法追求虚无的东西时却忘记了生存是第一要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潘云贵在《回归》中有如下诗行:“森林之外的工厂飘浮幽灵般的灰色,阴沉沉的现代文明正隐藏所有真相。道路与建筑间飘满自然的亡灵。”酸雨毁坏了树叶并腐蚀了钢筋水泥,工厂排放的气体污染了鸟群的天空并掠走了肺部的功能,现代工业文明用华丽的建筑和超越想象的技术掩盖了其潜在的危害,我们生活在“无法消退的雾气里”,无法送还的电波和辐射中。在压抑浑浊的环境里,相比都市的灯红酒绿和昼夜喧哗,诗人更愿意接受乡下清淡如水的生活,他“悼念大工厂未曾到来的时代,风像青草一样鲜嫩,黄昏下的花田像片金色的海”。(《熄火的城市》)可如今人类不仅在扼杀自我的生命,而且给其他物种也带来了直接的威胁,我们的作为和生存状态何其可悲?人类“回归”自然万物的行列与天然无忧的生活之途漫长无边,甚至背道而驰地演绎着南辕北辙的荒唐“追求”。此外,潘云贵在《黎明尚远》《工业城市》等诗篇中均对工业文明给人类和生物界造成的生存危机进行了严厉的控诉,并对昔日清新宁静的乡村生活生出几许留恋。
对现代社会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忧思,对工业文明和物质欲望的厌恶,对传统文化和思想遗落的叹息等情感让潘云贵产生了回归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的愿望,他希望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能够还原成清澈纯洁的蓝色海洋。带着这样的人文关怀和理想情结,潘云贵创作了《人的一半面孔是鱼》,其中“鱼”这个意象既指心思处于纯洁阶段的人,又指处于自由生活状态的人;“海洋”这个意象则是一个滑动的能指符号,可理解为与陆地相对的区域,也可理解为生活的现场,而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海洋”可能是没有融进浑浊之物的场所,也可能是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需要特别阐明的是,诗人笔下的“海洋”主要喻指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诗人希望人类就像自由自在的鱼群那样“蠕动如云”,在“干净如瓷,一潭清泉”里简单悠闲地生活着。而我们生活的现实空间已经沦为“混进浊物的汪洋,从未消退,只在混沌中伪装透明,散漫地于空气中吸食,吞咽和倾吐个体的命运。”只有到了夜晚,我们独自面对内心的时候,才可以卸掉白天的伪装而倾听心灵真实的声音,那些“复杂困窘的人事总在无灯之夜模仿大海的潮涌,席卷而来”,人事的黑白、善恶、真假不断搅合并重组成俗世的面目。每每此时,潘云贵便开始“怀念一只鱼的自由和单纯:水、食物、游动。简单生存,仅此而已。”人类自以为“高贵,太在意一种仰视”,因此常常被各种欲望撕扯得精疲力竭。诗人希望人类像鱼群一样生活在绿色的海洋里,而现实却恰恰相反,我们“无果地被现实剥夺了鳞片、光鲜的梦,连站在洪流前的勇气都没有。”在无奈的现实语境中,“鱼的故事只能由鱼去演绎。人只在童年时拥有鱼的指纹,成熟时便已交还大海,像陌路人从相视的镜中走来,即使认出彼此,也要学会背离。”我们为什么不能像鱼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一直像童年一样拥有“鱼的指纹”?我们为什么要残酷地学会背离纯洁和天真?在诗人看来,欲望的大海淹没了人本初的模样,而人与人之间的“数落、赞美、嘲讽、讥笑和伤害”又让现实矛盾重重,我们一旦离开大海上岸之后,“席卷而来的欺骗、麻木与贪婪,在加速水蓝色星球前程的穷途与末路。”我们就身不由己地被带到了浑浊的世界里。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很多人就像鱼一样在其中肆意徜徉游动,“它们健硕有力,从江河到深海,一路划开云烟与叠嶂,像一张弓拉开,惊慌的雁阵垂落。”古人在中国人文社会的汪洋大海里自由穿梭,阐发自己对江山社稷、生命情感的看法,很多思想在历经沧桑之变后仍然言之凿凿。然而,今天“在墨一样的天空下,在流水线上”,我们被动地变得如同失去鳍的鱼群,找不到平衡、推动以及引导自己前进的动力,我们的身上早已没有祖先的光芒,大海已不是昔日的大海,我们亦非昨日“带鳍”的“鱼类”,精神和肉体的蜕化成为现代人的集体标志。现代科技看似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但人却失去了自我隐私和活动自由,各种条例和程序规定着我们日常的路径,各种摄像头和电波检测者我们的行动,各种证件制约着我们的身份,导致“我们逐渐成为透明的鱼或者一个赤裸的人,鳞片和机体不再深藏秘密和生命。”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由人和精神世界建构起来的人文环境在物质欲望的冲击下已经坍塌,而我们的生存环境在工业生产的污染下也失去了昔日的清澈:“在多久以前,没有工厂、马路、矿井、脚手架、争执和妥协,鱼只是鱼,吞吐自己的泡沫,摇摆自己的长尾或者短尾、燕尾或者蝶尾。”人类对物质无休止的追求带来了环境的恶化,我们再也不能像鱼游海底那样轻松自由地生活,我们不得不面对生存空间的异化,不得不面对“望不穿的公司大楼,穿不透的车水马龙”。因此,诗人希望回到“母亲的子宫”,因为那里“纯粹的泡沫多么丰盈与可爱”,那里是孕育人类生命的原初海洋,也是人类最自在和安全的生活场所。
诗人生活在当下,却对现实社会的工业和都市文明产生了反感,那些“活在昨日的村庄、田野、山林和果实,已经去世”,(《去黑暗里找寻一些东西》)他希望离开“齿轮继续转动,城市没有停下”的生活现场,在黑夜里和回忆中找到一些接近自然的东西。诗人在《鹏的眼泪》中借助庄子常用的文化意象大鹏的翅膀,标示出对现实生态环境的担忧:“青峰在黑暗中碎裂,露出铜色的本身。树木抽离地表,鬼魅般飘向空中。”因为工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开垦荒山,砍伐森林,地球到处布满了伤口。令人忧心的不仅仅是生态的破坏,而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不可化解的隔膜,即便传统的“金文、铭文、篆书或者隶书”摆在眼前,我们也“早已辨认不出祖先的文字”。因此,诗人写道:“鹏的翅膀上有一丝哀泣的血痕”,环境遭遇了严重的破坏,传统文明遭遇了严重的遗忘,我们今天的“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人们从“发展”中又究竟获得了什么?此处诗人用的是“血痕”而不是泪痕,道出了诗人对传统文化失传的担忧,对承传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强烈心愿。
除开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忧思之外,潘云贵的散文诗还深入地思考了人伦社会的阴暗面孔。《最后一只蝴蝶》这首散文诗充满了隐喻性,“银杏树上唯一闪耀的叶子”暗示着人格化的诗人,而这片叶子的下落并“很快被尘土覆盖”,表明品格高尚之人也许会在生活的“染缸”里被各种陋习或俗礼所改变。世界是残酷的,当你处于“堕落”之途或力求远离尘埃时,所有人都“冷漠”地看着你在泥沼中越陷越深,没有人会理睬或帮助你完成夙愿,也“无人会同情那只即将死去的金色蝴蝶”。“金蝴蝶”的跌落预示着人类社会理想情怀的陨失,该诗表达了诗人对社会价值和道德理念的担忧。潘云贵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淳朴的,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和谐的。《天真皮肤的同类》中的“萤火虫”的光亮牵动着童年时期纯洁而美好的梦想,但这些梦想在现实的“夏夜”里只能“忧伤而行”;“乌鸦”的黑在时间的递进中一再加剧,如同月光下人类“抖动的伤口”。为什么这些美好的事物总会“被时间熏黑”?诗人在此诗中流露出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他希望“透明的人类”不会被尘世玷污,我们应该与那些负面的事物“绝缘”,像孩子一样脚踏跷跷板,“眺望银河”并仰望星空,身旁栀子花开,一切都天然而美好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与人类一起诗意地在大地上栖居。
我们无法选择既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世界尚且如此,但我们的内心却会生出几许理想的光芒。潘云贵通过他的散文诗给我们展示了“荒原”般的现实,也通过他的作品唤起了我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二
很多人在尘世的喧嚣中追名逐利,富贵荣达之后仍然会形同草木,消隐于山林和尘土之中。世间万物都有相同的归宿,所以我们生前不必计较太多的得失,也不必歇斯底里地傲视万物,每个人都会臣服于无情的生命定律。
在光明中想到黑暗,在希望中看到绝望,心思细腻的潘云贵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和最终归宿:好景怡人不常在,好花美丽不常开,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更多的是平淡乃至凄清。在《大地的列车》一诗中,诗人清晨看着树枝“相互拉手”,听着“鸟雀被温暖的爱唤醒”,心中顿时充满了对生活和大地的热爱,由此衍生出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这首诗看起来无异于在诠释“一日之计在于晨”的陈理,倘若如此便无新意可言。但接下来的诗句“山楂花簌簌落着,年轻的心事飘满世界”,突然将一种高昂的情绪带入低谷。山楂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就像有人在簌簌地掉着眼泪,此时“年轻的心事”一定包含着忧伤,这种情绪迅速弥漫在诗人身处的世界里,它让天边的晨曦黯淡无光,让远处的杉树披上了“冷”而“黑”的外衣。为什么诗人会在充满希望的清早产生愁绪呢?诗人置身无人的清晨,看着苏醒的大地,想着人生天地间的虚无意义,不禁悲从心来。“大地是尘埃组成的列车”,倘若大地是尘埃构成的,寄居大地的人类也同样来自尘埃,我们的成败得失于浩淼的宇宙而言更不足为道;倘若大地是一趟列车,从清晨的时间开始出发驶向未来,个体生命也将随着无数个清晨的到来而奔赴未知的前程,“一节节”车厢看似充满光亮,一生也就悠忽而过。因此,这首诗蕴含着无限悲凉的意蕴,道出了生命的渺小和短暂。类似的情感在《嘘》中表现得更加直接,“嘘”的声响是诗人力图保存江南春晨美景和生命萌动状态的心之声,但就是在这个“清澈如同少年”的景致里,潘云贵的情绪却低落了下去,因为他在“崭新的生里有对死的担忧”。华年易逝,我们的韶华时光如同昔日光鲜照人的花朵,最后便会蜕变成“恹恹的雌蕊”,“不久便有花落”。绚烂的樱花预示着春之盛事和夏之繁盛,但灿烂之后也就预示着花期的结束和一段春之心事的终结,所以诗人说“樱花里住着爱情的亡灵”,爱情终归要从激情步入平实,生命也终归要从青春步入暮年。
《兰亭序》是潘云贵散文诗中的佳品,综合了诗人对人事、生命、情爱以及历史、文化产生的复杂思考。潘云贵取王羲之的经典散文《兰亭集序》(又称《兰亭序》)之名为自己的散文诗命名,是因为诗人在阅读了王羲之作品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在山阴兰亭举行春游聚会,每人赋诗一首,整理成“兰亭集”,今日所见《兰亭集序》遂为王羲之为该诗集所写之序。《兰亭集序》首先记叙兰亭周围的美丽山水和聚会时的热闹投缘之情;接着抒发王羲之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虽时逢盛世,但“盛世不常”,虽此刻人生得意,但“老之将至”。因此,王羲之作品表现了魏晋以来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对世事无常和人生短暂的喟叹,与后来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的豪迈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事实上,由盛世想到衰败,由年华正盛想到衰老将至,在月圆之夜想到月亏之时,这种思维方式和行文抒情正是潘云贵散文诗创作的主要路向,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阅读了王羲之的文章之后会产生“相见恨晚”的感觉。潘云贵在他的散文诗《兰亭序》中颂赞了王羲之书法和文字的柔美坚硬,追思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文友在水边草地上吹奏弹唱、吟诗附和的热闹场景。人生得意之时应当豪饮千秋,“岁月不回头”,世事变幻无常,且当“今朝有酒今朝醉”。这首散文诗虽属潘云贵与王羲之的心灵邂逅之作,但毕竟我们生活的年代与东晋有很大差异,历史自那时起又积淀了近1700年,民族文化在承传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夏商周如烟出岫,子规的叫声啼破春晓,青铜从炉火中涅槃,铿锵的打造声,远了。”但人类的生命观念再怎么演化也逃不过死亡的结局,“人活于世,沧海一粟”,个体生命在漫长的历史面前轻薄如纸,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在浩淼的宇宙中也显得无足轻重。因此,潘云贵在认同人和人类社会单薄无力的同时,认为王羲之的文章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它“只能摘取一个视野,而不是一个世界”。人生天地间,最不能释怀的莫过于风月情感;“人雁南飞”,别离的伤痛自古困扰了多少才郎貌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潘云贵的《兰亭序》最后认为,个体生命在历史和时间的节点上偶然出现,我们应该看淡浮华,“得失莫计,宠辱皆忘”;而我们的心“应如白纸,洁净单纯,没有高墙、密林、深渊、汪洋。它只应是清澈的溪流,钴蓝的天空,与自然的内涵,平静地交流。”在物质和科技迅速崛起的今天,在欲望吞噬着我们生存空间的当下,倘若生命素朴如此,倘若心绪平静如是,我们便理解了潘云贵作《兰亭序》的初衷和愿望。
生命的真假和虚实不断转换,我们应具备洞察生活与明辨是非的能力。现实世相纷乱复杂,我们的内心如“山阴的湖水”般明澈而清晰地映射出它的倒映,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虚幻的?“有人站在实像中,有人愿意活在虚像里”,活在当下的人们难以辨明是非曲直,总有人愿意蛰居到“虚像”中。倘若虚幻的梦境能够慰藉现实中受伤的心灵,倘若虚幻和梦境并无本质的差异,更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都有自己投射给如烟往事和迷雾现实的“信任”,那“真相”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真相“只会在风的审判里恒久”,但风什么时候吹起,又将会向哪一个方向吹,那些“恒久”的真相有没有统一的审判标准?时间脚步和岁月风尘最终会让遮蔽的东西敞亮,但在近于偏执的主观情感面前,并非只有“真相”可以留存下来。潘云贵在《真相》这首诗中认为真相和虚像是没有边界的,尤其是对富于情绪性和主观性的人类判断而言,二者的存在更是取决于主体的情感趋好。人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很难作出明确的选择,但只要给我们带来片刻美感的事物都值得为之心动。诗人晚上独自一人穿行在“黑压压”的森林中,仿佛置身于无限压抑的生活现实里,如同一只“在林中穿行的鹿”,因为遭遇到令人烦心而失落的事情而发出沉重的“哀鸣”。但他马上停止了抱怨和叹息,像“趴在湖边”的鹿子“看自己的倒影”那样,开始进行自我反省或自我欣赏,并在忧郁中看到了那依稀泛着光亮的梦想。“天空和水面有两个月亮,世界有一双眼睛”,(《眼睛》)真实的东西如同天上的月亮那样遥远,虚幻的东西如同水面的月亮那样垂手可触,我们该怎样去甄别自己的梦想?这首诗与其说是年轻的诗人在孤独寂寞的夜晚抒发对爱情的渴望之情,毋宁说是他在真实与虚幻的抉择中作艰苦的挣扎,道出了世事的艰难和人生选择的不易,每个人都要有审视现实和期待未来的“眼睛”。雨过天晴的傍晚时分,清新的空气和明亮的蓝天让人神清气爽,天边那道彩虹仿佛是连接往昔与当下、现世和彼岸的桥梁,造物主赐予我们如此祥和美好的景致和心情,我们心里除了感恩便是珍惜。“这时候,谁心上的忧伤还在哭泣?”(《虹》)即便平日的生活欺骗我们太多,但“这一刻的欢愉,要纯粹享用”。现实如此残酷无情,人们穿行在欲望和物质的满足与企及中,很久都没有人倾听内心本质的诉求,与利益和温饱无关的精神建构也被人们遗忘在都市的角落,诗人在彩虹的幻影中找到了久违的诗意。因此,即便生命中那些梦想或梦境是不真实的,但只要能给我们带来片臾的纯美感受,都值得为之心动。
生命如此轻薄,个体却渴望在有限的生年里获得超度,于是便有了潘云贵散文诗对人格修养的关注与提升。茉莉花原产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其传入中土与佛教东渐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散文诗《茉莉香》中,潘云贵始终将茉莉花与佛心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茉莉花洁白的身影和芬芳的气息有了更为高尚的精神与灵魂。茉莉花在中国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它见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坎坷历程却初心不改,年年初夏不约而至,“以一身白裙包裹娇小娉婷的自己,以水般纯净的眼眸蓄满一世的真情”。诗人喜欢茉莉花的素雅,喜欢它在高贵的牡丹和孤傲的蔷薇之外,“把最纯澈的目光投向万户千家”。正因为茉莉花具有纯洁而善良的亲和力,具有朴素而不妖艳的气质,自北宋开始便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吟诗作词去赞美茉莉花,从而让这种洁白的小花逐渐积聚起雅致的审美趣味。茉莉花的“白”带给人们持久的审美感受,它可以在历经岁月的洗礼和时间的残忍之后,仍旧保持一贯的“洁白”并让万千世界的喧哗和躁动黯然失色:“世俗的墙垣被剥落,空灵的白将是世界唯一的镜子,照出喧嚣后的落寞,照出繁华后的衰败,照出桃红柳绿后的无限灰蒙”。茉莉花在北宋以前主要种植在福建等地,而后才开始在黄河流域铺展开来,因此住在闽都的福州人将茉莉花视为市花,一则因为该地种植茉莉花的历史,二则因为茉莉花的洁白与芬芳符合福建人的审美要求。随着茉莉花种植范围的扩大,以及被制成茶叶之后行销各地,走出故乡的茉莉花让更多的人欣赏并品尝到了它的香气。如果世人之前爱慕茉莉花素雅的外表和恬适的香气,对之赞美停留在感官的审美上,那潘云贵则更喜欢茉莉花荣辱不惊的精神和不为情困的淡然之心。于是他在诗中写道:“你或许在佛的手心许过下世的誓言,虽为花,但不为情所困。……有些爱无须浓烈,淡然处之,心静如水,沉默亦是一种爱。”在诗人看来,茉莉花制成茶叶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洗礼和涅槃的过程:“烧去人世间的淫邪、卑劣、肮脏,以及无数的迷惘与苦难,愿这一切焚烧干净,而后剩下最美最美的自己与最善最善的人间。”自此以后,世人就会品尝到茉莉花茶的香气,沁人心脾的芬芳让人心静如佛,茉莉花也因此而涅槃成了坐于杯中的“真正的佛”。潘云贵在这首散文诗中采用他一贯细腻而优美的文笔去表现他内心的情感,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呈现了茉莉花及制茶的历史,呈现了茉莉花外表的洁白和香气,更在于熔铸了高洁的人格和有修养的品格,熔铸了佛心和与世无争的平静心态,由此寄予了诗人的超脱之志和心性追求。
在孤独而晦暗的人生旅途中,在短暂而愁肠万断的生命里,我们要远离那些叫人愈陷愈深的痛苦,在青春岁月里怀着美好的梦想去期待爱情的来临,只有内心闪亮的人才会获得期待未来的视力,也才会在真实与虚幻的生命中获得洞明世事的眼光。
三
潘云贵从珍视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对那些打着仁义道德或宗教信仰旗帜从事利益争夺的行为予以深刻揭露,尤其是在和平与博爱的幌子下为政治企图而发动战争的行为更让诗人感到痛心疾首。
潘云贵对无视生命尊严的战争表示深恶痛绝,因为政治家的阴谋最终损害的是黎民百姓的生活。中东的巴以冲突导致连年混战,最富戏剧性的是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宣扬自由、民主、仁义乃至博爱的宗教发源地,在今天却遭遇了其教义的挑战,这里的人们长期处在枪林弹雨中,饥饿与死亡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主题,他们距离基督的福音越来越遥远。诗人在《透明的耶路撒冷》中痛斥战争的发动者,同时也对那里普通百姓的生活表示同情与担忧,他希望耶路撒冷能够摆脱鬼魅的迷惑,摆脱战争的创伤,人们能够从政治的迷雾中清醒过来,让耶路撒冷变得“透明”而祥和。在这首散文诗中,潘云贵抱着珍视人类文明的眼光与虔诚的宗教视角,首先对今日之耶路撒冷的颓废荒芜表示深深的遗憾:“城门紧锁,风是黑色饱满的瞳孔,是犹大遗留下的子嗣,在窥探烛光亮起的秘密。蜥蜴、壁虎和眼镜蛇藏匿在黑夜深处的洞穴中,尝试用变形来对抗神像的崇高。”这种借故伤今的情感易于让人想起拜伦对希腊昔日荣光不再的叹息之词《哀希腊》:“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热情的萨弗在这里唱过恋歌;/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波!/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1]潘云贵进而在这首散文诗中表示出对宗教精神的怀疑,面对满目疮痍以及众人的祈祷,神却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从饥饿、疲乏和困顿中挣脱的信徒,在雏菊和镣铐间选择一条出路。妄想在尘世中减轻肉身和欲望的重量,却在河岸丢失了火把与眼睛。”因为有了信仰,也许信徒们可以摆脱饥饿、疲乏和困顿,借助宗教精神来获得力量;因为有了信仰,也许人们可以在虚幻的世界里减少肉身的欲望,但信仰的力量终究敌不过枪炮的残害,也敌不过肉身的消亡。因此,残酷的现实最终模糊了人们的眼睛,人们在信仰诞生的地方失去了生活的信念和希望。耶路撒冷的历史就是一段连续遭遇他族和信仰入侵的历史,众神不能拯救这块土地,那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出的众神又能拯救人类吗?“一块不能自救的土地,有什么资格向信仰的乞讨者敞开归途的家门?”这句诗是对基督教本质目的的拷问,它连自己的诞生地都无法拯救,还能拯救芸芸众生吗?“痛楚的信仰中,透明一定会成为谎言最后的结局”,诗人相信人们在经受了生存的考验之后,定会看清宗教信仰的本质。
潘云贵的散文诗借助战争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爱,同时又借助战争对人性的堕落加以了严厉的拷问。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1986)是当代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诗人,1984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6年,由于纳粹德国侵略和屠杀的威胁,捷克被迫与之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慕尼黑协定》。从此,塞弗尔特的祖国陷入了法西斯战争的白色恐怖之中,同时也激发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在1937年便创作了著名的诗篇《别了,春天》。潘云贵引用塞弗尔特诗歌中的诗句“别了,春天”作为《在奥斯维辛以后,眼泪只是空洞的抒情》的开头,表明他对法西斯战争的仇恨和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也预示着他对人性的拷问和对生命的珍视。“奥斯维辛”本是波兰南部一个安静的小镇,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波兰后,纳粹德国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40年4月27日下令在此建造集中营,这里从此成为可怖的“死亡工厂”,从此“灰暗的天空笼盖住大地和人性”。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些反对希特勒的正义之士和无辜群众被关押在不见天日的囚房里,“当教堂废弃,雨水冲刷猛烈,念《圣经》的牧师已经失业”,人们再也接收不到来自太阳和上帝的光芒,立意拯救人类的上帝此时面对法西斯的残暴也无能为力。一百五十多万无辜的生命被德国卫军用各种残忍手段杀害,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剧,也是对人类尊严和生命价值的践踏,追悼者的眼泪在杀戮面前都是“空洞”而无力的。尽管法西斯德国恶魔般的行动最后被制止,但奥斯维辛集中营带给人类的伤害却难以抹去:“人性的废墟,谁能重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战争的烽烟远离孱弱的生命,让阳光与和风重回大地,人与万物共享世界的祥和静好,这是潘云贵的散文诗一直坚持表达的情感和美好愿望。
四
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认为现代诗人写的内容,与三千年前的《诗经》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君子好逑”,他们与古代诗人的最大不同在于艺术表现形式的差别。据此,赵先生认为:“形式论是专业批评,内容论实际上人人做得,是业余批评,是‘读后感式’批评”[2]。对潘云贵散文诗的批评同样应该秉承形式论的原则,唯有如此才能彰显出其作品的艺术特质。
潘云贵的散文诗创作善于使用“兴”的表达方式,比较符合王国维的“意境”说以及朱光潜的“情趣与意象的契合”等创作观念。他很多时候都会在言说忧伤情绪之前,将外在世界刻画得美丽而静谧,然后再转入心灵情感的表达,是典型的“先言他物已引起所咏之词”的创作方式。但潘云贵营造意境的方式十分独特,他通常并不选取情趣相谐的景物作为表达自我情感的铺垫,在表达悲伤心情前多刻写宁静和美之物,而在抒写感恩或珍惜之情前多刻写虚幻之景,由此造成非常强烈的情绪对比和审美落差,如此便能鲜明地凸显出他意欲表达的情感。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在潘云贵的散文诗创作中运用很多,比如《失忆的山羊》这首诗,他的书写旨趣在于表达人生旅途的孤独和无助,我们就像一只迷途的老山羊只能“呆呆看着自己的影子”,找不到回归群体和温暖的道路。但诗人在此之前却花费大量的心思和文字去描写山野傍晚的美景:“螳螂停在狗尾巴草上发呆,落在水中的晚樱浣洗粉色的裙摆。野果从枝头跳下,在山路弯弯的手臂上打滚。叶尖垂落的露水里,云霞在天空飘得很慢。”又比如《赶路的人类》这首诗,潘云贵想要表达冬去春来的季节轮回以及梦想的起飞,但在这首诗人为数不多的积极向上的诗篇前半部分,他却详细地描述了人类周而复始的奋斗无异于西西弗斯的传说,前行的过程充满了叹息、汗水和眼泪,最后却成为“俗世的佣人”。前后对照,方觉诗歌情感的起伏和跌宕之美,方觉每个人追求梦想的艰辛,但万物复苏的春天却为我们铺展开一条通往未来旅程的道路,我们在春光灿烂中都成了追梦人。
潘云贵在创作散文诗时善于调动各种感官知觉,善于捕捉生命的瞬间感受,用心聆听世界的声音和自然节奏。潘云贵的内心是丰富的,其观照世界的触觉是敏锐的,哪怕是一场细雨之后的清风和屋后花园的景致,都会勾起他对生活往事的回忆并产生无限感动。时间似乎可以静止地定格在某个瞬间,风也因此而“渐渐静止”,但心思却跃出时间的藩篱,外面的世界让他有了滋长理想的冲动,“像蒲公英那样轻,飘出现在,飘往未来”,那些开花的蔷薇让他“拨开层层叠叠的密叶”,(《风渐渐静止》)从而看清来路的方向。远离现实的尘嚣,回归天然的生活状态,让时间静止,从忙碌中抽身出来,我们便会“谛听”到大自然的声音和律动。在心如止水或“虚静”无为的时候,“大地是一只巨鸟”,生机勃勃却又静默无声,它“一尘不染的寂静”具有“安宁,庄严,肃穆,纯真,高尚”之态,却又“接近空白,仿佛神的呼吸”。在诗人看来,“生命律动的声响”无处不在,只要我们具有“婴儿”般未经尘世玷染的“耳朵”,便可听见来自大自然和生命搏动的声音。《谛听》这首散文诗不禁让人想起当年徐志摩对自然律动的阐述:1924年12月1日,由周作人、钱玄同和孙伏园创办的《语丝》杂志刊登了徐志摩翻译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死尸》,在译诗之前有一段徐志摩阐述音乐的文:“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3]徐志摩的话道出了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后来他在介绍济慈的《夜莺歌》时,认为济慈《夜莺歌》的律动带给读者无穷的想象,激活并带动了读者的所有情感:“沉醴浸醉了,四肢软绵绵的,心头痒荠荠的,说不出的一种浓味的馥郁的舒服,眼帘也是懒洋洋的挂不起来,心里满是流膏似的感想,辽远的回忆,甜美的惆怅,闪光的希翼,微笑的情调一齐兜上方寸灵台”。[4]鲁迅是《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看了徐志摩的文章之后觉得不免夸张和扭曲,于是说徐志摩是有福气的人,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甚至调侃徐志摩的神经出现问题,产生了幻觉,才听到如此美妙的音乐,将他“送进疯人院”[5]也不足为奇。远在国外的刘半农收到周作人从国内寄去的《语丝》杂志,看了徐志摩和鲁迅的文章后生出几许异议,写成《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文。他风趣地说,如果徐志摩高寿后百年归世,“我刘复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6]。
鲁迅和刘半农对徐志摩的诟病有合理的地方,但却没有理解到徐志摩对宇宙万物所具有的节奏的发现。潘云贵的此诗与徐志摩的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告诉我们世间万物的律动自是最优美的音乐,受到俗世干扰的耳朵自然听不见这天籁之声。这种洞悉世间万物生命律动的感受在《神与孩子》中也有所表现,诗人在描述了夜间深林水边的生命迹象之后,转而写到自身的状态:“兰汀上,幼童在行走,沿着内心的声音寻找家园。唯一能与神对望的是孩子的眼睛。”年轻的诗人自比“幼童”,意味着对外在世界有太多的未知,也意味着心灵世界的纯洁;“内心的声音”就是生命在本真状态下流泄出的音乐和律动;“与神的对望”就是人与大千世界的声音形成的呼应,而这种呼应需要一双“孩子的眼睛”,必须摆脱世俗的功利性目的而怀着单纯的审美眼光,方可达到康德所谓“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审美效果。
散文诗长于表达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但潘云贵的散文诗似乎更长于写景,他常以周遭寻常景物的错位组合营造出浓厚的情感氛围,读者往往会陷入其诗歌意境中难以走出,淡淡的忧伤或浓浓的幸福萦绕心间,回味良久却意犹未尽。从这个角度来讲,潘云贵的散文诗仍然将情感作为主要的表现内容,只是他不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而多“立象以尽意”,从而避免了情感的直写和表达的非诗化倾向,这样的散文诗自然具有较高的艺术隶属度。潘云贵散文诗的这种特点反映了其作品审美视点的独特性,“所谓审美视点,就是诗人和现实的审美关系,更进一步说,就是诗人和现实的反映关系,或者说,诗人审美地感受现实的心理方式。”[7]潘云贵散文诗的审美视点决定了他观照世界的方式与散文创作有所不同,他多采用借景抒情的方式,从外在自然物象中去窥视人的内心世界,发掘世界和人心所蕴含的美丽音符,进而也赋予其作品高度的心灵性和含蓄美。
文学批评或作品解读因为带有强烈的主体情绪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误读的发生,偏颇之见也在所难免。况且,潘云贵的散文诗作为丰富的存在,任何一篇对其解读和批评的文章都只能窥见一斑,要穷尽其中的情思和深意只是枉然。因此,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潘云贵的散文诗,以丰富我们对他作品的认识,并鼓励他在今后的岁月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飨读者。
[1]穆旦.穆旦译文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0.
[2]熊辉.从新批评到符号学:一个形式论者的坚持——赵毅衡访谈录[J].重庆评论,2012,(3).
[3]徐志摩.《死尸》译诗前言[J].语丝(第3期),1924-12-01.
[4]徐志摩.济慈的夜莺歌[J].小说月报(16卷2号),1925-02.
[5]鲁迅.“音乐”?[J].语丝(第5期),1924-12-15.
[6]刘半农.徐志摩先生的耳朵[J].语丝(第3期),1924-12-01.
[7]吕进.中国现代诗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20.
On the Emotional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Pan Yungui's Prose Poetry
Xiong Hui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s a special kind of style,the creation of prose poetry has been developed o lot in recent years, the good example of which is that some young prose poets appeared.Pan Yungui,one of the young poets,has been making courageous attempts and great efforts on the spirit and art of the prose poetry,so he is one of the best poets in the 1990's.With the strong humanities contents,Pan Yungui's prose poetry expressed not only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thought,but the heavy compassion and the society dreams,and which have his poems resented the special artistic style.
Prose poetry;Pan Yungui;Emotional feature;Artistic Style
I206
A
2095-3763(2015)04-0072-07
2015-06-17
熊辉(1976-),男,四川邻水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