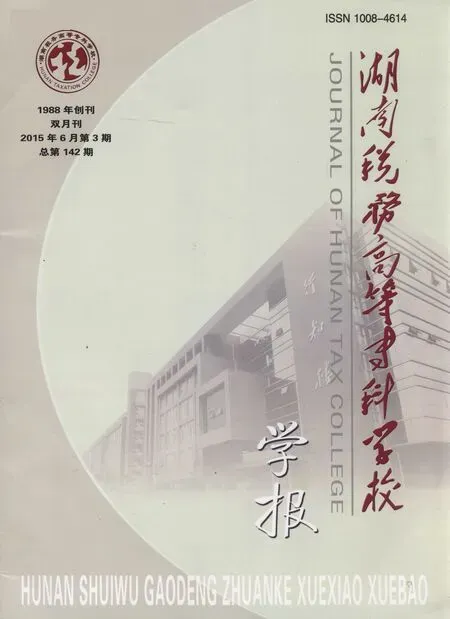认知诗学视角下的戏剧剧本分析
——以奥尼尔《送冰的人来了》为例*
□ 涂雨晨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
认知诗学视角下的戏剧剧本分析
——以奥尼尔《送冰的人来了》为例*
□ 涂雨晨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
以认知诗学中的可能世界理论为依据,对尤金·奥尼尔剧本《送冰的人来了》被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多重世界进行重点分析,并深入论述文本中出现的多重主题,从而使读者能够进一步领悟到文本的多重内涵。
认知诗学;戏剧剧本;多重世界;《送冰的人来了》
认知诗学的提出是从以色列学者楚尔开始的,目前在中国已有许多学者、研究人士对此理论作了深层次的探讨,并进行了许多尝试。但对认知诗学的运用,许多学者们只停留于对诗歌与小说的解读范畴,较少涉及戏剧这种文学的最高样式。本文通过对认知诗学中可能世界理论的运用,分析探究了美国戏剧大师级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晚期作品《送冰的人来了》,并对它的主体进行了深入解析,以此领悟到巨作的深刻内涵。
一 戏剧之中虚构的文本世界的展示
作为认知诗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可能世界”理论主要解决认知诗学中的文本世界的真实性与价值问题。在赖恩提出的“最少偏离原则”中,对可能世界作出了详细解释,他认为文本虚构的真实世界是同读者所处的真实世界近乎一致的,只是在少数的文本标志上和后者进行了区分。运用“可能世界”理论对作品进行分析,能够使我们对虚构文本及各种文本的内部结构进行辨别,从而明晰文学作品的流派风格,使戏剧之中的虚构文本世界充分展示出来。
在《送冰的人来了》剧作中,奥尼尔凭借文本所铸就的多重世界,有些符合读者的真实世界,有些却产生了偏离。但正是由于这时而真实时而虚幻的多重世界,才使进入它的观众从中获得多重的启发,并领略到戏剧的独特魅力。
在《送冰的人来了》中,作者所描述的“霍普旅馆”与奥尼尔年轻时居住过的三家酒店有着很高的相似度。如“霍普旅馆”的房间陈设布置与他住过的吉米酒吧的陈设完全相同。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真实的吉米酒吧充斥着喧闹声,在该剧中却出奇地安静,除了经常出入的老顾客以外,再无任何客人光顾。在相同中少有不同,与赖恩的偏离原则相契合,说明剧作家为观众虚构了一个文本世界。
由18位有对白的人物组成的《送冰的人来了》,是奥尼尔戏剧中最多人物的一部,其剧情由等待希基、遭遇希基到送至希基这条主线,经微观对话将一个个文本世界互相连粘起来。在每个文本世界中,剧作家对关于信仰、婚姻、生命、死亡等话题铺展开来,塑造出一个富有多重可能的文学世界。在这个纷繁错杂的世界中,戏剧人物与作家、读者的可能世界相互碰撞、交互来推动着剧情不断向前发展,并突出剧作的多重主题。
二 “人性”是世界的连接
在《送冰的人来了》剧中,“人性”主题把真实与可能的世界里连接在了一起,成为可能世界中的内在逻辑。那些居住在霍普酒馆的下层边缘人物,有的自甘堕落,有的一蹶不振,在酒精的麻醉中一天天消磨着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他们在心底仍留有一丝希望,即使意味着自身的毁灭。这就是可能世界与文本世界中“人性”的连接。
在《送冰的人来了》剧中,青年人唐·帕里特由于母爱的缺失,揭穿母亲的“无政府主义”,致使母亲被捕。在他的可能世界中,他告密母亲的动因不是出于自己畸形的情感,而是爱国情感的驱使。
霍普作为旅店的老板,经常把竞选市议员作为自己的口头禅。那么在他的可能世界中,他会走出旅馆,参加竞选,融进社会。他一直将妻子的去世作为他潦倒的主要原因,认为那是他与文本世界唯一的联系纽带。
曾由于玩忽职守而离任的前警官麦格洛音是个粗野而贪欲极强的人。在他的可能世界中,他的案子会获得重审,并能够恢复原职。而在哈佛大学学生威利的可能世界中,是父亲的冤枉导致他的流落。他可以为受理麦格洛音的案件而把酒戒掉。尽管他没有做过律师,但是他相信以自己的水平可以赢下这场官司,从而一战成名。
以上这些生动、鲜活的形象被剧作家写进形形色色的可能世界中,让他们在那里找到安慰,做着自己的美梦,以此逃离让他们千疮百孔的“文本真实世界”。与此同时,当他们的尊严与价值遭到剥夺后,他们心中所留存的最后一丝人性,使他们依旧渴望进入文本的真实世界中。这个无意义的希望,是他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剧作家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与悲悯的情怀,即不管人多么的贫穷、卑劣,都有自己想象的权利与自由。
三 多重主题,多重世界
剧作家通过对场景的布置、情节的编排凸显了剧作的多重主题,就是那个富有多重意义的可能世界。“宗教”是奥尼尔的可能世界中的重要关注点,他将自我的兴趣放在人与上帝的关系研究上。于是,在他的可能世界中蕴含着希望耶稣为人承受苦难的热切渴望,也有对耶稣的许久等待却未来的愤懑与失望。
在马太福音中,运用10个童女的比喻暗示天国的降临就像新郎的来临,只有准备充足的童女才能将新郎接到。这里耶稣的意图是让信徒时刻准备好迎接基督的到来,以获救赎。奥尼尔效仿人们等待希基每年一次的款待,就如信徒虔诚地等候基督救赎一般。而这漫长的等候正如“最后的晚餐”一样,有着郑重的仪式感。但相比之下,奥尼尔富于了“等待”深刻的内涵,即等待的结果不是获得救赎,而是毁灭。这就使得这些整天沉醉自己白日梦之中的醉鬼们彻底破灭了希望,最终走向黑暗的深渊。
在剧作文本的真实世界中,效仿宗教仪式和“原罪说”与读者的可能世界是相契合的,但是最终的结局与读者的可能世界中对宗教能带给人们救赎的思想却是背道而驰。在这个过程中即读者的审美过程中,文本真实世界与读者的可能世界的相合与相离,都是以宗教这个中心进行展开的。
“狂欢”主题将可能世界与文本真实世界叠合起来,在《送冰的人来了》剧作中,作为剧中人物的狂欢之处,小酒馆的所有客人都参与其中,其最具仪式感的表现是霍普的生日宴会。此次狂欢,把被禁锢在森严等级制度中的人们解放出来,纷纷迎接希基的来临,并由此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形成了平等、自由、和谐的关系,与酒客们对可能世界的期冀相符合。
在除去一切阶级地位带来的地位差别后,酒客们一同沉浸在自己创造的和谐小世界中,并与文本的真实世界等同起来。在酒精的促进下,酒客之间也越发亲密起来。拉里被帕里特不断暗示自己可能是他的父亲;罗基激发了玛吉和珀尔母性的情怀;哈里与莫舍修复了姐夫和小舅子关系,作为无政府运动中的“同志”,雨果和拉里志趣相投,产生了亲密的情感;就连在布尔战争中,属于敌对关系的刘易斯和韦乔恩也握手言和。
这场宴会为狂欢中的每一位酒客带来了一个愉悦与喝醉的机会,但在希基由于谋杀妻子被警察带走后,酒鬼们开始不安起来,他们再也无法逃避自己的可能世界越来越远离于文本真实世界的事实。于是,大家利用“狂欢”再次把这个两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在吝啬店主许诺众人由他买单,且在大家共同判定希基的精神已失常的情境下,迎来了狂欢的第二次高潮。
在可能世界中,“送冰的人”是其另一个关注点。在剧作家虚构的可能世界中,希基所虚构出来的妻子出轨的对象就是送冰的人,并最终成为了“死神”。由此全剧从等待希基开始最终演变为等待死亡,这也成为了全剧的主题。当希基将沉迷于自己可能世界中的酒客,强制赶离酒馆,使之进入真实世界后,所有人在精神上获得了完全的死亡。
在进行后期的创作中,奥尼尔由对天主教的信仰转向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中,因此,整个剧本中的可能世界都被无为、循环、回归、和宿命论所充斥着。为了不争于现实,所有酒客们终日以酒为乐,纵情于逍遥自在中。尤其是剧中的拉里,他是所有人之中最“无为”的一员,他不再对各种世俗积极追求,而是消极度日,无动于衷。
在此剧开放性的结局中,剧作家以酒客重返酒馆,恢复平静作戏剧的最终落幕点,这样不仅呼应了道家的“回归”思想,而且传达了剧作家对命运在冥冥中起到的强大力量的认同。正如奥尼尔在该剧进行首演时说过的,如果他没弄错的话,现在他们都负有一种命运感……由于一些隐晦的原因,使原本可笑而滑稽的事情转瞬变得沉郁、伤感起来。
四 多重世界,跨界联系
可能世界理论把时空联系和内在相似性联系,作为不同可能世界的跨界联系的两种主要方式,为戏剧中对可能世界的塑造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送冰的人来了》剧本中,时空联系相当明显。剧本中对时代与环境的描写,使剧中人物拥有重叠或相互可及的时间与空间世界。即使不同人物会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度过他的一生,但每个可能世界终会在某天重合。
剧中全部人物的共性是内在相似性的体现。不管以前他们有多么令人钦羡的身份,多么辉煌的成绩,但现在他们都是社会底层中的失败者,都只能将自己整日麻醉在白日梦的美好中,聊度终日。
在文本的真实世界里,多重可能世界是经由话语表征来加以连接和通达的。如“笑”这个典型表征。所有酒客在酒醉前,都是充满笑意的。大笑(1augh)、嘻笑(tease)、嘲笑(mockery)、抿嘴笑(chuckle reminiscently)、亲热地笑(grin affectionately)、勉强地笑(forcing a smile)、哈哈大笑(tickled);不管是犀利嘲讽的笑,还是幽默机趣的笑;不管是开心快乐的笑,还是冷漠斥责的笑;不管是充满欣赏的笑,还是鄙夷嫌弃的笑。酒客们不同类型的笑成为了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物的特征。
拉里的表征是“悲悯”。他总是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悲悯之情流露出来,他同情雨果,但在同情中又掺杂着一些迷惑,他是剧作家可能世界中的“代言人”,把他悲悯与他所悲悯的对象的可能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意象也可以作为话语表征。在《送冰的人来了》剧本中,“白日梦”与“死亡”就是反复出现的意象表征。在第一幕中,拉里自称他的“白日梦”已经破碎,霍普嘲讽吉米做“白日梦”,玛吉觉得科拉想与查克结婚并把家安置在农场是“陈旧的白日梦”。
此外,这个小酒馆里业充斥着“死亡”的意象。首先是在对小酒馆的陈设、布置描写上,脏乱的墙壁,昏黄的光线,宿醉的客人,阴森沉郁。罗基看来“这些人就是死人”;拉里读着海涅关于死亡的诗;威利经常性地疑神疑鬼;玛吉则称有尸首在酒馆停放。
在肮脏阴沉的小酒馆中,满载着众多醉生梦死的酒客,他们只想无为而终,做好自己的白日梦。其中众酒徒各种样式的“笑”,拉里冷酷而深切的“悲悯”以及“白日梦”“死亡”意象的不断出现,完成了多重可能世界的连接。
结束语
本文试图通过认知诗学理论的引领,把剧本作为虚构中蕴藏了内在逻辑的文本世界,为戏剧中的各类人物构建了多重世界,从而使戏剧主题得到多重体现。观众在对戏剧进行观赏时,剧中人物和他的活动会进入观众的心智中,使可能世界得到恢复或是重构。观众要理解其中的蕴意,并理顺各个可能世界的关系,这样就能够更深切得体会和把握剧作的潜藏涵义了。
[1]康建兵.近20年国内尤金·奥尼尔研究述评[J].齐鲁艺苑,2008,(4).
[2]李金妹.吴晓云.基于概念合成理论的矿冶戏剧认知诗学分析——以《钢铁夫人》为例[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3]符熠.生——梦——死:尤金·奥尼尔艺术世界的狂欢化特征[D].辽宁师范大学,2010.
[4]王迪.尤金·奥尼尔晚期现实主义戏剧的现代主义特征研究[D].兰州大学,2012.
I106.4
A
1008-4614-(2015)03-0052-03
2015-4-29
涂雨晨(1980—),女,江西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