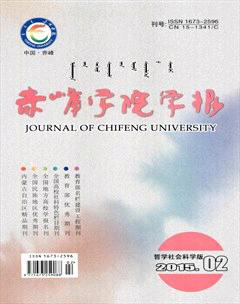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法定事由的合理性
段宇瑛 梅哲宾
摘 要:目前我国《婚姻法》禁止有关重型精神病人结婚,并将与有关重型精神病人的婚姻一概做无效化处理,此限制侵犯了精神病人及其配偶的婚姻自主权且与《民法通则》对民事行为的规定不一致。根据实践状况和可撤销婚姻制度与无效婚姻制度的不同,区分对待严重程度不同的精神病患者,将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可以平衡婚姻自由与婚姻秩序两大价值并对精神病人的子女和财产权利加以保护,是十分合理的。
关键词:精神病;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婚姻自由;婚姻秩序
中图分类号:DF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24-03
基于精神病人基本无法承担婚姻家庭义务与优生优育的原则,我国《婚姻法》明确将精神病作为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之一。然而,不分类型的一概将与精神病人的婚姻做无效处理侵犯了精神病人配偶的婚姻自主权以及既已产生的亲属关系的稳定性,且与民法基本精神相悖。本文从目前将精神病规定为无效婚姻事由的不合理性及区别对待轻型精神病与重型精神病的角度浅析将与轻度重型精神病人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婚姻的合理之处。
一、目前我国关于精神病人结婚权利的规定及不合理之处
(一)目前我国关于精神病人结婚权利的规定
在我国,精神病人并不享有结婚的权利。《婚姻法》第七条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结婚;第十条的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尽管《婚姻法》条文并未明确,但实践中一般将《母婴保健法》中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涉及的疾病作为“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该法第八条明确将有关精神病囊括在婚前医学检查的范围内,又在第九条规定有关精神病人在发病期的,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另在第三十八条明确了所指精神病的含义,即“有关精神病,是指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根据上述规定,我国禁止处在发病期间的“有关精神病人”结婚,无论其有无对缔结婚姻的认知能力;而结婚时处于发病期,婚后尚未治愈的“有关精神病人”,即使办理结婚登记,其婚姻也为无效婚姻。
(二)现行法律对精神病人结婚限制的不合理之处
出于保障后代健康,实现婚姻三大职能与维护社会婚姻秩序的目的,目前我国对精神病人结婚权利的限制体现了立法者对婚姻职能的定位,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婚内权利义务的实现和优生优育,对社会婚姻秩序和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但直接将有关精神病作为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并不合理。
首先,与宪法精神相悖。结婚是带有强烈个人意志的主观选择,只要公民能表达主观意志且没有损害国家、社会或第三人合法权益,其选择就应得到宪法尊重。《婚姻法》选择禁止精神病人结婚的原因之一是促进优生优育,但在某些精神病并不属于遗传疾病,且有其他手段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前提下直接选择剥夺精神病人结婚权利的做法有倚仗国家强制力管控私权之嫌。同时,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相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以婚姻当事人患有精神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向法院宣告婚姻关系无效的申请主体还包括当事人的近亲属,不利于保护精神病人的自主权。
其次,与《民法通则》相悖。根据《民法通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为人欠缺行为能力,或者该行为严重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均需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宣告。《婚姻法》在缺乏对相关精神病人行为能力前置认定的情况下,未加区分的一律将有关精神病人的结婚认定为无效,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缺乏一致性。
再次,“无效婚姻在否定既成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产生,如果刻板的坚持无效婚姻的自始、当然无效,就不可避免的造成法律与事实的脱节,并且对其间弱者的打击也是致命的”[1]。目前,婚前强制婚检被取消,越来越多的“有关精神病人”缔结无效婚姻的现象将更为普遍。这类精神病人与其配偶一起共同生活,甚至孕育了子女,一概让他们承担婚姻无效的责任和后果,让原本的婚生子女受到非婚生子女的待遇,在立法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同时不加以区分的对精神病人的婚姻无效化无异于将本处弱势地位的精神病患者置于更不利的地位。
二、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法定事由的理论基础——平衡婚姻自由和婚姻秩序
婚姻的两大价值在于婚姻自由和婚姻秩序,在设计婚姻制度、对某类特殊人群的婚姻权利加以限制的时候也应以平衡两大价值为标尺。由于轻度重型精神病人与重度重型精神病人的不同特点以及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不同,将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可以很好的平衡婚姻自由和婚姻秩序,具有正当性。
(一)以平衡婚姻自由和婚姻秩序的角度区分对待轻度重型精神病人和重度重型精神病人
根据临床表现分类,医学上有轻型精神疾病和重型精神病之分,而在重型精神病中也存在不同严重程度之分。事实上,存在相当部分的重型精神病人对结婚这一行为有认知能力,也能在其不发病时适当履行婚姻权利义务,本文对这部分精神病人称为“轻度重型精神病人”。
对于重度重型精神病人来说,因为其无法认知结婚这一民事行为的意义,也当然无法表达其对婚姻的选择意志以实现婚姻“合意”,法律应主要从维护婚姻即社会秩序的角度禁止其结婚,将与这类精神病人缔结的婚姻完全作为无效婚处理。而轻度重型精神病人,其对婚姻有部分认知能力,也能做出自我判断和选择并与其结婚对象达成“合意”。在限制这类精神病人的制度设计上,不能只注重婚姻秩序的维护,而应注重其婚姻自由的保护,与重度重型精神病人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也与《民法通则》中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效力做不同认定的态度相一致。
(二)将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的事由的合理性
无效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以因行为人的要求而撤销从而使婚姻关系自始无效的婚姻。在采用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里,精神类疾病几乎都被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例如,英国1973年的《婚姻诉讼法》将由于精神不健全,一方未有效同意的婚姻作为可撤销婚姻[2],而美国的《统一结婚离婚法》和大多数州的法律则将“一方精神耗弱”作为可撤销婚姻的事由[3]。这种既注重有关精神病人结婚权利又不放弃婚姻秩序维持的趋势体现了上文分析的平衡婚姻两大价值的理念,而我国是否需要借鉴则需具体比较将有关精神病作为无效婚姻事由还是可撤销婚姻事由的不同之处。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均在不同程度上违反了婚姻成立的要件,其区别主要有以下4点:
1.违反的要件不同。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最早被一起规定于1900年德国民法典,无效婚姻被设计为违反公益要件,可撤销婚姻被设计为违反私益要件,无效婚姻的违法程度一般比可撤销婚姻的违法程度要高。
2.认定的程序和请求期间不同。有些兼采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国家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认定程序做不同规定,可撤销婚姻必须通过判决宣告撤销而无效婚姻则自然无效。
3.法律后果不同。根据最初的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婚姻被宣告无效的,自始不产生婚姻的效力,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于无效婚姻中受胎所生的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婚姻因法定事由被撤销的,撤销之前的婚姻为有效婚姻,撤销前当事人为夫妻关系,所生子女为婚生子女,撤销后当事人之间无夫妻关系,所生子女是否为婚生子女在学术界存在争论。①
4.制度功能不同。无效婚姻调整违反公益要件的婚姻,其后果是自始无效,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利益的维护,对违法婚姻加以制裁。而可撤销婚姻调整的是违法程度较低的婚姻,有些国家的可撤销婚姻被撤销后其无效不溯及撤销前,可撤销婚姻这一制度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无效婚姻制度的价值在于通过消除非法婚姻对社会的危害实现稳定的婚姻和社会秩序,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针对社会危害性较低但尚存违法性的婚姻给予婚姻自由的适当保护。与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重婚和近亲婚不同,同有关精神病的患者缔结的婚姻既未挑战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也未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婚姻法》对基本于公益无害的精神病患者施以同样的严格限制显然有失公允。同有关精神病患者缔结的婚姻又属于社会危害性较低但可能危害私益的婚姻,因此,由可撤销婚姻制度来调整轻度重型精神病患者的婚姻是合理的。
三、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法定事由的具体裨益
将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不仅可利用除斥期间规则维持婚姻的稳定性,还可以更好的保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子女的合法权益,这种设计兼顾婚姻自由和婚姻秩序,明确了婚姻权利限制的标准,对我国婚姻制度的完善也有裨益。
(一)保护双方的结婚自主权
在普遍承认婚姻契约说的西方国家,婚姻自由被推向新的层面,当事人的合意作为缔结婚姻的必要条件越来越独立于其他人的意志,甚至越过国家的婚姻管理程序使婚姻关系取得法律效力[4]。如果说对重型精神病人结婚权利的限制是出于对精神病人配偶结婚权利的保障,那么这种限制不仅剥夺了有意志表达和婚姻认知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结婚自主权,那些自愿成为有关精神病人配偶的公民的结婚自由同样受到了侵害。如果一方明知对方有生理上的缺陷,自愿与之结婚,在生活上相互扶助,互相慰藉、照料,行使夫妻间其他权利义务,于社会和双方并无害处,法律非要宣告他们之间的婚姻无效欠缺正当理由。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无效或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尽管与相关精神病人的婚姻并非自然无效,而是需法院宣告,但令与相关精神病人的婚姻自始陷入无效且近亲属也有申请婚姻无效权的制度设计难以保障既成事实婚姻的稳定性,反而使有关精神病患者及其配偶时刻陷于婚姻无效的恐慌中。相比直接让有关精神病患者的婚姻无效,将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可以保护婚姻双方的结婚自主权,婚姻法规定,可撤销婚姻存在一年的除斥期间。轻度重型精神病患者的配偶如果在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则婚姻合法有效,稳定的婚姻关系得以建立和延续。
(二)保障精神病配偶的离婚权利
离婚自由也是婚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精神病人异常的精神状态和由此导致的婚姻义务的不完全履行,与禁婚精神病患者的合意离婚较难实现。
具体到轻度重型精神病人,即使其能够表达解除婚姻的真意,与其进行合意离婚也并非易事。一方面,轻度重型精神病患者在婚前隐瞒其疾病,其配偶婚后才得知其患病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而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在婚前蓄意隐藏其病情无非是为了促成婚姻缔结,令带有强烈结婚意志的精神病患者主动提出或同意离婚十分困难。另一方面,轻度精神病患者本身无力承担完整的婚内义务,作为被照顾扶助的对象,其自主提出解除婚姻关系的概率较低,反而存在极力阻挠离婚的可能。
针对以上两种情况,有必要给予婚后才得知配偶患病情况的公民及自愿与轻度重型精神病人缔结婚姻的公民以特殊保护。对婚前不知配偶身患禁婚精神病的公民而言,其结婚的意思表示建立在重大误解之上,赋予其对婚姻的撤销权与《民法通则》有关可撤销民事行为的规定相一致。而对于自愿与轻度精神病人结婚的公民,尽管其结婚时自愿与精神病患者结为连理,但相较精神正常人员的配偶,其需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甚至完全无法享有婚姻权利。法律赋予这类精神病患者的配偶以再次选择权,即在其发现自身无法履行相关婚姻义务时撤销婚姻的权利,对其提供法律上的救济是必要的。倘若自愿与轻度重型精神病患者结婚的公民放弃撤销权,则可在一定层面上推定其具有在婚后承担更多婚内义务的强烈意志,有利于婚姻秩序的维持,若嗣后上述婚姻无法被撤销也无法通过协议解除时,也完全可以利用诉讼离婚制度保障当事人权益。
(三)保护已发生的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系列人身、财产关系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可推知无效婚姻当事人的子女属于非婚生子女。子女对于婚姻无效并无过错,父母的违法行为不应累及子女,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严厉的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5]。尽管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非婚生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也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将本由事实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置于非婚生子女的地位与事实不符且会使其面临歧视及舆论带来的社会压力。对于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婚姻法》并未明确其属于婚生还是非婚生,但这一点可以通过区别规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加以补全。参考其他国家,英国法规定无论婚姻是否合法有效,只要子女出生在婚姻成立之后,即为婚生;而《法国民法典》第202条规定:“即使缔结婚姻的双方均无善意;婚姻对子女仍产生效果。”[6]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设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是为惩治恶意当事人,但如果要以牺牲子女利益为代价就并不合理。但从法理上讲,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前的婚姻效力也是得到法律肯定的,所以将婚姻被撤销前出生的子女作为婚生子女于法不悖。
根据《婚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无效婚姻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具体到与禁婚精神病的无效婚姻财产分割,由于精神病人本处于弱势地位且无法完整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志,一方面协议分割财产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容易出现胁迫同意分割财产的现象,则易将精神病人置于不利地位。而在当事人协议不成时法院将根据无过错原则分割财产也因很难证明一方过错与否,或在双方均无过错时导致个人收入仍属个人财产,使重型精神病人失去特殊保护。与婚姻被宣告无效后的财产分割不同,可撤销婚姻被撤销前是合法有效的,因而同居期间的财产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由夫妻共同财产制度调整,可以很好的保护弱势一方的利益,进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增加配套规定以完善对轻度重型精神病人结婚权利的限制
首先,由于需区别对待轻度重型精神病患者和重度重型精神病患者,《婚姻法》应限缩禁婚精神疾病的范围。又由于《婚姻法》有关优生优育的考量,需明确允许轻度重型精神病人结婚的前提,即如果此类精神病可能遗传,结婚双方自愿放弃生育权并配合相关节育措施。其次,尽管从法理上分析,可撤销婚姻当事人的子女应属婚生子女,可撤销婚姻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实践中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与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并无二致。因此需增加有关可撤销婚姻溯及力及子女、财产问题的明确规定。再次,尽管轻度重型精神病人的配偶在婚姻中将承担更多的婚内义务和家庭责任,但不乏一方恶意与精神病患者结婚后直接撤销的可能性。又基于精神病患者本身所处的弱势地位,有必要规定对恶意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行为的惩罚及相应赔偿。
区别对待轻度重型精神病患者和重度重型病患者并将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是建立在实践和平衡婚姻自由和婚姻秩序基础上的合理分类,这种规定一方面可以弥补当前我国《婚姻法》一律将有关重型精神病作为无效婚姻法定事由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很好的保障既成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体现了法律对已经发生的身份事实的宽容,使法律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配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加以补强,这种符合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立法国际潮流的规定不啻为《婚姻法》完善的重要选择。
注 释:
①关于婚姻撤销后所生子女,有学者认为在婚姻撤销前受胎即使在婚姻撤销后出生,仍为婚生子女:巫昌祯.婚姻家庭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66;也有观点认为即使是婚姻撤销前受胎但在婚姻撤销后出生,为非婚生子女:饶红琼.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法律问题研究.四川大学,2005.
参考文献:
〔1〕杨遂全.婚姻家庭法典型判例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05.
〔2〕夏吟月,蒋月,薛宁兰.2l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210.
〔3〕王竹青,魏小莉.亲属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59.
〔4〕邓丽.婚姻法中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以婚姻契约论为中心[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80.
〔5〕常素巧.婚姻家庭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50.
〔6〕于东辉.无效婚姻制度探析[J].法学论坛,2007,(4):135.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