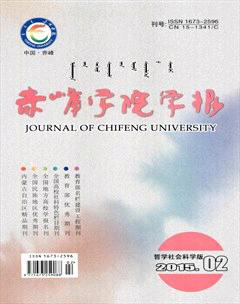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建设
徐小稳
摘 要: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修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邓小平从意识形态、政府治理绩效和制度规范等层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关键词:邓小平;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069-03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任何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为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性统治,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并创建有利于自己执政的资源。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在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伴随着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出现,合法性资源建设的步伐被迫中止,建设的良好局面也遭到了破坏。对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进行了切实的维护与重构。
一、修正并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资源
在恢复并发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对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采取去伪存真、去神圣化的态度,并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的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作为其执政的基础,那么它的地位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它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但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也混淆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质疑甚至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以此为开端,吹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角,要求人们以正确的态度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资源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以去伪存真的态度,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的失误,把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真理加以固守,把另外一些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针对这一现象,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逐步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枷锁。对“四人帮”鼓吹的“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简直荒谬得很!”……“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
对于社会中庸俗化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现象,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要求“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3]。7月,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1979年,在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指出:“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4]
(二)以神圣化的态度,全面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色彩,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深不可测的理论,不可能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深奥,它是很朴素的东西,都是很朴素的道理。但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就要了解群众,明白他们所需要的不是长篇的东西,那是少数专业人士读的,都读大本子是形式主义的做法,在现实中办不到。针对另一些人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邓小平指出这种认识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没有搞清楚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作为现时代的领导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朴素的道理,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要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5]表现出来。为此,邓小平文选的文本从“独白范式”转变为了“对话范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了结合,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满足了新时期党和人民的理论需求。
(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
理论必须运用到实践中才能发挥其应用的作用,从而增强其可信度。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不仅作为一种真理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指导思想,指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改革开放后,在总结国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战略步骤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发展全局的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理论等一系列重大的思想,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增强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二、重构政府治理绩效层面的合法性资源
不仅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实现经济绩效,而且要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还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民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政府治理绩效的合法性建设是指政府通过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利,履行自身的职能,为民众提供必需的服务,实现公民福祉和社会进步,从而增强人们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对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掌握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生活的改善对于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利于让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代领导集体尤为重视治理绩效的合法性建设。
(一)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确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但是,随后的实践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轨道,工作的中心再次转向了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几乎停滞,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同他们的需求和理想产生巨大反差。改革开放后,发达国家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刺激了人民群众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对此,邓小平提出物质利益的重要性,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就是唯心论的表现。因此,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要看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一切的标准。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又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发展经济,不坚持改善人民生活,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样,邓小平就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同发展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紧密地联系起来,表明经济绩效是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二)强调社会主义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否合法性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即社会公正程度的高低。因此,仅有经济增长还不够,还要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以符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同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否则将危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6]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但是要防止两极分化。要使所有的中国人从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受益,既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让大家的日子普遍好过。如果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或者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
(三)社会主义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因此,在经济绩效增长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将此作为其治理绩效的一个重要标准。为此,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要求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79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1980年12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7]把精神文明建设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了研究。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之一。同年7月,又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三、努力推进中国共产党在制度规范层面的合法性资源建设
加强社会的民主化、法制化和政党制度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在合民意性和合法律性方面都得到提升。
亨廷顿曾说,从长远来看,一个更深一层的合法性基础能使政权生存下去,即便其经济成效低或当其面临一些不祥事态时[8]。这里所说的更深一层的合法性就是制度规范层面的合法性,即把合法性建立在制度上,作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强有力的支撑。对此,邓小平也深有体会,他曾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极大地增强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加快社会民主化建设的步伐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既包括执政党的权威性又包括公众的认同性,为了达到这双重的目的,执政党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的生活获得极大提高的同时,人们对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为此,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大概有三百多处提到民主的问题。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缺失民主的社会主义存在着丧失执政地位的可能性。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要切实保障公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同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0]
(二)加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力度
在结合对个人崇拜批判的基础上,我国的法制建设也迈上了新台阶,从人治逐渐地走上了法制的轨道。1978年12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邓小平要求,为了保障人民民主,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空缺,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我们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要做到国有国法,党有党章党法。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党风搞好。1979年,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7个法律。同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又明确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1]这些论断充分表明,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主张要依靠法制治理国家,因此,我们要加强法制,完备法律体系。
(三)改革政党制度
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经历时代变迁而生存,必须不断增强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了严重的问题:退休制度急待实行、党员队伍问题突出、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关系需要加强等。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废除任职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并强调这是影响到党国存亡的问题。1981年,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此后,邓小平多次提到要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它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12]。此外,邓小平还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强化党内纪律监督机制。1980年11月,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论断,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此后,这一论断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指导方针。1983年10月,党中央又做出整党的决定,决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另外,中共加强了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关系。肯定了各民主党派都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因此,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13]。这些论断对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55.
〔2〕〔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4-255,379.
〔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57,1253.
〔4〕〔7〕〔9〕〔10〕〔12〕〔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1,367,333,144,397,187.
〔5〕毛泽东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07.
〔8〕刘军.新权威主义[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318.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