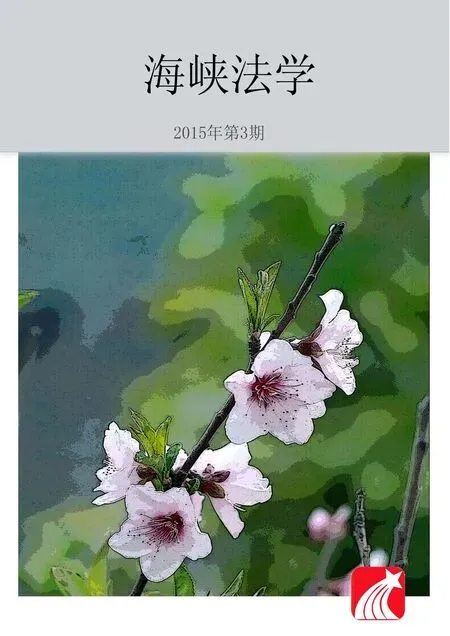中国法上的“亲属拒绝出庭权”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误读、缺陷与重构
马 康
中国法上的“亲属拒绝出庭权”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误读、缺陷与重构
马 康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规定严重破坏了刑事诉讼法所力图构建的证人出庭作证体系。而且理论界存在将此项规定误读为中国封建法上的“亲亲相隐”和西方“亲属拒证特权”。《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总结为中国法上的“亲属拒绝出庭权”,既阻碍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也剥夺了被告人的对质权,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趋势。在厘清对《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误读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刑事诉讼法》已确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制度,采用授权性规定为主、例外性规定为辅的模式进行重构。
亲亲相隐;亲属拒证特权;拒绝出庭权;缺陷;重构
一、引言
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已久的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证人作证保护、证人作证补助等措施同近亲属作证一起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证人作证制度,以求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证人出庭难”。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法院可强制其出庭作证,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严重破坏了刑事诉讼法所力图构建的证人出庭作证体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一经颁行,对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的问题立刻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议的热点之一,而且在实务裁判中也已初现端倪。在广受瞩目的薄熙来案件中,辩护方两次要求薄谷开来出庭,认为薄谷开来固有的精神障碍不能保证作为证人的可信性,而且作证的环境较为特殊,证人很有可能是基于特定压力或者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而提出证言。法庭对此的回应则是,薄谷开来属于被告人薄熙来配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8 条第1款的规定,在证人拒绝出庭时,不能强制她出庭作证。①引自薄熙来案判决书,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19206397.html?keywords=薄熙来&match=Exact,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5月19日。
上述裁判表明,当控方证人同时是被告人近亲属时,由于证人利用《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拒绝出庭作证,而被告人无法有效行使辩护权对其加以反驳,这进一步恶化了被告人在庭审中的处境。但在薄熙来案之后,仍有研究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仅契合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特免权制度,而且源自我国传统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②刘昂:《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载《证据科学》2014年第1期,第23~24页;马涛:《论亲属免证权及其构建——以港澳台立法为视角》,载《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85页。这一认识不仅是对我国封建时代“亲亲相隐”和西方近代“亲属拒证特权”的误读,更为重要的是忽视了此规定的内在缺陷。而且,《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存在立法定位的模糊和妥协性,使得这一制度进退失据。
本文拟在分析“亲亲相隐”和“拒证特权”的基础上,指出对《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误读,在厘清《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真正含义及其内在缺陷的同时提出重构意见。
二、对《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误读
(一)误读之一:混同中国封建法上的”亲亲相隐”制度
诸多研究者之所以将《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误读为”亲亲相隐”制度,根源在于对“亲亲相隐”制度的错误理解,仅看到了二者价值取向上的趋同,并未深入研究“亲亲相隐”制度的本源及其在封建伦理中的特殊作用。因此,在厘清两种制度之前,有必要对中国封建法上的”亲亲相隐”制度做一梳理。
“亲亲相隐”制度根植于礼法制度之中,其源头可追溯至儒家经典《论语·子路》,并逐渐内化为中国古代封建法的一个重要原则。经过汉代初期的儒家化过程,董仲舒倡导“春秋决狱”,率先在司法审判中开容隐之例。汉宣帝在地节四年下诏,明确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父子之亲, 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一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亲亲相隐”正式由儒家学说转变为封建法律制度,并在整个中国封建时期沿用。
封建时代的容隐制度发展到唐代趋于完善,并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汉代“亲亲相隐”的适用范围还仅限于父母、夫妻和祖孙之间,唐朝则在具体适用范围上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为封建统治者所盛赞“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中,“同居有罪相为隐”成为基本原则,《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露其事,及擿 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此时容隐的主体已经不仅限于血缘亲属,延伸至同主人共同生活的部曲和奴婢。除“谋反、谋叛、谋大逆”的三谋之罪外,奴婢、部曲不可告发主人,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处以绞刑。这些细微的变化都体现了“亲亲得相首匿”逐渐向“义务化”的方向发展。此后,从宋代一直到《大清律例》,基本沿袭了唐代的规定,容隐范围也逐步扩大到了岳父母和女婿等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混同为“亲亲相隐”制度,根源在于对“亲亲相隐”制度的错误理解,主要原因在于仅看到了形式上的相似,而没有结合具体的法律环境加以分析。概括而言,二者的关系恰如“形似而神非”。《唐律疏议》规定的亲属间容隐主体限于“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严厉禁止他们“漏露其事”和“擿 语消息”,也即是容隐主体对于尊亲属的犯罪事迹,既不得向普通民众“泄露”,也不得向国家机关“擿 语”(告密)。诸多研究者正是看到此点,指出《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免除了被告人近亲属出席庭审作证的义务,等同于《唐律疏议》规定的禁止“漏露其事”、“擿 语消息”。认为立法意旨似乎在一般作证义务之外设立例外,通过豁免被告人近亲属的豁免义务来维护伦理亲情。
但是,封建法中的“亲亲相隐”制度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着本质区别。“亲亲相隐”制度一方面从法律上剥夺了义务主体的作证资格,另一方面以施加刑罚的方式迫使义务主体遵守规定。利用最严重至绞刑的刑事处罚这来防止卑下作出对尊长不利的证言,可见,亲亲相隐的本质是一种封建义务,而非现代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诉讼权利。而《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涉及近代刑事诉讼意义上的权利概念,完全不同于中国封建法中作为被强制的义务主体所承担的义务。由于被追诉人近亲属的身份不同于普通证人,为了维护家庭伦理价值,允许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提供证言时,遵守不同于普通证人的特殊规定。
可以认为,“亲亲相隐”制度内含的人伦精神和合理部分被《刑事诉讼法》所吸收,但不能据此全面接受“亲亲相隐”制度,将其作为《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历史渊源加以称颂。
(二)误读之二:混同西方近代法上的亲属拒证特权
亲属拒证特权是指依法提供证言的证人基于其同被追诉人的婚姻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拒绝作证的一种诉讼权利。①张保生主编:《证据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页。在英美法系证据法中,亲属拒证特权具体表现为亲属特免权,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证据规则。美国“所有的司法区都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夫妻特免权,此外,在内容上夫妻间还享有秘密交流的特免权”。②卞建林著:《美国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大陆法系国家将这一权利通常称为“拒绝作证权”,以“有权拒绝作证”的方式规定了亲属拒证特权。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人的订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3.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③李昌珂著:《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规定不适用于“虽然不是被告人的配偶,但与其象配偶一样共同生活的人或者曾经与其共同生活的人;已同被告人分居的配偶;对其宣告撤销、解除或者终止同被告人缔结的婚姻关系的人。”④黄风著:《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论者将“亲亲相隐”和“亲属拒证特权”混为一谈,作为中西制度的共性来论证。⑤步洋洋:《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 的修改为视角》,载《政法学刊》2014年第4期,第79页;刘昂:《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载《证据科学》2014年第1期,第23~25页;马涛:《论亲属免证权及其构建——以港澳台立法为视角》,载《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85~86页;钱叶六:《论“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刑事法律中之重构》,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6期,第26~29页。前文已述,中国封建法中的“亲亲相隐”本质上是基于儒家伦理而设立的封建“义务”,以严苛的刑罚迫使相关主体遵守义务。而“亲属拒证特权”则是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权利,权利主体完全可以基于个人意愿决定是否作证。如果从中西制度的共性角度考察,属于中西曾经共同适用的类似制度也只有“亲属拒证特权”。“亲属拒证特权”曾短暂存在于我国历史之中,清末修律虽然保留了亲属拒绝作证的内容,但已不再将亲亲相隐作为法定义务加以规定,标志着“亲亲相隐”制度逐步向西方的权利本位转变。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167条明确规定了拒绝证言的权利属性:“证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 正式取消了中国古代相隐制度中的义务性规定,采用“得拒绝证言”的权利性条款,标志着特免权制度在此时期的正式确立。⑥吴丹红著:《特免权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亲属拒证特权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接受,是由于其符合认识规律和人权理念。这一制度的理论假设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时面临众多价值的冲突,证人作证体现的价值是保证最终的裁判符合案件事实本身,与之相冲突的是亲属之间的社会伦理价值。牺牲后者虽有利于短期内发现案件事实和惩罚犯罪,但长期来看破坏了亲属之间的天然感情和后天建立起来的良好信任。信任一旦被破坏,为了避免被亲属披露对己不利的信息,被追诉人难以同亲属之间保持原有的信息交流,近亲属作证将难以提出有利于追诉犯罪的信息。
近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明确其性质是个人权利,主体“有权”拒绝作证而非“应当”拒绝作证。换言之,是否放弃此一权利完全取决于权利主体的个人意愿,如果权利主体愿意披露本受保护的秘密交流,将相关信息呈现于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则必须同时受到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约束,即作为普通证人接受“传闻证据规则”的限制,当庭接受被告人一方的交叉讯问,而非以不出庭的形式提供审前证言笔录证据。
回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明确了证人不需接受被告人一方的交叉讯问,审前证言的笔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因此,结合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的规定。可知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并没有被免除在审前阶段的作证义务,只是赋予一项免于同被告人对质的权利,这一权利使得证人避免了同亲属当庭对质的尴尬,减轻了他们提出不利于被告人证言的心理负担。这种立法设计有效地去除亲属作证的后顾之忧,有意或者无意地强化了打击犯罪的力度,显然不同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亲亲相隐”和鼓励社会伦理价值的“亲属拒证特权”。因此,《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并非任何意义上的亲属拒证特权,被告人的近亲属仍负有“作证的义务”,只是避免了规定在庭审中的对质。这一理解也在权威解释部门的相关著作中得到了印证,指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免于强制出庭,不是拒证权。并没有免除被追诉人近亲属作证的义务,只是规定在庭审阶段可以免于强制到庭,但仍然有庭外作证义务。①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最新修正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张军、江必新主编:《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对此可以称为“拒绝出庭权”,以示区别于“亲属拒证特权”。
三、《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缺陷
根据参与立法人员的解读,《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立法用意主要是避免强制出庭作证对家庭亲属关系的破坏。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politics/2012-03-08/content_5355219.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6月24日。维系人情伦理的立法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任何美好意愿都不会自我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条文是否能够自洽于现有法律体系?现实环境是否存在制度运行所必须的配套措施?这些问题往往决定了具体制度的最终效果。而《刑事诉讼法》恰恰在此出现了致命的缺陷。
(一)阻碍了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
《刑事诉讼法》第60 条第1款确立了公民普遍作证的义务,该条第2款规定,只有“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才不能作为证人。因此,除非上述特殊情形,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只要知道案件情况,当然具有作证的义务。由于我国并未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和直接言词规则,侦查机关在获得证人提供的证言之后,通过询问证人形成书面的证言笔录具备证据能力,作为重要的控诉方证据进入后续的诉讼程序。在庭审阶段,通过宣读证言以代替证人出庭已经成为实践中的普遍做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司法解释的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8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司法解释确立的“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采用标准,使得证人不必接受辩护方的当庭质询,其在审前阶段所作出的证言除非有受到真实性的质疑,一般可作为证据使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434条也明确了公诉人在法庭上应当宣读书证、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等。《规则》第442条规定公诉人在庭审时针对证人当庭的虚假陈述,应当宣读证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的证言笔录。
由上分析可见,我国刑事诉讼从法律文本到实践活动,都确认了审前阶段证人笔录的证据能力。换言之,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即使不参加庭审,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所提供的证言,同样可以用于对被追诉人的指控。
此外,鉴于侦查阶段固定证据对后续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影响,我国律师是否在侦查阶段享有向证人取证的权利,一直存在较大争议。①汪海燕、胡广平:《辩护律师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辨析——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1期,第87~88页。被告人无法在庭审中通过当场质证来反驳对自己不利的此种证言,辩护律师又无法在侦查阶段通过调查取证的方式加以核实。这些规定进一步恶化了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处境,控辩平等对抗原则在此处无从谈起。虽然检察机关在我国属于法律监督机关,应当满足客观、中立的法律要求。但是处于控诉方追诉犯罪的职责,难以全面、客观地收集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刑事诉讼庭审通过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逐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可以促使法官客观、全面地认定案件。英美法系的学者认为,对抗活动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最好方法,在实践中也运行良好。②[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经过上述考察,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他规定和刑事司法的运行实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规定,不仅没有实现维护亲属伦理的功效,而且破坏了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查明真实。
(二)剥夺了被追诉人的对质权
对质权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与此相对应,大陆法系国家则通过直接言词原则来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虽然直接言词原则与对质权存在一定联系,但直接言词原则主要用于大陆法系,只有对质权制度通行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质权是在促使证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的最有普遍性的制度。③易延友:《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63页。
时至今日,充分尊重和维护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已经成为公正审判的最低保障标准之一,逐步被国际公约所吸收、借鉴 ,构成了公正审判权的内在要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 条第3 款(戊)项明确规定了对质权,“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障……(戊)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对欧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人权公约》也将对质权赋予刑事诉讼的被告人,《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规定:“被诉刑事违法的任何人均享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d.对不利于他的证人进行质询,并在与不利于他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使有利于他的证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对质权在《欧洲人权公约》的确立,使得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一律享有对质权,并可以此权利受到侵犯为由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
域外法治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刑事诉讼中普遍赋予被告人对质权,是基于对质权对程序正义的重要意义。对质权的存在,使得证人如无特殊情形,必须在法庭上接受审查。被告人因此获得了当面询问证人的机会,针对不利于自己的证言进行反驳,有效地甄别了证言的真伪。与对质权密切联系的交叉询问被威格摩尔赞誉为发现真实最伟大的法律装置。④John Henry Wigmore, 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 Peter Tillers Rev..Vol. 5,Boston&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3,1367,at 32)。转引自易延友《“眼球对眼球的权利”— —对质权制度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1期,第55页。对质权虽然在实体上通过利害关系人的当面质证,但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加强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在程序上维系了被追诉人的参与感,最大限度实现了被告人的程序公正。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必然存在部分案件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案件的事实真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对案件当事人而言,完整的实体公正此时已经无法达到,唯一可以实现的就是程序公正。如果程序公正,即使实体处理没有达到预期,当事人也可能因为程序的公正从而理解并接受实体处理。对质权促进了程序的透明度,让当事人充分参与到诉讼活动中,进而增强了司法裁判的正当性。
对质权是世界范围内广泛适用的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但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质权就是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第一步,应当适当承认并强化被告人的对质权。①魏晓娜:《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90页。
在此大背景下,仍然变相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既不符合诉讼法理,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重构变得势在必行。
四、中国法上的拒绝出庭权:重构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不仅降低了案件事实真相的可能性,而且剥夺了被告人的对质权,不符合当前审判中心的司法改革趋势。鉴于此,虽然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是维护法律权威和实现法治的必要条件,但“拒绝出庭权”的存在使本就不甚严密的作证体系出现了重大疏漏,需要“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②[德]卡尔·拉伦次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6页。因此,应对《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加以重构。
在中国的法学研究中,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似乎是我国在立法时天然的模仿对象。虽然域外法治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我国刑事诉讼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比较法并不能成为解决中国现实法律问题的直接根据。笔者并不否认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和法律文本的简单粗疏,但这些并不能得出中国法律必须接受比较法的结论。相反,在吸收借鉴域外经验的同时,制度的漏洞更应当从《刑事诉讼法》固有的体系和精神中去吸取营养,使制度更加亲和《刑事诉讼法》,也易于为刑事司法实践所接受。《刑事诉讼法》第46 条确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同“亲属拒证特权”具有天然的相近性,其理论基础多有相似之处,可以作为重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参照。虽然我国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存在内容过窄,特免权的例外情况适用不清楚等不足之处,③关于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具体内容,参加马康《新刑诉法视角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思考》,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98~99页。④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页。但毋庸置疑,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巨大进步。可在借鉴我国律师——委托人特免权规定的基础上,重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相关规定。
(一)授权性规定为主
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亲属拒绝作证权需要通过立法上以授权性规定的方式进行。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亲属拒绝作证权一般以授权性的立法方式明确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④美国《1999 年统一证据规则》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绝作出对被指控的配偶不利的证言的特免权。”⑤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增补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年版,第29页。
《刑事诉讼法》第46 条以授权性的规定明确辩护律师有权对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予以保密:“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这表明授权性的特免权制度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固有内容,将《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修改为“授权性规定”是同刑事诉讼法体系相融合的。因此,建议应当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语言表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拒绝作证。”之所以没有采用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有拒绝作出对被指控的配偶不利的证言的特免权”的表述,是考虑到一旦将拒绝作证的范围限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言”,可能会在法律解释方面存在疏漏,以近亲属的证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从轻量刑”为由曲解此项规定。因此,笔者认为,以采用德国式的立法表述为佳。
(二)例外性规定为辅
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中,应当权衡亲属伦理和社会秩序,当近亲属拒绝提供证言而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时,应当限制被追诉人近亲属此项权利的行使。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也是采用授权同例外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46条在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之后,以但书的方式规定“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辩护律师一旦发现法定的三种例外情况,就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因此,作为亲属拒绝作证权的例外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中应当增加但书部分:“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除外。”
(责任编辑:林贵文)
D925.2
A
1674-8557(2015)03-0114-07
2015-09-10
马康(1990- ),男,河南平顶山人,中国政法大学2015级诉讼法学司法文明方向博士研究生。
——以“亲亲相隐”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