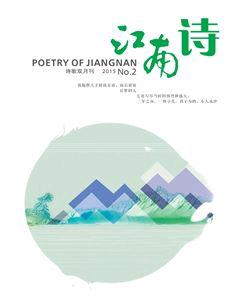“我说出”,“我看见”,“我抓住”
——诗人伊甸精神肖像
◎沈健 Shen Jian
“我说出”,“我看见”,“我抓住”
——诗人伊甸精神肖像
◎沈健 Shen Jian
一、千禧之年:“名字正式改为伊甸”
在公元新千禧之年深秋一个工作日,笔名伊甸完全覆盖真名曹富强,标志着诗人伊甸的公民身份在法律维度上得到了国家确认。在诗集《黑暗中的河流》“伊甸创作年表”中,诗人郑重记下一笔:
“2000年,嘉兴教育学院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为‘嘉兴学院’,我在文学院仍然教写作与当代文学。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名字正式改为伊甸。”
上述轻描浅写的“改”字,及其修饰状语“正式”,我更愿意读之为罗兰·巴特“零度写作”范式的一个诗句,中性、客观,近乎新闻叙述,一行荒唐字,满腔辛酸泪。自以笔名伊甸正式向汉语诗坛跋涉起算来,到世纪末整整18个年头,诗人伊甸的灵魂蜗居在锅炉工、大学生、教师曹富强的肉身内,经受了怎样一种“我正历尽沧桑”的憋屈与泪奔?
众所周知,1949年后所构建起的身份认同与户籍管理制度的铁血运转中,作为个体百姓骨肉欲裂的痛感,如果不是亲历其齿缝内部的残酷绞动,并且拥有“说出”能力者,谁又能够深切体会,并透彻“说出”?就曹富强而言,比如稿费单收款人“伊甸”,不是被查无此人退回原址,就是在派出所、街道办、工作单位的大红印章之间反复拉锯;再如1988年女儿伊水出生后,户口申报时由于与父母姓氏不一而遭遇的扯皮与口舌。诸如此类,无以穷尽,有形的桎梏与无形的刑枷,对以自由为天性的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灵魂脱下了曹富强的外套,而与肉身伊甸融合之后,诗人的生存将有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对诗人的写作会产生何种影响?这,需要我们以历史的显微镜去细细究察。
在撰写《吹进灵魂的风:伊甸论》一文时,我曾写道:“从曹富强到伊甸的历程,是一个俗世之人走向著名诗人的历程,是曹富强在艺术之路上脱胎换骨的历程”。现在看来,仅仅从艺术视角考察其间的嬗变信息,也许还只是方法论上的皮相之见。从曹富强进展到伊甸,实现诗人与公民身份的双重确认,让日趋衰弱的伊甸肉身收纳诗人伊甸不断强大的灵魂 ,也许不仅仅意味着方法论上的进化,其间潜藏着本体论日益成长壮大的踪迹,是否值得我们深思?在诗集《黑暗的河流》中,伊甸非常自信,仿佛重新生长出观照世界的器官,“我看见”,“我说出”,“我抓住”,一种理性主义主体在场的写作姿态,低调而谦卑,闪耀在伊甸的文字丛林之中,“渐渐地逼近着冰山”。
二、“我看见”:“沉默着沉默着有人不沉默了”
《黑暗中的河流》共收209首小诗。“看”可以视之为诗人主体存在的关键动词。直接以“看”来统领的组诗《看夜》有7首。另以“看见”、“我看见”、“对视”、“看不见”、“蓦然回首”为题的诗大约20来首。以“看”作为关键词义在文本内逐一搜索,与“看”、“目”、“视”、“瞧”等眼睛相关的诗涉及近百首。
诗人流沙河在《白鱼解字》一书中,对“看”字作了非常有趣的解说,他用小楷写道:“‘眼睛’二字形声,已属晚造。‘眼’即目,‘睛’指眼珠。甲骨文‘目’多为左眼。注意内眼角,睑皮搭下,谓之蒙古皱折,为我东亚人之特征。篆文‘目’作偏旁,只好竖立,大不近情。篆文‘看’,左手搭棚远方。‘见’比‘看’进一步,本人去见面”。这段文字抄列在此,作为“我看见”的肉身在场支撑,将诗人伊甸直接胶着在“低处”、“暗处”、“深处”、“弱处”、“别处”……而不是像罗·巴特所谓的那样“写作主体自身悄悄抽身走开,留下自己的‘符号—影子’来虚拟地与现实打交道。”
《黑暗中的河流》就是一首典型的以伊甸肉身在场介入存在的诗:
“我们看不见河流/但是它在流/我们听不见水声/但是它在流//我们爱它,我们给它们写一千首赞美诗/但是它们在流/我们恨它/我们发誓忘记它/但是它们在流//我们远远逃开,一去不返/但是它们在流/我们寻找它,像寻找圣地一样虔诚/但是它在流//我们气急败坏地吼叫,咒骂,威胁/但是它在流/我们取消它,删除它,否认它的存在/但是它在流//黑暗愈来愈黑,愈来愈暗/但是它在流/天塌下来,堵塞了它以外的所有河流/但是它在流。”
“河流”,由数不胜数的水滴构成,是母性、生命、自由、爱的象征空筐。作为一个时间性总体意象,如若与《广场》对读,则会产生时空拆卸、打乱、重组、新建诗性时空的审美效应:
“那些鸽子白得/像是纸做的//那些灰尘严肃得/像是穿便衣的黄金//……那些石缝里残存的血迹/像问号等待注释//……//那些遗忘,那些冷漠/像是洪水漫过广场……//那些石板下沉默的泥土/像冷峻的时间——一切的见证者。”
上述诗句有节选,将其中过于直白的句子去掉后也许更具发人深思之震荡力量。“广场”是块状固化了的“河流”,而“河流”则是流动液态的“广场”;“广场”既有总体性大一统的国家治理空间象征意涵,又粘附着开放、自由、多元心灵诉求空间的能指语义;“河流”也是如此,既有“流动、开放、汲纳、激情”等活力磅礴的隐喻,也包罗着“死水、臭水、干涸、消失”的死亡修辞。当《广场》与《黑暗中的河流》汇聚于“见证者”这一历史性意象时,诗,对自由的政治诉求被巧妙转换为审美的诗学诉求,显性的社会命运修辞被隐性地转换成历史命运修辞,启迪心智的力量沛然而起。
出生于1953年的伊甸事实上是与北岛同代诗人。北岛大他4岁,芒克大他3岁,舒婷大他1岁,而王小妮则小他2岁,顾城小3岁。作为外省诗人,伊甸因文化信息的落差而成为后“朦胧诗”一代诗人,几十年的写作所创写的泛拟人化的抒情话语,已经为诗人赢得足够的声名。如果诗人仅仅停泊在时空意象宏大主旨下摇镜头式地罗列他的“看见”,那么,其同质化写作的局限性将成为一种个人风格的陷井。正是在这样语境下,诗人不断地放低身段,“转型”、“换血”,以“黑暗”参与人与受害人的双重身份,沉入陡峭的“黑暗”,“学会在黑暗中看透黑暗。”
“血流着流着不见了
开枪的人松了一口气
泪流着流着不见了
指挥杀人的人松了一口气
呼喊声响着响着不响了
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气
……沉默着沉默着有人不沉默了
地下的灵魂松了一口气”
这首诗只有短短8行,题为《血流着流着不见了》,“不见”是“看见”的另一面,“看不见”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看见”主体能力、勇气、胆识问题,也有阻扰力量的邪恶、强大、无底线问题。诗通过日常口语的普泛平朴,写出了深蕴历史人心的时间伟力。
显而易见,对瞬间的尖锐质疑,对永恒的本质追寻,呈现出的是一种典型主体在场品格,一种从理想主义出发,杂糅着陀斯妥耶夫以降的现代诗学品格:质疑而非盲从;个人而非群体;肉体而非物质;在批判中建构,而非在消解中毁弃。立基于此,伊甸完成了诗学自觉的转身,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变得节制、客观、镇静了。诗人早期关注的公共事件与外部历史主题,通过戏剧性场景内化为一个个“我看见”:
“它依然凸着白眼珠/死死地盯着我。我鼓起勇气与它对视/‘看谁盯到最最后!’我一步一步/向它逼近,它的眼珠突然消失了/咄咄逼人的光芒——蜘蛛死了/它不是被我盯死的。一只早已死去的蜘蛛/用一粒掉在它头上的白墙粉/审判了我,谴责了我,恐吓了我”——《与一只蜘蛛对视》
“整整两小时/我就这么坐着/盯着书桌上一张白纸/整整两小时/我就这么盯着——/盯着——盯着——/书桌上一张白纸/整整两小时/我不喝茶,不小便,不想女人/书桌上一张白纸/大脑中一张白纸/我盯着——盯着——盯着——/盯得两张白纸/一点点渗出血来”——《白纸》
“起先以为是一种错觉:看黑看得太久了/从黑中看出了白。像要反驳我似的/那白一点点亮起来,它仿佛在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看着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仔细察辩这一状态,“我看见”中的“我”,已经接近物我合一主体间性的“我”,相当于庄子“吾丧吾”中的“吾”,通过浑茫与苍凉、包容与厚重、沉郁与执着来观照对象并蓄发诗意。《与一只蜘蛛对视》、《白纸》特别富有意趣,它们通过戏剧性的“紧张”描述,让诗歌的话语主体直接外化为一种“行动”,让独幕剧式的事实在运行中凸现其自身发展的力量与意味,情感评判和价值倾向如水随形深蕴其中。在这样写作中,伊甸变得那么谦卑、和蔼、低姿态:
“我看见了未来——它多么模糊”(《羊城夜雨》);
又是那么的清醒、自律、博大:
“对庞大的劫难必须俯瞰/对细小的柔情必须仰视”(《帕斯捷尔纳克》)。
他甚至渴望通过“慢”来抵达“快”,通过“少”来达成“多”:
“我喜欢看一些老人/慢悠悠地散步/慢下来,慢下来……甚至停住脚步/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我羡慕他们/有那么多好看的东西/我想,与其老了才慢下来/不如现在就慢下来/我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看的东西”——《看老人慢悠悠散步》
这是一种历尽沧桑的绚烂,饱尝忧患的成熟。诗,在这样的语调与节奏中,不再是黄钟大吕震荡人心,而是个人化幽径上的独省沉思;美,不再是悬搁在隐喻天空中宏大的预设理念的传达,而是润物无声的悄悄话,悄悄地修正人心,唤醒感性。
三、“我说出”:“我的喉咙发不出一丝声音”
“我说出”,是“我看见”的主体衍展,肉身在场支撑着我们对存在目击之后的诘驳与拷问。在《说出》一诗中,诗人写道:
“我想代一棵草说出它被歧视的痛苦/代一缕风说出它无家可归的惶惑/代一片落叶说出它的衰老、它的疾病/代一粒泥土说出它的委屈——它竭尽全力奉献/却摆脱不了被践踏的命运……我代它们说出了这一切/我就不用说自己的什么了”
存在于“被代表”境域内的卑微生命,其痛楚、委屈、惶惑、抑郁、焦虑,是那么地逼真而触目,但他们“说出”的能力已丧失殆尽,更别说“说出”权利与通道的自主运用!在“我”代为“说出”的语链中,“草、风、雨、落叶、泥土、天空”……这些天地环宙间底层草根、形态各异的卑微生命,通过“伊甸”之唇“说出”他们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获得了尊严的确认,重树了权利的大纛。
我们知道,话语权是人权核心。“说出”,就是直击真相,就是对存在的重新命名;“说出”就是“替”人“行道”,就是在“黑暗的河流”中,“点燃小小的火焰”,让意义重返人心,照亮绝望;“说出”就是要像萨义德所定义的那样,以“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角色,“对抗正统与教条”,“对权势说真话”。
而这,需要能力,更需要勇气。生活中的伊甸不善言辞,小说家草白在《那个叫伊甸的诗人》一文中,以女性的敏锐直觉看出,伊甸是一个“不擅于说话的人”,有一种“天性中的笨拙,倔强和隐约的孩子气”。确乎如此,伊甸从来不曾滔滔不绝,永远也不会绘声绘色,普通话很“方言”,急起来还会结结巴巴。但是,伊甸在他最初的诗歌中却轻松洒脱,阳光诙谐,找不出任何吐字木讷、话语涩滞的蛛丝马迹。
“劳动者又从黎明出发了/歧路上已派乌鸦驻守/喜鹊的歌唱代替了知了的聒噪/指引一条没有陷阱的道路/每一颗心都是一曲英雄交响乐/有着黄河般肤色的人群/命运注定了黄河般曲折的经历/命运注定了奔向大海的使命”——《开桔花的土地》
这是1981年诗人参加浙江“桔花诗会”的一首诗片断,节奏昂扬铿锵,激情浩荡澎湃,意象富蕴丰盈,结构开阖自如,与后来诗人构思奇巧、意象鲜活的“生活流”诗歌一起,为诗坛留下了乐观主流的精神肖像,至今仍令人不无赞叹。
到了写作《喧闹的正午》的时候,伊甸明显地有了“口吃”“失语”的症候。
“蝉儿叫得多么起劲/像撒娇的孩子任性地呼唤着亲娘/少年的嚷嚷声穿过鱼网/像无赖的黑鱼在水塘里窜来窜去//迎亲的锣鼓声愈来愈近,男女老少涌向村口——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成亲//……如今喧闹的是钢铁,是钱币,是遗忘/这个衰老的正午,我的喉咙发不出一丝声音”
“正午”是一个诗人十分偏爱的明亮语象,约翰·多恩就曾写过“正午,它的下一分钟就是黑暗”,表达了对辽阔光明的“正午”稍纵即逝的眷恋与悸怖。是的,“正午”是一个开放性的语域,它指向充盈、丰富、旺盛、壮年、成熟、丰收、灿烂、广阔、自在、无限、客观……这样一些强大的生命能指。然而美好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成亲”的“正午”,却突然笔锋一转,堕入了“衰老”的“如今”,进而生发了毁灭性“失语”。显然,这是一场个人柔软内心的空前火灾,也是一场人学文明的史无前例的海难,跌宕其间,人何以堪?置身其中,“我的喉咙发不出一丝声音”,“我的舌头锈迹斑斑,而城市的舌头——灰尘飞扬的马路,却整日絮聒不休”。究竟,这是一种悲催到何种程度的时代镜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海子之死与女儿伊水的出生,以及身边亲朋文友生离死别的惨遇,驱使着伊甸对过往的天真进行触及骨髓的反思与批判,大量的阅读与对话让他获取了一种“一个人走进黑暗”的能力。“新千禧年”前后,伊甸“替”人“行道”“说出”的语速明显慢了下来,语调也趋于低沉、凝重,像“赤裸着身子的河流,被北风卡住了喉咙”(《羊群和老人》)?“用沉默说话,用唯一的黑色概括生命”(《树殇》)。
在想象力的严寒与生命力的荒凉中,诗人孑然一身,“走进黑暗”,口中念念有词:
“你必须有比这片废墟更大的耐心/甚至,更多的伤口……”(《在废墟上》)。
眼中所见耳中所闻:
“一场冷酷的雪面无表情地埋葬了/大地上所有的问候、祝福/叹息、哭泣、申辩、控诉……”(《在沉默中》)。
究竟,这是怎样一种嗫嚅,一种哽咽,一种曼德斯塔姆式被“掐住喉咙”的控告?究竟,这是一种怎样一种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我怕我配不上我承受的苦难”,一种叶芝式的“向生活,向死亡,投上冷冷的一瞥”的沉默与怅惘?究竟,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个人悲凉之景像?
这简直就是一个Internet时代的哈姆雷特!一幕又一幕,目睹着他那灵肉吁请与良知索要,黑暗已不仅仅是某一肉体的黑暗,而是他所属群体的良知黑暗;“衰老”也不仅仅是肉体的“衰老”,更是他所属时代的“衰老”。
就这样,诗人伊甸找到自己的方式,泅渡在“黑暗的河流”中,“让我用沉默说出尊严”!他深深地相信,在光明和真相“开始说话的一天,我们终将全部变成哑巴”(《童年的冰》)
四、“我抓住”:“抓住自己的良心,直到抓出血来”
在知识分子身不由己地内嵌于利益网络之中的今天,疏离体制,恪守尊严,“抓住诗歌这只扶手,在角落里站稳”(《角落》),除了伊甸,谁还能够保有这样的定力?
“你路过角落/或者一直呆在角落/你像一位秋收后田野里捡稻穗的老农/辛勤地捡拾这里的悲悯/和安详”——《在角落里》
除了伊甸,谁能像塞弗尔特那样失声吞语:“让我抓住……抓住自己的良心……直到抓出血来”(《诗人》)。除了伊甸,谁耐得住秋收后大地辽阔的寂寞,放弃物质的狂欢与欲望的消费,安享于悲天悯人的感恩、沉思与慈祥?
“抓住”是诗人连接世界的一个“榫扣”,也是世界联接诗人的一个“铁锚”。一方面,肉身必须“我抓住”,通过“抓住”确认肉身“在场”,向虚无、荒诞亮出反抗的“一朵小火焰”;另一方,世界必须“抓住”我,通过“抓住”显现时间永恒、美的短暂和人的虚无。随着年岁增长,一种衰老、病痛、死亡的恐惧几乎“抓住”了诗人,身体每一个风吹草动的细小变动和身边亲朋的任何坏消息,给他脆弱身心施加的打击都是致命的。而随着智慧的成长,对命运、生死、殉道与意义的思考,诗人的灵魂越来越达观,因乐天知命而“学会“弯成一个直角”,沉醉于“用一把锄头跟土地亲密地交谈。”(《在山村》)
2014年,伊甸正式退休,女儿结婚。在退休之前,他连续两次被嘉兴学院学生评为“心目中的好老师”。这个荣誉完全由学生投票产生。在9月份开学典礼上,他代表老师作新生发言:
“大学时代,我们要学好我们的专业,更要在精神和人格的层面上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一个正直、善良、独立、理性、对人世间的美好事物充满热爱的人,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人,一个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的人,一个对复杂的人生和社会有基本判断力的人。”
发言在微信贴出后,点赞与跟帖者不计其数。绝大多数是伊甸历年来的学生。是的,无论教书,还是写诗,或者育女,抑或打牌、娱乐,伊甸都以一个彻底忘我、全心投入的“在场者”姿态“抓住”今天,“抓住”此刻,“抓住”诗人伊甸的“在场”创造,“抓住”公民伊甸的人生承担。
即将出版的诗集《颤栗与祈祷》(或名《在天地之间》),是一本以“我在”我“抓住”为主题的诗集。全书190余首小诗,长短不一,全都由“在……”为题,昭示出一种对人生和世界充满热爱与负责的诗人绝不怯场、永不退场的“介入”:
“像一连串问号的疯狂旋转//你忘了哪是天,哪是地/你被裹挟,被绑架/你没有一秒钟的时间呼救/你的挣扎比不挣扎/还要糟糕//在监狱里可以咬牙等待/在黑夜里可以仰望星光/在漩涡里你无法控制自己的任何动作/你丢失了全部思想//它甚至不让你流泪/不让你流血/不让你感受疼痛//它要你彻底晕眩/它要你百分之百忘记/你还是一个——人//你甚至不是一滴水/你什么也不是/你只是晕眩本身。”——《在漩涡里》
“漩涡”是流体力学作用于水的结果,也是风在大自然中高速旋转的结果,具有丰盈的生命、自然、力量、心灵、场域的象征意义。这首《在漩涡里》,是诗人主体清醒地“抓住”自己清醒肉身的宣示。只要稍有松懈,就会“你什么也不是”,就会成为“晕眩本身”。而“漩涡”的存在价值恰恰是因为有“你”的角力,因为“抓住”了“你”而意义培增。“你”与“漩涡”之间紧张,是诗人与世界紧张的互文缩写。
读一读这首《一个人走进黑暗》:
“一个人走进黑暗/走进这块比世界还要大的岩石/他不是来寻找宝藏/他来看看这黑暗/摸摸这黑暗/他想发现它坚硬和柔软的部分/黑暗最柔软的部分/也像蜈蚣、蝎子和蛇/又狠毒又狡猾/但他走进了黑暗/他要看看这黑暗/摸摸这黑暗/他要用自己最坚硬的部分/去撞击最黑暗的部分/只要撞出一点火星就够了/只要有一点火星/……黑暗/就不会比世界还要大了”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存在象征,“黑暗”大过整个世界,怀着“只要有一点火星,黑暗就不会比世界要大了”的痴妄与执著,“一个人走进黑暗”内部与深处,他要“看看”“摸摸”“撞击”“黑暗”,他要“抓住”黑暗最坚硬的部分,他也让“黑暗”“抓住”自己最坚硬的部分。就这样,在与专制、暴力、虚无、死亡诸如此类“黑暗”的角力中,诗人荡涤内心黑暗,完善自我人格,赎拯个我灵肉。
这个“走向黑暗的人”,就是诗人与公民合一的伊甸!
五、微诗微解:“吹进灵魂的风”
2014年9月5日微信“朋友圈”伊甸发了一段文字,伊甸的诗《吹进灵魂的风》,并配“沈健赏析”,查了《浙江先锋诗人14家》一书,与这段文字有出入,这是我写的吗?恍兮惚兮。转录如下,结束本文:
“小时候,风能吹倒我的身体/但吹不进身体里面去//长大以后,风吹不倒我的身体/却能一点点吹进身体里面//中年时,风吹进骨头/有时我听见骨头里飞沙走石的声音/风正一点点吹进我的灵魂/等到灵魂灌满了风,我要在灵魂的壁上//戳一个洞,‘呼——’/把自己的身体吹得杳无踪影”。
生命的历程就是一个层层递进的方程式,灵魂的成长与肉体的衰老正好成正比,骨子里飞沙走石、布满自然与社会内容的时候,正是肉体摇摇欲坠之际。“吹进灵魂的风”,为理解“衰老的正午”提供了诠注与参考,是生命应对种种“火灾”的审美细雨。
风是诗人们喜欢用的一个意象。“我麻痹的灵魂要向它飞去,好让我呼吸故乡的薰风”,叶赛宁渴望的是自由主义的爱情之风;“好风不吹两遍,百思能炼纯金……崭新的思想在一切之废墟之上诞生……啊!让它们震颤吧,让它们震颤吧!……让它们的锐利将我们激励!犹如那浸了松脂的弦索被乐师的指尖弹奏……”佩斯的风是比风还广阔、比风还自由的创造之风;“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盛大。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让秋风刮过田野……”里尔克吁请与恳求的风中,饱含了对生命完满之际灵魂无可皈依的孤独和迷惘,满载着超越自然秩序,抵达上帝神性的渴望。吹进伊甸身体里的风,既有政治秩序的压抑,也有现实人生的宿命,更有俗世的人向超凡的神修炼进程中的无奈与怅惘,一种超越一切的自由之吁请,一种趋于永恒的恳求,一种对神性的憧憬。在灵魂的壁上戳一个洞,让伟大的自然把自己回收茫茫宇宙中去,实乃生命化境:消失即诞生,瞬间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