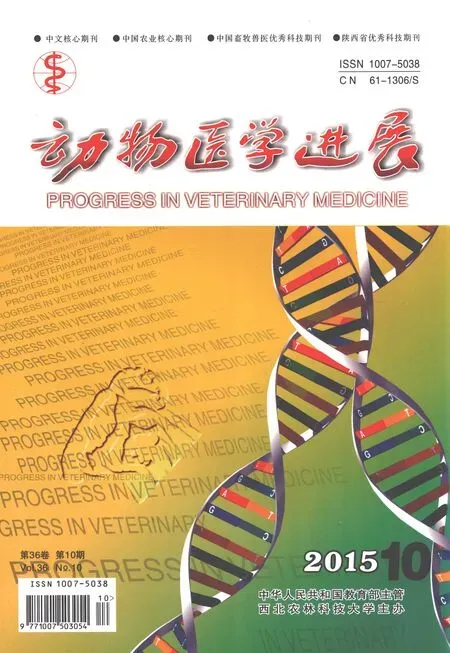免疫抑制性疾病防治的复杂性
摘 要:鉴于免疫抑制性疾病的复杂性及其多种因素往往是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互为因果,使其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认为经典科学的“单因素线性分析”已不能适应其要求,免疫抑制性疾病防治应转变科学观念,以复杂性科学的“多因素非线性分析”理念来指导;它不仅要重视病毒、疫苗与药物等因素的本身作用,更不能忽视其作用的“初始条件”;中兽医学的辨证施治是一种“状态分析与处理”,在“初始条件”认识上可以为其提供帮助与借鉴;通过不同途径或环节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增强或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达200余种,但其使用要辨证施治,才能取得更好的临床防治效果。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038(2015)10-0110-05
收稿日期:2015-01-13
基金项目:科技部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项目(2013EG134236);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2013FY110600-8);甘肃省青年科技基金项目(145RJYA267)
作者简介:罗超应(1960-),男,陕西户县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西结合与临床兽医学研究。
畜禽免疫抑制性疾病不仅种类多,发生原因复杂,而且其所造成的免疫抑制也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往往是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互为因果,使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变得更加复杂,给其防控带来了很大困难,使以往建立在经典科学“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基础之上的现代兽医学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考验。笔者在此谨从复杂性科学与中西兽医学结合的角度,对其做一探讨,以抛砖引玉。
1 免疫抑制性疾病所带来的挑战
针对免疫抑制性疾病,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用免疫增强剂或免疫调节剂。如猪用转移因子、干扰素、白细胞介素以及免疫核糖核酸、高免球蛋白、胸腺肽等,已成为人们预防免疫抑制性疾病发生的最常见选择。还有人参多糖、灵芝多糖、黄芪多糖、猪苓多糖、党参多糖、香菇多糖等,以及清热解毒、抗菌、抗病毒的清开灵、柴胡、板蓝根、双黄连、鱼腥草、大青叶、杜仲、穿心莲、连翘等中药制剂,以及左旋咪唑、维生素C等,都因为具有激活免疫细胞、调节免疫功能、增强免疫力之功效,而成为人们推荐应用的对象 [1]。然而,不仅是由于免疫抑制性疾病种类繁多,发生原因复杂多样,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往往是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互为因果,使其发生与发展变得异常复杂,不仅给其防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且也使免疫增强剂或免疫调节剂,并非是简单地应用即可奏效的。如资料表明,不同的免疫抑制性病毒的亚临床感染在规模化畜禽群体中是非常普遍的,但往往只有在同一个体发生二重或多重感染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下,对个体和群体造成的免疫抑制和其他病理反应才比较明显。不同病毒分子在共感染细胞中可以发生基因重组的现象,病毒在同一感染细胞中的基因重组,大大加快了其生物性状(致病性、抗原性等)发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变异的突变毒株的形成;但这类不同的突变毒株是在感染动物体内不断发生的,为什么只有少数突变株能够成为在动物群体中流行的野毒株?这涉及到病毒与感染细胞、感染个体与感染群体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不仅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也使建立在经典科学“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认识基础之上的现代兽医学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如我国猪瘟兔化弱毒疫苗对预防猪瘟是世界公认最好的,我国猪瘟病毒野毒株中也并没有出现能抵抗现行疫苗免疫作用的突变强毒株;但近十多年来,却不断有猪场在多次使用疫苗后仍发生猪瘟的报告 [2]。猪繁殖与呼吸疾病综合征、圆环病毒病、伪狂犬病、支原体肺炎等都能破坏猪的免疫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免疫抑制,除了容易导致细菌性疾病混合感染或继发感染外,更为严重的是导致相关疫苗免疫失败 [3]。鸡新城疫病毒(NDV)的控制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艰难。商品肉鸡、蛋鸡和种鸡群,不得不从生命一开始就一再使用弱毒苗和灭活苗多次强化免疫,以减少由NDV造成的经济损失;但近几年来不少大型鸡场反映,鸡群产生的抗NDV的抗体水平都比前几年低得多,使控制NDV感染的目标变得更难实现 [4-5]。再如,目前已知通过不同途径或环节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增强或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达200余种,这其中既有多种补益类药物,也包括多种清热解毒、清热利湿、活血化瘀、利水等类的中药及其复方制剂,似乎所有的中药都有增强或双向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但临床实践证明,其并不是随便应用就可以起效的。如果药不对证,尤其是“中药西用”,不仅不能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还有可能引起严重的毒副反应 [6-7]。
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为不仅在免疫抑制性疾病防治上,而且现代生物医学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与挑战。如据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报道,在美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都同时患有2种以上的慢性病症,其中14%的人患有6种以上的常见病症,超过三分之二的医疗费都是用于多种慢性并发病症的防治。然而,已有充分证据表明,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因为费用高与疗效不佳,而在多种慢性并发病症的防治上面临着挑战。为了应对此公共卫生的挑战,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在2010年发布了“多种慢性病症战略框架”的报告 [8]。再如,今天基因组技术可以对人体基因组进行常规的扫描,以探讨其任何紊乱的遗传改变。有2 000种以上的单基因疾病已经通过这种方法得到阐明;然而,尽管剩余的2 000余种孟德尔疾病的遗传学改变似乎唾手可得,人们也已做了很多努力,但在普通病、慢性病与复杂性疾病中要获得类似的理解,却已经令人失望 [9]。人类基因组大约有21 000个不同蛋白质编码。而现在,这些基因近一半的功能只能靠猜测来获得。即使我们知道某一种特定蛋白质的准确功能与结构,把其导入常常具有极其复杂相互作用的细胞后,就像药物治疗一样,其结果却很难预料 [10]。具有罹癌风险的基因名录正在快速增加,而同时能对许多基因进行测序的费用则已下跌,致使如今美国基因测试包括了数十个基因。然而,一位《科学》杂志记者在阅读了有关携带某有害基因突变但却没有疾病家族史妇女中的乳腺癌和卵巢癌的一篇报纸文章后,决定接受测试。尽管多年来花时间报道基因检测,但她从来没有将镜头对准她自己的DNA。而她自己的经历证明比她所预计的要更令人胆怯,且在科学上耐人寻味,那就是意义不明 [11]。
2 从复杂性科学“初始条件”到中西兽医药学结合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鉴于传统科学(经典科学)每每在近乎于圆满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出错,在对其认识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不同于传统科学只强调世界的“物质性”,而更加关注复杂系统中的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因为人们发现,事物和过程往往处在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也不遵从叠加原理,一定的宏观行为是在复杂系统中微观组件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下而自发涌现(突现)的,体现出一种奇异的自组织特性。所以,复杂性科学认为,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由于其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不同,由于其作用的“初始条件”的不同,其物质或因素的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即复杂性系统(如动物机体)有时对一个小的作用可以做出巨大的反应,而有时对一个较大的刺激却又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受性,使其作用具有了“非线性”的特点 [12-13]。在免疫抑制性疾病的防治中,崔治中教授针对一些鸡可同时检出3种甚至4种不同的病毒,其先发生感染的病毒并没有直接引起发病,以及其中相当多的病毒只是温和性病毒或要在一定条件激发下才会引起发病的事实,参考“条件致病性细菌”的说法,提出了“条件致病性病毒”的概念;并认为其一,这一类病毒感染仅在造成免疫抑制,从而促发其他病毒或细菌发病时,其致病作用才显示出来;其二,确实有一些病毒感染可引起典型症状和病变,但其只有在其他病毒感染同时存在时才表现出来。接受和应用条件致病性病毒的概念,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在控制鸡群疫病的实践中一直很难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也会有助于更加重视控制那些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温和性病毒感染 [2]。这从传统科学“单因素线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也许并不太好理解,而从复杂性科学的“多因素非线性作用”的特点来讲,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根据复杂性科学理论来说,由于“初始条件”对物质作用的重大影响作用,在免疫抑制性疾病的防控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对各种致病因素及其疫苗与药物的作用,更要重视对其作用的“初始条件”的认识、把握与处理。如由于各种因素的不断变化与相互作用,使得病毒与感染细胞、感染个体与感染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疫苗、药物与病毒、感染细胞、感染个体与感染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关系与条件都发生了改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虽然我国猪瘟兔化弱毒疫苗对预防猪瘟来说是世界公认最好的,我国猪瘟病毒野毒株中也并没有出现能抵抗现行疫苗免疫作用的突变强毒株,但却不断有猪场在多次使用疫苗后仍发生猪瘟的报告;商品肉鸡、蛋鸡和种鸡群,不得不从生命一开始就一再使用弱毒苗和灭活苗进行多次强化免疫,而不少大型鸡场却反映,鸡群产生的抗NDV抗体水平都比前几年低得多,使消灭NDV感染的目标变得更难实现。因此笔者以为,不仅有必要提出“条件致病性病毒”的概念,而且还要对病毒、疫苗与药物等的作用条件(初始条件)的认识、把握与处理,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能对这类疾病的认识、把握与处理更加准确与全面,也才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众所周知,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是中兽医学的两大特点。中兽医药学的“辨证施治”实质上就是一种“状态分析与处理”。由于“证候”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能与某一种因素或组织器官相联系,而往往被认为不科学;但根据复杂性科学来讲,其作为各种因素或物质进一步作用的“初始条件”,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西兽医学已往所忽视与缺乏的。其一,多因素共同决定,其一方面导致了疾病发生、发展与表现的复杂性,而另一方面却又使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即决定疾病的各种因素组合也许是变化不定的,但其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病理状态或证候,反复出现却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其病理状态或证候的出现规律进行认识与把握,就可以达到认识与把握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综合规律的目标 [14-15]。其二,由于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是针对病理状态(证候)这一不同“初始条件”进行认识、把握与处理的,使其作用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等复杂性科学的认识特点,不仅其药味要随证而变化与加减,而且其每一种药物的用量在不同处方中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与西兽医学“致病因素与药物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的认识有很大不同 [16-17]。如据报道0.2mg乌头碱就可引起人中毒,2mg~6 mg即可致人死亡;而中医在临床上对心衰进行辨证施治,在不同的证候状态下与处方配伍中,附子用量从0.3g到600g,其间相差2 000倍,却都收到了良好的疗效而未见毒副反应 [18-19]。
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中药抗病原体的作用一般的来说都很弱甚或完全没有,但中西兽医结合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仅可以克服中兽医无证可辨与西兽医无病可识之不足,而且能够显著地提高与改善中西药物的临床疗效。如王今达等根据中医药解毒清热方药多具有对抗中和内毒素的作用,而在抗菌方面作用较差的事实,在救治感染性多脏器功能衰竭中提出了“菌毒并治”的新主张,采用抗生素抑菌杀菌,配合神农33号中药制剂拮抗内毒素的毒害作用,使其救治感染性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病死率由非菌毒并治的67%降至30%,尤其是五脏衰与六脏衰,由国际上几乎是100%的病死率降至50%和57%,为世界所瞩目 [20-21]。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有关单位开展的动物穴位免疫研究,采用疫苗后海穴一次注射,不仅可以使仔猪传染性胃肠炎(TGE)弱毒苗、细胞灭活苗、组织灭活苗、仔猪流行性腹泻灭活苗(PED)和TGE与PED二联灭活苗、猪旋毛虫可溶性抗原苗、羊衣原体卵黄囊灭活苗、牛乳房炎三联灭活苗、仔猪大肠埃希菌腹泻K88K99基因工程菌苗、马传染性贫血弱毒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双价弱毒苗、鸡新城疫弱毒苗,共计5种畜禽12种疫苗的用量节约50%以上,仍能达到或优于常规最佳途径的免疫效果;而且打破了“TGE、PED等消化道传染病疫苗,非经口服或鼻腔黏膜接种不能免疫”的国内外传统学术观点,至1998年底推广应用各种畜禽2 019.2万多头只,收到了良好的防病效果与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并已成为TGE与PED等疫苗的当前常规接种方法 [22~25]。
3 几点启示
免疫抑制虽然是免疫抑制性疾病的一个共同问题,但不同的免疫抑制性疾病或由不同原因所致的免疫抑制性疾病,其免疫抑制的机制、特点与结果是不一样的,要求对其防治要区别对待;尤其是免疫抑制性疾病种类繁多,发生原因复杂多样,其因素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往往是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互为因果,使其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变得异常复杂,不仅使建立在经典科学“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认识基础之上的现代兽医学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考验,而且也要求我们要转变科学观念,以复杂性科学的理念来指导其防治,以便更快地走出免疫抑制性疾病防治的困惑。
在免疫抑制性疾病的防治中,不仅崔治中提出了“条件致病性病毒”的概念;而且根据复杂性科学理论来说,在动物机体等复杂性系统中,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对同一物质或因素的作用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非线性”特点。因此,在免疫抑制性疾病的防治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对病毒、疫苗与药物作用的认识与把握,而且更要对其不同“初始条件”下的作用进行认识与把握,才能使我们对疾病的处理更加准确与全面,也才能取得更好的临床防治效果。
由于临床实际中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化性与不确定性,使得经典科学“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不能准确对其进行认识与把握,使现代兽医药在免疫抑制性疾病的防治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中兽医学的辨证施治是一种“状态分析与处理”,其实质就是针对“初始条件”进行认识与处理的,具有“多因素非线性分析”的特点,可以为其提供认识方法上的帮助与借鉴。
通过不同途径或环节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增强或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达200余种,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可以不加区别使用它们。因为不仅从中兽医学的角度来说,它们既有多种补益类药物,也包括多种清热解毒、清热利湿、活血化瘀、利水等类的中药及其复方药物,要求要用药对证,而如果不加辨证施治的乱用或滥用,尤其是中药西药化应用,不仅发挥不了防治疾病的作用,还有可能引起各种毒副反应;而且从复杂性科学的“初始条件”理论来讲,中兽医学的辨证施治也是必不可少的。
辨证施治以往给人的印象就是个体化治疗,然而,由于现代畜牧业集约化与规模化养殖的畜禽个体与饲养条件等的高度一致性,不仅使其疾病发生与临床特征趋于一致,而且也使临床辨证施治在畜禽群体上共同进行成为可能。这既为免疫抑制性疾病的防治带来认识方法上的帮助,也将为中兽医学的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