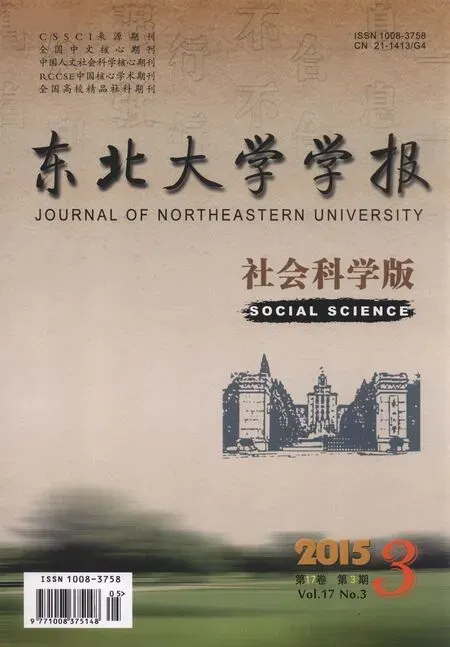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的立法构造——兼论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多数人侵权的差异
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的立法构造——兼论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多数人侵权的差异
王国柱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的“目标导向”与多数人侵权制度的“意思导向”存在着根本区别,多数人侵权制度无法替代间接侵权制度,有必要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进行法定化。我国关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立法虽有亮点,但总体上存在缺陷。应当在知识产权单行法中分别设立间接侵权规则,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进行类型化和体系化的规定,并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多数人侵权进行制度协调,进而对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关键词:知识产权; 间接侵权; 直接侵权; 多数人侵权; 共同侵权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5)03-0295-06
Abstract: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meaning orientation” of multiple tortfeasors. Since the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ld not be replaced by multiple tortfeasors, it is necessary to enact the legalization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though there are strengths in China’s legalization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aknesses do exist as a whole. The rules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 be set up respectively in the slip law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rules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 be categorized and systematized, and the indirect infringement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multiple tortfeasors should be coordinated so as to perfect the legalization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3.014 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3.013
收稿日期:2014-12-08 2014-10-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资助项目(14YJC71002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309150131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4AGJ004)。
作者简介:卢德友(1983-),男,贵州龙里人,南京理工大学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胡加祥(1963-),男,浙江嘉兴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刘婷(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
Legislative Structure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System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 Also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Multiple Tortfeasors
WANGGuo-zhu
(Law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Key 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rect infringement; direct infringement; multiple tortfeasor; joint infringement
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作为一种没有直接侵害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侵权形态,其合理性在于该种行为往往对直接侵权的发生具有诱导或帮助作用,即使在某些情形下与直接侵权无关,也导致权利人利益的损害。传统民法上的多数人侵权行为是由数个行为人实施,对同一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的侵权行为[1]。一般认为,多数人侵权分为共同侵权和非共同侵权(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前者实行连带责任,后者实行按份责任。就现有法律制度而言,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多数人侵权的关联性最强,两者在制度适用方面会发生交错,间接侵权的归责方式和责任承担方式可以从多数人侵权制度中找到根据,多数人侵权制度可以为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提供一般性的法律方法支持,以至于有人认为间接侵权可以被多数人侵权制度所替代,进而质疑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独立存在的必要性。本文从分析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多数人侵权的差异和多数人侵权制度的局限性入手,探讨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法定化的必要性,并评析现有立法和立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进而提出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立法完善的路径。
一、 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法定化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能否被多数人侵权制度替代,是探讨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法定化的核心问题。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知识产权直接侵权是相互对应的范畴,而共同侵权与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是多数人侵权体系中相互对应的范畴。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和直接侵权是以行为人是否直接实施了侵害专有权利的行为作为区分标准,构成直接侵权的行为都是受到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构成间接侵权的行为不受到专有权利的直接控制[2],两种行为的“目标导向”不同;共同侵权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是以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作为区分标准,共同侵权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而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则不存在,多数人侵权是以“意思导向”区分不同的侵权形态。从根本上讲,间接侵权和多数人侵权是不同区分标准之下形成的不同制度,并且分属于不同的制度体系。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设计的“目标导向”与多数人侵权制度设计的“意思导向”终究是有差异的。间接侵权制度根本上要解决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而多数人侵权制度是为多数人参与的侵权行为寻找解决方案,两者侧重点不同,多数人侵权制度无法替代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
1. 多数人侵权制度无法充分反映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属性
知识产权除了具有私权属性之外,还具有公共政策属性,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其地域性和阶段性的政策目标,知识产权战略就是着眼于发展大局而对知识产权这一政策工具的运用[3]。“较之其他私权而言,国家之所以提出知识产权战略而不是‘物权战略’、‘债权战略’,关键在于知识产权具有某种超越私人本位的公共政策属性。”[4]对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在符合本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的基本标准的前提下,由本国自主决定。对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大小、保护程度的高低,需要由各国根据本国国情的需要作出安排。就知识产权侵权而言,由于知识产权专有权利明确而具体,在国际上又有普遍适用的条约进行指引,因此各国关于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规定共性较多,而涉及到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各国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裁判呈现出多样性,其根源就在于各国基于本国国情作出的政策考量不同。技术、文化和商业领先型国家对知识产权有着强保护的需求,而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排斥过强的保护,强保护的支持者会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采取相对宽松的认定标准,而反对者会对间接侵权的适用采取审慎的态度。这种对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调控要想达到稳定的预期效果,只有通过立法进行制度设计方可达到。多数人侵权制度是典型的民法制度,以意思自治原则基础上的过错责任和自己责任为依托,根据当事人的具体行为确定其承担的民事责任,无论是数人实施的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行为还是间接侵权行为,都可以通过多数人侵权制度加以分析并得出结论,尽管很多情况下分析结论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的宗旨相吻合,但也存在着依据多数人侵权原理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本国实际国情和当前立法政策的情形。
2. 多数人侵权制度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
如果不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进行特别的规定,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上的多数人侵权制度来解决相关问题,不仅无法体现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属性,也会带来侵权认定的不确定性。例如,要通过共同侵权原理认定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相结合的情形,认定教唆、帮助行为及行为人主观过错就是核心问题,行为人生产和销售商品、提供经营场所或平台、生产特定部件等行为如何被认定为教唆或帮助,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或“明知”的判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困境[5]。不同的法院在认定时差异较大,甚至出现案情基本相同,但裁判结果截然相反的情况。立法欠缺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范围的界定、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间接侵权构成要件、没有对特定情况下是否构成侵权作出明确规定等问题都将带来司法裁判的困惑,当事人也会因此丧失行为预期,可能在冒险之后陷入侵权泥淖,抑或因为畏惧侵权而拒绝创新。司法审判的权威性受到质疑,间接侵权既保护专有权利又防止权利不适当扩张的制度功能也无法实现。因此,单纯依靠多数人侵权制度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知识产权间接侵权问题,通过立法对间接侵权进行规定是不可或缺的保护方式。
3. 多数人侵权制度无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单独存在的情形
关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存在着“从属说”和“独立说”之争。通过考察不同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我们发现知识产权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较为宽松的国家,多认为间接侵权从属于直接侵权而存在;而在知识产权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较为严格的国家,多认为间接侵权独立于直接侵权而存在。这两种不同的制度选择主要是基于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考量,从根本上讲,并无实质差别。以我国的专利侵权制度为例,我国的专利直接侵权必须满足“生产经营目的”这一要件,属于比较严格的限制条件,宜采取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独立说”作为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发生的实际情况看,间接侵权不仅可以独立于直接侵权而存在,有些情况下也意味着必须独立于直接侵权而存在。例如,A未经专利权人B许可,制造了B享有专利权的产品的主要部件,并且A明知该部件除了生产B的专利产品外,没有其他的用途,普通消费者C购买了该零部件组装了专利产品,用于个人生活目的。在我国,C的行为不构成专利侵权,无需承担侵权责任,并且不考虑C的主观心态如何,应当单独认定A构成间接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此种情形应属于单独侵权,没有多数人侵权制度的适用空间。但是,2014年7月3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公开征求意见稿)第25条却将此种情形认定为《侵权责任法》第9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该征求意见稿第25条规定:“明知有关产品系专门用于实施发明创造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物等,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将该产品提供给无权实施该专利的人或者依法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人实施,权利人主张该提供者的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的帮助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明知有关产品、方法可以用于实施发明创造,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通过提供图纸、传授技术方案等方式积极诱导无权实施该专利的人或者依法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人实施,权利人主张该诱导者的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的教唆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于“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人”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将间接侵权行为与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人的行为相结合的情形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是不正确的做法。
二、 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立法现状评析
我国现行立法及立法草案中存在着有关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规则,这些规则既有对国际条约的转化,也有对我国司法实践要求的回应。但各个单行法的具体情况不同,既有因为争议较大而影响规则法定化的情形,也有因为抓住修法时机而有力推进规则法定化的情形。已经法定化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规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除《商标法》以外,《著作权法》和《专利法》关于间接侵权的规定呈现零散状态,体系性和涵盖性较差。具体评析如下:
1. 著作权间接侵权的立法现状评析
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48条第(一)至(五)项、第(八)项都是对著作权直接侵权的规定,因为“著作权保护是一种赋权法保护路径,也即它要保护的是边界确定的权利”[6],第47条是对《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著作权专有权利的逻辑推演,在第10条已经确定了专有权利边界的情况下,立法上没有单独规定直接侵权情形的必要。第48条第(六)项和第(七)项是关于故意避开或破坏技术措施及删除和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规定,由于不属于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因此这两种行为属于间接侵权行为。在2014年6月9日国家版权局呈报国务院审议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现行《著作权法》第47条关于直接侵害著作权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取消,相比之下,著作权间接侵权的规则得到凸显。《著作权法》第72条专门规定了破坏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民事责任。《著作权法》第73条第四款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教唆或者帮助他人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应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第75条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基础上完善了计算机程序复制件持有人的间接侵权责任。从现行立法及草案送审稿的规定看,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著作权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目标导向”的认识正在深化,并逐渐形成共识。在《著作权法》规定专有权利的情况下,直接侵权的构成就不言自明,而间接侵权则没有明确的预设目标。因为“著作权法以平衡作品创作者利益、传播者利益和使用者利益为目的”[7],对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既要考虑足以保护专有权利,又要防止专有权利的不适当扩张和滥用,建立可预期的规则很有必要。现行立法和草案送审稿关于著作权间接侵权的规定还欠缺体系化,在侵权判断方面没有和多数人侵权制度形成有效的关联,教唆侵权和帮助侵权的情形不明显。
2. 专利间接侵权的立法现状评析
在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的过程中,引入间接侵权规则的呼声一度很高,但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专利间接侵权问题已经落入专利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十分敏感的灰色区域,有关规则的制定和适用略有不当,就会损害公众自由使用现有技术的权利。间接侵权的行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有关共同侵权的规定获得相应救济,在专利法中规定专利间接侵权的时机尚不成熟[8]。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最后的上报稿中删除了间接侵权的条款,第三次修改后的《专利法》也就未能规定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这种结果令人遗憾,因为这种质疑专利间接侵权规则化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观点存在着两个方面的认识误区:其一,认为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实际上,间接侵权制度是在保护专利权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结合点,间接侵权的司法实践已经积累了不少成熟的经验,可以将其规则化,通过法律规定实现制度化,通过设置间接侵权制度的适用条件,能够保证制度适用的正当性。其二,认为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可以被共同侵权制度所替代。这种混淆间接侵权制度与多数人侵权制度的观点显然是经不起考验的。由于通过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对专利权进行保护的客观需求一直存在,法院在无法从《专利法》获得裁判依据的情况下,会依据地方法院的内部指导意见(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等)进行论证和说理,加之《侵权责任法》中多数人侵权制度在逐案认定中的不确定性,司法裁判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3. 商标间接侵权的立法现状评析
尽管商标间接侵权在理论研究中受关注的程度不及著作权间接侵权和专利间接侵权,但2013年8月30日颁布的新《商标法》对商标间接侵权进行了规定,其规则的完善程度超越了现行《著作权法》和《专利法》。新《商标法》第57条将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一并规定,涵盖了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其中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是直接侵权的规定,第(四)项规定了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间接侵权行为,这种行为没有与商标直接侵权行为相结合,独立于直接侵权行为而存在,却对商标权人的权益危害极大,将这种情形认定为间接侵权确有必要。第(六)项规定了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两种间接侵犯商标权的情形,体现了间接侵权的典型特征,即实施了帮助行为,为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创造便利条件,从而使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相结合。这种规定使得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和多数人侵权制度形成了关联,值得肯定。当然,新《商标法》关于商标间接侵权的规定,在体系化和类型化方面尚有完善的空间。
三、 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立法完善路径
鉴于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立法的必要性和现有制度的不完备性,应当在修改知识产权单行法时,及时完善间接侵权制度。知识产权实践发展之快超过其他法律部门,因此,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也较其他法律部门频繁,这就为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尽管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在制度设计上差异较大,但对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而言,仍然有可以把握的共性内容。法律目的实现应当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合适的立法意图;二是规制技术能够在现实语境中实现其立法意图。”[9]应当重视立法技术的运用,从以下方面对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1. 在知识产权单行法中分别设立间接侵权规则
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知识产权单行法中分别设立间接侵权规则,既是知识产权单行立法的现状使然,又是由不同知识产权之间的差异性决定的[10]。例如,著作权权利形态的丰富性要超越专利权和商标权,互联网的融合性、全球性、交互性、技术性和无中心性[11]使得网络著作权侵权具有特殊性;专利间接侵权中的“技术性”因素如何考量;商标权人的“禁止权”范围要大于“专有权”[12]等。确立间接侵权规则,最重要的是确立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前文在阐述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多数人侵权的关系时并没有对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主要是因为不同情形下的间接侵权构成要件存在差异,例如,是否以直接侵权行为的实际发生为前提就足以导致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迥然不同。这就要求知识产权单行法在针对不同知识产权类型和不同侵权方式确定间接侵权时,应当对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进行清晰表达,尤其是独立存在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行为,因为没有直接侵权行为做支撑,缺少“教唆”或“帮助”行为,是否认定为侵权行为,更多依靠的是政策的考量,多数人侵权规则应当服从于政策考量的结果,这就依赖立法对不同行为类型作出不同的规定,尽量将政策考量的任务交给立法去完成。
2. 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进行类型化和体系化的规定
对间接侵害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等权利的侵权行为进行梳理并加以类型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将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行为进行类型化规定,能够为一类案件的处理提供依据。比较典型的著作权间接侵权类型包括提供侵权工具、设备等帮助行为;提供侵权场所或服务的帮助行为;直接侵权的预备行为;造成直接侵权损害后果扩大的行为;基于公共政策认定的其他间接侵权行为等。专利间接侵权的类型包括为他人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提供所需要的设备、工作场所等帮助;引诱他人购买相关零部件组装专利产品;告知他人利用相关产品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方法;明知某产品只能用于实施特定的专利,仍然提供给无权实施专利的第三人使用情形。商标间接侵权的类型包括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志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志;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侵权工具、场所、服务等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引诱经营者实施商标侵权行为;不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商标侵权行为扩大等情形。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应当重视间接侵权规则的体系化,将间接侵权规则集中和全面地规定,避免分散化和碎片化,发挥规则体系化的解释力。
3. 协调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与多数人侵权制度
间接侵权制度与多数人侵权制度的关系是间接侵权规则法定化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方面,相对于多数人侵权制度,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属于特定领域适用的规则,如果存在明确的间接侵权规则,《侵权责任法》中的多数人侵权规则就没有适用的必要。如果没有明确的间接侵权规则可以适用,可以运用多数人侵权制度对是否构成间接侵权作出认定,但是应当进行符合知识产权立法政策的评估。《侵权责任法》第9条关于“教唆和帮助侵权构成共同侵权”的规定可以为依附于直接侵权而存在的间接侵权认定提供依据,第12条关于“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规定可以用来认定独立存在的间接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对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认定而言,政策考量的分量绝不低于多数人侵权规则的运用,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规则的法定化,究其根本是对政策考量的法定化。在缺少相关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规则的情况下,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认识到多数人侵权制度在对行为进行政策考量方面的局限性,在运用多数人侵权制度认定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行为时,应当对结论是否符合间接侵权制度“既保护权利又防止权利保护范围不适当扩张”的宗旨进行判断,如果结论与宗旨不一致,应当对结论进行符合立法宗旨的修正,也就是说,在立法没有完成政策考量这一任务的情况下,司法应当不得已而为之。
总之,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与共同侵权乃至多数人侵权制度存在着关联,但多数人侵权制度在调整间接侵权行为时具有局限性,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具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制度功能,有必要将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规则法定化。应当以知识产权单行法的修改为契机,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进行类型化和体系化的规定,不断完善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
参考文献:
[1]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44.
[2] 王迁,王凌红. 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4.
[3] 王国柱,李建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研究[J]. 当代法学, 2013(1):13.
[4] 吴汉东.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场景——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知识产权协议》10周年[J]. 法学, 2012(2):3.
[5] 徐伟.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认定新诠——兼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论[J]. 法律科学, 2014(2):163.
[6] 张丹丹. 影视节目名称的法律保护路径探析[J]. 当代法学, 2015(1):132.
[7] 王国柱. 作品使用者权的价值回归与制度构建——对“著作权中心主义”的反思[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5(1):80.
[8] 于立彪. 专利间接侵权理论探析[J]. 中国专利代理, 2007(4):19-25.
[9] 孙良国. 论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主要规制技术[J]. 当代法学, 2014(4):79.
[10] Andrew L, Tiffany V. Ebay:Its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on the Doctrines of Secondary Trademark and Copyright Infringement[J]. 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aw, 2012,18(2):382.
[11] 毛牧然,乔磊,陈凡.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发展[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1):18-19.
[12] 刘春田. 知识产权法[M]. 4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278.
(责任编辑:王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