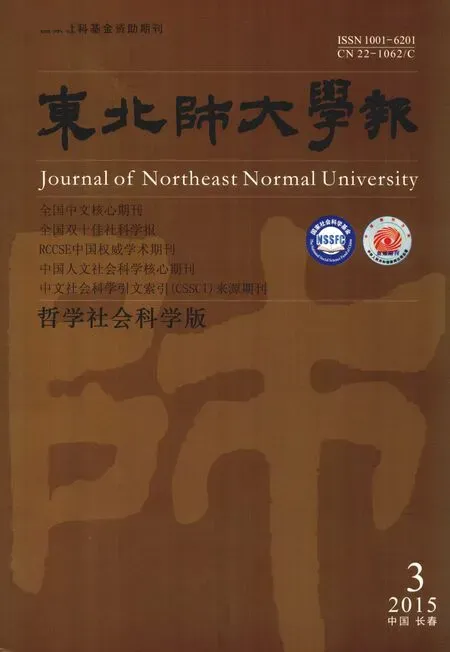民国初年(1916
—1918)北京的贫民救济活动——以《晨钟报》为视角
佟 宇,奚方圆
(1.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2.长春师范大学 校团委,吉林 长春 130031)
民国初年(1916
—1918)北京的贫民救济活动——以《晨钟报》为视角
佟宇1,2,奚方圆1
(1.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2.长春师范大学 校团委,吉林 长春 130031)
民国初年,北京贫民人数众多、生活困苦。为了改变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社会各界针对不同贫困、弱势群体发起了形式多样的救济活动,展现了官方和民间并举互助、救济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重视教育救济等救济特点。有力的财政支持、重视民间救济的作用、发挥新闻媒介的宣传和反馈功能是这一时期的济贫活动给我们的启示。
《晨钟报》;北京;贫民救济
《晨钟报》*《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团——进步党的机关报。本文所关注的是1916年8月15日—1918年9月24日,即该报从初创到遭封闭这一时间段的内容。于1916年8月15日创办,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具有深远影响的报纸。该报的创办宗旨是“商榷时政得失,宣究民群疾苦”。面对北京贫民比重大、人数多、生活状况极差的现实,办报人将目光投射到社会下层,关注常年生活在北京地区、收入微薄、穷困潦倒的民众,报道官方和民间对贫民的救济活动,反映贫民的生活状态。此外,该报还刊载办报人和社会有识之士对贫民表示关切、呼吁政府有所作为的文章和评论。以《晨钟报》为视角,可以洞见民初北京的贫民生活状况和救济活动的图景*学术界关于民国北京的贫民救济活动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者多将《晨钟报》作为重要的原始资料频繁引用,但以该报为视角来反映民初北京贫民生活和救济的仅有一篇。该篇论文为李小兰:《审视与批判:〈晨钟报〉视域中的民初社会》,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1年。。
一、民国初年北京的贫民状况
民初的北京尽管政治动荡,社会失序,但是依靠“首善之区”的特殊优势,工商业仍然获得了一定发展。在此背景下,几年间,北京吸引了大批的外来人口前来经商、供职、求学、谋生等。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因兵祸、灾害逃到北京乞食的灾民和难民,使北京人口规模尤其是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进一步加重了北京的城市负担。根据当时内务部的统计,当时北京的贫民主要有两类人,一种是从事车夫、劳力和仆役等活重、工资低的卑微职业者,占从业人员的23.09%。他们的收入微薄,但几乎是全家的生活来源;另一类属于社会边缘群体,包括乞丐、妓女、帮会成员[1]125。根据京师警察厅1916年的北京人口调查数据来看,北京地区约有130万人,贫困人口约有50万人[2],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28%,说明贫民人口总量已经相当大了。
贫民群体的生活十分困苦,许多人连温饱都很难保证。尤其是冬季,贫民无衣无食,甚是可怜。每天早晨在官方为济贫开办的六处粥厂排队领粥的人均不下千人[3]。身体相对好点的贫民靠着免费的稀粥和社会救济的简单衣物尚可维持过活,那些患病者和露宿街头者往往抵御不了饥寒交迫的打击而惨死街头[4]。很多贫民无法忍受穷苦的生活而选择自缢、跳河等自杀方式结束生命[5]。
举目皆是的贫困人口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市区中,到处游逛,这既与我们这个大国首都应该具有的美好形象相背离,更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抢劫、盗窃、斗殴、杀人之案每日不断。为了改善贫民的艰窘境遇,缓解社会压力,北京市府当局也在很大的范围内对贫民展开了救济的工作,如设立教养局、贫养院、贫民工厂、济良所、贫儿学校、贫民养病所等救济机构,秋冬季开办粥厂及发放棉衣等。但因贫民数量太大,加之各级财政困难,政府的救济能力有限,救济工作很难惠及所有贫民,有时甚至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大量的贫民还是得不到基本救助,继续挣扎在死亡线上。
二、救济对象和救济活动
面对贫民社会的穷苦现实,《晨钟报》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屡屡发出“人民生计难”的慨叹。在报上设专栏每日报道贫民人口的生活状况,呼唤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对贫民伸出援助之手。正是在报界的积极努力下,一个有重点、分层次的救助难民和贫民的社会运动在民初的北京展开了。
(一)对贫困妇女和贫困儿童的救济活动
1.贫困妇女
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救济活动当然会受到资金、时间、人力等多方面制约,必须有针对性地选择好优先照顾对象和照顾尺度,以保证其时效性和社会影响力。妇女和儿童在所有的平民社会中都是应该特殊关注的弱势群体,救济活动自然也要以这两个群体作为首选。民国建立后,妇女的政治地位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因女性就业环境改善相对小,所以家庭地位仍然处在弱势状态。与经济环境连在一起的医疗条件更是没有任何改善,许多妇女因生育孩子难产而失去生命。一般平民的情况是这样,那些贫民和难民妇女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为了让贫困妇女掌握谋生的技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参与救济的京师警察厅在内城贫民教养院内附设了妇女实习工厂,专门招收附近的贫苦妇女,前来工作,按其工作实绩发给薪水[6]。因此,很多妇女在改善经济条件的同时,也掌握了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实际能力。
为尽可能保证贫民妇女也能获得与其他阶层城市妇女同样的就医权,京师警察厅令卫生处在内外城设立贫民养病所数处[7],步军统领衙门在四郊地方各设立医院一处[8],专为贫苦者尤其是贫苦妇女就医提供便利。一些民间志士设施医馆,为贫困妇女施诊不收脉金,并且酌给药料[9]。一些医院将免费施诊券交与各区署,凡贫民妇女罹患疾病者即可到本区医院就诊[10]。妇女工厂和妇科医院的设立对于妇女缓解困境、解除病痛、重新树立起生活希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贫困儿童
虽然在总体数量上,北京的贫困儿童要比贫困妇女少得多,但因儿童在承受贫困的打击和压力上,比之妇女群体自然要弱得多,因此在救助工作上自然需要更大力度。北京的儿童救助具体实施了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增设育婴堂。北京地区被抛弃的婴孩和失养的孤儿孤女人数众多,官方和民间设有育婴堂、孤儿院和孤女院收养。这些收养机构的设立多是依靠民间力量的捐款。1917年5月,步军江统领和警察吴总监约集京师绅商劝募捐款,要设立育婴堂一处。在育婴堂成立一周年时,收养的婴儿已达数百名以上[11]。这些收养机构的持续运营仰赖绅商、慈善家的慷慨解囊,因此孤儿院、育婴堂每年都要开办纪念会,敬请他们参观、指导[12]。这既是对志士募捐的感谢,也是呼吁和倡导社会各界对孤儿孤女给予进一步关爱。
二是加强贫儿学校的建设。民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配合新式教育改革,注重强化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陆续建立了一批面向贫民子弟入学的社会教育学校、露天学校、补习学校和各种宣讲所。接着,北京政府于1914年2月19日公布了《半日学校规程》,规定“半日学校为幼年失学便于半日或夜间补学者设之”,招收12到15岁的学生;一般每周18学时,主要补习“国文、算术、体操、修身”等课程,修业三年[13]。京师警察厅首先设立贫儿半日学校且成绩显著,之后通饬各区署长广泛设立贫儿半日学校[14]。京兆尹则通饬所属各县知事设立贫儿学校并强迫入学[15]。入学贫儿无须交费,学校聘任学问优上、热心公益者做教员。至1918年6月中旬,官办的贫儿学校共有53所,先后入学的贫儿达到6 500余名[16]。就办学的数量来讲,这些贫儿学校的设立对于普及小学教育,增长民智是有很大益处的。大批贫困子弟陆续进入课堂,相应地减少了文盲人口。
1915年7月,教育部通过了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该会的宗旨是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17]。为补助学校教育,救济失学儿童,该会创办了露天学校,在京师学务局所定的学区,每区各设一处。6到14岁的男女儿童,“未经读书者,均可入席听讲”,“学费讲义费一概不收”[18]。学校的授课内容遵照教育部初等小学教则,授课时间为每周一或两次,每次两个小时[19]。每年深秋到第二年开春天气严寒,露天学校会改为有校舍的冬日学校继续开办。露天学校是在教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最大程度的推行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素质而办。露天学校吸纳了无法进入贫儿半日学校的6到12岁的失学儿童,与贫儿学校一同承担起贫儿教育救济的责任。
1917年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教育思潮流行开来,因为职业教育“收效之速罕与伦比,吾国游民众多,尤非注重职业教育不可。”[20]由露天学校和贫儿学校毕业的学生和未能接受到小学教育的贫儿还有机会进入到职业学校学习技艺。京师成立多所公立和私立的职业学校和工艺学校都愿意招收贫民子弟。游民习艺所是直隶于内务部,专管幼年游民的教养和不良少年的感化等事项,以获得有普通知识、谋生技能为宗旨。游民习艺所招收年龄在8到16岁的游民就学和习艺。游民习艺的年限为3年,初等小学为4年,高等小学为3年。为求术业有专攻,习艺所要求“游民习艺者,不兼就学,就学者不兼习艺”。游民习艺的内容有,染织、打带、印刷、刻字、毡物、铁器、木工、石工、制胰、缝纫、制帽、制鞋、抄纸等[21]。又如京师公立艺徒学校招收14到20岁的初等和高等小学毕业者,且免收学费[22]。一些学校在校内附设职业班或设立工艺传习所招收贫苦女生,无论识字与否,均到校授以相应技术,待毕业后自谋生活[23]。
官方的教育救济要依靠绅商的捐资。如若学校学款难以筹集,京师警察厅和市政公所再给予补助[24]。此时,民间助学、兴学的热情很高。很多县镇的绅士或其夫人眼见附近贫寒子弟甚多,捐资开办国民学校,召集贫寒子弟授以国民教育。有些则专门设立贫女学校,无论识字与否均可入学。可见,民间力量成为教育济贫的重要力量。
(二)对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活动
1.人力车夫
民初北京地区的人力车夫可谓是“填街塞巷”。无论是烈日暴晒还是“阴雨连绵”,人力车夫都得上街招呼客人,否则“妻儿老小不能举炊”。人力车夫为争抢客人互相殴打、被马车撞毙或急驰致死的新闻屡见不鲜。车夫们竭力赚钱生活,但仍无力阻止家庭惨剧的发生,例如一车夫的妻子因贫穷无路,携3个孩子投河[25]。人力车夫生活状态可见一斑。
1917年9月,京师警察厅修正了人力车规则。新规则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上18岁以下、身体羸弱、患传染病或恶疮、披发或不减发、盛暑严寒不戴帽者,裸体、衣服破不蔽体的车夫,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则停止营业[26]。该规则限定了车夫的年龄、健康状态和衣着,还考虑到酷暑和严寒天气对车夫的考验。这不仅对限定车夫人数和保持车夫气力有益,还利于保障乘客的安全和树立卫生和雅观的城市形象。然而一心求生计的车夫却屡屡违规,如幼童拉车、赤足拉车等,因此京师警察厅不得不反复重申规则,禁止各种违规行为。夏季,京师警察厅为避免车夫染患疾病和疾行猝死,特饬内外城各区署的岗警遇到急驰的车夫即行阻止[27]。此外,每年冬夏两季,警察厅会在各人力车夫休息所施茶,步军统领署会在各城门和街要之处施茶或暑汤[28]。
2.娼妓
民国年间,娼妓比前代更为发达和普遍。1917年至1918年间,北京政客云集,因此娼业达到最盛的时代,“民国六、七年间,北平公私娼当在万人以上。”[29]这些女子除卖身卖艺之外别无其他的谋生技能,如若脱离妓院,很难生存下去。因此,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救助。
北京的济良所于1906年由外城巡警总厅督同绅商办理,1913年由京师警察厅接管[30]。入所女性需满足以下条件:(1)被逼为娼的妇女;(2)被妓院老板虐待并失去人身自由的妓女;(3)愿意从良的妇女;(4)无处容身及无依无靠的妇女。然而,济良所的容量有限,只有在有空缺的时候才允许进入。所内设置了国文、算术、家政等课程和浅显的工艺,要求所女一律学习以增加知识。济良所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所女招配。济良所将所内达到结婚年龄的女性的照片、姓名和编号挂在济良所的相片陈列室,供前来领娶者挑选[31]。京师警察厅会在相关报刊上发布为济良所适婚女子招配的通告。为保证所女确实被娶作妻室且婚后可摆脱贫困的生活,警察厅要求领娶者须年在40岁以下且开具有三家铺保的证明[32]。符合条件者要在申请表上填写各项真实信息呈交济良所批示。济良所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致申请入所的人数有时会超过容量的两倍[33]。济良所为娼妓提供了脱离苦海的机会,又通过择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她们贫苦的命运。
3.穷困的八旗子弟
清代规定旗人不事生产,只能从政和当兵,完全仰赖朝廷的奉饷。清末国家财政日趋困难,清政府放宽对旗民就业的限制,允许旗民自由谋生,并要八旗子弟入实业学堂和手工业工厂学习实业来解决其生计问题[1]124。民国的成立宣告了八旗制度的崩溃,大批旗民失业、破产,沦为贫民。关于旗民因贫自缢、饿死、贫窘不堪衣食无着的报道屡见于报端。
专门救济旗民的机构是民国元年设立的八旗生计处。该处和各旗都统共同筹措八旗生计问题,如调查无靠的旗民,为救济事项做准备[34]。还与清皇室总长商议将抄没的贪赃官吏的财务变卖,所得资金开办八旗工厂[35]。救济旗民的钱款还来自于清室王公大臣的捐款,主要用于设立工艺厂让贫苦旗民入厂学习。然而,八旗生计处的救济工作并不积极,这引起了旗民长久以来的不满。1918年6月,旗民认为八旗生计处“自民国元年以来,每月虚弥经费,成绩毫无”,并纠合同志联名上书生计会,要求限期答复。事后三个月,没有得到答复的旗民再次联名呈请生计会给予日款开销的账目和筹备生计的成绩[36]。但八旗生计处始终没有给出答复。作为旗民仰赖的最重要的救济机构,八旗生计处不司其职,无疑加剧了旗民生活的困窘。
三、民国初年北京贫民救济活动的特点
通过《晨钟报》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出北京贫民救济有以下特点:
(一)官方和民间救济并举互助
辛亥革命之前,“北京的慈善救济事业很差,它几乎全部是由个人或者民间组织主持进行的。”民国后几乎全部由政府接管,大部分由京师警察厅主持。步军统领衙门、京兆尹公署、八旗生计筹办处和教育部设立的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等也是重要的官方救济机构。然而,困于中央财政拮据,用于救济的资金有限。官方救济之前均要按户调查贫民,只有被列为极贫和次贫的居民才能得到政府的救济金和救济粮。半日学校教育也因教育部财力不足,在实行后不久便延期开办和缩减规模,请求校外教育的帮助。因此,官方劝募民间捐款助济、助学是官方救济得以持久延续的必要手段。民间的施救主体有社会组织、绅商集体、慈善家和热心志士等。为借助民间力量广开救济之途,官方不限制民间救济的项目,但必须呈请京师学务局和京师警察厅批准。官方规范了民间救济机构的开办规则,给予其正确的指导,也要在私办的学校、工厂等缺乏资金时给予帮助。官方和民间的并举补助,使得救济能够长期延续。民间一般采取就近救济的原则,即士绅、志士在本区或县镇筹办救济活动,促进了救济力量深入到偏远的村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施救的不足。
(二)由传统的收养救济向教养救济过渡
传统的收养救济只能让贫民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不致冻饿而死。但会使贫民依赖救济,滋生懒惰和不劳而获的心理。传统救济种种弊端的显现、西方以教代养等新型救助思想的传入和实业救国思潮的流行使政府和社会各界转向提倡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的长效救助模式。清末,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这种办法。1906年,清政府设立了京师习艺所,“工场收取轻罪人犯,并酌收贫民,使作工艺。”[7]152民国后,官方酌情在所设立的教养局、贫养院等收养机构中设工厂。而后又在四郊和周围各县设工厂、习艺所,专门招收贫民,为其提供简单易学的手工工艺,使得贫民很快就能熟练掌握并投入正式生产。同时,民间具有救济性质的工厂纷纷开办,尤其注重招收贫苦妇女做工。让贫民学习技艺是将社会负担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对于重新树立贫民生活的信心和弥补官方救济的疏漏有益。
(三)重视教育救济
民国初年既注重基础教育又重视职业教育。官方和民间将这两种教育方式结合起来运用于社会教育,救济贫困儿童和少年。贫儿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或帮助父母劳动养家或是无人看管,流为盗贼。因此,对贫困的儿童、少年进行教育尤为重要。露天学校和贫儿学校主要是对6到15岁的贫儿进行小学初等教育,培养基本道德。艺徒学校、工艺学校和公立学校附设的职业科和传习所专为14到 20岁的贫困少年免费设立。教育救济是帮助贫儿摆脱贫困命运的重要途径。贫儿通过学习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谋生的能力。贫儿就学避免他们提前进入社会,这既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减小社会就业压力。
(四)救济水平和质量较低
民初北京的贫民救济处在传统救济方式向近代救济方式过渡的阶段。虽然官方和民间在采取各种方式救助贫民,但救济的水平和质量较低。首先,“教养”的救济方式仍不够普遍。民初北京所开办的救济机构在数量上呈现较大的救济力度*民国初,计有内城官立贫民教养院、游民习艺所、博济工厂、外城教养局、教养二局、首善贫民教养院、外城收养贫民所以及资善堂、公善养济院、兴善养济院、利济养济院、育善教养工厂、普善教养工厂、商水会教养工厂、崇善女养济院、普慈女工厂、掛甲屯成善教养局、龙泉寺孤儿院、北京贫儿院等。(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但“无教者盖居其半”[37]。这说明还有大量收入厂院的贫民未能得到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要在其余一半的救济厂院实现“有教”,显然还需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财力支持来完成。其次,官方救济工作效率低和无成绩的问题。1916年,京师警察厅特饬卫生处在内外左右四路选择地址筹办贫民养病所。然而两个月后,只有外右路的地址确定下来[38]。这样的工作效率不禁让人怀疑很多官方救济的项目会在拖延中不了了之。八旗生计会成立6年,每月虚靡经费,成绩毫无。面对八旗贫民的集体质问,生计会拖延数月,始终没有给出答复。本应作为贫民仰赖的最可靠的救济机构,却毫无工作成绩又不肯改正,这显然违背了救济贫民的目的。最后,对贫妇的救济力度仍然薄弱。1915年的冬季,在京师警察厅管辖的粥厂有超过100万人次的贫民前去领粥,其中幼孩占44.06%,女性占43.72%[39]。可见,女性和幼孩需要社会下大力度救助。但是,民初京师警察厅辖属的教养局、游民习艺所和贫儿半日学校等救助机构却明确规定只收男性。京师贫民教养院男女贫民均收养,但男性人数是女性的4—5倍[40]。可见,官方对贫妇救助力度很薄弱。屡屡出现在报纸中关于设立贫女学校、招收贫民妇女入工厂、习艺所学艺做工的新闻,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大量的贫妇需要救济。
四、民国初年北京贫民救济的启示
民国初年北京动荡的政局和拮据的财政无法为救济提供持久有力的政策和物质保障。在北京不依赖赈济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的贫困家庭占全市家庭的26%,仅能维持每日生活的家庭占全市家庭的47.34%[41]。尽管以京师警察厅为代表的官方部门在竭力救济贫民,但是由于资金缺乏,贫民无法都得到救济,因此贫民饿死、冻死、自杀的悲剧屡屡发生。近代自然灾害和兵祸不断,各地灾民涌入北京,政府为不使灾民流离失所,尽力妥善安置灾民。这无疑加大了北京救济贫民的难度,以致京师警察厅不得不取缔灾民来京,另请资金遣送灾民返回原籍[42]。可见,政府有力的财政支持才能保证救济工作持久、全面地进行。而国家统一安定,经济繁荣发展才能增加财政收入。
官方和民间大力开办学校为贫儿提供学习基础知识和实业技能的机会,但是贫儿相对于工厂商店里的学徒在就业上处于劣势[43]。解决这一问题,除大力发展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之外,就是要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对贫儿的职业教育救济,使贫儿真正能够学有所长,为社会所用,摆脱贫困的命运。
民初济贫活动中,民间力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关注不同的贫民群体。如北京社会实进会在夏令假期之际,设立3处露天学校,供贫寒子弟学习。又如妇女慈善会致力于救助广大痛苦挣扎的妇女。绅商、慈善家和热心志士纷纷捐资兴学、建厂、施医。民间力量在筹措资金和减轻官方救济压力方面有重要作用。因此,救济贫民、赈济灾民等方面,政府应重视和鼓励民间救助。
另外,新闻媒介在民初济贫活动中发挥督查、反馈民情和宣传、鼓励救济活动的作用。《晨钟报》如实地报道贫民的困窘境地和不幸遭遇,是对贫民走投无路的痛心和对政府施救能力的质问。它还宣传官方和民间的救济活动,及时发布学校招生、工厂招工、施粥舍衣地点、施医院开诊时间等救济信息。通过信息的发布和传递,一则使更多的贫民受惠,二则起到安抚贫民和为贫民树立生活希望的作用。此外,《晨钟报》对于民间救助的热心人士给予很高的赞扬。即使是普通市民,《晨钟报》也称其为“慈善家”,认为其行为“可以风矣”。这既是对民间助贫的赞扬和感谢,也是鼓励和倡导更多善心人士慷慨解囊。因此,新闻媒介是官方和民间救济活动的宣传者,也是贫民生活状况的反馈者,重视新闻媒介在济贫活动中的作用将有利于扩大受惠人群,亦有利于济贫活动及时调整和改正。
[1] 袁熹.北京城市发展史:近代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2] 北京最近之户口[N].晨钟报,1916-10-07(6).
[3] 贫民何多[N].晨钟报,1917-12-04(6).
[4] 冻死贫民八名[N].晨钟报,1918-01-06(6).
[5] 自缢身死汇志[N].晨钟报,1918-03-30(6).
[6] 附设妇女工厂[N].晨钟报,1918-03-15(6).
[7] 设立贫民养病所[N].晨钟报,1916-09-17(6).
[8] 四郊将设施医[N].晨钟报,1917-12-21(3).
[9] 集同志开设医馆[N].晨钟报,1916-11-10(5).
[10] 中央医院免费[N].晨钟报,1918-04-03(6).
[11] 育婴堂周年纪念[N].晨钟报,1918-06-04(6).
[12] 孤儿院定期开纪念会[N].晨钟报,1916-09-19(6).
[13] 教育部公布半日学校规程令[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547-584.
[14] 扩充贫儿学校[N].晨钟报,1916-08-25(5).
[15] 仿办贫儿学校[N].晨钟报,1916-08-31(5).
[16] 贫儿学校总数[N].晨钟报,1918-06-19(6).
[17] 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3卷[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812.
[18] 露天学校暂行规则[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3卷[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818.
[19] 北京通俗教育会实施露天教育简章[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3卷[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817.
[20] 通令赶办职业学校[N].晨钟报,1918-03-10(6).
[21] 游民习艺所章程[A].戴鸿映.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Z].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103-104.
[22] 艺徒学校招生[N].晨钟报,1918-02-10(6).
[23] 高等附设女工所[N].晨钟报,1918-06-12(6).
[24] 准予拨款补助小学[N].晨钟报,1916-11-20(5).
[25] 全家四口投河[N].晨钟报,1918-03-15(6).
[26] 修正车夫规则[N].晨钟报,1917-09-09(6).
[27] 禁止车夫急驰[N].晨钟报,1918-05-09(6).
[28] 区署施舍暑汤[N].晨钟报,1918-06-19(6).
[29]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上海:生活书店,1934:330.
[30] 蔡恂.北京警察沿革纪要[M].北京:北京民社,1944:54.
[31] 所女添设授课艺[N].晨钟报,1918-06-01(6).
[32] 招领济良所女[N].晨钟报,1918-04-02(6).
[33] [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M].陈愉秉,袁嘉,等,译.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278,289.
[34] 调查无靠之旗民[N].晨钟报,1916-10-13(6).
[35] 请赃款创办八旗工厂[N].晨钟报,1916-10-16(6).
[36] 将□质问生计会[N].晨钟报,1918-06-21(6).
[37] 内务部呈报扩充游民习艺所办理情形拟具章程请训示并批令(附单)[Z].政府公报,1915-12-22:13.
[38] 设贫民养病所[N].晨钟报,1916-11-07(5).
[39] 丁芮.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的妇女救助——以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为例[J].北京社会科学,2011(1):43.
[40] 贫养院贫民之统计[N].晨钟报,1916-10-24(5).
[41] 袁熹.北京近代百年生活变迁(1840—1949)[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16.
[42] 取缔难民来京[N].晨钟报,1917-11-16(6).
[43] 范源廉.说新教育之弊[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3卷[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051.
Poor Salvation of Peking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916—1918)——From the Perspective ofTheMorningBell
TONG Yu1,2,XI Fang-yuan1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2.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1,China)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in Peking had been suffering greatly from poverty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lower-class, all sectors of society organized relief activities in various forms aiming at different vulnerable group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se activities were mutual help of the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relief,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medies and tendency of the education relief. Storng financial support, the importance of unofficial relief and the function of news media are the valuable enlightment for today.
TheMorningBell; Peking; Poor Salvation
2014-11-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S071)。
佟宇(1979-),男,吉林兆南人,长春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奚方圆(1989-),女,吉林临江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F258
A
1001-6201(2015)03-0102-06
[责任编辑:王亚范]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