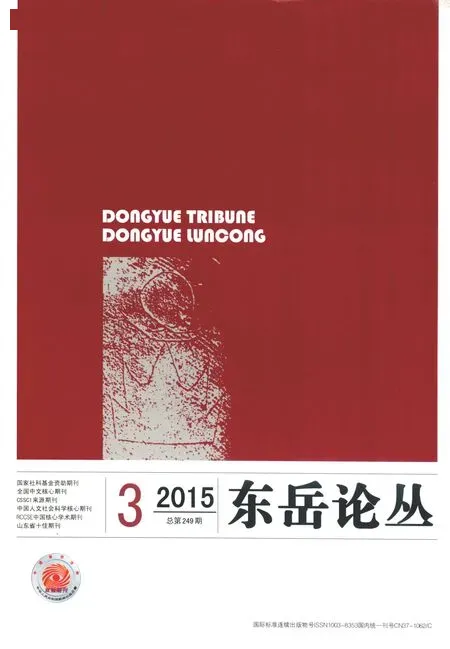人性与和平
——墨子和平思想的当代价值
傅永军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人性与和平
——墨子和平思想的当代价值
傅永军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先秦诸子学说中,墨子学说是与儒家学说并立而行的两大时代显学。我们今天仍不断地从墨子的思想中发现东方古老的和平智慧。墨子的和平思想与他的人性理论密切相关。墨子用人性恶解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必然性,而将人性善看作是和平的伦理学基础。人的善良本性唤起人的良知良能,使得人们之间“兼相爱,交相利”,遵行和平共处、友爱共利的行为规范,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友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尊重和互利的关系,实现永久和平。可见,墨子是从“所染”、 “兼爱”、“非攻”、“天志”等篇所阐述的道德哲学角度,演绎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国际交往伦理规范,与康德所奠定的国与国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法治规范相映生辉,同为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理想的普遍理性基础。
兼爱;非攻;人性;和平;交往伦理
东亚传统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和平思想。这些思想可以远远地追溯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核心文明发端的所谓“轴心时代”。在东亚,“轴心时代”大约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是中国学术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自周王室东迁以后,中国的学术中心转移至民间,继孔子、老子之后,涌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如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这批被称为“先秦诸子”的思想伟人皆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而他们的学说与思想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思想史上占据着后世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可谓后世诸思想学派的源发地。了解中国乃至东亚思想何以有今日之面貌,就不能不时常回溯先秦诸子的原创性思想。
先秦诸子学说中,墨子学说是与儒家学说并立而行的两大时代显学。我们今天仍不断地从墨子(公元前468 —公元前376)的思想中发现东方古老的和平智慧。墨子的和平思想涉猎方面颇为广泛,既可以从“天志”、“明鬼”等篇所阐述的形而上学角度,分析墨子述说的“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从而“兼而明之”①参见《墨子·天志上》,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9页。的大道,为不同政治共同体的和平共处提供哲学论证;又可以从“亲士”、“尚贤”、“尚同”等篇所阐述的社会政治哲学角度,析取出由德才兼备的干才治理国家,实行王道政治,消除恃强凌弱之霸道政治的具体举措,更可以立足于“所染”、“兼爱”、“非攻”等篇所阐述的道德哲学,从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演绎出国际交往的伦理规范,为世界的永久和平寻求普遍的理性根基。在这篇论文中,我无意全面阐述墨子的和平思想,我的目的仅仅在于,从人性与和平关系的角度,对墨子的和平思想进行道德哲学分析,发掘墨子和平思想的当代价值,以一斑窥全豹,同时就教于方家。
一、墨子对人性的解释
在人性论问题上,墨子坚持人性后天塑成说。在墨子看来,人性无所谓善或者恶,因为人性并不能被看作是人天生的自然“倾向”或者原初禀赋。必须超越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这样一种单级思维的限制,也必须超越人性善恶两元并立这样一种二元思维的限制,把人性理解为人之后天自我造成的性状,而人之获得善或者恶的性状,关键取决于人在与环境诸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自我选择。根据《墨子·所染》篇,墨子将人性的养成与染丝相比较,明确地表明,人性为素丝,本无善恶,其善恶全在所染*冯友兰指出:“墨子以人性为素丝,其善恶全在‘所染’。吾人固应以兼爱之道染人,使交相利而不交相害;然普通人民,所见甚近,不易使其皆有见于兼爱之利,‘交别’之害。”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取决于后天之所与。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人自身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善的环境诸因素(主要包括人与事)影响则养成善的本性,受恶的环境诸因素影响则养成恶的本性。墨子说: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
《墨子·七患》具体描述了人性善恶如何为环境所染成,墨子的论证如下: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墨子·七患》,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30页。
《墨子·所染》篇还举例说明,人所交朋友对人的本性品质养成的影响,墨子举出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他指出:
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下,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墨子·所染》,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页。
由此可见,人性塑成如丝之染色,必须十分谨慎(“必择所堪,必谨所堪”)。唯有以善良的本性(兼相爱)影响人,促使人们相互友爱而不相互加害(交相利而非交相害),才能远离造成恶的本性的环境和因素,培养出健全而善良的人性,生自爱爱人之心,求互惠公正之利,积极而主动地张扬人的价值与尊严。
然而,现实社会复杂诡秘,人在世上的生活难以预测,德性并不是总能抗衡物欲,因此,将墨子的人性塑成说具体落实到人的现实本性生成上,就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既存在造成人性善的环境及因素,也存在造成人性恶的环境及因素。人性趋于善与人性趋于恶,具有同样的理性根据。由此可以推定,墨子人性塑成说既承认了人性本恶的必然性,也承认了人性本善的必然性。墨子实际上是将人的本性理解成一种可以变化的品性,可以根据影响它的环境诸因素的不同做出与被影响因素直接关联的解释。教化不足,人性处于“自然状态”,人就会“染成”恶的本性。若有充足的人文德性教化,人脱离人性的自然状态而体现出人之为人应必须具备的德性表征,人就会被“染成”善的本性。明确地说,按照墨子的说法,若人受自私自利之心的蒙蔽,就会萌生恶的本性。若人以兼爱为本,涵养本心,就能将自私自利之小爱转化为兼善天下之大爱,达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6页。之崇高境界,善的人性熠熠发光。至于如何协调自然状态意义上理解的人的本性与理性化道德意义上理解的人的本性,墨子并没有给出解释而任由两者相对独立存在。墨子没有历史目的论思想,亦未提出历史进步主义主张,因此,他并没有将人的历史从理性角度理解为一个从自然状态走向自由状态及道德状态的历史,从而从理性角度将人的历史描述为善克服恶而走向至善的过程。就此而言,墨子只是把人性或善或恶看做是一个有经验依据的感性事实,分别对应利他的友爱伦理观和利己的自爱伦理观。两种不同的伦理态度具体落实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就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接受利己的自爱伦理观容易造成人之恶的本性,接受利他的友爱伦理观有利于养成人之善的本性,前者导致人人“相贼相害”的混乱世界,后者导致“友爱互利”的太平天下。由此可见,墨子的人性论是他治乱和平思想的伦理学基础。
二、和平的人性基础
墨子从人性角度解释天下大乱和天下大治两种现象的思想,主要见诸他的《非攻》篇和《兼爱》篇。按照我对《非攻》篇和《兼爱》篇的解读,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相关的问题意识。《非攻》篇抨击不正义的战争,其理论诉求是消极的。而《兼爱》篇则积极倡导友爱伦理学,探究实现人类和平状态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兼爱”中直接推出“非攻”*劳思光先生就坚持这种观点。劳先生指出,“盖人既应兼相爱,交相利,则自不能互为攻伐。” 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但不能从“非攻”中直接引申出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和国与国之间交往关系的“兼爱“原则,因为出于“自私自利”(最明显的就是,交战双方通过计算战争所造成自己收益与损失的比例,就可以决定是战还是和)的原因,人们也会做出在当下看来是最佳利益获取的选择。“兼爱”显然是超出利益计算的一种更高价值,而为人性自身的光辉所笼罩,人类只有受这种超出利益本能的社会性价值的支配,以“类”(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种”) 的视野彼此善意对待,才能造就基于人类社会亲情的友爱互利、和平共处。这种友爱互利、和平相处若超越个体意义而进入共同体层面,特别是进入政治共同体层面,就会造就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可见,《非攻》篇对战争的谴责不是墨子友爱伦理学的最终目标追求,《兼爱》篇所追求的“相亲相利”、天下太平目标才是墨子友爱伦理学能够产生出来的积极的理论后果。就此而言,“非攻”谴责战争的不仁不义,分析造成战争的原因(主要是伦理的角度),可以看作是“兼爱” 的前提。而“兼爱”则把“兼相爱、交相利”理解为结束战乱的根由,是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性保障,因而可以看作是“非攻”的根据。“非攻”和“兼爱”之间所存在的这样一种相互论证的循环诠释关系,为墨子从人性角度解释他的和平思想开辟了两条不同的路径:批判的路径和建构的路径。
批判的路径主要是从否定的角度为和平理想清扫地基。也就是说,《非攻》篇并没有直接阐述墨子的和平思想,而是通过对战争危害的现象描述,探寻战争发生的原因,指引出实现和平的道路。首先要指出的是,墨子对战争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他以自己强调友爱精神的伦理思想为尺度,将战争分为“诛无道”的正义征伐(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和“攻无罪”的侵略行为。正义的战争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消弭祸乱的善举。而非正义的战争,则是大攻小,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兼恶天下百姓,背仁负义,实为天下之大害。墨子所反对的就是这类背离人类相爱共利原则的战争。对于这类战争,墨子痛陈其有三不利(危害)。《非攻》下篇是这样论述的:
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力利人也博矣!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墨子·非攻中》,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 169页。
除此之外,在《非攻》中篇,墨子还特别指出了战争对黎民百姓的伤害,他说: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 157页。
战争对人民和国家造成的伤害不言而喻。既然如此,为什么世间仍战乱频发呢?墨子主要从伦理角度给出了解释。在他看来,天下之乱的根源就在于本恶的人性。那些掌握权势的王公大人,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列强私心固而失去善的本性,好利益而喜劫掠,兼相利而忘仁义,所以才动辄坚甲利兵,征伐劫掠,“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参见《墨子·非攻下》,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 168-169页。。结果,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不仁不义的“恶的关系”。在这种“恶的关系”笼罩下,“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墨子·兼爱上》,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0-121页。由此也可以反证,如若想消除战乱,“国家务夺侵凌,即语兼爱、非攻。”*《墨子·鲁问》,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9页。故此,墨子强调指出:
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兼爱中》,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3页。
然而,《非攻》阐述的“天下之治道”是消除战乱之道,这是进入更高的和平之天道的前奏,之后才是华彩的乐章——更为积极的人类生存的伦理状态即“兼相爱、交相利“的和平时代。这种更高的“治道”是由《兼爱》篇来诠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攻》篇为《兼爱》篇的诠证奠下了良好的基础。直白点说,当墨子将战争的根源联系于人性之恶时,在他那里,人性善与和平状态的联系就成为一个自明性的前提。墨子是把人性善当作自己的友爱伦理学以及伦理地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奠基性理念*人性如何驱恶成善是墨子诠证自己和平理想的关键一步。在《所染》篇中,墨子也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可惜的是,墨子对人性善的教化问题既没有给出一种形而上学证明,也没有从人类学角度给出一种经验证明,他只是提供了一种示例性说明:“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下,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见《墨子·所染》,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页)显然,从哲学角度看,墨子的论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对于说明问题依然具有一定的效力。本文的目标不是处理这个问题,因此对此问题就存而不论,有待专文论述。。由此,墨子对友爱和平理想的论证进入了建构的路径。
建构的路径旨在直接从墨子友爱伦理学的基本伦理理念出发,直接阐明实现人类和平的理性基础。承接前论,墨子是把人性善当作人类理性地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奠基性伦理理念,具有自明性特征。为了强化这个自明性前提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墨子在《天志》篇中为这种自明性理念提供了一个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我把墨子的人性善理念理解为他的友爱伦理学中的一个自明性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个被我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阐明”。在这个关于天及天道仁义的直接说明中,墨子的论证基于“天” 的绝对性。按照墨子的思维,作为绝对本身的天是不能也无需进行理性的质疑与讨论的。作为源始性的本体,以它为基础直接建立的原则、原则和规范具有自明性质,并因为这种自明性而获得使用的合法性。在笛卡尔“普遍怀疑”原则和康德“批判哲学”不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时代,虽然这种有独断意味的思维方式缺乏反思性,但并不缺少直接使用的自然合理性。某种意义上,这是东方传统思想重直观体悟特征之运思传统的一个典型表现。。墨子说:
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墨子·天志上》,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5页。
这就是说,循“兼相爱”而追求“兼相利”以实现天下大治是“天道” 的要求,天要求人们“爱人利人”,人们只有“顺天之意”,才能得到天的奖赏。天是有意志的,“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墨白也。”*《墨子·天志中》,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4页。可见,性本善的个体,接受天道的主宰,必须践行“兼爱“这种伦理法则。只有做到了友爱互利,人才能摆脱自然状态,成为理性的社会人。作为理性的社会人,“兼爱”唤起人的良知良能。善良的本性使得人们行事如“仁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4页。。这样,“圣王之道”可望成为现实。这将是一个万民欢愉、天下太平的温暖人间。这是墨子的理想,他本人做了如下描述:
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兼爱下》,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0页。
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方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6页。
不能简单地将墨子的这种基于伦理道德的和平主张看作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念。墨子实际上是把“人性善”所体现出来的“兼爱”原则当作实现人类和平理想的普遍伦理基础和行为规范,它上合天道,下是天恩泽万物公正不偏私的实际表现。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内部能够建立友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那么国与国之间只要本着同样的伦理精神也就能够建立起一种尊重和关爱的关系,用“兼相爱、交相利”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与争执,就能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实现和平共处的伦理路径。这显然是一种用伦理教化的方式达成政治上目标的问题解决方式,据此,我们可以把墨子根据友爱伦理学之“人性善”原则建构的人类和平状态称之为和平理想的伦理学模式,它的作用是为人世间的和平共处、友爱关怀提供一种伦理交往规则。
三、返本开新:国际交往伦理的建构
墨子以“兼爱”、”非攻“思想为主体所建构的和平思想,经过现代的新诠释,可以成为构筑当代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论。
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惠互利,共赢发展,是近现代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各国人民之间用血的代价所形成的基本共识,它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关心人类生存状况的哲学家们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政治理想。从古到今,东西方有许多哲学家都在自己的哲学活动中,探讨了人类和平问题,既提供出许多充满真知灼见的理论智慧,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实践智慧。远的不说,影响世界的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曾以自己不凡的智慧致力于人类永久和平理想的理论探索。1795年,年事已高的康德写作了《论永久和平——一个哲学策划》,表达了他渴望人类永远友爱共存的渴望。在这篇充满哲学家济世情怀的长文中,康德基于自己关于历史是人的本性由恶走向善的历史目的论思想,从主权国家角度探讨了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的途径*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个哲学策划》一文中,提出了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六条“临时条款”和三条“确定条款”。六条“临时条款”分别是:① “任何和约的缔结,如果是以为了一场未来的战争而秘密地保留物资来进行的,均不应当被视为和约的缔结。”②“任何独立自存的国家(大或小,在此都一样)均不能应当能够通过继承,交换,购买或者馈赠而被获取。”③“常备军应该逐渐地完全废除。”④“任何国家国债均不应当在涉及外部纠纷时举债。”⑤“任何国 家均不应当武力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宪政和政府。”⑥“任何国家在与另一个国家作战时,均不应当容许自己采取必然使得未来和平时的相互信任成为不可能的那些敌对行为,诸如雇佣刺客和放毒者,撕毁条约,在敌国煽动叛乱等。”三条“确定条款”分别是:①“每个国家的公民宪法应当是共和制的。”②“国际法权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一种联盟制度制上。”③“世界公民法权应当被限制在普遍友善的条件上。”这些条款表明康德在实践理性的政治运用方面,强调“一切政治必须臣服于法权”。参见中文版《康德全集》第八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366页。。十分巧合的是,康德也是基于人性的观点阐发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与墨子不同的是,康德是从人性恶的角度,阐述自己的和平思想。由于康德对人性采取一种悲观主义态度,而人的道德本性的实现基本上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完成,人性由恶迁善是在人类完成自己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历史的最终目的得以实现的,因此一个道德自觉的世界事实上仅是一个可能的世界。有鉴于此,康德认为,永久和平的基础不是德性的,而是法治的。尽管对于建立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道德力量不可缺少,但人类的永久和平只能法治地实现。换句话说,人类的永久和平是国与国之间订立并遵守普遍的国际法规范的结果*康德指出:“大自然是通过战争……来推动人们进行起初并不完美的种种尝试,最终达到理性即使没有那么多痛苦经历也会告诉人们的东西,那就是:摆脱野蛮人的那种无法则的状态进入一种各民族的联盟里,每个国家,哪怕是最小的国家,都不必靠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的法令,而只需靠联合的力量和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就可以指望自己的安全和权利了。”见康德:《什么是启蒙?——历史与哲学文集》,Jurgen Zbhbe 编辑出版,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in Cottingen,1994,,P.47.,因而总体上应该是在近代所形成的国际法格局下,以权利为基础的国际和平关系的法治表现,它指向一种国家和平关系的法治实现模式。*在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我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读到了黄裕生教授论述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文章,该文清晰而细致地分析了康德如何从法治角度,基于权利意识和契约意识论证人类永久和平理想的实现。读者若是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这篇文章。
对应于康德,墨子将和平建筑在人性善基础上。依据墨子的见解,人类的和平状态取决于人类能否改变对待生存世界和人的历史的功利态度,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不能从属于功利之目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应该道德地相互对待,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这种道德化的伦理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人的道德自觉。由此决定了墨子把人类和平的可能性建筑在伦理规范之上,诉求于一种国与国之间道德化交往的普遍伦理规范。因此,与康德不同,墨子所描绘的人类和平状态是以友爱(“兼相爱”)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国际和平关系的伦理表现,目的是建构规范国际关系的一种伦理实现模式*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主张墨子致力于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公共道德以实现普遍的社会关怀,他指出,“墨子不仅为有主义的打仗专家,且亦进而讲治国之道,侠士之团队中自有道德,墨子不仅实行其道德,且将此道德系统化、理论化,并欲使之普遍化,以为一般社会之公共的道德。”见冯友兰:《原儒墨》,载《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第325页。。
人类永久和平的实现既需要一种权利尊重的法治之基础,也需要一种友爱关怀的伦理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康德提供了永久和平的法治基础,而墨子的和平思想经由现代性转换,必能成为现代世界和平的伦理资源。就此而言,墨子和平思想的现代价值就在于,它为现代国际秩序下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一种睿智的交往伦理思想。
[责任编辑:杨晓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研究”(项目号:12FZX025)、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经典诠释与哲学创新”(项目号:IFYT1213)。
傅永军(1958-),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B224
A
1003-8353(2015)03-0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