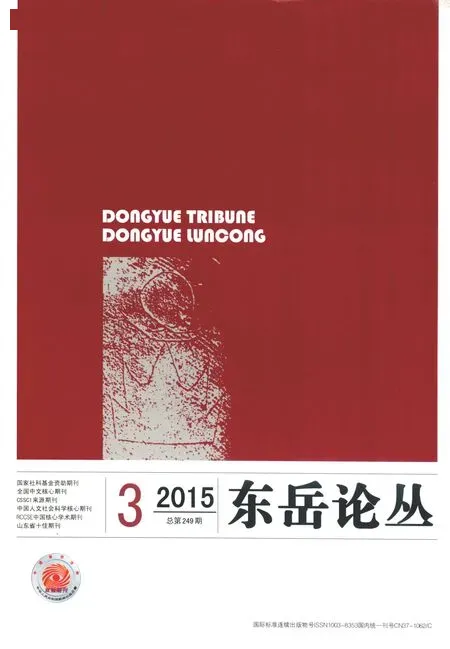沙汀讽刺小说中道德距离的展示与控制
马学永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1)
沙汀讽刺小说中道德距离的展示与控制
马学永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1)
讽刺文学是一种道德距离的展示,也是带有浓厚的道德惩罚意味的文学样式。但是如果道德距离过大必然会损害被讽刺对象的真实感,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也会缺乏沟通交流的可能性,被批判者会完全成为污名化叙事的对象。沙汀的讽刺小说也存在“污名化”的叙事特点,但是沙汀试图控制其讽刺小说中的道德距离,并尝试构建一种带有主体间性的讽刺小说。
沙汀;讽刺小说;道德距离;污名化叙事
一、沙汀讽刺小说中的道德距离与污名化叙事
讽刺文学是两种或多种道德观念的对立和呈现,是作者与讽刺对象之间道德距离感的展示。没有道德上的距离感,便无法形成讽刺,原因在于失去了道德考察的参考标准便无法发现讽刺的对象。就如对科举制度的描写而言,在不同道德范畴下的对比会产生不同的文学描述。处于元代种族制度下的王实甫等汉族知识分子倾向于科举文化制度,因而《西厢记》中的科举制度是获得个人幸福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的吴敬梓则通过《范进中举》中科举及第的故事,讽刺了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到了现代时期,在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和以立人为核心的现代性启蒙思想的道德参考体系下,鲁迅笔下的科举制度就彻底沦为了讽刺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可见,不同道德范畴之间的距离感会造成讽刺的产生。
沙汀对于讽刺小说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从沙汀自己对于讽刺小说的定位来看,他是带有明确的意图进入到小说创作中的,即要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表现出来。他已经意识到不同道德范畴直接冲突,并希望通过“讽刺”达到改良社会与人生的目的。因此,他是带有一定的道德距离进行文学叙事的,并且这种道德距离感的形成要早于文本的形成。换言之,作者在创作之前已经意识到自己和讽刺对象之间的道德距离,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对落后人物、反动人物进行道德上的惩戒。
道德距离感的产生和由此所引发讽刺现象是道德优劣性划分的结果,并且在讽刺形成的同时也便意味着道德惩罚的形成。这种道德惩罚的实施者为作者,因为作者在不同文化和道德的距离中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这种道德上的制高点赋予了作者充分的话语权,可以对讽刺对象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揭露、奚落并心安理得。因而,作者将讽刺之物吸入到自己的文本中的同时便设立了“排斥”的主题。作者用各种手段表现讽刺对象,但目的只是强化道德上的排斥感,使讽刺对象处于不合理的位置上。这种道德上的排斥感和距离感主要通过“污名化”叙事来达成。
“‘污名化叙事’,是指在小说叙事中叙述者从自己一方的‘正义’伦理出发,把对方‘污名’为‘敌人’,或‘非正义’的一方,以便给后来这些‘敌人’的被屠杀留下‘正义’的理由,让读者得到‘杀而快之’的美感。”*王成军:《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这种污名化比较典型地体现着主客体之间对立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在讽刺文学中尤为明显。在此叙事策略下,作者占据着伦理道德和文化上的制高点,拥有对事物进行解释和评价的权利,从自己的立场和观念出发对笔下的讽刺对象进行批判与讽刺。符合作者理念的人物和现实将不会以讽刺的笔调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只有那些有缺陷的、需要改善和改进的事物才能被讽刺。在作者和讽刺对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关系,作者是叙事的主体,而笔下的人物只是一种被解释、被描述、被批判的客体。
作为一种文学描述的手段,沙汀的讽刺小说同样具有污名化叙事策略。这种策略的体现主要集中在漫画式和夸张化的表现方式、标签式的外在称呼等讽刺手法的应用中。
沙汀在使用漫画式和夸张化的手法时虽然比较克制,这种表述方式在整个文本中所占比例也较少,但是它作为一种讽刺手法仍旧存在,并且具有明显的污名化特征。在《淘金记》中,沙汀对于彭尊三的“胖”的描述似乎是单纯的写实,强调的是一种细节的真实——彭尊三是一个胖子,但是作者对于这种“胖”过于强调,以至于他把眼光聚焦在一个地方并将其扩大,使得这个人物“胖”得出乎意料、令人难以想象,这便具有了漫画和夸张的色彩,这种漫画式的处理方式最终的结果便是彭尊三成为一个“为富不仁”式的人物。《李虾扒》中关于李虾扒的描述:“保长李虾扒有五十岁。又黑又瘦,神色冷峭,拖着两撇向下直垂的胡子。眼睛小而灵动,从不轻易正面看人。”寥寥几句话,沙汀便将这个人物性格中的狡猾之处刻画出来。按照常理来看,作品中出现人物的相貌往往并不怎么可靠,从相貌之中也难以发现人物性格中的真实成分,但是就讽刺小说而言,简单勾画并带有一定评价的漫画式描述方式是一种可靠叙述,它代表着作者对此人物的情感态度。在《人物小记》这篇小说中,沙汀对极度吝啬的主人公——“幺鸡”的刻画,充分发挥了漫画和夸张的特点。“当收到一块洋钱的时候,他总先用大指头去审查一下花边的匀称,然后拿两个指颠钳住适中的地方,放进挺直的胡须边吹一口,赶紧送到耳朵边去。”这种场景可能在沙汀的那个时代较为常见并不稀奇,但是沙汀却将这个动作所延续的时间大幅度地延伸,以至于在这个时间延伸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主人公动作里所潜藏的人物的吝啬和嗜钱的心理,从而达到作者对这个人物行为方式的道德评价的目的。戏谑感是这种讽刺手法带来最直观的效果,虽然人物有其可怜之处,但是这些动作中所体现出的可笑之处已经深深地将“幺鸡”这个人物进行了非常态化和另类的处理。可以说,作者借助人物性格中极度吝啬的特点,成功地运用漫画式的处理方式,“丑化”了这个人物形象并将其排除在正常人的行列之外。这便是夸张和漫画最为重要的污名化功能。
沙汀的讽刺小说虽然以“客观主义”、情感的节制和内敛为主要特征,但是在文本中仍然和其他讽刺小说一样存在着对人物外在标签式称呼这种手段。这种标签式的称呼往往以一种外号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如《还乡记》中的“徐烂狗”、“罗懒王”,《李虾扒》中的李虾扒,《丁跛公》中的“丁跛公”、“干黄鳝”,《淘金记》中的“林狗嘴”、“芥末公爷”、“气包大爷”、“白酱丹”,《毒针》中的“郭老娃”等等。标签式的外在称呼在讽刺小说中是一种带有强迫或强制意味的称呼,它代表着作者对这个人物“主体性”的评价。使用这种评价时作者无意于考虑或不需要考虑到笔下的人物能否认同这种评价,作为被塑造和被描写的对象只是被迫承担这种具有“污名化”特征的符号,并且在讽刺小说的文本中这种符号已经成为现实。从沙汀对于这种讽刺手段的运用来看,外在标签式的称呼在其文本中属于一种“可靠评论”*[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傅礼军译,西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因为作者对这些人物行为的描述印证了作者强加于这些人物身上的标签的合理性,如白酱丹下药的本领、林狗嘴骂人的本事、李虾扒的恶毒、徐烂狗的走狗行径等等。作为作者的可靠评论而存在的标签式称谓在文本中所引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作者的主体性地位下将一群人标上了非常明显的道德符号,并且此行为强化了读者对这些人物的认识,从而在话语中于作者和被讽刺对象之间划定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德界限,并获得了在这群人物面前的道德优势和对这些人物进行惩罚的权利。
在“污名化”叙事中,揭露丑行与人性中的弱点,将其视为“自我”的对立面,这便意味着讽刺对象失去了合理存在的理由,成为一种应该被改造和被革命的对象,从沙汀的讽刺小说中不难发现这种污名化的叙事所产生的后果,白酱丹、林狗嘴、李虾扒等人成为狡猾、恶毒的象征,郭老娃、何人种则成为一种愚昧、落后和不成熟的代表,幺鸡则意味着吝啬,《一个绅士的快乐》中的绅士则意味着好色和无耻,《老烟的故事》中的老烟的行为则呈现着懦弱、胆小与神经质,《代理县长》中的县长则代表着苟且者,龚老法团则意味着无所事事和一团和气等等。从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在揭露和“爆料”的过程中,道德惩罚的目的已经完成了,因为作者已经给他们贴上了种种污名化的标签。
二、沙汀讽刺小说对于“主体间性”的探索
沙汀往往以一种揶揄和戏谑的笔调对于讽刺对象身上的缺陷、行为上的弊端以及人性中的丑恶进行揭露和讽刺,在各种讽刺手法的运用下,描写对象的种种缺陷往往会被扩大和集中从而使其成为反面典型。 可以说,沙汀的讽刺小说如同其他的讽刺文学一样,无法摆脱道德上的距离感对于作品的影响,也无法摆脱污名化的叙事策略。但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些缺陷等同于人的全部,对于缺陷的揭示也没有成为否定整体和全部的理由,而是在描述被讽刺对象的缺陷时也兼顾到人物的其他方面。这种貌似多余的描写对于小说所追求的讽刺效果来说“确实有点铤而走险”*万书元:《火焰式的讽刺——论〈淘金记〉的讽刺艺术》,《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但是作者却将小说从单纯的批判和揭露转向了寻求改良社会和改善人生可能性的主题上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讽刺小说一贯的二元对立模式,并逐渐显露出主体间性的思维模式。
《一个秋天晚上》主要描述了三个人物:流娼筱桂芬、公所班长陈耀东、所丁谢开太。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流娼筱桂芬的过去和当下的遭遇,但这并不是故事的重心,而只是作者展开讽刺不可或缺的背景和契机。所丁谢开太则提供了一个道德参照系,在他对流娼筱桂芬的态度上体现出善良、厚道、老实等品质,这种朴素的道德品质为评价陈耀东的言行和心理提供了一个评价的标准,同样也代表着作者的道德立场。作者试图改变一个心怀不轨的人的邪恶念头是小说的叙事重心,中心人物便是公所班长陈耀东。作者对于陈耀东的描述在故事的开头部分是带有敌意和嘲讽意味的:“班长是个三十挨边的青年人,长条子,生满一手疥疮。小粮户的独子,除了红宝摊子,以及纸牌,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致;但又往往十赌九输。他来服役不到一年,目的在逃避壮丁。因为无聊,他的脑子里早就盘踞着一个邪恶念头,想糟蹋下筱桂芬。”从这种描述中不难发现作者对这种人物持有一种敌意,这种带有敌意的描述本身也就意味着作者与笔下的人物于道德上划清了界限。为了突出这种道德上的距离感,作者不免对这个人物进行讽刺和揶揄一番,甚至疥疮等生理上的缺陷也成了嘲讽的对象:“他受了同伴的传染,竟也忍不住呵欠起来,感觉到了困乏。而且经火一烤,他的疥疮更加痒了。而当一个人搔着疥疮的时候,任何幸福都很难引诱他的,倒是尽情抓它一通快活的多”。作者丝毫不回避这种人物身上的缺陷,并且以明显的笔调将其叙述出来。但是作者没有对这个人物进行一味的鞭挞和讽刺,作者的讽刺仅仅停留在讽刺对象罪恶念头发生的那一刻,并在后边的故事中阐释了一种道德转化的可能性。
当陈耀东将被扣押在荒地上遭受寒雨侵袭的筱桂芬带到乡公所里时是带有龌龊想法的,但是当筱桂芬进入到乡公所后事情发生了变化,陈耀东的邪念逐渐消失。这里面有三个阶段。一,筱桂芬在空场上时,陈耀东与筱桂芬处于一种想象的空间中。但是当筱桂芬被带入乡公所之后,以一种真面目出现在陈耀东面前,想象的空间被打破了。“他感觉得有点丧气,因为她那毛耸耸的头发,她那被雨水和眼泪冲没了的脂粉,他那有着一只尖削的鼻子和一张微瘪的嘴唇的黄脸,他那蜷缩着的单薄的身体,以及她的假笑,她的不大耐烦的口声,都在在引起他的不满。他多少是失望了,兴致开始慢慢降低下去。”二,当谢开太善意对待这个低贱的女人时,存有邪念的陈耀东被谢开太的举动所感染,“便是班长,也都忽然开朗,为了所丁的善良憨直而发笑了。”三,当筱桂芬陈述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时,陈耀东“从筱桂芬的谈话,想起他自己来了。他也出了好几次钱,但他现在还被逼起来当班长!他的父亲也不健康,母亲、老婆做不了多少事,目前又正在种小春,老头子真活该受罪了。”陈耀东在短暂的时间内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程:生理上的厌恶、精神上的感染、与推己及人的联想。在这三个过程中,作者虽然对于这个人物一直持有嘲讽的态度,但随着故事的进展,作者对于这个人物的描述逐渐现实化和常态化,而非简单地将其排斥在正常人的行列之外。
作者在对陈耀东的描述中将其现实化和常态化,这反映了作者试图拉近讽刺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距离感。他并不希望自己笔下的人物是一群集丑恶于一身、毫无人性的异类,而是试图将这些人物放入到真实的生活中来,既让人们看到这些人身上的缺陷,同时也让人们看到种种缺陷之外这些人物也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而这便提供了一种道德转换的可能。毕竟这些被讽刺之人和作者一样处于不能“止于至善”的现实中,谁也无法成为一种完全合乎道德的人,因此完全的排斥和丑化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沙汀的这篇小说中作者用陈耀东的故事便提供了这种道德转化的实例。虽然这种道德转化在其他的小说中并非完全形成,但是作者却在情感态度上拉近了自己和被讽刺人物之间的距离,他让我们看到一群喜剧性的人物,也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些人物的辛酸。
在沙汀的众多讽刺小说中,也存在着沙汀有意拉近讽刺小说文本中两极化的道德距离的现象。如《淘金记》中作者虽然对于白酱丹极尽讽刺之能事,但是作者仍然没有完全妖魔化这个人物。当白酱丹看到骨瘦如柴的女儿时,他也心生怜爱之情。在等级森严、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他也只是一个小角色。现实的困顿是促使他走向恶毒的一方面原因,但最终仍旧无法摆脱更大的黑暗对于他的侵扰。因而虽然这种人物可恶,但是在作者的笔下仍旧是一种可怜的人。《艺术干事》这篇文章虽然不乏对于那对年轻夫妇的嘲讽,但是从整个故事的走向来看,这些人物身上仍旧有闪亮的一面,他们仍旧是一群可以改造的人。在作品中作者也对他们投以怜悯之情。《人物小记》中的“幺鸡”,吝啬程度已超乎人的想象,仿佛是一个怪胎,但是作者却在现实中对于他的这种性格进行了解释。正是由于这种现实因素的衬托,这个人物身上的反常便有了合理的因素。《丁跛公》中的主要人物丁跛公是小说中的主要讽刺对象,但是作者却将其设置为一个小人物,并且认为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悲剧。
三、沙汀讽刺小说“主体间性”的意义
讽刺产生于道德上的距离感,但这种道德距离感应该具备一个适当的“度”,即在讽刺文学中道德上的距离感不能“差距”也不能“超距”*[瑞士]布洛:《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美学译文》第2辑。。“差距”指的是创作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过近,以至于在主客体之间难以形成明显的道德距离感。没有道德距离感容易造成读者对于讽刺对象道德上认同的错觉,讽刺小说的效果便无法出现。“超距”则意味着给人造成不真实、虚假和空洞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超距往往会造成道德上的冷漠感、叙事上的不理性和非人道的行为。
沙汀注重人物多面性的展示,而这便意味着作者对于讽刺有着严格的限制。可以说在沙汀的小说世界中,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加以讽刺的,只有如此方能彰显道德的力量,有些东西是不能进行讽刺的,而这则关乎小说的道德品质和知识分子言论的有效性。作者对于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有着严格的划分,因此出现在沙汀笔下的带有讽刺意味的人物大多具有平常人的色彩,而非是一群被作者彻底孤立和抛弃的人。就如李庆信所言,在沙汀的小说中充满“严峻苦涩的笑”*李庆信:《严峻苦涩的笑——论沙汀小说的讽刺艺术》,《当代文坛》,1985年第4期。,而这并非酣畅淋漓的大笑,这意味着在作者的道德观念中他无法割舍这群人。作者将自己的情感尤其是人道主义情怀倾注在现实中,而这现实同样包括了一群有缺陷的人们。这便无形之中削弱了污名化的叙事所带来的两极分化的现状,被讽刺对象被涵括在共同存在着的现实中无法剥离。因而,这种“严峻苦涩的笑”便具有了主体间性的思维模式。作者无法洒脱地将笔下的人物放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并对其进行毫无顾忌的批判和讽刺,而是将其描述为一种缺陷扩大化了的但又具有常人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的人。在这些人物身上不仅可以发现作者作为批判式知识分子所常有超越性的思想特征,更可以发现作者试图对这些人物进行精神和情感上的沟通和对话。
从讽刺效果而言,引起注意、促人反省,是讽刺文学的主要目的,因而作者往往将一些夸张、变形、漫画等手段应用于对讽刺对象的描写中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但这种手段应该适可而止,否则讽刺对象便会非人化,只是成为一种笑料,不能引起读者的反省和深思。而沙汀的小说在揭露人物缺陷的同时,能够将讽刺对象现实化和常态化,让读者在看到缺陷的同时能够将讽刺对象视为一个真实的人物,从而能够从讽刺对象身上看到存在于己的问题。
从讽刺文学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而言,讽刺文学更应严格控制“讽刺”背后的道德距离。作者持有道德上的优势从而能够将笔下人物的缺陷加以突出或变形,从这一点讲,讽刺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即作者无论是从何种道德立场出发、站在何种群体的立场上,他在进行文学叙事时总是设置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策略,作者自身与讽刺对象从属于不同的道德阵营中。在这种叙事结构中,由“主体性”的道德距离形成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是极其重要的特征。这种二元对立具有明显的道德排斥性,它在文本中隐含着这样的思维逻辑:“我”对于讽刺对象的描述是促进其死亡和消灭的,而“我”则应该站在死亡的对立面;“我”对于讽刺人物的描述是一种故意的惩罚,让其丑行陋习和思想上的缺陷公之于众,而行使这种权利的则是“我”。不能否定这种道德上的距离感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优越感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因为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文学本身便意味着一种现代性的趋向,文学作品中蕴含的道德诉求和伦理诉求体现着作者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对未来的良好愿望。但因为讽刺无法脱离“人”这个载体的特性,这便要求作者能够在主体性高扬的同时必须兼顾到主体间性。讽刺文学的创作者需要明确的是,讽刺文学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并非是惩罚而应该是改造,并且讽刺并非是一种针对偶然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叙述,它指向的是群体的弱点和人性中的缺陷。因而,当讽刺指向一个群体和人性中的弱点并希望将其改造时,就要求作者谨慎对待手中的惩罚的权利。他必须承认自己和笔下的人物都是“人”而非其他,惩罚的是“弱点”和“缺陷”而非“人”。他必须适当拉近文本中的道德距离感并兼顾到主体间性的问题,承认自己和这些讽刺对象同处于同一种现实中,都具有人的特征;并且承认自己是主体的同时,也承认讽刺对象是主体,两者虽然在道德上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批判、嘲讽甚至辱骂只是一方面,而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促人猛醒”的目的,否则一味地捉弄便沦为残忍、毫无节制的嘲笑便成了冷漠、以正义和道德的名义进行的批判便失去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以此观察沙汀的创作实践,不难发现沙汀在道德审判中的深沉思考。他希望自己的讽刺作品能够达到改良社会与人生的作用,因而对于讽刺对象持有强烈的厌恶感,并通过各种手段揭露了他们的丑行,从而在幕后履行了自己道德审判者的角色。但是他并非只是以惩罚为目的,也没有一味地捉弄和嘲笑,而是试图将讽刺对象视为具有多面性的整体和一群需要改造而非抛弃的人,在讽刺和批判的同时寻求精神沟通和道德转化的可能性。这种创作方式既保证了小说的讽刺效果,又保证了“文学是人学”的道德品格,同时又涉及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言论文化介入现实、改造现实的有效性的问题。在现代文学的讽刺文学范畴内,甚至是在心态失衡的现代文化思潮内,沙汀对于道德的谨慎态度是值得我们重新考察和深思的。
[责任编辑:曹振华]
马学永(1982—),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I207.42
A
1003-8353(2015)03-0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