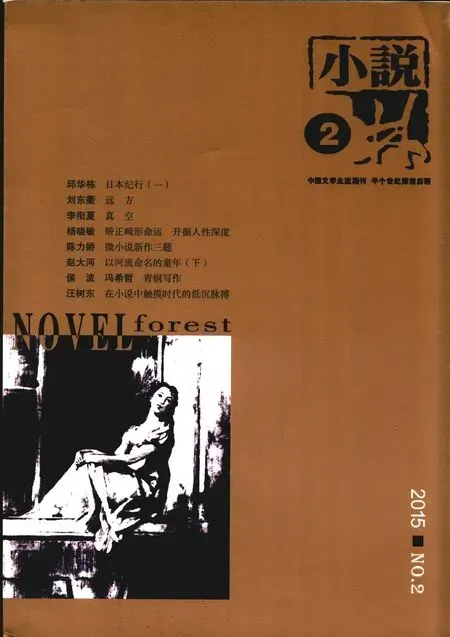小咖啡店靠窗子的餐桌
◎胡泓
小咖啡店靠窗子的餐桌
◎胡泓
在哈尔滨这个洋风盛行的城市里,这家小小的咖啡店可是不同寻常的。它除了有美味的咖啡和可口的俄罗斯传统饮食,还死心塌地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独有的一段俄侨的历史。
据国内外史学家考证,1903年7月1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后,就从世界各地向哈尔滨涌来几万外国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暗杀后,1923年那一年就有二十多万拥戴皇帝的俄国贵族上流社会和了不起的艺术家逃亡到了哈尔滨。据日本的哈尔滨研究学者的论著称:“哈尔滨在这一时期成了俄国沙皇贵族在全世界唯一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文化的实际所在地和避难地。”那么,这几十年当中,在哈尔滨生活的俄罗斯侨民一定有它独特的魅力和美妙的故事。正如当时欧洲对她的评价——东方小巴黎。
与中央大街交叉口的西头道街上,有一幢华丽的俄国人建造的两层楼。一楼稍稍靠里面的墙上、门旁、大窗子四周,爬满了枝繁叶茂的山葡萄藤。夏天一过,阔大茂密的叶子也遮不住缀满串串的黑色小葡萄。窗户和牌匾上的葡萄藤每年夏天都要修剪几次,以免被遮挡。窗前有十丛紫丁香树,也是由女店主与葡萄藤同时埋下的小树苗。转眼十几年了,两米多高的丁香树遮了大半个玻璃窗。当它们在四月底开出拥挤成团团束束紫色的小小十字花瓣时,这个城市也四处飘起又香甜又温情的香气了。
房子是1914年建的,粉刷着橘黄色的外墙。六年前对面建了一幢难看的高楼以后,在夏天只有早九点到十一点,下午一点半到四点,阳光才会照进大窗子里,落在靠窗的双人座的小桌子上和赭石色地面上。大厅里也变得明晃晃的到处闪动光辉。墙壁上和高高的天棚上反射到了柔和的光晕,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神圣感不禁会把过分的不以为然和放松收敛起来。室内按照三十年代的俄侨家里的大客厅风格陈设的。家具都是更早年代的。墙壁上挂满了1903年至1942年代在哈尔滨生活的俄国人的照片。另一面墙则是店主的母亲(也是俄国人)的朋友,九十一岁才故去的哈尔滨俄侨妮娜和她家人的照片。那架1889年的黑漆立式钢琴,是妮娜的妹妹——音乐教师年轻时的爱琴。她的一家人去了澳大利亚。钢琴现在依旧能弹出一百多年前的好声音。还有玻璃橱柜,里面用心地摆置着许多古老的餐具和茶具,看起来可不是普通瓷器。窗台及可能的地方都放着盆花,枝叶精神抖擞。总之,这间小咖啡店,从里到外再从外到里,都与四周的景象截然不同或者说格格不入。它很特别,很顽固,在这间小空间里精致地展示一个过去了的时代,虔诚地纪念着曾经在这个城市生活过的俄国侨民。
这个小咖啡店完全拿出了欧洲大城市中有名咖啡店的风度。因此,谁也学不像它。这里有个很客观的原因:据说拘谨有礼的女店主是个不平常的雕塑艺术家,正在名声大噪的时候退隐下来。她是1978年随母亲离开哈尔滨去了澳大利亚。丈夫去世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几年。等女儿结婚了,她就放心地回到故乡开了这么个小店。问她为什么一定要回哈尔滨呢?她回答说:“没什么理由,就是想回来,就回来了。”每年都回悉尼的家住两个月。女店主的母亲就是个在哈尔滨出生的俄国人。至于她的祖上是不是沙皇俄国的什么人物,就无从考证了。熟人都认为女店主血统高贵,这也不算是玩笑话。因为对待女店主这样的好人绝不会有人失礼取笑她,尊敬还来不及呢。这就是这家小店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既不做作,又清高又雍容华贵的原因了。
当然还要说明一下,小店的名气可不小。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客人,特意来吃上两个油煎包,喝上一盘红菜汤再品尝一杯咖啡的人可不算少。今天的网络时代,一切瞬间传遍地球各个角落。有客人在网上看到有这样一段描写,并且抄写在了放在钢琴盖上的客人留言簿里:

窗前的小桌子
“……上午和煦的阳光,像凡·高的画一样的阳光,柔情地紧紧贴在奶油黄色的墙壁上。像钟表的分针那样不易察觉地移动。这是一幢古老又美丽的俄国式的两层楼房,高大厚重又有华丽的雕塑。仅看这一隅,谁都会忘记自己是在哈尔滨。墙面爬满了青藤(其实是山葡萄藤,藤架粗壮,枝健叶阔)。推开古老沉重的绿色木格子门(其实门是新做的,刚十几年),突然入耳的是清脆欢跳的门铃声。坐在靠窗的双人桌旁,叫来一杯香热的摩卡,打开手中为享受这时光而带来的书,书名是《流动的盛宴》。
“阳光落在桌子上,我知道我的脸庞会被桌上的光涂上了一层圣洁。我爱这桌子上的阳光,爱从鼻子下面飘来的咖啡香气,在这间如同三十年代的俄国人的咖啡店里,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和忘记了俗尘四起的世界,恍惚中是在巴黎或圣彼得堡……”
没错,这像是一个青年女性写的。要表现超脱又注意细节。现在的女青年或大学生们,也许就一时心血来潮,受了一本书的蛊惑或者怎么说呢,都存在着那些太容易多变的情绪。每天都挣扎在堕落的追求金利又无法脱身离开的污泥浊水里,偶然想起离群索居一下,进到咖啡馆体味一次欧洲或从前的俄国侨民的咖啡与茶,也可能为了时尚中的某种心境吧。细心的店主的确看到过留言簿里有前面那么一段描写。她情绪一闪,产生出了一阵冷风似的为他人的惋惜。她希望她的这间小店给更多喜欢它的人以更多的温情。在另一种立场上说,这个小店又是一家哈尔滨“俄侨纪念馆”(这也是店主自己做的一块牌子)。在1960年前后俄国人都被驱赶似的离开这座城市。那时中苏两个政府如仇敌一般。自然,在哈尔滨的俄国人侨民只有提着简单的行李赶紧滚蛋。这些人,实实在在可以这么说,他们是俄罗斯帝国历史上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一漂贵族。众多的高官显贵,上流社会人士,还有一大批优秀的流亡艺术家们。这些人不是苏联公民,因为他们是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幸免于被新政权屠杀而逃亡到这里的俄国人。女店主的曾外婆就是几十万逃亡到哈尔滨“难民”中的一家人。她只说自己是俄罗斯人而绝不承认是苏联人。

窗前丁香树
再回来说这小咖啡店。也许是网上那一段的描述实在感人,这张靠窗子的桌子的确有很多人喜欢它。看得出来有时候急急忙忙闯进来的男人或女人都是为了这张桌子而来。当她推开门扭过头这一刻,看见这张桌子空着,就会快步滑到它跟前拉开椅子立即坐下,露出庆幸的小小喜悦。如果扭头看见了这张桌上已经有主落座了,手就会慢慢地松开了门拉手,脸上显出失落和泄气的神色。只好在别处选个位置,拿出书,要杯咖啡。不论在哪个位置,只要闻到了咖啡的香味,人们心情都是愉快的。再读上十几页书,这段时光可真是再好不过了。在这间与世隔绝般的1930年氛围的大厅里,还弥漫着面包的香味,奶油和草莓甜酱的香味。“叮铃铃铃……”绿色沉重又高大的格子木门被推开,有人进来了。“叮铃铃铃……”门又被拉开,有人出去了。铃声脆脆的,也提醒人们抬起眼睛轻松地看看窗外的风光和室内四周。
刚刚五月初的一天早上,天空虽然晴朗,可街道四周都像是覆盖了灰尘一般。树上的枝子已经鼓出细小的芽苞,又小又干,像快要枯掉了。店员们刚到店里就开始用塑胶管子把清水洒在地面上,喷在树上、葡萄藤上,把布满一夜灰尘的大玻璃也冲刷干净了。接着开始整理室内。拿出去桌单抖掉上面的面包屑,加满瓶罐里的糖、盐、胡椒。擦干净所有银器,浇好盆花水和换好鲜花瓶子里的水。这时,会有人打开CD播放机,播放出合适的音量。所有的曲子都是店主从国外亲自选的,她对音乐可不是一般程度的理解。从原版CD上刻录下的音乐,音色完全够这个小咖啡店享受的。

店内风景
这样的小店,一个收款员兼咖啡师,一个厨师,一个店员。店主也就是老板,也和店员一样,哪儿忙她就在哪儿。这点的确和其他餐厅的老板不大一样。她做得最多的是擦地做清洁卫生这类的事,她把卫生间里摆上小瓶子鲜花,布置得又整洁又雅致香喷喷的。客人们也不知道这个个子不高、温柔谦逊的中年女人是谁。现在她去市场买菜了,也快回来了。三个人都在做着各自熟悉的工作,准备迎接客人。绿色高大厚重的对开木门,每扇门的上半截有八个方格子玻璃,阳光把所有狭窄的菱形光斜着投在褐色瓷砖地面上,形成了四条连续的白光线段。一大块由外面某个神秘地方反射进来的光,强度较弱投在了墙上,这块亮光也粘在进小厨房的门口上方用水泥抹出来又描上色彩的玫瑰花和叶子上,使人想起阳光照耀的玫瑰花廊架。随后不久,一窄条明晃晃的上午阳光斜着划在了那张惹人喜爱的小方桌上。还不知道它等来什么样的人坐在跟前。桌上刚换上了碎花满布的白地桌单,擦亮了不锈钢小托盘和里面晶莹可爱的盐瓶胡椒瓶和糖瓶。店员都在默契专注地忙于自己手头的活儿。在这个安静的时候,门铃的一声响就很令人心惊。通常这个时候还不进来客人。也许是送广告宣传杂志或报纸吧。不是,从推开的门背后慢吞吞地侧身进来一个二十几岁模样的姑娘。她向大厅粗略地看了一遍,多少有点旁若无人地向右一转脸,立刻从眼睛里露出好看的喜悦神色。径直向那张有了宽宽一条阳光的桌子走去。女店员向她问好并送上了菜单。她独自翻看,紧绷着脸颊,身体略略前倾坐得很直。和许多人那样,要特意摆出清高傲慢的样子。可有的人就绷不了多一会儿,刚开始还像那么回事,用不了多久就散架子了。其实这也不必多有指责。这个女孩子开始就对自己的样子很没自信。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做着这种姿势和表情,她是第一次故意要这么做的。她坐在这样的一家令人紧张恐慌不知所措的咖啡店里,第一次走进这种具有某种精神威慑力的餐厅,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平静不下来的慌乱,又要做出老练和很适应的样子。她的衣服除了满是皱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点。肩后背着一只土黄色脏糊糊的背包。裤子和鞋也都没有什么个性。还有乱蓬蓬的头发和没有洗过的脸,加上沉重没有光泽的眼皮和不能给人留下些好记忆的眼睛和面孔。她衣着不整,而且肯定是多日没洗过衣服。作为这样年轻的人的确邋遢。可以断定:她是乘火车或长途汽车,经过一段难耐的长时间旅途直接来到这里的。尽管是早上九点半钟,她的脸上混合着疲倦困乏和新鲜的四周所带给她的兴奋和趣意。她理所当然地坐在了斜划过一道明亮耀眼阳光的那张令人留恋的桌旁。她总是认为自己受到了注视,动作上表现出了缺少应有的自然流畅。而且,她还要努力拿住一种架子,她当然有理由想象把自己提到比店员还要高些的层次上。在我们的四周这是一个普遍的就餐者的消费心态。当下形成了这么一种社会风气竟被当作时尚。很难看到有客人对店员恭敬有礼,尊重自谦。其实就是花些钱吃顿饭。花钱的交换条件是走进餐厅,坐在桌子旁,等待店员把所点的吃食送来也就为止了。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通常花了点钱就要当一回大老爷以至上帝。这些男人女人神气阔现大声喝唤:“服务员!”“把牙签拿来!”“再拿一根来!”就是吃上四元钱的两个包子,也要声色俱厉地支使下人般地喝道:
“把酱油拿来!”
“酱油在您身后的桌上。”服务员收拾着碗碟,边回应。
“你给我送来,你凭什么让我去拿?”这种事在餐厅,特别是一些普通的小餐馆,是平常事,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都是些底层人,也难得有机会摆摆威风。在中国就是这样。而一般来西餐厅的人都还规矩,偶尔也有张牙舞爪、吹吹呼呼不可一世的。这家小咖啡店,进来的人还都很注意自己的举止言行。他们说话声音很小,与店员说话也能放下架子,表现出屈尊俯就,常常也能和颜悦色甚至有笑容。因为这是一家有名气的小店,又有特别的俄侨历史背景。还有从外到里的氛围和欧洲的咖啡馆一样,气质优雅的女店主又总是彬彬有礼,待人谦恭和气热心容忍,从不露不悦之色。客人心里有一种尊重,自然就安静多了。毕竟有那么一些人也真是想要有一种文明社会正常的好气氛。那么说到这个姑娘,她做的可真不过分。只是在眼皮掀上去看店员的一瞬间,或者把腰靠在椅背上,双肘支在桌沿,手指蘸着舌尖过分用力翻动菜单的表情上,可以隐约看出她沾了一点点前面说的那种心态和风气。但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去想它。也可以原谅她仅仅带着那么一点点社会上的灰尘。因为她很安静,语音也极弱小,店员没听清楚还要再问她一次。再次说出来的语音,仍然语弱气虚。也不能再怪这姑娘了,现实的社会中下等心态像流溢四面八方的病毒,太臭太多。人们只要有机会就想要毫不顾忌地凌驾于别人之上(当然遇到另一种机会人们又像下贱的奴才不计丑态)。病毒怎么可能不落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姑娘身上呢?她也会感冒。但是她只是小小的沾了一点儿病毒。她其实很紧张,所以声音很弱。人应该有畏惧心,一定场合里畏惧心是一种涵养。她第四遍说过之后,店员才听懂是要“摩卡”咖啡加牛奶。可是姑娘已经临近最后一口勇气了。店员当然像对待每天众多的顾客一样,也不会去多想。转身就到后面的小厨房把手写单子交给咖啡师兼收银员。然后等着把做好的咖啡放在托盘里送给顾客。店员把小勺子放在椭圆形的白瓷碟子边缘,鼻子吸着早上第一杯咖啡的香味,觉得一阵恬静。特别是正播放的这首曲子,是一首英国的老爵士曲,英国一代大牌爵士乐歌手正唱着:“……上午的阳光,照在我窗子外的小杉树上,你从窗前走过,还是那件旧衣裳……”
店员把碟子和上面的一杯咖啡放在顾客的面前,又仔细地摆到最适合的位置。再把精巧的小玻璃奶盅放在咖啡杯左手边,里面是半下浓牛奶。糖瓶就在桌子里侧,半圆的镜面不锈钢瓶盖正把一个极亮的光点反射在你的眼睛里,只要你看它,那个强光点就像电弧光那样刺你的瞳孔。接下来,这个姑娘一开始就把她想象的整个喝咖啡的浪漫优雅给搞砸了,真是搞砸了。

店外风景
她让人所看到的实在是不忍目睹。最初,这个姑娘从挂在椅子背上的背包里抽出一本书放在桌子上咖啡杯的旁边,她的手油腻腻的。她真应该先去化妆间洗洗手再擦擦脸,然后坐下等咖啡。明摆着她是一个偏远的农村女孩子。开始看像是个学生,然而更像是偏远山村的初中教师(我们暂且认为她是初中的老师更合适。那股子执著劲,她实在是太像老师)。指甲早几天就该剪了。每个指甲前端都有一条弯曲的黑边。她好像两天没洗脸了,耳朵后面和脖子上有一层不均匀浅色的污渍。仔细看看,她整个人长得挺瘦,皮肤灰黑色。两侧的颧骨稍稍突出,也没有红晕。眼睛很普通,眉毛很淡。这是第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女孩子,十几年来这家小店里从未进来过这般邋遢的青年女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不仅要一杯摩卡咖啡,还摆在桌上一本书,一小盅牛奶。她只是不在意地瞥了一眼牛奶却连碰也不碰它。她用明显不清洁的手,从咖啡碟上捏起了晶亮亮,形状乖巧秀丽的半搪瓷柄压花银色小糖匙。她也要像别人那样从水晶糖罐里舀出一小匙糖,顺着咖啡杯边缘绕一周,把又细又白的砂糖撒进杯子里。不,她搞砸了。她把漂亮的小匙子直接伸进了咖啡里,连一两圈也没绕就舀出了那么浅浅的仅仅几滴泪水一般多的摩卡,送进嘴唇之间立刻紧紧抿起了嘴唇,脸色变得奇怪像是要哭出来。接下来,这个姑娘打开了书。翻到目录那页看了一小会儿,就翻到正文,开始读书了。女店员依旧背着身忙碌自己每天必做的工作,好在并没注意到她的所有举动。姑娘仍旧用可爱的小匙舀起那么少的一匙咖啡含进嘴里,把炒糊了豆粒般的苦味不情愿地咽下喉咙。她急速地瞭起眼睛向四周扫了一眼,目光胆怯又害羞。刚才还有一点小小的超脱感,微弱得像一颗被冷风抽得紧抓住蜡烛绒芯闪动的小火星。就是这么小小的高傲的虚荣心也一下子熄灭掉了,变成了一缕细微白烟,那么快,那么彻底。桌上的阳光正是通亮反光的时刻,半张桌子,斜着像对角线那样,半边暗半边耀眼。然而反射映照在姑娘的脸上的光晕,却一点不美妙,毫无诗意,没有任何想象力。因为她的脸色很糟,像是在孤岛上遭到了幽禁。仿佛那阳光是从一米乘以两米的牢墙上方的小洞口里透过来的,她烦这个和她没任何关系的强光,这个让她出丑的光芒。她没洗过的面孔,稍稍突出像新石器蒙古人的颧骨,粗糙的灰色皮肤,黑边的指甲。这些,在这公平又千百万年如一不变的阳光中,在桌布上反射的光晕中,不仅变丑,而且表情渐渐开始变得无助、惊慌。这时,门铃响起来,姑娘立刻抬起头。女店主推开门走了进来,她一眼就看见了这屋子里唯一的顾客。她正好看见姑娘用小糖匙舀出咖啡送进嘴里,女店主向客人眯起眼睛微笑着问早安。见顾客只是看了她一眼而别无表示,便带着微笑走进后面的吧台和小厨房去了。她知道一定不要对她喝咖啡的方式表现出一星半点惊异,更不能被对方察觉。她步伐轻松和店员们愉快地打招呼,减少这个姑娘对外界的不适感。她想让姑娘轻松自若。咖啡怎么喝都行,当然可以用糖匙喝。也可以用大匙子更可以用吸管。这都没什么,都没任何关系。只要姑娘不察觉,只要你知道这里的店员什么也没在意什么也没看到,只要你愉快地读书,就着咖啡。你开心,你对整个世界的冷言碎语都听不见就行!本来对一个人来说,她可以看不见任何人,听不见任何声音,这全由你自己做主。再说谁都有第一次。
“只要你能够开心就好,不要在意别人。”女店主默默重复着。
这时候,姑娘摆了一下手,叫服务员。她的声音很弱很不容易听到。
她要付款了。她一共只咽下了四小匙咖啡,从上衣口袋里她抓出了十八元钱,两张五元,八张一元的,纸币揉在一起。很皱,很黏,很值钱,又十分可惜。
收款员伸手接了她的钱,两张五元,八张一元。平平常常,没有什么不同。收了钱,回应了一句“谢谢”。完了。姑娘把书合起来快速地塞进背包里。拉上拉锁时又往里推了一下子。看得出来她还是在那种在被人注视的心态下做着各种动作。她要快快逃离这里!她尽量想把背包整得平整些,把衣服向地下的方向拍打几下,把尘屑拍打到地上,只顾衣服干净。女店主看到了这些,这是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的举动。姑娘不会想到这种动作是给别人造成了不便或困扰。其实能有什么东西掉落在地上呢,每个人都会带进来浮灰。她做这个举动是说明她爱清洁,是个文明的爱干净的人。反过来却表示出从未被察觉的自私和不善于考虑对别人有什么弊端。没错,人人都会这么做,在飞机上也一样。进过餐,把掉落在身上的东西掸拂在机舱干净的地毯上。没人觉得不对。这个坐在阳光洒满餐桌旁的女孩子当然没有什么不安,没有多想。店主全都看到了,她发自内心地原谅这个姑娘。第一眼看见她就要满心善意地维护这个勇敢的姑娘。她想象得出来,这个姑娘平时根本没有这么细心清理自己的习惯或者时间。她是在时时作祟的被注视的错觉下,自然就做出了这种只清理自己,不顾周围环境的举动。这不该怪她,一点也不要责怪她。她很快整理好自己的行装背在了肩上。大步走到门前,又在伸出手拉门把手的时候不合时宜地掂了两下肩后的背包。门铃“叮铃铃铃”地响了一串脆脆的声音。她又推开外面的门,然后完全走出了这间小咖啡店。女店主在她站起来的时候,想替她弄平扭了劲的背包带,但是她放弃了这个打算。女店主看见满满的咖啡如同没动过一样,她唐突地伸出手帮这么个小忙,反而更让姑娘心中不坦然。姑娘是要拿出那么一个喝咖啡老手的派头来,可是她不是老手也没办法做好。看得出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尝了如此苦涩难咽的汤水。她万没料到人们在电影、电视、书籍、杂志上描写的咖啡……那种特别香味的浓咖啡,那种普通农民从未想象过,从未沾过一滴的美味,喝起来就变得又高贵优雅又时尚超脱。喝咖啡的人就不是不喝咖啡的人。喝咖啡的人是一种艺术人、文明人、高贵人、时尚人、洋气人,有上等品位的人。一个高级层次的人,走起路来可以仰起头,有一种特别的风雅派头,随时都可以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尖叫道:啊,真想找个地方坐下喝杯咖啡呀!
喝咖啡可很不一般。而且,有时间的话一定喝杯香热的咖啡,读上几页名著。
这个衣着脏旧不整的姑娘,怀着什么样的想象从大老远的地方乘车来到哈尔滨,就为了走进这间小咖啡馆呢?她背着一个双肩背的行囊,做好了全部准备当中最重要的准备,借来一本应该是很潮流的书装进了行囊里,决心来这张小桌前坐一个上午,喝一杯所谓的香得妙不可言的摩卡,边借着神圣的光晕读书。原来她喝不下那苦涩的浓汤。书虽然双手捧在眼前,实际上连一个字都没读进去。
一个遥远农村来的女孩子,心里总在窜动着一个向往,打算让自己向另一个生活情景中迈去一步,却没迈出去反而绊了一跤。还有那些皱巴巴数了几遍卷在一起的黏糊糊的纸币,都是为了今天上午坐在阳光下临窗的桌上,喝着咖啡,读上几页书。
现在,一切都终结了,结束了,完了,再见了。
女店主站在她坐过的椅子旁,一只手按在椅子靠背上,低着头看着空座位。也许在想象着刚才那个女孩子还坐在这里。这里还弥留着姑娘身上带来的车厢里卷烟的臭味和酸哄哄的怪味道。女店主曾经想要坐在对面和她说几句轻松又得体的话,没有这个时机。或许早些想到她会像逃脱似的离开这里,再送给她一大杯橙子汁或者可乐这样的饮料,谁都喝得惯。
女店主站在那足有十分钟。
她带着一种过失般虚弱的口吻说:“刚才这个姑娘是第一次喝咖啡,你们看到她根本不习惯就应该再送给她一杯果汁饮料。真可怜这个女孩子,她拿出那么多的小额纸币,真不该收下。她是为了体会一种好感觉,可是她太失望了。也许她一辈子也不想再进咖啡店了。真希望她会再来这里,也许她不想再来了。”
那个言语不多表情倨傲的女店员,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她没在意女店主惋惜的表情和伤感的语调。她把收拾下来刚用过的咖啡杯放在后面的吧台上,回过身对女店主说:
“我倒觉得没什么,不是那种人为什么偏要做个样子,还拿出一本书来。这叫人怎么说呢,还不如不进来好。”
“你这么说不好。谁都会有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是有一个好动机。她在尝试一个追求,她以后也许会很习惯的。喝咖啡是非常好的事,全世界到处都有咖啡店。但是她的家乡没有,这是她第一次尝试。人绝不该去讥笑别人无辜的偶然出丑。我们应该帮助她,有时候发生过的一件小事会一生忘不掉,不经意想起来都为自己所做的傻事羞愧。”
以后几年,至今,那个女孩子也没来过这家小咖啡馆。店员换了又换,可是每来新店员,女店主一定要讲起这个故事给他们听,让她们懂得尊重别人的虚荣心。
可是,再没有类似的人出现,也没有类似的情形发生
这是一个让人想起来就有点苦涩又有些酸溜溜的故事,夹杂着一缕令人感动的淳朴。很像一杯“摩卡”咖啡的味道。
女店主总在盼望:那个姑娘会来的。我要亲自给她做一杯咖啡,坐在她对面,再送给她一本她肯定会喜欢的书(当天她就买了一本萨冈的书《你好,忧愁》,还夹进了女店主做的书签。至今还放在咖啡店的五屉柜里)。
和她聊一些她愿意听的奇闻轶事或者国外的中学是怎么上课学习的。
想做她的好朋友,是的。
胡泓,确是1951年出生于哈尔滨,四岁开始学习音乐,后来师从于日本老师佐藤康正学习小提琴。1968年去“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油画、雕刻、雕塑、建筑设计。1971年考入兰州空政文工团,开始写作。1976年复员在医院工作。1984年创建装饰公司。1987年去日本TERRAPIN株式会社任建筑设计师。2000年回故乡哈尔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