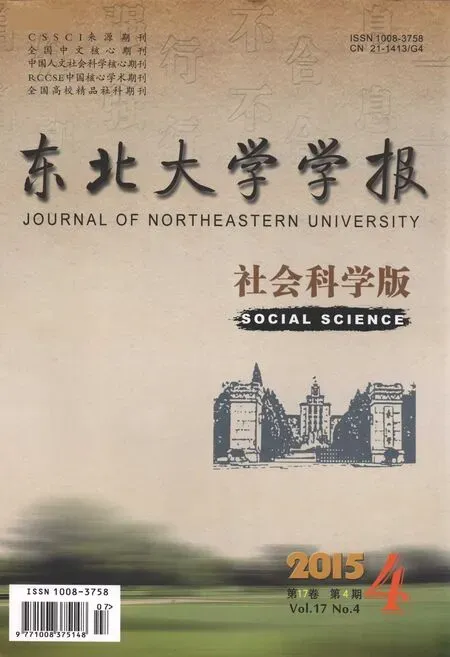理智德性的协作认知
——————————--
理智德性的协作认知
孙保学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理智德性是德性知识论的核心概念。对这一概念有两种竞争性的解读:能力型德性和品质型德性。前者认为理智德性是稳定的、可靠的认知能力,例如知觉、记忆和推理等;后者视理智德性为后天的品质特性,如坚韧、理智勇气和思想开明等。究竟哪种解读揭示了理智德性的本性,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其实,两种解读本质上并不冲突,它们实际上分别揭示了统一的理智德性的两个不同方面。当前争论的根源在于未能恰当地区分两种德性在认知过程中体现的不同价值:能力型德性更适合解释低阶知识,品质型德性更适合解释高阶知识。两种德性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兼容互补的协作关系。
关键词:德性知识论; 理智德性; 能力德性; 品质德性; 协作关系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4.004
收稿日期:2015-01-15
作者简介:孙保学(1986-),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知识论、认知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17;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5)04-0349-06
Abstract:As the core concept of virtue epistemology, intellectual virtue has two competitive interpretations-competence-virtue and character-virtue. The former argues that intellectual virtue is a stable and reliable cognitive ability such as perception, memory and reasoning; the latter regards it as acquired traits of character such as tenacity, intellectual courage and open-mindedness. There exists a perennial controvers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which reveals the nature of intellectual virtue. In fact, the two explanations do not conflict in essence, which explore respectively two aspects of the unified intellectual virtue. The current debate is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two types of intellectual virtue are not identified i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i.e., competence-virtue explains low-level knowledge better while character-virtue is better suited for explaining high-level knowledge. They are synergically related and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rather than in a life-or-death struggle.
Synergic Cognition of Intellectual Virtue
SUNBao-xu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Key words:virtue epistemology; intellectual virtue; competence-virtue; character-virtue; synergic relationship
当代知识论正在经历一种“价值转向”[1]。知识论学者们的关注点已经开始从信念作为知识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分析与辩护逐渐转向认知活动的规范性和价值问题的探讨。德性知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正是这种最新趋向的开启者和主要推动者。当前,有关认知价值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种来源:真理和认知德性。真理作为认知活动的目标,是绝大多数知识论理论追求的价值源泉;认知德性强调对认知者的评价要根据他们是否在认知活动表现了相应的能力或品质,而不是他们是否遵循合理的信念规范或推理程式。有关这些价值问题的考察,最终都落脚于对德性知识论的核心概念“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的解读。可以说,对理智德性的内涵的不同理解,直接决定着德性知识论的发展向度。
一、当代知识论中“理智德性”的提出
德性知识论主张,理智德性这一概念应该在知识论中发挥核心的和基础的作用。在当代,它被引入知识论有着内外两重促成因素:一方面,传统的分析知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表明,它似乎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知识的“概念危机”。理论困境的出现迫使学者们做出研究策略的革新;另一方面,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为知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和效法的范本。
盖梯尔难题(Gettier Problem)的提出引领了知识论在当代的复兴,同时也引发了知识的“概念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当代的知识论学者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例如因果知识论、过程可靠论、适切功能主义和语境主义。这些理论集中分析知识和认知辩护问题,沉湎于寻找知识的充分必要条件。各种竞争性的知识理论层出不穷,有的是对已有观点提出改进,有的是另辟蹊径重新寻找解决方案,都力图避免反例出现。然而,新理论一经提出,其反例也紧跟着出现。长期的争论不仅没能使学者们达成共识,反而使知识论深陷沼泽不能自拔,变得像托勒密天文学体系一样越来越繁琐,俨然成为学者们的一种“智力游戏”。不过,或许这也提醒人们可能误入歧途。传统的分析知识论在理解知识的本质时,以信念作为基本概念和认知评价的基本对象来处理问题。尽管它们在研究策略上有所差异,但都是以信念为基础的知识论(belief-based epistemology)。事实证明,这些理论无一能打破盖梯尔反例的魔咒,原因可能在于没有将认知者及其思维特性考虑在内,“根据信念对知识进行分析的进路是错误的”[2]。
德性伦理学在上世纪后半叶的复兴是德性知识论兴起的最重要外在因素。以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为代表的一批伦理学家试图冲破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争论,不再将人的行为作为基本的评价对象,而转向行动者及其品行的考察。这种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进路很快成为第三股力量屹立于伦理学的舞台。受此启发,一些学者提议在知识论领域也要进行类似的转向和变革,从以信念为基础的知识论转向以认知者的德性为基础的知识论(virtue-based epistemology)。这种转向的可行性在于,德性论者认定信念的辩护与知识的获得都与认知者的理智德性存在着密切联系。人的规范属性在概念上优先于信念的规范属性,信念不过是认知者理智德性的产物,认知者及其德性是比信念更为根本的东西。所以,在本质上这是一种主张“德性优先”的进路。
基于上述的背景认识,索萨(Ernest Sosa)最早提出在知识论中引入“理智德性”概念,试图为知识提供统一的解释,以此化解有关认知辩护的结构讨论中的基础主义和融贯论之争。自此,一种新型的知识论研究范式得以开启,很多知识论学者开始从信念形成的可靠性的研究转向认知主体能力的可靠性的研究[3]。他们试图从德性视角切入传统知识论问题(如盖梯尔难题、内/外在论之争和怀疑论),试图寻找新的解答。这种新思路将理智德性视为一种稳定的、导向真理的、可靠的能力或机能*在索萨的著述中,作为“能力”三个词ability、faculty和competence经常互换使用。在不同时期及其使用语境上三者有细微差别,在此不做严格的界定和区分。,如知觉、记忆、推理、直觉和内省等。这样,认知者及其德性就取代了信念成为基本的认知评价对象。这种进路被称为“德性可靠论”。
寇德(Lorraine Code)最早对索萨的理论作出回应和批评。她赞同索萨将理智德性作为知识论核心概念来处理知识问题的转向,但是,她认为是认知责任而不是认知能力处于理智德性的中心位置。我们应当根据认知责任来理解理智德性,聚焦探究活动中认知者的品质。她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德性责任论”。在她看来,一个在认知上负有责任的人更有可能在认知活动中获得成功。大体上,这种进路视理智德性为一种后天的品格特质或性格倾向,如思想开明、理智勇气和坚韧等。
可见,当代知识论对理智德性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形成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竞争性进路:以能力为基础的德性可靠论和以品质为特征的德性责任论。两者都声称自己的理论真正揭示了理智德性的本质。那么,究竟哪种解读更符合我们智识生活的实际状况呢?下面,笔者将对比双方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在知识解释问题上的分歧来分析这场“德性之争”。
二、能力德性与品质德性的争论
其实,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于德性是什么就有着不同的看法。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即知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说“视力是眼睛的德性,听力是耳朵的德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就是那些状态,以其为基础,人们很可能会获得真理的状态。”[4]在他看来,理智德性是那些通过肯定或否定的方式使得灵魂拥有真理的状态,其中技艺、知识、实践智慧、哲学智慧和直觉理性是五种核心的理智德性。可见,在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智德性主要被理解为一种认知机能或力量。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智德性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导向性’(truth-conduciveness)而被定义。真理目标被设想为在概念是上先于德性概念”[5]。基于这样的认识,索萨发展出一种与真理相连接的德性解释:真理是认知活动的目标,信念得到辩护是通过理智德性的运用实现的。任何有助于真理产生的认知能力都算是理智德性,尤其是生理上遗传得来的能力,比如知觉、演绎和记忆等。由此可见,索萨定义的理智德性在外延上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并不相同。按照索萨的理解,理智德性是有助于最大化一个人的真信念同时减少错误信念的禀赋。德性就是使事物很好地发挥其功能(能力)的性质。切东西就是刀子的德性,写字就是铅笔的德性。这种对理智德性能力本位的理解得到后期戈德曼(Alvin Goldman)和格雷科(John Greco)等人的发展和完善。
然而,在很多责任论者看来索萨等人错误地理解了希腊人的德性概念。他们认为,应该从亚里士多德对待道德德性的模型来分析理智德性。“德性应该归于它们的拥有者,而不是拥有者的能力。”[5]理智德性是认知者后天形成的品格特质,我们对其具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如果我们将信念的辩护理解为一种具有认知责任的活动,好比说正确行动是一种具有伦理责任的活动一样,那么德性的归因应该更恰当地指派给人,而不是人的某些能力[6]。赞格泽比斯基(Linda Zagzebski)和丹西(Jonathan Dancy)就曾指出,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德性与自然能力(机能)有着明确地区分,德性是一种后天状态或倾向,遗传得来的能力不能归于德性。
对此,索萨的早期回应指出,即使他的解释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但仍然是古希腊意义上的。他曾引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著作中关于德性的使用做出例证,并且指出这种用法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那里依然被沿用。“德性标示能力的某种完美,……现在,某些能力自身决定它们的行动,例如,主动的自然力。因此,这些自然力本身就是德性。”[7]
关于这一点,责任主义者似乎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这些传统用法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但是,他们仍然选择忽略掉亚里士多德对两种德性的对称性处理。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德性知识论要求提供理智生活目标的多元的和整体性的统一解释。亚里士多德对道德德性阐释恰恰为这种统一提供了最佳模型,统一的基础就是品质。德性可靠论试图通过能力德性将真信念最大化和错误信念最小化的认知目标并非那么容易达到。事实上,在信念形成过程中这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目标,而且它们的实现实际上是依赖于品质德性:最大化一个人的真信念依赖于理智勇气的德性,而将错误信念最小化则需要理智谨慎的德性。
另外,赞格泽比斯基也指出,可靠论虽然正确地将问题的源头追溯至德性,但仍然落脚于对作为德性之产物的信念的评价。这种研究进路仍然停留在对脱离情境的单个信念的评价,从而忽视了对行动者和探究活动的社会情境的评估[5]。正如贝尔(Jason Baehr)所言,责任主义的、能动的向度对于走出传统知识论误区是极为重要的,作为群体成员的人的认知活动要比简单个体的知觉认知机制复杂得多,而前者同样属于知识论的问题领域。可靠论者必须扩展他们的焦点,“不仅仅关注那些认知上机械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向度,而且应该关注那些积极的、意志的或以品质为基础的认知向度。如果不将后者包含其中,可靠论者将不能解释那些为我们人类所最关心的具有恰当认知地位的知识的可靠性”[8]67。所以,索萨恰当地强调了德性与认知的关系,却忽视了品质德性在历史的和文化的语境因素中对知识价值的塑造[9]。
索萨积极地回应上述指控。他力图消除这样的误解:德性可靠论仅仅被框定在那些简单的、模块化的、自动的信念形成机制或过程。索萨援引自己的著述,力图证明德性可靠论从未排除或忽视能动的、积极的和责任的自主性维度。在早期理论中,他将知识区分为动物知识(animal knowledge)和反思知识(reflective knowledge)两个层次。后者包含一种对前者的来源及其可靠性的融贯的“认知透视”。他指出,理性行动者形成的适切的(apt)信念需要反思性的理性能力辅助,“至少理性一直是一个隐秘的伙伴,它密切注意着其他相关材料,这个非常隐秘的伙伴恰恰是人们输出信念的一个起作用的原因”[10]。近年来,索萨一直强调他所说的信念形成过程不单是那些简单的输入—输出机制,“机制可以是某种类似于反应能力的东西,也可以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中央处理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一个灵敏的批评者在复杂的和周详的考虑基础上来‘决定’如何评价一个工作成为可能”[11]87。
正如索萨所指出的,责任论者的批评刻意规避了反思知识的自主性维度,指责可靠论遗漏了这一方面。事实上,索萨只是将他的知识说明集中在一些简单知识的例子中,“在不太简单的知识例子被强调时,其他问题当然可能出现。然而,重要的是,首要地而且坦率地说,它已经足够挑战尝试首先要处理的更简单的例子”[12]。责任论者片面地讨论他对动物知识的强调,忽视了在他的知识分析中其实内含一种反思能力的作用。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索萨关于反思知识的主张与德性责任论在理论旨趣或出发点上是完全不同的。根据索萨最近的观点,在解释人类知识问题上他仍然坚持德性可靠论的中心兴趣点是能力型的“建构的”理智德性,品质德性只是“辅助的”理智德性[12],只是能力德性的某一方面。相反,在责任论者看来,知识之所以是人的知识关键就在于它是由有动机或主动成分的品质德性产生的。它们是促动人类欲求真理的认知活动的内在推动力,彰显着知识的独特价值,而这种价值在纯粹真信念的传统分析中很难被找到。可见,当代的“德性之争”不是术语之争,而是一种立场之争。
三、知识的解释
与索萨区分动物知识和反思知识类似,赞格泽比斯基区分了低阶知识与高阶知识[13]273-83。在她看来,低阶知识是指在正常的环境条件下只要人们的认知机能运转良好就会自动地获得的知识类型。我们的感官知觉获得的知识就典型地属于这一类。它们通常是被动获得的,并不需要明显的意图或动机,成年人、婴儿甚至高等动物都能有这类知识。与此相反,高阶知识则属于人类更丰富的理智成就,它的获得需要认知者积极的、有意图的探究,这类知识一旦获得便可以通过证言的形式在人群中传递。它们包括科学知识、哲学知识、道德知识和调查应用型知识等[14]17。传统知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定义知识,但它主要是分析低阶知识。其实,高阶知识的分析同样有着重要的知识论意义,因为我们的很多知识都属于高阶知识的范畴,这是任何完整的知识理论所不能忽视的领域。
基于上述的这种区分,有学者提出我们可以由此相应地区分出获得两种知识分别需要两种德性:低阶的能力德性和高阶的品质德性[15]。显然,大部分高阶知识的获得如果仅凭能力德性是难以完成的,同样有些低阶知识的获得完全能够在没有品质德性的参与下即可完成。然而问题是,一些德性责任论者和德性可靠论者认为,他们各自对理智德性的定义能够涵盖两类知识的解释。不过,实际上他们很难完成统一解释的任务。
1. 低阶知识的解释
赞格泽比斯基主张:“知识是一种源自理智德行的信念状态。”[13]271她认为,低阶知识的获得并不要求行动者表现出稳定的有德性行为的习惯或倾向,不必具备全面的德性。行动者执行一种有德性的行动即可获得相应的知识。但是,即便是这样低的标准,对于获得低阶知识仍然要求太高。按照她的说法,德行要求行动者做有德性的人应做的行动,同时要具备相应的动机成分,行动者通过这些行为特征才能获得真信念[13]270,而且,理智的德性动机成分与道德的德性动机成分一样都是在实践中后天获得的,同时理智的行为是志愿的(voluntary)。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知觉知识并不要求对真理有后天动机和志愿的理智行动。例如,我在看书时屋里的灯突然灭了。这时只要我视力正常,我肯定会立即地、自动地甚至是下意识地形成“屋里是黑的”这一视觉知识。“显然,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显示出任何理智上的动机或行动。我甚至没有在低的或下意识的水平上探究这一事态的真理性。在相关的动机意义上认为我是‘信赖我的感觉’也并非可信。”[8]44因此,动机条件对于知识的获得不是必要的。
信誉理论(credit theory)是目前德性可靠论最主要的分支。它主张行动者获得知识当且仅当他获得的真信念是源自他的理智德性(认知机能),而非出于偶然或运气[11]92。这样,行动者应得到对知识或相信真理的一种信誉。这种信誉具有一种内在价值,它赋予(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晋升为知识的资格。“在知识的情形中,主体的成功应该归因于主体的能力。”[16]在上文的案例中,我知道“屋里是黑的”完全是拜我天生可靠的视觉德性能力所赐。在这种解释中,德性无需牵涉后天的动机或志愿成分,行动者不必表现任何对于真理的德行活动便可获得知识。
2. 高阶知识的解释
显然,能力德性对于获得高阶知识是必要的,但它却并不是充分的。因为能力德性的良好运用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获得想要的知识。现实中的很多活动都要求获得高阶知识,例如神经科学中关于大脑定位系统细胞的发现、医疗实践中医生对病人症状的诊断、侦探在侦破案件时对凶犯身份的确认,等等。这些活动需要行动者的专业知识背景、工作的耐心、专业的洞察力等专业品质,这些高阶知识显然不是门外汉仅凭诉诸认知机能就能获得的。或许,一些可靠论者会诉诸反思能力来作出回应,但在索萨看来反思能力同样是能力德性范畴。“当某人旨在实现某些目标时,一般地讲,能力是成功的倾向,而正确相信的能力就是这样一个特例。”[12]
在赞格则比斯基那里,“知识要求一种理智的行动:首先,它是源于德性的动机;其次,它是有德性的人将会做的;第三,达到了动机所要求的结果;最后,获得真信念是因为德性的动机和行为”[14]23。她要求行动者在获得知识的活动中表现出一种志愿的、有动机和意图的行动。例如,爱因斯坦为了想弄清楚物体惯性和它自身能量之间的关系,为此付出了艰辛的理智思考。在初步获得一个假说后,他还要进行各种推算和检验活动,最终才得出质能方程E=mc2。在这一复杂的智识过程中,仅凭认知官能的正常运转是难以完成的。
可见,能力德性更适合解释低阶知识,品质德性更适合解释高阶知识,任何企图用一种德性涵盖对方的知识的解释都难以为继。其实,两者在我们的智识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德性主要是负责形成我们的基本信念,而品质德性则更侧重于调控我们已形成信念[17]27-30。当前的争论根源恰恰就在于未能对两种德性在认知过程中的不同功能作出界定,未能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四、协作的理智德性
其实,两种德性在认知过程中具有一种协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无法通过合取或析取的方式表达。认知科学中的“双进程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能够为我们说明两种理智德性的协作关系提供经验证据上的有力支持。
如果我们认可知识解释应该将两种德性统一起来考虑,或许会最先考虑到合取和析取的这两种基本的定义方式。合取式定义要求同时满足德性可靠论和德性责任论,即一个真信念是知识当且仅当它的产生既要求在适宜环境下行动者的能力德性正常施展,同时也要求他表现出品质德性的行动。这种定义是不成功的。在上文中已经证明,高阶的品质德性对于低阶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必要条件。很多低阶知识的获得只要求我们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认知机能正常发挥即可。合取的失败促使我们转向析取式定义,即一个真信念是知识当且仅当它的产生或者是由于适宜环境下行动者能力德性的正常施展,或者是由于他表现出品质德性的行动,但两者不必同时具备[17]11。这种定义同样不成功。因为品质德性的发挥离不开低阶知识作为基础,而低阶知识只有通过品质德性的协调作用才能使认知者获得高阶知识。单独强调任何一方,都会造成顾此失彼,无法完成知识的解释。
基于这种定义上的困难,很多当代德性知识论学者主张应该放弃传统的“S知道p当且仅当……”的定义方式[17]83,[18],要求综合地考虑我们的智识生活。实际的情形很可能是,两种德性其实不能互相解释,它们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认知评价的两个维度,各自负责处理有所侧重的认知任务,协作地完成复杂的认知过程。因此,两者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协作关系:一方面,在认知过程中,高阶知识的获得必须建立在低阶德性正常施展之上,“认知机能与品格之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品格的体现总是通过某种机能的运行”[3];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性的智识生活要求低阶知识上升为高阶知识,高阶德性调控认知过程以使信念系统融贯地发挥作用。
对德性的协作解释并非一种凭空猜想,认知科学中的“双进程理论”能够为这种协作关系提供有利的支持性说明。这种理论揭示,人们的思考或推理等认知活动实际上是由两个相互协作的系统或过程共同完成:一种是无意识的、自动的或隐性的,称为系统1;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可控的和明确的,称为系统2。这两个系统所形成的信念,可以相应地区分为基础信念和高级信念。前者形成的是一种内隐知识(tacit knowledge),后者形成的是一种外显知识(explicit knowledge)[19]。信念偏见测试(belief-bias test)的fMRI影像显示,被试对不同问题的回应明显地受到两种不同的心理进程控制;但是,这看似分立的两个进程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共享同一命题内容,并且在认知过程中是协作地发挥作用。例如,在我过马路的时候,我相信闯红灯是危险的。这属于系统1(能力德性)形成的一种基础信念。但是,如果有人问“在我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是否是危险的?”此时,我则是在系统2(品质德性)的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外显的高阶知识一旦作为一种规范被行动者接受,便可作为系统1的一种内隐知识,为展开进一步的认知活动提供基础。因此,系统1(能力德性)为认知活动提供基础,而系统2(品质德性)为认知者的信念体系提供内在的一致性,发挥一种规范性的作用。
可见,两种解释本质上并不冲突,它们实际上分别揭示了统一的理智德性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体现着不同的认知价值,以不同的方式贡献于我们的认知目标,引导我们最终获得有意义的真信念和知识。这种兼容互补的协作式的理解框架对于跳出非此即彼的德性之争是必要的,将有助于整体地或全面地理解我们的认知成就。
参考文献:
[1] Riggs W. The Value Turn in Epistemology[M]∥Hendricks V, Pritchard D. New Waves in Epistemology. Aldershot: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ing, 2008:300.
[2] Williamson T.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4.
[3] 方红庆. 索萨的德性知识论:问题与前景[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3,29(1):8-13.
[4]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105.
[5] Axtell G.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the Reunification of Epistemology[J]. The Monist, 1998,81(3):488-508.
[6] Code L.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M].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7:47.
[7] Greco J. Two Kinds of Intellectual Virtue[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0,60(1):179-184.
[8] Baehr J. The Inquiring Mind: On Intellectual Virtues and Virtue Epistem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9] 郝苑. 理智德性与认知视角——论欧内斯特·索萨的德性知识论[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27(4):20-24.
[10] Sosa E. Knowledge in Perspectiv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240.
[11] Sosa E. A Virtue Epistemology: Apt Belief and Reflective Knowledge, Volume I[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 索萨. 德性知识论:品质与能力[J]. 郑伟平,曹剑波,译. 世界哲学, 2014(5):5-20.
[13] Zagzebski L. Virtues of the Min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Virtue and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 Battaly H. Virtue Epistemology[M]∥Greco J, Turri J. Virtue Epistemology: Contemporary Reading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2.
[15] Lepock C. Unifying the Intellectual Virtues[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11,83(1):106-128.
[16] Greco J. A (Different) Virtue Epistemology[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12,85(1):1-26.
[17] Roberts R, Wood W J. Intellectual Virtues: An Essay in Regulative Epistemolog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Kvanvig J. Virtue Epistemology[M]∥Bernecker S, Pritchard D.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199-207.
[19] Frankish K. Dual-process and Dual-system Theories of Reasoning[J]. Philosophy Compass, 2010,5(10):914-926.
(责任编辑:李新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