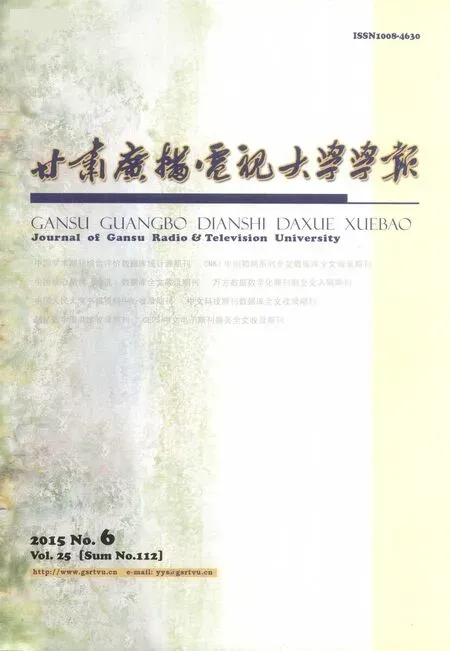简媜散文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戴志杰(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简媜散文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戴志杰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简媜作为台湾本土作家,她的散文创作风格是传统与现代并举,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涵是对中华传统的文化认同,包括崇尚自然的审美观,重亲情、尚人伦的和谐伦理观,通过追溯家族历史寻求身份认同的历史观。因历史文化原因,在台湾多元文化语境下,台湾作家对中华文化认同呈现多样性、个性化特征,简媜散文中所体现出的中华文化认同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简媜;文化认同;崇尚自然;和谐伦理;家族历史
简媜是台湾新世代散文作家中的佼佼者,自20世纪八十年代登上文坛以来,笔耕不辍,创作颇丰。一方面简媜的散文创作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与“五四”散文创作一脉相承,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创作技巧,但是贯穿始终的是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她通过对自然、生命的尊崇,对和谐人伦关系的推崇,对家族历史的追溯和书写,进而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构建。另一方面,面对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处在西方与东方、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碰撞的情景,简媜表达了她对社会文化的观察和对传统文化在当时台湾社会中面临的新问题的再思考。
一、崇尚自然的审美观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导,在此基础之上创造了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长期以来,中国人形成了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亲和、平等的关系。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把世界分为天、地、人三类,人与自然等万物皆产生于天地之间,和谐相处。随后,儒道释从中汲取养分,形成了完善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西方文化中亦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同的是“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天’从来都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物质)对象,而是作为精神寄托乃至信仰膜拜的(情感的、精神的)对象,而与天‘合一’,代表的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不是西方式的对自然规律的终极认识”[1]。换言之,中国人对天(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最高的伦理信仰。自然也是思想的源泉和审美的对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理想的审美境界。
简媜是继承了中国崇尚自然的美学传统的。她出生在宜兰乡下,那里气候湿润,环境优美,启蒙她去追求爱与美。“在生命最活泼的前十五年完整地生长在与世无争的平原农村,听懂天空与自然的密语、窥视山峦与云雾的偷情、熟悉稻原与土地的缱绻。”(《台北小脸盆》)在散文集《水问》中表达出她对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赐予万物的自然的珍惜与感恩。如《千百层》、《花之三叠》、《美之别号》等篇章均以托物言志的形式,透过植物的生命窥探人的品格、价值和信仰。大自然虽美,但也有无情的时候。宜兰由于处于台湾岛东北部沿海,东邻太平洋,经常遭受台风、水灾的侵袭,所以,宜兰自古以多雨闻名,台湾的谚语“竹风兰雨”,指的就是新竹多风和宜兰多雨的现象。简媜外出求学工作多年,回忆起家乡“保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她旧时的彪悍与沛然莫之能御的水魔个性”(《雨神眷顾的平原》)。于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寻求生存、改造自然的艰难过程造就了宜兰人柔情与悲壮糅合的个性,这种特质相比较男性而言,在女子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简媜的散文中“地母”是一个常见的意象,与《易经》中一样将大地比作孕育人与万物的母亲,具有包容而坚韧的特质。中国文化中对“地母”的崇拜要追溯到生产力低下、人口出生率低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作为生命延续的载体,对“地母”崇拜即对生命的赞美,带有神秘的原始宗教色彩。简媜在散文中用“地母”表达了对女性的赞美和歌颂:“一半壮士一半地母,我是这么看世间女儿的。”(《女儿红·序》)自然环境对人的审美情趣、个性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昭然若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都市化进程使植被遭到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经受着考验。在《水姜哀歌》、《仇树》中,简媜因看到城市高楼、街道对山川花树等自然物生存空间的挤压而呼吁道:“人应该与大自然的繁花草树为友。”都市化的同时造就了人们追求快捷、便利、物质化的生活方式,而日常生活中原有的传统习俗,可以使生命与自然亲近的温暖记忆等被逐渐遗忘。简媜在散文中表达出对洗衣机、微波炉、冷气机等现代化设备的拒绝态度。“像我这样的人,曾经过度纵容于手工时代农业社会的,不可避免地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把机器当做杀父弑母的嫌疑犯。所以,宁愿在现代浴缸上搁洗衣板,慢慢搓洗棉被套,回到乡村时期女人家在河边洗衣的想象。”(《传真一只蟑螂》)简媜认为,农业社会造就的文明应当保留和传递下去,同时,她对乡村与都市的态度是辩证的,她自称“半是乡下人,半是台北人”。她并不是反对都市化,眼前如同鸽笼一般的都市使很多人实现了梦想,漂泊迁徙的人们在城市落脚并安定下来,现代与传统交织的故事使得城市更具有魅力,也为作家提供了观察的对象。“不挑剔地说,我颇喜爱台北,但严格地审视,我现在还在努力适应台北。”住在都市里怀想乡村是接近自然的方式,乡村是简媜心目中的“原乡”,是心灵上的乌托邦,是平衡和调节乏味苦闷的都市生活的和谐之道。简媜十分推崇老庄的生存哲学,其散文中与庄子、屈原、李白相关的仿写、隐喻、典故甚多,如《相忘于江湖》、《水问》、《梦游书》等。她推崇游离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游世”。只有这样,一个怀揣着自由与理想的乡下人生活在喧嚣的都市中,既不会放弃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又避免了思想陷入虚无中,精神上可以自由和超脱,保持自我,进而“使敏感多思的我不至于变成人性扭曲的城市客”(《台北小脸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高明的生存智慧,即“一种使布衣和名牌同等美丽的生活美学”(《心动就是美》)。
二、和谐的人伦观
人伦,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血缘宗亲联系而成的家庭本位的伦理道德观,“重亲情,尚人伦”是中华文化影响下的普遍价值观念。对故乡、亲情、童年的描写是中国文学中常见的题材,而这一题材又在情感细腻的女性散文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延伸。“五四”以来,台湾女性散文作家中的琦君、张晓风、席慕蓉、三毛等人都对故乡、亲情、童年的温暖记忆有所描写,简媜亦不例外。在散文《银针落地》中讲述阿嬷一生辛勤劳作,把爱都奉献给子孙,昔日油亮的黑发渐渐变白;在《渔父》中对猝然逝去父亲的追思,震撼感人;在《缝纫机》中感受到母亲宽容的教育方式的伟大;在散文集《红婴仔》中,作者记录了自己孕育生命过程中的温馨和感动……不仅如此,简媜的家庭成员也悉数在散文中出现过,简媜家境平凡,也遭遇过厄运,如爷爷、父亲、弟弟先后去世,家庭重担依靠祖母和母亲担当,但这个三世同堂之家的亲人之间相互依靠,浓浓的爱化解了许多难题和磨难。因为简媜生活中有过心痛的经历,使得她对亲情、故乡、童年的描写比起前辈和同辈的女作家,在感情上更加理性、克制和深刻,清新明丽的语言之下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执着追问具有哀而不伤的美感。
简媜散文中还有对“重亲情、尚人伦”的传统观在当下台湾社会中的新思考。社会日益老龄化,人口流动量加大,致使空巢老人越来越多。时代文化更迭速度加快使得代沟形成的时间不断缩短、观念差异的程度日益加深,身为长辈和晚辈都面临着观念转变的问题。如,何种方式才是尽孝道?垂暮老人如何体面、有尊严地度过晚年生活?面对死亡和病患,是讳疾忌医,还是理性面对?“把死亡当做不详、邪秽、冥暗的观念里,跟死相关的话题都是不能碰触的禁忌。仿佛一句话漏了馅,邪灵将附身,恶魔会纠缠。然而,既然死亡是每个人必须走的一条最平等的路,有什么道理活到一大把岁数、累积数箩筐人生滋味的人不能勇敢地面对死亡?”(《谁在银光闪闪的地方等你》)由于生老病死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是亲人之间不愿直接提及的问题,也是对亲情的终极考验。所以,简媜指出,无论老人还是子女,都应该放下传统观念,直面问题,未雨绸缪,这才是真正为自己、为他人做出的合适交代,因为“完整的人生应该五味陈杂,且不排除遍体鳞伤”[2]。
简媜散文中和谐的人伦关系不仅包括亲人之间,还包括陌生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简媜在散文里描写了一系列城市底层劳动者的形象,如,话不多但尽职尽责送报纸的女人(《一枚煮熟的蛋》),不染纤尘亲和待人的街头卖小吃的女人(《粉圆女人》),每天会用微笑和别人打招呼、憨厚老实而又寡言的砌石老人(《迟来的名字》)……他们都是勤劳、善良的人,用自己的爱温暖别人。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仍是男权社会,尽管社会经济已经得到发展,普及化的教育给女性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机会,但是男尊女卑的文化心理依然根深蒂固,处于新旧时代交替中的女性遭受着生存、观念的困境。简媜在散文集《女儿红》、《只缘身在此山中》以及其他篇章中讲述了诸女性对传统观念的反抗,寻求独立和自由的故事,如 《天阶月色凉如水》、《母者》等。有的女性身处都市,在事业上独立,却是感情里的落寞者,精神上孤寂、空虚;有的内心向往着自由、公平,却不得不受困于都市的喧嚣、偏见之中,如《口红咒》、《忧郁猎人》、《哭泣的坛》等。简媜指出男权社会下的语言系统就好像“害了性病”,对于女人的要求仅在于“胸围、腰围、臀围及一对傻乎乎的双眼皮上”(《哭泣的坛》),指责长久以来对女性教育方式的古板,以及对女性轻视和羞辱的痛恨。值得注意的是,简媜的观点并不是主张女性对男性的僭越,而是主张构建“和谐的自我伦理”[3],即通过“女性自我完善的新思路”[4],独立坚韧,创造自己的价值,在社会中立足,以此消解男权社会的压力。
三、家族历史的书写
文化认同回答的问题是“我是谁?”,而族群认同回答的问题是“我从哪里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包括其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认同。在台湾后殖民文化的语境下,文化认同呈现出差异性、多元化特征,于是,认清自己的“根”,对个体、族群的文化认同显得尤为重要。简媜突破了女性散文的狭隘视野,开拓了家族历史视野,以简姓氏族在台湾为坐标,寻找族群的轨迹和群体命运,她“寻找一种高度,足以放眼八荒九垓又能审视自己这卑微的存在”[5]287。通过对家族历史的追溯,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进而对自我身份进行构建。
简媜探寻族群的历史缘起于对自己三代以前旧事的一无所知,说的闽南语为什么带着宜兰腔?对于台湾新世代的本土作家而言,“原乡”的所指不同于有着大陆生活经验的白先勇、於梨华等作家,他们的原乡是模糊的中国地理想象,正如简媜所说:“对我而言,原乡是一团迷雾。”于是简媜通过对族谱、祠堂牌位信息等有限资料的搜集研究,探寻祖先的起源和足迹,寻求族群认同。对于简媜而言,意外的是最终遭遇的是一部近三百年沧桑的中国历史。在寻根的过程中,发现祖辈竟然是来自福建省南靖县的客家人,时过境迁,“无从推测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福佬话,在南靖来台之后?不知道他们用语言换取身份抑是隐藏身份?……我的祖先最后入垦宜兰,留下一口据说掺着南岛语系的宜兰腔福佬话给后代,完全遗忘客家渊源”[5]30。她感知到祖辈生存的艰辛,祖先、台湾岛的命运和中国历史的沉浮息息相关。“每一支姓氏迁徙的故事,都是整个族群共同记忆的一部分。当我们追索自身的家族史,同时也钩沉了其他氏族的历史。唯有大时代足以歌泣时,我们自身的故事才足以歌泣。”(《天涯海角》前言)寻根之旅中,简媜对历史的严肃和宏大有了更深的感悟,台湾这个美丽的小岛承载着历史洪流下的浪子的梦想和归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这里落脚生根。“一人、一家、一族历史皆是时代洪流之旁支,我沿着幽深的时光甬道洄溯,原以为会找到我的先祖——他年轻力壮,在彼端等我,没想到一摊开台湾开发史,出了时光甬道,赫然看到成千上万荷锄戴笠,正等待船只欲寻找海外天堂的浪子。”(《天涯海角》)
同为台湾新世代散文作家的张大春,不同于简媜对波澜壮阔“大时代”的厚重感和主动“寻根”。张大春书写家族历史的动机略显被动,他的书写源于父亲的突然病倒,这让他有了一种危机感,同时,身为外省籍二代的张大春对家族历史的书写带有私人化、主观性意味,显示了历史的误谬和戏剧性,以及历史对个人命运的残酷玩弄。如张大春在《聆听父亲》中写道:“如果你问我‘大时代’是什么意思?我用我父亲的话回答你:‘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对家族、民族历史认同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外省籍一代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内战,后漂泊至台湾,逃难中躲避炮火的恐惧感、无根的漂泊感、对命运的不可捉摸感、信仰的崩溃和坍塌都会传递到下一代,这对历史的严肃的权威解读起到解构作用。因为,他们认为自身就是可歌可泣的“大时代”的亲身经历者,对历史的解读也最有发言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省籍二代会沉浸在历史虚无主义中,事实上,他们身上背负的历史包袱更沉重,心情也更矛盾、复杂。外省籍二代作家经历了台湾的省籍矛盾,身为“外省人”的他们在台湾始终在努力寻求个人的身份认同,但眼前的现实才是现实的家,对父母口中的大陆经验常常当作唠叨。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矛盾的身份认同随着省籍区分的日益淡化,两岸往来的日益密切,“寻根之旅”冲淡了原先父辈的骨肉分离的痛苦,随着自己也迈入中老年的行列,对父母、历史的认识逐渐深入,对于父母的原乡情结有所体会,家族的历史书写经常是处在不断解构和重构过程中,又带点现实的酸楚和悲情。正因如此,张大春的《聆听父亲》比起爱炫技巧的小说创作显得更有诚意。如,龙应台的《目送》收起了锋芒与犀利,显得温情脉脉;朱天心的《击壤歌》虽然描写的是中学时代,但是对父亲的乡愁也怀有深刻的感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处于后殖民文化语境之中,“经济繁荣却遭遇国际孤儿的窘境,使得台湾知识分子特别关注文化身份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定位,也使得关于文化认同的思考方兴未艾”[6]。新世代作家或多或少地对台湾地区文化归属问题进行着思考。因为台湾地区处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新世代作家对其文化认同呈现多样性、个性化特征。简媜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和其散文中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以及在现代社会中对传统文化的再思考,是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这促成了简媜散文创作的独特性,也使她在台湾散文作家中占得一席之地。
[1]徐瑾.论中西方“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区别[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6.
[2]简媜.谁在银光闪闪的地方等你——老年书写与凋零幻想[M].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社,2013:12.
[3]简媜.女儿红[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72.
[4]程国君.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创作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6.
[5]简媜.天涯海角[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6]刘伟云.穿越都市表象的探索——台湾新世代小说的文化认同书写[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8.
[责任编辑 龚 勋]
2015-06-25
戴志杰(1989-),女,江苏邳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6
A
1008-4630(2015)06-00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