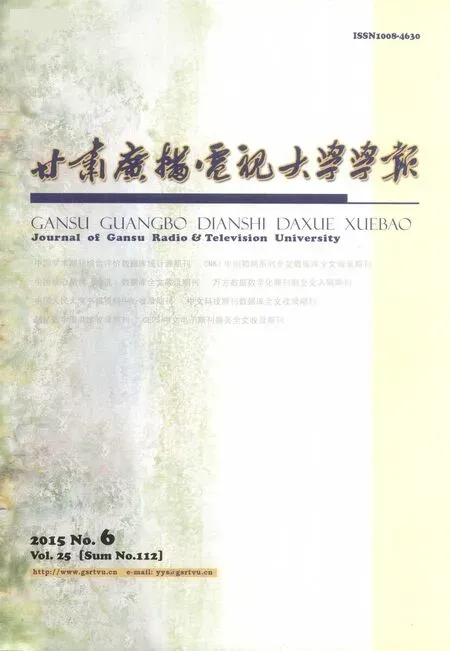澄明的本心:陇东南童谣的民间哲学智慧
郭昭第(天水师范学院 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甘肃 天水 741001)
澄明的本心:陇东南童谣的民间哲学智慧
郭昭第
(天水师范学院 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甘肃 天水 741001)
虽然儿童可能在生活经验和生活能力方面与成人有一定差距,但不能视其为有待启蒙的愚昧者。虽然儿童不见得在灵性方面弱于成人,但也不能说“儿童是成人之父”。所有这些偏激的看法其实都是成人在用自己的眼光判断和评价儿童。儿童恰恰是因为没有经受世俗社会束缚而具有澄明的无所分别和取舍之执著的本心,以及周遍无碍、平等不二、明白四达的哲学智慧。陇东南童谣如催眠曲、游戏曲等,显然呈现着无所分别和取舍的澄明本心和民间智慧,甚至可视为解决成人生活矛盾的金钥匙。
陇东南;童谣;民间哲学;无所执著;心体无滞;明白四达
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儿童看成没有任何灵性乃至大脑如白板的愚昧者,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涉世不深的顽童,以及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乳臭未干的待启蒙者等。这其实是人们在用成人眼光判断和评价儿童。事实上虽然儿童在生活经验和生活能力方面可能确实与成人相差甚远,但并不见得在灵性方面弱于成人,儿童的大脑并不就是一无所有的白板。虽然不能说“儿童是成人之父”,但说儿童常常比成人具有更多灵性乃至潜质,则是毫不夸张的。儿童尤其婴儿虽然缺乏生活经验和能力,但这恰恰是其未接受世俗社会束缚而具有无所分别和取舍之心,以及无所执著、心体无滞、明白四达的智慧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些可能更多通过童年生活的某些习惯乃至实绩获得显现,相对来说最能集中彰显童年智慧的可能是童谣。
虽然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童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过童年时代。应该说没有经过口口相传乃至耳濡目染的童谣教育的童年,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童年。童谣在儿童的文化传承乃至思维训练、智力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童谣不仅是儿童哲学智慧的结晶,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参与了童谣的创作,甚至在童谣中寄寓了各自的思维方式、认知基础和哲学智慧,而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了童谣教育,而且正是借助这种口口相传的童谣积淀、传承并形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虽然相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而言,童谣似乎只能是人类童年时代梦想的延续和传承,但正是这种童年梦想却凝聚着几乎每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基础乃至哲学智慧,而且往往是最接近于原始、本真的本心乃至本性,以致最接近于人类原始本心的自然呈现和澄明的哲学智慧。
童谣是无所执著的。这不是说儿童比成人有着更为缜密的思维、深邃的思想、高度的智慧,而是因为儿童尚未接受后天的世俗化教育,尚未形成斤斤计较于成败得失乃至是非曲直之类的分别和取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与生俱来的原始本心,而这种原始本心恰恰建立在无所分别和取舍的基础之上。正因为无所分别和取舍,也便可能因为无执无失而具有周遍万物、明白四达的哲学智慧。相对来说这种无所执著的智慧似乎更为普遍地存在于催眠曲之中。虽然催眠曲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父母创作并相沿成俗的,虽然所有的父母作为成人并不见得能够真正达到周遍万物、明白四达的境界,但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在相沿成俗的催眠曲中彰显出无所执著的智慧特点。这不是说作为父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下了一切分别和取舍,放下了一切执著,而是说几乎所有父母都无意识地沿袭了催眠曲对睡眠特征的最大尊重。因为睡眠的最大特点便是无所执著。人们只有放下一切执著才可能进入睡眠状态,否则除非疲劳过度,不然是睡不着的。几乎所有失眠的人都是因为过分执著于日常生活的成败得失、是非恩怨乃至生活琐事,以至于斩不断理还乱,而陷入失眠状态。有些人虽然表面上并不执著于诸如此类的恩怨得失,但往往执著于睡眠与否之类,以致仍然陷入失眠的状态。所以即使没有经验的父母也会沿用口口相传的催眠曲使儿童渐入睡眠状态。
虽然绝大多数催眠曲并不十分有趣,但往往能够使婴儿在对诸如吃喝等基本生理需要看似放纵实则抑制的渐进过程中逐渐放松注意,以致使思维、情感和意志渐入无所执著境界,乃至达到睡眠状态。否则,如果所谓催眠曲不是逐渐抑制婴儿的思维、情感和意志,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情节,或者对诸如吃喝等基本生理需要不断满足,便可能使得婴儿因津津有味而兴奋异常,以致无法入眠。但催眠曲也不能过分乏味,以致使婴儿一开始便觉得兴味索然,产生焦躁不安等情绪乃至久久无法平静。如以要馍馍为主题的催眠曲在陇东南童谣中较为普遍。如一则陇东童谣有云:
娃娃乖,睡觉觉,睡醒来,要吃馍馍哩。馍馍啦?猫叼去了;
猫啦?老鼠洞里去了;老鼠洞啦?牛草塞了啊。牛草啦?牛吃了啊;
牛啦?上山去了啊;山啦?塌了啊;土啦?活了泥了啊;泥啦?漫了墙了啊。
墙啦?猪毁塌了啊。猪啦?刀杀了啊。刀啦?切了菜了啊。菜啦?人吃了啊。
人啦?走了啊。
类似的催眠曲还见于陇南市西和县,如:
噢噢睡觉觉啊噢噢,睡着起来要馍馍啊噢噢。
馍馍啦?老鼠拉着走了啊噢噢。老鼠啦?钻了窟窿了啊噢噢。
窟窿啦?窟窿草草塞了啊噢噢。草草啦?草草牛娃吃了啊噢噢。
牛娃啦?牛娃喝水去了啊噢噢。水啦?大河淌了啊噢噢。
大河啦?日头阿婆晒干了啊噢噢。日头阿婆啦?压山了啊噢噢。
山啦?野猪喙塌了啊噢噢。野猪啦?猪匠杀了啊噢噢。
血盆啦?上坡里(正堂)放着哩啊噢噢。刀子啦?门背后挂着哩啊噢噢……
类似催眠曲也见于天水市清水县,如:
噢噢噢,睡觉觉,睡着醒来要馍馍。
馍馍啦?猫吃了。猫儿啦?抓老鼠去了。
老鼠啦?跑到窝里了。窝儿啦?叫草塞住了。
草草啦?叫牛吃了。牛啦?树上拴着哩。
树啦?木匠锯了。木匠啦?走了舅舅家。
虽然此类催眠曲内容稍有不同,但大体上围绕要馍馍这一主题,而且往往采用顶针的修辞方法,借助诸如走了或挂起、归土等结局使希望逐一落空,最终归于无。貌似有趣实则无趣,貌似无趣实则有趣,以致对有趣与无趣乃至其他一切无所分别和取舍,才可能是童谣之所以能够使婴儿较快进入睡眠状态的根本原因。作为催眠曲的童谣往往有着微弱的叙事功能,具有一定时间顺序且符合因果逻辑,甚或在某种程度上利用相继出现的事物以及带有顶针修辞格的句子,使得儿童在保持注意持续的同时,也由于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地逐渐落空,使得儿童注意力逐渐涣散、思维逐渐模糊、情感逐渐淡化、意志逐渐松弛,以致迷迷糊糊进入睡眠状态。或更确切地说,所谓催眠曲其实是以舒缓乃至微弱的叙事,使婴儿不至于因为索然无味而焦躁不安,但最终因为舒缓乃至一切归于无而不十分有趣,才具有了催眠功能。
陇南礼县童谣《割韭菜》还将割韭菜的游戏与要馍馍的主题糅合在了一起,而且同样借助顶针修辞格而使希望逐一落空最终归于无,以致使婴儿在丧失耐心的情况下达到催眠的目的:
割割割韭菜,割了三担五口袋,
你吃箩儿头级的,我吃箩儿底下的。
你吃油饼圈圈,我吃油饼边边。
你的半个吃上了,我的半个给放羊娃留下了。
放羊娃来了要馍哩。馍啦?老鼠拾走了。
老鼠啦?钻了窟窿了。窟窿啦?草塞了。
草啦?牛吃了。牛啦?上山了。
山啦?河淌了。河啦?日头阿婆晒干了。
日头阿婆啦?压山了。山啦?裂了啦。
相较而言,天水市麦积区《扯扯儿》似乎更为诙谐幽默、生动有趣,如:
扯扯儿,麻姐姐,你掸胭脂我掸粉。
咱俩掸了个油烧饼,你半个,我半个。
你半个吃上了,我的半个给放羊娃留下了。
放羊娃来了要馍哩,馍哪?猫叼了。
猫哪?上坡了。坡哪?雪盖了。
雪哪?消成水了。水哪?和成泥了。
泥哪?抹墙了。墙哪?猪拱了。
猪哪?放羊娃娃拉着杀了。刀子哪?口里噙着呢。
肠子哪?腰里系着呢。尿泡呢?头上戴着呢。
有些催眠曲似乎并不都用诸如人走、归土之类使希望逐渐落空,却多用没完没了的舒缓叙事及其延宕效果,同样使儿童因为逐渐丧失耐心,以致渐入睡眠状态。陇南童谣虽然并不都将叙事的结局直接地归结为无,但没完没了的舒缓叙事实际上仍然贯穿着绕来绕去却无果而终的主题意蕴。也许与此类叙事模式相适应,母亲轻微的拍打和舒缓的吟唱,也恰恰与婴儿的心律相和,以致使儿童在这种吟唱、动作和心律的节奏相和谐的完美乐章中渐入催眠状态。这些催眠曲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大概都与吃饭有关。可见对婴儿来说,吃仍然是最本真、最原始、最基本且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需要。因为这体现的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虽然绝大多数催眠曲常常以无果而终为特征,但也并非都是如此。与这一版本不同的催眠曲,虽然并不直接与吃有关,但仍然不能离开吃的主题,只是将吃这一主题安排于婴儿之外的其他人,诸如亲家、公公、舅舅等,如陇南市西和县《板凳子板》明确指向亲家:
板凳子板,板红花,门儿开开两亲家。
亲家亲家你坐下,我给亲家说话家。
给你装烟,烟园子里没打尖;给你煨茶,茶园子里没发芽;
给你杀鸡公,鸡公叫鸣哩;给你杀鸡婆,鸡婆下蛋哩;
杀鸭子,鸭子跳着后院哩,惹下娃娃大汉乱骂哩。
天水麦积区《闪担歌》也有指向亲家的内容:
闪,闪,闪担哩,亲家来了做饭哩。
吃白面,舍不得,做谷面,丢人哩。
宰公鸡,叫鸣哩,宰母鸡,下蛋哩。
杀鸭子,鸭子飞到后院里,打得核桃枣儿乱溅哩。
陇南市西和县《星宿星宿满天》也有指向公公的内容,如:
星宿星宿满天,那岸院里擀毡。
擀的啥毡?擀的花花毡,擀了个白白毡。
花花毡上倒碗油,白白毡上倒一碗水,叫大姐,叫二姐洗手哩。
洗下的手白拉拉,擀下的饭哗啦啦。下着锅里莲花转,捞到碗里一根线。
阿公(公公)吃了八碗半,气得媳妇子把脚拌(使劲跺脚)。
媳妇子你把脚莫拌,灶火里煨下两罐茶。茶罐倒了,吓得媳妇子跑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版本的催眠曲似乎更为有趣,且叙事也似乎更为生动,甚至有着渐趋紧张的特点,但其结局仍然以“媳妇子跑了”的模式归于无,虽然故事的叙事模式略有不同,但与要馍馍的童谣归于无的结构模式基本相同。此类童谣看似可能多了几分世故,且多了几分明显的成人生活气息或痕迹,有些虽然变换人物,不再是亲家和公公,而是变成了舅舅,但舍不得给饭,乃至嘲弄的色彩并没有削弱。如陇南市西和县《扯锯锯》:
扯锯锯,改板板,舅舅来了没碗碗。
舅舅先坐冷板板,没碗舀饭打转转。
看舅舅,没面面,藏在门后挤眼眼。
舅舅气得冒烟烟,我跑到了院里打颤颤。
叫舅舅,你缓缓,喝口热水把肚暖暖。
扯锯锯,改板板,明年给舅舅买碗碗。
还有一首为:
打锣锣,吃面面,舅舅来了吃啥饭?
吃白面,贵得很,吃黑面,丢人哩。
杀母鸡,下蛋哩,杀公鸡,叫鸣哩。
把舅舅关在驴圈里。
舅舅你又没饭吃,你还不走着做啥哩。
另如陇南市文县童谣也指向舅舅:
红箩箩箩面呢,舅舅来了做饭呢,
杀鸡公叫鸣呢;杀母鸡下蛋呢;
擀上一案荞面吃,舅舅吃了涨肚子。
天水市张家川县《砂锅砂》也指向舅舅,如:
砂锅砂,砂把把,舅舅来了吃啥呀?
吃白面,舍不得,吃荞面,推着哩。
宰公鸡,叫鸣哩,宰母鸡,下蛋哩。
宰鸭子,鸭子飞到花园里,花园的门儿关着哩。
舅舅屋里哭着哩,娘家嫂嫂门上听着哩。
在陇东南童谣中,无论是给亲家、公公,还是给舅舅吃饭,都表现出极不情愿的态度,至少使得诸如亲家、公公、舅舅等往往不大满意。这可能是生活困难时期人们节衣缩食生活习惯的一种曲折反映,而且也可能反映出养育婴儿的公婆对待亲家、儿媳对待公公、妻子对男方舅舅的一种态度。但是此类催眠曲无论出于什么态度和动机,对于婴儿来说,只是一种游戏,甚或类似游戏的说辞。也许正由于这种并不能够信以为真或付诸实施的游戏,才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一定的虚拟性甚或自由游戏性质。有些虽然仍然与吃有关,但并不具有特别明确的结果,甚至可能揭示了不同人的不同态度。如一则陇东童谣有云:
乖乖,洋洋,吃肉肉喝酒酒。
走到舅家门,舅——舅——开门来,挡狗来;
你外婆说给娃杀公鸡,你妗子说给娃擀长面;
你外婆说给娃擀长面,你妗子说给娃烧剩饭。
有些催眠曲虽然与吃有关,但并不一定与婴儿有关,甚至可能直接关涉动物,而且往往并不一定以希望落空为结局,倒是以欲望的最大满足为特点。在诸如《月亮光光》中这类童谣最为多见。如陇南市西和县童谣有:
月亮月亮光光,牛娃吆到梁上,
梁上没草,吆到沟垴,
沟垴没牙子,一口一坨子。
如天水市秦州区童谣有云:
月亮光光,把马吆到梁上。梁上没草,吆到沟垴。
沟垴有狼哩,吆到花场里。割花草,喂花马。
花马喂得胖胖的,骑到南疆打仗去。
另一种版本的《月亮光光》则以烧香为题材,如天水市秦州区童谣有云:
月亮光光,满院烧香。
前爹爹后妖婆,打着山里拾柴火。
柴也没,粪也没,拾了一把野鸡毛。
拿到河坝摆去了,一摆摆了三四年,
锯倒檩子砍倒椽。
如陇南市西和县童谣有云:
月亮月亮光光,赵家院里烧香。
烧的啥香?烧的花花香。
花花院里一对蛾,扑楞儿扑楞儿飞过河。
河那边,采角儿。采角儿,像牛角儿。
牛角儿弯上天,媳妇儿就在河那边。
此类催眠曲虽然没有借助舒缓叙事而使婴儿渐入睡眠状态,但较为快捷的节奏,以及打破生活惯例和思维逻辑同样可能达到放下执著进入睡眠状态的效果。因为牛娃吆到梁上的目的是吃草,但梁上恰恰没有草。吆到沟垴的目的仍然是吃草,即便有草但沟垴没有牙齿,按理没有牙齿就不能吃草,只好“一口一坨子”。这几乎与傅大士所谓“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如“锯倒檩子砍倒椽”,“媳妇儿就在河那边”等,在以出乎意料的结果打破惯常生活逻辑的同时,其实彰显了了无所得乃至无得而无所不得的智慧。这确实是值得人们认真领悟的。如陇南市西和县有这样一首《月亮光光》的童谣显然富于禅意:
月亮月亮光光,照着马家房上。
马家房上有狼哩,把娃吓得叫娘哩。
娃娃娃娃不要哭,爷爷给娃打豆腐。
豆腐香,买辣酱;辣酱辣,买枇杷。
枇杷皮,买条驴;驴不走,买条狗。
狗娃呀,吱儿吱儿,把门打得嘭嘭嘭。
开开门,才是你,你是一个磨面的。
在这首童谣中,先是以有狼来吓唬婴儿,必须听从爷爷的劝告,紧接着便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婴儿愿望,但正是在接二连三地满足愿望之时,却又戛然而止,活脱脱提供了一种意想不到但确实能起到抚慰人心至少可克服畏惧心理的结局。也许这里所彰显的是放弃畏惧乃至执著,才可能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的意思。在司空见惯的童谣里其实有许多让人捉摸不透的智慧。尽管可以说此类催眠曲往往只是成人按照婴儿心理特征创作的,只是适合或体现了婴儿心理特征,并不见得便是婴儿心理特征的自觉反映,因为所有这些相沿已久的童谣,并不见得或不可能是婴儿自己创作的。康德认为“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1],紧张期待突然落空乃至转化为虚无,其实还具有醍醐灌顶的智慧力量:使人们在瞬间的强烈反差和对比中认识到,某些看似完全不同甚或截然相反的事物其实有着完全同一的特征,看似全然不同的事物其实具有平等不二的性质。庆阳市镇原县有一首童谣《烟囱烟眼》似乎更具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烟囱烟眼,簸箕扇;桃花女,绣花毡。
两个猫儿打秋千,一打打到平凉府。平凉府里买豆腐。
豆腐香,买辣姜;辣姜辣,买荜卜。
荜卜贱,买牛角;牛角尖,顶上天。天高跌下一把刀。
刀儿快,切芹菜;芹菜长,噎死狼;
狼没血,变成鳖;鳖没蛋,变成燕;
燕没脚,变个老鸡婆;老鸡婆没有鸡嗉子,把老娘活气死。
如果说顶针格的使用常常使陇东南童谣的故事情节更为连贯,也更适合儿童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那么富于想象乃至将奇奇怪怪以致不可能的故事情节按照顶针的逻辑顺序加以安排,而且给予最终的子虚乌有结局,常常会使其富有哲理性韵味。虽然并不是所有童谣都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但基于顶针修辞格的首尾连接式叙事结构仍然是其基本的叙事模式,如庆阳市镇原县另一则童谣《撇花花手》:
撇花花手,买凉酒,
凉酒好,闪闪腰,腰里别了个黄镰刀。
割黄草,喂黄马,
黄马喂得壮壮的,老娘骑上告状去。
告了个啥子状?告了个扁担状。
扁担不会挑水,一挑挑了个鸡嘴。
鸡嘴不会剜拉拉,一剜剜了个瞎妈妈。
瞎妈妈不会养娃娃,一养养了个秃大大。
秃大大不会开铺子,一开开了个大肚子。
首尾连接的叙事结构最大特点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能够最先满足欲望,吊起儿童胃口,使之产生兴趣,继之欲望落空,使之产生更大好奇和兴趣,在起伏中暗合着儿童的生命节律。如果说买凉酒,凉酒好,是对欲望的首次满足,那么,闪闪腰,别镰刀,就是对欲望的再次满足,割黄草,喂黄马,黄马壮,还是对欲望的满足,骑上告状,告了个扁担状,仍然是对欲望的满足。但后面的叙述峰回路转,先是对欲望的肯定,接着便是否定,如扁担不会挑水,是一次否定,鸡嘴不会剜拉拉,是第二次否定,瞎妈妈不会养娃,是第三次否定,秃大大不会开铺子,是第四次否定,最后开了个大肚子,更是最大否定。
如果说庆阳市镇原县的《撇花花手》的否定主要还是因为客观能力不够,那么另一首《滚豆儿滚》则似乎完全是由主观因素所造成的,如:
滚豆儿滚,娶了个媳妇爱搽粉。
粉买上,她不搽,她嫌滚豆儿不买麻。
麻买上,她不做,她嫌滚豆儿不搅醋。
醋搅上,她不调,她嫌滚豆儿不捉猫。
猫捉上,她不挡,她嫌滚豆儿不买棒。
棒买上,她不捶,她嫌滚豆儿不做贼。
贼做上,她不管,她说滚豆儿不要脸。
这一叙事似乎塑造了一个专门刁难丈夫滚豆儿的媳妇形象,她每一次所提要求,其实只是为了更大程度贬斥乃至否定滚豆儿。类似的形象也见于天水市秦州区的童谣《棒槌棒》:
棒槌棒,满院滚,你说男人不买粉。
买来粉,你不做,还说男人不买醋。
买来醋,你不调,还说男人不买勺。
买来勺,嫌把短,还说男人不洗碗。
洗了碗,你不放,还说男人不烧炕。
炕烧了,你嫌烫,还说男人不买糖。
买来糖,你不拿,还说男人不煨茶。
煨下茶,你不喝,还说男人不搧扇。
搧了扇,你嫌凉,还说男人不铺床。
铺了床,嫌不展,还说男人不打扮。
打扮了,你不爱,还说男人不勤快。
勤快了,你还骂,像你这样的婆娘真麻达。
也许媳妇刁难丈夫,只是因为看不上丈夫。陇东南还有一些以寻嫂嫂为题材的童谣,如天水市清水县的童谣《找嫂嫂》:
白鹁鸽,搭柳梢,大哥哥你等我着。
给我找个好嫂嫂,担起水了忽绕绕。
揽起柴来跌倒了,米下锅里煮烂了。
要捞饭,没罩儿,跑着娘家要罩儿。
去时花开来时落,拾个软桃哄娃娃。
哄得大姐会扎花,一扎扎了水莲花。
哄得二姐会纺线,纺车端上满炕转。
哄得三姐会洗锅,跳进锅里去洗脚。
哄得四姐会打场,连枷扛上去打狼。
哄得五姐会锄地,搭个台子会唱戏。
类似的例子也见于天水市麦积区的童谣《白鹁鸽》:
白鹁鸽,搭柳梢,二哥哥,等我着。
我给你攀个好嫂嫂,担水去,风绕绕。
扯柴去,跌倒了,嫂嫂下来我烧锅。
要罩罩,没罩罩,跑着娘家要罩罩。
半路拾了个蔫桃桃,拿回家中哄娃娃。
哄下的儿子会念书,哄下的女子会扎花。
大姐扎了一朵水莲花,二姐扎了一朵牡丹花。
唯独三姐不会扎,扳倒车儿纺棉花。
一天纺了三两八,爹爹背上见人夸。
夸了一骡子一匹马,妈妈背上转娘家。
人们常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总是看轻儿童以及儿童生活的意义,其实看似稚嫩的童谣却往往蕴含着极其睿智的思想。陇东南童谣虽有使愿望一再落空的模式,也有一再满足愿望的模式,但其实都是为了劝勉人们放弃执著以赢得自由解放。所以诸如意想不到或戛然而止的结尾,常常使人豁然大悟。这可能是陇东南童谣最常见的结构乃至结尾模式。如陇南市礼县的童谣《出门碰着姐姐》通过愿望的逐一落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愿望一再满足,从而彰显了一切执著的子虚乌有:
杏核杏核瘪瘪,出门碰着姐姐。
姐姐拉个大黄狗,把姐姐咬了两三口。
姐姐姐姐没了哭,给姐姐买了个水萝卜。
水萝卜没耙,买个锥耙。
锥耙不会锥鞋,买个台灯。
台灯不会点灯,买个板凳。
板凳不会趴下,买个爸爸。
爸爸不会舀水,买个小鬼。
小鬼不会戴帽子,顶头两砲子(木制农具,用来击碎土块之类)。
学者宇文所安对所谓“沉默的美学”情有独钟。他指出:“诗人所以会创造出无言的雄辩,在他自己来说,是因为除了在本来可以继续写下去的地方停住不写外,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在诗文中它表现为演进过程中的间断、裂隙和省略。沉默可以表示其情调、主题、背景或意向的一种突然的转变,读者的注意力准确无误地被引而不发的东西吸引过去。不过,诗歌中最常见的是出现在一首诗的结尾的沉默,在诗的结尾很容易落入俗套之前就同语词分手。这样的沉默为诗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形式,使他可以把诗的不完整作为来自生活世界的一个片断,而发掘出它更深一层的涵义。”[2]也许陇东南童谣最具艺术魅力的便是出乎意料或戛然而止的结尾。这种结尾在宇文所安看来也许是民间抒情诗人迫不得已所采用的最具效力的结尾方式。其实这种结尾方式最突出的艺术效果在于对成人醍醐灌顶般的启迪。叔本华常常将愿望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刹那间的快乐过后又有了新愿望以及为实现这种新愿望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看成痛苦的根源,但在陇东南童谣中,这种痛苦似乎并不存在。虽然人们可以将此类结尾与虚妄联系起来,但其实质也许在于赢得生命的自由解放。所以无论“顶头两砲子”,还是陇南市礼县的童谣《嘎鸦子嘎》“烟雾上来炮响哩”,其实都揭示了相同的道理,无异于对迷误者的当头棒喝:
嘎鸦子嘎,嘎红花,红花院里坐亲家。
亲家亲家你坐着,我和妹妹搞话去。
一搞搞到月明了,拉的白马接来了。
一接接到戏场里,烟雾上来炮响哩。
这首童谣虽然没有以明确方式宣告终归于无的主题,但烟雾与响炮其实仍然有着不可捉摸乃至稍纵即逝的性质,仍然有着无的意蕴。此类童谣可能是成人试图借助希望最终归于无的方式而使儿童放弃执著,以致尽快进入梦乡的寄寓,却也宣告着执著的虚无飘渺与人生的自由之间相悖亦相联系。
有些童谣虽然并不一一否定人的欲望,也不一一满足其愿望,而是以看似稀奇荒诞的情节来揭示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类的主题,常常在超现实的叙事中彰显着某些游戏的成分,尤其凸显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道理。如陇南市礼县童谣《打老虎》:
古今古,打老虎。
老虎吃的面疙瘩,一把打到案底下。
案底下一泉水,湿了姐姐的花裤腿。
姐姐姐姐莫了哭,大大来了买棉裤。
棉裤穿上咬人哩,变个草人哩。
草人斜斜,变个爷爷。
爷爷会剥蒜,一天剥了八斗半。
还说爷爷剥去慢,门担提上打着断(追赶)。
一断断到盐官,吃了一碗咸饭。
类似童谣也见于陇南市西和县:
古今古,三两五。古今湾里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变了个野人。
野人的眼睛斜斜子,变了爷爷子。
爷爷子不睁眼,变了个灯盏。
灯盏没油,变了个枕头。
枕头没花,变了个王八。
王八会剥蒜,一晚夕剥了二斗半。
还说王八剥得慢。
这种修辞手法和叙事模式,所彰显的是滑稽荒诞的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游戏性。这些荒诞故事看似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但也启示人们,看似极其真实的现实世界仍然不过是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世界。如天水市秦州区童谣有:
古今古打老虎,老虎扎的红头绳,羝羊端的酒壶瓶。
你一盅我一盅,我俩喝了拜弟兄。
你的拜在高粱上,我的拜在窗台上。
你的打了百十石,我的打了一瓦罐。
老鼠揭过就要看,把老鼠打了一门担,打得老鼠不见面。
另一首童谣似乎更荒诞,更能凸显如梦如幻的游戏主题。如:
古今古打老虎,古今湾里拴老虎。
老虎扎的红头绳,羝羊担的酒壶瓶。
你一盅我一盅,两人喝了个醉醺醺。
走呀走到鸡架旁,叫了一声鸡大娘。
鸡大娘穿的云云鞋,扑拉拉飞到锦鸡台。
锦鸡台,女儿多,上槐树,掏鸟窝,鸟儿窝里一条蛇。
大家齐心打蛇来,死蛇掉在树底下。
剥了蛇皮做连枷,连枷做得重重的。
麦子打得净净的,白面磨得细细的。
咚咚咚打起来,又唱歌又跳舞。宝宝快乐又幸福。
如果说催眠曲等童谣只是体现了儿童被动接受的心理,那么游戏常常能够最大限度体现儿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自由自觉的生命意识。儿童的游戏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倾向于在适当场所寻找相应物品的捉迷藏显然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游戏方式。也许正是这种游戏方式典型地体现了蒙台梭利所阐述的儿童心理特征。蒙台梭利有这样的阐述:“如果游戏的目的是快乐(事实上,儿童很高兴重复这种荒唐练习),那就必须承认,在儿童生命中的某一个时期快乐就在于在适当的场所找到物品。”[3]66虽然诸如捉迷藏之类的游戏最接近于蒙台梭利的阐述,但这种游戏见诸童谣的并不多。倒是陇南童谣似乎与捉迷藏有些关系,至少表现了鸦雀无声、深藏不露的情形。如陇南市西和县童谣有:
猪八戒,十五岁,把一个老头儿叫安徽。
安徽安徽不知道,爸爸教你三句话:
一不许动,二不许笑,三不许露出大门牙,
四不许放屁打电话,五不许露出小脚丫。
在这一童谣中,虽然没有较为明晰的捉迷藏性质,但告诫儿童不得出声的情形类似于捉迷藏。在童谣中最常见的游戏方式大概是点屁虫。儿童一起玩耍,如果有人放了屁,在没有人承认的情况下,便用点屁虫的办法定夺,而点屁虫只是一个字一个字依序而念,最后一个字落在谁的身上,谁便被认定是放屁的人。这种结果谁都知道只是与参与点屁虫的人数及起始点有关,并不一定是真实的结果。如所谓:“点,点,点屁虫,家家户户过事情;一碗麸子一碗米,放下屁的就是你。”类似的童谣还有割韭菜、整火盆、弹棉花等游戏,如云:“割,割,割韭菜,割了三石五口袋;我吃细箩儿过下的,你吃荞皮拌下的。”虽然诸如此类的童谣,指向往往有分别,但这种分别可能没有实际意义,至少不与成败得失密切相关。
有些游戏明显带有一定竞争性。如挤鳖娃,拥挤在一起的儿童,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保证自己不被挤出来,但确实被大家挤出来,以致被指称为鳖娃,其实也是无所谓的,大不了当时成为大家所取笑的对象,但游戏过后,不会有人再计较这一结果。其童谣有云:
挤,挤鳖娃,
挤不过了叫三大(三叔);
三大叫不喘,把娃撂得远。
另外,如“背板,腰闪;馍馍香,豆腐香,我俩坐下一商量”的背板游戏,常常使二人背对背,一替一换背起对方,谁没有耐力,就可能最先败下阵来,但同样没有人长时间计较于力气和耐力的大小,充其量只是一时取乐而已。其实重要的就是取乐一时,保持天真无邪、生动活泼的生命本真状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似乎诸多童谣恰恰是人生的寓言,只是这个寓言并不在童谣的言辞之中,而往往显现于言辞之外,甚至呈现于诸多游戏活动之中。
如席勒、康德等之所以看好游戏,便是因为游戏往往有着较之现实活动更为自由的性质和特点。如果说人类生命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赢得自由解放,那么这一自由解放虚拟的实现方式便是游戏,以及类似于游戏活动的艺术创作活动。因为现实活动势必涉及活动的结果,作为现实活动的结果必然有成败得失之类分别,至少作为活动者不得不考虑。但对游戏而言,则无需过分执著于结果,因为无论成败得失其结果都具有虚拟性,都归于无果而终。这才是游戏的终极价值和意义。认真是为有执,无果是为无执,认真而不执著于有果是为无执,无果而又认真是为有执。这也许便是游戏乃至见诸游戏的童谣等有着无执而有执,有执而无执,乃至有分而无分、无分而有分的哲学智慧的体现。
惟其如此,显现于童谣中的游戏活动自然免不了虚拟乃至自由的特点,而且这种虚拟乃至自由有时候似乎与游戏没有直接关系,但其中玩耍的性质和诙谐幽默的特点却表露无遗。如陇东童谣所谓:
美国大鼻子,偷吃中国然糜子,
雀儿粑(拉屎)了一鼻子,跑到河里洗鼻子,
河马弹了一蹄子,跑到医院看鼻子,医生片了一刀子,
跑到铁匠跟前焊鼻子,铁匠叮咣两锤子,
跑到木匠跟前修鼻子,木匠安了个木鼻子。
类似的版本在陇南童谣中也有:
我是美国的长鼻子,来到中国的凉荫子。
辣椒茄子西红柿,给我瀌(喷射)了一鼻子。
我在河边洗鼻子,毛驴过了一蹄子。
把我送到医院里,给我一颗糖果子,
我给换上了一条三角裤衩子。
在这两个不同的版本中,虽然叙述人称有所不同,但无疑都是嘲弄美国大鼻子的,这里并不见得有多少排外思想,倒是说明白种人高大的长鼻子确实给中国儿童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使其成为他们关注和凝视的生理特征。蒙台梭利这样阐述道:“儿童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那些我们毫不关注的小东西,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存在精神生活的证据。但是,被小东西吸引并全神贯注于它的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些小东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是因为对它的凝视表现出一种富有情感的理解。”[3]78从这一意义上讲,童谣中出现的美国大鼻子,实际上倾注着儿童“富有情感的理解”,只是这种理解中不乏好奇淘气的成分,而且看似连环套式的戏弄仍然以无果而终。也许正是这种无果而终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并不执著,以致享有无限自由的精神表征。人们总是以为奇特的童年常常是令人欣慰的,其实默默无闻乃至寻常无奇的童年更能彰显出人类心灵世界的本来面目。由于童年往往充满梦想,以至于常常更能够赋予人们心灵发现的世界,甚或理想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童谣中常常显现得更为充分,以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融为一体。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童谣的世界常常是童心所发现的世界,而且是童心所愿意过甚或值得过的世界的见证。
人们可能认为童年是微不足道的,是手无缚鸡之力,以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时代,其实童年最伟大。这不仅因为童年常常最少受到世俗世界的感染乃至蒙蔽,以致是本心最为清净最为澄明的时代。成人迫于各种世俗原因可能并不便于经常吐露心声,但童年可以没有多少顾虑,甚至也不用那么世故,或即使有些世故,也不必急于掩饰,所谓童言无忌大概便是这个道理。这是因为儿童在没有接受家庭熏陶、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之前一般没有严格的善恶、是非、美丑之类的分别,以致能够最大限度保持原始、淡泊、宁静的本心,也能够最大限度发现最原始最本真的世界本来面目。所以老子强调:“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4]72巴什拉也指出:“童年一贯是我们身心中深沉的生活的本原,是与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一致的生活的本原。”[5]157惟其如此,儿童所看到的世界并不仅仅是最理想化的世界,而且是最接近原初状态的本真的世界。也许正是这个世界为文学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和灵感的源泉。有些童谣看似有些世故,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成人生活的自私自利,但因为无所顾忌、天真率直而仍显得富于儿童情趣。
还有一些童谣有着模仿成人生活、向往成人生活的痕迹,如有的陇南童谣实际上表达了对身强力壮、自食其力的向往,如:
脚力攀攀,一攀攀到南山;
南山哥哥会纺线,麻布织了几十担,背上麻布满山转;
拾了一窝野鸡蛋,拿到屋里擀长面,肚子吃的像锅圆。
有些还涉及朦胧的两性意识,如:
月亮月亮光光,赵家院里烧香。
烧的啥香?烧的花花香。
花花院里一对蛾,扑楞扑楞飞过河。
河那边,采菜角儿。
采菜角儿,像牛角儿。
牛角儿弯上天,媳妇儿就在河那边。
弗洛伊德指出:“一个孩子的游戏是由他的愿望决定的:事实上是一种单一的愿望,希望自己是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这种愿望在他被养育成长的过程中很起作用。他总是以做‘成年人’来作为自己的游戏,在游戏中他尽自己所知来模仿比他年长的人们的生活。他没有理由要掩饰这种愿望。”[6]虽然这种模仿有目的,有执著,但由于并不掩饰,又仅是一种朦胧的虚拟性游戏活动,不见得执著于最终的结果,所以仍然不乏自由的性质。如镇原县的另一首童谣同样彰显了无果而终的无所执著的智慧:
拍花花手,卖凉酒;凉酒高,闪闪腰,腰里撇了个黄镰刀。
割黄草,喂黄马,黄马喂得饱饱的,老娘骑上告状去。
告了个啥?告了个扁担;扁担不会担水,一担一个鸡嘴;
鸡嘴不会剜拉拉,剜上拉拉喂妈妈;妈妈不会生娃,一生一个秃娃。
每一个儿童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赤子之心,所以说每个儿童都是令人惊讶的存在,并不为过。巴什拉也指出:“在童年的某个时刻,任何的孩子都是人类惊讶的存在,都是实现存在的惊讶的人。”[5]146这是因为每个儿童都可能保持着无所执著乃至无所分别和取舍的清净之心,都可能保持着人无弃人、物无弃物的赤子之心,至少较之成人有着更为明白四达的智慧,如老子所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4]138。蒙台梭利指出:“儿童的建设性活动有一种精神起因,它们具有一种智慧的性质。当一个儿童要做某件事时,事先他已经知道这是什么。”[3]91许多人以为儿童的活动是漫无目的、毫无道理,甚或荒诞离奇的,其实儿童的活动有着成人所无法预料的目的性,只是这种目的性并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保持着人类最原始、本真的哲学智慧,虽然这些哲学智慧不见得体现为概念、判断和推理。
有些童谣看似简单无奇,却往往有着化解儿童之间矛盾冲突,维系亲密关系的功能。如儿童之间玩耍,发生争执以致闹红了脸,往往用“鸡儿鸡儿豆豆吃,给鸡儿一颗豌豆吃”之类童谣劝架,使其破涕为笑,重归于好;如果有儿童没高没低,不讲辈分和礼数,便用“打灯蛾儿,黄翎子;不叫哥哥叫名字”之类童谣打趣,使其改口;如果嘲弄了人,便用“哄了,鼻子疙瘩肿了。肿三年,肿四年,寻个刀刀儿剜屁眼”之类童谣来自我开脱,以求重新获得信任。有些童谣甚或有着某种程度的辛酸和无奈,但这种看似辛酸和无奈的童谣却仍然掩饰不住童真的趣味,如:“腊月八,眼前花;还有二十二天过年家。有猪的把猪杀,没猪的打娃娃。娘啊娘啊你莫打,门背后有个猪尾巴,唆得口上油辣辣。”儿童永远是达观的,而且是乐观的。他们的这种生命态度本身值得成人学习。蒙台梭利指出:“儿童自身隐藏着一种生气勃勃的秘密,它能揭开遮住人的心灵的面纱;儿童自身具有某种东西,一旦被发现它就能帮助成人解决他们自己的个人和社会问题。”[3]24如陇南市文县《玲珑塔》所揭示的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
玲珑塔玲珑塔,玲珑宝塔第一层;
一张桌子一盏灯,一个和尚来念经。
玲珑塔玲珑塔,玲珑宝塔第二层;
两张桌子两盏灯,两个和尚来念经。
玲珑塔玲珑塔,玲珑宝塔第三层;
三张桌子三盏灯,三个和尚睡昏昏。
观音发现生了气,罚他三个念长经。
童谣中的每一首诗歌都可能是人们认识美好世界的一个富于诗意和梦想的窗口,人们应该关注儿童乃至童谣,这不仅因为“童年时代的每种气味都是回忆库中的一盏长明灯”,而且因为“具有诗意的梦想能赋予我们所有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诗的梦想是一个宇宙的梦想。它朝着一个美的世界的开口,朝着一些美的世界开口”[5]18。
如果说城市儿童的生活是有缺憾的,那么这个缺憾便是没有童年,也没有童谣,这使他们从一开始便丧失了通过浅显易懂、活泼有趣的童谣获得精神成长的机会;如果说现代儿童包括农村儿童是不幸的,那么这个不幸便在于本来可以借助有趣的童年获得智慧的启迪,但由于沉重的课业负担,以致丧失了真正的童年;如果说我们的教育是令人悲哀的,那就是以儿童服从乃至符合成人观念和规范的程度来衡量儿童,不仅束缚乃至蒙蔽了儿童富于智慧的心灵,而且也使成人世界永远丧失了复归澄明本心的机会和能力。
[1]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80.
[2]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的往事再现[M].郑学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87-88.
[3]玛利亚·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M].马荣根,译;单中惠,校.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4]奚侗,集解;方勇,导读;方勇,标点整理.老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M].刘自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6]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 [M]//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4.
[责任编辑 张亚君]
2015-07-20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智慧美学的世界视域会通研究”( 12YJA751018)。
郭昭第(1966-),男,甘肃西和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I276.2
A
1008-4630(2015)06-0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