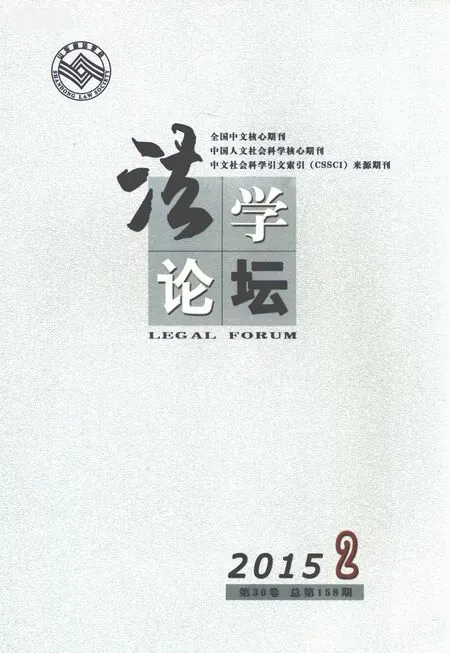先行调解制度重述:时间限定与适用扩张
李德恩
(九江学院 政法学院,江西九江 332000)
先行调解制度重述:时间限定与适用扩张
李德恩
(九江学院 政法学院,江西九江 332000)
法学界对于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先行调解规定的理解及实施还存在较大争议。调解之“先行”必须与特定的时间节点相比较才有意义。从体系解释及术语使用规范的角度解读,先行调解是当事人将纠纷起诉至法院之后,在立案之前进行的调解。先行调解的适用条件“适宜调解”强调的是不能违法调解或不应在案情复杂、当事人对抗激烈之类的纠纷上徒劳消耗资源,是否“适宜调解”宜采取个案判断的方法。人民法院既可以通过立案庭或专门机构实施先行调解,也可以将纠纷委派人民调解组织、行政机构,在先行调解中实现三调联动。调解协议只具有普通民事合同的效力,但通过诉调对接,即当事人自愿选择立案签发调解书和启动司法确认程序两种方式,能够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先行调解;诉讼调解;诉调对接
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以下简称“第122条”)规定了先行调解制度,“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虽然该法实施已逾一年,但法学界对先行调解的理解和相关研究依然存在争议和误区,存在自说自话、与司法实践脱节的现象。本文认为先行调解之“先行”二字是强调进行调解的时间先于某个节点,即先予立案,其立法之首要目的在于将法院调解扩展至诉前,然后在此界定的基础上针对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实施主体以及最终效力展开研究,希望能够在澄清误区、凝聚共识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先行调解之时间限定
(一)先行调解进行时间的误读
在法学界,认为先行调解既可以在立案前也可以在立案后进行的学者为数不少。有法院系统的研究人员认为,“对于先行调解的适用时间并未有所限制,只要是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即可,至于是收到当事人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后、尚未立案之前,还是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后、移送业务庭审理之前,抑或是开庭审理前或者开庭审理后均在所不问。”*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页。立法机关的研究者存在类似的观点,“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主要指向法院立案前或者立案后不久的调解”,“案件受理之后尚未开庭审理前,人民法院仍然可以进行调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理论界的李浩教授也将第122条的先行调解分为两种性质的调解:立案前的调解和立案后的调解。*参见李浩:《先行调解制度研究》,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
以上针对第122条所规定的先行调解发生时间的理解过于宽泛。作为符号的法律术语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情景下才有其特定的含义。*参见程乐、沙丽金、郑英龙:《法律术语的符号学诠释》,载《修辞学习》2009年第2期。对于先行调解这类使用时间意蕴限制词语的术语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先行”之意为先实行、先进行,即先于某个特定时间或程序运行而进行。上述针对第122条的理解都没有明确一个与调解相比的特定时间或特定程序,因而不符合法律的文义解释的基本要求。
(二)基于体系解释及术语使用规范的解读
诚然,《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示先行调解进行的时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该规定所处位置、从法院各种调解形式彼此的关系推导而出。考察第122条在新《民事诉讼法》中所处位置,我们可以发现,先行调解处于第二编“审判程序”、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第一节“起诉后受理”中,而在立案期间要求的条款之前。在逻辑关系上,先行调解之“先”应该是与立案相比较,先行调解也就是在当事人起诉之后人民法院先于立案针对纠纷组织调解的意思。从调解制度的立法体系上看,第122条的先行调解与第133条的审前调解、第142条的判前调解等关于诉讼调解的规定是并列关系,互不包括,共同体现了新《民事诉讼法》对于延伸适用调解的追求。
在将122条的先行调解界定为立案前调解,也就是诉前调解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主张,122条对先行调解这一术语的使用应该具有排他性。新中国的其他立法文件中早已多次出现“先行调解”的字眼,由于语境不同,与调解进行相比较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先行调解的词义明显有别于122条的规定。法学界有学者对此进行总结之后认为,先行调解作为一种程序上的安排,包括三种含义,即作为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非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交错意义上的先行调解。如此解读相关法律规范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不同语境下先行调解的词义。但是,在新《民事诉讼法》出台之后,先行调解已经逐渐被法学界作为术语加以使用。术语的使用必须满足单义性和稳定性的要求,达不到这种要求就会造成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混乱。这就意味着,作为术语使用的先行调解必须存在一个且只允许一个与调解相比较的特定时间,这个特定的时间就是第122条界定的当事人将纠纷起诉至人民法院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如此认定的原因有三:其一,从立法颁布的时间而言,后法优于前法;其二,从立法的层级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优于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其三,先行调解的表述在我国立法中虽然早已出现,但被学术界作为术语广泛使用却是在新《民事诉讼法》出台之后。
概而言之,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而言,先行调解必须与特定时间相比较,其词义随比较时间的不同而变化;而从术语使用规范的角度出发,先行调解应该专指当事人将纠纷起诉至法院之后,法院在立案之前进行的调解。笔者认为,在新《民事诉讼法》出台之后,即使以前立法对于立案之后的调解规定出现了先行调解的字眼,也不宜冠以先行调解的称谓。先于开庭审理、先于法院判决而进行调解的规定可以称之为庭前调解、判前调解,与立案调解、庭审调解一样都属于诉讼调解,它们与先行调解不在同一层级。与先行调解处于同一层级的应该是诉讼调解和执行调解,三种调解方式分别代表人民法院将调解全程延伸至诉前、诉中和判后的努力。
将先行调解界定为立案之前的调解,即诉前调解,并与诉讼调解、执行调解并列,这种分类对于学术研究以及司法实践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三种调解性质上的不同直接导致了调解协议效力上的差异。先行调解发生于立案之前,诉讼程序还没有启动,因此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诉讼外调解,调解协议自身缺乏强制执行力,但可通过后续程序而获得;诉讼调解发生于立案之后判决之前,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可以通过调解书结案,调解书具有与判决相同的强制执行力;执行调解发生于当事人依法启动执行程序之后,执行调解的成功往往以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而呈现,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也没有必要获得强制执行力,原因在于和解协议之外还存在原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为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之时提供强制执行的保障。这体现在新《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款的规定之中,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适用先行调解案件范围之解释
(一)关于“适宜调解”解读的评析
第122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先行调解的案件范围,只是设立了“适宜调解”这一条件。对此应如何解读呢?李浩教授采取的方法是将纠纷划分为三类,“适合先行调解的纠纷”、“不适合先行调解的纠纷”以及“可以先行调解的纠纷”。*李浩:《先行调解制度研究》,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其中“适合先行调解的纠纷”指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确定的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的六类民事案件:(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这种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有学者进一步建议将先行调解的案件类型规定为:涉及相邻关系的纠纷;涉及亲属间的纠纷;事实清楚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涉及共有物的使用和分割的纠纷;符合小额诉讼案件的纠纷等为宜,待司法实践经验丰富之后再进行扩大或限缩。*参见田海鑫:《论〈新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先行调解》,载《西部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
采用以上方法界定先行调解的范围是存在疑问的。首先,李浩教授对纠纷的这种分类是建立在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的范围既涵盖立案前的调解也包含立案后的调解这种认定的基础上,立案后先行调解的案件范围当然也就适用于立案前的先行调解。但如前所述,这种认定本身就不正确。其次,这种分类的标准本身也不科学。李浩教授界定“可以先行调解的纠纷”的用意还是尽量扩大先行调解的覆盖范围。但是,“适合先行调解的纠纷”和“不适合先行调解的纠纷”已经是对于纠纷的一种完全分类,不应存在一种既不属于“适合先行调解的纠纷”也不属于“不适合先行调解的纠纷”的纠纷,在这两种纠纷之外再出现“可以先行调解的纠纷”在逻辑上就难于证成。再次,笔者对根据纠纷类型来界定纠纷是否适用先行调解的做法也持反对意见。总体而言,熟人之间的纠纷比陌生人之间的纠纷、小额的纠纷比大额的纠纷适用调解固然更有必要也更易成功。但这并非绝对,也不能成为除此之外的案件就不能适用调解的理由。起诉到法院的纠纷是否适合调解应该采用个案判断而不是类型划分的方法,这样才不致于遗漏“适宜调解”的纠纷。最后,《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的案件与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存在太多不同之处,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对立法的误读:前者是先于开庭审理而进行的调解,而后者是先于立案而进行的调解;前者仅在简易程序中使用,也就是案件必须符合以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条件,而后者则是针对所有适合调解的案件均可启动;前者是典型的诉讼调解,而后者本质上应该属于诉讼外调解;前者之前的应当二字隐含不必经当事人同意就可启动调解程序之意,只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而后者则明示当事人拒绝调解就不能启动调解程序。
其实,如果使用术语来概括《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六类案件,强制调解比先行调解更加接近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六类案件要求“应当先行调解”,其词义自然包括了调解先于开庭审理进行之意,但更核心的内涵却是通过“应当”二字得以展现,即这些案件在简易程序中,基于修复当事人之间合作关系的目的或纠纷解决费用相当性原理的考量,可以不经当事人同意而直接由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如果将强制启动调解程序的严格的案件适用限制机械套用于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的先行调解,实际上是大大压缩了先行调解适用的可能性。
(二)“适宜调解”之再认识
如果我们认可先行调解的初衷是将法院调解的触角从诉中向诉前延伸的话,也就应该同意,凡是法院可以调解的案件就不应该在先行调解中受到限制,单独限定先行调解案件范围的做法就明显与立法目的相悖而不可取。因此笔者认为,“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并非限制先行调解的范围,而是强调不能违法调解或不应在案情复杂、当事人对抗激烈之类的纠纷上徒劳进行调解。“适宜调解”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案件争议的民事权利属于当事人处分权的覆盖范围,涉及公益的人身纠纷以及非讼案件则不得适用调解。其二,纠纷当事人有调解的意愿,存在调解成功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对于当事人处分权覆盖范围内的纠纷,是否“适宜调解”最好由法官进行个案判断。在对第122条进行解释时,我们应该始终牢记,立法规定先行调解的初衷是对法院调解时间的延伸和扩展。
三、先行调解实施主体之扩张
(一)委托调解与委派调解之区分
当事人将纠纷起诉至人民法院,即可视为当事人已经表达由人民法院处理纠纷的意愿,人民法院成为先行调解的实施主体也就顺理成章。先行调解可以由立案庭负责实施,也可以另行设立负责诉前调解的机构。例如,常州市新北区法院于2006年3月首创设立诉讼服务中心,此后常州中院、江苏高院先后对这一做法进行完善推广。*参见张宽明:《江苏诉讼服务中心“遍地开花”》,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1月10日。江苏省的各级法院已经全部设立了诉讼服务中心,80%以上的人民法庭和部分地区的乡镇社区设立了“诉讼服务站”。诉讼服务中心承担的职能除了诉讼服务之外,还包括纠纷化解和纠纷分流,先行调解当然可以成为其工作任务之一。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先行调解可否由人民法院转介负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加以实施。对于诉前调解的法院转介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给予了肯定。其中第14条规定了立案之前的委派调解: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后,委派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第15条规定了立案之后的委托调解: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后将民事案件委托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协助进行调解。当事人可以协商选定有关机关或者组织,也可商请人民法院确定。
由于委托调解和委派调解在《民事诉讼法》中都缺乏明确规定,再加之两者最终都表现为法院之外的调解组织参与调解,混用委派调解和委托调解、将委派调解纳入委托调解的现象在法学界非常普遍。其实两者在性质和效力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14条对于立案之前使用的词语是委派调解以区别于15条的委托调解,显然是因为“委托”意味着将自己的事务托付他人管理,只有在立案之后,人民法院才取得对纠纷的专属管辖权,可以行使审判权解决纠纷。人民法院同当事人作为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必须受到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调整和约束。人民法院也才因此具备将纠纷委托调解的资格。在委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应以委托人的名义处理事务,因此委托调解成功之后可以由法院直接签发调解书;而委派调解的结果却应以调解协议的形式呈现,想要获得调解书则还须通过法院立案,将诉前委派调解转化为诉讼调解才能实现。鉴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严格区分委派调解和委托调解实属必要。
(二)先行调解中委派调解之适用
法学界对于诉前先行调解能否由法院外的调解组织调解也存在争议。李浩教授认为受理前的调解可“委托”给附设于法院的人民调解室。而赵钢教授的观点则相反,对于第122 条规定的“先行调解”,人民法院并无权力通过“委托调解”或“委派调解”的方式作出处理。其理由在于,“先行调解”时人民法院并没有立案受理,并没有最终取得或者说实现对这个特定案件(其实应称为“民事纠纷”)的管辖权;既然法院自己都尚未立案受理,它又凭什么“依职权”将纠纷委托或委派给其他主体去处理呢?*参见赵钢:《关于“先行调解”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
“依职权”委派或委托调解意味着当事人不能拒绝。在正式立案之前,纠纷还没有处于诉讼系属之下,人民法院确实不能“依职权”将纠纷委托或委派其他主体处理。但笔者认为,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将先行调解的案件委托或委派处理并不意味着先行调解不能由法院之外的调解组织实施。调解与审判在本质上的区别在于调解属于自治的纠纷解决方式。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以法院正式立案为标志,但调解程序能否启动的关键因素是考察当事人自愿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而非法院立案与否。质而言之,是否立案能够决定调解的性质和效力,却不会对调解能否启动产生实质影响。人民法院诉前不能依职权将纠纷委派调解与人民法院经当事人同意之后采取这种做法并不矛盾。按照第122条的规定,当事人明确拒绝的情况下是不能启动先行调解程序的,这样已经足以保证委派调解的启动不会违背当事人意志。
在司法实践中,全国各地法院均存在将诉前调解委派人民调解机构或其他负有解决纠纷职能的机构的做法,诉前调解大量采用委派调解的方式已经是普遍现象。开展学术研究不能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陕西丹凤县法院通过纠纷诉前审查对案件进行合理分流,以调委会为主体,以法官为指导进行诉前调解,调动各方力量包括派出所、司法所、土管所、林业站、综治办、妇联等部门共同调解。*参见李政:《关于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的若干探讨——以陕西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2012年,扬州市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进入诉前调解程序的有16328件,调解成功8270件,诉前调解成功率为50.6%;诉前调解案件成功数占同期新收一审民事案件总数比为28.34%。按诉前调解的方式分,法院附设的调解工作室调解结案4860件,占诉前调解结案数的29.8%;法院对外委托调解案件585件,占诉前调解结案数的3.5%;由法院法官自行调解案件10883件,占诉前调解结案数的66.7%。*参见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诉前调解运行现状及其对先行调解制度实施的启示》,载《人民司法》2013第19期。可见,将社会力量引入诉前调解的司法实践早已如火如荼,并且运行情况良好。第122条一直被视为立法对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的诉前调解的肯定而不是否定。即使从立法者的意图进行解释,先行调解可以适用委派调解也无疑义。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言,先行调解过程中适用委派调解可以更好贯彻各级党委政府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的倡议。出于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需要,“三调联动”机制在200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2013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中一再得到强调。“三调联动”已经被视为接纳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参见李德恩:《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三调联动”》,载《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期。人民法院在其主导的调解中引入社会力量、行政力量的参与,是积极融入三调联动工作体系的具体表现。
四、先行调解与诉讼程序之衔接
(一)立案程序之跟进
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制度使得法院调解向诉前延伸具有了法律依据,必然成为人民法院构建的诉调对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调对接是诉讼和调解的双向度对接,向度之一是调解进入人民法院主导的纠纷解决的整个过程,向度之二是诉讼程序对调解支持和衔接。诉调对接后一向度对于先行调解而言有两方面的意义:调解失败后诉讼程序的快速跟进与调解成功后通过法定的司法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这就意味着,在经过先行调解不能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应该及时立案,启动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调解进行与诉权保障并行不悖。新《民事诉讼法》第123条规定,对于当事人的起诉,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赵钢教授发出疑问,第122条的先行调解是否应遵守七日时限的规定呢?他的回答是应该遵守,不过同时认为如果原告同意,可以在七日时限届满之后继续先行调解。*参见赵钢:《关于“先行调解”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赵钢教授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将先行调解的时间计入七日期限,不过将原告同意继续调解作为例外,可以突破该时限。
如果将先行调解的时间也纳入到七日的立案时限,立案庭将难于从容组织和开展先行调解工作。在原告起诉之后如果实施先行调解,除了调解进行需要时间保证以外,还存在通知被告和调解机构(委派调解)、与被告协商调解时间等问题。与其让时限被突破的例外规定在实践中成为常态,导致七日时限规定有名无实,还不如允许先行调解的时间在法定范围内不计入时限。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普遍规定了先行调解进行的时间。规定先行调解的时间并不意味着不遵守七日立案时限,而只是进行先行调解的时间在法定期限内不计入立案时限,超出法定期限的时间则应计入其中。这样,先行调解的进行在时间上就有了保障,而且不会以侵犯当事人诉权行使为代价。
(二)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之赋予
对于先行调解的效力,有学者主张,由于先行调解是在法院认为案情适宜且当事人并不拒绝调解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旦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主动认可其效力,无须当事人申请。*参见胡晓涛:《关于先行调解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人民法院主动认可调解协议效力表面上方便了当事人,但同时也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将司法为民的真谛“为民服务”演绎为“为民做主”并非处理民事纠纷的正确做法。当事人同意先行调解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同意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更何况由法院认可先行调解的效力,不论是立案后以调解书结案还是通过司法确认程序加以进行,都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的,人民法院主动认可先行调解效力无异于强制消费。
笔者认为,由于先行调解在性质上属于诉前调解,也可以说是诉讼外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只应具有普通民事合同的效力。在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之后,应允许当事人在撤回起诉书和要求人民法院认可其效力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当事人选择后者,人民法院应遵循便民原则,依先行调解实施主体的不同而分别对待。由法院立案庭或其他专门机构组织实施的先行调解,纠纷一直在法院的掌控之下,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可以直接立案并依法制作调解书结案。由人民法院委派人民调解委员或承担调解职能的行政机构等调解成功的案件,鉴于当事人之间已经不存在实体争议,启动非讼程序更加符合立法原理。新《民事诉讼法》在第15章“特别程序”第6节中专门增加了“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当事人可以据此向委派调解机构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程序。为避免或减少当事人在不同法院之间来回奔波之累,应该规定法院诉前只能委派本院所在地的负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这样就能保证受诉法院和司法确认程序的法院是同一基层法院或同一地域的上下级法院,为当事人可能选择的后续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提供很大方便。不论是以立案后以调解书结案还是通过司法程序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都不能认为是先行调解本身具有的效力,而应当理解为是诉调对接的结果,即通过诉讼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通过这种方式,先行调解解决纠纷的实效性将得到很大提高。
[责任编辑:王德福]
Subject:The Restatement about Mediation First System:Time Limit and Application Expansion
Author & unit:LI Deen(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332000,China)
There is much controversial in the jurisprudential circle about the rule of mediation first in Article 122 of the new Civil Procedure Law. The word “first” can show its meaning by compared with a specific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interpretation and the using rule of the terms, mediation first is such kind of mediation which is carried on after the parties file the lawsuit and before the case is registered.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 “suitable for mediation” stresses to prohibit illegal mediation or the consumption of mediation resources in vain. We can make the judgment in every single case. The people's courts can implement the mediation first either by the case acceptance tribunals,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the delegated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he conciliation agreement has the effectiveness just the same as the common civil contract, but the parties can voluntarily entrust the mediation agreement with enforceable effectiveness by making a mediation record or initiating a judicial confirmation process.
mediation first;lawsuit mediation;the mechanism of litigation and mediation connection
2014-11-05
李德恩(1969-),男,四川隆昌人,法学博士,九江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调解制度。
D915.2
A
1009-8003(2015)02-0047-06
基金荐: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3年)规划项目《“调解优先”司法政策研究——以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为视角》(13FX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