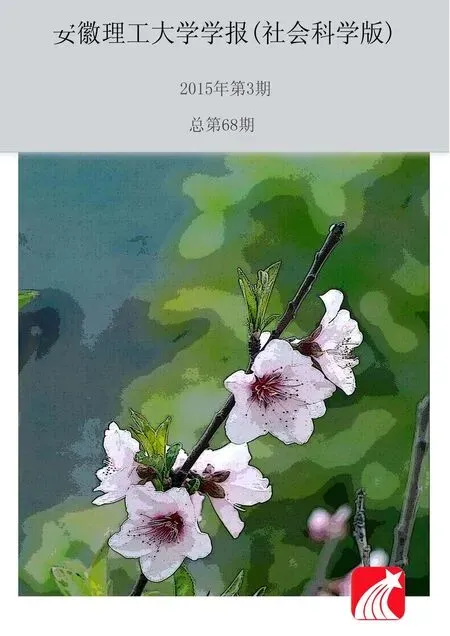宋词“销魂”主题的美学考察
郑 虹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广州 511442)
宋词“销魂”主题的美学考察
郑虹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广州511442)
摘要:“销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学主题,在诗、词、戏曲和小说等诸多文学体裁中都有所体现。它既代表一种情感范式,同时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宋词中的“销魂”,可以从文学源流、审美意象群以及美学意境三个方面展开多种维度的阐释和理解。销魂主题,是中国诗化思维和身体诗学的艺术呈现。
关键词:销魂;源流;意象群;美学意境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人善于运用类比的思维方式,将人的感官、形体以及精神名词赋予外物,从而实现一种物我相融的“通感”效应,这在文学创作和批评方面表现地淋漓尽致,“销魂”便是其中之一[1]。“销魂”在诗、词、戏曲和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中都不乏出处,它的存在既有语言结构层面的实用考量,同时也是审美境界营构不可缺失的一环。“销魂”,亦作“消魂”,同“断肠”、“梦”、“无语”等意象一道,抒发了人的离别之痛、相思之苦以及感念之深,构筑多维的审美空间。
一、“销魂”的源流考察
“销魂”一词的使用最早或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如江淹《别赋》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又有碑记云:“遂丁太妃忧,泣泗消魂,哀号毁骨,水浆不入,扶杖不出,一二年间,几于灭性。”[2]可见,早期的“销魂”语义较为单一,多取悲伤沉痛之意味。
唐代诗歌繁荣,为“销魂”的出场提供一种更为便利的载体。“销魂”的出现频次开始增加,所涵盖的情感色彩也更为丰富,营造一个无限延展的诗学空间。如形容人的离愁思绪:“有别时留恨,销魂况在今。”(钱起《别张起居》)或是人的惊恐万分:“销魂避飞鏑,累足穿豺狼。”(杜甫《入衡州》)以及一种闲逸悠长的情趣:“尽日池边钓锦鳞,芰荷香里暗消魂。”(李舜弦《钓鱼不得》)“销魂”所承载的意蕴变得丰厚,不仅延续了原初深沉蕴藉的心理积淀,并且开始向明朗欢快的审美维度拓展。从创作对象看,诗人们在心理描写、情感抒发、情境合一等方面都有所造诣。
宋代,“销魂”在词的运用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不仅使用频率较高,而且在语义的丰富性、语境的延展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一方面,“销魂”在宋词中具有重要的修辞功能,如秦观的《满庭芳》词云:“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上片采用宏观叙事的手法写景,下片用“销魂”二字转折,抒写离别之无限感慨,点明文章主旨。另一方面,则起到情境的绵延作用,如杜安世《诉衷情》云:“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报黄昏。碧云又阻来信,廊上月侵门。愁永夜,拂香茵。待谁温。梦兰憔悴,掷果凄凉,两处消魂。”全篇描述作者孤身一人,唯有月相伴,词人巧妙地将思念幻化成“两处”,留给人们对于远方之人的无限遐想。
“销魂”主题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经典主题,在五言诗、七言诗和其他词曲形式中都有所展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时期由于戏曲、小说体裁的日臻完善,使得文本内容得以极大地扩充。由于“销魂”在对人物相貌、性格、情态、动作等的描绘上通常起到“言语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因而对其的使用变得更为广泛。如明代张四维的《双烈记?灭醜》云:“神兵到处,闻者即消魂。”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却奁》云:“枕上余香,帕上余香,消魂滋味,才从梦里尝。”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亦云:“宝玉听了此曲,散漫无稽,不见得好处,但其声韵凄惋,竟能销魂醉魄。”从战场、闺房到梦境,“销魂”所出现的情节和场景各不相同,明显增添了明清时期所特有的时代特征——奇幻色彩,目的在于增强读者心理层面的共鸣,丰富人的审美体验。因此,“销魂”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特殊主题之一,深刻地展示了中国民族性思维中的“身体诗学”的艺术韵味。
二、“销魂”的审美意象
文学主题从漫长的文学史中逐步演化而成,是一个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深层积淀和集中展现,通常带有集体性、延续性、隐秘性特征。而同一个文学主题往往由多个趋同的意象构成,因而对于一个文学主题的分析需要多层次、多维度的展开,而非单一向度的挖掘。“销魂”主题下的意象营构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化用,二是互构。即一方面巧妙地转化为魂销、断魂、消凝、醉魄等语用,另一方面则与梦、断肠、无语等意象和修辞相互结合,共同营造余味无穷的审美体验。
“梦”是现实之外的另一种空间,是文学题材发挥的重要场所。梦境中拥有无限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现实中冷酷的必然,弥补文人的各种心理缺憾。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人的欲望的满足,潜意识才是真正的精神现实[3]。
宋词*所引宋词皆出自《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本。里大量的梦境描摹被用来弥合时空隔阂。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为凸显当下和过往的落差,常用对比、衬托等手法。如晏几道的《蝶恋花》:“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却依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词人欲与“离人”在梦里相会,不曾想却寻无所得,梦醒时分更觉失落怅惘,只好抚弦弄筝,全文通俗直白却意味深长,情深意切。再如朱敦儒的《行香子》:“宝篆香沈。锦瑟尘侵。日长时、懒把金针。裙腰暗减,眉黛长颦。看梅花过,梨花谢,柳花新。春寒院落,灯火黄昏。悄无言、独自销魂。空弹粉泪,难托清尘。但楼前望,心中想,梦中寻。”词中刻画的女子慵懒度日,眼前的一切物什已成摆设,毫无兴致可言。春寒料峭,灯火昏暗,独自神伤,只是眺望远方,所有的思绪都化作一番春梦。
文人创作“销魂词”[4]的潜在动机促发了“梦”的产生。“梦”,给“销魂”提供了温床,让文人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寻觅,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但每当梦醒时分,却又陷入更深的惆怅之中,给读者创造了递进的延展空间。
从语法上看,“断肠”之“肠”不是实指而是借代。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5],情感和思维的生发都维系于“心”,是人思考、感受、判断的核心器官,肠、肝、胆、魂、魄等与“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相互指涉。在人的负面情绪和感受方面,“断肠”可等同于“销魂”。柳永的《诉衷情(一声画角日西曛)》:“一声画角日西曛。催促掩朱门。不堪更倚危阑,肠断已消魂。年渐晚,雁空频。问无因。思心欲碎,愁泪难收,又是黄昏。”伴随夕阳西沉,哀厉高亢的画角声响起,贵族豪庭关上红漆大门。词人凭栏远眺,年岁渐晚,大雁南飞,思念之人音讯全无,不禁肠断魂消,感慨为何又到黄昏时候。又如韦庄的《应天长》:“碧天云,无定处,空有梦魂来去。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想象爱妾置身于幽静的深闺,风雨之夜思君心切,埋怨为何音书断绝,无处诉衷肠,惆怅不已,泪沾红袖。这是典型的文人“女性化”写作方式,借“她”之口诉己之思,委婉表达思念之柔情。
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为文化消费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得益于统治者的“崇文”理念,宋代朝野之间的文人士子享乐之风和奢靡之风日盛,各种柔弱、精致、轻盈、艳丽的文学意象纷纷涌现,构成了“销魂词”的基本特质。如欧阳修的《鼓笛慢》更是无所顾忌地表露对侍妾风情万种的深深眷恋:“眼穿肠断,如今千种,思量无奈。花谢春归,梦回云散,欲寻难再。暗消魂,但觉鸳衾凤枕,有余香在。”
情到深处是“无语”。在“销魂”一类诗词中,常常会产生“无语”的境况,或者是“失语”的境地。不是创作者不言,而是难以言表。古代文人不苦求语言的逻辑缜密,而是取“言简意丰”之巧,抒发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把“言不尽意”这一语言表达的缺憾,转换为“言尽意长”的圆满效果。这种创作话语的不足和缺失,更能让人体悟到“销魂”的魂牵梦萦。如柳永的《竹马子》:“向此成追感,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凭高尽日凝伫。赢得消魂无语。极目霁霭霏微,暝鸦零乱,萧索江城暮。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回首往事,一切已成追忆,只好独自凭栏远眺,目送残阳西斜。用景色来替代言语,以无声胜过有声,艺术的审美内蕴便在有限中呈现无限,“无语”修辞体现了文人无以言表的真实心境,同时用艺术的手法将情绪的描摹升华至最佳的层次。时隔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从文本中还原古人的“销魂”感慨,从“无语”的留白想象中获取心灵上的呼应。
由上我们可以发现,“销魂词”中的意象通常是成群的,相互之间构成完整的“物理——心理”情境,而且在文人的情感渲染中不断得到升华。
“意象”是“意”与“象”的完美交融,“情”、“志”即为主观之“意”,“景”、“物”即为客观之象[6]。意象的堆砌不仅不会造成意境的割裂,反而别有一番景致,这是汉语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在“销魂词”中,文人将意象的特点用精炼的词语描绘出来,串联成意象群,意象与意象层叠,画面与画面相接,用最贴切的物象展现深沉的情致。如柳永《竹马子》里的“登孤垒荒凉,危亭旷望,静临烟渚。对雌霓挂雨,雄风拂槛,微收烦暑。”孤垒、危亭、烟雨等组合在一起,风雨飘泊之人的画面如在眼前。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词意的密度,为读者预留充分的想象空间。
“意象”使感情具体化,并渗透了主体的审美理想,在这个过程中“移情”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作者为突出某种强烈的感情,有意识地赋予客观事物一些与自身相一致的特性,大致包含身体的泛化以及情感的泛化两种。“近清明,翠禽枝上销魂。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黄孝迈《湘春夜月》)、“回廊影、疏钟淡月,几许销魂?”(贺铸《绿头鸭》)这些词句里的“销魂”况味都采用了“移情”的表现手法。“移情”是与人的孤独状态紧密相关的审美心理现象,因此,在“销魂词”中,孤云、孤山、片花、独雁反而更能触动人的内心深处。“物我之间的内在共通产生了强大动力,吸引着审美主体去追求”[7],运用“移情”手法,使物我相融,从而更好地传达人的炽烈感情,产生意想不到的接受效果。
三、“销魂”的美学意境
文人情感的寄托和生发有赖于现实的物理场景,但文学主题从来都不会囿于单一的景物描写或是情感抒发。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8],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触景生情才是文学亘古恒存的生命力所在。“销魂词”所酝酿的美学意境,大致有以下三种:
其一是“无语凝噎”的离别场景。古代因战争、迁徙、流放、贬谪、考试、出游等造成频繁的离别,交通不便造成信息传递的延宕,路途艰险则蕴含无时无刻的生命危险。因而,短暂的离别过后意味着长时间“魂牵梦绕”式的煎熬,人的痛苦在离别之际首先集中爆发。宋代词人柳永极擅长写离情别意,表现人内心的“销魂”之苦。以脍炙人口的《雨霖铃》为例,“寒蝉”、“长亭”、“骤雨”、“杨柳岸、晓风残月”集聚了清秋的所有寒气,给情感的抒发提供铺垫,船家的声声催促加速离别的进程,“念去去”三字之后,大气包举,一泻千里,直抒胸臆。以“念”字领起,设想别离后的征程。“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看似写景,实际上深含“景无边”而“情无限”的寓意,更增添了“销魂”的哀婉情调。分别的感伤场景加上晦暗的意象媒介,“销魂”的柔情透进骨髓,给人真切的“魂断”体验。
如果说,柳永在《雨霖铃》里写的是一种深醉,无限放纵的“销魂”之感。那么在《竹马子》中“凭高尽日凝伫,赢得销魂无语”便是一种深沉、静态的“销魂”。“危亭”、“雄风”给人一种急促感,加快了情感的蔓延速度,“孤垒”、“残蝉”的出现制造一种相对的落差感,引发无言的失落。“暝鸦”更是给这种失落氛围增添浓墨的一笔,深深地暗化了色彩及色调,惆怅感达到极致,对故人诚挚而深刻的思念转化为无法排遣的忧愁。
晏几道的一句“离歌自古最销魂,闻歌更在销魂处”(《梁州令》)道尽古今无数“离人”的愁肠。“南楼杨柳多情绪,不系行人住。人情却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以飞絮为喻,慨叹“离别”的无可奈何。文章最后却峰回路转,取顺其自然的态度面对人生的各种“离别”,将沉重的思念瞬间化为温情的祝福。
其二是“断香残酒”的相思场景。“思”或“寄”,是人类最复杂的情感机制之一,求之不得、欲罢不能,这种心理需求上的无法满足能在最大程度上刺激人的情感迸发,再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显得格外得真挚动人。这种相思的“销魂”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新境“销魂”,二是故地“销魂”。
新境“销魂”即是指作者经历离别之后,独自一人在某一特定环境中触发“销魂”的体验,这种情境重在排遣。如李清照的《醉花阴》,这首词是前期的怀人之作。婚后不久,丈夫赵明诚便“负笈远游”,深闺寂寞,她深深思念着远行的丈夫。借惜春悲秋来抒写自己的离愁别恨。从字面上看,作者并未直接抒写独居的痛苦与相思之情,但这种感情在词里却无往而不在。“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句以“瘦”示愁,瘦硬之笔中愁情浓郁。全词未曾使用一个“菊”字,但“菊”的形、香、色却跃然纸上。瘦菊的羸弱姿态与思妇的愁云满面相互映衬,将“一往而深”的相思之情描写得刻骨铭心。
故地“销魂”是指作者重游故地,可以是回忆式的虚游,也可是实地重游。回想昔日之情境,与今日形成强烈对比,在对比中释放惆怅之感。这种回放式的二次体验,是一种追忆、欲罢还休的“销魂”。故地“销魂”可以说是“二次感伤”的心理体验,旨在不断地回忆昔日的场景,这场景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悲喜杂糅,是人的潜意识里想要直面却又逃避的。贺铸的《绿头鸭》的上片即是不断地在回忆与京都艳妓的恋情,回顾“玉人”住所的华丽艳冶与巧闻“彩箫流怨”之音,遂发“回廊影、疏钟淡月,几许销魂”的感慨。晏几道的“睡里销魂无说处,觉来惆怅销魂误”(《蝶恋花》)则是在睡梦红重温别离场景,“销魂”二字,前后重叠,跌宕起伏,倍增绵邈。
其三是“梦归故里”的怀古场景。怀恋故国是特殊的文学题材,之所以能上升到“销魂”的情感高度,一是因为作者将个人际遇融入了这种情感当中,二是对时代幻灭感的深切体悟,自然而然产生“销魂”之感。
张炎的《祝英台近(与周草窗话旧)》:“水痕深,花信足,寂寞汉南树。转首青阴,芳事顿如许。不知多少消魂,夜来风雨。犹梦到、断红流处。”表达了词人在宋亡后的遗民心态,由自己的处境联想到故国的没落,只剩“美人迟暮”的无奈与惆怅。在杜鹃鸟“不如归去”的啼声中归隐,而不似那豢养的鹦鹉般取悦于人。鲁逸仲的《南浦》词云:“好在半胧淡月,到如今、无处不销魂。故国梅花归梦,愁损绿罗裙。为问暗香闲艳,也相思、万点付啼痕。算翠屏应是,两眉余恨倚黄昏。”上阕写景,“孤村”、“惊雁”、“乱叶”、“寒云”等意象,昭显战乱之后的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下阕抒情,“故国”、“梅花”、“啼痕”、“余恨”等无不表露自己浓烈的家国之思,在幽韵的景致里暗藏对痛失家园的愤懑,寄旨遥深,耐人寻味。
综上所述,宋词中的“销魂”主题,是中国诗化思维和身体诗学的艺术呈现。“销魂”作为文学主题的展开,自南北朝始,在宋代形成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峰,构建了数目繁多、意蕴丰富的“销魂词”。“销魂词”深刻描画了宋代文人的悲欢离合,从中得以一窥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更重要的是,在展示宋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同时,“销魂”二字还勾勒出曼妙的人性之美。“销魂”所涵盖的复杂、多元的审美层次,早已超出文学体裁的拘束,也超越了语言本然的悖论。
参考文献:
[1]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1244.
[2]温瑜.宋代“销魂词”及其文学史意义[J].北方论丛,2013(4):31-35.
[3]佛洛依德.释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14.
[4]唐圭璋.全宋词(全5册)[M]. 孔凡礼,补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胡雪冈.意象范畴的流变[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7]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64.
[8]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
[责任编辑:吴晓红]
Aesthetic study on the “ecstasy” theme in the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ZHENG Hong
(Guang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Guangzhou 511442, 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timeless themes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ecstasy” has been embodied in many literary genres, like poems, dramas and novels, etc. It is not only a kind of emotional paradigm, but also a kind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cstasy” in Song Ci can be conduct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iterary sources, aesthetic image groups and aesthetic artistic conceptions. The theme of “ecstasy” artistically represents both Chinese poetic thinking and body poetics.
Key words:ecstasy; origin; images group; aesthetic conception.
作者简介:郑虹(1977-),女,广东汕头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与文化传播。
收稿日期:2014-11-25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3-006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