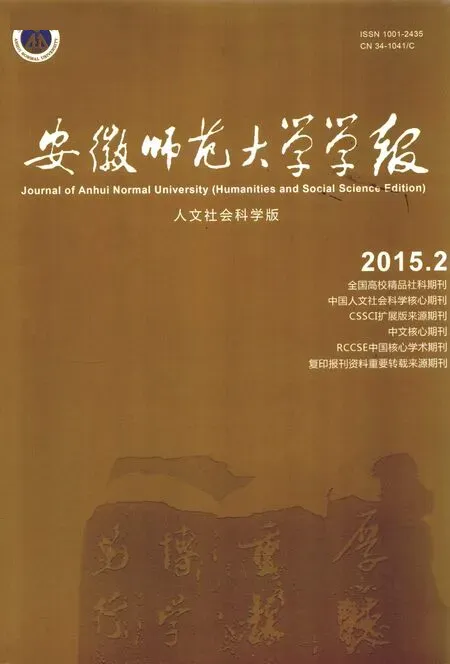未决犯认罪示众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100024)
从古代的斩首示众,到 “文革”时期的批斗示众,再到 “严打”时期的游街示众,尽管饱受非议,示众行为却依然屡禁不止。现如今,又出现了新的形式——将未决犯认罪过程在电视荧屏上示众或是通过网络示众。法院尚未审理,理论上说他 (她)们都是无罪的。既然无罪,让其在媒体上自认其罪,无论是出于自愿抑或是被迫,于法于理都应禁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呼吁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很显然,无论是在露天广场还是电视荧屏再或是网络媒体,将未决犯认罪情形进行示众,都依然属于 “人治”思维,与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相背离。
一、未决犯认罪示众的形式和特性
当前,我国未决犯认罪示众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其一,传统媒体在得到公权力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制作和播出未决犯认罪的节目。其二,以微博为首的新兴媒体所主导的网络反腐的过度曝光。诸多违法违纪的人员被处理可谓大快人心,但是也有学者担忧:有的媒体爆料与事实不符,对嫌疑人 “定罪”的新闻报道不仅与新闻运作规律不符,同时还涉嫌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为了吸引公众的关注,诸多爆料内容太过露骨,会对青少年网民产生不好的影响。其三,公权力机关主导的 “公开逮捕”和 “公开审判”。例如,实践中公安机关逮捕未决犯的过程中通常不给其遮面,让其在公共场所曝光;“公开审判”之时,没有律师在场,甚至让未决犯带着认罪的牌子,五花大绑地跪伏在地。其四,还有普通公众实施的示众,例如比较常见的小偷示众,被偷者抓住小偷后剥光其衣服,将其绑在电线杆上示众;公司员工因违反公司规定而被挂着牌子当街示众;学生因迟到被学校要求穿着 “劳改衣”游校园示众……上述未决犯认罪示众的形式多种多样,却有一些共同特性。
(一)违背现行法律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因此,将已决犯示众等同于 “公开处理”,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将未决犯示众则是违法的。首先,我国 《宪法》明确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行使公权力不仅要严格遵守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还要尊重权力相对人的自由和权利。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剥夺任何个人的人格性权利,因此可以说未决犯认罪示众属于 “野蛮执法和司法”,系一种违宪行为。
其次,案件尚未进入法院审理环节,根据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既然无罪,让其自认其罪,无论是出于自愿抑或是被迫,都违背无罪推定的原则。该行为属于典型的未审先判,而无论是行政机关或是媒体机构都无权对未决犯做出有罪判决,因为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同时,这也与依法治国的理念背道而驰。而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同时也是十八大以及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的重点。[1]
第三,媒体进入看守所拍摄未决犯的认罪视频,不仅违背我国 《刑事诉讼法》和 《看守所条例》的相关规定,还会给接下来的审判工作带来干扰。我国 《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查证,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并且设置了证据排除原则。其中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所有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电视荧屏或是新兴媒体展示的当事人供述,需要检察机关审查和审判机关查证,另外还要经过质证环节。审判程序尚未开始就公开当事人的认罪信息,势必会影响审判进程。
(二)背离人道主义
惩罚的目的①关于惩罚的目的可参见翟中东:《当代国际行刑领域正在发生的变革》,《河北法学》2012年第10期,第39-60页。“不是通过罪犯的受罪而赎罪,也不是威慑可能的欲犯者,而是让罪犯知道社会对他们违法行为的不赞同与谴责。也就是,无论肉刑,还是监禁刑、财产刑、资格刑,都应当将社会的反对的声音带给罪犯”[2]44。很显然,未决犯认罪示众与上述惩罚目的不符。另外,我国刑事司法政策的基本要求就是 “对于违法犯罪人员,不能贬低甚至侮辱其人格尊严,要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给予相当的惩罚”,这项规定与人道主义精神相一致;然而在实践中,“我们至今还没有把人道主义摆到应有的位置上……它既非家庭美德,又非职业道德,也非社会公德,其实它是一切道德的起点,是起码的道德原则。人道主义道德原则,不过是承认每一个人的平等地位,自己是人,他人是人,人人平等。”[3]将未决犯或是已决犯认罪示众,有违人道主义精神。
人道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司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这在诸多国际条约中已有体现。如我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未获得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所以尚未在我国生效。该公约第七条明确规定 “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十条规定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第十六条规定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1988年获得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于当年实施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也规定反对施以令人肉体或者精神遭受痛苦的刑罚。人道主义是世界各国所倡导的精神和基本准则,如果有的国家或地区不遵守,必然要承受相应的制裁或谴责。国家作为有理性的组织体,必然会根据自身的国情做出趋利避害的决策。
从人权的角度看,未决犯认罪示众说到底就是打着法律的旗号侵犯当事人的人权,也正如学者所言:“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强调打击犯罪可能会以削弱甚至牺牲人权为代价。反之亦然,在某种情况下,强调人权保护可能会影响打击犯罪。当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价值相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在一个法治社会,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人权保护放在第一位,打击犯罪不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4]埃德加·博登海默也指出:“只要政府效率不被视为自身的终极目的,就必须将实现人权保护的适当措施视为是一个进步的行政司法的基本条件。”[5]356
(三)彰显符号暴力
媒体参与的未决犯认罪示众,还有一个特征——彰显符号暴力。媒体报道不仅具有传播信息和表达观点的功能,同时还发挥着建构现实与影响公众的作用。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符号暴力理论认为,公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媒体传播的 “看不见的、沉默的”符号暴力。这种符号暴力在新闻节目的表现形式、时间分配和内容限制等方面均有所体现。
由于法制新闻的报道对象多是已决犯或是未决犯,所以与其他类型的新闻报道相比较,若不依法依规报道,其符号暴力特征就会更为显著。如有的媒体机构倾向于将报道的重点放在 “黄”“赌”“毒”等方面,在其报道中已决犯或是未决犯通常都是 “十恶不赦”“罪有应得”或是 “魔头”;或是将报道对象 “标签化”,比较常见的“官二代”“富二代”和 “星二代”等。另外,在有的法制节目录播过程中,无论是问题设置或是后期剪辑,完全由媒体机构主导,报道对象甚至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得不回答预设立场的问题;新闻编辑后,报道对象的话语会被选择性地播放,不免会被断章取义。这种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话语显然是一种符号暴力,不仅对案件当事人是一种伤害,同时还会影响到观众和网民的认知。
未决犯在审判前是无罪的,只是因违反了法律法规,在社会中扮演着反面角色,就要以已决犯的形象示众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侵害,应该予以杜绝。另外,将已决犯示众要按照法律程序公开,否则也会遭受诟病。2013年电视直播 “糯康死刑”案件,便引发了各界的热议和质疑,有学者认为电视荧屏示众与广场游街示众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是 “我国法治文明的一次倒退”[6];还有学者提出此次报道证明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违法且缺少职业道德,同时还欠缺审时度势的政治眼光”[7]。
二、示众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
未决犯认罪示众,对实施主体而言,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对国家而言,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破坏法治中国的形象。那么为何有关部门和媒体机构依然热衷于认罪示众?很多人将其归因于缺乏相关规范,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早在1980年实施的 《刑事诉讼法》就已经规定: “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此后中央政法机关先后下达了很多类似通知,如1984年的 《关于严防反动报刊利用我处决犯人进行造谣污蔑的通知》、1986年的《关于执行死刑严禁游街示众的通知》、1988年的 《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已废止)、1990年的 《关于严格控制在死刑执行现场进行拍摄和采访的通知》、1992年的 《关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等,多次强调:“已决犯、未决犯和其他违法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或变相游街示众”。由此可见,示众行为的屡禁不止并非缺乏法律规范,而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来自 “耻辱刑”传统的影响
“耻辱刑”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诸多国家。据 《汉穆拉比法典》的记载,古巴比伦已有髡刑;据英国 《1547年流浪者条例》,男人和女人能劳动而不劳动的,就在胸前烙上V型烙印,并罚做两年奴隶。如果这些人逃跑,就在他的额头或面颊烙上S型烙印。1551年及1694年的法令,对烙印刑均有规定,直到1829年英国才废除了烙印刑。除了英国,古印度、法国和日本都使用过烙印刑。[8]我国古代也有诸多“耻辱刑”,例如枭首、弃市、象刑、明刑、髡刑、耐刑、枷号刑、墨刑和劓刑①髡刑是指剃除罪犯的头发;枭首是指斩首后将罪犯头颅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弃市是指将罪犯在闹市处死;象刑是让罪犯穿着与众不同的服饰来加以区分;明刑是将罪犯所犯罪状写在板上置于其背;耐刑是指剃除罪犯的鬓发和胡须;枷号刑是让罪犯戴枷锁于监狱外或官府衙门前示众;墨刑是在罪犯的脸上或额头上刺字或图案,再染上墨;劓刑是指割去罪犯的鼻子。等。“耻辱刑”与纯粹的肉刑、自由刑和经济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让罪犯承受精神上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源自耻感和罪感,这在古代熟人社会显得更为突出。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法治观念的更新,“耻辱刑”这种示众性惩罚开始受到激烈抨击。于是许多国家纷纷制定法律法规,禁止对任何人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尽管如此,时至今日这种源自 “耻辱刑”的认罪示众仍然没有完全杜绝,反而是愈演愈烈,由原来的已决犯发展到现在的未决犯。从某种角度来讲,未决犯认罪示众就是 “耻辱刑”的一种衍变形态。
(二)示众有助于普法宣传的偏误
支持认罪示众行为的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教化公众,降低犯罪率。通过示众,可以向公众传达一种观念——如果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是社会的敌人,将会受到惩罚。由于对惩罚的恐惧,人们在犯罪时就会进行权衡,进而得出结论可以遏制公众犯罪的倾向。然而目前并没有研究数据可以确切地证明认罪示众可以降低犯罪率,也就是说从长远效果来分析,示众的目的未能实现。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执法机关采用以公开逮捕、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为主要形式的示众执法无可厚非;但是盲目追求惩戒效果,高举 “打击反革命分子”“震慑阶级敌人”的旗号,将其异化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工具,显然是非正义的。为了扭转治安日益恶化的境况,某些地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常常采用运动式的 “严打”刑事政策,通过将有代表性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示众,来警示公众。不可否认,在短期内可以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让公众了解法律法规,也会起到些许威慑作用。但是,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其道德和情感也会影响其行为;当其感性超越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时,法律法规的约束力也会失去效果。况且违法犯罪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现实中知法犯法的现象屡见不鲜。此时,示众不仅不能显示法律法规的威慑力,反而践踏了公民的合法权利。
(三)示众等同于公开的偏见
支持认罪示众行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示众属于公开处理方式的一种,符合行政公开和司法公开的要求。这无疑是混淆了公开与示众的内涵和目的。公开是依据法律法规将行政信息和司法信息告知公众,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出发点,让公众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公开的对象是行政行为和司法活动。而示众特指当众惩治已决犯和未决犯,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其目的不仅在于威慑潜在的犯罪分子,警示公众,更在于以贬损人格的方式惩处罪犯。很显然,公开并不等同于示众。退一步讲,即使将示众美化为公开处理,也需要考虑其合理限度,我国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均有法定不公开和酌定不公开之内容。
还有支持认罪示众行为的观点认为,示众顺应民意,是公众的呼声。以2014年10月底,发生在湖南岳阳市华容县的公捕公判大会为例,让未决犯挂着牌子站在囚车上游街示众,有媒体报道称 “公众对此拍手称快”。普通公众并非法学专家,他们关注的只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治安状况的良好,对于违法犯罪行为只有感性的认知和判断,对其生成原因和防治策略没有深入思考——示众是不是合法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在他们看来,只要示众直接改善了治安状况,就会持支持的态度或者至少是不反对的态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采用不合法的手段来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最终实现惩治违法犯罪的目的,也不应该倡导。
由此可见,认罪示众的传统仍然没有根除,只是呈现出新的表现形态。与古代直接的示众方式相比,现代的示众方式更加 “文明”,也更加隐晦——透过语言符号来传递,通过网络 “讨伐”来实现。事实上,无论是何种形态的示众行为,都不能给实施者带来预期效果,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三、未决犯示众行为的防治路径
那么,如何预防和治理这类过度的示众行为呢?示众主体主要是行政和司法机关,而媒体机构只是 “帮凶”。为防治和根除示众行为,应该从立法、执法和法治意识等层面着手。
(一)通过立法救济保护未决犯的合法权利
构建并完善权利保障体系和权利救济制度,让未决犯因受到侵权而得到充分及时地救济。例如,修改和完善我国 《国家赔偿法》,扩大权利救济范围。如果未决犯 (也包括已决犯)因为认罪示众行为,人格性权利受到侵犯,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和 《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行政复议或诉讼;还可以根据 《国家赔偿法》提出赔偿请求。具体补偿金额的计算,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另外,通过 《民事通则》和 《侵权责任法》具体条款的增补,增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明确侵权行为的形式和应该承担的责任,让他们的权利得到更好地救济。
立法保护层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宪法地位。该原则对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等人格性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人道主义和人权保护的基本要求。它不应该仅体现在刑事诉讼领域,更应该上升为宪法原则。许多国家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和土耳其等用宪法来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因此,我国也应该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宪法地位,让公权力机关、媒体机构和社会公众重视并在实践中自觉遵守该原则。
针对媒体机构对未决犯未审先判的现象,可以通过专门的新闻传播立法来规范。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启动新闻传播立法工作,并且已经制定出 《新闻出版法》(送审稿)以及后来的 《新闻法》和 《出版法》两个新草案,然而上述法律法规未能颁布实施,主要出于保护新闻自由的考虑。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毫无限制和边界的。正如约翰·洛克曾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9]36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必须依法管理各项事业,新闻传播亦不例外,也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走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如果不能划清新闻报道底线和新闻自由的边界,媒体机构很容易误入歧途,也将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未决犯认罪示众的案例再次提醒我们,媒体监督权的行使应该在合理限度内,杜绝法院未做出有罪判决,媒体报道先给涉案人员定性定罪的现象。为了防止媒体滥用监督权,同样需要法律来规范。2014年11月底,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带来立法的最新进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新闻法治化再次提上日程。通过立法,将法律、道德、社会秩序的底线划清,让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行使赋予的职权。
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实践,我国法律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还限定在民事领域,无法约束非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也就是说只能对抗私权力,而无法与公权力抗衡。今后法律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都应该改变既往的 “维稳模式”,转变为 “法治模式”,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将基本权利的维护作为出发点,将人格尊严的保障作为价值目标。
(二)建立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目前,我国关于惩处示众的立法虽然明确,例如规定:出现示众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要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但是具体罚则却没有细化。这使得示众行为受到法律追究的情况非常少见,多是受到纪律处分,可以说是无违法成本或者说违法成本较低。为减少直至杜绝认罪示众行为的发生,应该制定详尽具体的罚则,让相关人员承担违法违纪的后果,如此才能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与实施效果。根据情节设置不同程度的惩罚,如果情节轻微,让具体承办人和实施者赔礼道歉;如果情节较重,不仅需要追究具体承办人的责任,还需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开除其公职。
此外,还需要通过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和执法程序建设步伐,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外部监督方面,需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程序,健全未决犯的投诉和控诉的审查机制;将各类执法和司法事项的依据、权限、流程、时限、裁量权、责任以及权力相对人的权利等信息进行公开,让媒体和公众进行监督。内部监督方面,加强上级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和总结违法行为,防止和消除随意性和选择性执法现象。
不仅立法层面需要以保护人格尊严作为基本目标,行政和司法机关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并尊重人格尊严。“阳光执法和司法机制”要求公开执法和司法过程,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同时,还需要兼顾到未决犯的合法权利。因此,公开逮捕之时应该使用头套或者口罩给未决犯遮面;公开审判之时,应该有其律师在场,让其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三)树立尊重人格尊严的法治意识
维护和尊重人格尊严,需要执法机关以维护人格尊严为出发点,严格地遵循法律法规,通过文明合法的手段行使公权力,杜绝 “有法不依”的现象。除了法律层面规范执法行为和司法活动以外,还应该借助道德约束和法治意识的提升。实践中,法律与道德约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于一些损害人格尊严但是尚未构成侵权或者违法的行为,就需要道德谴责来约束。法律对人的外部行为产生约束力,而道德作用于人的内心活动;当尊重人格尊严依靠禁止性和强制性规范难以奏效之时,树立尊重人格尊严的意识、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法治社会的构建还需要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进而自我控制。如果我们的执法行为和司法活动本身就是违法,不仅无助于法制宣传和教育,同时还会降低执法和司法的公信力,更会动摇公众对法治的信仰。2012年,腾讯网做了一项 “被公审的尊严”的受众调查[10],尽管只有近40万网友参与,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数据结果显示:50.29%的网民支持;47.32%的网民反对;其余网民持无所谓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仍有不少人赞同示众,这预示着在短期内示众现象还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这就需要我们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在提高自身法律修养和尊重人格尊严的同时,通过不同的渠道向普通公众进行相关宣传和教育,不断引导公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克服示众传统带来的不利影响,让刑罚人道主义、保障人格尊严的观念更加普及。法治意识的生成和培养,还需要通过参与立法和旁听庭审等多种途径,让公众主动参与和亲身体验,感受法治的威严,进而转化为守法的内在自觉。例如,可以充分发挥新兴媒体互动性强的优势,通过以案说法论理、专家学者释法和律师当面辩论等形式,让公众积极参与论案评案,对于提升其法治和人权的意识和观念大有裨益。
综上,认罪示众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被沿用至今,不仅违背现行法律、背离法治精神,还侵犯未决犯和已决犯的合法权利,同时会对其亲属带来伤害。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社会治理
主体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坚守法治精神,因此,建设法治化国家,不仅需要依法规制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让其在阳光下实施;同时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也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行使新闻自由权,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当然,还需要普通公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我的法律素养和维权意识。经过几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信未决犯认罪示众的现象就可以减少,最后彻底杜绝。
[1] 王姝.四中全会10月召开[N].新京报,2014-7-30(A05).
[2] D.Garland.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3] 黄枬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10.
[4] 陈兴良.“严打”利弊之议[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5):120-123.
[5]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 徐迅.一次“死刑犯的电视游街示众”——“糯康死刑直播”批判[J].新闻记者,2013,(4):51-52.
[7] 陈力丹.传媒要有法治意识和对大局的政治把握——央视“生命倒计时”现场直播分析[J].新闻界,2013,(12):21-24.
[8] 杨鸿雁.中国古代耻辱刑考略[J].法学研究,2005,(1):127-138.
[9] 洛克.政府论:下册[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0] 腾讯网.被公审的尊严[EB/OL].(2012—04—06)[2014—12—04].http:∥page.vote.qq.com/?id=2026146&result=yes&to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