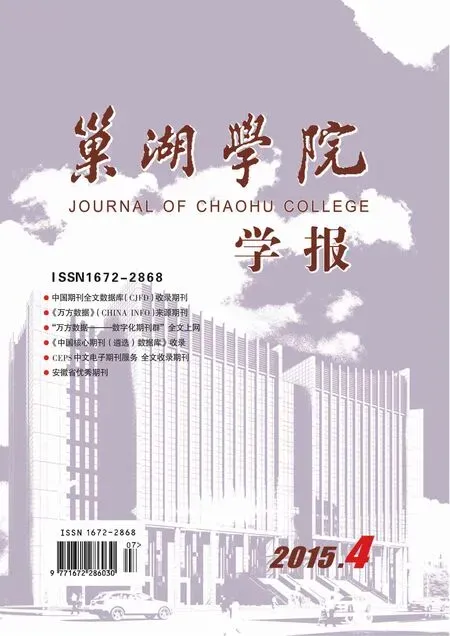生命苦闷的象征——曹植后期诗综论
刘伟安
(昭通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生命苦闷的象征——曹植后期诗综论
刘伟安
(昭通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昭通657000)
人生后期的曹植至少受到了来自以下四个方面的困扰:遇谗被疏,性命之忧,四处迁徙和有志难伸,并因此体验到了巨大的生命苦闷。上述状况对曹植后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其笔下的事物皆染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我们若要全面而形象地理解曹植后期的悲剧性生命处境以及由此引发的生命苦闷,则仅仅从其部分直抒胸臆的诗篇求之显然不够,也许其数量众多的咏物诗、闺怨诗、游仙诗等才是更好的考察对象。因为从本质上说,这些诗歌均是生命苦闷的象征。
曹植;后期诗;生命苦闷;象征
日本现代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深刻指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1]如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为界线将曹植的人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厨川白村的这一论断用之于其后期诗歌的创作可谓恰如其分。据《三国志》等史书记载,曹植早年的人生顺遂得意。由于才华杰出,他曾深受曹操青睐。但不幸的是,曹植卷入了他本不应当卷入的太子之争,且以失败告终。太子之争的失败给曹植带来了异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曹操去世后,失去庇护的他一直受到了魏文帝曹丕及其子魏明帝曹睿的猜忌、防范乃至迫害。概而言之,人生后期的曹植至少受到了来自以下四个方面的困扰:遇谗被疏,性命之忧,四处迁徙和有志难伸。
人生命运的转折极大地改变了曹植的个性、情感以及生命体验。早年的曹植乐观开朗、恣性任情、风流自赏,但后期的他则始终在无边的哀怨、忿怼、压抑、失落中挣扎,体验着巨大的生命苦闷。而个性、情感以及生命体验的改变又对曹植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其早期诗歌主要是叙写游宴,流连光景,感激恩宠,歌功颂德,充满了昂扬乐观的精神,那么其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则是抒写心中的忧愤与苦闷。在曹植的后期诗中确有直抒胸臆的,如《怨歌行》、《赠白马王彪》等皆是,不过此类诗篇所占比例并不大,且多具有“愤而成篇”的性质,主要表达的是曹植在特定遭遇下的诸如怨怼之类的情感体验,因而尚不足以让我们对其后期的生命处境以及生命体验有一个完整性的了解。虽说人类的情感体验与生命体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截然分割,但两者其实是有所差异的,总体而言后者要比前者更深刻,更持久,更复杂也更具有整体性和本原性。生命体验深者,其情感体验必深;生命体验浅者,其情感体验亦必浅。虽然曹植后期诗中几乎每一篇都既表达了情感体验也表达了生命体验,但毕竟有所侧重,那些直抒胸臆式的诗篇侧重的是前者。我们知道,曹植是一位主观性极强的作家,“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此语形容他后期的创作可谓十分贴切。因此我们若要全面而形象地理解曹植后期的悲剧性生命处境以及由此而体验到的生命苦闷,则仅仅从其部分直抒胸臆的诗篇求之显然不够,也许其数量众多的咏物诗、闺怨诗、游仙诗等才是更好的考察对象。毕竟,曹植后期许多咏物、闺怨等题材的诗歌表面上抒发的虽是外界事物如转蓬的苦闷,他人如思妇、弃妻或美女的苦闷,但曲折含蓄地传达出来的实乃自我的苦闷。而其游仙诗抒发的虽是对于游仙的向往,但折射出来的依然是曹植自身在囚徒般的现实处境中所体验到的苦闷。综合分析曹植后期的咏物、闺怨以及游仙等题材的诗歌,即可发现它们至少传达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生命苦闷:
1 “流转无恒处”的漂泊苦闷
曹操去世后,曹植受到了曹丕父子连续不断的迫害。这种迫害是多方面的,如曹丕一上台就借故将被视为曹植的所谓羽翼的丁仪、丁廙并其男口诛戮,且迫令曹植离京前往其封地。黄初二年,曹植甚至差点因监国谒者灌均奏其“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而被治罪,幸亏卞太后干预,才留得一命,被贬爵安乡侯。而为了防备包括曹植在内的同姓诸侯王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根据地威胁到其统治地位,曹丕父子还采取了削弱他们的实力,且不让他们在某地长期定居的措施。史学家陈寿曾指出:“魏世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止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而曹植又“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曹植在其《迁都赋序》中自述:“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在曹植后期的诗歌中,这种因“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而产生的漂泊的生命苦闷被沉痛地抒发了出来,如《杂诗六首》其二:
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
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
转蓬离弃了本根,四处漂泊,不知会被狂风吹向何方,唯一知道的是天路无穷。而捐躯从戎,远离故乡的游子也是有类转蓬,毛褐不完,薇藿不充,饥寒交迫,只能在沉重的忧伤中渐渐老去。而转蓬和游子的遭遇象征的实际上就是曹植自身的命运,转蓬和游子的苦闷也就是曹植自身苦闷的写照。更为沉痛的则是《吁嗟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
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
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严格意义上说,本诗虽然通篇写的是转蓬,但并不是咏物诗,而是以物自喻的寓言诗。诗歌描绘了转蓬离弃本根之后,东西南北,漂泊不定,忽而入云,忽而沉渊,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只能任人摆布的困境。转蓬的命运是如此,处于人生后期的曹植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时时在四处漂泊的困境中挣扎,不知何年是个尽头,只能借转蓬之口哀怨地感叹:“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以至于他宁愿如中林草一样,在秋天到来之际被野火焚烧,忍受糜灭之痛,也要与根荄连在一起。从中可见,东西南北永无终期的漂泊生涯给曹植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精神痛苦!
2 “贱妾当何依”的被弃苦闷
早年的曹植深受其父曹操的宠爱,拥有大量志同道合的友人,且经常置酒交游,吟诗作赋,斗鸡走马,声色娱情,正如其《箜篌引》所云:“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而其《名都篇》亦云:“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此时的曹植是诸多友人众星捧月的中心,自然不会产生被弃感,但人生后期的他就不一样了。按照当时魏国法制,诸侯王受到的禁锢甚严,极少有相互来往的机会,以至于曹植哀叹:“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惟妻子。”(《求通亲亲表》)等于是被打入了冷宫。更甚者曹植还随时处于“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赠白马王彪》)的险恶政治环境之中,动辄得咎。就如蒋寅先生指出的,后期的曹植“最终实际上是陷于一个无君可事,无业可为,无人可友的境地。”[2]因此,他的心灵深处有一种生命被废弃的苦闷。这种苦闷通过其闺怨诗得到了抒发,如《七哀诗》云: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君”者,曹丕父子也,“贱妾”者,曹植自喻也。“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独栖”,独守空闺的孤妾是多么热切地企盼着游子归来,可是这种企盼总是一再落空。同样,曹植是多么希望曹丕父子能够回心转意,注重骨肉之情,重新亲近自己啊,可是无论他怎样忠心耿耿,怎样幻想着“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也无法感动曹丕父子。“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贱妾的苦闷不也就是曹植的苦闷吗?他并非不欲向曹丕父子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正如其在《当墙欲高行》中感叹的:“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愦愦俗间,不辩伪真。愿欲披心自说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除了在被废弃中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曹植还能何为?刘履在《选诗补注》中云:“《七哀》诗,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信然!又如《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
在昔蒙恩惠,和乐如瑟琴。何意今摧颓,旷若商与参。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
新人虽可爱,无若故所欢。行云有返期,君恩倘中还。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诉?
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发箧造裳衣,裁缝纨与素。
诗中女主人公“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曾经“恪勤在朝夕”,结果却是“无端获罪尤”,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无情地冷落了,遗弃了。回想“在昔蒙恩惠,和乐如瑟琴”的恩爱欢乐的场景,再比照“何意今摧颓,旷若商与参”的现实,她真是心乱如麻,坐立不宁,一个“何意”的感叹不知包含了多少被无情遗弃的伤痛、屈辱和苦闷!但曾经恩爱的丈夫早已变心,自己的愁苦又该跟何人诉说呢?想到日月易逝,人生将老,她不禁泪下如垂露,只好通过“发箧造裳衣”来排遣苦闷,打发光阴。而曹植披肝沥胆,忠心为国,换来的却是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不也是无端获罪尤吗?而其被疏远乃至被抛弃的命运与诗中的弃妻又何其相似!陈祚明说此诗“应是自寄思恋之怀,故慨然于年命之不俟,缠绵悱恻。”(《采菽堂古诗选》卷六)可谓知言者也。
3 “盛年处房室”的促迫苦闷
如果说建功立业是汉末三国那个动荡时代里众多士人的共同理想,他们普遍将其视为让生命不朽的最重要途径,那么“生乎乱,长乎军”,从小受到其父曹操的旷世功业耳濡目染的曹植就更不必论了,他几乎将建立不朽功业视为生命的全部意义。如其《与杨德祖书》云: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在强烈的建功立业理想的驱动下,人生后期的曹植甘冒被猜忌的风险,不断向曹丕父子献诗明志,并一再上表求自试,如《责躬诗》云:“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圣皇篇》云:“思一效筋力,糜躯以报国。”在《求自试表》中曹植更是恳切地表示自己的理想就是“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以讨伐“违命之蜀”和“不臣之吴”,若能“虏其雄帅,歼其丑类”,则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那一首首《责躬诗》、《圣皇篇》,那一份份《求自试表》、《陈审举表》几乎是在哀求曹丕父子:给自己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即便战死疆场也胜于闲居丧志。但无论曹植怎样哀求,曹丕父子都置若罔闻。据《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载:“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翼试用,终不能得。”这也难怪!猜忌之心极强的曹丕父子怎么可能放心让曹植领军出战,建功立业呢?正如清人吴淇指出的,曹植一再求自试,而且“请之于罹罪之余,非徒无益,更深文帝之忌耳。”(《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曹丕父子不但不可能让曹植执掌兵权,反而会更加严密地监控防范他。在受到曹丕父子猜忌的情况下,曹植唯一能做的就是废置闲居而已。这对视建立不朽功业为生命最高甚至全部价值的曹植而言,是一种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对他昂扬的生命力又是一种多么严酷的压抑!“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赠白马王彪》),“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临观赋》),“信有心而在远,重登高以临川。何余心之烦错,宁翰墨之能传?”(《幽思赋》)眼见有限的生命时光一天天虚掷而去,曹植心中所体验到的时光促迫的苦闷也越来越强烈。在其后期诗歌创作中,曹植借美人之迟暮将这种苦闷一再曲折含蓄地抒发了出来,如《杂诗六首》其四: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孔子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人命如露,年华易逝,但曹植却只能如“容华若桃李”的南国佳人一样虚耗生命,眼见“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其内心的苦闷又当几何?又如《美女篇》云: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这位容华耀朝日的绝代美女痛感“求贤良独难”,因而深深体验到了一种青春不再,盛年将逝的苦闷。郭茂倩评论《美女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乐府诗集》卷六十三)其实更具体地说,诗中的美女实乃曹植自喻也,美女不嫁隐喻的则是自身的怀才不遇,只不过写得含蓄委婉,意味深长。诗歌结尾处云:“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何其生动地抒发了曹植那种时光促迫,功业未成的生命苦闷啊!前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清人王尧衢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古唐诗合解》卷三)而刘履亦评论《美女篇》说:“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选诗补注》卷二)
4 “九州不足步”的拘囚苦闷
正如上文所说,处于人生后期的曹植虽名为藩侯,实则无异于“圈牢之养物”。而我们知道,渴望自由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天性。一个人的生命受到的拘束越严酷,则其对自由的渴慕也就会越强烈,曹植也不例外。在生命被近乎拘囚不得自由的状况下,后期的曹植创作了一系列游仙诗,表达了对游仙的向往。如《游仙诗》: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
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登玄渚,南翔陟丹丘。
此诗中的“松乔”乃赤松子与王子乔,皆传说中的仙人,“鼎湖”则是传说中黄帝乘龙升天处。在诗中曹植痛感人生短促,且戚戚寡欢,因而幻想如赤松子、王子乔、黄帝一样蝉蜕成仙,翱翔九天之上,东西南北,随意所至。又如《五游咏》:
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
华盖芳晻蔼,六龙仰天骧。曜灵未移景,倏忽造昊苍。阊阖启丹扉,双阙曜朱光。
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伏西棂,群后集东厢。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
踟蹰玩灵芝,徙倚弄华芳。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
曹植痛感 “九州不足步”,因而 “愿得凌云翔”,并由此展开了丰富奇妙的想象。他想象自己驾着六龙来到仙界,在天宫的殿堂里尽情游览,受到了上帝、群后以及众多仙人的热情款待,并且服食了仙药奇方,因而得以延寿无疆。清人丁晏在《曹集铨评》中评价此诗云:“精深华妙,绰有仙姿,炎汉已还,允推此君独步。”
游仙乃是古代尤其是魏晋时代的诗人们常有的一种幻想,非独曹植为然。但在不同个体身上,激发游仙幻想的原因不尽相同。曹操也写有不少游仙诗,如《秋胡行》:“愿登泰华山,神人共与游。”但那是在建立了不朽的政治功业,即获得了世俗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渴望生命的永恒和逍遥。曹植则不一样,他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建立任何可以名垂青史的世俗功业,而且从本质上说他也并不是神仙家之流的人物。在早年作的《辨道论》中他曾痛斥“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为“虚妄甚矣哉!”其《赠白马王彪》亦云:“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但其后期“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的处境却终于使他产生了“翱翔九天上”、“逍遥八紘外”的游仙幻想。知人论世是解读文艺作品的一个基本原则。考虑到曹植后期近乎“圈牢之养物”的生命状态,我们就可知其游仙幻想的本质是对生命之自由的渴慕和追求。正如清人朱乾所说:“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太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亦有取焉。”(《乐府正义》卷十二)
一般而言,幻想固然具有积极作用,就如现代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的:“幻想是取得心理平衡和心理补偿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3]但对曹植而言,痛感“天命与我违”(《赠白马王彪》)的他越知道神仙为虚妄,其游仙幻想的悲剧意味就越浓重。其《远游篇》云:“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但试问曹植果真能胁生双翅,离弃中州,飞上昆仑吗?可见,曹植在现实中囚徒般的困境并不会因为游仙幻想而有任何改变,其内心的拘囚苦闷只会与日俱增,成为了一种无法解脱的漫长的精神煎熬。这种囚徒困境彻底扼杀了曹植曾经如火一般旺盛的生命力,让他以四十一岁的盛年赍志而殁,抱恨终天,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叹惋。
结语
曹植本非等闲之辈,自许甚高,其终极追求乃是 “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求自试表》),这种终级追求的目标在于张扬生命,使之克服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获得永恒价值,而他又偏偏遭遇了异常严酷的拘囚和压抑,只能在岁月的流逝中徒然老去。于是生命力的压抑与张扬之间形成了尖锐且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长久地激荡着曹植的心灵,使之充满了苦闷。这种苦闷是生命被拘囚不得自由的苦闷,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苦闷,亦即渺小而短促的个体生命将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地湮灭的人生大悲。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而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也指出:“对于人生,有着极强的爱慕和执着,至于虽然负了伤,流着血,苦闷着,悲哀着,然而放不下,忘不掉的时候,在这时候,人类所发出来的诅咒、愤激、赞叹、企慕、欢呼的声音,不就是文艺吗?”[1]可见,文艺绝不仅仅是供人玩弄的小摆设,它是人类的生命体验的产物。而在所有的生命体验中,苦闷又是最易为人们所普遍感受到且最足以激发文学创作欲望的一种。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曹植后期的咏物、闺怨与游仙诗不但表达了丰富的情感体验,更表达了更深层次的苦闷的生命体验。当然,在文学创作中苦闷乃至其他各种生命体验或情感体验不一定非要直接倾泻出来不可,委婉含蓄地抒发出来,也许更符合审美的要求。正如法国十九世纪著名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指出的:“直陈其事,这就等于取消了诗歌四分之三的趣味,这趣味原是要一点儿一点儿去领会它的。暗示,才是我们的理想。”[4]而我国当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写景诗宜于显,言情诗所托之景虽仍宜于显,而所寓之情则宜于隐。”[5]“显则轮廓分明,隐则含蓄深永。”[5]由于人生后期的特殊处境,曹植虽强烈地体验到了包括漂泊、被弃、促迫以及拘囚在内的多种复杂的生命苦闷,但未必都能直接倾诉出来,于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便以咏物、闺怨与游仙等题材来含蓄诉说之。也正因为如此,曹植后期诗中的诸如转蓬、思妇、弃妻、美女、仙人以及其他许多意象,大都具有比兴、隐喻或反衬功能,寄托着他的苦闷却又并不明言。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植虽非第一个大量运用比兴、隐喻和反衬这些修辞手法从事诗歌创作的诗人,但第一个大量运用比兴、隐喻和反衬来象征且抒发自我的生命苦闷的诗人则非他莫属。通过象征来掩抑吞吐地抒发自我的生命苦闷于曹植有两种效果:既不触犯曹丕父子的忌讳,又使其诗更富于含蓄蕴藉,余味曲包的文学意味。众所周知,曹植的诗歌尤其是后期诗歌受到了后人极高的评价,如钟嵘在《诗品》中称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而追根溯源就不难发现,曹植后期的诗歌之所以取得那么高的艺术成就,具有那么强大的感染力,除了他本人所具备的天下才共一石而独得八斗的卓越文学才华以外,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不是无病呻吟,亦非游戏笔墨,而是生命苦闷的象征。
[1](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1、24.
[2]蒋寅.主题史和心态史上的曹植[J].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5-12.
[3](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3.
[4](法)马拉美.谈文学运动[A].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象征主义·意象派[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2.
[5]朱光潜.诗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55,55.
SYMBOL OF DEPRESSED LIFE——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Cao Zhi’s Later Poems
LIU Wei-an
(School of Humanities,Zhaotong University,Zhaotong Yunnan 657000)
In Cao Zhi’s later life,he was troubled by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at least:being alienated because of slanderous talk,the danger of life,wandering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ideal that could not be achieved,and feeling the heavy depression of life.All of those we talked about above influenced his poetry creation in his later-period deeply,making many things under his pen had a strong subjective color.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Cao Zhi’s tragic life situation and depressed life experience comprehensively,it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for us to pay attention to some poems which poured out his feeling straightly.Perhaps many of his late-period poems,such as poems of chanting things,poems of depressing things and poems of tourism,are the best researching objects.In terms of the essence,Cao Zhi’s late-period poems are symbol of li
Cao Zhi;late-period poems;depressed life;symbol
1206.2
A
1672-2868(2015)04-0081-06
2015-06-15
刘伟安(1970-),男,湖南安化人。昭通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陈澍斌
——关于文学游仙的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