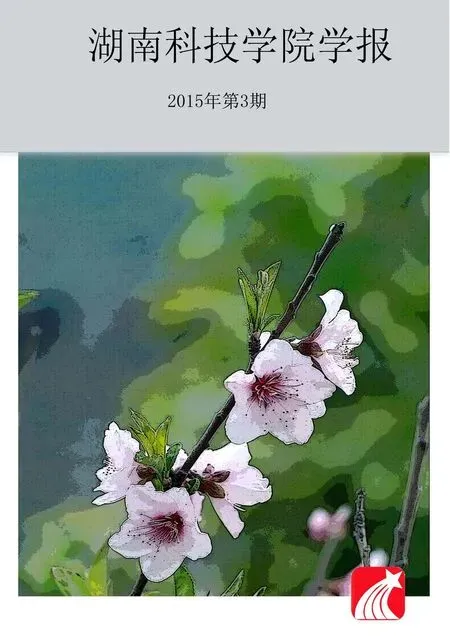晁跋本《花间集》源流递变考述
李博昊
(吉林大学 珠海学院 中文系,广东 珠海 519041)
晁跋本《花间集》源流递变考述
李博昊
(吉林大学 珠海学院 中文系,广东 珠海 519041)
《花间集》编纂于五代时期,其一成书即有可能刊刻。至南宋,晁恭道以之为“正而复刊”的底本。蒙元时期,《花间集》诸本皆失。到明代,杨慎于昭觉寺偶见之,《花间集》乃重新流传,而杨慎所见版本,极有可能为晁本。
《花间集》;晁跋本;宋词
《花间集》今存两个南宋本。其一是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在建康刊印的晁谦之跋本,此为最早版本;其二是用南宋淳熙十一、十二年(1184、1185)的鄂州册子纸刻印的鄂本,此本具体刊刻时间学界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晚于晁 跋本。南宋另有一个开禧本,即陆游跋本,但原本已经不见。到了元代,《花间集》极有可能失传。目前不仅没有发现元本《花间集》,公私著录中亦未见任何关于元本的记载。至明,《花间集》开始被重新刊刻,其中,多以晁跋本为底本,其首传而为正德年间陆元大的覆锲本,即正德覆晁本。这是目前明代最早的版本,写校和印刻都比较谨严,校正晁本错刻约三十处。另将《竹枝》、《杨柳枝》这类极易两首混为一首的七言四句体的词,分别加以“其二”、“其三”等标识。正因如此,覆晁本很多时候被去掉后末页“正德辛巳吴郡陆元大宋本重刻”字样,充当宋本。[1]P211-212以晁本为底本的正德覆晁本流传十分广泛,明万历庚辰(1580)茅一桢刊本(茅本)即以其为底本。从茅本而出的又有万历壬寅(1608)玄览斋巾箱本(玄本),万历年间师古斋吴勉学刻本(吴本),天启甲子(1624)钟人杰刊本(钟本)及明末雪艳庭活字本(雪本)。相比之下,另外两个宋本显得默默无闻。明代未见版本从鄂本出。陆跋本据说是明汲古阁毛晋本即《词苑英华》本的底本。有毛晋跋云:“余家藏宋椠,前有欧阳炯序,后有陆务观跋,真完璧也。”考陆氏二跋,亦载《渭南文集》卷三〇,其一题开禧元年十二月,并不言曾刻是集。因此言毛氏重刻本乃依陆务观的开禧本,恐无据。[2]P333明万历汤显祖的《花间集》评本亦似从陆跋本而出,但“顺移序次,别厘为四卷,率加圈点甚至勒帛,又多着眉批,辄作肤泛之语,如读时文制义,绝少精思,每卷末均附音释,虽习见之字亦然……可征其陋。并有序跋不详所自出”[3]。从文字上看,其接近鄂本,但某些鄂本误而晁本正的地方,又多从晁本,和毛本又大有区别。汤评本是一个接近鄂本而又比较独立的本子,从版本、卷帙、序跋、目次等方面,都无法测定其来历。[1]P217此外,明代未见其他刊本以陆跋本为底本。因此,晁跋本不仅是最早的《花间集》版本,也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
一
既然《花间集》已于元代失传,其又如何现于明代?明人杨慎《词品》卷二毛文锡条言,“《花间集》……久不传。正德初,予得之于昭觉僧寺,乃孟氏宣华宫故址也。后传刻于南方”。明代杨慎在昭觉寺发现了失传于元代的《花间集》,使之重新流传。此说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汤显祖评本序言“《花间集》久失其传,正德初,杨用修游昭觉寺,故孟氏宣华宫旧址,始得其本,行于南方”。清徐氏丛书覆正德本徐干序言“赵宏基辑《花间集》盛行宋代。降及元、明,寖以失传。杨用修游昭觉寺,始得其本。汤临川又评隲之。《花间集》始复显于世”。明正德覆晁本罗振玉题识言“此集杨用修游蜀昭觉寺,始得其本”。
杨慎所见《花间集》,或为宋本中的晁跋本。不仅因为明代诸本多从其出,且因其各个特点同杨慎《词品》的表述相符。正德覆晁本为正德辛巳年(1521)刊刻。正德为明武宗朱厚燳年号,时间起讫为公元1506-1521年,而杨慎发现《花间集》乃正德初年,陆元大得到杨慎所发现的《花间集》之后,又对其进行了编排校正,此可解释《花间集》从发现到刊刻过程中的时间间隔。陆元大的“吴郡”同杨慎所说的“刻于南方”亦相吻合。杨慎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虽不能见到万历茅本及其后诸本,但可以看到覆晁本在南方的刊刻和流行。如此,杨慎于昭觉寺所发现的《花间集》极有可能是晁跋本,经陆元大覆刻后广为流传。
《花间集》为五代时所编选,而其现存的最早刻本却是南宋晁跋本,在晁跋本之前,是否还有其他版本存在?据现有材料,当曾经存在。
双照楼覆正德本吴昌绶序言,“谦之字恭道,乃无咎从弟,敷文阁直学士,知建康府。跋称‘建康旧有本’、‘是正复刊’,盖其守郡时也”。晁谦之是晁氏家族中较有名望的一位,登进士第,绍兴七年(1137)曾编次其从兄晁补之《鸡肋集》七十卷,刊于建阳。绍兴十五年(1145)知建康府,《建康志》记“(绍兴十五年)四月十一日,敷文阁直学士、右朝奉大夫晁谦之知府事。十八年五月初四日,谦之罢”[4]P15。绍兴本《花间集》的跋语乃谦之为建康府守郡时(1145-1148)所作。其言“建康旧有本”,表明在作跋语之前,建康已经有《花间集》出现。晁又言“比得往年卷例,犹载郡将、监、司,僚幕之行,有《六朝实录》与《花间集》之赆。”可知《花间集》还曾与《六朝实录》一起,作为送给建康卸任官员的礼物。建康这样的大郡有批量储藏、赠送、消耗、自行刻印的情况,那么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临安、嘉兴、建阳、绍兴、成都、隆兴、福州、泉州等南宋大郡,应该都有这样的藏、赠、刻的情况。[5]P168《花间集》随卸任的官员的流动而散向各地,亦可能因为抄写、刊刻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版本。晁氏又言“又他处本皆讹舛,乃是正而复刊,聊以存旧事云”,进一步证明《花间集》当时曾有多个版本,而晁谦之认为这些版本多讹舛,于是以一部不讹舛的《花间集》为底本,审定且重新刊行。这个不讹舛的《花间集》当是时间上相对接近编选时间的版本,这个版本的时间可以上推至五代,五代蜀及赵崇祚具备刊刻《花间集》的诸多条件,而杨慎发现《花间集》之地亦是蜀宫旧址。
二
蜀有编书的风气。《十国春秋》记“王衍颇知学问,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丽之辞,唱尝集艳体诗二百篇,号曰《烟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传诵焉”。《直斋书录解题》言:“《烟花集》五卷乃王衍所编,蜀后主王衍集艳诗二百篇,且为之序。”前蜀王仁裕曾编《国风总类》五十卷、王承范编《备遗掇英》二十卷,后蜀韦縠曾编纂流传较广的《才调集》。蜀中富庶,扬一益二即是证明,其有刻书的财力,所以蜀编书亦刻书。蜀地出产的质量上乘的益州麻纸,是蜀地印刷业发展的基础。五代蜀刻书除民间私刻外,政府复出版大批课本,刻书地区比唐代的范围扩大了。四川在唐末已有很多书坊,为出版业的中心在唐朝灭亡后的第二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赁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年内雕成四百六十余板,藏在龙兴观,印造流行前蜀乾德五年(923),蜀国昙域和尚检寻师父贯休的诗稿曰一千首,“雕刻板部”,题号《禅月集》。[6]P64-65
清人王明清《挥麈余话》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至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此事明焦竑《笔乘》续四亦有记载,“蜀相毋公……显于蜀……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毋昭裔“初在蜀雕印之日,众多嗤笑。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嗤笑者往往从而假贷焉”。刻书赚利,众人纷纷仿效,蜀地刻书业得到蓬勃发展。此后逢“艺祖好书,命使尽取蜀文籍诸印本归阙……是时其书遍于海内”。宋开国以后,太祖即派人到成都监刻大藏经,表明蜀地刻书品质的上乘。如此,五代时期《花间集》或已刊刻。尤袤《遂初堂书目》言有“唐花间集”,似可为佐证。
编纂《花间集》的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有刊刻《花间集》的能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崇祚字宏基,事孟昶为卫尉少卿,而不详其里贯。《十国春秋》亦无传。案蜀有赵崇韬,为中书令廷隐之子。崇祚疑即其兄弟行也。”《十国春秋》虽未记载赵崇祚乃中书令赵廷隐之子,但《九国志》赵庭隐条下明确记载“子崇祚、崇韬”。赵崇祚后蜀明德四年冬曾与林罕讨论林氏的《说文》学著作《林氏字源编小说》,《全唐文》卷八八九载有林氏自序,略云:“至明德二年乙未复病,迄于丁酉冬不瘳,病中无事,得遂前志,与大理少卿赵崇祚讨论,成一家之书。”此书撰成不久即刻石蜀中,颁示学界,可能和赵崇祚的参与及推荐有关。宋马永易《实宾录》载,“五代后蜀赵崇祚,以门第为列卿而俭素好士。大理少卿刘嵩、国子司业王昭图,年德素长,时号宿儒。崇祚友人,为忘年友”[7]P69。崇祚父庭隐为后蜀开国重臣,备受蜀主重视,《九国志》记其“久居大镇,积金帛巨万,穷极奢侈,不为制限,营构台榭,役徒日数千计。十年被病,恳让兵柄,疏再上,从之。仍旧第册为宋王。经岁不能起,赐肩舆入朝。既谒见,昶感动涕泣,赐金沃盥及绘锦,加太师”。赵庭隐在后蜀的地位几次于王。2011年,赵庭隐墓在成都成功发掘,墓葬的规格很高,在上百件随葬品中,有10多个手执各种乐器的彩绘陶质伎乐俑。据考古人员介绍,这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最为精美的陶质伎乐俑的组合,胜于前蜀王建墓出土的伎乐俑,展示出墓主人生前作为达官显贵的乐舞生活。《花间集》编于后蜀广政三年,而赵庭隐薨于广政十一年冬十二月,广政三年正是其晚年生活安逸之时,家中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赵崇祚才能欣赏到“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才有能力“广会众宾,时延佳论”,“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并请当时的武德军节度判官司欧阳炯为之作序。《花间集》成书的广政三年亦是毋昭裔政治上较为平顺即将升为宰相的时期,他的刻书之业也在这个时候不断扩大。这样的条件下,赵崇祚编纂《花间集》后再行刊刻,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此,晁跋本《花间集》可能有着五代时的底本,蒙元时期,各本皆失,杨慎于昭觉寺偶见晁本,才使之重新流传。这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终未掩于纤尘,散发着玉石般的光泽。
[1]李一氓.花间集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饶宗颐.词集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赵尊岳.词集提要[J].词学季刊,1935,3(3).
[4]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2004.
[5]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6]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闵定庆.花间集论稿[M].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责任编校:王晚霞)
I212
A
1673-2219(2015)03-0043-02
2014-12-10
李博昊(1982-),吉林榆树人,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中文系讲师,澳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