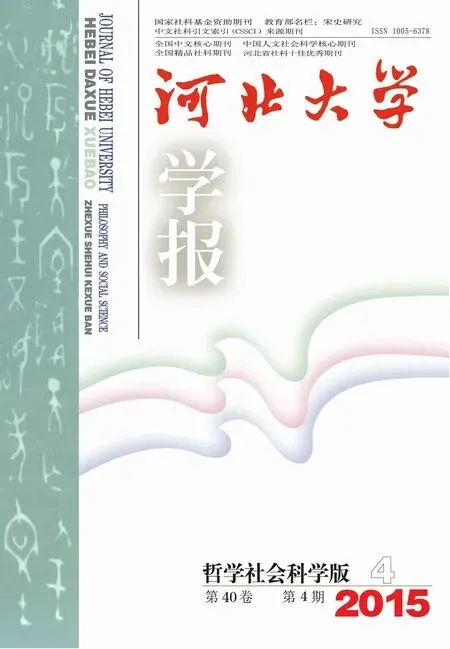社会公德的调控机制
郝艳梅
(河北师范大学 高师培训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一、内在羞耻心的约束
按照《圣经·创世纪》的说法,羞耻心与人类文明的内在关联,最早可以追溯到关于亚当和夏娃的传说。据说亚当和夏娃在食用了智慧之果后,懂得了善恶对于人类的意义,开始用橄榄树的叶子遮挡自己的私处,这既是人类认识羞耻心的开始,也表征人类文明进程的开端。由于羞耻心导致个人难堪的感受,进而从内心深处调节自己的言行,掩饰某种被认为不雅的动作或部位。在这里,言行中的“雅”或“不雅”之标准的确立,恐怕就是西方耻感文化的起点,也是人类道德调控机制确立的过程。
在公共生活中,人的羞耻心之所以能够发挥道德调控功能,主要原因在于,羞耻能够促进个人行为上的自我节制,即个人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不能够完全凭借自己的偏好或生理需求行事,而是参考或顾及他人和社会准则的要求,合理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社会联系日趋密切的当代社会中,个体羞耻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引导,逐渐成为社会文明的内在化要求和具体表现。大多数人认识到,在很多社会交往过程中,不是因为感到羞耻而节制,而是作为文明社会的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人文素养和道德要求。文明社会的公民,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超越了羞耻的底线要求。当然,个人行为中羞耻对个人欲望的节制,不过是实现健康的道德生活的手段,而不是行为的目的本身。但是,在自我节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不能排除羞耻心的内在约束力。羞耻首先是人之为人的条件,作为文明社会的主体来说,羞耻心是内在地发挥作用的。就此而言,以羞耻为基础的自我节制乃是伦理文化的重要范畴。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羞耻感都是个体的心理感受。作为道德心理文化的重要规范,羞耻主要调节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由于羞耻心的存在而感到脸红,说明道德会牵涉到个人“面子”上的难堪。实际上,人们的羞耻心的存在,往往与内在的道德人格相关联。这种内在关联主要是通过触动人的内在良知而实现的。因此,如果羞耻心能够引发个人的道德思考,从而监督个人加强自我修养,才能真正达到羞耻的价值目标。不过,在我国传统社会,耻感文化最初只适用于家庭生活,即使有人感到在“外人”面前做了不道德的事,并且因而丢了“面子”,它所考虑的首先也是对家族的负面影响,家族利益和家族荣誉为此而受到的损失,而不是首先考虑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林语堂曾说过,家庭是一座壁垒。对个人来说,家庭之外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1]86。对家庭生活而言的知耻,未必就是对社会大众的知耻。在这种情况下,欲在公共生活中利用耻感调节行为,就必须实现耻感文化的现代转换——由私德传统转向现代社会公德。
二、制度性的惩戒措施
承认耻感文化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调控,必须以个人对羞耻心的敏感性为前提。由于人的心理因素是偶然的、暂时的和不确定的,因此,维护公共秩序不能完全依赖偶然的心理引导。况且单纯依靠耻感文化,也无法培养个体的公德心,使全社会形成完善成熟的公德意识。应当说,社会公德制度化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当代社会,随着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对制度的关注和研究才逐渐步入正规。有学者提出的“制度伦理”或者“伦理制度”概念,就是把人类的道德行为纳入相应的制度安排的重要尝试。简单来说,“制度化”就是具体化与可操作化,它需要明确分析行为发生的境遇,采取细则化的方法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详细对策。
为了使人们更好地遵守社会公德规范和各种规章制度,需要在充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掌握客观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公正而合理的社会公德制度或规则。惟有社会公德规范合理而科学,才有可能得到公众的理解、认同和认真遵守。
因此,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为了规范千差万别的个人行为,避免由此带来的各种纠纷和冲突,道德行为必须成为“规则化”“制度化”的行为,这本质上是社会有序发展以及维护个体利益的内在化要求。一旦规则被破坏,公共秩序就会走向混乱,每个人的利益都将会受到损失。公民社会注重个人权利,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和追求,但是,个人权利的来源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惟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成长,对公共生活尽义务是获得个人权利的基本前提。这应当成为个人的自觉理性。因此,在社会公德问题上,强调统一性是公共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进行公民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向人们指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协调角色冲突的方法——严格遵守社会公德的基本规则,它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道德本身属于柔性的力量,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与刚性的制度措施相结合,才能够发挥调节行为的作用。
三、公共舆论的外在监督
对社会公德而言,舆论监督是一种他律的方式,即以外在约束和行为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发挥舆论监督对行为的影响力。由于舆论监督不针对具体的个人,而是主要针对某一类的典型或普遍现象,所以难以从根本上触动行为者。然而,受到各种不良行为危害的,往往是行为者身边的每一位公民。惟有这些公民及时进行必要的舆论谴责,或者对不道德行为进行坚决抵制,才是矫正不良行为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对生活中的各种不道德行为,公民有监督和举报的义务,谴责和制止各种不道德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乃是全体公民的道德责任。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曾说过,在面对邪恶势力和社会犯罪时,如果目击者对他们行为的厌恶与义愤变成大声的抗议或积极的抵抗,那么,做恶者(真正的罪犯)还会进行邪恶的行为吗?[2]216对于缺德者来说,公民监督能够造成“道德压力”,督促其改变不良的行为方式,或者暂时收敛自己的某些行为,降低不道德行为的社会危害。我们过去形成了“不管闲事”的传统,总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面对侵害公共利益、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喜欢做旁观者或者假装没看见,这是缺乏起码的公民意识、推卸公共道德责任的表现。对于此类现象的发生,公共舆论也应当发挥自己的监督职能,引导公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舆论监督不是限制个人行动自由,而是将个人对自由的理解导入正途,并培养公民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旧的行为习惯的改变,乃是通过新的习惯的培养来实现的。
舆论监督能否发挥其道德效能,关键在于能否真正触动人的良知,引起“灵魂深处的道德革命”。观察得知,目前人们的规则意识依然淡漠,并且在别人提出批评意见时,还振振有词地说“少管闲事”。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个人若有一次乘车逃票的记录,就是人生永恒的“道德污点”,将永远无法抹掉。这种信用记录被归入档案,警醒人们在道德上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从而强化了人们的道德自觉。借鉴西方社会公德建设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公共舆论监督必须与制度约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此外,经验也表明,舆论谴责要发挥作用,还必须触及其根本利益。惟有使个人利益受到某种损失,才能引发理性思考和反思行为,今后类似的违规现象才可能减少。当然,公共规则或制度需要严格的执行者。在一般公共生活中,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则提示,甚至没有专门的规则管理机关,导致人们遵守规则的效果不明显。只有那些有专人管理和监督的场所,当面指出行为者所犯的错误,甚至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的时候,行为者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实,规则管理即意味着人的管理,同样体现着人类的尊严和权利。既然规则是人们为自己制定的,代表着“众意”——一种普遍性的要求,那么,规则也就是人的尊严和权威的体现。不尊重规则就是对“众意”的背离和亵渎。
四、习俗道德权威的引领
所谓习俗道德权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使人们崇敬并信奉的某种力量。通常习俗道德权威有不同的类型,它可以是某个具体的人,如学术专家、道德楷模、领袖人物等,也可以是某种外在于人类生活的信仰对象,如上帝、神灵等。不同类型的权威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不同的意义,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在公共生活领域,道德权威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不是依靠简单的命令或者内心的良知,而是榜样的示范性和公众的模仿性。道德权威往往以道德人格的力量发挥作用,它有助于约束和整合个人行为,促使人们消解差异、排除纠纷,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和统一性。
习俗道德权威寄托着某种文化传承的现实需要。权威不是自己生成的东西,而是某种外在命令“内在化”的结果——总是需要有一些特殊人物(或精神因素)引领道德生活的进步。当社会的公德规范转化为个体行为要求时,就成为个人的道德信念。所以,信念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扎下根的道德原则,是被个人内在化了的道德诉求。我国近代伦理学家黄建中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是政治伦理。“圣哲在位,以身作则,而民皆化之;其政治重在养成道德人格,纠正不道德之行为。”[13]84政治作为公共生活领域,其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官德。官德支撑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对民众的道德生活具有权威性的意义。所以,官德历来为各个王朝所重视。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实施“德治”的基本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官员的道德示范作用对整个社会加以引导。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看到,君主的道德表率作用引人注目,能够成为全体人民仿效的榜样。
我国现阶段,在推进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手段,社会公德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公众的社会公德意识相对滞后,混乱的公共生活秩序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为此,必须深入探索社会公德建设的新思路、新途径。由于社会上层人士、道德楷模或领袖人物的公德素养,不仅是衡量整个社会公德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同时也可以作为提升全民社会公德建设的有效途径。作为习俗性的道德权威,他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带头实践社会公德原则和规范,捍卫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以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德水准,为社会主义道德现代化服务。因此,充分发挥公众人物尤其是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公共生活中引领广大群众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规范,模范践履社会公德义务,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黄建中.比较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