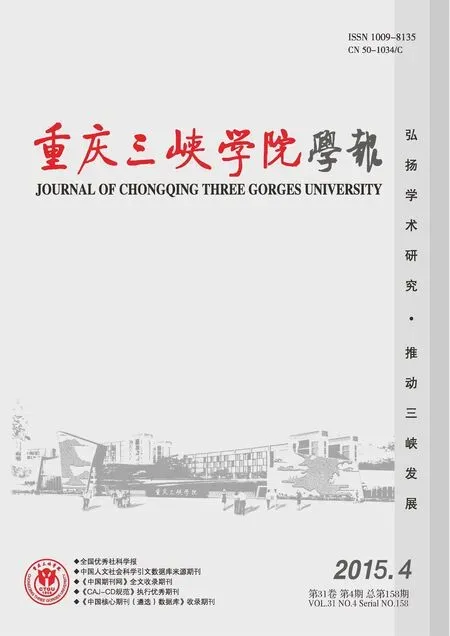身体的言说:丁玲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再解读——以《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车凯旋
身体的言说:丁玲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再解读——以《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车凯旋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丁玲的作品《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创作于1920年代,阿英是一个通过赤裸裸的世俗追求来体现女性自主意识的形象,《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于1940年代,讲述抗战时期的贞贞在女性与革命话语之间做出的选择。两部短篇小说都是以妓女为主体从而对自身身体进行言说的短篇小说,尽管这两篇文章分别写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里,但是将两部放在一起来解读,它们都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张扬背后的男性构建的权利话语以及女性的艰难处境,这也是丁玲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困惑所在。
丁玲;女性;主体意识;身体
五四以来,在描写女性形象尤其是妓女形象时,男作家由于性别原因总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讲述,他们要么以启蒙者的姿态来俯视这群弱势女性,着力描写她们的苦难与卑微的地位,要么将女性作为欲望化的客体符号,从而寻求他们的利益所在,不管是以哪种姿态写作,在男作家的笔下女性总是置于男权文化的笼罩之下,并且总是处于“失声”状态。而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女作家,她从始至终都在关注女性,关注她们真实的内心世界以及生活状态,从而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关于妓女形象的描写,丁玲更多地深入到妓女的内心世界中去,通过女性自身身体的言说打破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坚固堡垒,使女性与男性地位平等,重拾女性的话语权。
关于妓女形象,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在《第二性》中将妓女分为妓女和高级妓女。她认为“从低级妓女到高级妓女,有很多等级,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以女人纯粹的一般性来做交易,结果竞争使她处于悲惨的生活水平,而后者竭力让自己的特殊性得到承认:如果她成功了,她就能期待更高贵的命运。”[1]408在笔者看来,波伏娃的妓女就是指那些被迫失去贞操或者迫于生活压力的低级妓女,而高级妓女往往包括上层社会的舞女以及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军妓。丁玲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和《我在霞村的时候》都是从妓女的视角切入来讲述女性的心理变化以及最后做出的选择,前者表现的是普通妓女在一天内通过内心活动的斗争来作出去留的自主选择,后者是讲述从被迫成为慰安妇到自主地选择作为光荣象征的军妓的故事。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两篇小说都是描写女性最初的被迫到最后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不再作为男性话语的附庸,而是作为发声的主体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出路,丁玲描写这两篇文章旨在从女性身体言说的角度出发来反抗男性的权威地位,从而张扬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也许是大多数读者的观点都与此相似,但是笔者通过深度审读这两篇文本发现,丁玲的女性主体意识在当时是微弱的,她们的身体言说最终还是建立在男性权利话语之下的,这也是丁玲为女权主义一直奋斗不息却不时感到失落的原因所在。
一、性政治下的女性悲剧——以《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为例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是丁玲发表于1928年的一篇短篇小说,该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主要讲述的是普通妓女阿英在庆云里一天之内的生活体验以及心理欲求。男性在这篇小说里几乎是作为“抽象”的存在,丁玲并没有去正面描写男性的外貌以及行为活动,而是通过妓女阿英的心理活动得以展现,这些男性大都没有名字(除了陈老三,但并非全称),而且只是作为性与金钱的工具。在这里男性成为女性需要的执行者。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和《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中都隐含了对男性将女性作为需要的执行者的谴责。
作为女主人公的阿英对服侍过的嫖客进行了比较,她认为穿洋服的后生“人虽说干净,斯文,只是多么闷气啊!”[2]41而那穿黑大布长褂的瘦长男子“人是丑,但有铜钱呀,而且……阿英笑了。她把手放在自己胸上摸着,于是越觉得疲倦了。”[2]41显然,作为社会地位与文化象征的男性在丁玲这里遭到了女性的歧视,并且只是被看做金钱和性需要的符号。当阿英梦见自己以前的丈夫时,她由最初怕丈夫嫌弃自己而另有所爱的担忧到无所谓婚姻的坦荡,这种前后心理的变化无疑体现了阿英追求自由的物性生活的表达。“她为什么定要嫁人呢?吃饭穿衣她并不愁什么,一切都由阿姆负担了。说缺少一个丈夫,然而她并不虚过呀!而且这只有更觉得有趣的……”[2]44阿英不完全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她觉得既然陈老三满足不了她基本的物质生活享受,为何还要像其她女子一样苟活,阿英已经对婚姻、家庭彻底失望,她有追求自由生活的权利,即使是动物性的性欲望和物欲的崇拜。可以说,阿英不管是选择留在妓院还是嫁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内心愿望去做判断,不受传统伦理道德的限制,此时的她获得了一个主体的地位,也是一种不自觉地反叛。丁玲企图通过颠覆男权的形象来建立女性的话语权利,让女性自由的发声,她始终通过她的努力来实践着自己的行动。丁玲让男性“失语”,在法国女权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多娃那里被解释为“逆向的性别歧视”[3]10。
应该说,丁玲对女权主义的实践已然迈出了一大步,重视性别这一点说明了丁玲女性寻求独立解放的特殊性。但是仔细探究发现,丁玲在努力刻画阿英这一形象从而彰显女性主体意识时并没有将男性置于与女性平等的地位上,男性始终处于弱化的地位,美国女权主义学者玛丽•朴维曾在《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一文中用男女二元对立的理论来解说,她认为女权的本质只有在与男权的对话过程中才能得以确立,这种一味地压抑男性的行为其实正表明了女性在追求自主独立时不敢面对男性,不敢与之平等对话导致的尴尬局面。丁玲刻画的女主人阿英不过是追求物欲的女性,她并未真正地从精神上肯定自己的女性价值,从而实现自我的主体意识,她因追求理想的生活而逃避婚姻与家庭,殊不知庆云里这一妓院场所又是一个束缚女性的牢笼。阿姆是庆云里的主管,她负责这里妓女的一切日常生活,她代表着封建文化家族中的长者,阿英则是家族中一个听话乖巧的女儿,一切行事都要看阿姆的脸色,稍有忤逆都会受到阿姆的责骂与处罚。尽管她在与男性玩乐时是自由的,同阿姆的关系也不错,但她始终局限在受阿姆所困的圈子里。即使她在以后的某一天选择离开庆云里,结束妓女生活,但是到那个时候好的工作她不一定干得了,又脏又累的工作她又不一定愿意干,她已经惯于那样的生活了,走投无路的她也许会选择一个男人作为依靠,也许会孤苦无依,连乞丐的生活都不如,也许会随着新政策的变化生活会有所改变,但是一离开庆云里,她始终会受到周围人的冷眼旁观,这个大的男权社会集团是很难接受她的。我们已经看到阿英的悲剧也是所有处于同样位置的女性的悲剧,她们终究还是“第二性”。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强调的“把自我实现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方面,她仍会面临比年轻男人更多的困难,如我指明的家庭和社会习俗都不会赞成她在这方面做出努力。”[1]264
二、革命与贞操选择下的困境——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去延安之后写的又一部有关妓女的短篇小说,那时她已投身于火热的民族革命的洪流中。这篇小说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十八岁少女贞贞因反抗封建婚姻而被迫作为“慰安妇”,后又作为替我方传递情报的军妓的故事。这个故事由贞贞的失身与献身两部分组成,贞贞最后置霞村人的言论于不顾,毅然决然地献身给国家革命的伟大事业[4]。这是贞贞自己做出的选择,她选择抛弃夏大宝这一男性个体,希望在为民族战争的“献身”中找到自身的价值,“我想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2]162贞贞在革命与贞操之间选择了前者,在这里,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丁玲所刻画的贞贞这一形象明显表达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那么笔者不免提出疑问,贞贞到了延安之后就能获得更好的出路吗?以自我贞操的付出为代价所获得的回报是什么,是国家法律道德的重新认可,还是需要女性自身默默地承受不幸?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女性除了受阶级与种族的压迫外,女性自己本身就是同谋,她在下卷中引用让保罗•萨特的话,“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像所有人一样。”[1]1《我在霞村的时候》整篇文章都充斥着霞村人对贞贞的议论,尤其是那些村妇们对贞贞的鄙视,认为贞贞连破鞋都不如,她们不但没有站在同是弱势群体的角度同情贞贞,反而庸俗麻木,将窥探与嘲笑视为无聊的谈资,丁玲的女性解放启蒙运动在这里显得无比微弱。霞村人的歧视使贞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叙述者“我”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歌颂贞贞的奉献精神,在革命面前,女性的失贞算不了什么,在全民抗战的特殊时局,这种大义凛然的举动在革命话语之下遮蔽了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主义被充斥在以男性为代表的国家民族主体身份里。国家在这时更看重的是女性身体抗日的积极意义,但是并没有给与女性相应的法律以及道德上的保护,女性身体失贞所做出的贡献在国家那里并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承认,女性的牺牲在革命的合理性面前应该受到深深的质疑。当民族革命结束之后,国家是否还会重视这一批特殊的人群,或许国家太平后,这些“军妓”又会被抛弃在主流话语的边缘,不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或许还有可能恢复到以前遭众人嫌弃的处境,那时候贞贞又该何去何从?
英国女权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在《父权制、亲属关系与作为交换物品的妇女》中提到,“承认区别在个人程度上也是绝对必要的”[3]435。她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认为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总是将女人作为男人交际中的示意符号。《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反映的其实仍是女性的自身利益(包括贞操问题)和民族革命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体制在女性解放上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完善,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这种体制运行背后的男权文化以及男性对女性性别的漠视。
三、总 结
每一种文学现象浮出水面都与它的社会政治以及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丁玲所宣称的女性主体意识并非空穴来风,它不仅受到世界上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而且是中国社会时局发展变化的结果,是新时期女性作家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参与文化建构的反映。
一直以来,社会的主流话语都是由男性主宰,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也可以与男性处于平等的地位,她们通过“女性口吻”、“身体写作”来作为对抗男性的武器,将男性置于符号化(或丑化、或抽象化)之下。在这一领域女权主义者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她们不免也在实践中遇到一些问题,最终发现有意的弱化男性其实本身也说明了女性的处境,女性所宣扬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她们发现话语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他们掌握着制定体制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的大权。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玛丽•雅各布斯曾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么,对于语言,是否可以这样评论:是语词在说我们,而不是我们在说语词?”[3]17女性主义者不免又陷入了某种困境。
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登上文坛,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她从一开始就以女性的视角来观照她的人物,关注女性身体的书写与内心世界的言说,丁玲在前期塑造了莎菲、阿英等形象来寻求女性的生存价值,确立女性意识的主体性。30年代后期,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向左翼文学转换,丁玲到达延安之后投入到民族革命当中去,她的小说中女性意识明显减弱,女性的话语隐藏在民族革命话语之中。女性意识是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折射,是女性自我生存状态的自我窥探。丁玲试图颠覆男权文化的中心来理性地考虑两性的关系,以求得女性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与男性的平等地位。但是在与政治话语相结合下[5],丁玲更多地倾向于国家话语,她并不是对女性的关注减弱,而是表现出某种暧昧的话语立场,我们瞥见的是她游曳于两种话语立场之间,想要化解这种困境却又暴露了矛盾之下的焦虑。晚年的丁玲尽管多次受到政治迫害,但还是坚持似乎很微弱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解放事业。她的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作品也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丁玲的创作发展变化以及她内心矛盾困苦的心境[6],在男权社会并未消退的情况下女性的生存处境还是比较艰难的,丁玲的女权主义道路的探索为后来的女性作家开辟了道路,只要女性争取权利的信心一天不灭,那么女性解放的道路也会更加靠近一步。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丁玲.丁玲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吴佳楠.女性的伟大与悲哀——《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形象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
[5]游文慧.艺术的艰难突围与政治意识的无奈选择——丁玲《夜》的再解读[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2).
[6]吴建萍.从丁玲《在医院中时》看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成长[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责任编辑:郑宗荣)
Narration of the Body: Revisiting Woman’s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Ding L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and
CHE Kaix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Ding Ling’s work, written in1920s, depicts a character A’ying who gives play to the woman’s subject consciousness by naked worldly pursuits; the work, written in 1940s, is about a girl Zhenzhen who makes a choice between female and revolutionary words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Both short stories are centered on prostitutes who make narration on their bodies. Though they are written in different political situations, if interpreted together, they both demonstrate male’s construction of power words an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women behind the unreserved displaying of woman’s subject consciousness, which is also the confusion Ding Ling had felt in her writing process.
Ding Ling; women; subject consciousness; body
I206.6
A
1009-8135(2015)04-0056-04
2015-02-16
车凯旋(1989-),女,山西吕梁人,重庆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