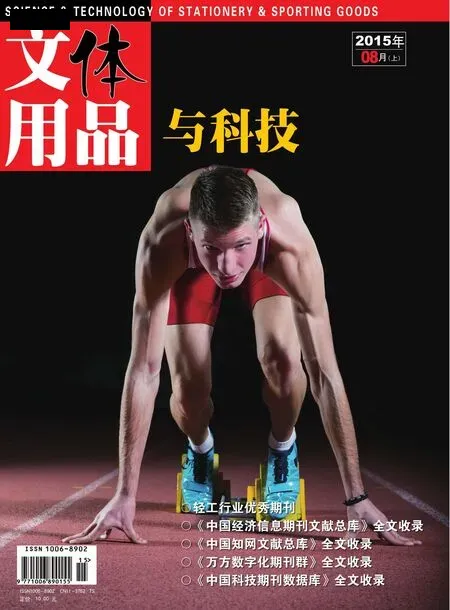论民族传统体育的内生式发展
颜下里(四川省内江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12)
论民族传统体育的内生式发展
颜下里(四川省内江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12)
作为决定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结果关键性变量的民众参与,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话题。从经济上吸引,从政治上教育,但并未能使民众从旁观而实际参与。实践表明,村民自治的实施才为村民参与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保证: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表达自己的体育要求和愿望,从而对于体育活动有了一定积极性。但是村民自治下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中群众的主体地位的实现,应当是建立在对自身体育权利认识基础上的一种自觉。
民族传统体育 内生式发展 体育基础 参与主体 环境因素
1、前言
“内源性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也译作“内生式发展”,是上一世纪70年代产生于国外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由“发展”和“内源性”两个部分组成,前者是理论的第一要义,是其根本任务,后者是实现前者的原则、方式和要求,体现为基本动力、资源和环境制约因素。现在,内源性发展项目已成为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援助的重要选项之一。
近30年来,在政府、企业、知识分子精英、媒体、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动力的推动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发展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社会动力基本上都是采取“外推式”、“干预式”的参与方式来推动发展的,因而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外生变量。在推动传统体育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外生变量从其各自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目标决定着包括民族传统体育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方式、方向与进程。而作为最重要、最关键主体的民众,却处于旁观者的地位,并未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以致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推动力的外生变量的推动,不能总是同民众的体育需求在目标上保持完全一致,不能提供符合体育发展切实需要的条件,在其推动下传统体育呈现出负性发展的结果。为此,要使包括民族传统体育在内的传统文化得到正常发展,必须对保护和发展理论进行认真反思,必须在新的理论指导下从新的视角对实践形式进行指导;应当有效动员民众充分参与发展事务,以消除制约传统文化发展的不良因素。在此情况下,人们自然转向新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方式的探索。
2、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的体育基础
2.1、作为发展的基础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根本属性,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性决定着传统体育的基本面貌,决定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构建。在民族传统体育各种特性中,它是首要的、主导的,是基本性质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这是因为任何时代的体育实践和观念都不可能与历史断裂,不可能抛弃先人的劳动成果,无视漫长岁月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认知财富。正因为这样,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性为其未来的发展有着极大的铸造和制约作用。不管一种体育形态的继承者主观意愿如何,他们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抛弃民族传统体育。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之为起点,都有意或无意地从中吸取养料,并且只能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变革的实际出发,在已有认识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和创新。这里还有必要说明,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形态和观念形态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二者总是在其适应自身存在的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历史证明,民族传统体育总是随着导致其产生、形成、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代,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条件的变化、文化观念的更新,都使得传统体育中某些成份因实用性的丧失而逐渐淡出生活以至衰亡,成为历史;而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新的因素,因能满足同时代人的体育需要在经选择、整合后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并经传承而成正统,得以存留下来,成为新时代的具有现代性质的体育传统。民族传统体育就是这样与时代保持着直接的联系而不断获得自己的时代特征。
2.2、作为存在的标识
在古代,民族之间,国别之间,虽然体育接触和交流一直不曾间断,但是,任何—种体育形式都只存在于一个局部范围之内,因此,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体育只能说是由一些相对独立的体育单元构成的。
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伴随世界性经济的出现,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也摆脱了民族和国家疆界的限制,朝着世界性方向发展。体育也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世界性整体发展的历程。
在此背景下,体育也便成为一个区别民族的标识性特征之一。这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体育自觉,它使得以传统体育作为发展基础的思维的产生有了时代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3、脱离传统的发展代价
脱离传统必然付出代价。1883年日本的西化风中鹿鸣馆高调登场亮相。鹿鸣馆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在东京建成的一所类似于沙龙的会馆,是供改革西化后的达官贵人们聚会的地方,来客多是推动日本近代化的头面人物。在他们的努力和影响下,日本上层社会吃西餐、穿西服、留分头、跳交谊舞、玩西式游戏、盖洋楼等西化风潮风靡一时,鹿鸣馆成了日本近代西化主义的象征。但是这种脱离了传统文化的形式上的模仿,并未能在日本立足生根。在人们眼里,鹿鸣馆只是在“东施效颦”,是一场“公开的大闹剧”,因而最终销声匿迹。
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传统基础上重建新的传统体育,都必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任务。
3、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的参与主体
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源性发展,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如民众、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企业等社会力量。他(它)们所处社会位置不同、充当的角色有异、具有不同行为逻辑。他(它)们的参与直接关涉到传统体育的发展方向与结果。
作为决定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结果关键性变量的民众参与,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话题。从经济上吸引,从政治上教育,但并未能使民众从旁观而实际参与。实践表明,村民自治的实施才为村民参与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保证: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表达自己的体育要求和愿望,从而对于体育活动有了一定积极性。但是村民自治下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中群众的主体地位的实现,应当是建立在对自身政治-体育权利认识基础上的自觉的、主动的参与过程,而当前村民的参与还多半仅仅是以兴趣的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
虽然中央及省部一级政府所制定体育政策法规都必然关涉到传统体育,而事实上与民族传统体育关系最为密切的却是乡政府。乡政府作出具体的体育计划,并进行活动的组织和统筹。在村民自治前,乡、村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政府对于村的体育事务的介人是以权力为依托,具有某种强制性质。我国的村民自治自1987年开始试行推广以来,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村民自治在中国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因而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不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村民自治主体的民众参与方式、程度、目的,乡政府与村委会体育新型关系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在市县普遍对乡镇建立了严格的问责机制和政绩考核制度,特别是“一票否决”的硬性规定迫使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的情况下(如前所述体育计划,具体体育活动的组织和统筹),乡政府对于村民族传统体育的扶持、指导工作仍然存在着极大的研究空间。
专家学者是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的有力推手,因为他们具有该领域活动的相关知识。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便是由学有相关知识的知识分子所推动,整个内源性发展程序都有其参与设计并实施。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并未涉及旅游开发一类事项,因而企业与传统体育的内源性发展无甚关联,但来自高校的志愿者既帮助了体育发展工作,又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锻炼。志愿者活动值得提倡。
4、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的环境因素
就民族传统体育而言,环境是由对体育有着巨大影响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构成。如同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上也没有两个环境完全相同的村落,因而在任何具体环境中形成的体育也各具特点,基于这,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源性发展,必然是以体育适应其关涉的内在环境要素的变化为内容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环境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性巨变,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的对传统体育的弃用、承续和创新的过程,是此后数十年间的基本内容。在新的环境条件下,这一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于传统体育的扬弃。
例如西昌传统体育的扬弃表现为:传统民俗活动至今保留了大量传统体育内容,如赛马、摔跤、爬油杆等。而同时,跳牛、棕球、月亮棋、老虎抢蛋、杠术等简单易行的项目,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而较之过去的传统项目更富有时代气息的项目和活动,如斯诺克台球、象棋、旅游、交谊舞、麻将等,则进入了新的体育结构,甚至连洋节也加入进来。
这种传统体育的扬弃是其实践主体按照自身的体育理念,通过接触、吸纳、转换等方式,选择性地将异质体育内容或要素纳入本民族的体育之中,并形成新的民族传统体育结构、机制和功能,以适应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主体需求,从而使本民族的传统体育在持续的体育建构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这一过程中,从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角度着眼,课题组正视一些项目因与当前社会存在巨大的时代落差,缺乏同现实生活的相容性而淡出体育舞台现象;对于新进入的内容,也并不是一味地加以贬斥,而是从体育发展角度加以审慎选择。但是,人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总是受时代的科技、生产、生存状况等条件制约,一个人在自己时代就某一问题作出与未来相关的决定时,容易误判,而误判导致的误行,对于传统体育来说,经常都无法补救。因此在项目退出之前,必须采用静态保护方法将其保存下来,以留待今后可能之用;对融入的体育内容,不仅对其存在价值需要做认真研究,更要参照其在其他民族地区、在汉地,以及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存在状况,加以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民族村落传统体育的现代建构要比单纯关注其衰退消亡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难度也要大得多。
5、结论
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的研究对象是体育发展的内生变量,这反映出研究重心在由过去外在因素向内在因素的转换,这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观念的一次质的转变,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虽然如此,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在学术领域呈现的这些优势,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完全排除外生变量的配合去单打独斗,更不能认为,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当代发展进程中,内源性发展就一定较外源性发展更为优越。正确的认识和做法应当是:内源性发展与外源性发展应当是互为补充、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在立足内生变量的前提下,必须同时借助正能量的外在力量的辅助,借以在此基础上形成超越单一内源性发展或单一外源性发展的推动合力。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深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内生变量的地位和作用,将是未来内源性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体育领域,应将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内容,进行知识启蒙和普及;应将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的理念和思维贯穿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政策制定合理制度设计的工作中。
而且,由于内源性发展本身并非一种单学科理论,而是一个关涉了文化学、社会学、环境学、生态学、民俗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等跨学科的学术问题,这些学科学者的参与将从各自领域对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进行积极的、有意义的拓展和诠释,从而不断丰富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政府、民族传统体育学界应将吸引各门相邻学科学者参与内源性发展研究作为完善该领域建设的必要举措。
[1]颜下里.也论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性质[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人民出版社,1972:67.
[3]张余胜.县乡政权和村民自治[M].兰州市: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102.
[4]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J].新华文摘,2005,(11):263.
[5]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2010.23:115.
[6]马晓京.民众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再认识[A].民众政策研究文丛第三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492.
[7]罗曲.凉山彝族传统民间歌舞[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0).